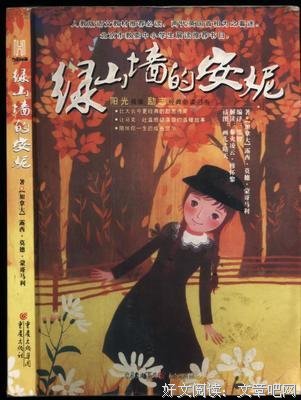
《第一堂课》是一本由巫鸿著作,湖南美术出版社出版的平装图书,本书定价:98,页数:2020-5,特精心从网络上整理的一些读者的读后感,希望对大家能有帮助。
本书是巫鸿先生在哈佛与芝大教授中国美术史课程的讲稿的集结,在每次课程的第一堂课,巫鸿都会介绍课程的研究内容,研究方法,以及课程课程开设的思考。
书中涉及的课程讲稿包括90年代之前的3篇,90年代的8篇,2000-2010年5篇,2010年以来8篇。 相较巫鸿的学术著作本书可能显得过于概略,但这些课程的议题大致勾勒出巫鸿在不同时期学术研究的面向,同时也折射出中国美术史学科在这30年间(1987−2018)年间所面对不同的问题,以及形成的新的研究路径和方法。
近年来对学者课堂的关注无疑是一个值得关注的话题,比如葛兆光先生曾出过《思想史课堂讲录》及续编等,与葛兆光的精讲课程不同,巫鸿老师的第一课堂在努力的保持着课堂的新鲜感,也同时提出了一些值得深思的问题,这是本书所谓方法、视角上下编的最大价值。
在此值得反思的问题是,作为一名视野极为开阔的美术史学者,巫鸿在古代中国美术史与中国当代艺术研究领域皆有深入研究,而本书却未能展现巫鸿在第一堂课教学中更多的提及中国当代艺术。其中的原因可能有编者选择的倾向,也可能与课程面向西方听众的接受有关。而巫鸿在第七讲,作为通识课的中国书画,谈到传统绘画的笔墨问题,实在感觉过于简略。这恰恰提示了作为美国高校课堂的美术史的欠缺之处,也提醒我,尊重巫鸿先生的同时也要指出和发现其局限所在,在学术研究中迷信偶像是万万要不得的。
《第一堂课》读后感(二):艺术爱好者和美术史学人都值得一读的《第一堂课》
关于本书的主要内容和结构,豆瓣里已经有很详细的介绍,在此不赘述,笔者更多的谈一谈阅读完后的感受。
笔者现在是研究生在读,从本科时期认真思量着选课,到研究生阶段担任助教时看到在每学期第一堂课上学生们对这门课程内容、教学方式、作业与考核等问题的关注,我深知一门课程的第一堂课在学生心中的重要程度,它直接影响了学生是否有继续跟这门课学习下去的意愿,这就决定了第一堂课通常是非常出彩的——它要引起学生选课的兴趣,也是提纲挈领的——它要让学生了解整个学期里每周花费几课时在这门课上要做些什么,本书直截了当以《第一堂课》命名,合集了巫老师开设过的二十四门课程的第一堂课,其价值不言而喻。
对新入门的艺术爱好者而言,这是一本并不“高高在上”的艺术类书籍,巫老师的写作一向深入浅出,哪怕是他很多富于思辨性的学术专著,也不会让人在阅读过程中觉的费解,而是在他行云流水的文笔里感叹艺术真是美好,读罢酣畅淋漓。同时在这本书里汇集了很多巫老师个人有创新性和代表性的研究美术史的思路和概念,如他对“纪念碑性”、“女性空间”、“废墟”、墓葬美术、礼仪美术的研究,若是作为一个新人进行阅读,笔者想会与自己当时初入门时读到《美术史十议》的感觉一样,收获到的并不是一本厚厚的对美术史知识点和作品的罗列,而是对中国艺术有了更丰富的看待方式,生出一种豁然开朗之感。
对美术史专业的人来讲,大概没有没阅读过巫鸿先生的著作并受到启发的,巫鸿先生是笔者非常崇敬的一位美术史家,在阅读这些文字时,我脑中时常会浮现出巫老师站在讲台上娓娓道来的样子(脑补的素材也许来自之前参加他的学术讲座和对谈),不是所有人都有精力和机会去芝大和哈佛听巫老师开课的,但这本书里老师形象的巫鸿多少弥补了这样的遗憾,也让我看到了他在研究生课程中对学术训练的要求,并勉励自己。此外,就像郑岩老师谈到的:“这些稿子其实蛮有意思。慢慢地你会发现他讲的很多东西,后来都发展成他的文章和书了。”在这些课程里,有太多曾经读到的巫鸿先生之著作的影子,看着这些第一堂课就好像看到了这些专著还在”幼芽“时期的样子,你甚至能从时间性上看到它的”成长“, 例如第二十讲和第二十一讲中国绘画中的”女性空间“,在跨越二十余年的时间里不断有新材料和想法丰富进来,最终形成了2018年的新书,也回答了笔者过去的巫老师出书又快又好的望洋兴叹——这背后其实是有丰富的沉淀在的,同时,也能看到巫鸿作为老师的身份,总是在不断把自己最新的研究想法分享给学生,达到教学相长的目的。
书是常读常新的,就像我们重新审视美术史上的很多材料时,总能结合自己新获得的经历或知识,而生发新的感受。《第一堂课》里的很多内容笔者之前算是比较熟悉,但在阅读这些讲稿的时候,还是会有很多备受触动的地方。例如在笔者短短几年的美术史研究中,已经从大量吸收知识的状态过渡到在自己感兴趣的领域开展深入研究的阶段,在进行专题论文的写作时对能掌握的资料总不尽满意,觉得美术史研究就是在碎片化的史料中努力拼凑出一个“真相”,如果能看到更完整的资料,是不是很多问题就会好解释很多?巫鸿老师在第四讲中提到“资料不完备,也永远不可能完备”一段给了笔者很多启发,“匮乏的史料是历史研究中不可能轻易越过的一道障碍……任何现存的图像和文字……它们都填补了某种历史空白,其作用往往超越自身所在的历史空间……”,这些话语让笔者更能平心静气的面对一些材料的缺失,并学会去妥善利用现有的“时间的恩惠”。又一例是笔者无奈于目前对艺术感兴趣的人总体上还是少数,以及很多自媒体等不负责任挑选很多噱头进行艺术科普等等现象,一直反复追问自己做美术史也包括做很多人文学科的意义,在第七讲中巫鸿先生提到”在我看来,美术史之所以重要……是因为它为你们提供了分析“视觉材料”的必要训练和学习途径……如果这样想的话,你就会发现自己其实完全生活在一个视觉的世界里”,这部分的言论给了笔者更广阔的思路,凡此种种不一一列举,但这些启示,都是笔者在读这本书之前没有预期到的意外收获,那种读到好的观点时豁然开朗的感觉真是太棒了。
从更长远的角度来说,本书是对珍贵的一手史料的保存和记录。美术史还是个年轻的学科,在我们在研究美术史学史的时候,就像我们会记得沃尔夫林在课堂上同时投放两张幻灯片一样,巫鸿先生的这本著作为我们记录了在二十和二十一世纪之交以及二十一世纪初一种美术史教学的状态。此外,当我们反思这本书中讲稿的“原境”时,就会发现它们的观者是芝大和哈佛来自各国的学生(而且大部分应该是非中国国籍的西方学生),如何向没有东方文明背景的学生们讲述中国艺术呢?在选择的材料和选取的视角上会有什么不同呢?这本书也提供了一种解答,也是对世界应该如何理解中国美术的一种探索。
最后,本书值得称赞的细节是,全彩印刷对看图非常友好,图片也很清晰,同时线装书的装订方式让在看将近四百多页的厚书时展开依旧非常轻松。
如果说对本书还有什么建议,作为一个美术史专业的学生,还是很“贪心”的希望对每门课程在附录里不仅仅有对巫老师论文的引申,要是能附上这门课列出的参考书单就更完美了。
《第一堂课》读后感(三):“第一堂课”:巫鸿思想导读
这本书收录的是巫鸿先生在哈佛和芝加哥大学开设的各门课程的“第一堂课”的讲稿的译文。
诚如巫鸿先生序中所言:
1. ”第一堂课“为何重要?因为它相当于开题,题开不好,自然不能吸引学生。因此必定要问题明确,思路条贯,要能“留”住学生。
2.讲稿观点多见于著作,为何重复发表?一是讲稿可窥作者学术思想的变化;二是对专业读者而言是导引,对业余读者而言是入门。
一言以蔽之,《第一堂课》可谓巫鸿先生学术思想的导读本。
此书分为上、下两编,上编为“概论·方法”,下编为“主题·视角”。讲稿分类难在内容上或有交叉与重复,但该书的分类可见编者的用心,试举两例:
1.上编先列中国美术通论,再列礼仪美术—由大汶口陶器到汉代墓葬,再及考古、叙事画,最后提及敦煌。“中国叙事画”在前,再看上编最后一章“敦煌经变画”时便好理解。
“中国叙事画”简单回顾了学界关于叙事性图像的三个经典定义:
1)魏兹曼:“叙事性艺术是指艺术家试图通过此种艺术形式表现一个由特定人物参与的特定事件,而该事件本身又是值得被记录的。” p145
2)温特:“重要的是,叙事不能与故事等同。叙事是指通过特定框架来讲述故事内容,故事的组织方式本身形成了叙事。”p147
3)戴维·派柏:“叙事,或故事讲述,指示了一系列发生的事件,因而也意味着一种由起始、发生、结束所组成的真实时间维度。”p149
以上三种定义分别强调了图像与文本的再现关系,图像表现的意图,图像与时间的关联。后来者总是对前者的质疑与补充。尤其是图像与“时间”的关联,叙事图像仅仅指涉叙事时间吗?有没有可能造成泛化,指涉“真实时间”“心理时间”“超自然时间”等等?p150 在基本了解艺术史界对“叙事艺术”的界定后,就能更好理解为什么在“敦煌经变画”中,巫鸿先生质疑周一良先生把经变画纳入叙事艺术的论述:“虽然一些经变画包含有叙事元素,但它们与三种典型的叙事画都有所不同,这三种即‘本生’或佛陀的前世、‘佛传’故事和称为‘本缘’的因缘故事画。我认为把这三类绘画称为叙事艺术更符合这个学术术语的概念,经变画则可以说是‘偶像’和‘插图’这两种图像的结合。”p196
经变画简单来讲就是表现作为文本的佛经,p186 而常见经文如《心经》《金刚经》确实不具备“叙事艺术”以上三种定义中的任何一种,尽管它也具备一定的叙事元素,如佛陀“ 于其城中次第乞已,还至本处,饭食讫,收衣钵,洗足已,敷座而坐 ”的不言教法和后来须菩提为大众请法。如果不了解“叙事艺术”的界定,乍看巫鸿先生此论可以说难知此中差别,只能囫囵略过,但此种区别不得不细察。
2. 下编依次介绍了巫鸿先生颇具创见的“纪念碑性”“祖先崇拜”“废墟的故事”“超越的山水”“女性空间”等多个重要主题,后以“中国绘画:作品与原境”“中国绘画的媒材与形式”两章收束,略作为中国艺术史研究的方法论总结。
在“中国绘画:作品与原境”章中,巫鸿先生指出研究新手常常忽视绘画作为物质实体的特征——包括形制、材料和尺寸,决定了绘画的创作过程和欣赏方式——而仅仅关注其图像。p328 紧接着的“中国绘画的媒材与形式”章中,就有了关于二维画像媒材(包括丧葬语境中的便携式绘画、手卷、画幡、立轴等)和三维画像媒材(建筑性媒材包括棺、石窟、墓葬、地上建筑,可移动媒材包括承载图像的物件、屏风、册页、扇子、书籍插图、纺织品等)的概览。媒材与形式在研究中的重要性在巫鸿先生于复旦大学所做的系列讲座中有精彩论述,参见《全球景观中的中国古代艺术》。
.S. 编者在书后专列“延伸阅读材料”,巫鸿先生未尽之言都可按此索骥。
作为文学研究者看此书既有共鸣也有启发:
共鸣在于:
1. 绘画研究分“内部特征”与“外部特征”,文学研究也分内部研究与外部研究。前者的内部包括画的形式、材料、图像、主题、构图等,后者的内部包括文体、意象、主题、韵律等;前者的外部包括画家的生平和经验,以及种种社会、政治、宗教、教育、文化、商业因素,白谦慎《傅山的世界》虽是研究书法,但大抵属于此意,也就是艺术社会学的范畴,后者的外部也大抵相同。
2. 绘画史研究的五种倾向:“风格进化论”的扬弃,“原境”研究,“赞助人研究”,“性别研究”,“视觉文化研究”(不仅是作品的“原境”,而是某一历史环境中的视觉文化的状态和趣味)。文学史研究同样出现类似的倾向,比如论及晚明文学便提“童心”“性灵”“重情”,解放人欲又冲破封建礼教的束缚这类话语得到重新审视;“文化诗学”同样强调恢复作者、作品的历史语境,关注作者、作品的一系列状态,包括文本的内与外;出版史、阅读史研究的兴起,同样开始关注精神世界的现实构成因素;“赞助人研究”在思想史中的典型研究如艾尔曼《从理学到朴学》,精要地介绍了清代江南学术共同体的形成中,阮元等“赞助人”对朴学推广的直接影响等等。
启发在于:
1. 比如“废墟的故事”中 ,绘画似乎更少表现“丘”“墟”“迹”,而诗歌中尤其是怀古诗则有大量凭吊“废墟”之作,为什么同主题的抒发会偏好不同的艺术形式?
2.比如“女性空间”的问题,在文学研究中也有一个相关现象,即“男子作闺音”。在男子创作者占主导的世界中,绘画中的女性空间可以直观地呈现出来,诗歌这类文学文本又是如何想象和展现“女性空间”?
通观巫鸿先生的各类作品,可以看出他在比较中西,沟通中西上的努力。这种努力也为他惹来了麻烦与不解。在异域研究中国古代艺术,困难可想而知,不同的学脉、不同的文化传统,都为中国本土学术对话西式学术带来阻力。尤其是他的代表作《中国古代建筑与艺术中的“纪念碑性”》,被讥讽带有中国学术特有的“连续性偏好”。这种涉及中西学术对话困境的问题,我认为也是有志深入了解人文研究的读者必须了解的事情。李零先生称此遭遇为学术“科索沃”,虽然事情已过二十年,但如今翻看仍有方法论反思的价值。详情可参见刘东先生主编的《中国学术(第2辑)》,此处就不做转述之赘了。
《第一堂课》读后感(四):作为思考方式的中国美术史 ——跟巫鸿教授走进世界顶尖高校的课堂
如今,我们获取信息的途径与过去相比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手机、Ipad、电脑、影院荧幕、电子广告牌……这是一个充斥着各种屏幕的时代,信息如洪水,透过屏幕向人们袭来。生活在这个越来越视觉化的世界中,应该如何培养视觉信息分析的能力,将屏幕上的图像变为自己的知识来源和了解世界的手段,在信息洪流中拥有自己的判断力,而不仅仅是成为一位被动的消费者呢?
在巫鸿教授的这本新著——《第一课堂—在哈佛和芝大教中国美术史》中,我们或许会找到一些启发。
这本书汇集了从1987年起,巫鸿教授在哈佛大学和芝加哥大学三十年间执教中国美术史课程的讲稿。二十四篇引人入胜的文章展示了作为老师的巫鸿先生在课堂上的魅力,这是为大多数读者所不了解的。从书中可以看到,除了教授学生中国美术本身丰富的视觉材料和历史知识,培养学生视觉信息分析的能力之外,巫鸿教授更注重通过不断的提出问题,来引导学生在全球视角下进行独立思考。
当然这些讲稿最初的听众大部分为外国学生,中国美术作为非西方的艺术传统,对他们来说是陌生和新奇的。但同时,对于我们这一代在全球化和现代性的背景里接受教育的年轻人来说,又何尝不是相同的呢?巫鸿教授曾提到过,“过去即异域(The past is a foreign country)”。过去即是一个陌生的国度,我们和中国艺术的关系其实是模糊不清的。
在此层面,这本书适合每一位对我们“熟悉而又陌生”的传统文化和艺术感兴趣的朋友阅读。在阅读之中,穿越时间和空间的界限去超越自己狭隘的视野,启发新的思考方式。
那么巫鸿教授在中国美术史的课堂上,为我们提供了哪些新的思考方式呢?
开放视角下的“全球美术史”
“全球美术史”的概念始终贯穿在巫鸿教授的研究中,读者在本书中也能一窥这种崭新且开放的研究视角。“全球美术史”的思考方式是将世界作为一个整体,把特定地区或国家的个案放归至这种整体语境中,去寻找个体之间的差异与共性。
这与巫鸿教授本人的生活和工作环境是密不可分的。许多在哈佛和芝大听课的学生对中国古代艺术的了解是不多的,甚至不懂中文,在这种情况下讲述中国艺术,势必要进入这样一个全球视野当中。
本书“下编”中收录的几篇文章体现了这种研究思路。比如十三讲“全球艺术中的’纪念碑’”、十七讲”中国美术和视觉文化中的’废墟’“,十九讲“汉代墓地中的’门’”,二十讲和二十一讲“中国绘画中的’女性空间’”和二十三讲“中国绘画的媒材和形式”。在其中,“纪念碑”、“废墟”、“门”、“女性空间”和“绘画媒材”等主题和视角就来源于“全球美术史”的思考方式。这些特性不仅存在于中国艺术里,也为其他文化背景下的艺术所共享。
在美术史研究中,相较于编年体、地区以及风格划分、艺术品物质属性等传统研究思路,巫鸿教授的视角更像是从一个有机体的侧面出发,抽取出许多看似无关的碎片。当这些碎片被串联到一起之后,则呈现出一种预想不到的形状。这些形态各异、自由且迷人的“形状”正产生于“全球美术史”的思考方式之下,成为美术史研究中崭新的“元视角”。
让艺术品回归“原境”
对艺术品回归“原境”的强调体现在巫鸿教授包括墓葬艺术和中国绘画艺术在内的多个研究中。它是指通过把艺术品“重置”于他们原来的建筑、礼仪、宗教、意识形态和政治等环境中,从而更加准确、全面的理解艺术品在他们所属社会中的位置、意义和功能。现代美术馆的出现使我们形成了一种固有的观看习惯,把艺术品与其“原境”分离,将其视作孤立存在的“客体”,从而忽视了艺术品原先所处的物质和空间环境。
回归“原境”的思考方式有助于将这种“割裂”和“分离”的观看方式转换到“整体”和“融合”的视角上来。本书第六讲“汉代墓葬美术”和第二十二讲“中国绘画:作品与原境”中探讨了“原境”问题。以书中的内容为例,巫鸿教授写道:一件“作品”总是和其他的形式、和它的环境密切相关。比如说寺庙和石窟中的壁画通常作为塑像的背景,在敦煌洞窟中经常可以看到这种情况。以及许多唐宋时期的绘画杰作现在被装裱成卷轴画的形式,但他们曾经是屏风或画幛,是建筑陈设和装饰的一部分。
这促使观者开始意识到,艺术作品处于不同的环境里,就会产生不同的意义和功能。这种从“整体”出发的思考方式,更加注重艺术品的“背景环境”,启发观者打破时间和空间的限制,在变化中解读中国美术史。
跨学科的思维方式
跨学科的思维方式是巫鸿教授研究中最显著的特点之一。这与他多元的学术背景、广博的阅读经验和丰富的人生阅历是密不可分的。本书在以美术史作为研究主体的同时,参杂了大量考古学资料和多样的社会学与人类学研究观点,读者可以充分地感受美术史与其他学科交叉互动带来的思想火花。
巫鸿教授在《中国古代艺术与建筑中的“纪念碑性”》一书中曾写道:“人类知识的每一分支都建立在分类的基础之上。在世界能够被解释之前必须建立某种次序,混乱无序的现象必须被分成可以把握的组或类。由于最重要的分类标准总是从被分类对象的诸多特征中选择出来的,所以分类的结果常常由分类者的立场观点所决定,因而必然是具有时间性和目的性的历史现象。”跨学科的思维方式正是突破类别间的壁垒,还原事件本身的复杂性,从而超越单一的思考方式以及历史局限性的一种途径。
作为每学期开学的“第一堂课”,这门课程面向的学生往往来自不同的专业,这种跨学科的思考方式给多元化的学生和读者们提供了更广阔的视角和更多样的启发。
以上三点谈到的内容只是巫鸿教授这本新著中的零光片羽。正如郑岩教授在访谈中所说:一位聪明的读者、一个聪明的学生,能在这本书里读出好多的论文题目来,可以学会怎么去寻找题目。这本书一个最大的特点是:它不同于一般的教科书,是非常有启发性的一本书。
因此,这本书不仅适合所有对中国传统文化和艺术感兴趣的读者阅读,同时也会将所有渴望开阔视野、打破思维定式的读者们带上一场奇妙的艺术之旅。
《第一堂课》读后感(五):巫鸿与佛教美术
提及巫鸿的中国古代美术研究,往往述及其对“原境”与“媒材”的讨论,前者多见于对“墓葬美术”的探讨,后者则以作者1996年出版的《重屏》为代表。巫鸿师从张光直,以早期考古入手美术史,博士阶段的关注点也集中于早期,最终提交了《武梁祠》(1989)这一以汉代墓葬祠堂为个案的博士论文。
与此同时,作者也对中国美术在汉代之后的变革有着浓厚的兴趣,在《中国古代美术与建筑中的“纪念碑性”》(1995)一书的末尾,以《透明之石:一个时代的终结》来收束对早期中国美术的讨论,同时对下一时代的美术发展进行展望。同样的,在本书的讲义中,作者以公元三世纪区分前后期中国美术,提出的划分依据是独立艺术家和艺术品的出现及佛教美术的传入与普及(p25)。
巫鸿之后的学术发展如前所述,围绕“原境”与“媒材”展开,作者对“墓葬美术”这一亚学科的提出与完善无疑也是作者最为人称道的学术贡献,有时甚至会成为一个潜在的“刻板印象”。而从本书的讲义中,我们可以了解到作者更为广泛的学术兴趣与方向。讲义中的题目多已结为专著出版,但其中唯有一个例外,即是佛教美术。
在本书收录的二十四篇课堂讲义中,有五篇与佛教美术相关,其中三篇围绕敦煌展开,列举如下:
1997年,《敦煌经变画》
2007年,《敦煌视觉文化:传统与互动》
2010年,《艺术与宗教:佛教与基督教艺术比较研究》
2018年,《中国美术和视觉文化中的瑞像、神物与灵境》
《敦煌石窟美术史研究法》
几门课程均为研究生讨论课,从中也可看出巫鸿对佛教美术尤其是敦煌的关注。而如果将视野转向作者所发表的论文,有关佛教美术的(据笔者不完全统计)共有九篇,列举如下:
1986年,《早期中国艺术中的佛教因素(2-3世纪)》
1991年,《佛教美术如何植根中国》
1992年,《何为变相?:兼论敦煌艺术与敦煌文学的关系》
《敦煌172窟<观无量寿经变>及其宗教、礼仪和美术的关系》
1993年,《经变和讲经:唐代佛教美术、文学和礼仪的一个交接点》
1996年,《再论刘萨诃:圣僧的创造与瑞像的发生》
1998年,《城市寺庙、可移动佛像及“行像”礼仪》
2002年,《什么是敦煌艺术?》
2003年,《敦煌323窟和道宣》
从中也可注意到,巫鸿对于佛教美术的兴趣主要围绕敦煌展开,从1986年读博阶段到如今,想是有足够的积累与思路,一直未有出版相关专著,也颇令人好奇。但这些研究也确已成为研究佛教美术所不可忽视的,以下暂对作者上述研究做一简要的梳理与评述:
前文述及,巫鸿以三世纪为界将中国美术分为前后两期,一个很重要的区分就是佛教的传入,而作者博士阶段的《早期中国艺术中的佛教因素(2-3世纪)》与之后的《佛教美术如何植根中国》则也都围绕“佛教对中国的改变/反改变”展开。
其后,则围绕敦煌进行了一系列的研究,大致可分为三类,即经变、灵瑞与原境。经变无疑是一个微妙的题材,作者这一研究顺应了欧美学界叙事画与跨学科研究兴起的趋势,将“图”与“文”这一对富有张力的关系引入中国美术的讨论中;灵瑞则主要围绕瑞像展开。在对早期美术的研究中,作者即强调古代美术中所包含的超自然力量,而对瑞像的研究则是其将佛教美术材料置入佛教语境下的尝试,以寻求不止于在题材与风格上讨论美术史。正如作者所言,历史事实永远是阐释的中心和主题,但我们的证据却可以是多元的和不断扩充的(p242)。
而原境则是作者所一直在探索的,在此可分为单个石窟与总体,前者见其对172窟与323窟的讨论,其中一则侧重石窟内的竞争,另一则则引入“建筑与图像程序”,强调配合与统一;后者则顺应欧美学界“总体艺术”与“空间转向”的潮流,将敦煌石窟放到作为整体的敦煌之下进行讨论,也延续了最初对佛教与本地传统关系的讨论,其中特别重视仪式的功用。作者在本书讨论墓葬美术研究法的部分曾提出两种方法,一则围绕时间性的仪式,重构社会关系及展示场合的意义,一则揭示空间的逻辑与理念,发掘观念(p85)。这也可以与上述佛教美术研究相对应。
作者的这些研究,也收到了来自佛教美术研究者的一些回应,如颜娟英《从凉州瑞像再思考敦煌323窟、332窟》一文,即指出了作者在论述323窟时存在的一个问题,作者将研究对象视为一个逻辑严密的整体,但实际情况则往往是复杂的。在整体的、原境的立场上思考一定情况下的确可以还原其完整性,但与此同时,也存在着消解部分特殊性的风险。但没有疑问的是,这无疑是一个极具启发性的思路。
如果回归本书中的五则与佛教美术相关的篇目,则可发现两者呈现出大致对应的状态,这里需要提到《艺术与宗教:佛教与基督教艺术比较研究》一课。这是作者与埃尔斯纳(Jas Elsner)合开的一门课程,围绕两个宗教的起源、圣像、圣物与朝圣进行比较。埃尔斯纳一直致力于一种“全球美术史”的书写,这门课无疑也展现出了比较的潜力。这里则需提到巫鸿的佛教美术研究乃至本书的一个突出点,由于作者在国外进行教学研究,因而也有更多了解其他地区美术史研究的机会,而不断地交流与比较,无疑也是作者的佛教美术乃至中国美术史研究得以取得如此贡献的一个重要因素。
最后,试对巫鸿的佛教美术研究做一个大致总结,这些研究的目的指向无疑都是“达到对视觉艺术的历史事实的不断深入的理解(p242)”,在视野上注意汲取其他地域及主题研究的成果、引入跨学科研究;方法上则立足于“建筑与图像程序”与“空间转向”展开对个案原境的讨论,两者分别指向宗教与社会;最后,在研究对象上,作者最初关注佛教传入的这一时间段,试图解决“转型问题”,90年代后则转入唐代背景下的敦煌佛教美术讨论,这一关注点的转向是值得注意的。
上述因素无疑也贯彻在作者的其他研究中,作者虽非专门研究佛教美术,但其新颖的角度与方法无疑予学界以诸多启发,从此也可见作者研究方法的潜力。将原本被拆散研究的造像、壁画还原到其所处的“原境”中,无疑突破了传统的图像志及风格研究,而对灵瑞等超自然表现的关注,无疑也能够使研究更加贴近佛教本身,进而寻求一种更为接近的“内部理解”。同时,也期待作者在佛教美术领域进一步的开拓与补充。
以下为书影:
《第一堂课》读后感(六):郑岩 | 《第一堂课》展现了作为老师的巫鸿,这是从其他著作中感受不到的
活字文化:艺术史这几十年有一个很大的变化,就是人类学、社会历史、物质史等等,对美术史的研究提供了非常重要的材料和观念,像巫鸿先生就是这方面研究转型的一个很重要的代表人物。
巫鸿先生大家可能都比较熟知,他是著名的美术史家,现在是芝加哥大学的教授。最近又要出版一本巫鸿先生的新作叫《第一堂课:在哈佛和哥大教美术史》,这本书是巫先生给哈佛大学和芝加哥大学的学生每学期上美术史课的第一堂课的讲稿,下个月就要面市了。这本书跟您也有很大的渊源,您是出版这本书的直接联系人和推动者,您能给我们介绍一下这本书的内容和成书的过程吗?
著名美术史家巫鸿教授所著《第一堂课》,即将面世郑岩:好,巫鸿教授大家比较熟悉了,他出版了很多的书,很多朋友都读过。我想这本书不太一样,它说到底不是一个著作,也不是一个文集,是一本讲稿合集。我在介绍这本书的时候,我在跟一些朋友说,我们过去读他的书,能看到作为一个学者的巫鸿,那么我们在这儿就能看到作为一个老师的巫鸿,这是除非你在现场听他的课,否则是没有机会感受到他这方面的学养。
因为他在美国教书这么多年,从哈佛到芝加哥,他是用英文讲,他有一个习惯,为了准确,他要提前写成讲稿,有时候我过去听他的课,他手里拿一个稿子,有时候看一眼有时候也不看,有时候念一段有时候又在发挥,这些稿子其实蛮有意思。慢慢地你会发现他讲的很多东西,后来都发展成他的文章和书了。
我印象比较深的是三联书店出的他讲女性美术史这本书(指《中国绘画中的“女性空间”》),我第一次听他讲这堂课是在1996年,大家老觉得巫鸿教授写东西很快,其实他从开始讲这个问题到写出来,已经是二三十年的时间了。所以我觉得《第一堂课》这本书一个最大的好处就是,我们可以看到一个学术生产的过程。
艺术史研究中长期以“仕女画”或“美人画”来表述以女性为主题的绘画作品,但这样的术语不仅相对晚出,在形成过程中还带有一定的画科定位和评论取向,也无法囊括所有围绕“女性”产生的绘画作品。本书中,巫鸿先生提出了“女性题材绘画”这个概念,并引入“女性空间”作为讨论的核心,意图把被孤立和抽第二个方面我觉得这本书对国内研究和教学的互动关系很有启发。我们现在高校的评价体制,都要看论文、看C刊、看你做了多少项目,很多人抱怨这是影响了和冲淡了我们的教学,很多人觉得因为教课多就没有时间做研究……你会发现很多的议论总是把这两个方面对立起来。但其实如果没有好的研究怎么能够教好书呢?如果没有在课堂上跟学生的教学相长,又怎么能做好的研究呢?这两个方面其实是统一在一起的,所以我觉得这本书就提供了这样一个向度。
另外我觉得这本书对于读者来说也不一样,他是写给学生的一本书,因为它叫《第一堂课》。在美国有这样一个制度,它鼓励老师不断地要开出新课来,你不能二十年来老讲一门课,这样当然激发出一些新的研究来,也带动学生不断地跟进这些研究。
它称作“第一堂课”,这个课是每一门课程的第一节课,而美国高校有一种制度,有一个学生选课的时段,他可以先试听,即shopping time,“买课”,学生有兴趣就听,没有兴趣就走,下一次课就可以不来了。所以“第一堂课”老师总是要热情饱满、引人入胜,很鼓动人心。所以那部分讲稿我觉得是相当有意思的。
当然它也不单纯是广告或者是表演,我觉得更重要的是怎么样提出问题,它展现了一个开端,是在讲一个问题的时候,怎么带领我们进入,是授人以“渔”,并不是直接把那个结论告诉你。巫鸿先生是一位好老师,比如他从来都不给学生发论文题目,不会说我命令你写一个什么题目,他也不告诉你我认为这个怎么样,你应该把它写下来,他从来都是启发学生去提问,自己去探索解决这个问题的方法,这些在这本书里边都会有体现。我觉得一位聪明的读者、一个聪明的学生,能在这本书里读出好多的论文题目来,可以学会怎么去寻找题目。我觉得这是这本书一个最大的特点是:它不同于一般的教科书,是非常有启发性的一本书。
活字文化:您说得特别对,因为我也看了书稿,非常有启发。这是巫鸿教授对于他所开的课程的总体介绍,这里面牵涉艺术史的很多领域和方向,在这第一堂课上,他都做了一个高屋建瓴式的总括性的介绍。所以这本书不仅对于相关专业的学生是一个入门,对于很多对艺术感兴趣的年轻读者,也可称作一本入门读物。
如您所说,巫鸿先生很多著作原文基本上都是英文,现在国内也出版了很多他的专著,也有了非常大的影响力。我知道巫鸿先生著作的中文版最初也是您来联系拟定的,所以他的著作能够持续出版,您也功不可没,当然这背后是您跟他多年的友谊和互相的了解。你能不能给我们讲讲巫鸿先生的故事?
郑岩:我和巫鸿先生的交游相关故事很多了,因为时间有限我就特别简单地说一下。我认识巫鸿先生是从1996年到现在,已经有二十余年了,我认识他的时候他就是我现在这个年龄,所以那个时候我一直称他先生,我觉得那是对长者的称呼。
我认识他的时候,他已经出版了好几本书,像《武梁祠:中国古代画像艺术的思想性》《中国古代艺术与建筑中的“纪念碑性”》《重屏:中国绘画中的媒材与再现》都已经出版了,而且他已经开始在做当代艺术的展览。他当时对我的影响非常大。我那时候还不到30岁,眼界很闭塞,读的书也很少,以前就是学考古、学历史,我觉得他为我提供了另外一个系统,我原来完全没有接触过的知识系统:一个是美术史的系统,再一个就是当时西方学者在做中国美术史和中国研究的一些东西。所以我自然就和原来所学的知识产生一种关联,在考虑它们之间到底有什么联系,我觉得对我来说一下子就感到眼界大开。
本书首次尝试把中国绘画既视为物质产品也看作图画再现,正是这两方面的交互合作与相互制约使得一张画生意盎然。这种新的研究方式打破了图像、实物和原境之间的界限,把美术史与物质文化研究联系起来。我觉得其实巫先生不仅是一位好的学者,他也是一位好的老师,这一点在《第一堂课》这本书里也能体现出来。我不是他“在编”的学生,我大概算是他“编外”的一个学生,我觉得他作为一位老师,有两点和别人不一样的地方:一点是他总能对学生存在的问题一针见血地指出来;第二点我觉得更重要,他总是能适时地给学生以强大的信心和鼓励。这样我们既能知道我们的问题在哪里,但同时我们不会失去继续向前发展的自信心。我觉得这是他作为老师的独特方法,在这本书里多少也能够体现出来。
我和巫鸿教授多年来保持着亦师亦友的关系,他也是我学习的榜样。我觉得他在学术研究上有几个方面对我影响很大:第一是他不断强调学术史的重要性,他对方法论充满自觉;第二点是他相当有责任感,他对整个学科,我们再说大一点,对于中国文化在国外的传播、甚至中国文化的整体形象,他都有强烈的责任感,他很少谈这个问题,但是在接触当中我们能够感受到;再一个就是在研究的时候,他强调既不重复前人也不重复自己,所以大家会看到他从史前一直做到当代艺术、前卫艺术,涉及的面那么广,在中国美术史的研究当中,以前是非常少见的,他是一名非常渊博的学者。
更重要的一点,可能大家也都感受得到,就是他极其勤奋,他的勤奋、他的精力之充沛是我们这些比他年轻二十岁的人都自愧不如。我后来问他为什么每年能写那么多东西?他说我只有一个窍门,就是每天写一点。他说他有一个座右铭,如果一个事情你不提前完成的话,那么你一定会耽误,一定会逾期,没有正好卡点那回事,所以他把时间抓得非常紧凑。但无论多忙,每次我们给他写邮件,他都在第一时间回复,这是他的勤奋,是我们学习的榜样。有时候我们白天跟着他开一整天的会,晚上回到家后他还继续工作,第二天一早,他又和我们一起起床、一起吃早餐,巫鸿先生就是这样一位学术超人。
美术史学家巫鸿有一次在芝加哥开会那一年,我问他,您觉得美术史最重要的训练是哪些方面?他说两点,一点是训练学生的视觉分析能力,第二点就是context,外部的各种关系,这种社会的、文化的、历史的联系。我觉得他概括得很对,中央美院薛永年先生概括美术史的研究,他说一个方面可以叫做内向观,另一方面叫外向观。我觉得怎么找到这两个向度之间有机的关联,可能也是我们要思考的问题。
“
如何在当代重新激活中国美学传统?
”
活字文化:我还想问一个问题,像《年方六千》也好,《第一堂课》也好,里边提到了很多文物,现在我们有一个比较热的倾向,就是对于中国古代的物质文化,大家都很愿意去了解。那么您能谈谈我们中国古典文化的审美特点吗?
郑岩:这是一个特别大的问题了,这其实是很多理论家们讨论的问题,像做美学、做哲学的学者想得比较多。我们作为历史研究者,有时候不太想太大的问题,历史总是处理一些非常具体的物人事,是吧?当然这个问题我们也时时都会思考,我想一句话两句话说不清楚。
我觉得巫鸿先生这些年试图在讨论这个问题,他在三联书店出过一本书,您也知道,讨论国际视野中、比较视野当中的中国艺术(注:《全球景观中的中国古代艺术》),那是他在复旦的讲座系列,我觉得蛮有意思,可能跟他生活、工作的环境有关系,他要不断跟别的科系的老师交流,可以想象很多听他课的学生,甚至都不懂中文,他要讲中国艺术的时候,势必要进入这样一个视角当中。
全球景观中的中国古代艺术”系列讲座采用 “全球美术史”的视点,对中国古代美术的重要特点进行反思。这个反思建立在两个基础上,一是把全球美术看做一个整体,其中包含着许多即独立又互动的地区性美术传统,每个地区传统都对人类美术的整体做出了宝贵的贡献。二是这些地区性的贡献是不同的,正因如此我自己也在想这些问题,我寒假还在一读一本大书,是关于基督教的美术,也确实感到一些非常的不一样的东西。因为基督教的背景,包括西方古典美术的传统,都是以偶像崇拜为核心发展出来的,跟中国以玉器、青铜器发展出的非偶像崇拜的美学观念,一开始就不一样。虽然之后佛教进入中国,但其实精英知识分子除了对《维摩诘经》、对禅宗有点兴趣,对怪力乱神的东西也不太感兴趣,特别是在艺术上,比如敦煌遗迹和文物,其实多少年来都不在知识精英的视野当中。
我认为自19世纪以来,我们都是采用近代的、西方的一些观念来观照中国的美术史,这套理论当然贡献很大,我们也有了中国的雕塑史、中国的建筑史,这都是了不起的贡献。但是从另外一个角度讲,这些分类的系统和概念也都是从西方慢慢产生出来的,它还不是中国文化内部生发的东西,所以我们从这个角度去谈中国古典美术,多少还有点儿隔靴搔痒。所以我们仅仅用西方传统的基本概念来谈中国古典审美特征的话,还是有很大局限性的。所以这个问题我觉得还可以继续再发展。
这就有点像过去大家谈中国科技史,像李约瑟先生所阐释的著名命题:为什么中国没有产生工业革命?后来大家说你用的“科学”和“技术”这些概念,可能本身就是西方系统的概念,移植到中国文化的语境下来回答这些问题就非常困难。
所以接下来的问题是,怎么样从中国文化内部来反思、修正,并发展这些西方的、现代的概念?中国有自己的一些理论系统,比如中国的绘画之学、禅宗,怎么把它重新激活,变成现代学术的有机组成部分?我觉得要回到内部,要在一个更高的层面上来总结中国文化审美的这些特征,可能我们就会更有底气来回答这个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