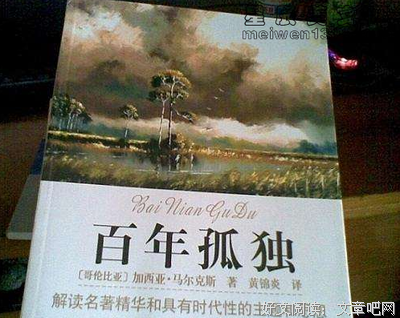
《空巢:我在这世上太孤独》是一本由弋舟著作,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的精装图书,本书定价:58.00元,页数:208,特精心从网络上整理的一些读者的读后感,希望对大家能有帮助。
《空巢:我在这世上太孤独》读后感(一):这不是孤独,是绝望,是恐惧
看了这本书,才知道,孤独不光是精神上小资的词,更是一种多余的感觉,一种无用的感觉,来自内心的恐惧。
当一个人置身于时间之中,无事可做,无人可依,无话可说,无处可去,能让你打发寂寞的只有病痛,和嫌弃,甚至这嫌弃来自最亲的人,来自一个本来你付了钱要买他服务的人,而你,哪怕曾有金戈铁马的豪情,曾有凌云万丈的才华,这个时候,你可能连死你都做不到,你能做的只能是“苟且偷生”,你也休想将来复仇,因为时间上已经不允许了……
这不是孤独,是绝望,是恐惧。
书里那些夫妻相互扶持的还是让人羡慕的,相濡以沫已经是一件非常奢侈的事情。那些绝望的老年人有的铤而走险,住牢竟然成了一种归宿。
这本书,给我印象最深的是,是何婶,何婶经常去看她村里的一个老婶子,老婶子已经糊涂了,她认不得人,瘫痪在床上。
何婶去看她,老婶子躺在床上,自说自话。
不管当成啥,何婶也都应着,反正也是瞎聊。
老婶子把她当闺女的时候,说得肯定是自己年轻力壮的故事,把她当娘的时候,说的是肯定是自己小时候的事。
老年人,面对孤独,面对恐惧,能做得也只有回忆了,回忆自己这一生,可惜没有听众,何婶能在那聆听是多么可贵,多么善良。
我想起了我们村里的一个老太太,我会老家,她问我:“你见过我儿子没有?”
我说没有。
她说我儿子在外面被别人招成了上门女婿,回不来了。人家那一家可有钱了小轿车就有三辆。
我只能说是是是,其实我知道,她儿子早就死了……
《空巢:我在这世上太孤独》读后感(二):看到“我在这世上太孤独”感触良多
社会发展的步伐太快,带来的结果出乎人的意料。几年前,很多专家都在预言中国要进入老年化时期。然而,在目前中国这样一个变化剧烈、没有定型的转型期,老年化究竟到什么程度,老年化究竟给我们带来了什么问题?
有人从空巢老人的角度对城乡老年人的生活进行了一番调查,得出了一个结论,形成了这样一本书:《空巢:我在这世上太孤独》。
在拿到这本书时,起初我感觉副标题“我在这世上太孤独”是不是太夸张了,是不是编辑为了吸引读者的眼球,增加销售量而起?但当我一口气读完,看到最后一篇的结尾也写着的“我在这世上太孤独”时,眼泪不禁流了下来。虽然知道并不现实,我还是迫切的想借用本书腰封上的一句话表达我当时的想法:“愿我们老去的那一天,不再独对空巢“。
《空巢》最早在豆瓣阅读上发表,由于读者众多,且推荐人数众多,由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本书关注于当代中国的老年化状况,对目前庞大的老年群体进行了调查,提出了很多问题:如老年化中国对于已经处于老年期的单独个体有什么影响?他们对当前生活的关注点是什么?在未来他们又可能会面对什么困难?有没有可能解决这些问题?老年化中国对即将步入老年、但是已经有了一定收入的中年人,对于忙碌于提高位置、增加收入的青年人又有什么影响?他们又会如何看待老年化问题,他们的关注点又是什么?同样处于老年化社会的外国社会,有没有同样的问题?他们又是如何解决的?这一系列问题有没有答案?每个人都会知道,答案一定是会有的,但我们实际上关心的是我们能解决父母面临的这些问题吗?当我们面临这些问题时,我们能够解决吗?怎样解决?
推荐每一个人找个时间读一下这本书,相信每个人都会自己的答案:从有相似状况的老年人的角度,从没有相似状况的同辈人的角度,从将要步入老年的角度,从儿女辈的角度,关注他们的生活,提前了解他们面临的问题,为未来做好准备,不再感到“我在这世上太孤独”。
《空巢:我在这世上太孤独》读后感(三):我想顽强如野草,倔强的坚强
前几年开始,总是隐隐有一种自己会孤独老死的悲观感。
我想到了死后几天才被人发现的张爱玲,想到了孤死在海外的邓丽君。人家张爱玲是一届才女,身后还有无数读者为其文字倾倒,人家邓丽君也有甜甜蜜蜜的歌声余音绕梁。我呢?我还剩什么?
如今的时代人与人之间的距离更遥远了。看似有便利的交通,飞速的互联网,可心中思念之人却未必能够相见。
和留守儿童一样,乡间、城镇街道里,也有很多空巢老人在盼望着,盼望着,盼望着和家人相见,甚至悲观到盼望着早日解脱。
书里的老杜,老了老了反而回归婴儿状态,活了几十年,最后连起码的尊严都不得。书里的老陆赌气一般的说,社会总不会让他躺着等死。……
亦舒在喜宝里说,我要很多很多爱,如果没有爱那就要很多很多钱,如果连钱都没有,那么有健康也是好的。
爱、钱、健康,想要安度晚年这三样缺一不可。
孤独老死的确也没什么,很多老人也有婚姻,有家庭,有子女,可老伴儿可能先走一步,子女终有自己的生活,人的开始和结束说到底还是一个人。
也许空巢是我们每个人都会面对的问题,这种孤独有些人甚至可能自儿时便要学着面对了呢。既然人终归要一个人走,似乎孤独老死也成了一种不可避免的客观存在。
中村恒子奶奶说,孤独老死也没有那么凄凉,起码也是不会给别人添麻烦。
这是理想状态。
能够坦然、淡定的面对孤独老死的晚年,不仅需要强大的精神力量,更加需要健康的身体。现实是,有很多空巢老人不仅患有常见的老年疾病甚至有些人生活无法自理。压垮人意志力的最后一根稻草往往都是那些不起眼的小事,这才是最可怕的。
天大地大至少能有一处地方落脚,有一角屋檐遮雨,有一堵墙可以避风,让人不至于流离失所,不至于寄人篱下。然不仅是对于老年人,能有这一方小小的安乐窝,对我们每一个人来说都是极其难能可贵的吧……
年轻时候做月光族可以说是洒脱,可都不用等老了,若是某天要拿出一笔钱救急,此刻的洒脱是否又会打脸了呢。老人看似每月生活开销不大,但要想维持正常的、安逸的晚年,说到底没钱还是不行的。日常生活要花钱,维系精神世界在一定程度上也需要一笔开支,享受晚年自由的时间更需要钱。钱这个东西,永远没人嫌它多。
还有,永远都是可遇不可求的,爱……
相爱的伴侣,相爱的子女,相爱的家人……
此情可遇不可求。
我想相信中村恒子奶奶说的,孤独老死没有那么凄凉,起码还能不给别人添麻烦。
我想相信梅萨藤女士说的,独居有失去,也是能够有获得的。
谁都别说大话,没真正到那一天的时候谁也不知道会怎么样。我不知道老去的时候会怎么想,只是此刻的我既然已然存在于此,我想能够顽强一些,如同野草一般顽强,在这苍凉又广阔的世界上倔强的坚强,坚强的生活下去,在孤独中不断挣扎直到耗尽一切永远休息。
《空巢:我在这世上太孤独》读后感(四):老年独孤,越想越疼
这是一本记录空巢老人的书。按老人的生活地点,分为乡村和城市两大部分。作者采访老人之后,会先在文章之前写一些自己对于这位老人的基本介绍和生活描述,然后把老人口述的内容,以最小的改动呈现出来。看完深感沉重,一方面是对于空巢老人们独孤的无力感,另一方面是对于自己那终将老去的未来感到无助。
被采访的老人们生活情况多种多样。有支付得起3000每月养老院的,也有每年只有几百元生活费的。有儿孙满堂母慈子孝的,也有孤家寡人狼心狗肺的。有身体健康四处游乐的,也有瘫痪在床无人照看的。大部分老人生活上孤苦无靠,每一位老人精神上孤独无依。孤独来自哪里
人到老年,经历过了风风雨雨。老来的孤独,一方面是情感得不到基本的满足,另一方面,自己也没有途径填上那漫长时间。
有一位王妈让人印象深刻。王妈为人活跃,办事利落,院子邻里邻居家长里短都愿参合,人缘很好。她有六个女儿,丈夫去世后一个人住在老院子里,退休后女儿每人每月给她200元钱,加上退休金生活惬意。
某日外出买药不小心摔跤,成为王妈生活的转折点。膝盖骨裂让生活自理有些困难,花2000请了负责做饭和清洁的保姆,这对本不富裕的王妈来说是一笔不小的支出。某天王妈在家倒地不起,幸好被保姆发现,叫了救护车送进医院。出院后保姆请假回乡,对于王妈的照顾进行的家庭会议让做惯了一家之主的她感觉自己像是一件交易,讨论的结果是每家住两个月但没法解决她白天独自在家的问题,觉得自己像是六家轮流转的流浪猫,拒绝了这个方案。
很多案例都类似如此,两口子和睦幸福的过着退休生活,突然有一天发现疾病,病情轻的自己照顾另一半,病情严重的不得不找保姆照顾,随之而来的是子女赡养的亲情问题和照顾不周的家庭问题,最终都走向精神上的孤独问题。
老两口都健康长寿的案例也有,但是也避免不了孤独。毕竟一年里和子女聚少离多,孙子也逐渐长大成人,经历了那接送放学天伦之乐的十年,大部分时间还是老伴两人在家过日子。大城市里有老年活动、社区生活,老人之间聊天可能会投机,农村里能不下地干活就是在身体上的享福了。活动回家后的时间,总是格外漫长的。日复一日,几乎完全一样的老年生活,或在夜深人静或在午后睡醒,都可能瞬间孤独充满。
自己的姥姥姥爷可以说是非常幸福的,有着够用的退休金,孝敬的孩孙,生活能自理,朋友常相伴。但还是能想象到老人的孤独。他们相伴住在130平的房子,每天生活不停在重复,幸好有手机和电视消磨时间,有我们时不时的视频通话。再过10年,疾病的出现可能让他们生活直转而下,只剩一人的话另一人的生活也很难想象。尽管明天会越来越好,但还是不敢细想,细思极恐。
自己的爷爷奶奶比姥姥姥爷还要大将近20岁。没有智能手机,没有好的视力听力,疾病缠身的老年生活可能唯一追求的就是活着。早早睡,晚晚起,自己买菜自己做,等到过节晚辈回家,享受那段时间的幸福高峰,然后归于平淡。
怎么办
面对老无所养,老无所依的无情现实,可能不仅仅需要顶层设计上出台一些好政策,也需要社会上的机构通力合作,普通人一起贡献力量。这个值得认真思考,好好再写一篇文章。用现在自己的眼光看50年后的老年时光,想想看到底自己怎么做才能和空巢和平相处。
《空巢:我在这世上太孤独》读后感(五):专访弋舟:老去就是生命在收缩
“70后”小说家弋舟从2000年开始不断发表小说作品,长中短篇均受业内肯定。但在他自己看来,拥有最多读者的,其实是一份不到15万字的非虚构作品。这份作品,有关我国的空巢老人。
2013年,一则新闻在弋舟心里挥之不去:三月中旬的一天,宜春中心城区东风大街一名九十五岁老人在家割腕自杀。新闻照片里,被救的老人躺卧在病榻之上,形容枯萎,但神情宁静。消息称老人此番已是再度试图结束自己的生命,唯一的原因,只是因其独守空巢,害怕孤独而失去了生活的勇气。
“孤独”一词让他陷入了沉思。他从来以为,相对于物质力量对于人的压迫,人类心灵上巨大的困境更为强烈地作用在生命中。“我永远在意的是,是什么,让我们的心灵都无法自已?如果说,空巢,衰老,对于我们还是未来之事,那么,孤独,此刻便潜藏在我们每个人的内心,它柔韧地蛰伏着,伺机荼毒我们的灵魂。”
在那后不久,弋舟就展开了具体的采访工作。他还带上了当时只有十三岁的儿子,利用了一切可能的时间段。大部分采访完成于2013年的暑假期间和多数周末。
2015年,弋舟将采访文稿《我在这世上太孤独》首发于豆瓣,引起23万多人次的阅读,评价高达9.4分。豆瓣阅读公号的一篇选载曾达到了全网100万+的点击量。今年5月,这份作品由上海文艺出版社再次结集推出,取名《空巢:我在这世上太孤独》。
弋舟坦言,这部书在他的写作中成为一个特例。“在某种程度上讲,它不是一本我写给无数未知读者的书,它几乎就是我和这数十位受访老人之间私密的对话,他们中的大多数不会阅读到付梓后的这本书,但这本书的真正作者,却只能是他们。”
和其他以空巢老人为主题的调查文本不同,他将这次写作聚焦在空巢老人们的“孤独”上。老人们的生活背景各不相同,但孤独的情感却是藏不住的一致。
比如,村里的老何喝酒前一定要把手机电池抠下来,因为他一喝醉就想给闺女打电话,酒后胡说八道能把闺女说哭了,他要用这个办法“管住自己”;比如,住在城里的曹姐最愿意帮邻居接孩子,她说学校门口放学时人多,挤在里面,抬头踮脚地张望,就忘了自己其实是一个孤老太婆了;再比如,李老夫妇进养老院之前把孩子们从前的照片都整理了出来,分门别类,按照年代的顺序扫描进电脑。除了养老金卡、身份证件,他们觉得唯一值得带在身边的就只有孩子们的照片了……
“这样的细节比比皆是,它们不是我作为一个小说家虚构出来的。对于空巢老人,我曾经有过一些概念上的想象,甚至还沾沾自喜地以为那是我的精神强项,但它一旦落在一个你完全无从想象的事实时,你才会发现‘概念’距离‘真实’有多遥远。”
尽管弋舟和受访老人中的几位还保有联系,但在疫情期间,他害怕主动联系其中任何一位。“我害怕听到的是一个个已经离去的消息。我们可以设想,因为疫情来了,孩子们出不去,反而多了在家的陪伴。但有没有反向的可能,疫情反而构成了更严酷的隔离?经过了这次书写,我对他们的境遇已经不敢夸大自己的想象力。”
4月30日,弋舟接受澎湃新闻记者专访。他直言,这一次采写经历也对他之后的写作产生了巨大的影响,最直接的是有了小说《出警》(编者注:该小说获得第七届鲁迅文学奖短篇小说奖),但更大的影响在于,它让他对心灵,对人性,对人际关系有了更专注的思考。
【对话】
澎湃新闻:“孤独”是这本书的灵魂。在行文逻辑上,你也是用这个词把23位老人的故事连在一起。你从什么时候开始确定,把“孤独”作为这部作品的核心?
弋舟:一直以来,孤独是我写小说时格外关注的一个角落,一个向度。为什么写这本书时格外突出它,不仅仅源于我个人遥望这个世界的方法,更基于空巢老人客观的生存事实。
我们改革开放四十年了,“空巢老人”这一社会现象也和改革历程有关。四十年前社会上也有空巢老人,他们更多受困于具体的物质生活的艰难。但今天走近他们,我们会发现物质问题已经不是首要的核心的问题,他们更多陷入了精神上的困境,这个困境的核心就是孤独。
如果我们去想象社会上的空巢老人,你可能觉得“他们只要健健康康、不愁吃穿,那问题就不大”。但问题是,一个个苍老的心灵,常常被我们忽视与罔顾。你会发现生命进程有这么一个规律,人是渐渐走向生命收缩的状态。随着岁月流逝,人的社会属性、社会身份在收缩。我们现在出门,貌似和谁都是朋友,可以干无穷无尽的活,我们能和他人发生密切的交织,但是衰老的根本方向是人和社会的交织在减少,这是所有老人,尤其是空巢老人要面临的精神困境。有的老人还保有行动能力,但是社会不带他玩了,他的心理落差会更大。
澎湃新闻:在前言中你说到这次写作对于写作能力的考验只集中于一点——如何原封不动地采用老人的话并且做到使其容易阅读。这份考验完成起来感觉如何,比写小说更辛苦吗?
弋舟:这个问题,从难和易两面,都说得通。
说它更难,是真的。在精神层面,非虚构写作面对的是一个个活生生的生命事实。尤其我面对的是这么一个真的调动起自己丰富情感的群体,怎么把他们的话转为文学表达,里面的难度远远大于我平时的文学创作。
而在技术层面,其实跟老人的聊天是很混乱的,经常有一句没一句,正在说着东呢又说西去了,里面还夹杂着很多消极的负面的情绪。那我要怎么达成一个平衡?既不扭曲老人的表达,又能做到合适的调整。这里的难度大在我还是想尽量忠实地还原他们的本意,如果没有这样一个心理要求,那就按照我的给他采点就完了。换言之,我要做的是在自我和他者之间达成平衡。我写到后面越来越流畅了,是因为我渐渐放掉了自我的预设,让他们自由表达。
换一个角度,它也真是我相对流畅的一次写作经历。日常写小说时,我难免有一种工作的念想在里头,但这次写作我突出的感受是生活本身。我写的就是这么一段时间的所见所闻、真实感知,就像面对着空气和水,那又有多少难度呢?
澎湃新闻:采访时你带上了13岁的儿子。他能理解老人说的这些吗?
弋舟:这个生命事实对于那个年龄的孩子确实沉重。但既然是人类的基本生命事实,我们需要过多蒙住孩子的眼睛吗?
在我的观察里,一个孩子参与了成人世界的工作,他也有兴奋感。一开始他的理解可能达不到,但渐渐他听进去了,他对一些老人的态度,甚至自己的神情,都有了变化。我觉得他并没有被生命的严酷蒙上阴影,他在那样一个阶段表露出某种我愿意看到的一个男孩应有的镇定。
我也给他布置了任务,就是先把我们的采访录音整理一遍,做个筛选。他做得挺好。这份任务也有我的私心在,我想它既是一场情感教育,又能培养孩子的逻辑能力。
澎湃新闻:不管对于你还是对于他,这应该都是一次特别的经历。你会成为老人,他也会。日后回想起来,可能会感慨说当时曾一起去了解,去思考生命与亲情。
弋舟:是的。工作能和我们的真实生命构成关系,那当然是最好的。不管是成功的还是失败的经验,都能够成为对生命的作用。
澎湃新闻:书里也有写到你身边的一些老人,比如楼下摆摊的李大妈,比如任兄。那在今年春节期间,这么一段大家基本都足不出户的特殊时期,你感觉老人的境况是更差了,还是更好了?
弋舟:距离我采访这些老人,其实已经过去六七年了。这些年里,我和其中几位还保持着日常的联系。有读者在豆瓣上看了作品,联系我,说想给他们家的老人找一个伴儿,搭个鹊桥。也有慈善家找过来,对这样的反馈我都挺高兴的。但坦白说,在我们这个国度里,每个老人背后的家庭都有着复杂的人伦关系的交织,有很多隐私问题。所以我总觉得不要过度介入他们的生活。
对于“空巢老人”这个群体,最近不时有新闻出来,我当然也格外关注这个群体的消息。可说实话,这段时间我没有主动去联系任何一位受访者。我害怕,害怕听到的是一个个已经离去的消息。
他们的境况或许更差了,也或许更好了,都有可能。我们可以设想,因为疫情来了,孩子们出不去,反而多了在家的陪伴。但有没有反向的可能,疫情反而构成了更严酷的隔离?经过了这次书写,我对他们的境遇已经不敢夸大自己的想象力。
澎湃新闻:当下有关空巢老人的书有不少,虚构的有小说,非虚构的有社会调查、心理指南等等。我感觉一个小说家去做非虚构文本的采写,也有小说家的底色。比如我注意到你在采访中特别注重了解老人的人生背景,特别强调个人。非虚构文本依然能体现小说家的世界观、价值观。
弋舟:对。我也写了那么多年的小说,但在我的个人经验中,每一本小说的读者可能都没这本书多。2015年在豆瓣首发时,它真的受到非常多的读者关注,很多读者留言说他们会从中看到自己亲人的影子。
面对这样的题材,小说家比起简单的新闻采写肯定有技术优势。经过了这么多年的写作训练,我们都知道严格意义上的非虚构是不存在的,比如怎么取舍,怎么转述,其实背后隐含着写作者个人的态度。没有纯然客观和冷静的写作。
那为什么还有那么多读者会有共鸣?我想,可能就是小说家的世界观得到了大家的认可——对于孤独的眺望、对于个体的尊重、对于他人保有敬意。
澎湃新闻:文中也涉及到很多单独拎出来都足以成书的社会问题,比如老人犯罪、老人再婚、老人请保姆、老人去养老院。你写到了,但并没有给出方案或者结论。你希望读者可以想到什么?
弋舟:确实也找不到具体的办法,不然它也不会是一个社会问题。个人唯一能做的就是,在有了这方面的感触后,多和家里老人说说话。
我还想表达的是,对于他者,我们不要局限在概念化的想象里。很多时候,我们是在拿自己的经验去覆盖他人,比如“我家老人挺好的,退休工资挺高的”,这其实是在想我们自己,这个月工资还行,就还能挺高兴的。很多时候,我们要多去想想他们的需要。
也有时候,我们恰恰都想到了他们的需要,又因为种种原因提供不了。有时客观条件确实不允许,包括物质能力,但更多时候源于我们心灵的懒惰。我们明白应该去做,却没有真正行动起来。
有些老人,以我们目前的生命状态去看,确实也有一些我们不能接受的行为逻辑,也不能闭眼说“就是孩子不孝”“就是孩子的问题”。但我们不要因为结果就形成了简单的对立,也想想老人为什么会怪癖,背后的原因是什么?
澎湃新闻:任兄那部分采写在这本书里是特别的存在。身为作家,他的思考特别理性。比如他说中国人到了老年是以“被人服务”为基本诉求的,但是西方社会下老人希望为社会服务,这也是他们自我存在的一种需求。
这样的思考其实在今天的青年群体中也有,它还涉及到自我价值究竟是什么。比如有些“丁克族”就觉得“养儿防老”本身是非常不公平、也不人性化的一种观念。你怎么看待有关“养儿防老”的争议?
弋舟:经过了这么多年西方文明的熏陶,年轻人有这样的想象是完全可以理解的。但必须要承认的是,文明和文明有着巨大的不同,中华文明就是一个基于血缘和家庭伦理的文明,这是根深蒂固的。在观念上,我们或许会萌生比较西式的认知,但是你依然生活在这么一个客观文化中,内心有专属于这个文明的密码在流动,所以也就有了我们必须面对的专属于中国的伦理困境。我们的生活方式、抚养方式、教育方式都可以变化,但根本性的伦理方式依然强劲,这在养老方式上就呈现出天然的不匹配。
说“养儿防老”这个传统不人性化,我感觉这样说太轻易了。中国人的客观事实是“养不完的儿子”,等小孩读书毕业,还要操心买房。作为孩子,你不能说既享受到中国式父母的资源,到下一个阶段却要用西式方法回应父母的需求。就我个人的立场来说,唯一的事实是,不管我怎么受到西方文化的熏染,我还是一个中国人。我的小孩已经20岁了,我不照样还是牵肠挂肚?我想还是在自己的文化传统里寻求我们的解决方案。
当然,对于养老问题,中国有特殊的难度,也有特殊的优势。中国的养老问题还是相当依赖每个家庭的搀扶。如果你忽视老人,起码会受到道德上的谴责。
澎湃新闻:做完这次采写,你会去设想自己的衰老与孤独吗?
弋舟:会的,人对衰老和死亡的眺望和恐惧,是避不开的。如果我们有一天真的走到了生命里狭窄的窘境,我们该如何自处?这或许也是无解。很多东西在理论上好像都能成立,但一回到一个个具体的生命,又可能都不太有效。
唯一可以相信的是什么?是我们已经预先去想象这样的问题了,至少我们现在想到了哀而不伤的情绪,想到了要保持某种生命的尊严,至少我们去想了。如果压根儿没想,遇到的时候或许会更乱了阵脚。
我们眼下的疫情,也是这样。曾经我们以为很遥远的事,如今活生生就摆在我们面前。在这样的时刻,我相信上海文艺出版这本书还是有价值的。因为人在这样的时刻,重新回到了人的基本面,重新思考人性,思考人如何自处,思考人与人之间的关系。
澎湃新闻:眼下的疫情,会对文学创作带来怎样的刺激?
弋舟:疫情之下,我相信各行各业都会重新思考很多事。它不仅是人类共同面对的一次重大公共卫生事件,也是人类面对的一场巨大的精神事件。
在人类漫长的演进中,比如1918年的西班牙大流感,当时人们的心灵感受和我们现在不一样。我们身处的时代不同了,比如这个时代我们要处理庞杂的信息量。所以这是一个专属此刻我们每一个生活在地球上的人的心灵体验,可以说是“前无古人后无来者”。书本里写的、概念里有的、我们曾经在想象中抵达的,都没有碰着它。
就文学来说,经过疫情,那些依然保持思想能力的作家的书写一定会发生某种变化。具体变化是什么,我还不知道,但是可以认定的是,一定会有不同。
(本文转载于澎湃新闻,作者罗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