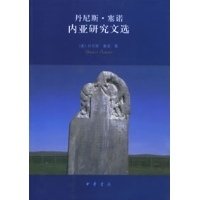
《丹尼斯·塞诺内亚研究文选》是一本由[美]丹尼斯·塞诺(Denis Sinor)著作,中华书局出版的平装图书,本书定价:34.00元,页数:480,特精心从网络上整理的一些读者的读后感,希望对大家能有帮助。
《丹尼斯·塞诺内亚研究文选》精选点评:
●与国内学者的风格差别很大,感觉逻辑和细致性还不够
●: K360.8-53/3137
●课上完了这本书也读完了,塞诺真是能把学术搞出乐趣的罕见学者,几乎是在通过文献和实物证据来推理破案。复想起来耶律阿保机的事儿,仿佛柯南大喊了一声“真相只有一个!” 篇终接混茫。
●灰常喜欢的一本,里面很多文章可以好好研究
●塞诺的研究很扎实,可以带来思考的东西很多,这本书也属于内亚史经典之作,值得一读。
●多为高屋建瓴的文章,翻译也流畅。其中《以切成两半的狗立誓》一篇,让我想起春秋战国时期的“歃血为盟”。
●塞诺(Sinor Denis)师从李盖提。作为匈牙利著名东方学家、阿尔泰学家李盖蒂(Ligeti,Louis),受马伯乐、伯希和等人的指导,李盖蒂在匈牙利的长期教学生涯,将伯希和的内亚之学移植到匈牙利,使布达佩斯大学和塞格德(Seged)大学一直是内亚史研究的重镇。
●十年后重读, 草场那篇刷新三观.
●一本教科书啊,虽然他老人家对中文翻译偏差很多,但其中探讨思路还是可以借鉴的
●201007-0803. 我是冲着罗新来看的,然后发现赛诺老先生很好玩——尤其最后两篇文。中间几篇很多语言学的成分、分析词汇源起,我跳过了。其余篇章往往针对具体现象或器物进行研究 比较容易懂XD 看完发现,从学术研究的角度,内亚游牧民族真是难搞啊,自身的语言、考古等留存非常少,要依靠文字史料的话,什么英文中文法文德文俄文日文拉丁文匈牙利文算好懂的,突厥文回鹘文古蒙古文粟特文满文通古斯文契丹文吐蕃文波斯文也算常见了,更有乌戈尔语爱斯基摩语哈萨克语吉尔吉斯语塔塔尔语库梅克语等等被作者引用。。。Orz 看完我最大的感受:还是得先掌握宏观的综述性知识啊,像我这样直扑具体讨论的,太费劲而且瞎子摸象XD
《丹尼斯·塞诺内亚研究文选》读后感(一):这其实是本比较轻松的学术著作:
作者是这个领域的大牛,但书里面选的多是些研究综述、学术演讲一类的文章,因此读起来并不费劲。这样编选的缺点就是读下来虽可见其研究思路、研究方向乃至这个学术领域的整体概况,但作者的核心研究成果却不得而知,这恐怕只能等今后其专著被翻译引进了。
《丹尼斯·塞诺内亚研究文选》读后感(二):塞诺(Sinor Denis)
塞诺(Sinor Denis)师从匈牙利著名东方学家、阿尔泰学家李盖蒂(Ligeti,Louis)。李盖蒂受马伯乐、伯希和等人的指导,在匈牙利的长期教学生涯,将伯希和的内亚研究之学移植到匈牙利,使得匈牙利的布达佩斯大学和塞格德(Seged)大学一直是内亚史研究的重镇,而李盖蒂最为得意的门生之一莫过于塞诺,正是20世纪60年代塞诺赴美国印第安纳大学教书著述,使得美国印第安纳大学成为世界内亚史研究的头号重镇。
《丹尼斯·塞诺内亚研究文选》读后感(三):帝国余烬:内亚研究的开创与匈牙利人的学术志业——读《丹尼斯·塞诺内亚研究文选》札记
纵观丹尼斯·塞诺(Denis Sinor,1916~2011)之生平与著述,可知迪奥塞吉·维尔莫什(Diószegi Vilmos,1923~1972)与霍帕尔·米哈伊(Hoppál Mihály,1942~ )两代匈牙利学者之萨满教研究传统其来有自。匈牙利人的族源认同与现代历史共同铸就了匈牙利内亚研究的学术关怀与取径:身为欧洲阑入者,马扎尔人的游牧属性及其历史文化与欧亚草原游牧文明的关系,成为近代匈牙利民族认同的重要特质;而曾属奥匈帝国与东欧社会主义阵营的经历,则为其学者承接德语的东方学、语文学研究传统和俄/苏民族学、萨满教研究传统及田野资源,提供了条件。
欧亚草原带迪奥塞吉在图瓦东北地区的实地考察(1958年8月6日至13日)匈牙利民族学家迪奥塞吉曾长期居留苏联从事学术活动,主持或进行了大量关于中亚、西伯利亚诸民族的萨满教信仰考察,多次倡议匈苏两国学者合作研究西伯利亚萨满教。因迪奥塞吉的英年早逝,其学生霍帕尔则在其基础上,将脚步迈向更遥远的东方——他先后5次赴吉林省进行满族萨满教调查[1],其专著《萨满:灵魂与象征》的匈牙利文版[2]和日文版封面,即采用了1991年8月初次到访吉林拍摄的九台满族老萨满赵云阁初入神灵附体之境的照片。[3]显然是自欧亚草原最西端的匈牙利平原投向最东端的松嫩平原的深情文化凝望——两者间民族、文化林林总总,却构成了一个渐变的光谱,其目的是为看到边界与极限(芬兰学者劳里·航科对吉林满族的民俗考察亦然)。
《萨满:灵魂与象征》,1994塞诺因师从伯希和开始接触汉文文献,从其深感汉文文献对内亚历史和语言研究之重要中,亦可见其对欧亚草原东端投来的深情目光。而在《内亚史上的马与草场》一文中,塞诺即使用了丰富的汉文文献,然而其研究最终却也落脚在匈牙利草原、马匹及马扎尔人对欧洲文明的征服问题上。马与草场的关系及马与游牧文明的关系的论述,以及在这种关系中体现出的与农耕民族的差别,使人对游牧文明有了更本质的认知。塞诺称“我却一直力图避免去追求那些‘无价值的知识’”[4],其论文集《内陆亚洲及其与中古欧洲的联系》(Inner Asia and its Contacts with Medieval Europe,1977)的命名,即可视为这一研究旨趣的清晰展示。新清史2.0世代高燕的论文《马的隐退:满人、土地开垦与江汉平原的地方生态》[5]关于清代马政的研究,可谓塞诺《内亚史上的马与草场》这一研究的某种接续。
塞诺的《突厥的起源传说》采取比较文学研究中常用的母题比较法,将《周书·突厥传》《酉阳杂俎》所述三个突厥可汗家族起源传说中各主题详尽列表以资比勘,发现其主题少有重合,并据此巧妙地否定了突厥民族族源构成的单一性,可谓与霍帕尔的比较神话学研究及韦勒克的比较文学研究中对民间故事主题及其流变的研究主张[6]多有同工之妙,却将着眼点最后归结为族源研究。(这一从神话传说入手考镜内亚民族源流的研究在近年的中国比较文学研究中仍不难看到。[7])
多语言和跨文化的思辨,是帝国文化基业,也是帝国的文化遗产。从清帝国的多语人才富俊(1749~1834,正黄旗蒙古,著《清文指要》《蒙古托忒汇集》)、松筠(1752~1835,正蓝旗蒙古,著 emu tanggū orin sakdai gisun sarkiyan《百二老人语录》),到出身生于奥匈帝国的捷裔美国学者、被誉为“美国比较文学之父”的勒内·韦勒克(René Wellek,1903~1995),其杰出的学术造诣均深受惠于此。丹尼斯·塞诺亦不例外——塞诺于奥匈帝国解体之前的1916年出生在今罗马尼亚西部的克卢日(Cluj,当时这个地区在匈牙利版图内),祖母外祖母均是奥地利人,德语和匈牙利语一样是其母语——这种多语的环境及由此培养出的语言学习能力与跨文化思辨,为其后来的学术研究——尤其是从事中央欧亚研究这一极度跨语的综合性研究,提供了条件。
1940年,丹尼斯·塞诺在巴黎首先提出“中央欧亚”(the Central Eurasia)这一后来广为学界接受和习用的历史文化概念,1943年他在法国图卢兹天主教大学开设了题为 “中央欧亚史导论”的系列讲座,以推广 “中央欧亚”这一学术概念取代此前的“高地亚洲”(Haute Asie)这一地理术语,并于1954年在其主编的《东方学与历史》书中撰写了《论中央欧亚》一章(译文收入本书),更是系统地检讨了“中央欧亚研究"的历史、方法和问题,使这一概念逐渐流行起来。在塞诺的认识中, “内亚”(Inner Asia)和“中央欧亚”(Central Eurasia)两个概念基本是可以等同互换的,其略微的差别在于前者相对来说并不十分精确而后者在使用上则略显笨重。[8]对“中央欧亚”(the Central Eurasia)的地域范围,塞诺从时空两个维度予以灵活阐释:一方面指出其空间边界常随历史的变迁而变动;另一方面又大致规划出了它的地域界限——西起黑海草原并包括北高加索﹑库班河草原﹑伏尔加河-卡马河流域和乌拉尔山,南至高加索山﹑帕米尔山、塔里木盆地南缘的山脊及内蒙古河套地区,东到太平洋并包括中国的东北三省,北抵北冰洋。[9]该区域从北到南可依次划为苔原﹑针叶林﹑草原﹑沙漠四个自然带[10],除其北部的一些例外,这一区域下民族所操语言多属乌拉尔-阿尔泰语系。[11] 他提出对内亚文化共性的研究应从各群体间上千年的历史文化交错着眼,这种共有特征体现在从艺术﹑诗歌到技术特性等诸方面。[12] 因此,中央欧亚研究强调跨语言、人种和经济生产方式的分类局限,把欧亚大陆的内陆部分作为一个整体来考察,这一深邃的学术视野,倒与迪奥塞吉、霍帕尔的萨满教研究、比较神话学研究和符号学研究理路相通(勒内·韦勒克的比较文学研究也“不遑多让”,只是其研究实践更注重作家文学层面以及西方文学内部)。
1948年秋塞诺接受剑桥大学新设立的阿尔泰研究(Altaic Studies)讲师席位——这是世界上首个以阿尔泰为名的大学教职——阿尔泰学由此渐突破并脱离传统东方学框架。1962年塞诺接受美国印第安纳大学邀请前往执教,并借助冷战期间美国国家安全需要下对区域研究的大力投入,在1966年创办"乌拉尔-阿尔泰研究系“并使其不断壮大。由于其在职期间的不断努力, “中央欧亚”概念被广泛接受,“乌-阿研究系”在其退休后改名为“中央欧亚研究系”(Department of Central Eurasian Studies)。
浪漫民族主义的历史与文化寻根意识和近代欧洲强烈的民族主义形构下,匈牙利人与芬兰人一道,将目光投向遥远的东方[13]。冷战的格局使居于社会主义阵营内的匈牙利人和离散海外的塞诺各自在继承帝国的余荫的基础上,开辟出内陆欧亚民族历史文化的学术道路。从这个意义上说,欧亚研究有远超于冷战格局和“东方学”背景的更为深远和复杂的历史动因;而如果将内亚研究、萨满教研究和比较文学研究均视为一种“跨文化比较研究”,则生于奥匈帝国解体前后的塞诺、维尔莫什、韦勒克在20世纪所推动的这三门学科,可以获得一种方法论与文化视野乃至研究内容上的交汇。这是帝国灰烬上开出的花朵,或许也是塞诺在1970年代后殖民理论兴起后,仍坚持不认为就自身而言“东方学”的使用含有贬义的原因。
奥匈帝国的解体,匈牙利诞生,这进一步催生出匈牙利人面对欧洲民族的文化寻根意识与民族主义,塞诺、迪奥塞吉的学术志业均可视为这一历史进程的学术投影。吊诡的是奥匈帝国的余烬滋养了一代人文巨匠,面对后帝国的的漫长岁月,民族国家下成长的新一代学人失去了帝国天然跨语言跨文化的土壤,其恢弘的学术气魄与跨语言、跨民族、跨文化的学术传统能否得到很好的后继,如韦勒克般兼通德语、捷克语、英语、俄语文学传统的比较文学学者的出现是否只能等待奇迹?历史在生长中,时间会给出答案。
【注释】 [1] 郭淑云:国际萨满教学会主席米哈伊·霍帕尔博士的长春“情结”,https://www.chinesefolklore.org.cn/blog/?uid-1029-action-viewspace-itemid-13851 [2] Hoppál Mihály.Samanok: Lelkek és jelképek. Helikon. 1991. 该书中译本被译为《图说世界萨满教》。 [3] 霍帕尔:《活着的萨满——中国萨满教》序 ,郭淑云、王宏刚主编:《活着的萨满——中国萨满教》,辽宁人民出版社,2001 [4] D.Sinor, Inner Asia and its Contacts with Medieval Europe, London:Variorum 1977, = 1 * roman i. [5] Yan Gao. The Retreat of The Horse: The Manchus, Land Reclamation and Local Ecology in Jianghan Plain (ca.1700s-1850s)". In Tsui-jung Liu ed. Environmental History in East Asia: Interdisciplinary Perspectives,Routledge, 2014,pp.100-125. [6] 勒内·韦勒克、奥斯汀·沃伦:《文学理论》,刘象愚等译,浙江人民出版社,2017,P34. [7] 汪立珍主编:《蒙古族及呼伦贝尔诸民族族源关系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4. [8] D.Sinor, Inner Asia: a syllabus, p5;同作者The concept of Inner Asia, in. The Cambridge History of Early Inner Asia, p2. [9] D.Sinor, Inner Asia: a syllabus, p2,pp7-8. [10] D.Sinor, The concept of Inner Asia, pp4-7. [11] D.Sinor, Inner Asia: a syllabus, pp19-23. [12] D.Sinor, What is Inner Asia, in.W.Heissig ed. Altaica Collecta:Berichte und Vorträge der Ⅻ PIAC 1974 in Bonn/Bad Honnef, Wiesbaden1976, p247,253-254. [13]芬兰学者为切断与属于印欧语系日耳曼语族的瑞典语之间的关系,将芬兰的历史文化与遥远的东方相联系,构拟出芬兰-乌戈尔语族(芬兰语、匈牙利语、爱沙尼亚语等),芬兰-乌戈尔语族与萨莫耶德语族共同组成乌拉尔语系。
《丹尼斯·塞诺内亚研究文选》读后感(四):钟焓:《丹尼斯 塞诺内亚研究文选》评述
原刊《中国边疆民族研究》第四辑,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2011年
2006年中华书局推出了由北京大学历史系民族史教研室组织翻译的目前西方学术界研究内亚历史文化的巨擎塞诺(Denis Sinor)的部分已刊主要论文,将其结集为《丹尼斯·塞诺内亚研究文选》,还附有一个极其详细的作者著述目录连同其他方面的丰富信息。这对于亟待掌握吸收国际前沿性学术成果,以求突破此前常局限于族别史治学格局的我国北方民族史学界而言,势必产生值得期许的积极影响。关于塞诺教授的治学历程与学术影响,译著的筹划人罗新教授已经在此书的前言部分作了扼要介绍,极便读者了解这位大家的学养背景,惟因体例与篇幅所限,有些地方不便展开论析。本文作为一篇学术评述,试从梳理塞诺经受的学术训练与其长期潜沿习得的治学方法着眼,同时结合对本书选收的若干代表性论作的解析,以勾勒展现战后西方学界在内亚史领域中出现的研究路数和学风上的新转向,并通过对其研究成果的客观评述来分析目前尚活跃在该领域的西方学术带头人的治学中所显现的优势与存在的不足,从而有助于我们更好地反求诸已,准确地定位自己在国际学术分工中的相对位置,同时也清晰地反照出现存于自身学术研究中的优长与弱项。最后我们还将就译文中出现的一些小疵略加讨论,以就正于本书的译者与更多的读者。
一 从布达佩斯到巴黎:塞诺的学术训练历程
就塞诺这位硕学大家的学术成就来说,无疑是眩目而辉煌的,其取得的成果早就突破了语言的隔阂而受到国际同行的广泛赞誉。他曾经受邀专门为1974年出版的《不列颠百科全书》的第15版撰写“内亚历史”的辞条;[1]他还凭借其受人尊敬的学术素养和出众的组织协调能力长期担任国际常设阿尔泰学会(PIAC)的学会秘书长,并因其为推动国际阿尔泰学研究所作的巨大贡献荣膺过学会颁发的1996年度金质奖章。当然最为重要的还是经过他不遗余力的长期工作和艰巨努力,实现了将内亚史整合入剑桥世界历史丛书撰写计划的夙愿——其标志便是由他担任主编的《剑桥早期内亚史》在1990年正式出版。[2]是书的付梓意味着内亚的历史地位在英语世界的历史书写中最终得到了承认。鉴于其作出的贡献与取得的成就,历史悠久的英国皇家亚洲学会(RAS)特地以他的名字来命名荣誉奖章,以奖励那些在内亚研究领域中成就斐然的学人。而我国学界虽然对塞诺的成就并不陌生,但长期以来对其学识的介绍多限于阿尔泰比较语言学方面,因此在不少国内学者的眼中,塞诺似乎主要是一位知识渊博的语言学家。对于上述认知倾向,我们有必要关注一下塞诺本人对其学术身份的界定。在为自己的阿尔泰比较语言学论文集所作的序言中,他鲜明地表明了个人秉持的身份认同:“我认为自己只是一位历史学家而非语言学家……,我所从事的任何研究的目的都是要有助于对一种历史过程(a historical process)的澄清,至少我自己的意图是这样的”。[3]由此可见,塞诺更倾向于将自己定性为历史学家,并以后者的使命与职责自期。但是如果我们仅仅注意到塞诺与那些通常以国别史或专门史为工作对象的历史学家的表面共性——都致力于对历史过程的澄清与描述,那么则容易忽视其人的学术个性:他所处理的历史课题往往是以精深赅博的语言学知识作为研究基础的。要相对全面地了解塞诺治史风格的成因,就不能不追溯到他早年所经历的学术训练。
根据其弟子编写的个人传记,原籍匈牙利的塞诺在布达佩斯大学求学阶段(1934-1939)主要接受的还是传统东方学的教育,受业于突厥学家内梅特(G.Nemeth)和对蒙古学﹑突厥学﹑藏学均有专精研究的李盖提(L.Ligeti)。[4]在此期间他不仅因学业表现优异而多次荣获奖学金,而且还在德国的学术刊物上发表了关于考察新疆境内佛教壁画年代的论文,这可以看作是他涉足内亚研究殿堂的入门之作。[5]这一时期塞诺所受的学术训练主要是以坚实的语言学学习作为基础,并将其与释读原始文献和历史考据紧密结合。多年以后,当业已迈入老年的塞诺在回忆其学术历程时用一种类似于新兵营的训练来比拟其年轻时所经历的语言学习的严格程度,并相信正是由于这种一丝不苟的扎实训练才使得他日后在伯希和(Paul Pelliot)的课堂上能够应对这位似乎拥有无限知识但又律人甚苛的严师的问难。[6]这里不妨指出,由李盖提院士发扬光大的“布达佩斯学派”在20世纪的西方内亚研究中一直占据着显要的地位,在他的卓越领导和出色栽培下,引领造就出了一个实力强劲的科研团队。个中佼佼者有主攻蒙古学与藏学的罗纳塔斯(A. Rona-Tas)﹑兼治突厥学与蒙古学的卡拉(Gy.Kara)﹑藏学权威乌瑞(G.Uray)和汉学家埃塞迪(I.Ecsedy)以及对北亚民俗学和通古斯研究均有独到造诣的乌瑞夫人(K.Uray-Kőhalmi)等。这批学者多在大学阶段受过系统的以语言学和文献学为基础并且旁及其他领域的多学科训练,因此既能在以后的学术发展中很快建立起各自的研究重心,同时又能切实作到彼此在学术交流上的互通有无,取长补短。他们发表成果的主要阵地就是匈牙利科学院东方研究所举办的学术刊物《匈牙利东方学报》(AOH)。可以预见,在布达佩斯受到良好学术栽培的塞诺如果当时选择留在国内发展的话,那么毫无疑问他以后必将成为该学派的中坚力量。然而主要出于对法国学者伯希和的景仰,塞诺在完成关于突厥佛教的博士论文后,未及举行口头答辩便来到了巴黎师从这位远近驰名的大师。对他来说,巴黎的求学经历预示着他以后选择的学术道路的重大转变。
据塞诺的小传,他在巴黎求学的导师除了伯希和以外,其他还有跟后者同辈的资深汉学家葛兰言(M.Granet)和当时正年富力强的戴密微(P.Demiéville)以及突厥学家让·德尼(J.Deny)等,自然其中以伯希和在学术上对塞诺的影响最为深远。塞诺晚年回忆称,正是在伯氏的课堂上,他才初次接触到如何处理艰深的汉文文献,并深刻体会到浩如烟海的汉文材料对于内亚历史和语言的研究具有何等重要的意义。而伯希和治学的最高明之处即在于他能够游刃有余地跨越那些传统上横亘在汉学和阿尔泰学之间的学科樊篱,同时攫取这两大学术领域的原始材料相互发明映证,以至源源不绝地贡献出丰硕的原创性成果,覆盖了历史﹑语言﹑宗教﹑艺术等诸多学科层面。伯氏所致臻的学识上的弘通气象和他在个案研究中表现出的惊人水准至今在西方学界仍然无人能与比肩。[7]事实上,成名后的塞诺不断向学界呼吁阿尔泰学的研究应该具有真正跨学科的特性,并提醒那些纯粹语言学背景出身的学者应当注意从阿尔泰学以外的学术园地(例如汉学)汲取有用的素材。[8]由此不难窥知伯希和的治学方法对塞诺的持久影响。而另一方面伯希和对这位初出茅庐的年青学人的研究成果也相当重视,总是立即把它们发表在他所主编的学术期刊上。根据塞诺的著述目录,这些在伯氏鼓励下诞生的论文有的属于阿尔泰比较语言学领域,有的则偏重于历史学和文献学的范畴。[9]虽然后来塞诺在把这些早期论文结集出版时并不讳言它们的阙失和不足,但这些“少作”既然能够通过伯希和的审查而顺利发表则证明尚不到而立之年的塞诺对于内亚研究的造诣业已步入堂奥了。[10]就伯希和在学术上对塞诺的启发和提携而言,塞诺终生保持了感激,并始终以伯氏的及门弟子而自豪。难能可贵的是,他对老师的尊敬并未陷入到一种无条件的顶礼膜拜中,在透视其导师治学弱点方面,塞诺的观察无疑是清醒而准确的。
1976年塞诺在为其即将于次年出版的个人史学论集《内陆亚洲及其与中古欧洲的联系》所写的序言中,首先回顾了伯希和对起其早年作品的影响,但随即话锋一转,点出在老师去世以后,他开始尝试开辟新的研究课题——处理那些对历史的进程具有重要意义的主题,并坦然表白了他与前辈们在治学上的分歧:“纵然不能宣称我已接近伯希和与马夸特在知识广博上所达到的那种程度,但我认为有时我的治学可以超出他们的研究成果,并且探察到历史进程中的发展趋势,对于后者,老一辈学人却不会去关注,我却一直力图避免去追求那些‘无价值的知识’”。[11]在晚年所写的回忆文章中,塞诺对伯氏的治学缺陷陈述得更加坦率,他明指其缺乏从事历史研究所必备的基本素质,不能或不愿去区分孰为重要与孰为次要,并为老师不能欣赏福兰阁(O.Franke)写作大型历史综述的优点而深以为憾。实际上塞诺早在追随伯希和治学的期间,就已经敏锐地发现老师的许多研究仅仅是澄清了若干无关紧要的事实而已,可以说是一种时间和知识上的极大浪费。[12]塞诺对伯希和的上述观察恰好同他对格鲁塞(R.Grousset)的名著《草原帝国》的推重构成了绝好的对照。格氏的学术擅长主要限于东方艺术史领域,对内亚历史和语言的研究显然远不如伯希和内行,但他却善于消化吸收那些一流专家产出的原创性成果,并将其有条不紊地整合组织进一部部综论性著作中,使读者在阅读过程中可以清楚地体认出历史发展的总体趋势。这部出版于1939年,从宏观上反映草原民族历史兴衰(上起斯基泰人,下到厄鲁特人)的《草原帝国》可谓格氏著述风格的典型体现。尽管因为成书时间过早而书中的不少内容已显过时,塞诺还是在文章中对其价值予以了高度评价,并在他编写的教材中将其置于综论性书目类的首篇位置。[13]
塞诺在法国的学习和工作期间还有两件事情值得一提,一是他于1942年至1943年在大学中作了以“中央欧亚史导论”为主题的六次讲座;[14]这是其尝试推广自创的“中央欧亚”(Eurasie Centrale/Central Eurasia)文化概念的开始,以取代早先那些地理探险家频繁采用,并被他的老师伯希和沿袭的“高地亚洲”(Haute Asie)这个地理术语。虽然他对如何界定“中央欧亚”概念的成熟思考最终定型于更晚的时间,但这种思考的发轫却无疑是在访学法国期间。二是他从1945年起开始编撰西方世界有关内亚研究的书目著作,其内容涉及语言﹑民族﹑历史﹑人类学等诸多方面,以便为专业研究人员提供必要的书目知识。[15]这份详细研究目录的编撰显然需要作者亲自查阅检览大量不同语种的各类学术出版物以求最大限度地避免遗漏,这对于当时正着手尝试突破传统学科分界的塞诺来说,无疑是一条拓展学术视野,增广知识储备并藉此熟悉前人研究成果的有效途径。
二 从译文集所收诸作看塞诺治史风格的特征
前面简述了塞诺的求学历程以后,下面转入对其史学研究特色的分析。最近30多年来,塞诺把他用英语和法语撰写的最为重要的著述编选为三本论文集,一本名作《阿尔泰比较语言学论文集》(Essays in Comparative Altaic Linguistics)的论集由印地安那大学出版社于1990年推出。两本内容全不重复的历史学论文集,均由在英语世界以专出学者论文选编而著称的伦敦Variorum出版社策划刊行,相继是1977年的《内陆亚洲及其与中古欧洲的联系》(Inner Asia and its Contacts with Medieval Europe)和1996年的《中古时期内陆亚洲的研究》(Studies in Medieval Inner Asia),前者所收的文章时限为1939年到1975年,后者结集的时限则为1977年到1995年。其中语言学论文集中的个别文章也分别见于两本历史学论集中。而为中国读者编选的《丹尼斯·塞诺内亚研究文选》选收的20篇译文中,原文均为英文,计有4篇来自《内陆亚洲及其与中古欧洲的联系》,12篇取自《中古时期内陆亚洲的研究》(占了该书所收的15篇英文单篇论文的绝大部分),1篇原刊于80年代初的词源学论文来自《阿尔泰比较语言学论文集》,剩下的3篇则源于近10年间出版的几种学术期刊。显然这部译文集主要彰显了塞诺在上世纪70年代后期到90年代中后期的史学成就。这一时段对于塞诺这样一位出生于1916年但直到最近仍然笔耕不辍的历史学家来说,正是学术产出的黄金时期,这二十余年间所发表的论文可以被看作是他经过漫长而艰辛的中年积累阶段之后到了老年才迎来收获的成熟之作。 [16]因此,译文集所收的论文在数量上固然仅占作者关于内亚历史文化著述的一小部分,但却大体勾勒出一位当今的西方学术权威在该领域持续攀登半个多世纪以后最终所登临的学术高峰。[17]
如果我们把译文集中所收的19篇专业论文(1篇回忆性文章除外)按照论著类型分类的话,那么可以大体上分为概论(或通论)﹑带有个案考察性质的专论和具有综合论述性质的综论。其中概论仅有一篇,即置于卷首的《论中央欧亚》;专论性质的则有《历史上的阿提拉》﹑《突厥的起源传说》﹑《突厥文明的某些成分》﹑《西方的契丹史料及相关问题》《突厥语balïq(城市)一词的来源》﹑《“乌迈”,一个受到突厥人礼敬的蒙古神灵》﹑《以切成两半的狗立誓》﹑《内亚的剥头皮习俗》;属于综论的则有《内亚史上的马与草场》﹑《北方野蛮人之贪婪》﹑《内亚的战士》﹑《略论中央欧亚狩猎之经济意义》﹑《大汗的选立》﹑《中古内亚的翻译人》﹑《中古内亚的外交实践》﹑《蒙古人在西方》﹑《论中央欧亚之水运》﹑《中央欧亚游牧帝国的历史与历史学》。专论性题目多数处理的均为内亚历史上的著名人物﹑某一民族的起源传说和内部成分﹑某种特定的精神信仰或者风俗习惯。而综论性题目则涵盖了内亚的经济基础﹑军事特征﹑权力构造﹑史学编撰以及内亚与外部世界的交流和互动等带有普遍性的课题,这批论文中征引的材料带有明显的跨地域,长时段特点。[18]像这类综合色彩甚强而又深富创见的论著显示出塞诺的关注视野已经大大逾出了伯希和的治学范围,从而成功地开辟出一大片深蕴研究潜力的全新领域。稍稍检视以上论文的标题,可见“内亚”或者“中央欧亚”的术语会时时映入读者的眼帘。由此延伸出一个问题,作者是如何定义它们的,而这对其史学研究又有何启发或者促进?
总的来说,“内亚”( Inner Asia)和“中央欧亚”(Central Eurasia)在塞诺的认识中是可以等同互换的,两者略微的差别在于前者相对来说,并不十分精确而后者在使用起来则显得有些笨重。[19]值得深思的是,塞诺一再重申,它们并非地理术语,而是文化历史概念。在1963年,他撰文称“中央欧亚”是语言学概念“阿尔泰”(Altaic)的历史对应名称。[20]另外在其授课提纲中,他又强调了该术语应该被理解为一个文化概念,至于在具体界定它所指涉的地域时,塞诺的处理又显得相当灵活:一方面指出其空间边界常随历史的变迁而变动;另一方面又大致规划出了它的地域界限——西起黑海草原并包括北高加索﹑库班河草原﹑伏尔加河-卡马河流域和乌拉尔山,南至高加索山﹑帕米尔山﹑塔里木盆地南缘的山脊及内蒙古河套地区,东到太平洋并包括中国的东北三省,北抵北冰洋。[21]而除了其北部的一些例外,分布在如此广袤区域下的民族所操语言多属于乌拉尔-阿尔泰语系的各个语言分支。[22]从生态环境角度着眼,该区域从北到南依次可以划分为四个自然带:苔原地带﹑针叶林地带﹑草原地带﹑沙漠地带,但是其中只有草原地带才能够承载起较高一级的政治体制,也只有草原才是理解内亚在人类历史上所起作用的关键。[23]因此作为一位立志走出琐碎考证,以澄清历史发展趋势为己任的史家,塞诺的关注重心自然落在了那些建立了游牧政权,并对人类历史产生了重大影响的草原民族身上。这也是为何译文集中多数论文皆围绕匈人﹑突厥﹑蒙古等主题展开的原因所在。这种研究对象的抉择实际上完全符合历史学家从大处着眼的工作通辙。
而一旦切入具体研究课题,他秉持的内亚或中央欧亚为文化概念的理念就立即得到了实践。塞诺受到20世纪上半期在欧洲曾广泛流行的文化-文明史观的影响,相信内亚与欧洲﹑中东﹑印度等其他文化区域类似,其内部同样是由若干语言和文化成分结合而成,并受到历史进程的打磨和自然环境的塑造,因此完全可以自成一个单独的文化区域,不同之处仅在于内亚的文化特征更难于被人们所洞悉。他进而提出,人们对内亚世界文化共性的考察不应仅囿于从语言分类角度衍生出的传统三分法(即把内亚的民族与文化分为蒙古-突厥-通古斯三个单位,并相信其文化的共同性源于他们有共同的祖先)的陈旧解释模式,更应从各群体之间长达上千年的汇聚交流中着眼,而且这种共有特征体现在从艺术﹑诗歌到技术特性等诸多方面。[24]塞诺的上述观念绝非空洞的理论主张,而是给自己提供了犀利独到的观察视角,并切实有限地渗透到有关著述中。譬如他在讨论阿提拉葬俗时,即点出其中的嫠面和围绕灵柩赛马的丧葬细节正是内亚世界的特有习俗,因此也构成了可以被识别到的内亚文化-文明的特征。在进行上述考察时,塞诺不仅援引了他非常熟悉的西方史料,而且也未忽略汉文史料中的相关记载,这给读者留下了旁征博引的印象。[25]同样塞诺在考察斩狗为誓和剥头皮习俗时,也是从东西方众多语种的资料中辛勤爬梳出数量可观的珍贵史料,从而为自己的立论筑就了坚实的证据基础。作者在这两篇文章的论述关键之处,还非常恰当地引证了容易为一般历史学者所忽视的考古数据,“二重证据法”的自觉运用使得作者的研究指向了全新的高度。这种熔多学科资料于一炉的恢弘气象,可以说是塞诺摆脱旧式东方学研究格局的鲜明体现。[26]当然这些成果的取得不仅得益于作者的文化史观所提供的独到视角,而且也要归功于其在求学阶段习成的处理多语种材料的深厚功力。事实上,如果作者掌握的史料不出西方古典文献的范围,而对于重要性还在其上的多语种东方史料所知寥寥,那么不仅译文集中的10篇全面揭示内亚世界各个方面的综论无法顺利完稿;甚至那些个案研究的精彩程度也要大为逊色。故前述杰克逊对塞诺独具的处理多语种材料的学力的盛赞完全是对其学识的客观评价。
塞诺的某些论文的具体研究思路和方法对我们也有令人耳目一新的启发。限于篇幅,本文略举两例。译文集的第三篇《突厥的起源传说》按说在国内读者看来,并非一个全新的题目,毕竟多年以前陈寅恪和韩儒林就已发表了主题相似的研究成果。[27]而塞诺却由于学术资讯的隔绝,对中国学者的研究竟一无所知,自不免让人遗憾。不过从另一个角度来看,正因为他完全没有读到这些论著,所以对问题的思考才没有受到既有结论的影响,这使他的考察具有自己独到的视角,某些结论也正好可以和陈﹑韩的观点相互补充,下面试作比较:
陈寅恪的论文将东西方关于蒙古起源传说的各种记载化约为四类因素:蒙古民族自身的感生说﹑从高车-突厥等草原民族吸收的狼祖故事和锻铁情节﹑西亚穆斯林文献中的希伯来人种起源传说﹑蒙古佛教徒史家所增加的印度-西藏王统世系。限于主题,其文重在论证晚期的《蒙古源流》是如何在整合了第一﹑二类传说因素的《蒙古秘史》的基础上新增藏传佛教色彩浓郁的印度-吐蕃王统世系,以形成一全新的蒙古王室谱系,故对于第三类材料仅在笔下稍带即过。[28]他在文章的开始曾以“七级之塔,历阶而登。其构造之愈高而愈上者。其时代转较后而较新者”来喻指蒙古传说的起源与发展。此后发表的韩儒林的论文完全承袭了上述思路,并进一步搜集东西方相关材料以对陈氏着墨不多之处详加论证,且对北方民族传说中的各种母题(如感生﹑狼生﹑崇拜苍色等)逐一分析,全面厘清了此类故事的发展轨迹,可谓后出转精。他们的这一认知理路适与当时风行学界的“古史辩”派提出的“古史的层垒构造说”相契合,故将探究的目光聚焦于传说故事的历时性变迁上,而对“共时性”问题却显得熟视无睹。在前一方面,塞诺的研究超出中国学者的地方不多,但是在后一点上,他的论述犹有拾阙补遗之功。
塞诺采取比较文学研究中常用的母题比较法,将《周书·突厥传》和《酉阳杂俎》所述的三个突厥可汗家族起源传说中的各个主题详尽列表以资比勘,结果发现它们彼此间只有很少的主题互相重合,据此他认为三者的差异反映了不同民族的各自传统,由此否定了突厥民族的单一性,因为一个单一的民族不可能出现多个主题全然矛盾互不重合的起源传说。他对突厥汗国族群混杂性的考察与此前他对古突厥语词汇中的外来借词研究是相互促进的,其结论均揭示了突厥汗国内部民众构成的异质性。这对于容易不自觉地以今天的民族概念来把握古代人群的现代学者来说,无疑应当引起大家的审慎反思。
译文集中还收有一篇《论中央欧亚之水运》的论文,则属于历史学与语言学汇流交叉的杰作。[29]全文可分为两部分,第一部分引用各类史料论述文献中所见的内亚民族对舟船等浮渡工具的使用。文中征引的材料在时间和空间上都显得跨度极大,充分反映出作者特有的娴熟驾驭多语种文献的能力,而且作者在文中并不满足于对相关资料的爬梳,还进一步将有关记载和各种舟船类型详加比照,以求更加精确地发掘出文献记载的价值,并通过自己的透彻解析将一幅幅栩栩如生的历史画面展示在读者眼前。显然只有对历史叙事富有精深造诣的史学名家才能如此成功地复原历史,这一点也是他在史才上超出其师辈的又一显证。
此文的第二部分,则着重于词汇学的考察。作者首先在蒐集阿尔泰语系中有关水运工具的词汇方面下了极深的功夫,就本文发表时的学科水平而言,作者汇辑的词汇可说近乎穷尽了当时语言学界所能提供的语言材料。正是在对资料充分占有的基础下,作者悉心探索了此类名词在阿尔泰语系中各语族之间的生成﹑借入与传播,并据此归纳出来源不同的语汇在后来所发生的词义衍生与转移现象,从中清理出物资文化交流的斑斑辙迹。作者由此得出了一些令人兴趣盎然的结论,如他发现阿尔泰语系中并不存在一个表示“船只”含义的共同词汇,蒙古人中最早使用的船仅是独木舟,表示桦皮船的词汇只见于通古斯语族中的各种语言等。同样他在文中所检出并讨论的大量阿尔泰语系从其他语言中所借入的船舶类词汇,也为我们考察各民族间的语言与文化的交流提供了生动的实例。总之,全文的这部分内容是作者特有的援语言入手研治历史的治学方法的精彩应用,深厚的语言学素养促使作者的治学起点远高于一般学者所处的观察平面。这对于尚待大力整合语言学研究成果的国内民族史学界来说,也是一个值得借鉴的正面例证。
三 从译文集中的某些阙失看塞诺治史的弱项
上文我们对塞诺治史的长处已有清晰的论说,且揭示了他青出于蓝的一面。但在另一方面,我们对其知识上的弱项也不必讳言。记得德国汉学家鲍吾刚(W.Bauer)在比较著名蒙元史学家傅海波(H.Franke)和他的导师海尼士(E.Haenisch)的学术工作时,曾说:“他在许多方面与海尼士比相距很远,但又在有些方面超出了后者。”[30]同样的评价似乎也很切合伯希和与塞诺师徒。首先伯希和的汉学造诣在20世纪的西方汉学家中可谓首屈一指,而塞诺仅仅是在他来到巴黎之后才初次接触到这门陌生而神秘的学科。虽然他也曾师从伯希和与戴密微学习中文,但毕竟不能流利自如地研读那些即使对东亚学者来说也非容易掌握的汉文文献,更不用说像伯希和那样能够凭借其渊博的的汉籍目录学知识,独立从原始文献中勾沉出以前不为人知的关键性史料。如前所述,塞诺的研究一旦超越个案层面,上升到整体把握内亚文化特性的综合性研究中,那么他就完全回避不了对中文史料的引用。事实上,我们看到,塞诺于此的主要补救之道,还是需要向西方的汉学著述求援。但是跟那些不精中文,只能有选择性地零散利用一些汉学成果的大多数阿尔泰学家相比,他浏览过的用西方主要语言写成的二手性汉学著述和有关的汉文史料译注的数量堪称可观,以至他对汉学书目的介绍在其书评总量中占有相当的比例。然而,研究历史的学者都知道,转引自己并不真正掌握的外文史料总是具有某种危险性,甚至还会促成比较严重的疏误。在这方面塞诺也未能例外。此外,跟运用汉文史料相近,塞诺对穆斯林史籍的利用常常也需要借助于西方语言的译本,这对他的有些研究结果同样会有负面的影响。当然一个志在全面研究内亚历史的学者还必须有能力处理其他学科如考古学和民族学等方面的专业知识,并且对前人的研究成果最好能做到穷尽似的掌握。而在现代学科分工日益专业化和精密化的今天,对于学者个人来说,要想完全具备上述条件,已经不太现实,故塞诺著述中的某些失误在一定程度上映照出“大师之失乃力有未逮”的教训。鉴于此,本文的商榷谨取《春秋》责备于贤者之意,避免进行任何学术层面之外的评论。此外,考虑到译文集所收的不少论作发表于多年以前,而某些领域的研究以后又有了新的进展,因此本文的讨论一方面尽可能以论文发表时的学术水准作为衡量评判的尺度,另一方面又对其后的研究进展稍加提示,以利于此书的读者了解较新的学术资讯。以下即按译文集的编排顺序和页码先后将有关意见列举如下,且为求慎重,对于书中所讨论的部分笔者均已事先按核了外文原文。
本书首篇《论中央欧亚》的第2页在注明辽﹑金两朝的迄止时间时,分别作辽朝(907-1125)和金朝(1125-1234)。作者此处对辽﹑金的始建年份的表述有误。如按学界的传统观点,“大辽”国号的建立根据《辽史》卷四《太宗纪下》,是在太宗会同十年(947),此前所使用的国号是契丹,虽然后者的创建年份仅有《契丹国志》的孤证,表明是在916年耶律阿保机称帝之时,但却不可能前推到907年。故塞诺以后一年份作为辽朝的开始时间,盖将阿保机称汗的时间与辽朝建立的时间相混淆。[31]而金的国号建立如按传统观点,当据《金史》卷二《太祖纪》,是在收国元年(1115)。近年也有学者认为实际以金为国号的建立时间,要晚于这一年份,但无论如何都不可能迟至辽朝天祚帝被俘的1125年。[32]
《历史上的阿提拉》(原刊于1991年)第35页在讨论青铜鍑与匈人的关系时,特申下说:“它们是典型的内亚冶金术的产品,从中国的鄂尔多斯到东欧的范围内,都可以找到。而且在新石器时代的岩画上它们已经出现了。(后略)”塞诺将青铜鍑的出现系于新石器时代的论断殊为失当,他在随后注明的资料出处是1973年出版的闵兴海尔芬(Maenchen-Helfen)的遗著《匈人的世界》(World of the Huns)中关于铜鍑的论述。按后者的书中第326-327页确实提供了南西伯利亚岩画中出现的铜鍑图象,但并未论证这些岩画的时代属于新石器时期。从岩画图象上看,这些铜鍑多数带有清晰的蘑菇状圆把手,这就给人们断定它们的时代提供了时间线索。实际上,早在塞诺此文问世以前,一位西德考古学家就已经在西方学术刊物上撰稿综述了前苏联考古学家对南西伯利亚早期考古学文化的分期研究,表明青铜鍑在当地的出现和流行是在塔加尔文化的晚期和结束期,对应年代约在公元前4世纪至前1世纪。[33]而该时段已经进入早期铁器时代,怎能断言铜鍑在新石器时期的岩画中就已出现呢?前苏联学者的断代得到近期研究结论的支持,因90年代以来两位国外学者在重新分析了上述南西伯利亚岩画上的铜鍑形态特征后,仍然倾向于维持公元前一千纪后半期的传统结论。[34]
另外文中把铜鍑归于内亚冶金术产品的提法也需要慎重考虑,首先所谓的“内亚冶金术”(Inner Asian metallurgy)一名并非一个有清晰界定的考古学习用术语,似乎只是作者基于其向来秉持的内亚文化观而创制出的概念,意在说明内亚文化区内有着统一的冶金工业传统,实际上既无法被考古学界所接受,又容易让一般读者产生疑惑。当前比较受到国际考古学界重视的是俄国学者概括出的欧亚大陆的十二大冶金技术区域(MMR)的划分,其中有七个冶金区的位置处于塞诺所定义的内亚范围中,但却拥有彼此不同的技术传统。[35]此外,如果仅仅从内亚的地理范围出发,那么至少目前还不能论定青铜鍑属于该地区冶金技术的典型产物,因为迄今我们所能找到的两件时代最早的此类考古发掘品,一件出土于北京市延庆县,另一件则出土于陕西省南部的岐山县,大致年代均相当于西周晚期。故80年代后期即有学者主张铜鍑起源于相当于后来的长城沿线区域内,而非传统上认为的欧亚草原。[36]不过在具体讨论其起源的地点和时间问题上,尚存有争议的余地。[37]要之,作为一篇发表于90年代初期的论文,由于对较新的考古资料全无措意,导致塞诺著述中的上述提法失之粗疏。
《突厥的起源传说》(原刊于1982年)第55页称《周书》完成于629年,误。据《旧唐书》卷三《太宗下》:“十年春正月壬子,尚书左仆射房玄龄﹑侍中魏征上梁﹑陈﹑齐﹑周隋五代史,诏藏于秘阁。”可知《周书》完成于贞观十年(636)。同页还将北周的建立时间注为556年,当作557年。第58页将唐朝的下限括注为930年,亦误,当改作907年。第59页称传说B记载了两位狼子:阿谤步和泥师都。按《周书·突厥传》原文作:“其部落大人曰阿谤步,兄弟十七人。其一曰伊质泥师都,狼所生也。”故狼子与阿谤步无关。第61页注1在解释《酉阳杂俎》中海神传说时,将“海”字译作英语中的“湖”(lake),并声明是受到了《周书·突厥传》中的“弃草泽中”的启发。按“海”一词在塞外之地一般均指湖泊,《酉阳杂俎》的用法与此正同,故无需借助与其毫不相干的《周书》的文句来强为牵合。有关该字的解说,可参北宋程大昌《北边备对》“四海”条:
若夫西﹑北二虏有西海柏海﹑青海﹑蒲类海﹑蒲昌海﹑居延海﹑白亭海﹑鲜水海,皆尝傍海立称矣。然要其实致,则众水钟为大泽,如洞庭﹑彭蠡之类,故借海以名之,非真海也。李吉甫辨白亭海而曰“河北得水便名为河,塞外有水便名为海”,其说确也。[38]
此外第61页以下在讨论《酉阳杂俎》中海神传说时,还应当注意到岑仲勉《突厥集史》辑录的开元十八年(730)去世的契苾嵩的墓志,志文开篇即作:“公讳嵩,字义节。先祖海女(之)子,出于漠北,(住)乌德建山焉。”岑氏最早指出其文可以和《酉阳杂俎》的海神故事相比较,并解释为初唐的突厥人中即已有此传说,以后才被由热海东迁到东突厥腹地的契苾家族所袭用。[39]虽然对于上述看法还可以讨论,但却表明塞诺在研究突厥史时仅能利用分量较轻的刘茂才之书而不知参证汇辑史料更为丰富的岑著,这在史料掌握上是有其不足的。同页在讨论射摩舍利的名称时,还据刘书,仅指出舍利是649年设置的突厥州的名字,似乎并不了解作为州名的舍利只是对当时归附唐朝的突厥部落舍利吐利的省称而已。在塞诺此文发表之后,学界对射摩的名称还原有过一些讨论,但其结论都不十分令人满意。[40]
第64-65页在讨论突厥的狼祖传说时,引用的均为汉文文献,似还应引证11世纪印度作家比鲁尼(Bīrūnī)对8世纪前期称雄健陀罗一带的突厥沙耶王朝祖先传说的记载,称其祖名为böri特勤,出生于一个洞穴中。[41]而正如塞诺所指出的,böri正是突厥语“狼”之义,故这个狼特勤出生于洞穴的传说与他所讨论的汉文史料应属于同一系统,只不过其形象已经趋于人格化。此外关于突厥语böri在更早时候的汉文文献中的出现,还应该参考卜弼德(P A.Boodberg)的两项研究,一是在他于1932年所撰的去世以后才正式刊布的《胡天汉月方诸》札记中,将曹丕《典论》论汉武帝的文句“刈单于之旗,剿阏氏之首,探符离之窟,扫五王之庭”中的符离也还原为突厥语böri,以该词与单于﹑阏氏等名号并列为由,赞同晋灼的“王号说”。[42]第二是他在正式发表的论拓拔语的文章中还指出北魏太武帝拓拔焘的小名佛狸也是böri(“狼”)的对音。[43]卜氏的以上论著均刊于塞诺此文发表之前,其论述主旨对于考辨突厥语“狼”一词在草原上的流传显然颇有助益。
第71-72页作者在讨论成吉思汗的远祖孛儿帖赤那由《蒙古秘史》中的“苍狼”形象向后来的人格化形象的转变时,使用的蒙古文史料主要是17世纪以来的清代史籍。根据他引述的材料,17世纪初期的《黄金史纲》首先将孛儿帖赤那换为人名,然后他又检出了喇嘛罗布桑丹津的《大黄金史》中出现了“天之子孛儿帖赤那出生了”的内容,并注意到同样的表述也见于另一部史书《黄册》(Šara tuji)之中。(按中文本72页的翻译有误,系混淆了两部《黄金史》的作者和名称,详见本文最后一部分)作者似乎很同意孛儿帖赤那从狼向人的转变是由于后起的佛教观念的影响,当然此前陈寅恪等人也有类似的看法。不过,在此问题上,我们不应忽略更早成书的藏文史籍的记载。撰写于元朝灭亡之前的《红史》(Hulan debther)在叙述蒙古王统世系时,首句即为:“在蒙古的君主世系中,第一位是天的儿子孛儿帖赤那。”(hor gyi rgyl rabs la dang por gnam gyi bu spor ta che)[44]而《红史》作者明确宣称上述蒙古可汗的世系材料是来自《脱卜赤颜》(yeke thob-čan),也即元朝宫廷内秘藏的历代大汗在位大事记,其中也包括成吉思汗之前的祖先谱系。在蒙元王室秘藏的史书中,《脱卜赤颜》和《史集》的来源《金册》同属一个史源传承的系统,而《蒙古秘史》则属于另外一个系统。[45]因此,成吉思汗的远祖孛儿帖赤那的“人格化”为天子早在元朝就已出现,而在元朝灭亡之后,包含了原属《脱卜赤颜》的这一片段的部分文本还继续在草原上流传不辍,并最终为晚期的《大黄金史》和《黄册》的作者所引用。塞诺的论文对此完全失考,这使他的研究结论出现了不可避免的认识缺环。我们这样评价并非是对其要求过苛,因为蒙古历史学者比拉(Š.Bira)早在60年代就在一份塞诺非常熟悉的学术刊物上发表了他对《红史》的初步研究成果,虽然其对《红史》的史源判断并不准确,以致于把孛儿帖赤那的修饰语“天子”(gnam gyi bu)当作是《蒙古秘史》中“从天降生的”(de’ere tenggeri-eče ĵaya’atu töreksen)一语的对译,但毕竟初次提供了珍贵的资料信息。[46]而在塞诺的论文发表以前,还有一位藏学家通过举证居庸关过街塔蒙古语铭文中所见的用“天子”指代元朝皇帝的用法,结合上述《红史》的表述,论证了“天子”一词被蒙元皇室运用的史实。[47]如果塞诺对这些研究能够有所措意的话,那么像文中所下的“除了《蒙古秘史》以外,好象还没有一部史书反映出苍狼孛儿帖赤那事实上是蒙古人的祖先这样一种观念,也没有什么地方将他列在蒙古谱系的开端”这一臆测即可以完全避免。另外作者在第72页把《大黄册》(Šara tuji)的成书时间误定为16世纪初期,应更正成17世纪中期(1651-1662)。[48]第73页将元朝的开始年份错系于1279年,应作1271年。
第77-78页在描述了穆斯林史籍中记载的蒙古人祖先熔山出穴经过之后,称根据拉施特《史集》,那时带领他们出山的首领不是别人,正是孛儿帖赤那,并说这位波斯史家还告诉人们,直到他生活的时代,每当蒙古人举行纪念这一事件的活动时,均由其统治者率先锤打烙铁,并使其官员为之仿效。按作者此处混淆了14世纪的《史集》和17世纪的阿布哈齐的《突厥世系》对同一桩事件的不同描写。塞诺引用的《史集》第一卷一分册俄译本的第154页以下在描述熔山经过时,并没有出现其时蒙古人首领的名称。他所指出的同书第一卷第二分册俄译本中第9页出现的孛儿帖赤那纯属误记,因该页的内容仅称孛儿帖赤那是逃往深山避难的蒙古人先祖的后代,其事迹与熔山迁徙主题无关。[49]事实上别的学者在引用《史集》以讨论孛儿帖赤那的事迹时,都没有产生将孛儿帖赤那和熔山外迁故事相联系的误解。[50]同样《史集》在描述蒙古人对出山一事的纪念活动时,也只是提到了锤打烙铁的仪式,但并未明说必须经由统治者带头执行。[51]事实上将孛儿帖赤那说成是率领蒙古人出山的首领始于阿布哈齐的文学创造,而且前述统治者率先锤打烙铁,并使其官员为之仿效的细节亦是出自这位晚期作家之手。故塞诺此处的误引导致他把晚期才有的情节归于早期的史著,并以之来讨论蒙古帝国时期的史学编撰情况,显然未中鹄的。此外作者在第78页还说根据《史集》,赤那思(chinos)就是借助七十个风箱离开山窟的那些蒙古人。按这里对《史集》第一卷第一册俄译本184页的理解有误,那里是说赤那思部落的一部分,又被称作捏古思;而后者的这一名称还可以指代另一个属于蒙古迭儿列勤部落集合中的一个参加了拉风箱工作的部落。[52]故作者此处的评论反映了他将在《史集》中属于尼伦部落集合的赤那思人与原系迭儿列勤部落集合并在熔山传说中拉过风箱的捏古思人混为一谈。
《突厥文明的某些成分(6-8世纪)》(原刊于1985年)第85页在叙述突厥兴起时,称土门联合中原王朝在522年结束了柔然在蒙古的统治。522年当更正为552年。第94页称胡峤947-953年间代表契丹人出游过一趟。按根据《契丹国志》卷二十五所收的《陷北记》中的胡峤自述,胡氏是辽朝北府宰相萧敌鲁之子萧翰的书记官,因受萧翰下狱的牵连而与萧氏的其他部曲一齐被安置到辽东的福州,福州的契丹人怜惜其遭遇,“教其逃归,峤因得其国种类远近”。故文中称其“代表契丹人出游过一趟”的提法也就无从谈起。第94-95页还作《曲江张先生文集》的作者是8世纪中期的张九龄。而据《资治通鉴》卷二百四十四,“开元二十八年二月,荆州长史张九龄卒。上虽以九龄忤旨意,然终爱其人。(后略)”故张氏在开元二十八年(740)年已卒,说他是8世纪中期人则不够准确。
第95页集中讨论了默啜突厥的问题,行文中引证了多位学者的观点,但所下的结论并不明晰,最后只是简短地表示“无疑默啜突厥是一个真实的部族,而不简单地是一个地名。”虽然该名称在汉文文献中仅于《曲江集》中出现了一次,然而根据敦煌出土的PT1283Ⅱ藏语文书,默啜突厥指的即是8世纪前半期活动于蒙古高原的组成东突厥第二汗国部落联盟体制的十二个主要部落,这就使人将其同汉文文献中经常提到的这一时期前后的北蕃“十二部”或“十二姓”联系起来。[53]考虑到该敦煌藏文文书中所揭示的十二部名单中,有的像悒怛(Hebdal)实际上是自有来源的民族,而有的如卑失(Parsil)和奴剌(Lolad)则应当说是与一般突厥人有相当差异的“别部”,故把默啜突厥理解成一个不同族群与部落的政治结合体较一个单一的真实部族(people)更为合适。[54]
随后的第95-96页又讨论了黄头作为部族名称的问题,其中提到他通过有关索引得知《契丹国志》中有三处涉及黄头室韦的地方,但因未检原书,不知它们是否和也被收入此书的胡峤的《陷北记》中的黄头室韦重合。按《契丹国志》中所见三处黄头室韦的出处中,仅有一处出自《陷北记》,另外两处则分别是在卷一的“太祖击黄头室韦”﹑卷十三《后妃传·太祖述律皇后》中的“黄头﹑臭泊二室韦乘虚合兵掠之”。第96页还以室韦曾为突厥臣民为由,推测《曲江集》中的黄头突厥即胡峤行记中的黄头室韦。这一推断证据不足,按黄头突厥见于《曲江集》卷十四的《贺圣料突厥必有亡征其兆今见状》,其中称根据从突厥脱出的契丹妇女报告,突厥汗国内部的默啜突厥与黄头突厥正各自整顿兵马,准备内斗。可是我们知道,黄头室韦的活动地带是在远离突厥本土蒙古草原的大兴安岭一带,似乎尚难断言这些僻处东北森林地带的室韦人会在作为突厥故土的蒙古草原上与默啜突厥发生直接冲突。塞诺在讨论这一问题时,仅引用了较早沙畹(E.Chavannes)对黄头室韦地望的简要注释,未能直接参考两《唐书》中对室韦各部尤其是黄头室韦的位置描述。实际上拉切聂夫斯基(P.Ratchnevsky)早在60年代就发表文章汇释了他从南北朝到隋唐时期的正史中辑录出来的关于室韦的汉文记载,其中也包括了黄头室韦的部分材料。[55]塞诺对此成果本应作到了然如胸。
第96页还评论了刘茂才对黄头一词的见解,后者认为黄头突厥是以颜色名称作为部族名字的表现,并举出了突骑施中的黄姓分部作为旁证。塞诺以“头”字未被解释为由,不赞成这种解说。国内学者也有持论与刘氏相近者,项楚在注释《昭君变文》中的“单于见明妃不乐,唯(传)一箭,号令□军,且有赤狄白狄,黄头紫头,知策明妃,皆来庆贺”时,即认为其中的“黄头紫头”或指突骑施的黄姓与黑姓。[56]此外还有学者将黄头解释为黄色的头发或者头缠黄布。[57]笔者认为,如从汉文文献出发,解释为黄姓或者黄发均于史无征,最恰当的理解还是出自陈寅恪检出的《新唐书》的《王式传》和《田令孜传》中的相关记载,这两条史料明确将“黄头”解释为黄帽。陈氏且疑唐末五代文献中常见的黄头军为胡族军队。[58]王永兴在此基础上详举了其他相关的文献用例,进一步证合了陈说。[59]联系上引变文中“黄头紫头”的用法,愈见此说信实可从。故我们倾向于将黄头突厥解释为以头戴黄帽为特征的一个突厥部落,同样的解说也应适用于黄头室韦及黄头女真。[60]
本文的第96-97页还讨论了所谓的牛蹄突厥问题,笔者认为作者的有关考察有其合理的部分,也有值得商榷的地方。作者质疑那种将牛蹄理解为雪橇的传统解释,自有可取之处。但他所持的牛蹄突厥并非神话民族,而是一个具有历史真实性的突厥部落的见解则立论不周。塞诺的主要证据仅限于前述PT1283Ⅱ藏语文书和《陷北记》都有关于牛蹄突厥的记载。除此之外,还应当补上8世纪中叶的杜环《经行记》中的一条史料:“苫国北接可萨突厥。可萨北,又有突厥,足似牛蹄,好噉人肉”。对比这三则关于牛蹄突厥的记载,可知它们的有关描述大体相合,尤其藏语文书和《经行记》均有他们好食人肉的记叙,这充分彰显了其记载的相同点,但三者在对牛蹄突厥的地理叙述上却出入甚大。藏语文书说此类人是居于突厥驳马部北面的大山对面。[61]而驳马部的大致方位是在西西伯利亚的叶尼塞河流域与鄂毕河流域之间。[62]故藏文文书中牛蹄突厥的方位当在较此更北的高纬度地带。《陷北记》对其的位置记叙则要模糊得多,仅笼统地说是跟单于突厥﹑黑车子等并在北方,基本方位似不出蒙古高原的北部。《经行记》则明指其在可萨突厥以北,按当时的可萨突厥主要活动于伏尔加河流域的中游与下游。[63]其北方主要是斯拉夫人的地域。故三者对牛蹄突厥所处方位的描述相差甚远,如果其为一真实部族的话,很难设想会出现这种难以解决的地理位置上的矛盾现象。只有将有关描写理解为针对一非现实民族的神奇传说,上述疑问才能得到合理解释。而其中所见的那些共性成分则反映了此一传说在欧亚大陆北方流传的情况。事实上,一直晚到13世纪的蒙古扩张时期,前往蒙古的西方教士还在当地搜集到了位于比萨莫耶德人更远的濒海北极地区生活着牛脚狗面人身怪物的离奇传说。[64]
作者在第99页讨论突厥九姓问题时,对那种将其勘同为突厥碑文中的九姓(Toquz Oγuz)的观点未持异议,并分析了PT1283Ⅱ藏语文书中所见的九姓突厥(Drugu rus dgu)的用法。作者认为该名称首次出现是在629-630年之间,把它定义为一个并非单一民族的部落联盟,称其名称与九姓回纥或三姓葛逻禄类似,并构成了突厥的一个特殊类别。这里首先似应区分一下作为近义名称使用的九姓与九姓突厥的不同出现时间,出现在630年前后的族称是九姓而非九姓突厥,这见于《旧唐书》卷六七《李勣传》中的传主与李靖会师时所说的一段话:“颉利虽败,人众尚多,若走渡碛,保于九姓,道遥阻深,追则难及”。《资治通鉴》卷一九三系此事于贞观四年(630)二月。汉文史料出现九姓突厥则是在《旧唐书》卷八三《薛仁贵传》中,称薛氏“寻又领兵出击九姓突厥于天山”,此事发生于龙朔二年(662)。两相比较,虽然它们内涵相近,但九姓在唐代史料中远较九姓突厥常见,故有学者怀疑《旧唐书》卷三八《地理志·关内道》所记的在燕然﹑鸡鹿﹑鸡田三羁縻州定居的“突厥九姓部落”中的“突厥”实乃衍文,更有人将文献中的“九姓突厥”均视为“九姓铁勒”之讹误。不过根据塞诺提到的PT1283Ⅱ藏语文书中的九姓突厥来看,所谓“突厥九姓”的提法确有史实依据,并非后世史官臆造或讹作。就此而言,塞诺强调该藏语文书对于研究一度存在争议的九姓突厥问题的价值是颇有眼光的。该条史料再加上1955年西安东郊韩森寨出土的《九姓突厥契苾李中郎墓志》,适足为这个此前曾在学界聚讼不休的话题判一定案。[65]不过笔者对塞诺将九姓突厥与九姓回纥和三姓葛逻禄这样的部落联盟体等量齐观的见解则持保留态度。实际上汉文史料中“姓”的含义随具体使用环境的不同而呈现出显著的差别。它有时是指代“部落”之义,如九姓回纥和三姓葛逻禄分别是由九个部落和三个部落组成的部落联盟。但“九姓突厥”则是一个比部落联盟更高一级的部族联合体,其名称中的“姓”应当被理解为部族才合适,因为九姓突厥下面包括了回纥﹑契苾﹑仆固﹑拔曳固﹑浑﹑同罗等诸多不同的族称,而且其中如回纥等下面还自分部落。故九姓突厥的内部结构远非普通部落联盟的体制所能涵盖,应当将其理解为一个因政治原因而结合在一起的多族联合体,这与前面我们论析过的默啜突厥有着一定程度上的形式相似处。
此外,作为一篇全面列举并考察突厥内部不同成分的论文,作者似还应增加对三十姓突厥和三旗突厥的考察。以笔者浅见,澄清这两例个案要比研究带有强烈传说色彩的牛蹄突厥或者史籍中语焉不详的黄头突厥﹑白服突厥更富历史价值。前者见于默啜可汗之女毗伽公主的汉文墓志铭中,志文称默啜可汗为三十姓可汗,由此产生三十姓突厥的指代范围问题。我们知道,在塞诺此文发表以前,东方学者不论,西方学者如沙畹﹑伯希和﹑鲍姆巴奇也都撰写专文讨论过这方墓志。[66]其中策格雷迪还就三十姓的组成发表过富于启发性的见解。[67]因此这一问题完全应该引起塞诺的充分重视并予以讨论。[68]而三旗突厥(üc tuγ Türük)一名则出现在8世纪中期前后记载回鹘在漠北草原取代突厥霸权的历史形势的突厥文碑铭中。1913年蓝司铁刊布了他对Sine-usu碑铭(中国学者称《回纥英武威远毗伽可汗碑文》)的译文,其中三旗突厥于碑文中两见,一见于北面碑石第8行,一见于西面碑石第7行。前者述其越过了黑沙沙漠,并详记了其随后所处的地点。后者则因三旗突厥后面的内容残缺而不知其详。[69]以后发现的Terkhin碑文中的东面碑石第7行也出现了该名称,可以与前述Sine-usu碑文相参照,具体内容也被学者作了相对完整的解读译释。[70]突厥学家巴赞在1982年还发表专文考察了碑文上与三旗突厥相关的地名的词源和方位,将其与内蒙古的大青山﹑黑山与黄河相勘同。[71]上揭诸文均是塞诺处理关本课题所不应忽视的,但他的论文竟全未涉及,不免令人遗憾。[72]
《内亚史上的马与草场》(原刊于1972年)第110页作者称929年时,党项和吐谷浑派往中原的使者翻了几翻。按此文译者已经指出该论述与作者间接引用的汉文文献不合。实际上塞诺此段论述完全引自哈密屯(J R.Hamilton)出版于1955年的《五代回鹘史料》(Les Ouighours à l’époque des Cing Dynasties)中对《五代会要》中的党项部分的译注,而作者的上述评语均不见于汉文原文和有关译文,显出于作者的误解。同页还将宋代茶马司的建立时间说成是在12世纪,这实际上是轻信了罗萨比(M.Rossabi)的有关论述。据《宋史》卷一六七《职官志七》的记载:“至元丰六年,群牧判官提举买马郭茂恂又言茶司既不兼买马,遂立法以害马政,恐误国事,乞并茶场买马分一司。从之”故茶马司的建立是在元丰六年(1083),并非晚至12世纪。
《北方野蛮人之贪婪》(原刊于1978年)第126页提到:Agathias对沙比尔人(Sabir)人在555-556年希腊-波斯战争中行动姿态的描述。按文中的希腊-波斯战争明显应更正为拜占庭-波斯战争。
《内亚的战士》(原刊于1981年)第135页将蒙古帝国时期的波斯历史学家志费尼(Juvaini)的生卒时间括注为“约1252-1261”,明显有误,当作约1226—1283,可参考波义勒(J.A.Boyle)为《世界征服者史》的英译本所作的导言。[73]第137页误将司马迁写作《史记·匈奴列传》的时间系于约公元前200年。第141页在论证内亚战士的英勇气质时,引用了7世纪东罗马作家对居住在中国边境的一支内亚民族Mukri的描述,但未对该名称作出勘同。按伊朗学家亨宁(W.B.Henning)早在50年代就已经将该名称与唐代《梵语杂名》中对高丽的称呼亩久里(﹡Mukuri)和藏语文书中对高丽的称谓Muglig以及突厥碑文中的Bökli合并考察,揭示了它们之间的联系。故东罗马史料中的Mukri指代7世纪时期割据辽东半岛西部和朝鲜半岛北部的高句丽当无疑问。[74]考虑到在塞诺的著述中,一般不把主要以朝鲜半岛为活动中心的民族划归内亚的范畴,所以这里似不宜以高句丽的情况来说明内亚的军事文化特征。
第142-143页在论述马镫的起源时,指出其并非是内亚地区的发明。这与本书前面第10页所持的中央欧亚的人发明了马镫的观点显然有别,应该说作者的新解较旧说更为可取。不过其随后所提出的一项论据却不无可议:最早的马镫图像出自朝鲜和日本,可以断代为公元4-5世纪。(按译者把原文中表示地理名称的Korea译作韩国,不可取)由于文中没有列出支持该说的参考文献,故只能推测塞诺大概根据某种二手文献的介绍方得出这一认识。在上世纪50年代,朝鲜的考古学者确实曾把高句丽时代的马镫断定为世界上最早的马镫,不过所给出的断代仅早到5世纪而已。[75]至于日本,则从未出土过5世纪以前的马镫实物。事实上,目前被断代在5世纪以前的与马镫相关的文物均发现于中国大陆,较早的一件铜制实物出土于断代相当于4世纪前半期的安阳孝民屯的墓葬中,另一件则是时代更早的长沙金盆岭西晋永宁二年(302)墓葬中所出的悬挂着马镫的骑俑。[76]在塞诺写作此文时,前者尚未出土,但后者的简报则早已问世。实际上截止到70年代末,对中国考古材料非常敏感的日本学者已经在他们争论马镫起源的论文中普遍援引了这一材料,其中如樋口隆康遂以此为基础明确提出马镫的中国内地起源论,最初可能是由3世纪后期不善于骑马的汉族发明的。[77]由于语言的隔阂,塞诺对于上述一手性中文原始报告和二手性日文文献均未能寓目,从而造成了其论说的缺憾。不过,此前乌瑞夫人的一篇讨论北亚游牧民族军事装备的法文论文中也已引证了上述永宁二年的骑俑马镫的材料,虽然她提出的马镫是由3世纪的匈奴人发明的观点尚嫌证据阙如。[78]复加上1979年出版的卜弼德文集中又披露了其生前对马镫见于4世纪时中国西北的文献证据的搜集分析,故塞诺对马镫早期出现地域的观察甚至未及汲取当时西方学界较新的成果。[79]第143页注释2在考辩中世纪时期的游牧民族中使用马镫的历史时,还下了一个令人疑惑的论断,他在反驳柔然-阿瓦尔同源论时,特地强调没有证据显示柔然和随后取代他们的突厥人使用过马镫。柔然人有无使用过马镫,目前确实因为支持材料的缺乏而难作结论。但突厥人对马镫的使用则久已为考古数据所证实。吉谢列夫(S.V.Kislev)在1950年出版的《南西伯利亚古代史》就已经揭示了6-8世纪的阿尔泰地区的考古学文化中所常见的马镫实物。[80]出土这些马镫的墓葬的主人必然有许多是属于当时业已加入汗国体制的突厥人。另外60年代前期曾在蒙古国考察的蒙匈两国联合科学考察队也在突厥时期的墓葬中发掘出了铁制马镫。[81]故作者认为古突厥人不使用马镫的观点失于武断。
第149页将匈人首领阿提拉活动的时期括注为4世纪,当纠正为5世纪。第153页曾引用司律思神父(H.Serruys)的《明蒙关系史研究之三:马市》(Sino-Mongol Relations during the MingⅢ. Trade Relations:The Horse Fairs1400-1600)中的一段史料概括,称在1437年明朝一位高官为自己辩护,否认曾用盔甲和弓箭与蒙古贡使交换骆驼。按这段史料实际上出自司律思原书第69页,事件所发生的年代是在1434年而非1437年。第154-155页在叙述传教士鲁不鲁乞的东行历程时,称当时居住有日耳曼战俘的Bolat小镇的方位不能确认。按该城的汉语译名作孛罗,在耶律楚材《西游录》和常德《西使记》中都有记载。其地理位置大致位于今新疆博尔塔拉蒙古族自治州的赛里木湖附近。此前伯希和的遗著和罗依果对《西游录》的译注对其所在的相对方位均有考察,而它们却不见于塞诺的注释中,反映了作者对前人的成果参考未周。[82]
《略论中央欧亚狩猎之经济意义》(原刊于1968年)第158页称627-628年的冬春之际,严重的寒冷和大雪造成羊马皆死,突厥陷入饥荒。为了获取食物,其可汗率兵进入朔州组织会猎。按译者已在同页注出本于《旧唐书·突厥传上》的上文原文:“其国大雪,平地数尺,羊马皆死,人大饥,乃惧我师出乘其弊,引兵入朔州,扬言会猎,实设备焉。”故原文仅说突厥人担心唐朝利用其陷入饥荒的窘境而出兵攻打他们,故才以狩猎为名义进入朔州境内,实际上是为战斗做好准备。作者的上述理解与文意颇有出入。第160页说在11世纪中国东北的女真部落中,存在着分别擅长捕捉鹿﹑兔﹑野猪﹑狼﹑雕和苍鹰的团体,并在此基础上作了更多的解说。据作者自注,其论据部分来自石泰安(R.Stein)在《通报》(T’oung Pao)上发表的《辽志》(Leao-tche)一文第99页的部分内容。复检石氏原文,可知其搜集列举了主要见于《辽史·穆宗本纪》中的从事捕猎和驯养任务的宫廷奴仆如兽人﹑鹿人﹑狼人﹑彘人﹑鹰人﹑鹘人等的名单之后,以辽代文献中女真人善于训鹰和向辽朝进献过鹿人为由,推断这些仆从中至少有一部分人应当属于女真人。故石泰安并未将上列诸类人均说成是女真人,而塞诺因为未核汉文原文,对这些人的仆从身份及其工作性质全不明暸,因此别出心裁地将其理解为女真人内部的一个个从事专业化狩猎活动的民族团体,甚至推测此类名称的来历可能与图腾崇拜或者跟相邻部族对他们的称谓有关。这就离汉文史料的本意愈行愈远了。
《大汗的选立》(原刊于1993年)第168页称根据《周书》,传说中阿史那的儿子因为跳得最高,结果被他的九个异母兄弟选为首领。按《周书》此处的原文作:“讷都六有十妻,所生子皆以母族为姓,阿史那是其小妻之子也。讷都六死,十母子内欲择立一人,乃相率于大树下,共为约曰,向树跳跃,能最高者,即推立之。阿史那子年幼而跳最高者,诸子遂奉以为主,号阿贤设。”细玩文意,可知参加跳高选拔而成绩最优者即阿史那本人,并非其子。文中的“阿史那子”即名叫阿史那的那个儿子之意,这跟诸子的意思是完全并列的。第171页则称契丹首领阿保机据说生自一道阳光,而且一出生即有三岁儿童的体质。作者此处未注史源,似根据《辽史》卷一《太祖本纪 上》:“初,母梦日堕怀中,有娠。及生,室有神光异香,体如三岁儿。”上述引文并无其出生于一道阳光之义。
第173页作波斯地理学家马苏底,按当作阿拉伯地理学家马苏底。第174页引用突厥文阙特勤碑铭的记载,说:“他们聚集起来,有七十七人。”按此处的七十七人在该碑文的各种现代语言译本中均作七十人,实际上本书前面第6页述及这段话时,也正确地引作七十人。第175页-176页在论证内亚社会存在的以相对和平的方式选举首领的现象时,以阿保机为例,称其做了九年的契丹部落联盟首领之后,被迫离任。但其后他得到机会建立了一个新的部落并迁往一富庶地区,并通过对那里的经济资源的控制,得以使其他部落也承认他的首领地位。根据作者自注,这段叙述的前半部分仍旧来自石泰安《辽志》第50-51页对有关汉文史料的法文译文,其原文见《契丹国志》卷一,称阿保机被迫离任时,对其他要挟其退位的首领说:“我为王九年,得汉人多,请帅种落居古汉城,与汉人守之,自为一部。”而后“七部许之”。石泰安然后对汉城的位置作了注释,但并未援用任何史料论证阿保机以和平方式再次取得部落联盟首领的地位,相反,在后面的第52页中他又将《新五代史·四夷附录》中所叙阿保机用阴谋手段假借与诸部首领会宴之机,杀害前来与会的毫无戒备的各部大人的故事译作法文。虽然此段记载多少带有传说性质,但阿保机通过武力而非和平的手段统合契丹各部并取得君主的地位则殆无可疑。惜塞诺对后面这部分译文未加注意,所以误以阿保机的事例来论证内亚君主以和平的方式得到拥立的权力特点。另外第176页的开始还把阿保机的卒年定为906年,当为926年之误。
第180页称在窝阔台死后,其皇后支持其长子贵由继位,而当父亲死时贵由正授命西征。按作者此说不知典出何据?或许与他对《史集·贵由汗纪》一段话的理解有关:“当窝阔台合罕去世时,他的长子贵由汗还没有从远征钦察草原中回来。[83]”这段话容易给人留下当其父于1241年底去世时,贵由尚身在军旅之中的印象。但《史集·窝阔台汗纪》却对贵由行踪作了更为清晰明确的交代:“贵由汗和蒙哥合罕在鼠年(1240)秋,奉合罕之命回去了,并且在相当于伊斯兰教历638年[1240.7.23—1241.7.11]的牛年(1241),在自己的斡耳朵中驻下了。”[84]《元史》卷二《太宗本纪》则说1240年“冬十二月,诏贵由班师”,所系班师时间晚于《史集》,又据后者记载,贵由受封之地是在位于今新疆西北部的霍博至叶密立一带,故《史集》中称其返回的斡耳朵当在此地而非蒙古本土。[85]考虑到行程距离,即使依《元史》所记,贵由在1240年底或1241年初才由钦察草原一带动身启程,也足以在1241年底其父去世之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