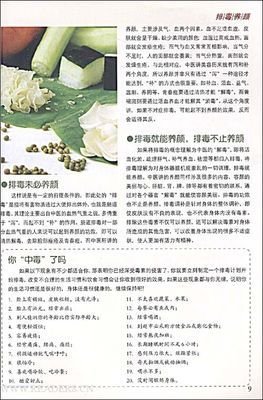
《中文解毒》是一本由陳雲著作,天窗出版出版的256图书,本书定价:98,页数:2008,特精心从网络上整理的一些读者的读后感,希望对大家能有帮助。
●我们应该如何保护粤语,不让这种优雅而悠久的语言被乱用或误解,粤语如今又是处在一个如何艰难的阶段,这本书是一本活色生香的最好教材,5颗星
●一語中的
●此书为专栏文字集结作。他认同文化价值的凝聚力,但不承认国家,因为这是党国;批驳大量内地的语句、文字实例,有些我们已经习惯的表达,用他认为适宜的方式说出,感到过于简洁,反而“词不达意”,可见我们的语文教育真是弱智;但是另一方面,过于简洁是否有约束力?合乎表达的语句会不会连生命力也没有?同时,也有些略偏激的说法,自然不可能在内地出版
●关心语言便是抵抗摧毁语言的意识形态的一部分,由于意识形态思想家与实在脱离了关系,发展出来的各种象征不是用来表达实在,而是用来表达脱离实在的异化状态,意识形态便摧毁了语言
●这个鬼才
●二〇一二年十月二十日第二遍读毕,期待再读
●極其難得的一本好書,非但重新教會大家學好中文,且深入分析了固中的文化政治社會問題,為我輩學習殖民地中文的一代,以及被愛國河蟹另類殖民的下一代「解毒」。雖然我也並非完全同意作者所有觀點,但我確實推介過不少學生去讀這本書!
文字、文言、文化,浩浩荡荡几千年,字形、字体、语音、语意有几曾有过一成不变的道理?本书说是解毒,不如说是卖弄学识兼有怀旧。
语言为工具,与锤子镰刀无异,若是把工具当大神膜拜,强赋所谓精神文化,未免搞笑。
诸君自重。
《中文解毒》读后感(二):只缘身在此山中
如果不是这个“大陆外的学者,大陆人恐怕很难发现中文语言的毛病,,正所谓旁观者清,香港同为汉文化圈,但幸在说不同的中文,甚至用的是不同的中文,又同英文世界近,比较之下,容易发现大陆变异的中文毛病,如此系统地总结出来,不知陈云用了多少时间。作为大陆人看了深感赞同,并且一身冷汗,语言竟可以腐化,垃圾化成这样,不看不知道,还吓一跳,可以肯定,当代白话文的变异,与特珠的意识形态,和单一的言论环境直接相关,其实,何止词汇,现代中文的表达很有问题 ,写文章说话甚至思维,都有一种深深的思维定势和官调。一些固定的句式,往往脱口而出。脱笔而出。完全是词不达意,。…。…。…。…好的语言应该是简洁,并口由心生,我笔写我口。
《中文解毒》读后感(三):文化壁垒
正如作者所言,本人作为大陆语文教育的产物,对于语文的感受力却已有钝化,故书中提到的多处大陆词语的使用问题和简化后的字形意义的曲解,我都无大感受。但此书还是给长时间生活在大陆的我打开了一扇窗,有益了解除大陆外的语言环境对于汉语的使用和理解。
作者极其反对共和国建立后的字体简化和普通话的普及,这在实行几十年后的大陆,同样遭到了各方人士的怀疑和要求改革的呼声。而更让作者感到危机的是香港的大陆文化侵蚀,几乎是随着政治经济的强势随之带来的。文化语言已不再是独立的个体,它被政治经济体所控制,并且绝不带有人文气息。这确实可以同时说是成功学的副作用,财富权力被人类崇拜和疯狂追求以致病态程度。
而同时本书带来的另一个命题是:知识的普及化与精英化。很难说明孰是孰非,本书亦是强烈的作者自身感情色彩。大众也不过是岁月长河中的一滴水……
《中文解毒》读后感(四):一毒既解,又中一毒
此书的副标题是“从混账文字到通顺中文”,一言以蔽之,就是要教人们如何写出清晰可读,符合国人阅读习惯的文字。书中,陈云鞭笞了洋化和赤化的中文,前者的典型代表是以英文文法来写中文句子,譬如表达“需要文学馆”这一句子,却写成“香港需要一个文学馆”,英文的不定冠词a怎么甩也甩不掉。后者的代表则是无故言重,譬如所谓“强烈谴责”和“高度赞扬”,“谴责”一词本义语气甚重,加上“强烈”之后反而削弱了词汇的表达能力。封底的文字首句,陈云就作出质问“什么时候‘骄傲’变成褒义词?”骄傲一词,本是贬义,今天却被当做“自豪”,殊不知还可以使用“荣誉”、“光荣”等词。
在书中,陈云毫不留情地批判了时下不合法度的“伪冒中文”。对于人们用英文文法写中文句子,以及用中文句式写英文句子的现象,他称此为“东不成,西不就”。究其原因,就在于脑袋僵化,思维堵塞,要解此毒,需得“语理清晰,思路通达”。
先生之言,确是一语中的。但细看之下,鄙人却发现作者犯了双重标准,对一众美言一概收下,却不考量其含混和暧昧之意。
譬如,马家辉对其的赞言“文笔犀利,思路清晰,把香港文化放进中国文化历史以至国际气候的大格局下拆解、检视、批判、珍惜,硬手段,软心肠,展现了知识分子的功力和气韵。”
所谓“文笔犀利,思路清晰”因指向明确,因此无需作说明,其意义也甚是清晰。但所谓“把香港文化放进中国文化历史以至国际气候的大格局下拆解、检视、批判、珍惜,硬手段”,却是语意暧昧,何为“国际气候的大格局”?所谓把香港文化“拆解”,又是一奇怪言论,分析而已,何须拆解?“把香港文化”一句后接“拆解、检视、批判”等词本也无大碍,但再接一个“珍惜”,就显得不伦不类了。中文何曾有所谓“把......珍惜”的说法?这显然是英文构句的被动语态,强加于中文句子罢了。
再举一例,罗耕写道:陈云的批判就是要拨乱反正,教大家认识何谓中文。读陈云文章,得到的不单是知识,而是学养;从陈云身上,领略的不只是道理,而是人格。
从语意上看,罗耕无非是想拍马屁,称赞陈云才华超众,品格高尚,本是递进的关系,却错用了转折关系词。“而是”当用“更是”,这样才能恰当地表达进一步的拍马屁。
然则,苏真真的的溢美之词更是用词不当,先生却对此视而不见,也实在叫人费解。“陈云的作品,狠狠地充实了我们这些无知的最后一代香港人的语文内涵,为我们注入了一支强而有力的文化补充剂。”
所谓“狠狠地”,当属无故言重,空有花架子,却无实意。“我们这些无知的最后一代”更是怪调,自知无知便可,何须牵连大众?“最后一代”也即“遗民”,但又不便明说,只好硬憋个“最后一代”。“为...注入...强而有力的...补充剂”陈云在书中花费诸多笔墨来批判此等程式中文,却又默许苏真真的推荐词,这又是怪事。
上述三例,其实也并非大问题,凡人皆喜欢听美言,这也是情理之中。然则,此书蓄意复古,却是得提防和注意的。遍览全书,之乎者也之言甚多,以今日文化传播角度来看,甚是累赘和迂腐。陈云所称的纯正中文,特指唐文,也即所谓正统中文。日常白话不能入文,更莫说市井之言了,凡事需“乎、焉,哉、也”一番,方可称之为中文。洋化及赤化中文自是毒物,然而,语言复古也不见得就是良方,剂量过了头只怕是为祸人间了,所谓过犹不及,便是此理。
上述种种,并非要贬斥陈云,事实上,笔者对其作品的评价甚高,就笔者所见,《中文解读》和《执正中文》当属佳作。只是,厚古薄今也实属不必,适当疏导便可。
《中文解毒》读后感(五):不认同书里诸多观点,但开始审视自己的中文使用
大概说了什么?
陈云对香港中文被洋化赤化非常痛心,英式中文横行,音节贫乏的北方普通话侵蚀南方语言,劣质简化字切割传统。陈云鼓励大众「养护」中文,警惕官方用词的变更涉及的政治概念与公权力的更迭。我觉得有道理吗?
支持作者所说应警惕官方用词以及「养护中文」的倡议;认同对简化字方案粗劣的判断,不认同作者对简化字日常使用上劣于传统字的评价;认同推行普通话是专制行径,但我觉得这是必要之恶,当然推行到禁方言的地步肯定是不正义的;不认同作者对北方普通话的各种看法,如因北方话音节少所以复合词多是一种弊病。
部分章节主要内容
00 自序
香港中文受到英国殖民者和大陆共产中文的影响(洋化赤化),遣辞用句非常糟糕,冗长的洋化表达取代中文原有的简洁表达,八股中文取代固有雅词。
01 程序
民间自行翻译外来词或是改变原有词用法是无可厚非的风俗变化,但官方的用词变更涉及政治概念与公共权力的更迭,应当警惕。英国殖民香港时在公共用词上花费颇多心思:如「市民」替代中国的「人民」与民国的「国民」;「政府」、「官立」取代「国立」、「国家」、「国民」;「开埠」取代「殖民」……
02 问责
从彭定康使用「问责」一词开始例举香港政府用词英译中的合理与荒唐,得出目前在香港法律条文的撰写上中文只是英文寄生、翻译乱象频生的遗憾结论。
03 救灾
「天灾」「灾难」到「自然灾害」的转变是信仰清洗。共产中文的目的是把话语军事化,而军事轶序是最稳固的社会轶序,所以救灾变成抗灾、防震变成抗震。
06 文癌
要想「养护」中文,必先认识到有哪些表达是洋化中文,比如用中式的「或将」代替洋化的「不排除」、「保留……的权利」。
08 官腔
官腔是因为北方官话同音字多,习惯用复词,但粤语音节丰富,不必滥用复词,应发挥汉字简练的特点。
10 正体
简化字造成不便的例子包括将不同姓氏合并、无法区分「髮」「發」,最大的恶在于强行规定字的特定写法,抺除了简正并存,简化利书、繁化以辨义的便利。
现代国家需要标准化,但对于复杂的中国文字,草率标准化弊病太多,「刀削面」这样的词语太触目惊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