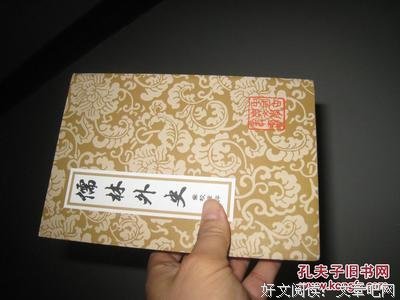
《儒林外史汇校汇评本》是一本由吴敬梓著作,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的平装图书,本书定价:76.00元,页数:782,特精心从网络上整理的一些读者的读后感,希望对大家能有帮助。
●多少衰飒,多少悲哀,一并径直写去了,就见得天地之大与人间之难。
●吐槽神作啊!!!@夜月生 里面大量的点评其实就是古人的弹幕吐槽啊!!!
●叙事回环:刘震云《一句顶一万句》得于此乎?
●正身以俟时 守己而律物
《儒林外史汇校汇评本》读后感(一):读后感
本书通过白描的写作方式向我们描述了科举制度下古代知识分子的生活状态,书中人物故事众多,那么接下来我想斗胆评一评我心目中的各种之最。 书中最让我感觉舒服的人物有虞博士(书中第一人) 王冕(高士) 鲍文卿/马纯上(品格)最表里不一者匡超人(前后差别忒大,只能说他其实本来就是那种人前期种种是装的)杜慎卿(开始以为是名士之风后来就…),最可恶者牛浦(顶了牛布衣的名儿老牛最后也没回到家乡),最矛盾者杜少卿(说实话我对他的识人不清很生气但是对他对于夫妻、迁坟二言论极为喜欢),景色最好者杭州(通过马纯上的眼睛让我领略了它的烟火气)和南京(古都气象),最可惜鲍延玺(身为鲍文卿养子一点儿好的品德没学到),最孝者郭孝子(一个纯字就可概括这位老兄),最唏嘘泰伯祠(大祭时的盛况对比几十年后的衰败,颇物是人非),最喜欢的一句话(世情看冷暖,人面逐高低),几对兄弟中最喜欢余持余特…… 比起各位知识分子,我更喜欢雇王冕的秦老头看坟的邹吉甫甘露寺老和尚开米店的卜老爹亲家牛爷爷,他们朴实善良可爱,这些身处社会底层远离名利场的人。 其实这书我看到鲍文卿死后就不喜欢后面的情节了,总觉得像拳头打在棉花上,后面的故事没前面好看了。 通常我们去评判一个人,好坏是最简单的标准。书中的人物各有各的不足,恰恰因为这种不足显得极为真实,就像你我身边的人一样。 @苹果
《儒林外史汇校汇评本》读后感(二):《儒林外史》核心人物之王冕
王冕是《儒林外史》中登场的第一人。对于一部小说而言,最难写的就是开头,小说的开头往往都暗藏玄机,且不论现代小说对完美开头的孜孜追求,单是中国古典小说的开头,大多字字珠玑,别有深意,并且喜好以诗词开篇。《儒林外史》亦是如此。
王冕是全书中作者最倾心、最具有人格魅力的人物之一,和杜少卿前后辉映,犹如两座山峰,拱起了整本小说。《儒林外史》中的反面人物众多,与对王冕杜少卿等人的推崇相比,吴敬梓无疑更重批判,而对众多腐儒昏儒的批判则更显出王冕的出场在整部小说中极其关键的作用。我觉得,王冕之所以被置于全书之首,盖在于王冕犹如一面清镜,站在队列最先,其身后的一干儒生次第经过,王冕的高洁正映衬出其后众多出场者低劣的人品和污浊的心灵。王冕仿似一杆标尺,衡量出众人的蝇营狗苟。
当然,王冕的出场的作用绝不仅仅是为了“对比”。这实际上是一个在对比中双向互动的过程——每出场一个反面人物,如范进,他们身上的某些弱点便在王冕几近完美的人格魅力的照射下凸显出龌龊,同时,他们的龌龊也加深了我们对王冕的敬佩,于是,几乎每有一个新人物出场,王冕的圣洁便加深了一层,王冕的人格并非只在第一回中被表现,其后的每一回都可以看做是对王冕人格的隐性描述。比如,周进欲撞死在贡院,表现的是其对功名的执着,而这正好映衬出王冕的超然,所以,吴敬梓在描写周进范进一干人的同时也更清晰地描摹出王冕的画像。王冕就像泉水之源,清澈甘洌,而其下游之水则清浊不定,但每一股细流都源于王冕,都能够在王冕这里找到一点影子。所以,王冕差不多只能出现在小说的开头,甚至只能是小说中出场的第一人,王冕若是在小说中部抑或后部才出现,则这种“正本清源”的安排就荡然无显了。
具体摹写王冕的章节只有第一回,但王冕的身影却贯穿全书,闪动在所有的五十六回之中。
《儒林外史汇校汇评本》读后感(三):微驳《儒林外史》“虽云长篇,颇同短制”
“……惟全书无主干,仅驱使各种人物,行列而来,事与其来俱起,亦与其去俱讫,虽云长篇,颇同短制;但如集诸碎锦,合为帖子,虽非巨幅,而时见珍异,因亦娱心,使人刮目矣。”
——鲁迅 《中国小说史略》
上边是鲁迅先生评述《儒林外史》的一段话,几乎已成经典论述,常被征引以说明《儒林》的结构特征。
鲁迅看得还是比较准的,但我认为这段话尚有可商榷之处。
《儒林》一书确实没什么“终极目标”,不像《水浒》要集齐一百单八将,不像《西游记》里师徒众人专心打怪取经,不像《红楼》绕着宝玉黛玉宝钗等人转。《儒林》诸多笔法出自《水浒》,此点前人多有指摘,不论。单从结构上说,其实两本书都有一个情节的高潮——《水浒》是公布英雄排行榜,《儒林》则是泰伯祠大祭。《儒林》第三十七回,泰伯祠大祭,在此之前,吴敬梓已尽述参加祭祀的诸人之事迹,这部分可算是全书的腰身(头部自周进范进起,王冕独为楔子,自不必说;泰伯祠大祭后的郭孝子、萧云仙及市井四奇人可算为腿脚)。所以,《儒林》确实没有可以统领全书的大事件,但说它“全书无主干”似乎也不准确。
鲁迅先生认为吴敬梓“仅驱使各种人物,行列而来,事与其来俱起,亦与其去俱讫,虽云长篇,颇同短制”。表面上看,《儒林》确乎有这种特色,但是,《儒林》中的人物和情节往往是前后勾连,互相映衬的。
我以前写过一篇评论,说“王冕之所以被置于全书之首,盖在于王冕犹如一面清镜,站在队列最先,其身后的一干儒生次第经过,王冕的高洁正映衬出其后众多出场者低劣的人品和污浊的心灵。王冕仿似一杆标尺,衡量出众人的蝇营狗苟。”我现在仍然是这么认为的,若没有王冕、虞博士和杜少卿等人,匡超人之流如何能显其低劣。
黄小田为《儒林》所写的序中尝言,“是书亦人各为传,而前后联络,每以不结结之。”可谓深得此书之妙。
第二十三回回末天二评曰:“写牛浦、匡超人往往相对……”其实《儒林》中这种前后对比的笔法实在不可胜数。若真将其视为“短制”,只看到一个故事或一个人物形象,可能就会错失吴敬梓的一片苦心。
本书书末附有陈独秀和钱玄同为亚东版《儒林》所写的序言,现在看来实在有趣得很。比如陈独秀写道——“《儒林外史》之所以难能可贵,就在他不是主观的、理想的,——是客观的、写实的。”钱玄同则认为《水浒》和《红楼梦》中都有黄段子,而《儒林》“没有一句淫秽语”,所以是“青年学生的良好读物”。
此外,鲁迅、陈独秀和钱玄同在评述《儒林》时都提到的一个情节是——王玉辉劝自己的女儿殉夫,事后又觉悲伤。由此亦可窥见五四时期思想的一个侧面。
(补充一下陈独秀的评论,以飨诸位朋友:“这一段文章(指王玉辉劝女殉夫),很看得出吴敬梓对于贞操问题,觉得是极不自然的。”)
《儒林外史汇校汇评本》读后感(四):二十一回~二十五回读书笔记
二十一回
内容概要:
牛布衣死后停柩甘露庵,留下诗稿一卷。在庵中读书的牛浦郎撬门撬锁,偷出诗稿,刻了印章,冒充牛布衣。
牛浦郎的爷爷牛老儿和邻居卜老爹聊天,为牛浦郎和卜老爹的外甥(孙)女定下亲事。甘露寺的老和尚因故人九门提督齐大人之邀进京,临行前叮嘱牛浦郎帮忙照管甘露庵。
牛家小店被牛浦郎经营不善,牛老儿一气而病,一病不起,撒手人寰,卜老爹帮忙照料一切后事。牛浦郎夫妇无钱可用,典当房屋,卜老爹让他们搬进卜家居住。
新年之际,卜老爹怀念死去的牛老儿,去亲戚家拜年喝酒,被侄女硬劝吃了四个糯米团,伤心+受风+消化不良,病入膏肓,于病中见勾魂传票。
小评:
1.牛浦郎先是撬门撬锁,一派小偷行径,后读到牛布衣诗,不为诗意所动,心之所系维以诗为结交权贵之途,生出冒名之想,偷窃行骗,全无礼义廉耻,本性卑劣。
2.卜老爹的两个儿子叫卜诚、卜信,谐音不诚不信,但于后文尚未看出二人十分不诚不信之做派。
二十二回
内容概要:
卜老爹终于一病不起,两位忠厚长者相继去世。
董孝廉瑛闻牛布衣之诗名,在甘露庵寻人不至,却被冒充牛布衣的牛浦郎(此时已改名牛浦,下同)邀至家中。牛浦要二位舅子帮忙洒扫庭除,掺茶倒水,并于席见有折损之语。
董瑛走后,牛浦与卜诚、卜信因席间礼数起了争执,居然闹到要告官,在县衙门口遇到郭铁笔劝开。
一气之下,牛浦出走,欲往淮安府安东县投奔董瑛,于南京往苏州的船上遇见阔客牛玉圃。牛玉圃吹一通大牛,见牛浦是本家,遂让其认自己做叔公。
船至黄泥滩,有一段插曲,牛玉圃携牛浦上岸行走,在大观楼碰见故人王羲安,同桌吃饭叙旧。本以为王羲安是读书人,却不料是个龟公,因为带着读书人才能带的方巾,被两个油胸口和破袖子的秀才饱以老拳。
行至扬州,二人到大盐商万雪斋处,书中对盐商家之阔绰描摹一番。万雪斋、牛玉圃、牛浦三人谈话,牛浦被大场面惊得说不出来话来,后又跌在水池里,遭牛玉圃大为嫌弃。
小评:
1. 卜家对牛浦有大恩,牛浦不图为报,反想借董县令之名“吓一吓卜家兄弟两个”,忘恩负义之徒;老和尚托牛浦照管甘露庵,却几乎被牛浦当个精光,所托非人,于牛浦郎之无耻又添一笔。
2. 牛玉圃在船上的长随、饮食,全从牛浦眼中写来,艳羡之情溢于言表。
3. 牛玉圃与龟公叙旧,龟公挨打一段,没有写到牛浦,却全被牛浦看在眼中,此时牛玉圃到底是什么样人牛浦心中早已料定。
4. 此回有从牛玉圃王羲安交谈中提到齐大老爷,有提到万雪斋堂上匾为两淮盐运使司盐运使荀枚所书,又从牛玉圃万雪斋谈论中提到国公府的徐二公子。三人后文不知是否还有出场。
问题:
1.文中卜诚道:“姑爷,不是这样说,虽则我家老二捧茶,不该从上头往下走……”所以捧茶到底是怎么个捧法?怎么叫“从上头往下走”?
2.牛玉圃心大,对初见面毫不知情的牛浦当下就认作侄孙,并带在身边,后文吃亏上当全从此来,为何当初如此轻率?
二十三回
内容概要:
牛浦落单,与子午宫道士于茶馆中闲谈,道士说破万雪斋底细,原是程明卿家的小司客,发迹后娶翰林女儿(于婚礼上还给了程明卿一万两银子),平生最忌人点破他的出身。
牛浦郎因此得计,捉弄牛玉圃,牛玉圃不知是计,在席间当万雪斋面道程明卿是他“拜盟的好弟兄”,与前文介绍王羲安同。(席间还有徽州的两个盐商,一个姓顾,一个姓汪)万雪斋发怒,借王汉策之手侮辱赶走牛玉圃。牛玉圃于丑壩饭店跑堂口中得知万雪斋的底细方知事情原委,在苏州寻得帮助万雪斋找雪蛤的牛浦,剥光衣服,暴打一顿,丢在粪坑边。
牛浦被黄客人所救,于船上害痢疾,丑态百出。二人齐到安东县,牛浦停妻再娶,娶黄客人四女儿为妻。安东县董县令瑛升任,替任的是向知县。董知县到京师遇到已升任主事、牛布衣的故人的冯玉琢,冯玉琢命管家带书信和银子给牛布衣的妻子牛奶奶,牛奶奶开始寻夫之旅,于甘露庵寻访不见,在郭铁笔指点下启程安东县。
小评:
1. 万有旗,是盐商的旗号招牌。弄窝子,是贩卖私盐。雪蛤,学名东北林蛙,因其在冬季冬眠五月之久故此得名,有“滋阴益精,养阴润肺,补脑益智”。
2. 这两回“方巾”之事多有提及,三教九流各色人等都想混入其中,“方巾”魅力很大。
3. 牛浦见盐商家大场面吓得说不出话,却与道士侃侃而谈,更胡诌董县令待他骑驴上堂,咯噔咯噔,银子数目细至十七两四钱五分,殊为可笑;后于黄客人搭救之时信口雌黄,随手编来,全然不似万雪斋家缩手缩脚之模样。
4. 安东县子午宫的道士、丑壩饭店的跑堂,皆知万雪斋底细及心事,且逢人便讲,随口就言,一者人之八卦本性,二者万雪斋在地方上待这些人应该不怎么样,否则多少为其掩饰回护些。
5. 前文匡超人未尝不孝,偏有个景兰江来教他变坏,牛浦本性就坏,偏有个牛玉圃来又来教他带他,小妖怪出场总有个老妖怪来带一带。匡超人于船中遇郑老爹,后娶郑老爹之女,又停妻再娶;牛浦于船中遇黄客人,停妻再娶黄客人之女,两相对照。
问题:
董县令与牛浦相见多次,并未识破其不会作诗,不知是董县令不懂事,还是二人只是泛泛而谈未言及诗,还是牛浦掩饰得好?
二十四回
内容概要:
无赖石老鼠借牛浦停妻再娶事向牛浦讹钱,闹到安东县衙,被衙役劝开。
牛浦回到家中,见牛奶奶与妻子撕扯,牛奶奶认定是牛浦杀了自己丈夫牛布衣后冒名顶替,后又闹到县衙。
向县令坐堂,审案三件,一者“为活杀父命事”,是个招摇撞骗的和尚;二者“为毒杀凶命事”,是胡赖状告医生陈安开错方子让自己哥哥跳井;三者“为谋杀夫命事”,是牛奶奶状告牛浦。向县令认为是牛浦只是与牛布衣同名同姓,谋杀牛布衣证据不足,被牛奶奶纠缠不过,派衙役带牛奶奶到绍兴县衙处理。
向知县因牛奶奶的案子被人告到崔案察处,被崔案察门下戏子鲍文卿求情所免,原来向知县有作曲之才,鲍文卿从小学的就是他的曲目。崔案察允了鲍文卿的求情,将鲍文卿送到向县令处,并附书信将求情之事告予。向县令感激不尽,与银相赠,鲍文卿坚辞不受。
崔案察病故,鲍文卿回到南京。鲍文卿是“世家子弟”,世代唱戏,祖上是梨园行中有德望的人。鲍文卿到茶馆中寻同行,碰到故人钱麻子,二人闲话之中,又遇到黄老爹,谈及一些南京地方上人与戏子交往之事。
小评:
1. 黄老爹之浩然巾,帽后有大披幅,相传为孟浩然所戴而得名。
2. 乡饮大宾,即“乡饮宾”,乡饮酒礼的宾介。乡饮是古代一种庆祝丰收尊老敬老的宴乐活动,一般乡饮都选德高望重长者数人为乡饮宾,与当地官吏一起主持此活动。“乡饮宾”又有“大宾”(亦称“正宾”)、“僎宾”、“介宾”、“三宾”、“众宾”等名号,统称“乡饮宾”,其中“大宾”(正宾)档次最高,由皇帝钦命授予。
3. 前二十几回文龌龊腌臜之辈几多矣,不意一知书达理洁身自好之君子鲍文卿,出自戏行之中,比所谓名教中人不知高出多少,两两对照,更觉可贵。
4. 前文已至牛奶奶寻夫至安东县,偏又写一石老鼠,旁出一笔;后向县令审案,杀父、杀兄、杀夫,骇人心目,以为件件人命攸关大事,结果都是荒唐名目。二者皆是小说家笔法,文笔摇曳,情节曲折。
二十五回
内容概要:
鲍文卿找到一位倪老爹修补乐器,言谈之间得知原来倪老爹是个老秀才,半生潦倒,以修补乐器糊口,本有六个孩子,死了一个,因家贫卖了四个。鲍文卿听罢惨然,商议买下倪老爹的六儿子倪廷玺做义子,两家结为通家之好,倪老爹感激不尽。
倪廷玺改名鲍廷玺,倪老爹过世,鲍廷玺依旧尽孝。
杜老爷家邵管家让鲍文卿的戏班为杜老太太七十大寿唱堂会,后来遇到已经升任知府的向县令。向知府对鲍家父子照料有加,并叮嘱让其到安庆府找自己。鲍文卿在南京去安庆的船上碰到两个书办,二书办欲以五百两银子请鲍文卿为两件事说清,鲍文卿拒绝并晓以大义。
鲍文卿父子来到安庆府衙门内,又被向知府好生款待,向知府为鲍廷玺做媒娶自家王总管的女儿。
忽闻府院差官来到向知府堂上,众人传闻要摘印夺官,忽生一笔,平地波澜,勾人眼目(看后文方知是一场虚惊)。
小评:
1. 本回中向知府云为王总管小儿买了一个部里书办,五年考满便选一个典史杂职。书办是管理文书的小吏,典史是原本职责是“典文仪出纳”,明清两代均有设置典史,是知县下面掌管缉捕、监狱的属官,属于未入流(九品之下)的文职外官,但在县里的县丞、主薄等职位裁并时,其职责由典史兼任。因此典史职务均由吏部铨选、皇帝签批任命,属于“朝廷命官”。
2. 前文鲍文卿主动为向知县在崔观察面前求情,后文鲍文卿拒绝为二书办说情,均是出于公义,并非私情。前有向知县酬谢五百两被拒,后二书办又是五百两被拒,足见鲍文卿品行高洁,令人起敬。向知县与鲍文卿的交往,也是书中写到现在难得的一段真情。作者意欲以此一深明大义之戏子羞杀无品行之士大夫之流乎?
3. 这五回有同样一个写法:写牛老儿和卜老爹不知其名,后于二十回末,倪老爹于病中见勾魂的批文上得见二人姓名。原文:那日天色晚了,卜老爹睡在床上,见窗眼里钻进两个人来,走到床前,手里拿了一张纸,递与他看。问别人,都说不曾看见有甚么人。卜老爹接纸在手,看见一张花边批文,上写着许多人的名字,都用硃笔点了,一单共有三十四五个人。头一名牛相,他知道是他亲家的名字。未了一名便是他自己名字卜崇礼。
写向知县初也不知其名,后于二十四回崔观察的揭帖稿中得知,原文:取来灯下自己细看:“为特参昏庸不职之县令以肃官方事,”内开安东县县令向鼎许多事故。
牛浦前妻更不知名姓,后于牛浦与石老鼠在县衙门口闹后,回家途中听得邻居言及前妻来闹,原文:自心里明白:“自然是石老鼠这老奴才,把卜家的前头娘子贾氏撮弄的来闹了。”
倪老爹之名于第二十五回过继文书上得见,原文:立过继文书倪霜峰,今将第六子倪廷玺,年方一十六岁,因日食无措,夫妻商议,情愿出继与鲍文卿名下为义子,改名鲍廷玺。此后成人婚娶,俱系鲍文卿抚养,立嗣承裆,两无异说。如有天年不测,各听天命。今欲有凭,立此过继文书,永远存照。嘉靖十六年十月初一日。立过继文书:倪霜峰。凭中邻:张国重、王羽秋。
每每如是。
《儒林外史汇校汇评本》读后感(五):閱讀《儒林外史會校會評》中所見點校中的問題
隨著閱讀《儒林外史彙校彙評》的進度,發現了由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的李漢秋先生點校的點校本的一些問題, 暫記於此。
[1] 第一回第一〇頁第七行“母于灑淚分手”,應為“母子灑淚分手”。李校本誤將“母子”訛作“母于”;
[2] 第一回第一三頁第十五行“正冕左手持杯”,應為“王冕左手持杯”。李校本誤將“王冕”訛作“正冕”;
[3] 第一回第一六頁【校記】[九]“‘戴’,原作‘帶’,抄本、蘇本和申一、二本均同。參齊本改。同一誤字,以下徑改不記。”李先生在校記中將“帶”視為誤字,其實不然。在明清小說的刊刻本中,“戴”均作“帶”,不同於現如今的標準用字,這不能算是誤字,按今天的標準只能算作“不規範用字”。所以校記中的“誤”字當刪去,只校訂爲標準用字。
[4] 第一回第一七頁【校記】[二六]“‘桌子’,原作‘卓子’,蘇本同。從抄本和申一、二本改。同一誤字,以下徑改不記。”李先生在校記中將“卓”視為誤字,其實不然。在明清小說的刊刻本中,“桌子”常作“卓子”,“桌椅”常做“卓椅”,“桌”“卓”不分,此也不能算是誤字,同樣以今天的標準只能算作“不規範用字”。
[5] 第二回第二一頁第四行“和尚又下了一斤牛肉面吃了”。“一斤”後有校記序號,回後【校記】[十三]說:“‘斤’,原作‘筋’,抄本、蘇本同。從申一、二本改。”校記中所說的“筋”,在聯經點校本中爲“筯”,在人文點校本中爲“箸”。問題來了,只好查閱臥本,原來是“筋”。第三回第四〇頁第十六行有“提着七、八斤肉”句,臥本作“提着七八觔肉”,“斤”作“觔”。並且在本回的後文臥本有“擺兩張桌子杯筋”,顯然應該是“杯筯”,臥本“筯”訛作“筋”。也可以說,臥本是“筯”“筋”不分。李先生不察此情況,誤將“一筯”校為“一斤”。此處聯經本和人文本均校正無誤。除此,“牛肉面”應為“牛肉麵”。
[6] 第二回第二二頁第十五行“呆,秀才,吃長齋,鬍鬚滿腮……”。“呆”,《正字通》“同槑,省古文,某作槑,某即古梅字。今俗以呆爲癡獃字”。《字彙》“古某字,今俗以為癡獃字,誤”。《康熙字典》“……又莫厚切,音母,古文某字,今俗以為癡獃字,誤也”。此處臺灣聯經版用字就比大陸嚴謹,從刻本作“獃”。 此後,凡刻本“獃”李校本皆作“呆”。此後,尤其第十一回第十二回言楊執中之“獃”,刻本中出現數處“獃”字,李校本皆作“呆”。想刻本全書之“獃”在李校本中皆作“呆”。
[7] 第三回第三八頁第七行“因向幾侗同案商議”。臥本爲“因向幾个同案商議”,李校本誤將“幾個”訛作“幾侗”。
[8] 第三回第四七頁【校記】[九]“’燙‘,原作‘盪’,抄本、蘇本、申一本同。從申二本改。同一誤字,以下徑改不記。”李先生在校記中將“盪”視為誤字。李先生在此可能忽略了,“ 盪,漡,湯 ”均為“燙”之異體字。在明清小說的刊刻本中,“燙”常作“盪”,因此這也不能算是誤字,以今天的標準只能算作“不標準用字”。所以,校記中的“同一誤字”之“誤”字,應刪去,改為“同一字”。
[9] 第四回第五〇頁第十行“慌忙燒茶、下面”第十一行“胡屠戶吃過面去”。“面”,臥本及聯經點校本爲“麵”,正字。《正字通》《字彙》“麵,俗麪字。”《說文解字》“麪,麥末也,從麥丐聲,彌箭切。”《宋本廣韻》“麪,束皙麪賦云:重羅之麪,塵飛雪白。麵,同上。”王力《古漢語字典》對“面”字的解釋:“一、臉。二、前面。三、物體的表面。四、向。五、見面。六、量詞。”可見,“面”並無“麵食”之義。“麵”或“麪”爲正字,繁體字版應從。“面”爲簡化字,在這裡實為繁簡混用,或說是錯用。相比之下,臺灣聯經版就比大陸版繁體字用字準確。此後第五二頁第七行“吃了開經面”,同誤。相信全書所有之“麵食”之“麵”都訛作“面”。
[10] 第四回第五四頁第六行“落腮胡子”。“胡子”,臥本及聯經點校本爲“鬍子”,正字。“胡”《漢語大字典》“胡,第17條,‘鬍’的簡化字。”《中華字海》“胡,第10條,‘鬍’的簡化字。”由此可證,繁體版應爲“鬍子”。“胡”,在這裡爲簡化字,或說是錯字。 其後第五五頁第七行“天一評:正與‘蜜蜂眼,高鼻梁,落腮鬍子’兩兩相對”、第五十九頁第八行“鬍子沾成一片”句,“鬍子”不誤。今大陸人對繁體字的運用可以說已經不會用了,這種似是而非的錯誤大陸出版社的校對也容易疏忽。
[11] 第五回第六三頁第九行“趕面的杖”。“面”,此處應該是“麵”,“麵食”的“麵”,又訛作“面”。
[12] 第五回第六九頁第十四行“兩位舅爺王于據、王于依都畫了字”。臥本及聯經點校本爲“兩位舅爺王於據、王於依都畫了字”, 包括民國時期的廣益書局、亞東圖書館、萬有書庫排印本 “王於據、王於依”均不作“王于據、王于依”。據《王力古漢語字典》所解:“于,⑴介詞。義同‘於’。①表示在於。②表示甚於。⑵語氣副詞,常用於動詞前面。[辨]于,於。不同音(于,羽俱切;於,央居切。),但義得相通。在表示至于某地時,多用‘于’;在表示甚於時(荀子勸學:‘冰,水爲之,而寒於水。’)和表示被動時(孟子滕文公上:‘勞力者治於人。’),多用‘於’。但並不嚴格。”另外,按慣例,人物的姓名爲專有名詞,用字不能隨意更改。可見大陸出版物用字太隨意了,相較臺灣出版物則很嚴謹。
[13] 第六回第七七頁倒第二行“二奶奶拜上大老爹”。“拜”後有校記,第八九頁【校記】[三]“‘拜’,原作‘頂’,抄本、蘇本同。從申一、二本改。”看了一下聯經版和人文版都沒做校改,保持原貌爲“頂”。查《漢語大字典》“頂”字條11:“拜。《西遊記》第四十四回:‘行者頂謝不盡。’《儒林外史》第六回:‘二奶奶頂上大老爹,知道大老爹來家了,熱孝再身,不好過來拜見’。”《漢語大詞典》217頁【頂上】條二:“頂禮拜上。極表尊敬。明陳洪謨《繼世紀聞》卷一:“公差出外及回京者,朝見畢,皆赴瑾(劉瑾)宅見辭。用涴紅箋紙寫官銜,稱‘頂上’字樣以為常禮。”又:“凡拜帖寫‘頂上’,不敢云‘拜上’,‘頂上’之稱自此起。”由此看來,臥本之“頂上”是原文,應保持原貌,不應作校改。
[14] 第七回第九二頁第六行“黃評:不忘饅頭、面筋之饋,多情多情。”“麵筋”之“麵”訛作“面”,簡體字版可,繁體字版不可。
[15] 第七回第九三頁第十五行“天一、二評:梅三相此番出丑,虧得周長兄救急。”“出醜”之“醜”訛作“丑”。《說文》“醜,可惡也。從鬼,酉聲。”《王力古漢語字典》:“醜。1.惡,不好。2.相貌難看,與‘美’相對。3.類,同類。4.指惡人,多指敵人。[備考]指動物的肛門。禮記內則:‘魚去乙,鼈去醜。’鄭玄註:‘醜謂鼈竅也。’[辨]醜,惡,丑。‘醜’和‘惡’都有醜惡、相貌難看的意義。‘醜’字在先秦主要用作醜惡義,相貌難看義主要用‘惡’字表示。漢代以後‘惡’字主要用作善惡、憎惡義,相貌難看義逐漸由‘醜’所取代,而‘醜’的醜惡義也漸衰亡不用。‘醜’字今簡化作‘丑’,古代‘醜’‘丑’音義都有別,是無關的兩個字。‘丑’是地支的第二位,聲母、介音也與‘醜’有別。”
[16] 第七回第一〇二頁第八行“一旦奮翼青云”。“青雲”訛作“青云”。
[17]第十二回第一五六頁第八行“天一評:權勿用底裏借胡子說出”;第一五七頁第九行“天一評:胡子一番說話尖嘴薄舌”、第十行“天二評:胡子一番說話尖嘴薄舌”。 “胡子”,應爲“鬍子”,繁體正字。李校本這裡訛作簡化字“胡”。
[18]第十四回第一八二頁第十行“你們原是‘氈襪裏脚靴’”。臥本及亞東圖書館排印本、世界書局排印本、萬有書庫排印本、廣益書局排印本、人民文學出版社排印本均爲“你們原是‘氈襪褁脚靴’”。李校本此處“褁”訛作“裏”。
[19]第十四回第一八四頁第四行“蘧公孫從墳上回來,正要去間差人”。臥本及亞東圖書館排印本、世界書局排印本、萬有書庫排印本、廣益書局排印本、人民文學出版社排印本均爲“蘧公孫從墳上回來,正要去問差人”。李校本此處“問”訛作“間”。
[20]第十四回第一八九頁第一行“也有賣面的”、第六行“街上酒樓、面店都有”。臥本及亞東圖書館排印本、世界書局排印本、萬有書庫排印本、廣益書局排印本、聯經排印本均爲“也有賣麵的”“街上酒樓、麵店都有”。李校本“麵”訛作“面”。
[21]第十四回第一九〇頁第一行“恰好一個鄉里人捧着許多燙面薄餅來賣”。臥本及萬有書庫排印本“恰好一個鄉里人捧着許多盪麵薄餅來賣”,亞東圖書館排印本、世界書局排印本、廣益書局排印本、聯經排印本“恰好一個鄉裏人捧着許多盪麵薄餅來賣”。李校本“麵”訛作“面”。
[22]第十四回第一九〇頁第十一行“一部大白須垂過臍”。“須”,臥本作“鬚”,諸排印本亦從刻本作“鬚”。李校本不從刻本,作“須”。“須”,《說文》解:“須,面毛也。”“鬚”爲後出字,雖說“須”“鬚”通。但此後的第十五回第二〇一頁有“船窗裏一個白鬚老者道”句,李校本卻又從刻本作“鬚”。看來李校本在此書中“須”“鬚”混用。
[23]第十五回第一九三頁第十二行“天一評:深悔牛肉、面餅先吃”。萬有書庫排印本“深悔牛肉麵餅先喫”。李校本“麵”訛作“面”。
[24]第十五回第二〇〇頁第十五行“書中自有黃金屋,書中自有千鐘粟,書中自有顏如玉”。臥本及亞東圖書館排印本、世界書局排印本、萬有書庫排印本、廣益書局排印本、聯經排印本“書中自有黃金屋,書中自有千鍾粟,書中自有顏如玉”。 “鐘”,《王力古漢語字典》解:“一.樂器,供祭祀或宴飨時用……二.古容量單位。淮南子要略:‘一朝用三千鐘贛。’許慎注:‘鐘,十斛也。贛,賜也。一朝賜群臣之費三萬斛也。’本亦作‘鍾’。”既然“鍾”與“鐘”此處義同,李校本當保留原刻用字——“鍾”,不應畫蛇添足。
[25]第十六回第二〇五頁第十三行“白挣自吃”。臥本“自挣自吃”。李校本“自”訛作“白”。
[26]第十六回第二〇五頁第十三行“尋的錢,兩口子還養下來”。臥本“尋的錢兩口子還養不來”。李校本“不”訛作“下”。
[27]第十六回第二〇八頁第十五行“父親的病才好些”。“才”,臥本作“纔”。此前同回第二〇四頁“方纔放下心”、第二〇六頁“纔扶了睡下”;此後同回第二〇九頁“方纔幾乎不認得了”、第二一〇頁“纔一總捧起來朝外跑”“纔得出門”……李校本均從刻本作“纔”。再後本回第二一四頁“寫匡超人孺慕之誠,出於至性,及才(刻本爲“纔”)歷仕途,便爾停妻再娶”卻異刻本作“才”,“纔”“才”混用。
第十七回第二一六頁“那人嘴才(纔)軟了”、第二一九頁“和奉事我的一樣才(是)纔”“剛才(纔)到家”“才(纔)走進城”、第二二〇頁“我今晚就走才(纔)好”“那人才(纔)立起身來爲禮”、第二二二頁“才(纔)到這裏”、第二二三頁“才(纔)到”“小弟方才(纔)在寶店奉拜先生”、第二二五頁“才(纔)知道天下還有這一種道理”……仍相異刻本,用“才”字。
[28]第十六回第二一〇頁第五行“芝麻糖、豆腐干、腐皮、泥人”。“豆腐干”,臥本“豆腐乾”。
“干”,《王力古漢語字典》 “㊀盾。書牧誓:‘稱爾戈,比爾~。’詩大雅公劉:‘~戈戚揚。’㊁岸。詩魏風伐檀:‘坎坎伐檀兮,寘之河之~兮。’㊂犯。左傳文公四年:‘君辱貺之,其敢~大禮以自取戾?’㊃求。書大禹謨:‘罔違道以~百姓之譽。’論語爲政:‘子張學~䘵。’㊄﹝干支﹞天干地支的合稱。甲乙丙丁戊己庚辛壬癸爲天干;子丑寅卯辰巳午未申酉戌亥爲地支。㊅﹝若干﹞指未知數。禮記曲禮下;‘始服衣若干尺矣。’㊆關涉,發生關係(後起義)。宋李清照鳳凰臺上憶吹簫詞:‘非~病酒,不是悲秋。’”。
“亁”,《王力古漢語字典》“1. qián渠焉切,平,仙韻,羣。元部。㊀八卦之一。易乾:‘~,元亨利貞。’2. gān古寒切,平,寒韻,見。元部。㊁乾燥,濕之反。詩王風中谷有蓷:‘暵其~矣。’引申爲枯竭。左傳僖公十五年:‘張脈僨興,外彊中~。’[同源字] 熯,暵,亁,蔫,旱。”
顯然,此處李校本之“豆腐干”,爲錯字,被簡化字所誤。應作“豆腐亁”。
[29]第十七回第二二〇頁第十行“稀稀的幾根胡子”;第二二三頁第九行“指着那一個胡子道”、第十行“浦先生胡子”。“胡子”,應爲“鬍子”,繁體正字。李校本這裡訛作簡化字“胡”。
[30]第十八回第二三二頁第五行“說着,捧出面來吃了”。臥本及及亞東圖書館排印本、世界書局排印本、萬有書庫排印本、廣益書局排印本、聯經排印本“說着捧出麵來吃了”。李校本“麵”訛作“面”。
[31]第十八回第二三五頁第十一行“買了些索面去下了吃”。臥本及及亞東圖書館排印本、世界書局排印本、萬有書庫排印本、廣益書局排印本、聯經排印本“買了些索麵去下了吃”。李校本“麵”訛作“面”。
[32]第十八回第二三六頁第八行“誰不知道我們西湖詩會的名土”。臥本“誰不知道我們西湖詩會的名士”。李校本“士”訛作“土”。
[33]第十九回第二三九頁第二行“黃胡子”。“胡子”,應爲“鬍子”,繁體正字。李校本訛作簡化字“胡”。
[34]第二十一回第二七〇頁第十行“齊評:卜老多情不异甘露僧”。“异”,《說文》“舉也。”《正字通》“古文異。”《字彙》“古文異字。”雖說“异”爲古“異”字,但“異”是繁體正字,李校本應從標準繁體字“異”。
[35]第二十三回第二八六頁正文第八行“茶館裏送上一壺干烘茶”。臥本“茶館裏送上一壺亁烘茶”。“干”,參看此前[28],“亁”爲繁體正字。李校本“亁”訛作“干”。
[36]第二十七回第三三七頁第十一行“我們纔得干净”。臥本“我們纔得亁凈”。“干”,參看此前[28],“亁”爲繁體正字。李校本“亁凈”訛作“干净”。
[37]第二十八回第三四七頁第十三行“捧上面来吃”,第十四行“到面店裏”“八分一碗的面”,第十六行“纔到面店裏去的”。臥本“捧上麵来吃”“到麵店裏”“八分一碗的麵”“纔到麵店裏去的”。“麵”,李校本“麵”全訛作“面”。
[38]第二十八回第三五五頁第二行“八分一碗的面只呷一口湯”。臥本“八分一碗的麵指呷一口湯”。“麵”,李校本“麵”訛作“面”。
[39]第二十八回第三五五頁第三行“後雲”。臥本“後云”。“云”,李校本“云”訛作“雲”(明顯是計算機繁簡轉換之誤,出版社校對也沒看出來)。
[40]第三十一回第三八一頁第十七行“下文是教他投王胡子”。“鬍子”,李校本訛作“胡子”。
[41]第三十一回第三八二頁第二行“他家有個管家王胡子”,第四行“你將來先去會了王胡子”。臥本“他家有個管家王鬍子”“你將來先去會了王鬍子”。“鬍子”,李校本皆訛作“胡子”。
[42]第三十一回第三八四頁第一行“好胡子”。萬有書庫排印本“好鬍子”。“鬍子”,李校本訛作“胡子”。
[43]第三十一回第三八五頁第六行“家人王胡子手裏拿着一個紅手本”“王胡子,你有甚麼話說”,第七行“王胡子走進書房”,第八行“天一評:來了。不知王胡子吃了多少酒,若韋胡子尚未見杯子面也”,第十行“王胡子道”,第十一行“黃評:王鬍子酒吃足了”“天二評:韋胡子尚未見杯子面,王胡子已吃多少酒來了”,第十四行“王胡子出去”,第十六行“王胡子道”。臥本及亞東圖書館排印本、世界書局排印本、萬有書庫排印本、廣益書局排印本、聯經排印本“家人王鬍子手裏拿着一個紅手本”“王鬍子你有甚麼話說”“王鬍子走進書房”“王鬍子道”“王(臥:玉)鬍子出去”“王鬍子道”;萬有書庫排印本“不知王鬍子喫了多少酒.若韋鬍子.尚未見杯子面也”。“鬍子”,李校本皆訛作“胡子”。
[44]第三十一回第三八六頁第三行“方纔我家人王胡子說”,第四行“王胡子道”。臥本及亞東圖書館排印本、世界書局排印本、萬有書庫排印本、廣益書局排印本、聯經排印本“方纔我家人王鬍子說”“王鬍子道”。“鬍子”,李校本皆訛作“胡子”。
[45]第三十一回第三八七頁第六行“王胡子又拿了一個帖子進來”,第九行“王胡子應諾去了”。臥本及亞東圖書館排印本、世界書局排印本、萬有書庫排印本、廣益書局排印本、聯經排印本“王鬍子又拿了一個帖子進來” “王鬍子應諾去了”。“鬍子”,李校本皆訛作“胡子”。
[46]第三十一回第三八八頁第十二行“天一評:胡子真老酒鬼”,第十六行“走到王胡子房裏去”“王胡子問加爵道”,第十七行“王胡子又問那小廝道”。“鬍子”,李校本皆訛作“胡子”。
[47]第三十一回第三八九頁第一行“王胡子道”,第八行“王胡子叫那小廝道”,第九行“王胡子想來沒錢賺”。“鬍子”,李校本皆訛作“胡子”。
[48]第三十一回第三九一頁第四行“胡子酒鬼殺風景”,第九行“王胡子領着四個小廝”“王胡子道”,第十一行“王胡子道”。“鬍子”,李校本皆訛作“胡子”。
[49]第三十一回第三九二頁第七行“王胡子,你就拿去同楊司務當了”,第十行“楊裁縫同王胡子擡着箱子”,第十一行“王胡子道”。“鬍子”,李校本皆訛作“胡子”。
[50]第三十一回第三九三頁第三行“至裁縫、王胡子,各各有算計少卿之法”,第四行“觀其不與王胡子通氣,胡子雖恨之”,第五行“豈可與張俊民、臧蓼齋、裁縫、王胡子輩同論”,第七行“串通王胡子”,第九行“王胡子吃飽”,【校記】﹝八﹞“王胡子,原作‘玉胡子’,抄本同。從蘇本和和申一、二本改。”“鬍子”,李校本皆訛作“胡子”。
(“鬍子”,訛作“胡子”。只第三八六頁第七行“少頃,請了一個大眼睛黃鬍子的人來”第八行“大眼睛黃鬍子”“大眼睛黃鬍子的人”,三處例外;再就是第三八二頁第十七行“一部大白鬍鬚”之“鬍”不訛。)
此後之“鬍子”繼續訛作“胡子”,應是貫穿全書,不再作記錄說明。
[51]第三十二回第三九八頁第十五行“王胡子又討了六兩銀子賞錢,回來在鮮魚面店裏吃面”,第十六行“王胡子過來坐下,拿上面來吃”。臥本“王鬍子又討了六兩銀子賞錢,回來在鮮魚麵店裏吃麵”“王鬍子過來坐下,拿上麵來吃”。“鬍子”,李校本訛作“胡子”;“麵”,李校本訛作“面”。
[52]第三十二回第三九九頁第十一行“說罷,張俊民還了面錢,一齊出來。王胡子回家”。臥本“說罷,張俊民還了麵錢,一齊出來。王鬍子回家”。“麵”,李校本訛作“面”;“鬍子”,李校本訛作“胡子”。
[53]第三十五回第四三五頁第十三行“隨教大學土傳旨”。臥本“隨教大學士傳旨”。“大學士”,李校本訛作“大學土”。
[54]第三十五回第四三六頁第十六行“天一、二評:纔是征君身分”。 “徵”,李校本訛作“征”。
[55]第三十五回第四三八頁第九行“黃評:翰林也來拜征君”。 “徵”,李校本訛作“征”。
[56]第三十六回第四四六頁第十二行“這征辟之事”。臥本“這徵辟之事”。“徵”,《王力古漢語字典》“㊀召。㊁求。㊂問,詢。㊃跡象。㊄證驗,證明。”“征”,《王力古漢語字典》“㊀行。㊁征伐。㊂抽稅。”“徵”,爲正體字,李校本訛作簡體字“征”,此訛在前回的批語中有若干次出現。
[57]第三十六回第四四七頁第一行“黃評:莊杜二人猶有‘征辟’二字存於胸中”。“徵”,爲正體字,李校本訛作簡體字“征”。
[58]第三十六回第四四八頁第八行“夾人此兩問答”。萬有書庫排印本“夾入此兩問答”。“入”,李校本訛作“人”。
[59]第三十六回第四五一頁第十五行“他有其麼沒品行”。臥本“他有甚麼沒品行”。“甚”,李校本訛作“其”。
至此,可以得出結論,此繁體豎版《儒林外史》的排版是由簡體字錄入而成(也可能李漢秋先生的原稿就是簡體字),再經由軟件繁簡轉換而成繁體版。所以出現了很多不該誤而誤的字。最具代表性的就是“云”訛作“雲”,“麵”訛作“面”,“亁”訛作“干”,“醜”訛作“丑”,“鬍”訛作“胡”,“徵”訛作“征”,“獃”作“呆”,“鬚”作“須”,“閒”作“閑”,“陞”“昇”作“升”,“掛”作“挂”,“讚”作“贊”,“遊”作“游”,“餚”作“肴”,“僱”作“雇”,“姦”作“奸”,“異”作“异”,“纔”“才”不分等等。繁簡轉換後出現的這些問題,出版社的校對們也沒有發現。大陸出版排印繁體版書籍最大的問題就在於此,都不肯直接用繁體錄入。轉換後出現的不明顯的問題,由於校對們對繁體字的運用又普遍缺乏嚴格的認知水平,很多問題看不出來,便造成大陸繁體出版物今天的這個局面。
暫閱讀至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