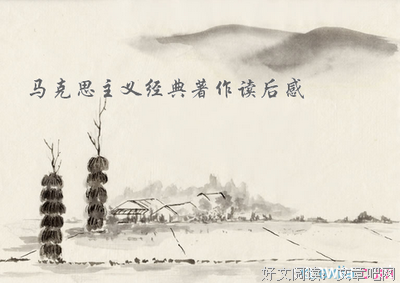
《文明2》是一本由[英] 戴维·奥卢索加著作,后浪丨中国友谊出版公司出版的精装图书,本书定价:88.00元,页数:264,特精心从网络上整理的一些读者的读后感,希望对大家能有帮助。
《文明2》精选点评:
●其实应该写一个中文版解题,比尔德的“单数还是复数?”叙述的是“多元文明”(兼论“女性与文明”);而奥卢索加的“交流与互渗”则引入了殖民史的视角。和室友一致认为这套书有点儿偏艺术史。非常喜欢内封的设计。
●算是一种科普,如果没有时间去读繁皓如星辰的艺术史,这本书可以带给你一种“眼光”,眼光有了,再去获取艺术的知识,会更加深入。
●比上一本扩展一些,读到末尾还是有些力不从心了,总体是值得一看的。
●与1969年版的相比,2018年版的《文明》显然对西方主流之外的文明抱有更开放的立场。戴维·奥卢索加的《文明2》可以说是对克拉克的「现代性」眼光的直接回应,但有趣的是二者都在书中留下了不少与名画名作的合影。和玛丽·比尔德的专题性讨论相比,《文明2》是一种对框架性的、大历史发展的叙述,侧重于世界史的动态发展下,各国间的经济往来是如何影响艺术作品创作,可以沿着作者的讨论思路继续做挖掘工作。
●在文明的多样性之后,一个随后不得不讨论的问题是,多种文明之间是否存在优劣之分?是否存在带有贬低意味的黑人的想象、抑或只是人类共同的想象力下不同的表达形式(结束语)?非洲人、亚洲人、美洲人和太平洋上的原住民的文明是否同样璀璨?在这个意义上,不仅整个人类文明建立在出走非洲的智人的肉体上,而且目前的现代文明作为整体也体现着非西方文明的影响,正如作者本人所受的优良西方教育也与他自豪的非洲民族血脉相连一样。
●美图,美文。 失落又兴起,无数个轮回,时间与空间的关系总和才是文明
●这册集中于讲述文明的碰撞交流融合与碾压。看克拉克版的文明已经是很多年前的事情了,那时候节目内容对我来说还太过令人消化不良。但我仍然记得他的调侃:文明是什么?我不知道,但只要让我看到它,我就能认出它来。作者在对前辈频频致敬的同时也提到前辈视角的偏狭,西方中心视角,纯男性视角等等。英国殖民者对‘东方学’态度的转变也说明我们对文明的理解一样受限于我们时代的视野和风气。诚如作者所言,文明是非常类似宗教的思想,它为我们的起源和终点提供宏达叙事,将人们聚集在共同的信仰中。
●历史感大于艺术感,但碍于篇幅,只能是蜻蜓点水。
●这一本讲的是历史。比第一本细致,但仍显浮皮潦草。比较适合博物馆导游对着艺术品进行讲解。所谓的“交流”和“互渗”更多地是一种文明对另一种文明的侵略。
●当高更流连于欧洲和政府官员之间,享受着自己的名气时,他那故作出来的波西米亚放浪姿态,已然成为法属塔希提殖民社会的特色之一。虽然高更的塔希提画作看似充满异域风情,但作为一位复杂而矛盾的画家,他不可能把塔希提岛描绘成欧洲人常规想象中的那种古典的岛屿天堂。他像许多人一样,把世界划分为截然不同的两部分:欧洲,和像塔希提这样的人们——在他以为——所处的自然原始状态。他不断地提及他需要恢复活力,而这只能发生在远离欧洲文明的地方。在他的一些信件里,他是把“文明”这个词作为贬义词使用的。高更的塔希提画作中无疑充满了他关于热带、性、文明和野蛮的个人观点和感知。即使搬到了波利尼西亚,那个“欧洲人高更”依然存在,当他描绘塔西提女性时,她们更常是作为一种当地的“类型人物”出现,而不是一个个个体,让人想起德加人物姿态
《文明2》读后感(一):交流与互渗:文明的多样性
随着大航海时代的到来,贸易、财富与宗教等因素推动着以西班牙、葡萄牙、荷兰、英国等国为首的欧洲诸国展开了世界范围内的航海探索,世界各地的文明开始以“欧洲文明-其他文明-欧洲-世界文明”的方式,即欧洲人探索发现了原本相互隔绝的文明,并与这些社会进行了文明的交流(不幸的是,这种交流越来越以暴力征服的强制形式展开),并通过各种形式(移民、教士的记录;对艺术品的掠夺等)使得这些社会的文明得以被记录、传播,以欧洲为中介,世界文明展开了交流与碰撞——这种交流,对于欧洲以外的地区,却往往以一种悲剧性的被迫的形式展开。而在《文明Ⅱ:交流与互渗》中,奥卢索加正是通过艺术的视角,从不同切面记录了自15世纪末开始的至第一次世界大战五百多年间世界文明之间的交流与碰撞。在15世纪末期到18世纪早期的那段时间里,真正的文明故事,就是这样一部接触和互动的历史,正是在这个时期,世界各地的各种文化第一次遇见彼此。
如何展现这段跨越五百多年的文明的交流与互渗?如何书写这段文明史?在历史的书架上,各类展现这段人类社会剧烈变迁的文明史、经济史、社会史、政治史著作汗牛充栋,在艺术的书架上,关于艺术发展史的著作也数不胜数。而当我们试图从艺术的微观视角去探求在这段世界文明史发展进程中的种种辉煌与落败、理性与疯狂、交流与蔑视时,却发现鲜有能够触摸到历史深处的种种脉络,探寻这一段令后世无限慨叹的世界文明之间交流与互渗的历史,却很难找到有关的著作,而这本由为英国广播公司(BBC)拍摄的记录片《文明》(Civilisations)所撰写的解说词所整理出来的稿件,通过对世界文明交流与互渗的诸多切面的叙述、通过对雕塑、画作、相片等艺术作品的叙述展现了文明的交流与发展。
在第一部分,奥卢索加叙述了大航海时代欧洲诸国与亚洲、非洲、美洲、大洋洲等地区之间的交流与碰撞——这些交流有的以暴力政府与蛮横掠夺的形式、有的以殖民地征服与管理的形式、有的以商业与文化交流的形式进行着。富有成果的航海探索、无往不胜的殖民战争、财富的不断积累使得欧洲人趾高气扬,对自己的基督教文明充满自信,对其他地区的文明嗤之以鼻——甚至认为在欧洲、美洲一些部落和地区甚至根本不存在文明,而当从诸如贝宁等地被掠夺的艺术品被运到欧洲的时候,在面对如此精美的艺术品时欧洲人不得不承认非欧洲文明的存在,随着航海发现、侵略与征服的世界范围的扩展,在给世界各地区带去各种奴役和传染病的同时,欧洲人还希望带去他们的信仰——基督教信仰——以向那些“野蛮人”传播“真正的信仰”、传播“文明”,在这个过程中,许多教士、学者开始去理解这些部落和国家的文明特征,他们试图记录、研究、改造这些地区的文明,由此,文明的交流与互渗在世界范围内展开。正如奥卢索加所说,“没有一个社会在经历了地理大发现时代之后还能维持原状,无论是征服者还是被征服者”。
而在这种欧洲对世界其他地区的征服过程中,欧洲人面对的不仅仅是在他们看来被视为无“文明”的文明,他们还要面对诸如印度、中国、日本等这些他们也不得不承认文明发展时间与发展程度丝毫不比欧洲基督教文明落后的地区与国家。“当欧洲开拓者们登陆更加强盛的帝国,例如印度和中国时,他们发现自己只是一个边缘角色,而在日本,他们面临的也是一个强大的封建社会,无法轻易攻克。”于是,在与这些文明交流的过程中,文明的互渗与借鉴进一步展开,诞生了诸多艺术史上最伟大的而一些作品,这些艺术作品融合了欧洲艺术与其他文明的艺术,这一点尤以日本在与荷兰的交流具有代表性。而英国东印度公司在印度的扩张中,也出现了短暂的、昙花一现的“合作时代”,不过,随着欧洲启蒙运动的开展、工业革命的发展,所谓的理性的“优越”与进步的狂热,使得西方文明对亚洲等地的文明持一种“退化论”的观点,他们相信,欧洲人的使命的“文明教化的使命”。于是,我们便来到书的第二部分“进步的狂热”。
在启蒙运动的指引下,欧洲革命风起云涌,资本主义在工业革命的推动下快速发展,建立更大的世界市场成为欧洲国家经济发展的目标。于是,欧洲国家掀起了对内对外的整合与征服。法国在拿破仑的带领下试图征服世界最古老的文明国家之一——埃及、英国最早开展了农业革命和工业革命、迈向工业文明的国家城市快速得到发展、美国这个新生的国家也抓住工业革命的历史契机,迅速发展起来,而这也意味着对原住民生存空间的大规模挤压,在这个过程中,现实主义、印象画派以及各种关注城市变迁、贫民窟、自然社会、原住民的艺术家与画作兴起。随着科技发展与消费社会的繁荣,出现了新兴的艺术工具——相机,对社会发展的记录形式更加多元化。在这一不可阻挡的历史进程中,艺术对“进步”进行了不同程度的回应,印象画派采用较为激进的艺术风格对不断扩张的城市与中产阶级、对现实而又虚幻的消费社会的人们进行了描摹。而世界博览会的召开则更是成为文明交流的一个窗口——当然,更多地还是欧洲工业文明的展示,甚至可以说是炫耀。
如果没有第一次世界大战,这种对“理性”的坚定信仰、对由欧洲主导的“进步”的坚信也许会继续向全球扩张,不仅欧洲人对其文明的优越性坚信不疑,世界其他地区的文明在面对欧洲文明的繁荣与扩张也不断反思自身文明的落后。但是,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残酷所具有的讽刺性——所谓“为了文明的伟大战争”——激起了许多人对所谓的“欧洲文明”的优越性的反思,在一定程度上击碎了这种对进步的狂热的情绪。
“文明”究竟是什么?——这本书没有给出一个明确的答案,但是,在这本简短而又精美的书中,奥卢索加尝试探索艺术在那些交会、互动和冲突的时刻所承担的功能,奥卢索加认为,恰是这些定义了世界历史上过去的500年。
在15世纪末期到18世纪早期的那段时间里,真正的文明故事,就是一部接触和互动的历史,正是在这个时期,世界各地的各种文化第一次遇见彼此。
启蒙运动中理性主义催生出的新的自信,让欧洲人开始认为自己的文化是一种更优越的文化。工业革命之后,欧洲在工业技术上领先了亚洲、非洲和其他民族一大步。到了19世纪欧洲的帝国时期,整个时代被进步的热望所包围。
欧洲文明与阿兹台克文明突然碰撞之时,也在一定程度上发生了对话交流。亡灵节——这项传统在和天主教船艇的万圣节和万灵之日融合之后,又获得新生。
《文明2》读后感(二):《文明II:交流与互渗》:探讨文明碰撞的“野蛮”与"温柔"
文/欧阳欣
文明的定义
在刘慈欣的《三体》中有这样一幕,当银河系被二维化处理时,罗辑要求程心将那些代表着人类文明的名画平展开置入二维平面中,为的就是将人类文明在宇宙中存在的印记保留下来。罗辑的行为让我不禁对文明产生了极大的兴趣,去细想“文明”到底是什么?
文明由“文”和“明”二字组成。“文”在《说文解字》中的解释是“文,错画也,象交文”,指的是相互交错的线条和色彩,是一种美丽而又深奥的纹理,厘清了纹理,我们便能够找到规律,找到那种交错之美。在《贲卦》中对“明”是这样的:“夫大人者,与天地合其德,与日月合其明”,意思就是所谓的大人,就是融合天地之德,闪耀日月之明的人。这里的“明”已有道德礼仪的意思了。
追寻文明的定义,我们会发现,“文明”二字经历了三阶段的发展。“文明”原来只是考古学家和历史学家的专业术语,是指原始部落从散居发展出古代城市及其物质的遗存。再后来,就演变成生活中的仪式,行为和礼仪,中国古代的周礼就是这一阶段文明的代表。文明演化到今日,人们更多的是站在历史长河的岸边去定义文明,“文明”变成了人类精神成就和物质活动的顶层设计和产生的结果的代名词。
要真正理解文明的深层含义,或许我们需要深入到各种文明之中,从历史的角度探索文明的发展,感受文明的内蕴,体会文明之间的碰撞与融合,才能真正理解文明的定义,它绝不是一个简单的代名词。
翻开《文明II:交流与互渗》,跟着英国著名历史学家戴维·奥卢索一起走进文明的发展进程,犹如行走在历史长廊之中,穿越古今,横贯西东。
“文明”的野蛮破坏
19世纪90年代末期,大英博物馆曾经展出几百样象牙和黄铜作品,这些作品有着极高的艺术造诣。来自于古老而一度繁盛的非洲文明—古老的西非贝宁王国。
在19世纪后期,几乎所有欧洲人都认为非洲是一个非常古老而落后的大陆,其所谓的文明也仅仅停留在原始阶段,并没有高速发展,更不可能出现精美的艺术作品。但大英博物馆展出的这几百件象牙和黄铜作品,却狠狠地打了所有自以为是的欧洲人的脸。
这些铜片和象牙雕塑所刻画的面孔,大都是西贝王国的国王与王后,以及他们身边的士兵,商人,猎人的形象,当然也出现了一种复杂的异教信仰的象征符号。通过这些艺术作品,我们能够清晰的判断贝宁王国的文明程度之高。
这些艺术品之所以能够运达伦敦,并在大英博物馆展出,却经历了野蛮对待,英国军队围困并且洗劫了贝宁城。他们烧杀掠抢,无恶不作,将镶嵌在宫廷墙上的黄铜雕刻揭下,对象牙制品一扫而空,于是,才有了大英博物馆展出震惊欧洲人的那一幕。
欧洲人的野蛮行为显然为他们所谓的高度文明抹黑,而他们对待非洲文明的傲慢态度,更让人嗤之以鼻。尽管许多人认为非洲文明是不可能高度发达的,甚至通过诋毁否定的形式拒绝承认非洲文明的发达,但西贝的大多数艺术宝藏却让许多人对这种观念产生了怀疑——既然是残暴与野蛮的民族,又如何拥有如此高的审美能力呢?又怎们能创作出如此炫目的艺术产品?
作为大英博物馆的策展人查尔斯•赫尔克里士•里德明确表达了他的困境:第一眼看到这些意外发现的卓越艺术时,我们的震惊是毋庸置疑的,但我们也困惑原因,当如何解释如此高度发达的艺术,居然出自于如此野蛮的种族。
而德国考古学家费利克斯•冯•路尚绝对被你艺术品给予了极高评价:技术上说,这些青铜器足以代表人类能够达到的最高工艺水准。
虽然西贝文明获得了考古学家的高度认同,但傲慢的欧洲人对西贝王国作出的恶行却始终无法挽回西贝文明。
都说太阳底下没有新鲜事,历史总是一遍又一遍重演。强势文明对弱势文明的侵略和洗劫在历史长河中数不胜数。
西班牙人征服阿兹台克文明,几乎是轻而易举的事情。西班牙人带来的天花,没有免疫力的阿斯达克人来说,简直就是强大的生化武器,任何一个感染天花的人都必死无疑。被感染的人们如同被割的稻谷,成群成群地倒下,到最后有些地方甚至人都死绝了,没有人为他们收尸,人们的家成了埋葬他们的墓冢。
除了武力入侵和病毒入侵,西班牙人并不满意于此,他们要从意识形态上完完全全地占领开始阿兹台克。于是,西班牙人在宗教上进行入侵,大量的神像和神庙被摧毁。有关数据统计,在最初的十年就有2000尊神像被推倒,500座神庙被摧毁。而新教的教堂就在旧神庙的基础上建立起来。主教的修士们致力于改变全体阿兹台克人的信仰,除了推倒神庙,他们还将重点工作放在当地富裕的贵族家庭身上,也在年轻人身上下功夫。
肉体上的侵略和精神上的野蛮暴行是自认为高贵者对于弱者的残忍。当一个文明要吞噬另一个文明时产生的野蛮破坏,着实让人无法直视。
“文明”的润物无声
贸易是文明交流最温和的一种方式。在贸易的过程中传播文明,容易让人接受,也更悄无声息。16世纪中国已是全球化贸易时代的中心,中国产品受到了许多西方人的欢迎。
中国瓷器,丝绸,刺绣,茶叶无意传播着中国传统文化的高深莫测,这些贸易商品带着中华文明走到了世界的各个角落。茶道本是中华文明的代表,但因为茶叶的备受欢迎,下午茶也成为西欧人礼仪的一部分,这茶文化,也一点一点渗透到西方人的日常生活之中。
文明悄无声息的交流与融合在一个17世纪流行于欧洲和日本的新兴艺术载体中体现得淋漓尽致,那便是南蛮屏风。绘画南蛮屏风的大师级艺术家,大都来自于鹿野、土佐和住吉艺术学校,他们以日本人的视角观察那个几乎被遗忘的16世纪全球化的时代。
屏风上画着刷了防水沥青的黑色远洋船只,船只上载满了中国丝绸和具有中国特色的家具,以及富有异国色彩的动物和其他产品。这屏风上不仅仅描绘了葡萄牙人,西班牙人,也有印度人,马来人,波斯人,甚至还有非洲奴隶。
而时常出现在屏风上的欧洲人有许多已经在日本定居,他们之中有很多是耶稣会士。在贸易的进程中,这些人的职责就是对日本人进行传教。在1550年,只有约1000个日本人改信基督,而到了1580年,这个数字就达到了15万,到了16世纪末期日本的基督基督教徒多达30万,之后很快又涨到了50万。
这种悄无声息的传教行为和西班牙人对阿兹台克人暴虐的传教行为形成了鲜明的对比,但温柔里也带着危机。川幕府虽然强烈支持对外贸易,最初对传教行为也较为宽容,但指数级别增长的基督教徒却让他们感到害怕。如果大和民族失去了属于本土的信仰,那么这个民族还可以称得上是大和民族吗?
1614年,德川幕府颁布了一项基督教驱逐令,这次开始对宗教传播,进行打压,并驱逐耶稣会士,要求日本当地人放弃基督信仰,如果坚决不放弃将会被判处死刑。
“温柔”的文明融合有时候也潜藏这巨大危机,对于当政者而言,文明的力量不足挂齿,伤害帝国利益,再温柔的融合,都需要撕裂开来,暴露原型。我是欧阳欣,一个热爱阅读的妹子,欢迎关注我,一起阅读,一起收获,一起成长。
《文明2》读后感(三):但凡不能杀死你的,最终都会使你更强大
在《007:幽灵党》《寻梦环游记》等电影中,知道了墨西哥的亡灵节。墨西哥人通过摆在家中的灵位、墓地上装饰的鲜花、洒在路上的黄色花瓣,让逝者感觉到亲人的思念,在亡灵的国度,踏上回家的道路,与亲人共度佳节。
亡灵节,脱胎于阿兹台克文化,又与天主教传统的万圣节和万灵之日相融合,是印第安文化和西班牙文化结合的产物。但是,在西班牙征服者的计划中,亡灵节本不该存在。十六世纪,西班牙对阿兹台克的征服者认为,基督教徒优越于一切异教民族,他们拆除了阿兹台克人的神庙,砸毁了阿兹台克人的神像,把记载着阿兹台克历史文化变迁的那些象形文字典籍,付之一炬,并在神庙的废墟上,建起了新教堂,妄图改变全体阿兹台克人的信仰。
西班牙征服者的这些暴力行径,使很多阿兹台克人改信了天主教,以致新建的教堂都不够用。但是,在阿兹台克人心中,植根千万年之久的文化血脉,并不是武力所能征服的。很多改信天主教的阿兹台克人,依然在家偷偷祭拜自己的神灵;传统的治疗者和占卜者,也仍然存在于偏远的乡村;亡灵节则承袭着阿兹台克的文化元素,一直传承到了今天。
而且,文明不仅难以被摧毁,它还带有着物理学中力的相互性。当西班牙的征服者们,试图改变阿兹台克的时候,他们也受到了阿兹台克文化的影响。埃尔·格列柯是西班牙文艺复兴时期著名的幻想风格主义画家,在他著名的画作《脱掉基督的外衣》中,即将登上十字架的基督,身穿深红的衣袍,这分明是在暗示观众,十字架之刑是一种血的祭献,就像阿兹台克人宗教中的“人祭”。而在他所画的《十字架上的基督》中,基督被钉在十字架上,身体扭曲,血迹斑斑,更是将祭献这个主题清晰的表达了出来。
就像西班牙和阿兹台克,在15世纪“地理大发现”之后,西方文明与其他地区的文明之间,有着冲突,也有着交融。BBC在2018年拍摄了纪录片《文明》,邀请英国著名历史学家戴维·奥卢索加,围绕文明的冲突与交融,对纪录片中的第六集和第八集进行了解说。之后,戴维·奥卢索加将解说词,进行了补充完善,成书为文明系列的第二本书——《文明II》。
在《文明II》中,戴维·奥卢索加认为,当文明之间发生交会,每个文明都会从其它文明中,得到新的东西,就好像这个全球化的时代,所有文明都在不断吸纳他者,也不断被他者改变。为阐述这一观点,戴维•奥卢索加列举了很多传世的艺术精品,给读者讲述着,在异族的相遇,和岁月的变迁中,那些艺术品所发生过的故事。
一、贝宁青铜: 无声之处的呐喊
19世纪末,英国处于维多利亚时代晚期,关于文化,在英国公众的心中,具有一个通行的理论,那就是存在一条金线,这条金线从古埃及文明开始,串连着古希腊、古罗马、基督教、文艺复兴、启蒙运动等时期。金线之外的,都是化外之族。
1897年,英国为了掌控棕榈油以及其他货物贸易,袭击了西非的贝宁王国,并洗劫了首都贝宁城。就像所有的侵略战争一样,侵略者总会找出一些堂而皇之的理由,以体现侵略的合理性。这一次,他们的借口是为遭受伏击丧命的士兵复仇,英国的媒体,也配合着侵略行动,大力渲染贝宁王国的原始与野蛮。
8个月之后,为庆祝维多利亚女王即位60周年,在洗劫贝宁王国过程中,得到的很多战利品,被送到大英博物馆,进行了展出。这些被称为“贝宁青铜”的艺术品,由富铜的合金铸成,刻画着国王王后,以及士兵、商人、猎人的形象,其制作精良,惟妙惟肖,一经展出,便赢得了参观者的赞美。
但是,这时出现了一个十分矛盾的问题。那就是,原始野蛮的非洲人,如何有资格、有能力去制作出如此精美的工艺品?因此,为了圆谎,英国人编造出各种理由,有人说这是葡萄牙人带去的技艺;有人说这是某个不明身份的白人文明留下的成果;甚至还有人说这是失落的城市亚特拉蒂斯的创造。然而,这些理由都无法解释,为什么这些艺术品描绘的是黑人形象。
而且,早在3个世纪之前,贝宁人已经与葡萄牙人有了接触。在贝宁人的艺术品中,还具有葡萄牙士兵形象的作品。葡萄牙人和英国的早期探险者,也认为贝宁王国具有着发达的文明。然而,3个世纪之后,为了贸易利益,英国侵略者却选择了遗忘。
对于英国侵略者的谎言,虽然贝宁人的声音,无法晓谕世人,但这些无声的艺术品,却发出了振聋发聩的呐喊。而这些艺术品的声音,是任何人都无法阻挡的。
二、《裂冰》:文明是一种液体
16世纪,日本人和葡萄牙人已经开展了贸易往来。但是,葡萄牙人不仅关注贸易,还热衷传教。1550年,日本的天主教徒大约1000名左右,但半个世纪之后,已经激增至50万人。
统治日本的德川将军们,听说了西班牙人在美洲的所作所为,也目睹了菲律宾的惨遭侵略,因此,对葡萄牙人深感不安。1623年,德川家康的儿子,第二代德川将军德川秀忠,采取了一系列禁教措施,在长崎处决了55名传教士,驱逐了耶稣会士,禁止日本人从事宗教活动。并且,逐渐确立了日本的锁国体制,在理论上要求日本与外界完全切断联系。
但是,对欧洲人建造起的坚固壁垒,却留下了一条缝隙,那就是荷兰,被允许在出岛通商。出岛,是一个在长崎特意建造的人工岛屿,也是日本对外通商的唯一窗口。而之所以选择荷兰,是因为荷兰人只看重经济利润,并不在乎宗教影响。
荷兰人在通商过程中,严格遵守着日本的规则,并且定期远赴东京参拜幕府将军。饶是如此,荷兰人还是起到了启蒙作用,将科学与艺术的新思潮,通过出岛带入了日本,包括钟表、地图、显微镜、天球仪、地球仪、眼睛、医疗器械等。特别是有一种叫做荷兰镜的事物,意外的影响了日本美术的发展。
荷兰镜是一套光学装置,由一个木盒和放置在其中的凸透镜构成,通过凸透镜,在观看按照欧洲透视法绘制的风景图时,能够呈现出立体感。
一位叫做圆山应举的日本画家,通过荷兰镜,掌握了透视法,并将其应用在日本的传统绘画中。他所创作的《裂冰》,是茶道仪式上使用的一种低矮的两面绘屏,展示了冬天河面上爆裂的冰面,因为使用了透视法,却让寥寥数笔的直线组合,呈现出一种立体观感。
文明很像一种液体,无论你如何闭关锁国,只要有一丝缝隙,它就能够渗入其中,与原有的文明混合在一起。并且,文明之间的混合,会如同发生了化学反应,形成一些新的东西。
三、维米尔:“坐井观天”的宅男
以《戴珍珠耳环的少女》闻名世界的约翰内斯·维米尔,是荷兰优秀的风俗画家,被看作“荷兰小画派”的代表画家。他1632年出生于荷兰的代尔夫特,生活在荷兰的黄金时代。在那个时代,无数荷兰人,在大海的惊涛骇浪之间,远赴万里之遥,去获取财富。但维米尔直到43岁去世,依然住在代尔夫特,一生之中,从未离开过荷兰的土地,可谓荷兰黄金时代的宅男。
维米尔的画作,也大多都是室内的布景,在封闭的空间内,呈现出一种温馨、舒适、宁静的观感。对于这些画作,人们通常会认为,是看不到世界其它地方的。但是,文明之间一旦有了接触,任何人都无法摆脱文明交融的魔力。
在他的《军官与欢笑的女孩》中,军官与女孩不知在说些什么,让女孩的脸庞绽放出美丽的笑容,军官带的宽毡帽,是北美的海狸皮毛制成,而墙上悬挂的,是一副地图,都标志着荷兰黄金时代的全球化进程;在他的《在敞开的窗户前阅信的年轻女子》中,桌面上摆着土耳其地毯,地毯上是中国的克拉克瓷碗,而且女子正在阅读的信件,也许就来自于遥远的异国他乡,与那张地毯和那些瓷碗一样,传递着远方的消息。
文明是流动的,即使维米尔终生在荷兰的井中安之若素,外界文明的天空,还是在不经意间丰富着他笔下的世界。所以,维米尔画作中的封闭空间,从来都不是完全封闭的,就如同他画作中的窗户,总会有屋外的光芒流淌而入。
通过戴维•奥卢索加在《文明II》中展示的这些艺术品,我们能够感受到,在全球化的世界进程中,没有什么能摧毁一种文明的存在,也没有什么能阻止一种文明的发展,文明的交融,就如同历史的洪流,滚滚向前,势不可挡。对此,我们或许能够想起,尼采曾经说过的一句话:但凡不能杀死你的,最终都会使你更强大。
《文明2》读后感(四):《文明》中的“砍二”是何来历?丨阿兹特克文明指南
一、用文明定义文明
自1991年席德梅尔的《文明》游戏发行以来,因其精良的制作与全新的互动方式,获得了全世界玩家的追捧。游戏制作人席德·梅尔也被GameSpot称为“我们的希区柯克,我们的斯皮尔伯格,我们的艾灵顿公爵”。《文明》的宏大之处即在于,所有“文明”的设定都取材于现实世界里人类历史上中曾经辉煌或是走向湮灭的各类文明,而玩家将创建及带领自己的文明从石器时代迈向信息时代,并成为世界的领导者。而当时代亦步亦趋地跟随在技术发展的脚步之后,《文明VI》也将现实世界的发展演绎为游戏中的设定:在《文明VI》的“信息时代”中,政策树的末端是社交网络与全球化——仿佛我们正身处其中的时代。
如果说《楚门的故事》预示了一个“后真相”世界的到来,那么《文明》系列游戏似乎给我们了一个机会得以重新审视这些或是熟稔、陌生、也或是带有偏见的文明(Civilization)——究竟为何?
《文明》系列游戏中,文明(Civilization)一般指主流文明,是玩家和电脑AI在《文明》中所选择创建和发展的势力。有关“文明”的讨论也在现实世界之中争论不休。
在BBC 1969年播出的纪录片《文明》的开头,主讲人肯尼斯·克拉克(Kenneth Clark)就曾带领观众思考过这一问题,“文明是什么?”他说,“我不知道,我不能用抽象术语来定义它——但我想只要让我看见它,就能认出它来。”
尽管在克拉克看似谦逊的定义背后,是对以欧洲文明中心的文明史观的推崇。但长久以来,我们似乎也有意无意地将文明理解为对“单一的西方文明”(the civilisation)的推崇,而习惯于长期以来被灌输的那些关于何为艺术中的“美”,何为信仰中的“诚”的陈词滥调。
在《文明》系列游戏中,每个文明都是独一无二的,每个都有自己的“特质”、战斗单位和基础设施。玩家对城邦基础单位、科技、人文、娱乐等方面的设置也会影响文明的进程,文明的领袖也会在竞争中体现出自己的独有特质——有些特质会在早期出现,而另一些则稍后才会出现。
文明6中的领袖在《文明》系列游戏中,不仅有秦始皇、亚历山大、克利欧佩特拉等历史上的重要政治人物,同时还有《战争与和平》《鲵鱼之乱》《楚辞》《月下独酌》这类巨作的设定。强大的政体或许是文明建立之初的必要,而文明的发展却离不开科技、人文、艺术等方面的发展。
二、“砍二”阿兹特克文明
在《文明VI》的DLC包中,以双头蛇作为城邦图腾的阿兹特克文明被称为“打架最强的文明”。在《文明VI》的设定中,阿兹特克人的领袖蒙特祖马一世堪称暴躁老爹、远古战狂,常常用“抓去做奴隶”这样的口头禅去威胁邻邦——也正是由于阿兹特克文明在文明6前期表现得过于生猛(中二),因此阿兹特克文明也被亲切地称为“砍二”。(此昵称也与一名玩“阿兹特克文明”的狂热网友的ID有关)
历史上的阿兹特克人也十分好战,并有人祭传统。这个民族的祖先来自北方,一个叫阿兹特兰的土地,后来他们来到墨西哥的特诺奇提特兰,建立了这座雄伟的城市。阿兹特克文明是世界历史上独树一帜的古文明,于15世纪在墨西哥中部建立了帝国。拥有较精确的历法系统。农业方面,灌溉技术发达;经济方面,已经出现了原始阶段的“货币”。但除了“好战”名声远扬,阿兹特克文明还有一个特点相当有名:他们从未发明出轮子,也不使用负重用的牲畜。
《文明》系列的的丰富之处或许就在于,我们既可以指挥一个没有车轮的文明成为世界之王,也可以在征服世界的同时,了解“文明”之于世界的必要之处。
阿兹特克宇宙观与其他“主流”文明相比,阿兹特克文明的宗教信仰与神话故事可谓是别具特色。作为城邦标志的双头蛇就体现了阿兹特克信仰的“双重”观念——这条蛇不但有两颗头,且与阿兹特克宗教信仰有着密切关系。由于资料的缺失,现在我们已经很难想象这个精美的双头蛇在宗教仪式中发挥了何种作用。但这个双头蛇很可能是阿兹特克神话体系中的一种混合的生物——蛇鸟,或长着羽毛的蛇,即阿兹特克的神明羽蛇神(Quetzalcoatl),象征着雨水与丰收。
双头蛇文明6游戏中的城邦标志除了双头蛇,阿兹特克的神话还体现在阿兹特克文明的军事系统中。在《文明VI》中骁勇善战的雄鹰战士,就是阿兹特克三大武士集团中的成员。除此之外,阿兹特克还有美洲豹武士(虎武士)、弓箭武士、骷髅武士等。对于阿兹特克人来说,美洲豹不仅是中美洲非各个神话中常见的动物,美洲豹获取猎物时的勇气和智谋也为好战的阿兹特克人推崇。因此在关于阿兹特克战士的形象描绘中,这些好战的阿兹特克战士们往往披着豹皮、长着豹爪。同时,因为美洲豹习惯于在黑暗中捕捉猎物,在一些中美洲的神话故事中美洲豹还时常与黑暗、冥府联系在一起。
尽管阿兹特克文明的战士们看上去都非常的生猛,但历史典籍中的他们却画风奇特——可以说是史上最大反差萌。阿兹台克的书写系统使用的是图像字符,而非是字母构成。因此,尽管今天看来这些卷轴画风奇特,但它们却真实地记录了阿兹特克文明曾经辉煌的历史。作为文化表达的重要形式,这些文献本身也是阿兹特克高度成熟的信仰系统中的神明的一种象征。
除了祭祀仪式、精美的艺术品、图画外,阿兹特克文明的信仰系统还体现在他们高超的建筑水平上。在文明6、《古墓丽影》中,都曾出现过阿兹特克文明的重要城邦——神秘的特诺奇提兰城。特诺奇提兰城是一个建在德斯科科湖中心的城市,一条条人造堤道构成的网络将它的各个城区以及它与陆地连接起来。16世纪的特诺奇提兰城内有 20 万居民,人口可能比当时任何一座欧洲城市都多。它存在过的所有证据,现在仅存在于西班牙征服者们的叙述,以及天主教方济各会托钵僧们记录下的几个阿兹台克人的话语之中。这个在前哥伦布时代最繁盛的大都市的瓦砾废墟,目前都被压在现代墨西哥城的巨大水泥地基之下。
那么,为何曾经生机勃勃的阿兹特克文明在历史的进程中戛然而止?
或许,我们需要将故事转向16世纪的某个时刻——1519年2月,一支西班牙远征军在墨西哥南部的尤卡坦半岛海滩登陆了。而那之后所发生的,可以被称为人类历史上最为灾难性的一次相遇。
三、伟大文明的衰亡总是容易被夸大
在文明6中,蒙特祖马一世是阿兹特克文明的统治者。
蒙特祖马一世生于1398年,是特诺奇提特兰城的第五代国王,也是阿兹特克的第二位皇帝。在他29年的统治期间,阿兹特克帝国完全统一且有大规模的扩张,历史上称为“三国同盟”,而且颁布了一系列的新禁奢律法(用以约束浮滥的物资消耗与颓废的生活方式),这让原已存在的阶级体制进一步地深入阿兹特克人生活的每个层面。
公元1469年,蒙特祖马一世逝世。继位的是他19岁的儿子阿哈雅卡特尔,阿哈雅卡特尔后来生了蒙特祖马二世。《科尔特斯攻占特诺奇提兰》而正是年轻的蒙特祖马二世将同样年轻的阿兹特克文明拱手让给了埃尔南·科尔特斯及其征服队伍。
阿兹特克人画的西班牙人登陆埃尔南·科尔特斯(Hernan Cortés)是一个西班牙贵族的儿子,同时也是一名职业军人。科尔特斯登陆尤卡坦,并不是要劫持奴隶,也不是对海岸进行小规模勘探,而是意在侵略。
可以说,他是历史上最敢下注的赌徒之一:这个西班牙人率领着600人、14匹马和14挺加农炮,就敢向拥有百万人口的帝国开战。
尽管文明的兴衰往往被理解为历史的轮回,而我们或许不得不这样承认以下事实:一个文明的衰落往往是另一个文明胜利的宣告。
英国学者戴维·奥卢索加曾在《文明II》一书中指出,埃尔南·科尔特斯和西班牙征服者对征服故事的描述或许是被严重地美化过:他们夸大了西班牙侵略者的勇气、斗志与决心,刻意无视阿兹特克人在保卫家园的过程中表现出来的聪明才智。同时,在传统的描述中,西班牙殖民者和诸修会托钵僧到来之后,阿兹特克文明被抹掉的程度也被有意夸大了。虽然 16 世纪西班牙与阿兹特克王朝之间的战斗,其惨烈程度无疑在整个人类历史上都是少有的,但还是有一部分阿兹特克文化残留了下来,甚至发生了一定程度的文化融合。毫无疑问,关于伟大文明衰亡的报告总是容易夸大其词。
戴维·奥卢索加一个世纪之前的1402年,曾经发生过另一场征服,那是卡斯提尔人对加那利群岛的进犯。一系列的登陆、战役和巩固战事几乎持续了整个15世纪,成千上万的当地瓜安彻人被屠杀或被捕为奴,其他坚持在漫长而无果的战事中抵御卡斯提尔军队的人们,也纷纷倒在了欧洲的传染病之下。
从15世纪90年代到16世纪前十年之间,在西班牙对古巴和伊斯帕尼奥拉等加勒比海岛屿的征服中,类似的事件还在多处上演,当地人民同样被俘为奴,承受着极端的暴力与残酷奴役。移居到这些征服区——加那利群岛、古巴和伊斯帕尼奥拉岛的西班牙统治者是第一批现代意义上的殖民统治者:他们意识到,在这些远方殖民地上的搜刮和奴役所得,不但是一笔巨大的财富,还能在极短的时间内提升自己在故国的社会地位。
蒙特祖马的军队在抵御西班牙人时,使用的剑锋是用石块打磨而成的,他们的箭是镶接的,但箭头不是淬过火的金属,而是火烤加硬的木料。他们起初尝试采取惯用的步兵战术抵抗西班牙人,但面对马背上的西班牙征服者们,这些英勇的美洲豹战士、飞鹰战士们也无计可施——如果打个比方的话,那就那时的阿兹特克人相当于面对16世纪的主战坦克。
科尔特斯攻占特诺奇提兰尽管有着诸多军事上的不利条件,阿兹特克人在人数上的绝对优势本来也不该让西班牙人有任何胜算——即使有特拉斯卡拉人加入科尔特斯麾下也不行。真正起到决定性作用的,完全是征服行为带来的文化冲击,以及西方传染病造成的灾难性后果。最严重的就是天花,这种在当时欧洲极其常见的病症,却让阿兹特克人完全无力抵御。
一位目睹这一事件的西班牙修士写道:“当天花开始袭击印第安人时,成了肆虐整片土地的恶性瘟疫,大部分地方,人口死亡超过半数……他们像臭虫一样成批成批地死亡,尸体堆在外面无人收殓。”但是被对黄金的贪欲所支配的科尔特斯及其手下,对阿兹台克人的遭遇是无动于衷的,他们也没有试图去理解自己击败的文明所拥有的文化和艺术。在对特诺奇提兰城的围攻与后续的破坏中,大量当地艺术品遭到洗劫,大部分的城市也被摧毁了。由于对阿兹特克地区广泛实施的人祭行为感到日渐憎恶,西班牙征服者们心中燃起宗教使命的热情,继而展开了更加激烈的宗教毁灭行动。就这样,来自西方的传染病与侵略的野心使得曾经不可一世的阿兹特克文明消失在了历史之中。
一个罗曼蒂克的故事背后,或许是另一种文明的消亡。带着对“文明为何”的疑问,2018年BBC开启了全新的《文明》(Civilisations)纪录片项目。在这部豆瓣评分高达9.1分的纪录片中,著名古典学教授玛丽·比尔德、戴维·奥卢索加等主讲人带领观众穿梭于古代南美洲奥尔梅克文明与古希腊雕像之间,在中世纪主教座堂、清真寺等世界建筑瑰宝中重新讨论了文明的多种形式。
《文明I》、《文明II》两本书,就是这个新纪录片项目的一部分。在这套书中,作者们用充沛的史料回应了以往论述中的“西方文明史观”,也向全世界的读者和观众有力证明了女性、非洲文明,以及许多之前在西方文化节长期被边缘化了的群体也有创造卓越文化艺术的能力,他们在世界文明史上扮演的角色同样不可轻视。
事实上,无论是文明本身,还是人们对文明的理解和评述,都是在不断的讨论和修正中得以演进的,而《文明I》、《文明II》也正是这种讨论的重要组成部分。文明,它既包含价值连城的杰作,也包括廉价的小玩意,它既是历史学家们对过去的追溯,也是一代又一代曾经使用、解读、争论过的这些形象,并为之赋予意义的人们。
当当直达: http://product.dangdang.com/27932699.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