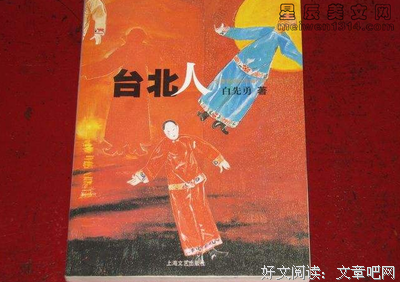
《台北人》是一本由白先勇著作,爾雅出版社出版的342图书,本书定价:240NT,页数:2010,特精心从网络上整理的一些读者的读后感,希望对大家能有帮助。
●因为某人,才读了此书
●断断续续地,终于读完了去年在台北买的《台北人》。此书在文坛的地位、所受的赞誉自不必多说,然而,或许是时代所限,我个人却对这种过于细腻与凄怆的文字难生好感,只不过是抱了一种对末日英雄的好奇与怜悯读罢此书。
●这本书像是开启了一个新的世界,我从没有接触过的。台北在作者的笔下,是搬去的上海与南京,缠绕着乡愁,缠绕着意气风发光辉岁月。年轻的军官,色衰的舞女,伶仃的仆人,在他们口中诉说出来一幅幅大时代背景下的悲剧。
●里面有些描写和用词很“道地”,跟我平常能接触到的很不一样,但是我有能马上明白什么意思。这种感觉太奇妙了。
●背井离乡后,我们缅怀过去的快乐与荣耀的时候,是否代表着我们在逃避现在呢?喜欢白先生笔下那些人物给我们带来无限的思考!
《台北人》读后感(一):悲情台北
白先勇的这本台北人由多个短篇组成,讲述了一个个刚从战乱中退守台湾的三教九流的悲惨故事。
有舞女,将军,教授,妓女,书生,贵妇人,军官以及国民党的普通士兵和他们的爱人,他们都经过战乱,他们又刚刚稳定生活。但他们没有任何一个能割舍掉海对面的过去,那里有他们挥不去的记忆、情感、亲人。
所以,他们是一群落魄的人,战争过后没有让他们有些许安定,他们是活在过去的人,他们苟且偷生,大都又悲惨死去。
看到《冬夜》那一則,我竟然有點想哭的衝動。
白先勇看過的生活,就算是退到台北的落敗,大部份也是透著華麗的姹紫嫣紅。背景怎麼昏暗,都要喧嘩出一段曾經的繁華。人物也是濃彩重墨,被虐殺的妓女,粉身碎骨的將士,落寞的將軍太太。
可是《冬夜》不同,畫面里兩個教授,在雨夜里,坐在露出棉絮的沙發,喝了一遍又一遍的龍井,是多么灰暗的景象。幾位曾經的五四青年,到了晚年,卻不知人生何處是歸途。灰色里的唏噓,真像那般雨夜,冷冰冰的雨水打在這個世界,無須解釋。
或许是看了太久的长篇,这部短篇集总给我一种人物丰满之后等待故事高潮时情节却“戛然而止”的感觉。而仔细想想,即使故事不甚“完整”,也很好地应和了“台北人”这一主题——这部书原本就是写人的。正是这种蒙太奇式的刻画,叫人对老一辈台北人有了直观的印象。而这些人物的特点——坚强、世俗、义气——也许正是台北人(抑或说是外省人)共有的性格基因吧。
不得不说,与余光中这样的海峡诗人相比,这部作品的文笔逊色了一些,对老上海十里洋场的描写,也总是少了那么一点神韵。但所有这些故事里,都有着一种苦楚的美,让人为之动容落泪,这种美是和如何叙写描述是没有什么关系的,正所谓“山河不幸诗家幸”,这种美,正是来自国家的不幸以及人民的多情和无情,正如余光中作品的美,并不来自于他的文字的。
值得一提的是,最最感动我的一篇,竟然是《梁父吟》。光光是故事里的那份谦卑和人物举手投足间的礼让,总让我着迷,十足的民国范儿,让人不禁反思这几十年来,我们大陆究竟失去了什么。
《台北人》读后感(四):为那些很“道地”的描写和那些切片式的故事
有幸去台北旅游,然后买了这本书,唯一原因是因为白先勇这个名字。
这本小说内容和质量没有让我失望,但是描写的场景却是那么苍凉,让我看完后有种对岁月很失望的感觉。
不管是灯红酒绿的生活,还是百姓人家的日子,不管是悲惨的妓女,还是失落的退伍军人,还有那些逃难过去的人,这些描写竟都让我读出一丝丝的悲哀。是因为失去家园?是因为人生起伏?是因为时间易逝?作者的这些哀愁就像点燃的一只香一样,袅袅扰扰,在我读它的时候无声无息地潜入我心底。
最动容的几个场景:
1. 两个教授相遇时的无奈。曾经的豪迈和张扬,曾经的报复和理想,如今却只剩下两个步履蹒跚的老人,以及一杯杯的龙井中的慢慢叹息。
2. 烟花女子从良之前的心路历程。这位“大姐”级的人物在青楼中打拼这么多年,最终带着心中诸多的遗憾离开。这个过程是喜还是悲?真的只有她自己能懂了
3. 退伍老兵的失意。只因为性子太烈,上得了战场,却下不了职场。最后让自己的下属反而超越了自己。而自己只能酒醉人生。
这本小说读得我尽是失落。只有失落。
看到失落,才知道珍惜。
《台北人》读后感(五):臺北人
《臺北人》,買了許久的一部小說,由於一直被《寂寞的十七歲》時期的白先勇吸引,因而未有一口氣看畢的衝動。可是,近來氾濫地接觸的臺灣歷史,牽扯著我那福爾摩莎濫觴。
我向來很喜歡白先勇,結果六小時讀完《臺北人》。經歐陽子的導向,我一樣「飛入尋常百姓家」,縱然我非「舊時王謝堂前燕」。那個憂患重重的時代,對過去的依戀,回憶的執著是如此要人瘋癲。渴望活在屬於自己的時空,自己的時代。
《花橋榮記》、《遊園驚夢》、《冬夜》是我最喜愛的三篇作品,而全書裡頭的人物彷彿就是當年衛星圖下的臺北人。不該說彷彿,因為他們就是貨真價實思念往昔的臺北人。作為香港人的我,有沒有那份感傷?我告訴你,只要是有過去的人,也能知道那種煎熬。
《冬夜》中積極尋求出國的余教授;《花橋榮記》裡等待愛人的盧先生;《遊園驚夢》不知潮流的錢夫人,他們都被稱為「臺北人」,但他們心靈與臺北的疏離與隔膜,形成生活的悲涼,對命運的無奈與諷刺尤其明顯。白先勇對這些人物有一種無可抗拒的憐憫,而現實中他們又是多少臺北人的影子?
說到人物,我最喜歡並且敬重是《梁父吟》的樸公,他未因過去的璀璨而忘記活於現在,也沒有為唏噓而失去面到現實的尊嚴。白先勇透過雷委員展現對他的尊敬,最後記下棋譜,下次再續的舉動,與今日青年人打電動時的執著過關無異,那是一種積極取態。
現代主義並非不寫實,但說到書寫內心世界,的確是爭脫寫實主義的外圍建築,更深地挖進人心。不過,寫作當然不是要表現主義,作家不是為主義而寫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