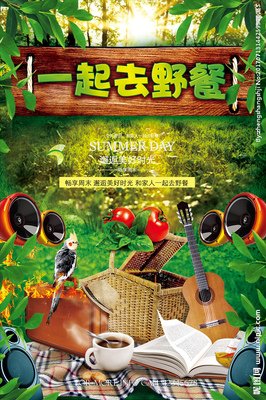
《路边野餐》是一本由(俄罗斯)阿卡迪·斯特鲁伽茨基 / (俄罗斯)鲍里斯·斯特鲁伽茨著作,四川科学技术出版社出版的平装图书,本书定价:15.00元,页数:168,特精心从网络上整理的一些读者的读后感,希望对大家能有帮助。
●最大感想——封!面!太!难!看!老塔原来仅仅只是用了本书的设定,之后走的比小说更远,不过小说本身也很有思想性,路边野餐理论见解独到,“跟造访带打交道,有这样一条法则:带战利品回来是奇迹,活着回来是胜利,巡逻的子弹没有打中你是狗屎运,如碰到其他结局是命中注定”,个中指涉和隐喻明显,我们都别无选择,我们都必须纵身跳下
●我没有看过《潜行者》,多年前看齐泽克的解读,对“只能实现人内心最深处的愿望,但人并不知道自己的愿望是什么“很感兴趣,但读了文本,打动我的更多是围绕这个外星人造访区,几代人的拾荒经历和特殊生态,让我想起了被火箭废弃物影响地区的人们。——不知道谁有《潜行者》的电影资源?
●2013.7.26
●挺有趣的。对故乡呢,就是,爱也说不上,恨也说不上,离开和留下的都很固执。
●给我震撼最大的一句话的大意是:你怎么确定外星人的理性和地球人的理性是同一种概念
●莫名其妙喜欢,里头有很多有趣设想,对小人物的解析也有独到之处。
●讲述的都是中年危机的事情。 第三篇算是有科幻色彩的中年危机。 概念很好,但是却没有按照类型向发展。结果就是太文艺了。
●科幻小说的意义之一在于展现人类的无知与渺小,这本小说做到了。
《路边野餐》读后感(一):一部封面醜哭了的科幻小說
這是本兩百頁不到的小書,起初很枯燥,讀兩頁我就丟在一邊,然而漸漸的越讀越覺得非凡。書名“路邊野餐”是故事中科學家對外星接觸事件的一種猜想,即外星“造訪者”並不像多數人想像的那樣對地球有任何企圖,他們甚至對接觸沒有任何預想,不過像一次路邊野餐一樣,在地球歇個腳罷了。
“路邊野餐”的猜想仿佛戲謔般,讓地球歐洲人神聖理性的標準變得搖擺不定,無論“潛行者”、投機者、科學家還是政客,在“造訪區”的所作所為都如群魔亂舞般荒謬而滑稽。究竟誰是理性的,而理性又什麼呢?
讀到結局不禁感慨,無論如何,人混亂的,隱秘的,執拗的嚮往(慾望?激情?)乃真實存在於與現實的對抗之下。至於外部世界、外星生物到底對人本身,或者說有限的人及其所接觸的有限環境能有多大影響呢?人終究要迴歸自己促狹又矛盾叢生的陋室中,跳自己的那隻舞。
《路边野餐》读后感(二):路边野餐:一次“事件”
根据齐泽克的考察,“事件”意味着“遭遇的”、“神秘的”和“打破世界结构的”。如果严格遵循这一标准,人类有史以来唯有耶稣降生算得上是一次真正的“事件”。这种事件实际上是一种更高的存在者的介入,而这一介入对于人们的世俗生活传统具有被动性(被卷入)、神秘性和颠覆性。
在同样的意义上,《路边野餐》建构了另一起“事件”,即外星文明的介入。更进一步说,这种介入是如此短暂却又造成了如此深远的冲击,恰如一次路边野餐:人们起初只是随意地拣一块草地坐下,等到野餐结束一哄而散,留下一地垃圾,却变成了穴中蝼蚁们的圣地。这一突如其来的“神迹”为它们提供了数不胜数的“资源”,于是它们甘冒生命危险流连于此,尽管永远无法理解其中奥秘。
对宇宙中的低级存在者而言,“介入者”无论是上帝、外星人还是人类,首要问题唯始终是当下可供充饥的面包碎屑。宗教和乌托邦高高在上,饥饿和痛苦却常伴左右,是真正本质性的生命体验。外星造访者介入的无目的性夸张地再现了这一境域。
小说主人公舒哈特就是这样的蝼蚁,为了延续自己的生存和治愈女儿的病痛,他与如他一样的“潜行者”出没于危险的外星“遗迹”内,周旋于市井之徒与秘密警察间。但比蝼蚁更为可贵又可悲之处在于,人类是居中的存在者,同时有着作为蝼蚁的生存欲念和朝向上帝的价值追求。如果尘世的处境越来越将二者对立起来,人最终就会被自身这两种力量撕裂:要么像蝼蚁一样苟活,要么像耶稣一样死去。
20200802补记
《路边野餐》读后感(三):哈哈镜折射的内心
在“猎人”的贴吧看到人谈论此书,说富奸构思“黑暗大陆”时恐怕借鉴了此书。为了了解最有想像力的漫画家需要参考什么样的小说,我立刻拜读了此书。果然,两者之间颇有气息相通。
皎然说诗有三偷,“偷势、偷意、偷句”,前者精巧,后二者罪不可恕。一个是漫画,一个是小说,富奸自然不能向《路边野餐》偷句,但他和斯特鲁伽茨基兄弟都各自营造了匪夷所思的秘境(黑暗大陆和造访带),并令其中充满了各种各样的神秘事物。虽然在细节上并不相同(如果相同,那就是偷意了),但两个环境的“势”绝对神似,这体现在两点:一、秘境的性质和机理全然超出人类的理解范畴,难以研究、难以解释;二、秘境事物都蕴含巨大的能力,或者如瘟疫黑洞,轻易取人性命,或如永动机长生药,价值连城。自然而然地,秘境会被政府和其他强力机构严格控制,既为了避免灾厄,也为了垄断利益。但也会激起部分人类的野心,让他们铤而走险、火中取栗。在黑暗大陆,这就是猎人,而在造访带,这就是潜行者。然而,接下来两个世界的发展就截然不同了。在富奸的设定里,黑暗大陆是包围人类已知世界的广阔天地,那里的事物都巨大无比。在比喻的意义上,猎人们的探寻也同样是向外的,是征服未知、壮大自我的过程。而在斯特鲁伽茨基兄弟的故事中,造访带是外星人在地球经过时擦出的几个小点儿,不过是区区几个镇子的范围(而故事只发生在其中一个小点儿内外)。换言之,造访带被广阔而平凡的人类世界囊括其中。同样在比喻的意义上看,这似乎暗示着潜行者的探寻是内向的,其本质上是对自身的欲望与观念的重新认知。这种暗示在本书的结尾体现得尤其明显。发现被有预谋地当作炮灰的年轻人怀着人人自由幸福的希望死去时,主人公瑞德的整个人都不好了。在他的歇斯底里状态中,故事结束了,但留下了一个开放的问题:内心深处,我们真正的愿望是什么?
以上两种关于秘境的构想并无高下之分,富奸也算是漫画家中相当有思想的了。但相比起来,斯特鲁伽茨基兄弟以神秘事物植入普通人生活的做法,似乎让人了想到更多的东西。
《路边野餐》读后感(四):从《路边野餐》到《潜行者》的转变
谈原书《路边野餐》,经过剧本《愿望机器》到电影《潜行者》之间经历的转变。
作为电影《潜行者》的原著小说,很多读者都是因为看了塔可夫斯基的电影,从而认识了本书。本书和电影之间的差异很大,孰优孰劣,影迷书迷朋友们至今争论不休。所以我抛砖引玉,谈一谈关于原书《路边野餐》,经过剧本《愿望机器》到电影《潜行者》之间经历的转变,希望帮助各位理清从《路边野餐》到《潜行者》之间的逻辑关系。
首先,《潜行者》的编剧是斯特鲁伽茨基兄弟,而非老塔。他们主导剧情的创作,甚至当时的片场工作人员中流传着一种导演不是老塔,而是斯特鲁伽茨基兄弟的说法。剧本的创作修改不下六次,电影最初版本设定和最终很不同,但这很大程度上是由于斯特鲁伽茨基兄弟而非老塔。
斯特鲁伽茨基兄弟在《潜行者》片场当时老塔读了斯特鲁伽茨基兄弟的《路边野餐》后,很感兴趣,想把它拍成电影。他欣赏斯特鲁伽茨基兄弟的作品,想借此机会也让两兄弟进军电影圈,就聘请了两兄弟来当编剧,负责剧本的写作和修改。 该片的第一版剧本、也是影片名叫做《愿望机器》。在最初版本里,潜行者的角色是一个邪恶的人,他杀死自己带进“区”的人,只是为了想让自己的女儿恢复健康。而我们知道,在最终的设定中,向导更接近于一个基督徒的形象,和最初设定完全相反。
在当时向苏联电影总局提交的剧本上看,《愿望机器》的背景设定是在一个70-80年代左右,一个不知名的资本主义国家里,在潜行活动出现的几年前,一艘外星飞船降落到一个小镇上,外星人走了,但是留下了“区”——一个充满诡秘奇异的地方。武装军团都想夺得这个外星宝藏,尤其是那部只要任何人走近,就能达成愿望的机器。而“愿望机器”受到各种致命陷阱的保护。向导“秃鹫”是一个无视任何道德法则和荣誉的人。武装军团派出代表和“秃鹫”达成协议,他要是能够潜入“区”,取得“愿望机器”,就能获得一大笔美钞。他于是潜入“区”,取走机器。
影片融入了惊悚元素和前卫的哲学思想,以及对小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批判。拍摄选址最先是在塔吉克斯坦的伊斯法拉,后辗转到了乌克兰城市塔林郊外,一处废弃的钢铁厂外围。之后老塔和天才摄影师雷贝格一起开始了电影的第一版本拍摄,第一版影片用了大量的特效来表现“区”里的奇异现象。
不同于一般的摄影师,雷贝格认为要想通过镜头更好的表达,摄影师需要参与剧本的修改。在与塔可夫斯基共同拍摄的过程中,他都参与了剧本的创作,《镜子》中的构图设计与场面调度,便是塔氏根据雷贝格的意见修改的。
在影片的拍摄初期,雷贝格和老塔便在广角镜头和长焦镜头的使用上起过不少争执,甚至直接找到斯特鲁加斯基兄弟要求修改剧本。但老塔对此一意孤行,凭借着自己拍摄电影的原初动力将潜行者第一部付梓。表面上看来,他是在最佳的状态下工作,但他也逐渐开始发觉到,这不是他想要拍的电影,他并不想拍摄第二个《索拉里斯》。但让他认错是不可能的,他不能说自己错了,并不能说:“我不过是一届小导,以后会拍得更好的”之类的话。大家都知道老塔对电影不满意,但又不敢说什么,片场的氛围越来越尴尬。
之后,由于冲洗人员的失误,导致送去冲洗的第一版胶片一片空白。这并非摄影师的过错,但对于老塔来说,正好找到一个人背锅。他责怪雷贝格平时生活作风放荡,没有仔细检查胶卷,以此为理由将摄影师,美术指导等一批人踢出了剧组。
之后,老塔重写了剧本,剧本是按照雷贝格的意愿来修改的。斯特鲁加斯基兄弟也重写了剧本,因为他们意识到,向导不应该只是个捡破烂的角色。并将《愿望机器》改名为《潜行者》。
至此,斯特鲁加斯基兄弟的思想经历了从原书《路边野餐》,剧本《愿望机器》到电影《潜行者》的转变。由此我们可以认为,《潜行者》融入了斯特鲁加斯基兄弟后期的更成熟的思想,而非塔可夫斯基一厢情愿的改编。
本书评引自以下影评,https://movie.douban.com/review/8408963/
《路边野餐》读后感(五):如果最后能让我许愿
主人公瑞德,乖戾,并且暴力,眼中只有钱的经验主义者。唯一的和颜悦色,是给一个异常执着异常专注的书呆子同事。
那个书呆子代表着沉重现实里的一丝进取之光,而书呆子的暴毙,代表着瑞德彻底跌进现实深渊——希望之光已陨落。瑞德与唯利是图的同行前辈勾心斗角,同处处逼诱的警察周旋,而原本外星人留给地球的造访带,人类文明飞跃的契机,却由于人类无法越过文明等级的鸿沟,成了名副其实的地狱,它不会给擅于探险的人带来声誉,只会带来周而复始的以命博弈。
书里,蚂蚁一样的人类对应着看不到自己存在的高大文明,朝不保夕的潜行者如瑞德,对应着让整个人类一筹莫展的文明阻碍大事件,在大事件里,个人的贫困愁苦犹如一粒沙对应着大海,它不值价,于是瑞德活法是行走的畜生。
乖戾,暴力,唯利是图。
这是一种变相的报复社会的活法。
世道艰难,才显形的妖孽活法。
许愿金球这种在太平盛世绝对不会有人追求的东西,却让一干或理智或贪婪或受过高等教育的人前赴后继。
瑞德带着傻白甜青年寸步移动地前行,傻白甜青年几次坏事,暴躁的瑞德都忍耐了下来,恰恰不是瑞德人到中年变得仁厚,反是瑞德彻底失去自我驱策,终向现实臣服的证明。
多么讽刺啊,能实现人愿望的宝物,却要让人丧失最宝贵的东西为代价。
让我们来重温细品这一段:
...Arthur突然跳了起来,一把拉开夹克上的拉链,脱下来扔在脚底下,扬起一阵白色的灰尘。他不知道喊着什么,做着鬼脸,挥舞着他的双手,接着他把手放到背后,跳了一小段快舞,就直接朝底下冲去了。他也没有再看Redrick一眼,他已经完全忘记了Redrick了,他也已经忘记周围的一切了。他只想跑下去,向它许愿,那属于一个还会脸红的大学生的一丁点秘密的小愿望,这孩子除了零花钱就没见过其他的钱,如果哪天回来有一点酒气,也会被他爸打个半死,这孩子未来有可能会成为一位有名的律师,甚至是内阁大臣,更远一点,也许就是总统。而Redrick,眯着眼面对着那片刺眼的白光,看着他跑了下去。他很冷静,早就知道这一切都会发生,他也知道他不该看,但看看也没什么大碍,所以他看着这个冒失的孩子一路跑下去,而实际上什么感觉都没有,除了内心深处有一只小虫子开始四处爬动,一口咬穿了他的肠子。
那个孩子仍在朝下跑着,不停地跳着混乱的舞,身后扬起一阵白色的灰,他还在兴奋地大声喊着什么--或许是在唱歌,也有可能是在念咒--Redrick想,这可能是历史上第一个像去参加一个狂欢派对的人一股脑冲下采石场。起初他并没有留意他的会说话的钥匙在喊些什么,但接着他听到内心深处有什么喀哒一响,只听见Arthur喊道:
“每个人都幸福快乐!...自由!...你想要多少就有多少!...所有的人都到这来啊!...每个人都会有的!人人都会实现他自己的愿望!...自由!...幸福!...自由!”
但突然他停下了呼喊,就好像有人对着他的喉咙重重打了一拳。Redrick看到那片潜伏在矿工木桶阴影里的半透明的东西抓住了他,将他抛向半空,慢慢他整个人开始旋转起来,就像一个家庭主妇在洗衣服那样。
Redrick甚至还看到他的一只鞋掉了下来,飞向采石场的更高空,他转过身来,坐下。脑海里什
么想法都没有,有段时间甚至连自我都感觉不到了。在他身后,那条路就躺在那,四周寂静,空气沉重。
傻白甜被绞成了碎肉。
后面瑞德疯了,他是带着无比明确的目的,给傻白甜设下的周密圈套,以及良心能承受的谴责评估,来到的这儿,结果他万万没料到,这场职业生涯的最危险之行,却是这样毁灭他的计划——将他一朝打回解放前,让他带着罪孽身,回到婴儿心。
他走过那个木桶,尽可能小心地将脚抬高避免踩到那些斑点,然后他趴下身,一步步爬过那个碎石堆,来到了那个跳动闪着光芒的‘金球’前。他浑身都汗湿了,炎热也让他不停地喘着气,同时,体内也涌过一阵寒意,他浑身抖个不停,就好像刚经历了一场严重的宿醉,而那些白色的灰尘也在齿间研磨,略带一点甜味。他在‘金球’前停下,想了一会儿,然后开始不停说他的那些祷告词:
“我是动物,这您也知道。我没什么冠冕堂皇的话,他们也没教我怎样说那些话,我也不知道该
如何去思考,那些混蛋也不让我去学习怎样思考。但如果您真的是...无所不能...无所不知...那您就自然会明白!看看我的心。我知道你要的东西全在里面,肯定在里面。我从没将我的灵魂出卖给过任何人!它是我的,它是人类的灵魂!你把我所想的那个拿走吧...而且它绝对不会是阴暗的东西!去他的,我这时候什么都想不出来,除了他说的这些话...‘每个人都幸福快乐,自由,人人都会实现他自己的愿望!’”
作为假刺激兄弟的最高水准之作,《路边野餐》有三个不同层面的贡献,一是造访带和潜行者的设定,延伸出一部探险游戏不在话下,事实上还没真正被拍成电影,也怀疑是这部上世纪70年代的作品设定太先锋,到现在电影技术以及头脑想象力依然拿不下。二是书中对人类遭遇高等文明方式的别开生面的设想,写实程度至今依然让人具有强烈共鸣,同时借由书中科学家之口提炼成一种蚂蚁对大象的哲学观,清醒到宛如入定。三是蚂蚁对大象的哲学观完美的映照到了人类个体对整个人类大事件,最终阐述无论你拥有怎样的个人意识,无论你凭这份意识日天日地横行直撞地挣扎,但你依然是整体的部分,你可能失去支撑你活到今天的意义,随时会为整体而牺牲。
也就是你再胡天胡地,胡作非为,做尽下作之事,你也可能会有为理想而牺牲自己的一天。
这可比安德烈塔可夫斯基的庸人自扰式唠唠叨叨,看上去是自我开解其实干我们屁事的意淫改编好多了,就像一个高中文科生对哲学巨擘的心血之作抒发了一番理解,辣眼睛。
更别说那部连本作品取名立意一丝精妙都没沿袭到的同名中国农村电影。
你把老年人给自己初恋的磁带献媚给路边发廊小妞,就问你的浪漫泡妞法是小学体育老师教的吗?这么猥琐。
个人问题请不要拿出来当现象,阴阳怪气,这类导演先举报100次再说。
想了想,如果瑞德走上傻白甜之路后,我能螳螂捕蝉黄雀在后,面对许愿金球,此刻过去所有许过的愿都在人到中年的我脑海浮现:
“考上重点高中。”
“家人健康平平安安我便足矣。”
“嫁娶一个好人。”
那就太便宜金球了,许一个大的,就发现,总归逃不过“成为一个成功的人”,而成为成功的人,终是到了回馈的时候。
不如趁早把它实现了,从此放了自己——
“愿每个人都快乐,自由,愿所有人都兴致勃勃,满载而归。”
这个翻译要好一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