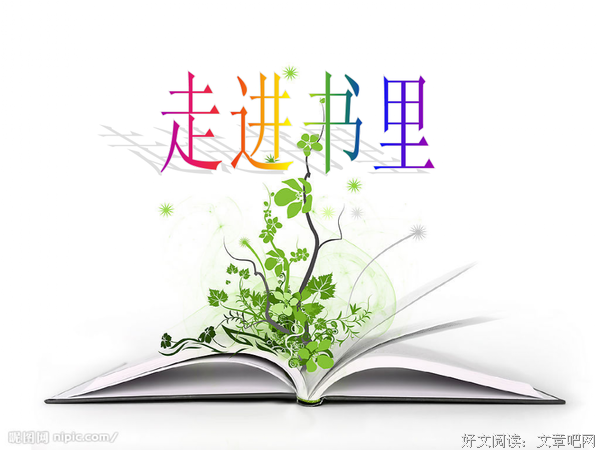
《自己的园地》是一本由周作人 著 / 止庵 校订著作,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出版的平装图书,本书定价:20.00元,页数:248,特精心从网络上整理的一些读者的读后感,希望对大家能有帮助。
●2017、9、22阅讫于宁乡梅家田。二读也。
●早上看票圈,发觉都在转洪爷的一篇文章,谈文学上的“意味”与“意义”。对于周作人,有讲到“意味”。读完这一本,我的感受是日常生活的观察者。若要说“意味”的问题,我觉得不只是意味,有些意义也许不那么明显,但还是有的,毕竟还是没有办法二元论的。
●略读
●周作人小品文迷~
●周大人~
●每个人有自己心中的园地,越来越喜欢在这样的心绪下遇见周作人。
●送给一个骚年了。
●好像饭后散步一样小时候惯常的仪式我流着哈喇子站在家兄的书柜前,他介绍到这本书的时候并没有揪出周作人是如何著名来讲,而说散文写到这个地步,有棱有角,又无痕迹,当牛逼视之。他这样说,以至于我将这本书的名字牢牢记下,却忘了作者是谁人。每每想起来原是周家二哥写的,都有一种新发现的奇异之情涌起。/ “他正如这样的一个人,走到猎人的寓居里,说道,你们看这月亮很奇怪,我将告诉你,月亮是怎样做的,又为什么而做的。既然告诉他们月亮的事情之后,他又接续着讲在树林那边的奇异的都市,和在独角兽的角里的珍宝。倘若别人责他专讲梦想与空想给人听,他将回答说,我是在养活他们的惊异的精神,惊异在人是神圣的。“ / 我希望他能在《旧梦》里更多的写出他真的今昔的梦影,更明白的写出平水的山光,白马湖的水色,以及大路的市声。
《自己的园地》读后感(一):“但是我们不妨听他说自己的故事。”
读到这本书中一段,感觉颇有深意,又不知道自己的理解是否与先生本意一致,想请教大家。
这段话的大概意思是讲,各个文明中曾光辉闪耀的圣人,在历经千百年后,他们所提倡的那些”道德“都不再被人们所关注(这里应该所指向了新文化运动之后对孔孟儒学态度的转变),作者认为这种现象是令人惋惜的,应当有可以理解他们的人存在,但另一方面,他也觉得在如今践行圣人所谓的德行是一件难如登天的事情。与圣人相对的,那些不讲究”道德“的文人,(以下是原文)“我们同尊敬圣人一样尊敬他。他的‘教训’在群众中是没有人听的,虽然有人对他投石,或袖着他的书,——但是我们不妨听他说自己的故事。”
我在想,这里把圣人与文人放在一起写,是为了说明那时的国民普遍没有深刻的思想性,而是随波逐流,追求浅层次的文学体验,并以此打造自己契合时代的文化气质吗?还是说在引导人们通过听听“他说自己的故事”来进入故事背后的精神世界呢?
《自己的园地》读后感(二):86. 自己的园地
2016.10.01-10.11
86.
《自己的园地》——周作人
原一九二三年所编成之后的重加编订的版本,留存“自己的园地”和“绿洲”两部分,将杂文完全除去,加上杂文二十三篇,为“茶话”一辑,共计五十六篇。
以内容论,自己的园地更接近于文艺批评(虽然作者在旧序中说“并不是什么批评,”但这主要是从行文态度和文体上来强调的)。“作者总结自己的创作生涯,说从写批评文章大概就从写自己的园地算起。可以说周作人的文艺批评理论,到此时逐告完善。这一理论有两个前提,一是承认文学的独立价值,一是承认创作的个人价值,二者是一致的。”
看了很一段时间,实在需要很费几分心力去看。周作人的文章博闻强识纵观中外,实在许多许多引用文献闻所未闻。对于作小诗等许多方面还颇有些共鸣,表达确实充分却又适当、克制。文品很棒,有风范。
行程上遇见的旅客问到说,莫不是只有台湾对周作人知道的人多些。我们大概是知道的,专业外不知道了,若果然则实在可惜。
书中《魔侠传》一篇,文末写道:
“本文以外,还有几句闲话。原本三十一章(林译本三之四)中,安特勒思叫吉诃德不要再管闲事,省得使他反多吃苦,末了说:‘我愿神使你老爷和生在世上的所有的侠客都倒了霉。’林君却译作,‘似此等侠客在法宜骈首而诛不留一人以害社会,’底下还加上两行小注道,‘吾于党人亦然。’这种译文,这种批注,我真觉得可惊,此外再也没有什么可说了。”
若我果然没有看错周作人的意思的话,实在太有同感之畅然了,忍不得要大笑三声。
248.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
2011.1第一版,第一次印刷
《自己的园地》读后感(三):说真话抒真情,便是最好的文艺
与嬉笑怒骂的哥哥鲁迅先生不同,周作人似乎一直以“冲淡平和”、“与世无争”的形象在文学史上占有一席之地。而《自己的园地》却让我见识了一个与以往刻板形象不同的,作为文艺批评家的凌厉的周作人。尽管作者本人极力隐藏自己批评家的棱角,但旧序中“批评是主观的欣赏不是客观的检察,是抒情的散文不是盛气的指摘”一句,已将其写作的目的暴露无遗。
“自己的园地”指“文艺”,无论是种果蔬,种药材,抑或是蔷薇地丁,在周作人看来,“只要本了他个人的自觉,在他认定的不论大小的地面上,用了力量去耕种,便都是尽了他的天职了”。周作人认为,“有益社会并非著者的义务,只因他是这样想,要这样说,这才是一切文艺存在的根据”,故文艺创作者无需将“载道”作为己任。在当时充分强调文艺创作的社会功能的时代背景下,周作人却充分尊重文艺创作者的个性表达。无论是否感染大多数人,无论是否符合社会发展的主旋律,只要是真实纯粹的作品,便是具有文艺价值的。
《自己的园地》中对于文艺创作者情感的抒发有着明确的界定。《诗的效用》中指出,诗的创作是近似于性欲一般生理上的需要的一种非意识的冲动,”个人将所感受的表现出来,即是达到了目的,有了他的效用”,这种情感的抒发带有某种不受控制的本能性。以这一观点为基础,我们也就不难理解周作人文艺思想当中对于各色文艺创作的包容与豁达。首先是宽容“文艺上的异物”,指出文艺作品应当用科学和艺术两种截然不同的眼光分别看待;接下来鼓励情诗的创作,支持在情的分限之内一切情感的表达;同时对强权之于文艺的粗暴干涉予以斥责,“倘若用了什么名义,强迫人牺牲了个性去侍奉白痴的社会,——美其名曰迎合社会心理,——那简直与借了伦常之名强人忠君,借了国家之名强人战争一样的不合理了”。
周作人的观点在当时收到了很多批评家的诟病,但其对于现代文学框架的奠定所做出的贡献却影响至深。时至今日,先生已经离开我们半个世纪,而我们却始终未能解开文艺创作上的桎梏。一味迎合大众心理的作品频频跻身书店的畅销榜,港台的文艺作品屡屡遭到封杀……或许,要做到真正的宽容,还需要一种植根于心底的文化自信。这种文化自信包括尊重个性的综合的国民性,而又不至于让这份尊重变为一种多事的帮助;包括容纳文艺的外缘,同时坚定地守住本性,而不至于一碰到外来文化便生发出一种本能的不安全感。文艺好比一颗稻或麦的种子,应当让其在自然的养护下生根发芽,任其自由生长,开花结果,创造出属于它自己的园地。
2018年4月1日
t.onSubmit(e.to
《自己的园地》读后感(四):瞎读记录
瞎读瞎写不负责任。
周作人散文的标签一直是冲淡平和、与世无争,而《自己的园地》中他所做出的批评和思考似乎打破了一直以来的形象,直击问题的批评可以说得上是凌厉,
特别是在《自己的园地》中,周作人做了很多有关艺术分析的批评讨论,一些内容仍然可以被用来当作思考现今问题的出发点。
周作人对人生派的艺术的界定并不是“为人生的艺术”:“‘为艺术的艺术’”将艺术与人生分离,并且将人生附属于艺术,至于如王尔德的提倡人生之艺术化,固然不很妥当;‘为人生的艺术’以艺术附属于人生,将艺术当作改造生活的工具而非终极,也何尝不把艺术与人生分离呢?”……“‘为人生’——于人生有实利,当然也是艺术本有的一种作用,但并非唯一的职务。总之艺术是独立的,却又原来是人性的,所以既不必使他隔离人生,又不必使他服侍人生,只任他成为浑然的人生的艺术便好了。”这正好符合了学界对于新文化运动的反思——强调了文学的工具化而导致文学的发展失去了自己的内在规律。读罢这一段,我体会艺术其实是在“自己的园地”中深耕出来的结果,“只要本了他个人的自觉,在他认定的不论大小的地面,用了力量去耕种,便都是进了他的天职了”。在文艺的社会功能备受关注的今天,我们对于艺术与社会的关系似乎更加束手束脚、不解放了。艺术果实培养的沃土虽然来自于社会,但并不意味着就应该都是符合主旋律正能量表达。对于艺术作品一刀切的做法并不可取,耕耘于自己的园地的艺术家们理应不该被社会上的主流价值所裹挟,他们值得独立的个性表达。
其实,不仅是艺术创作者,观众也应该具有个人合理的选择机会。《文艺的统一》一篇更直接地表现了个人与社会的思辨关系:“在现今以多数决为神圣的时代,习惯上以为个人的意见以至其苦乐是无足轻重的,必须是合唱的呼噪始有意义,这种思想现在虽然仍有势力,却是没有道理的。”个人是社会的一份子,其生活、感情确实是与社会共同的,但这并不代表艺术的观众可以被单一地定义,《文艺的统一》的呼唤要求“文艺上的宽容”,在这一点上周作人认为“宽容是文艺发达的必要的条件”,“不滥用权威去阻遏他人的自由发展是宽容,任凭权威来阻遏自己的自由发展而不反抗是忍受。”如同我国活力不高的电影市场,对审核的严加管制并不能让题材更真实、让创作更优秀,只会阉割了本该属于艺术的多元价值。文艺不是为人生的,应该是分离而非合并。因此电影市场才会如此呼唤分级制度,相比于统一标准更加符合观众不同,也给予了创作者更大更包容的创作空间。
《自己的园地》读后感(五):关于新版(转)
1 新版的周作人自编集与老版有什么不一样?
止庵:周作人生前出版自编文集(包括专著)三十三种,身后出版三种,老版自编集即包括此三十六种。老版出版后,我又发现了他从未出版的《近代欧洲文学史》,现在新版共包括三十七种,收录了目前所发现的周作人全部自编文集。周作人的集外文,将另外汇编成册出版。这是新版的第一个特点。第二个特点是根据原著和原刊文重新校订。第三个特点是在装帧设计上。周作人曾批评王尔德童话中译本说:“使我最不满意的却是纸张和印工的太坏,在看惯了粗纸错字的中国本来也不足为奇,但看到王尔德的名字,联想起他的主张和文笔,比较摊在眼前的册子,禁不住发生奇异之感。”对于周作人这样一位无论趣味还是文笔都讲究质朴之美和简洁之美的作者,我们也努力在文字校勘和装帧设计上做到能够与之相契合。
2 您多次校订周作人的文章,又写过《周作人传》,还没有审美疲劳吗?
止庵:周作人的作品有如一切真正的经典,是常读常新的。每次阅读,我都会有新的发现。我最早接触他的作品已有足足四分之一世纪了,随着年龄与阅历的增长,有些过去不很留意的问题,现在能够看出深意来了。举个例子,现在大家对某些译者的翻译风格有所反感,觉得“大俗若雅”,其实周作人早就指出:“譬如英文的Lying on his back一句,不译作‘仰卧着’而译为‘卧着在他的背上’,那便是欲求信而反不词了。据我的意见,‘仰卧着’是直译,也可以说即意译;将它略去不译,或译作‘坦腹高卧’以至‘卧北窗下自以为羲皇上人’是胡译:‘卧着在他的背上’这一派乃是死译了。 ”
3 您认为周作人的读者是什么人?
止庵:周作人本身是一位百科全书式的人物,是集中国文化与世界文明之大成的人物,他的读者群应该能够包括从初中到老年各个年龄层次。周作人曾在文章中引用别人的话说:“少年爱绮丽,壮年爱豪放,中年爱简练,老年爱淡远。”他的《自己的园地》、《雨天的书》有几分“绮丽”,《艺术与生活》、《谈虎集》有几分“豪放”,而《夜读抄》以后各集则极尽“简练”,晚年写的关于鲁迅的几种回忆之作和《知堂回想录》又颇有几分“淡远”了。
4 当下读周作人有什么意义?
止庵:前面已经说了,周作人是一位百科全书式的人物,是集中国文化与世界文明之大成的人物,读他的作品,可以从历史、现实、文化、知识、修养、趣味各方面获益。周作人向被称作“小品散文之王”,他的文章是中国白话文的极致,他又始终是一位人道主义者、个人主义者和自由主义者,“文化批判”是他的作品的主要基调。我们对于周作人的理解往往有些褊狭,以为他只是一味闲适,不问世事,但如果看了他的《谈虎集》,当知道他对于现实的批判是多么有力,涉及面又多么广泛。即便是在他三四十年代的作品中,文化批判也是以现实批判做底子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