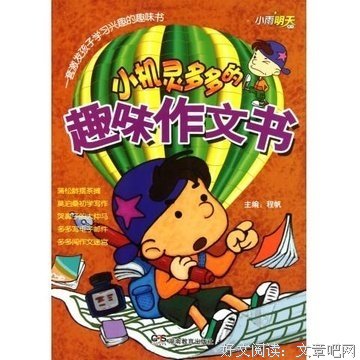
《书评家的趣味》是一本由李影心 著 / 陈子善 编 / 张可可 编著作,海豚出版社出版的精装图书,本书定价:19.80元,页数:192,特精心从网络上整理的一些读者的读后感,希望对大家能有帮助。
《书评家的趣味》精选点评:
●公允的书评,年代羁绊,隔膜之感,全书以《老舍先生<离婚>的评价》为最佳。
●要给这部书做书评,便要称为“为书评家的书评写书评”。书内容本来就不多,然而开篇的介绍,说明,序什么的便占了十几页,接着才是正文。李老的书评一般是两段式,前段就是简单的summary,然后再对书或小说做一些艺术上的评价。作为老一代人,自然没有我们现在的人那样的花花肠子,所以整体来说也比较平淡。对于我而言,主要是收获是了解一下当年的一些小心的故事情节构筑,至于李老的艺术评价不甚感冒,选择略读或跳过。又因书的开本小 ,拿起来称手,于是便多读了一阵。
●20160405购买。上世纪三十年代的书评。。。看不下去,就如同那个年代的很多书一样。
●对书评是有极大见解,从结构到内容都成熟而饱满,至于语言风格略微的不适那受困于时代,无可厚非。
●文字的滞涩感让人难以卒读,甚至怀疑自己的阅读能力或者编者的眼光。观点可取之处不多,表达观点的文字简直就是支离破碎的。
●没看书却看评,也真是没什么趣味
●没什么意思
●趣味不投,sigh
●又是一本故纸堆翻出的人物,本来以为书评无论如何不会无趣。但,看了前言推荐后,就预测到这位恐怕不是我偏好的风格。果然。为人物生平,感慨,满纸心血尚在人间,伊人已不知魂断何处。为这本评书的书,就……如果你实在有时间又对那段时期的那些文章感兴趣的话当然也可一读。
●品评的书我一本都没看过,不过分析的到挺详细,从字词句到写作背景都头头是道。
《书评家的趣味》读后感(一):你不必完全读懂一本书,只需读到自己想要的
这本书我实在算不上喜欢,而且书的后半段我基本看得不明所以。
这本书的阅读体验不能说好,短短8万字,却让人在阅读过程中屡屡有滞涩感。这种感觉来源于这本书的“不合时宜”:语言习惯上的,以及评论的作品上的。
本书收录的李影心的书评,集中写于1935~1937年,尽管他是新文学书评人,但语言习惯和现在确实不同。所以在内容之前,语言就是一个障碍。至于内容上,他评论的书籍我很少看过,且确信没有兴趣看。一是从阅读价值来看,那些书有特定的时代性;二是在发现会有阅读障碍后,不想去打消自己的阅读积极性。
本书书名应该就是出自代序,而我所说的语言障碍,看了代序之后,应该就能有所了解:洋洋洒洒一篇,看了之后反而让人不明所以。所以在看完代序之后,正文之前,就应该对正文的行文风格有所准备。
当然,这本书也有其积极意义,我们要从书中得到自己想读的。
一、我们能看到作者阅读视野的广阔,其书评内容涉及到小说、散文、诗集等不同体裁。这让我进一步认识到文学的边界。
二、虽然读不懂细节,但作者评论小说的这几篇,思路很清晰,让人能轻易撸清结构,引导人系统地去看待一本书。这也是我提到的,书评给人提供了一种看书的新维度。
三、部分文章仍有其现实意义。如评老舍的《离婚》中,对现行婚姻制度的思考;评《幽僻的陈庄》中,对农村题材小说的臧否;评《五月》中,对部分浅薄的都市言情小说的讽刺。
四、从作者李影心的文学趣味中,被科普了很多概念性的、基本的文学常识。比如短篇小说篇幅短的优点(p14、p15、p24);艺术创作和理论文字如何相辅相成(p34);应该以什么样的标准来评论农村题材小说(p50)、散文和诗的区别(p156)。
所以,这本书虽然我不推荐,但也并非全无收获。
《书评家的趣味》读后感(二):神秘的李影心
李影心是现代文坛的神秘人,我最初是在萧乾主编的《大公报·文艺》和凌叔华主编的《武汉日报·现代文艺》中得知此人,但所知也就是他的文章,就连毕生致力于现代文学史料研究的陈子善都对他生平、本命、经历一无所知。不过,要谈论现代文学,绕不开京派;谈论京派文学,绕不开书评;谈论京派书评,同样也绕不开李影心。
陈子善评价他的书评是“描述性和抒情性”,擅长文本细读,将作品放置在作者整体创作进程加以考察。不过,我觉得他的书评更有价值的地方,尤其是对当下的读者来说,是他的写史倾向。他在评价一本书的时候,非常重视创作和出版背景,他对朱自清所编《诗集》的评论,几乎就是一部新诗简史。又如,在评价儁闻《幽僻的陈庄》时,他提到了当时文坛“农村问题”的潮流。他认为当时很多作家“应时”创作农村小说,但是没有观察和体验过,写出来只是臆想。而儁闻好在对农村人是深刻,“精力的可佩”,这是他作品的长处。而可惜的是,他并没能将深刻的认识表现出来,缺少了艺术品应有的“整个的感人的力”。
我们当然可以就文本本身做出优劣评论,但是某一环境,孕育某一文学,尤其是现代时期,诸多文学样式都在探索之中,用今天的标准来看,大概都不值一提。但是或许,没有这些真诚的失败尝试,便没有后来的发展。回归文学场景,更有利于对作品作出客观的理解和判断。而对于脱离历史语境近百年的我们来说,更是需要李影心这种着力于语境描述的书评,进一步了解文本。
该书收录的书评,一半是小说,一半是诗歌,还有一篇散文。从评论的角度来说,李影心在小说方面更为成功。他的诗歌评论,和他对李广田《诗的艺术》的评价一样:“更像是解诗,而不是论诗。”较少有明晰的观点和批评。此外,由于时代的原因,他的语言生涩,句法欧化严重,不习惯民国文风的读者可能会有佶屈聱牙之感。
不过总的来说,李影心的这十几篇书评,构建出了一个他的阅读空间,展现了他“书评家的趣味”;以史和评相结合,描摹了现代文学的一角,有其独特的意义。而他和京派同人一道,在混乱的二十世纪三十年代,依然坚持创作纯文学书评,不被其它力量所裹挟,亦十分值得敬佩。
希望随着史料的发掘,能对这位神秘的书评人了解更多。
《书评家的趣味》读后感(三):李影心的故事,还能有谁知?
李影心《书评家的趣味》海豚出版社 李辉主编的《书评面面观》一书,意外看到收录有李影心的书评,想起了《书评家的趣味》,再接再励,接着看。 看看1930年代的李影心,如何评价书评。他认为“大多数文艺杂志中所载的“书评”之类,其本质,并不见得是批评的,有时,更充分流露着读后感的气息” “读后感”虽然“不见得尽然可以随意抹杀” 毕竟,“只是作。为未入轨道的批评的一种过渡中暂时的现象”。他主张新文学“书评”应该是分析的,批评的,应该在体现作者个性的同时又顾及到公平,书评虽不能替代文学批评,但好的书评应该“独具一种较高的对文学艺术的趣味”,体验了文学史家的眼光。(这段话,由陈子善先生编辑,总结) 在我看来,书评和影评一样 ,读者如果光看“评论”,意义不大,也未必能看得进去,如果说需要靠评论来做推广,那未免也迟了一步,各种图书广告反而更吸引。如果书评只是专业评论,那受众又未免太窄了。 看李影心点评沈从文,“作者文章风格实呈现极度的奇特,与其他作者都迥然异趣的。作者笔下触及得极广,且惯用为一般作者读者皆不大熟悉的题材,从生动故事中把捉某些类人物的生活,思索,性格及品德,加以逼真的刻描记载。” “沈从文先生有一支洒脱的笔,能流利而无拘的刻划故事人物性格,态度从容,使情节支配自如活泼,为风格强烈的一点特征。作者善于选择辞藻,字句类皆深刻机警,生动有力,每个词语皆用在一种适当的地方,使平凡句词具有特赋的生机,奇丽处为拙劣促陋中国文字上增加几许新的变幻。” 1936 年,李影心盛赞郭沫若。“五四后,新诗有过另一阵兴盛,是民十五《晨报.诗刊》的创刊。惟是这当中,尚有一个诗人值得提说的,是郭沫若。郭氏的豪放夸张,可称独步;且节奏单纯,情绪狂炽,有《女神》及《沫若诗集》。” 李影心还点评过老舍,林徽因,穆时英著名作家的小说,也评论过李广田何其芳,徐志摩,卞之琳的诗集。但是李影心是谁?他从哪里来,后来又从去了哪里?编《书评家的趣味》的陈子善先生,也没办法了解更多,编发过李影心书评的编辑,萧乾,沈从文他们,也没见为他写过什么文字。《书评家的趣味》出版也六年了,网上也没有李影心的“后人”来认领,这让我觉得有点惆怅,文人有小圈子不是很正常吗?为何他会无影无踪消失了? 140字自媒体一度占据社交平台,不少人抱怨文章字数多看不进了,像那些恨不得一夜暴富的人那样,有些人也巴不得一目十行,一个小时就要看完一本书,最好看一本书要给自己带来好处,很难再有像李影心那样,认认真真的给图书写评论了。
《书评家的趣味》读后感(四):湮没于故纸中的书评家
李影心,一个陌生的名字,即使是于专修现代文学的研究者而言。这种陌生,几乎是彻底的,或全然未听说过这个名字,更不要说读过其文章,或对其偶有所闻,却不知他文学活动的来龙去脉,“甚至李影心是否他的本名也不清楚”。以钩沉索微见长的陈子善教授亦有些束手无策,“在中国现代文学史研究已取得长足进展的今天,还出现这样不应有的空白,真是令人悲哀,也令人无可奈何”。如此看来,《书评家的趣味》一书的出版,是有双重的价值的:一为李影心作品的首次结集,具发掘之功;再有,让现在的读者看到曾湮没于故纸中的好文章,体尝一种“书评家的趣味”。
谈李影心,便不能不说起刘西渭(李健吾)。李健吾是剧作家、翻译家,还以刘西渭的笔名写书评、文学评论,结集《咀华集》、《咀华二集》,是“印象派”文学批评(偏艺术视角,与社会派区别)的代表评论家,名声不可谓不大。李影心与李健吾的交集,在于同为《大公报•文艺》副刊的书评作者班底,他们两位,再加上常风,写作的书评文章,不论从量还是质,均堪称翘楚。不过,历史的吊诡或曰不太公道之处亦表露无遗:李健吾的评论,成为一派风格的标杆,现代文学研究的对象;常风虽未有如此风光,但并没被人所遗忘,其著作仍在重版;而李影心,我们已然知道,无人知晓了。
其实,是中的缘由,亦不是不可以揣测一下。李健吾是文坛的多面手,其主要的身份是剧作家,文学评论为其副业,另从事法国文学的翻译,这样一位重要的文学家,任一领域的实绩都不会被人所忘记,何况他的文学评论确是文采斐然,开一派之风。常风曾出版《弃余集》、《窥天集》、《逝水集》,收录书评、文艺评论、散文等作品,事实上这位老人长期以来亦是声名寂寂,但因有一些晚辈学人的呼吁,而更重要的是,他曾在北京大学、山西大学长期任教,受其亲炙的学生及再传弟子,终究会续其衣钵,不会全然湮没的。而李影心,无法求证其大致的生平材料,不知其职业,不知其更多的文学活动,只能推测,他应该未在大学任教,否则不会没有学生回忆他,且不太热衷于参与文学社团及活动,否则这方面的记载亦可为其“留影”(现存的记录寥寥可数)。当然,我们也看到了单纯的书评作者的悲哀之处,哪怕写得再好,若只写这一种文体,却极容易濒于被遗忘的边缘。客观而言,写诗歌、小说、散文的作者,如果写到李影心之书评文章的水平,依如今的中国现代文学史研究搜罗程度之广之密,绝无遗漏之虞,但李影心的被遗忘,可说既是于其本人的不公平,亦是书评这种文体的尴尬处境。
不过,不管怎样,我们现在知道了李影心,还是来看看他的书评吧。李影心的文章写得好,而若拉来与当下颇为蓬勃的书评写作并置,恐有更大的意义,因为与这位前辈相较,现在太多的书评作者实要汗颜得紧。精准的艺术眼光、敏锐的艺术感觉、广博的学识自不待言,只论李影心将评论这一文体的独立艺术品之位置的磨练实践,即令人观止。试看他如何评《画梦录》:
“(何其芳)珍惜那份梦境的迷离,犹如珍惜于一个阔别之友偶然不经意的会晤;然梦中道路不常会经常现临,就有如阔别已久的友人在刹那飘忽间的再度相逢,于我们的思念上并非刻意预知。于是他有所怀想。而这怀想,代替了‘梦’,萦绕他想象的边缘,且常帮助他有所思索,他的文章,与其著作一个孤寂灵魂的独白,莫若说是这种怀想之所系,为一种静美阴郁揉和之不断追寻的抒写。”
不仅有着文本细读及对何其芳之创作心脉的准确把握,其书评文字本身之美,亦不让《画梦录》散文的水准,这大约是高妙的评论所应抵达的境界吧。其实就这一点上,李影心和李健吾的评论有异曲同工之妙,均使得书评具备了独立之艺术品的价值。就此看来,书评之为美文,虽非必须,但若能够成就,确为这一文体不至为人忽视、贱视的一关键所在。
李影心集中于评论新文学作品,在其时或未必觉得如何,但经时光的淘洗,我们现在读之,多了许多意味与趣味。如果说文学史是长矛长戟,那书评显见得是短兵相接,时鲜出炉,容不得时间让你“悔棋”,最见出评论者的眼光、洞察力。我们看李影心评老舍《离婚》、曹禺《日出》、沈从文《八骏图》、芦焚《谷》、何其芳《画梦录》、三诗人《汉园集》、陆蠡《海星》等,精微地道出了其艺术之价值,为后世的文学史所验证,可称评论的先锋营。而他对穆时英《五月》的批评,直击作品的“七寸”,抓住新感觉派小说的末流之软肋,毫不留情面。另有一部如今不见经传的小说《幽僻的陈庄》(儁闻著),李影心既赞扬作者对乡村生活的熟悉,也不做好好先生,而是直接道出艺术表现力的致命缺陷,导致作品的失败,这种评论,自然是秉笔直书,是评论人最基本亦是最可贵的素养。
不论是审美品位,还是文章发表的园地,李影心显然属“京派”阵营。他选择的评论对象许多是京派作家的作品,如老舍、沈从文、何其芳、李广田、芦焚等,还有如林徽因编选的京派小说集《<文艺丛刊>小说选》、朱自清编《中国新文学大系•诗集》,简直就是贴着“京派”显眼的标签了。而我们可以发现,这些作品的确合着李影心审美的脉息,他能够准确地捕捉到其间的微妙之处,作品的精义,作家的创作心态,都逃不过他的眼睛与感知,若合符节,相通如是。在京派作品之外,他选的多半为或现实主义或偏向左翼,如蹇先艾《踌躇集》、艾芜《燃烧的原野》、舒群《没有祖国的孩子》、万迪鹤《火葬》、何谷天《分》等,不太涉及别的流派,如即使选了一篇新感觉派的小说《五月》,也是批评为主。
李影心在《书评家的趣味》一文里说道,“书评家欲想忠于职责,他便得时刻牢记回避自我的直接参与。由于他的一切尽心为力最终倒不是为了他自己,至少说书评的成就不是发现自己,更很少是表现自己,虽说这样来作倒是一己存在的方便的安绥。”他对自己工作的职责认识得极清楚,而我们悲哀地发现,这种认知似乎连接着其后来被遗忘的命运,评论文章写出来,宛如为他人做嫁衣,衣裳裁好,光鲜的是着衣的人,裁剪者退居幕后,早已被忘得干净。这是遗憾的,可似乎时时避免不了,那我们拿起这册迟来的结集,算是挽留一下忘川的水流罢。
(南都载。说李影心,亦非仅说李影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