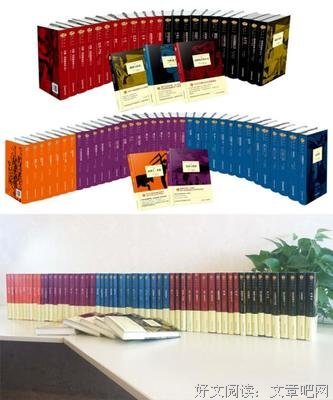
《窄门与圣杯》是一本由叶美著作,团结出版社出版的平装图书,本书定价:100,页数:97,特精心从网络上整理的一些读者的读后感,希望对大家能有帮助。
《窄门与圣杯》精选点评:
●每次阅读都像在战胜一个困难,可以说举步维艰。但是越是这样我在心里说这是诗人对惯常用词的规律和逻辑的抵抗和冲击,诗歌是语言的试验田,她就是率先完成了,那么,读懂它自己就是进步。读诗同感的加油啊✊
●有些恋人走远了,有些诗友走远了,有些译友走远了,无所谓,叶美不看重这些,叶美只看重自己的才华
●极其困难的阅读……
●需要再读!
●支持一发
●“谁逼已花呗的母语行巡礼618”
●好像浸立在叶美之众的水域里,给那些哗哗喀喀流过来的由塞壬歌声裂解成的浮冰之问给砸懵了。但外行如我,还是能感到这水域的灵性、视野和力道,纤毛触活。
●和马拉美、屈原遥相呼应。
●面对诗人劈手打出的一张逆位塔罗还有这先锋的诗歌流速,可以尝试从诗剧角度适应和通过这扇窄门。 诗体现在意象化隐喻化的加工,凝练又奥秘的用词加密了现实与非现实,锐利,无法忽视,其中椰城、泰湖、紫禁城算是容易破解的密文,性墓、蝶粉、铂心线、灵午云、剔骨女则是海妖的怪音; 剧性体现在各诗音色特异,如同戏剧中不同角色,诗体即身体,语调即口吻,思想穿梭于奇幻词域的高速公路,这些轮转的时空词场,轮换的发问音调,轮叠的修辞诗体,每个声音都昂扬登台热烈独白,轮番辩驳,又对着虚空和观众席发问,追问责问质问叩问之声此起彼伏,这是很具戏剧色彩的,它掀起场场狂风蝶浪,置身其中的读者只好逆风而行。 “她写出了我们这个时代缺失的东西。” ——《纽约时报》
《窄门与圣杯》读后感(一):不知所云的分段散文
叶美的诗歌最大问题就是散文化,其实她写得是分段散文。每一句,每一个意象,每一个比喻,都是散文化的。
当年与伟东兄论及此女,言床上可行千里,诗中寸步难行。今日读其诗,知其人也!
每一首诗都是极其轻浮,又流露着学养和教养的缺失。由于在辱骂中过日子,她的语言中不时溢出东北农村妇女骂街的语感,整个人的语言已经被自己败坏了。
诗非德性,而是知性。叶美天性良善,而被太多德性不高的男诗人沾污,于是叶美的诗歌中便若隐若现着无数男性的影子,那些影子如蚁附膻,鬼魅闪飞。你读叶美,你宛如观千男战一女,没得诗味。在知性上,叶美先天弱智一些,不然也不会跟那么多脏污的男诗人一起行周公之礼。这是智商上的缺陷,而性灵也由于自我陷入谩骂的泥淖里,沾污了诗神。
总体上,她的诗歌仅供研究被渣男遗弃后女性的心理状态的医生读,是极好的范本。普通文艺爱好者,不宜读她的书。因为精神中毒,比与叶美行房事还要有害。艾滋病,梅毒,在精神毒药面前,都是小病。
但诗歌散文化,病毒化,也是在中国诗歌圈子里独树一帜了,就是在中国三十岁以上的诗人里,叶美的诗最毒辣。
当然,她不会被后世记住。但可以作为一种社会学的资料研究一番。
《窄门与圣杯》读后感(二):急哭,拜托了,读过帮叶美打个分吧,写点评语吧,叶美想凑十个人刷个分出来
实际在我昨天的心镜下,我急于找到一种不要做‘怂逼’的同路人,我倾诉的绝望不满足于任何其他方案,这是叶美一向的秉性而已,若这会儿被谁听见造作了吗,不是一直有人清白得很心安理得吗,不要怀疑究竟是哪一群人,往往一边喊口号一边往他人口中塞抹布,谁又能牢记时代身上的痛,且同步自己刻舟求剑的感受,这就是周围做不了‘怼逼’的原因。一个能够身兼两者招摇过市的,必定某一时刻把自己从‘怼逼’换身到‘怂逼’,这比男权要求戴避孕套去怀孕还要匪夷所思,叶美又奢望怎样去辨别高仿真’怂逼’的人呢
一句话就可以把我叶美所有的努力否定掉,女人把女人看作无,从此叶美不想要什么理解了,叶美,你记住,女人之间也没有相同的困境,如果这一困境的解决不一致,你叶美可寻找什么友谊,我叶美所有的友谊是要建立在理解我自尊基础上的,好奇怪,我觉得我叶美可以理解他人的选择,但从没有人理解过我,我这是不是双向障碍了,可我不认为我是个病人,我曾说我对林亦晗对爱情的追求最终导致她自杀,那注定是幻灭,如今叶美对友情可能也要这么看待了,这令我叶美绝望,也许这个世界就没有一种方案可以修复暴力给我们的创伤,那就是我患自闭症了,我叶美患上了自闭症
《窄门与圣杯》读后感(三):叶美《窄门与圣杯》初读札记
诗人,批评家王辰龙
若已习惯叶美以往诗集中流畅自如的表现力,初读她的长诗《窄门与圣杯》时或会因其形式而生出些许陌生之感。首先,源自阅读经验的、凝固着文化意味的词汇(如“美狄亚”“玄鸟”“圣杯”“卷耳”“海尔茂”“汪伦”等)或场面,个人可能亲历的地点(如“德州”“春熙路”“渝北”等)或风景,古今中外其他写作者(如“贾岛”“萧红”“房思琪”“庾信”“策兰”等)的命运和抉择,以及抒情主体(直接以“叶美”之名现身)繁复的情绪和判断,这种种要素总是略去过渡便急切地组合成文本的局部,最终生发为骨骼清奇的整体。与此同时,句段间留白颇多,日常生活图像基本模糊,加之诗人无意为她写下的词与物搭配通常意义上一目了然的逻辑,因此,文本连缀起的时空因高速切换而显得稠密、抽象。显然,诗人有意将她擅长的清晰与精准悬置了起来。其次,诗中不常见的怪词(如“匕光”“轻忆”“雾伞”“盗影”“性墓”“身墙”)此起彼伏,或是作者兀自的铸造,或是对某些短语做出缩写,或是来自对古籍旧典的打捞与再造,但它们显然都疏离于当下汉语的词汇体系。另外,或许正是由于上述两种形式特征,使得整首诗在语感上不免硬涩拗口,难以直接地通过诵读而诉诸听觉,这亦与叶美以往诗歌中并不磕绊的言说有所不同。三处所谓的陌生之感,想必无法全然概括长诗的形式,但它们或许是必要的线索,以指示出长诗的初衷与完成度:从诗集《周年》《塞壬史》再到长诗《窄门与圣杯》,形式的新变实则有着明确的源头与坚实的路径,而非松懈间的退步甚或失败。
在诗集《周年》《塞壬史》中,叶美擅长的工作或可归结为:1.为不能忘却的经验找到形神兼备的喻体或场景,使诗歌中细节充沛的私人生活富于关乎时代的公共性,如她的《身体》《这海岛隐喻她的世界》《每天清晨她去早市》等;2.不沉溺于一己之私的痛楚或欢愉,将个人体验转化为超越限度的契机,把投向自我的目光转向众生,通过诗歌写作,“我”与共时性的他者、历时性的异在结成命运的共同体,如她的《女友》《女人一组》《家葬》《素描画》《婚姻》等;3.寻求既在场却又不被裹挟的旁观者视角,对当代生活做出概括,而无隔岸观火的冷漠,如她的《海岛》《世态图》等。这三重维度仍是她这首长诗的底色,并共同延续着叶美始终关切的一个命题,即女性如何在当代中国的语境中持续地校准命运的轨迹,怎样以正面的姿态去应对带有压抑性的权力意志和社会结构。这一命题诗人已在长诗中点明:“一个女人/就要选择活在/罗曼史里,/就要阻止道德/宣扬其对立面”;“媲美自己屈辱的/缄默,适时给/女性一副社会学的//想象力,以给男权/文化施以考古//当给爱情鼓掌/也知道观看文明//如何是暴力的温床”。由此,叶美在长诗中寻求的新变实则带有对自我进行“奥伏赫变”的意味。稠密而抽象的时空切换,大致略去了有生活指向性的细节,意图将对当代生活的概括推进到直击本质的程度。得益于阅读的词汇或场面,以及对其他写作者的书写,无一不有典故的意味,文字练达却附带广阔的表意空间,而当它们被融合进个人生活史的流转,文本中便不再仅有独白,抒情主体开始与各时空的景观、事物和人展开对话、和声。这样的设计似在宣称:非人的、严重的晦暗时刻始终不曾从我们的历史中缺席,与之相应,人对诚与真的追求也始终不曾因必须付出代价而中断。语言是权力的载体之一,因此,故作怪词也好,有意拗口也罢,诗人似乎试图从根本上瓦解霸权,正如她于长诗中所言:“而任何花朵的/标准,都不足以//缝补文学的达雅/谁又在真正//抱着这些疑问/犹豫中向修辞诉苦//定睛,就如这首/长诗,不可能事无//巨细地吸引/而是该知道如何//戏剧化情节/开始一场话剧式争论”。
《窄门与圣杯》读后感(四):《窄门与圣杯》的普通读者读后感
莱尼
初打开《窄门与圣杯》我可能像他的几乎每个读者,是懵逼的……其中有一半的诗歌是打开了每个字每一行都认识,引入的典故也有泛泛的了解,但读完全诗却根本不知道作者的意图到底为何。每个人都是羞于承认“我不明白”这件事的,我的虚荣心使我也沉默了这件事,作为朋友我对叶美表示我最喜欢的几首是《萼尘与花鞘》、《窄门与圣杯》,还有《钟鼓与巢穴》,之前对于其他诗歌的疑问或者说彻底的疑惑只字羞于提出,只模模糊糊心里知道作者其他的诗歌大约是历史意识过于丰富了……大概这几首是以普通读者的经验直觉来说,从一开始就比较容易抓住诗人情绪上的集中点,叙事的力度转换也让人容易把握。奇妙的是到昨天终于忍不住去问作者才解惑,对她来说最喜欢的其实也是这三首,并且它们几乎是同一个短的时期内完成的,是本诗集中最早完成的三首。诗人故意打乱了它们的顺序,从而使得整个组诗的编排线索更加扑朔难以理解,后期写作大量的引据和议论更加有些不近人情难以进入了。
我得以闲聊谈到关于诗集中的另几首诗的疑惑并得到解惑的快乐,是起于闲聊谈及西蒙娜·薇依,她是作者非常喜爱的一个思想家,我随口说着我的理解是因为她其实是个信仰或者说立场特别坚定的人,做出在生活境况的选择时她抱有对人类的苦痛、对他人的种种具体苦痛的非常强大的同情心,同时这种同情心同时又会造成对其他具体邻人的苦难和自身的苦难,把自己置于危险的和被憎恶的境地。对叶美来说她也从不因为这种危险而退却过,叶美的写作其实是与她的立场和她的理想融合的。
作为一个普通读者,我可能有少量的单纯文学阅读经验,但对于文学理论一窍不通,只能用一些具象的话语来描述我读到每一首诗的感受、疑惑以及慷慨又可爱的诗人给我的答复。我想引入单纯得以感受维度的两个描述。作者的诗歌的维度其一,描述物的世界或属于心灵的世界的成分在每首诗的可触摸的量都不同,这两个描述本身它们是相对而且广袤的词汇,但在每首诗歌中它们的显示却体现了参差不齐的状况。属于心灵世界的那部分作者给我的更详细一些的解释是诗歌情绪的易感性(诗人带我们能够更直接的、更容易去摸到诗歌背后的目的,更容易抓住并使得我们赞叹的奇妙)。比如窄门与圣杯中作者很喜欢的几节:
深夜,鸟性逆升时
即使扶住了香气
你也无法顺从,并折叠
成纸,总有谢烨必须博入
世界的矮小,巴塞尔姆
再从积芨草出来
给脱臼鞠躬,是变戏法吗
丝质的后悔能挽回吗
还有我也特别喜爱的《萼尘与花鞘》全诗……
而我出于直觉描述的属于物的世界作者所讲原因是引入了大量的历史论证和典故,我会觉得它显得如此的铺张乃至浪费,初看甚至糟糕到除了文字游戏什么也没看到。但它使我可触摸,并具有属于事件特有的肉感(桌子的肉感、猫砂的、敬亭山的,在此也称之为肉感,非特指任何动物的身体,杜甫这个词在我看来都是具有这种肉的物感的,我们很容易联想到一个具有血肉可触摸的诗人形象)。非说前段落提到的两三首诗歌没有引据,但前者的引据其本身较少而且具有强被目的遮蔽的状况。这种可触的肉感太过引人注意,以至于反而给按照常规普通路径进入诗歌造成困难。作者本人说她恰巧担心这种整齐的全部每首“砖块”式的写作,是否会给人带来厌恶的感受,在我的阅读中并没有对这种形式的厌恶,甚至读者都会发现处处挑出来都是妙语;她又认为是这些主题太过杂乱导致无法进入,而我的个人看法只是这种杂乱会给人造成错觉作者想要写特别宏大的史诗叙事,在形式和丰富的主题上来说的确如此并非错觉,但更加仔细聊过集中收录的每一首诗我发现她的目的亦并非如此,它们的路径如果重新排序可以说是向着她的实验路径的前进。
诗人越尝试只是就越是想尝试一种新的路径,虽然她对细节有许多很不满意,因为一鼓作气的焦灼,很多精微的东西就遗憾溜走了。整部组诗好像一个过于缤纷的万花筒,诗歌排序的迷宫之下有典故的迷障,也有几乎完全相反的拒绝以情绪进入这条路径的谜团。比如在《盘手与弥陀》:这是组诗中最长的一首,也是我疑问的一首,并且它排在组诗的第三首,根本容不得转变阅读思路的可能性就被很容易放弃了。对于它作者希望之后能为它加上注释。对于诗人来说,写作完全与她的生活不可分割,但这里她又将情绪隐藏在了对前人的质问,唐诗可以是议论的形式,作者希望在新诗中尝试这种传统,同时加以变形她自身的经验。
写作这首长诗的时候诗人本属于她女性作为继承人法定应有的权利边缘,男权传统和人情社会的双重习惯法则使得土地确认继承所有权时理所应当默认全部分配给他人,她的种种争取都被多数人甚至同伴视作叛逆和彻底的“无理”,她们退却了,而对诗人来说这块小小土地并没有什么收益可取,但却包含了关于每个流离失所女性身份的确认,是她抗争的一部分。像伍尔夫所讲的那句耳熟能详的“女人没有祖国”,自然而然不可能拥有自己的土地。难以想象是在处处声称平权被粉饰时,法条归法条的,这成为一种被几乎所有人视为无理、视为“损害”她自身的一种举动,除此再无其他。
在写作中我们的诗人也转向了她的新路径尝试:《盘手与弥陀》中,首先土地这个语词是被两次明确且具象提及的,继续则是广阔面向(时间的、空间的)的复杂引据和议论发散——以其与之具有渐弱相关性的逻辑,长诗到最后使人甚至忘记她在问什么。语词“土地”的掷出是起始的因诉求而质疑,这首诗共有一百三十多节,在前九节中它便出现了两次:
第一到三节:
越过吻的版图,匪首心如何
共情掉超值的禁忌呢?即使
出生地把我赢回在变元音的
错词中,即使戊午年的窥镜
递来尘土的食物,哪怕只有
一个人,我也愿以女身交换
而后引出了第四节起的发问:
山川的意志和最土地的纯洁
叶美,花海就是你,删除掉
纳粹的沙漏之“不”,要穷通
多少个波伏娃,才住进败絮
……
第九节到十二节:
如果土地是共享的所见,而
乡愁也修容了草木的春心
女性替谁完成时光的福祉呢
她,她们寄一生欢妄的帷幌
走进浮佻的修辞现场,就如
谁在书写娜拉出走的还原吗
在这里诗人从起始故彻底意剥除了那部分神秘,或者说剥除了我们习以为常的女性诗歌的“精巧”,建立了新的调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