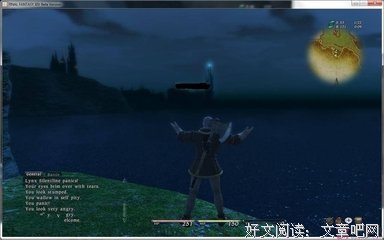
《死与重生》是一本由李虹著作,四川人民出版社出版的精装图书,本书定价:68,页数:336,特精心从网络上整理的一些读者的读后感,希望对大家能有帮助。
《死与重生》读后感(一):《死与重生》后记
十岁那年冬天,我无端添了一个毛病。每天晚上钻进被窝后我会再爬起来,站在床上,开灯,居高临下慢慢环视一周,看着光线洒满每一个角落,躺下,睡觉。
爸妈说,这孩子真是毛病大。其实不是毛病,是怕,怕闭了眼之后再也睁不开。说白了,是怕死。
大人也许会说,小孩子嘛,哪里知道什么生死。可是生死我是见过的呀。
在妈妈当年工作的“扫产料”(我儿时对妇产科三字的误识),我见过新生儿的出生,见过病人的离世,见过护士用手术盘端着皮球大的瘤子穿过走廊,见过我的玩伴笑着闹着轮流躺在医院敞着盖的棺材里。阳光强烈,我觉得冷。
我不知道这种恐惧为什么会在十岁那年发作,也不敢对人说。白天疯玩,晚上烦恼,我把家里放药的抽屉翻个底朝天,把一切看上去似乎对症的药吃下去,包括龙胆泻肝丸。很多年之后我才知道,当时的那个龙胆泻肝丸对肾脏有损害。
好在少年不知愁滋味,这种困扰并没有持续太久。若干年后,当我的博士论文终于选定汉代墓葬及其信仰,探究死与重生的研究方向时,我有一种冥冥之中自有天意的感觉。
在重新整理论文的日子里,我不时忆起当年在山东大学宗教所读书的情景,痛是真的,快乐也是真的。对我来说,读书乃一乐事,可是一想到还有一个叫作“毕业论文”的东西等着,心下就觉得烦躁。写不出论文的日子当然有,可是写不出来就写不出来吧,姜老师常说,我们是研究道教的。
王小波曾说,一个人活在世上,无非是要明白些道理,遇到些有趣的事,倘能如人所愿就算成功。我想再加一句,那就是读自己想读的书,做自己想做的人,不因旁人的好恶、环境的变迁违背自己的心意,对未知、有趣、激动人心的知识和生命抱有温暖的好奇心,用生 命去开花。
最后,要感谢我的导师姜生教授从论文选题到撰写给予的支持与帮助。先生总是不疾不徐,循循善诱,那些似乎脱口而出实则引人深思的言语常常令我惊叹,然而最令我惊叹的是他一语道破素常现象之后本质的睿智。
感谢四川人民出版社出版我的这本小书,感谢本书的策划冯渝杰兄与封龙老师,以及责任编辑冯珺老师的辛勤工作。
是为记。
《死与重生》读后感(二):未知死,焉知生
汉代墓葬的考古研究是近年来发展十分迅速的一个领域。众多的考古新发现使人们惊喜地看到汉代墓葬建筑和绘画的多样性以及高超的艺术水平。另外,中国考古学的研究逐渐打破了拘于器物本身的物质形态的研究,延伸至与器物相关的精神、思想、观念的阐释,汉代墓葬的信仰研究引起了学者们的多方注意。
李虹的作品《死与重生:汉代的墓葬及其信仰》正是该领域的一项综合成果。李虹在引言里对以往的汉代墓葬信仰研究进行了详细的蒐集分析,主要集中于20世纪90年代迄今的学界论著,包涵中国与西方学术界的看法,遍涉儒、道、释各派和民间信仰等内容。
李虹提出了“死而不亡者寿:死亡观念中的生命意识”的论点。相信死后灵魂存在是世界多数民族的共同信仰,在中国也由来已久。至汉代时,流行神仙信仰,这是灵魂不死观念发展到较高阶段的产物。求仙热的盛行,反映了汉代人希望通过某种方式延长现实生命,并使之达到一种理想存在状态的自觉努力。墓室是死者的居所,随葬器物是生者设想的死者在另一世界的必需品,而绘壁图像就是为了创造死后的空间和场景的说明书。
为了进一步阐发论点,李虹在该书的主干内容做了三方面的拓展。第二章围绕“清理”的具体仪式,结合曾侯乙墓、沂南汉墓等墓室的图像实例,从河南三门峡南交口东汉墓出土的镇墓陶瓶推导五石的神秘力量,继而讨论道教的符图并各种汉代墓仪文书,研究解除术如何给身体以圣洁。第三章围绕墓葬作为“生居与死所的中介”所起的作用。墓葬存在的前提是为死者提供与生前生活相似的环境。考察汉代墓葬的发展规律的一大发现是墓葬空间的设置受到当时宇宙论的影响,墓室建筑与棺樽图像都是按照人是宇宙的中心为出发点来布局。第四章研究“转换”,即“死后生命的变形”,通俗地说,就是“重生”。修道人的死是新生命的开始,是进入仙界的契机。着重分析了各种死而后生的想象,指出尸解信仰的实质就是从极端的爱生恶死观念出发所导致的用“生”的观念来对抗和诠释死亡现象。
身为山东大学宗教与社会问题研究所博士、太原理工大学艺术学院讲师,李虹长期专攻中外艺术史及中国工艺美术研究,这部作品突出体现了她的方法论途径。李虹掌握的考古材料极其丰富,熟悉典籍,熟悉学界的研究,将它们融汇到自己的理解之中,沟通了个案的细致解读和对汉代考古的宏观论述,令人信服地证明了汉代墓葬礼仪及其象征意义,又十分逻辑地引向了对于中国古代生死观念的文化史诠释。
墓葬并不只是安置死者肉身的场所。艺术史家巫鸿曾经强调,研究中国墓葬艺术及建筑,必须注意三个本质要素:空间性、物质性和时间性,必须意识到墓室整体环境是为死者灵魂创设的特殊的主体空间,以及过去、将来和永恒是如何在封闭的墓葬空间里创造运动的生机。考古学家郑岩认为,墓葬可以被理解为人们在生死这个最大的、具有普遍意义的哲学命题下,对物质的材料、造型的手法、视觉的语言,结合着相关仪式所构建的诗化的“死后世界”。
李虹敏锐地感知到了学界动态,沿着这条道路探索。在结语里,李虹归纳言明:“从本质上说,墓葬作为一种仪式,以生者对死者的处置方式体现了人们对死亡的看法,表达了对死后世界的认知,其内涵既有社会功能因素,也有人们信仰、意识层面的文化意义。”汉代的生死观念,经过历史文化的不断演变和熏养,逐渐深入人们的思想根基,后来又与佛教相互渗透,构建了我们中国人两千年的心灵史。
未知死,焉知生。不论贵贱贫富,不论殿堂民间,生死观念是与我们息息相关的困扰所有人的问题。李虹力求解剖这个问题,她的研究突破了学科史的范畴,扩展到了更广大的层面,触及了我们中国人思想与心灵最深层的、缔造传统文化的那些要素。
《死与重生》读后感(三):墓葬的信仰:死亡不是生命的终结,而是在另一个世界重生
如果说,我们每个人的一生如同一本书,那么无论书中的故事多么精彩曲折,死亡是这不同的书里,无法逃避的唯一结局。
作为生者而言,对于将逝之人,我们无法挽留,唯一能做到的便是对逝者进行安葬,让其能在地下安息,以此来缅怀与寄托哀思。清明节,也正是这样一个纪念离世亲人的节日。除了扫墓祭祖,从传统意义上讲,也希望离世的亲人在另一个世界能安稳度日。
墓葬习俗由来已久,对于现代人而言,大抵是为了能够安置逝者死后的身躯,为后世之人建造一个可以纪念先辈的场所;而古代先民却将墓葬赋予了更多的意义。《中国大百科全书·考古卷》中,将“墓”解释为防止身体或其残余的固定设施,而“葬”是指将死者尸体或尸体的残余部分按一定的方式放置在特定场所的仪式性活动。这种仪式背后体现了当时的民间文化与墓葬信仰。
李虹所著《死与重生》一书认为,墓葬信仰的基础,就在于相信另一个世界的存在。在先民看来,生与死不是无法跨越的鸿沟,通过死亡-埋葬仪式,死者可以借此进行转换,获得在另一个世界的重生。
一 灵魂不死与神仙信仰
相信死后灵魂存在是世界多数民族的共同信仰,在中国亦是由来已久。在汉代,先民们相信灵魂存在,灵魂是人之所以为人的根本,因此死亡不是生命的终结,而是灵魂与身体的分离。
在这样的认知基础上,南方楚地便出现了魂可以上天入地,无所不知的思想。从考古出土的文物看,汉代马王堆帛画出现了引魂升天图像;山东临沂金雀山帛画还描绘了蓬莱、瀛洲等仙境,以表明灵魂升天之后所到达的理想世界。
关于神仙的传说,体现了人们对长生不老与快乐自由的渴求。在汉代以前的认知中,神仙是天生如此,超越自然与社会命运。他们手中有着凡人所渴求的不死之药,凡人若想成仙,只能苦心去求索,处于一种被动的状态。而汉代时,这种神仙观念则发生了变化,凡人被动的求仙变为了主动的修仙。神仙变为了一种自主自为的结果。
汉武帝之后,求仙的思想更是从贵族阶层向平民化发展,求仙向着世俗化发生着改变。这种修仙主要朝着两个方向发展,一是希望活着的时候成仙,如炼丹,服用丹药等行为,希望达到长生不死的目的;而另一种则是希望死后可以成仙,于是花下重金在墓中营造出与生前居室相仿的环境,采用特定的方式升天。而死后成仙也分为了两种,一是在墓葬中描绘灵魂在仙人的引导下升天的场景,二是在墓中放入丹丸等神药,让死者在墓中进行修炼,以达到死后成仙的目的。
神仙世界被认为是现世生命的最高境界,也是死者灵魂的最佳归宿。前面说到,先民们相信灵魂的存在,而死亡只是灵魂与身体的分离。这种灵魂不死的观念,使得神仙信仰产生后不久,向着死后的世界延伸,成为了墓葬信仰的一部分。
二 再生信仰的逻辑
《死与重生》一书中写道,“不死”与“再生”来自于道教神仙信仰,这种观念也区别于其他的宗教。崇拜神仙是其信仰的一个方面,但其更重要的实质则是将人放在第一位,试图通过修仙来解决人的生死问题。
万物在成长的同时,也不可避免的走向衰亡,这是生命的常规态势。《道德经》中曾说:“道生一,一生二,三生万物。”此乃顺生变化观。与此同时,道教中也存在逆生变化思想,即修道者沿着万物相反的途径,通过一系列的修行可以返回最初的“道”。“万物含三,三归二,二归一”。若想获得长生不死,就必须逆生而行,回到最初的道,由死入生。
时间使人由生到死,万物由荣到枯,逃避时间的控制成为人的渴望。由此,先民们幻想出了一个没有时间控制或时间过得极慢的世界。这就是所谓的天界,天界与人间存在着一定的时间差,这在各种修仙小说与仙侠剧中也得到了充分的体现,“天上一天,地下一年”,天界的时间进程比人世间更为缓慢。这种仙界与凡间的时间差构成了“圣神”与“世俗”两种空间,且这两种空间与时间差同时存在。
对于想要成仙的凡人来说,想要在活着的时候获得长生不老,办法便是服用炼制好的仙丹,这种仙丹意味着将压缩的时间释放给了个人,从而使得服用者的寿命得到延长,扭转时间,获得长生。
而这种行为是否有所效用,当时的人们也产生了怀疑。即便长生不老、羽化登仙的观念依旧流行,但生前既无法成仙,他们便将目光投向了死后。
三 为死后重生所做的努力
先民们相信另一个世界的存在,但是如何进入另一个世界,则需要进入一个可以修炼的容器。
古代神话中对山的崇拜有着非常普遍的存在,从视角的直观感觉来看,山与天地相连。先秦时候的神话传说中也认为,神仙存在于昆仑山之中,聚集着仙人的灵气。随着时代的发展,这种转变发展成为了山洞的信仰,即洞天。洞藏匿于山中,是通往仙界的地方。同时洞也是子宫的象征,代表着降生、源头与中心。
成仙者居于山中,洞穴便成为修道者的不二选择,在此修行或许可以与神仙相遇,从而获得仙人的提携。从洞天的观念来看,将墓穴视作过渡与再生的场所,便也可以理解了。
汉人生前孜孜矻矻建造墓穴,死后将生前所用之物搬进其中,并尽量将之与生前所生活的场景一致,希望在阴间继续过着人世的生活。由此,死后的生活便成为了生前的镜像,而墓葬成为连接此世与彼世的桥梁。
在其所建造的墓穴背景中,描绘着天界与人间的图像,以帮助灵魂飞升。墓穴不仅仅是存放随葬物品的空间,同时它也成为了一个虚拟仙境,是墓主死后重生的过渡与中介。入葬意味着身份与意义的转换,借由这种仪式,逝者完成死后的重生。
在汉代先民的眼中,死亡不是生命意义的终结,而是在另一个世界的重生。丧礼则是生与死的两个世界连接方式,墓葬则是这种联系的具体体现。即使现代社会科学已经如此发达,但是古代先民的传统观念依旧对我们影响深远。从传统清明节日也可窥见,墓葬现在虽没有让逝者在另一个世界重生的意味,但从某种程度上而言,扫墓祭祀,也希冀着死去的亲人能够在彼岸世界过得安稳,即便这个世界是否存在我们并不知晓。
《死与重生》读后感(四):《死与重生》:汉代墓葬形式和信仰的变化,逝者如斯乎!
生死可谓是我们讨论最多的话题,也是每个人无法逃避的来往。阴阳相合、怀胎十月、呱呱坠地……一直到最后的寿终正寝,在这个美丽的世界上留下自己的足迹,何其幸福!
李虹的《死与重生:汉代的墓葬及其信仰》一书将“死”换成了“重生”,此处的“重生”并不是重新获得生命,而是一种精神上的安稳,在极其重视“身体发肤,受之父母,不敢毁伤,孝之始也”孝文化的华夏民族眼中,人死后的安置也是非常看重,这便形成了墓葬文化。
《中国大百科全书·考古卷》中解释道:“‘墓’是将死者尸体或尸体残余部分的固定设施,‘葬’是将死者或者尸体残余部分按一定方式安置在特定场所的仪式性活动。”由此可见,我们通常生活中所说的“墓葬”意思变窄了,仅仅是指丧葬活动。
丧葬活动承载着一个民族文化、信仰等,一个墓葬中的墓室形制、墓室壁画、随葬品及所附文字、内部陈设等,为今人提供了研究祖先的信息。这本书就是从全面研究汉代墓葬的基础上,明确汉代墓葬信仰发展的过程,还有在东汉末年道教影响下的信仰变化。
“灵魂观念是早期中国思想和信仰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汉代墓葬信仰的重要思想基础。”全世界范围内都普遍认为人的死只是肉体和灵魂的分离,而在中华道教文化中不光有灵魂,还细分为“三魂七魄”,其魂有三,一为天魂,二为地魂,三为命魂。其魄有七,一魄天冲,二魄灵慧,三魄为气,四魄为力,五魄中枢,六魄为精,七魄为英。
道教还认为“人要死时七魄先散,然后三魂再离”,书中举了西安半坡村遗址仰韶文化时期,儿童死亡用陶瓮做棺材,底部还有一个为孩子灵魂出入所留的小孔。在曾侯乙墓的漆棺图也画有小孔,同时还有一个包头老妇从其中探出头来,更解释了象征死者灵魂自由出入的理念。
《礼记·郊特牲》中说:“魂气归于天,形魄归于地”,也就是说魂为阳,是天气,上升而去,而魄是地气,归于地。在春秋战国就有灵魂升天的观念,多表现在帛画中,图画中表现出墓主人在诸多神异灵兽的引导下升天而去。
人们都希望真的存在另一个世界,人死了只不过是去了另一个世界,衣食住行依旧如常。而我们抬起头来的时候,更希望逝去的亲人升天后成为仙人,时刻陪在我们身边,保佑我们事事顺心。
古人有同样的愿望,他们害怕死亡但祈祷着新生命的到来,以此来维持聚落组织的延续,生生不息下去。都说中华民族就是务实,在困难面前我们是想方设法将其解决,所以我们造神也具有很强的实用性。而春秋战国时期的方士们顺应人们的需求开始了构架起神仙思想。
连千古一帝秦始皇及其以后的很多皇帝都想要长生不老,在汉代时秦始皇派遣徐福去找长生不老药的被动、无为状态发生了变化,编成了主动修炼。生时通过服食药饵、行气引导、房中术等修炼,死后在墓中放入丹丸、五石等供死者在墓中修炼。
当然在人们的观念里,并不是什么人都可以成仙,重要的先决条件是必须洁净自己的心灵和肉体,去除身上的“浊臭”,这也是修炼的目的。作者在书中研究并阐释了“解除术”,是秦汉魏晋时的一种避祸除殃的方术,也是汉代墓葬信仰的核心内容。
为了保护等同于初生婴儿一般的新入墓穴的尸体,不让鬼魂干扰,就需要采取诸多措施。在睡虎地秦简《日书》就出现了关于解除的记载,直到汉代已经发展成了一整套墓葬解除仪式。
根据使用解除术的位置不同,作者说明了墓门区域解除术、墓室内部解除术,根据解除术所用的形式不同又有葬仪文书和注鬼说、解注术释义。这其中包含了巫术,又包含了宗教,可以说是“巫术+宗教”的神仙道教。
最后一部分作者就“生居与死所的中介”——墓葬,讨论了汉代人们宇宙论的变化影响了墓葬建造的方式、形制,墓室壁画的题材、陪葬品的摆设方式等等。在中华文化中都讲究“天人合一”,当然在墓葬建造中就更加重视了。
人们都想为死者也营造一个和现在世界一样的生活环境,照着住宅的形式建造墓室,将贵重物品和生活物品随葬,希望在另一个世界亡者也能幸福生活。
总之,本书虽然只阐述和介绍了汉代墓葬形式的变化及信仰的变化,但墓葬文化是贯穿于中华文化全过程的,值得我们华夏儿女深入研究和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