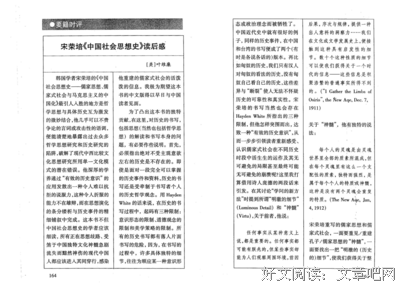
《什么是思想史》是一本由丁耘著作,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的平装图书,本书定价:36.00元,页数:402,特精心从网络上整理的一些读者的读后感,希望对大家能有帮助。
《什么是思想史》精选点评:
●第一个板块对初学者而言尤其值得一看:这是六篇外国思想史家关于思想史之研究对象与方法的论述。在《什么是思想史?》里,七位学者发表了自己关于“思想史”学科范畴的见解;施特劳斯反对历史主义、推崇经典的主张及其论据都呈现于第二篇文章里;阿兰·布鲁姆强调不带偏见地阅读原典,差不多是对施特劳斯主张的强调;波考克的研究思路涉及语言哲学。 宗成河《苏格拉底与现代政治》中关于“苏格拉底与现代科学”的部分对我颇有启发。彭刚对斯金纳的总结值得再读。 倒数第二个板块有西方学界研究中国近代史的最新动向——我很感兴趣,可惜毕竟是十数年以前的“最新”了,所谈都是我们已经熟悉的东西。最后是几篇书评,我没读过原书,因而没有看书评。
●貌似后面附的文章有点偏题,前面翻译的文章还是很有意义的,虽然有的是炒冷饭。
●选文和译本可圈可点。
●不错 不错 功利的说 拯救了我的考试 但 怎么又能满足于功利呢?
●主要看了关于剑桥学派与施特劳斯学派的几篇经典论文。什么是思想史或者观念史,历史主义、文本主义、语境主义以及新文化史研究都有着不同视角和侧重的回答。施派:施特劳斯《政治哲学与历史》阿兰·布鲁姆《文本的研习》 剑桥:波考克《语言及其含义》斯金纳《观念史中的意涵与理解》《言语行动中的诠释与理解》比较而言还是剑桥清楚一些。还有一篇彭刚对斯金纳思想史理论的梳理《历史地理解思想》后面对汪晖《现代中国思想的兴起》的一系列评论文章没有看,想来连书还没来的看呢。沙培德《西方学界研究中国近代史的最新动向》不错的综述。
●列奥·施特劳斯vs昆廷·斯金纳 1969年28岁的斯金纳发表《观念史中的意涵与理解》! 《政治哲学:来自剑桥的观点》蛮有趣的~
●斯金纳的文章精彩,其它一般。不过对施特劳斯的批评我看还是加大摩尔比较到位
●文章铺的面很宽,除了翻译有些地方让外行觉得困惑(实际上就是读不懂)之外,还是值得一看的。
●这本里主要收的剑桥学派的。彭刚那一篇是对剑桥学派和施派思想史研究各自得失的最清晰的分析。
●斯金纳的语境技术局限性相当大,既难以处理生活在大动荡时期的哲人思想,又夸大了许多无足轻重的语境的重要性。库珀评论剑桥学派致力于发掘思想史上的二流人物可谓入木三分。除去政治立场的对立,语境分析与“永恒问题”并不冲突,前者可以作为后者的技术性补充,更好地训练思想史研习者的头脑。至于永恒问题是否存在,我认为这不是凭理论可以清晰说明的,关键在于思想者本人能否达到哲人式的高潮体验,但是祛魅后的技术人(剑桥学派之流)当然不会承认这种多少有些神秘主义的东西,对于不可化约为语境的“人性”的丰富性也嫌重视不足。
《什么是思想史》读后感(一):有些文章好像译得不是太好
选题感觉还不错,但倾向性也比较明显。前面西学部分,选的大都是西方思想史界知名人士的作品,主要的当然是当今政治思想史上如日中天的斯金纳教授的作品,其它人的作品要么是作为其陪衬(如坡考克),要么就是作为对手(比如施特劳斯及其门下布鲁姆的作品),此三人都曾重点研究过马基雅维里。就翻译来看,译文似乎不是太好,读起来老起疙瘩,没有那种一气呵成的感觉,幸好手里有部分文章的英文版。第一篇是多人讨论什么是思想史,在后面“思想史论坛”部分也有剑桥学派对政治哲学的讨论;第二篇施特劳斯的《历史与政治哲学》(选自《什么是政治哲学》),我觉得启发挺大,尤其是对于历史主义的批评,这正好也是斯金纳反对的,由此也可见历史主义之深入人心,甚至在我当初读科林武德作品时,都没发现这种历史与哲学关系之紧张。后面有彭刚先生(曾译过施特劳斯作品)对当前思想史界的梳理,涉及对施特劳斯以及斯金纳的得失,可以参看。(未完待续)
先附個目錄:
什么是思想史?
什么是思想史?
政治哲學與歷史
文本的研習
語言及其含義
觀念史中的意涵與理解
言語行動的詮釋與理解
專題研究
歷史地理解思想
蘇格拉底與現代政治
思想史論壇
政治哲學:來自劍橋的觀點
經籍選刊
春秋要指
論語述何
思想評論
關于汪暉《現代中國思想的興起》的討論
西方學界研究中國近代史的新動向
讀書·評論
德國自由的起點——評 馬丁·路德《路德文集》
城邦的罪與罰——評伯德納特《神圣的罪業》
“雅努斯”:馬基雅維里的思想位置——評馬基雅維里《李維史論》
《什么是思想史》读后感(二):简述《观念史中的意涵与理解》
斯金纳的这篇文章一共分为六个部分,意在介绍他的方法论。 第一部分是要树立他的靶子,也就是传统的观念史家的研究方式——“研究和诠释经典文本”。这样做的理由是经典文本中包含着表现为“普遍观念”的“无时间性”的智慧,而其方法则是专注于言说本身。接下来,作者设身于其对立面进行了理解式的陈述,分析这一传统做法会造成谬误的原因。不同的文本表述中总会出现“相对稳定”的词汇,因此史家们只能依靠某种“家族相似性”或更正式的标准对其进行分辨,以使思想的历史可以被辨认。然而在这一分辨过程中,史家们不可避免地加入了“先入之见”,也就是他们的预期。斯金纳总结了这种困境:史家们为了分辨、解读这些文本,加入了先入之见,而加入了先入之见,则扭曲了文本自身的内涵。这种错误简言之曰“范式优先性”,它产生的是神话,而非历史。 以下的结构也很清晰,第二、三、四部分分别举例说明体系-学说神话、连贯性神话和预期神话。所谓体系-学说神话,是指认为经典作家必然在每个主题上都形成了自己的学说体系,反过来说,则认为未形成体系的则是不称职的。这种神话造成一种按图索骥式的研究,将只言片语无限放大,按理想形态追溯学说形态。连贯性神话是指,经典作家的文本一定是连贯的,反过来说就是,缺乏连贯性是一种罪过。这种神话导致了研究者的两种形而上学倾向,或忽略乃至放弃文本的不连贯之处,或勉强地建立联系。在这里,作者讥讽了列奥·施特劳斯为矛盾做辩护的行为,指出这种辩护的预设是:1.文本必然包含微言大义;2.没有看出微言大义的都是蠢蛋——其实陷入了一种循环论证的死胡同。预期神话是比以上两种神话更深一层的神话,意指史家们从其后观视角先带着预先判断来看经典文本,往往将不同历史时期的现象硬做比附,如妄谈“影响”,或任意的“概念化”。 第五部分,作者试图揭示造成以上神话的方法论漏洞,也就是只看文本不看语境。斯金纳指出,理解文本有两大任务,理解其意涵与理解其意图缺一不可。因为意涵随时代推移而不断变化,只有借助于理解意图才能理解意涵。作者进一步论述,如此一来,便不存在观念史,而只有不同的观念运用的历史和运用这些观念的不同意图的历史。他陈说自己之所以对传统方法产生怀疑的原因在于,他不相信概念的稳定内涵,也不相信经典作家们之言说行为的恒一性。 最后,作者再次概括性地陈述了自己的方法论,即注意言说针对的对象和言说的语境。其次,他高扬了观念史研究的哲学意义,即实际上不存在恒久的问题,不要试图从历史中获得解决当下问题的方法,要试着自己去回应问题。 从斯金纳的论述来看,我认为造成以上神话的根源在于其抹去了时间性,而斯金纳的一大贡献就在于他把“历史性”带回了观念史研究。 这篇文章初稿写于1969年,修订于2002年。作者在1978年出版了《现代政治思想的基础》一书,是对自己方法论的一次实践,在该书前言中,作者又简略谈到了这一方法论的意义,一是尽力提供历史真相,二是为从政治思想来解释政治实践提供路径,三是加深对文本的理解。
《什么是思想史》读后感(三):Memo:列奥·施特劳斯《政治哲学与历史》
我想列奥·施特劳斯可能不算一个思想史家,而是一个政治哲学家,写过一点政治哲学史——说是政治哲学史家也行。因为他追求的是永恒,而不是历史。不过,反对历史主义是否对他对过去的政治哲学典籍的理解有阻碍呢,这也是值得思考的。
1.政治哲学
“政治哲学不是一门历史学科。哲学追问政治事物之自然(nature),追问最好或正义之政治秩序,从根本上来说,这些问题不同于历史学的问题,后者通常关注具体事物……特别是,政治哲学从根本上不同于政治哲学自身的历史。”
2.政治哲学与历史的关系
政治哲学产生的前提是大量历史经验的积累:“如果没有对在不同国家、不同时代中的政治制度与信仰的多样性的体验,那么,对何谓政治事务之自然的追问、对何谓最好的或正义的政治秩序的追问,就永无可能出现。”(24)
而且历史所带来的变化能够避免政治哲学变成适应于某个特定时空的具体政治设计:“且这些问题被提出之后,唯有历史知识才能防止将某个时代和某个国家的政治生活的具体特征误作政治事务的自然。对政治思想史和政治哲学史亦当如是观。”(24)
但政治哲学不是历史,因为历史“通常关注具体事物:具体的团队、具体的人、具体的功业、具体的‘文明’、某一从起源迄今的文明进程,等等。”(24)换言之,政治哲学希望就某些问题得出答案,而政治哲学史是再现某些人为什么提出问题、为什么做出某种回答。
3.何谓历史主义:
“历史主义”首先被视作 混淆历史与哲学边界的人,历史主义将问题的历史放在了问题的本质之前。他们认为对一切问题的解答都受限于历史局限性,甚至据此认为应当放弃哲学,已取消传统哲学的普遍问题。
由于执着于“历史的局限性”,而后代人显然比前代人累积了更多的历史经验,因而历史主义倾向于怀有今人胜古的傲慢。
历史主义是不同于“历史意识”的。施特劳斯尊重真正的历史意识,因为它意味着客观性:“‘历史意识’反对这种方法,它正当地主张历史的真实性,主张历史的准确性。思想史家的使命就是理解以往的思想家,有如他们的自我理解,或者,根据他们本人地阐释来复活其思想。倘若放弃这一目标,也就放弃了思想史中唯一可行的‘客观性’标准。”(33 )他认为真正的历史意识就是明确“学说之创建者理解其学说的方式是唯一的,倘若他本人清醒的话。”(33)而思想史家应当还原这种唯一的理解。
【导师:历史主义并非强调历史的连续性,这是历史哲学。历史主义是指,认为事物唯有在具体历史情形中才能得以呈现与理解。】
4.反驳历史主义
就历史主义的基本思路而言,施特劳斯反驳道:“在不首先了解国家之所是,文明之所是,人之自然之所是的时候,怎么能够充分讨论现代国家、我们的文明、现代人这些问题呢?”(27)[我认为这个反驳并不很有效。因为他预设“国家”、“文明”或是“人”存在本质,而不是从历史中沉淀出了这些概念;他假想这些概念将一直存在并支配人们的生活(这些概念无疑是许多政治哲学“普遍问题”的基础),而且这些概念的本质不会突破他们从前包含的那些范围。类比文学,这就好比要求判断文学的本质,以求发明最美好的文学,但文学本身是在不断突破其原有概念范围的。……不过,“人”与“国家”、“文明”或是“文学”可能不太一样,因为人首先是实体,构成人体的物质可能决定了人具有一些不便的本质(不考虑赛博格)。]
历史主义者认为前代的政治哲学家是为了特定的时代背景而提出对应的政治哲学的,但施特劳斯提出:“他们理所当然地认为,政治行动由如下信念所引导:因其自身而成为最可欲之物,必然能够在一切场合实现自己,而不管场合的差异,这种信念适合于没有害人之意的良民,他们既非诡计多端,亦非明智通达之好人。”(28)换言之,因为政治哲学家追求的是“最好的”政治秩序,“最好”意味着它在所有场合中都是好的,因而任何一个背景下,政治哲学家都不会设想他的政治哲学回答在另一个背景下是恶的。因此,根据历史背景而否定政治哲学家在对普遍问题的回答上的客观性是不合理的。 此外,迎合时代的是政治行动,具有普遍意义的是政治哲学,施特劳斯相信前代政治哲学家将二者分得很清楚:“以往的大多数政治哲学家无视(或者更准确地说,因为)其思想的非历史特征,理所当然地在下述二者之间做了区分:一面是最好的政治秩序这一哲学问题,另一面是这一秩序能否或应否在某个时代的某个既定国家中建立起来这一实践问题。他们自然懂得政治行动不同于政治哲学,前者关注具体处境,因而必然是以对相关处境的精确把握为基础地,是以对这一处境之前提的理解为基础的。”(28)[但我想,问题在于我们如何辨别前代政治哲学家的哪些著作属于纯政治哲学的探讨,哪些属于实践的政治行动。尤其是那些面对他们的同时代人而写的著作——它们很可能是政治行动的,但是这些政治行动行动中难道没有包含他们的政治哲学思想吗?如果把属于政治行动的书籍移出政治哲学的研究范围,那么政治哲学研究将有许多损失;如果不移除,那么对它们进行历史分析是很必要的。]
历史主义误从没有政治哲学家一劳永逸地解答何为最好的政治秩序这一问题而得出结论说,非历史的哲学(也就是纯粹的哲学)应当终结。施特劳斯指出这种失败只能证明这个普遍问题尚未被回答,而无法证明普遍问题永远无法被回答。(29)
施特劳斯辩称,不同时代之所以会出现矛盾的政治主张,是因为政治学家们“是在着意使自己的观点迎合其他同时代人的见解”(30)。[我的想法:因迎合同时代人而扭曲、或是被同时代及后代人长久误读的思想,在思想史中有什么样的地位呢?思想史还有必要关注最初的那个没有被表达或是没有被接受的思想吗?我想,至少,对于政治哲学史而言前者是重要的,因为它是接近答案的一种尝试;对于思想是而言,后者是重要的,因为我们无法保证所有人都同样错误地诠释了它。]
而某种学说之所以“产生于”特定的时代,是因为这个时代有利于这种学说“被发现”:“与某一具体学说相关的某种环境,可能尤其有利于此种真理之发现,而其他环境则多少不利于它的发现。”(30)
另外,施特劳斯认为历史主义的态度妨碍了政治哲学研究。因为:“哲学批判首先要对被批判的学说有充分的理解。充分阐释就是像哲学家本人那样去理解他的思想。”(32)而历史主义,尤其是历史进步论使人们厚今薄古,不会在兴趣的支配下充分地理解过去的思想。
5.施特劳斯与斯金纳的对峙:本质论V.S.历史主义
施特劳斯明显相信人、国家、政治都具有本质。“换言之,一种政治哲学不能仅仅因为与其相关的历史环境尤其是政治环境成为过去而过时。因为每一种政治环境中都含有一切政治环境的本质要素,否则我们怎么能把所有这些不同的政治环境都称作‘政治环境’?”(31)他在反驳历史主义的许多论证都立足于该预设。
关于人的本质的证明,我觉得比对国家、政治具有本质的证明更铿锵有力:“然而,只要在人与天使、人与野兽之间的差异不曾被消除,或者,只要还存在着政治事务,那么,未来的可能性并不是无限的。既知是有限的,那么,未来的可能性就不完全属于未知的世界。确实没人能够预知未来所展示的可能性是明智的还是疯狂的(这两种情况都在人性限度之内)。不过,可以确知,那些当下所无法想象的可能性,也无法在当下言说。因此,我们不得不追随先辈,即追随先前的政治哲学对可能性所采取的态度,这些可能性或者已发现,或者已实现。至于那些只有未来才能知道的可能性,就把它留给未来的政治哲学家吧。”(37)
施特劳斯与斯金纳的根本对立可能就在于此。如果像施特劳斯所说那样,政治存在的本质,那么特定历史情境下的政治哲学思考就不会不适用于另一个历史情境,历史主义就是多此一举的。有点像柏拉图对话集里的那种思维:(理念的)善是不是在任何时刻都是善的,否则我们就不称其为善?[【我没有见斯金纳谈过“本质”或是“本性”这回事。】也许斯金纳也不是完全否定本质论的。在历史语境中还原思想,剥去历史加于某政治学说之上的那些部分,从而抽离出普遍性的政治哲学思想,这也未尝不可。】]
6.如何做政治哲学?
“政治哲学试图用有关政治基本原则的知识来取代关于它的意见,因此,政治哲学的首要工作就是使我们的政治观念变得清晰明澈,以便能够对他们作批判性的分析。”(38)
“‘我们的观念’只是我们的观念的一部分。在我们的观念中,大部分是民众的思想、老师(在该词的最广泛意义上)的思想以及祖师爷的思想的简化或残留,是过去思想的简化与残余。它们曾经是明确的,置身于思考与讨论的核心。甚至可以说,它们曾经极其晓畅易解。在代代相传中,它们发生了变化,无法确定这些变化是否为有意识作用之结果及是否是非常清晰的。不管怎样,这些曾经极其显白的观念(尽管并不一定是非常明晰的)被热烈讨论着,先在,它们蜕变成不言而喻的、隐晦的前提。因此,倘要澄清我们继承的这些政治观念,就必须使其在过去曾经是显白的隐微之意义,而现在,惟有通过政治观念史的方法才能使它重新成为显白地。在此意义上,哲学研究与历时研究完全融合了。”葛兆光在《思想史的写法》里提出任何一个时代的知识都是由一般知识与思想家的知识构成的,为了了解一个时代的思想、一个思想家思想的基础,有必要了解作为基础的一般知识。而施特劳斯则着意于将我们这个时代被广泛接受的一般知识还原为原来的深奥的模样。
7.历史主义之根源:现代哲学V.S.古典哲学
施特劳斯谈了由于现代哲学与古典哲学的不同,而导致历史主义的出现。但我没有看懂。【可能得补习哲学史。】大概意思可能是:古典时代缺乏历史意识,学者不觉自己的知识与古人有何差别,因此他们全力还原这些知识。这些知识在古典的任何时期都获得同等的阐释。但是现代出现了对原有知识的修正,何时、何语境下、为何有此观念则变得重要了。[但现代哲学为何会出现对古典的修正?其基础不正是一种注意到时代差异、意识到的古典之局限性的历史主义吗。因此,历史主义是内在于现代哲学的。我认为现代哲学不是历史主义的因,而是它的果。]
一些疑问:
1.历史主义与理性主义有什么关系?
“只是到了16世纪,才感受到一场根本的变化。这一开端的标志,是对以往一切哲学(尤其是政治哲学)的批判,是一种全新观念的出现:强调历史。在早期,转向历史,基本上被纳入理性时代的‘非历史性的’学说之中。17、18世纪的‘理性主义’从根本上说是更加‘历史的’,而不是前现代的‘理性主义’的。17世纪以降,哲学与历史以更快的步伐趋于和解。迄17世纪末,历史已经成为通常所谓的‘时代精神’。在18世纪中期,出现了‘历史哲学’一词。19世纪,哲学史通常被认为属于哲学学科。”(25-26)波浪线部分都令我困惑。
“建立在历史主义之上的哲学,一开始就是启蒙的,因为哲学的解答必定‘受制于历史条件’。”(36)
一些想法
1.我质疑施特劳斯关于“本质”的预设。
2.如我前面所说的,为了区别前人文本中哪些是纯粹的政治哲学思考,哪些是迎合时人的话,甚至是以语言的方式实现的政治行动,对经典作品进行历史主义的考察都是必要的。
3.诚然,先入为主地断定前人的思想因其历史局限性而不值得被仔细考察是不对的,但毕竟他们是有其语境的,随着其语境的消失,这些思想可能在当代的实践中变得不合适,这时我们就应该反思这些思想夹杂了多少时代赋予它的非真理。
延伸阅读:
施特劳斯《自然权利与历史》
《什么是思想史》读后感(四):《什么是思想史》读书笔记
丁耘编:《什么是思想史》(“思想史研究”第一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
【按:“思想史研究”第一辑收录了剑桥与施派文本方法论最核心的论文。施特劳斯这篇也收录于他的《什么是政治哲学》中,和波考克的那篇一样看的云里雾里;布鲁姆的对文本研习的温暖呼吁十分令人感动。最值得一说的是斯金纳的文章。斯金纳早年在剑桥求学时,拉斯莱特对《政府论》写作时间的考古证明了洛克的目标仅仅针对查理二世的绝对权力企图,而非发展成所谓自由主义责任政府的一般理论。这一论断极大地影响斯金纳的学术进路,他的一生就是就在不断努力将这种历史语境分析应用到所有研究对象之上——尤其是霍布斯。而二十八岁时的斯金纳的第一战便是以《观念史中的意涵和理解》对当时的英国历史学界的观念史、文本主义研究进行了毁灭式批判,堪称经典中的经典。看这篇文献最大的乔伊斯式享受当然是通过脚注考验下自己的学术鉴赏水平,果然萨拜因和罗素图样图森破;第二篇翻译得有点硬,先放着了。当然还要mark一下对汪晖大佬的评论】
什么是思想史
·编者按:施派翻译的代表如布鲁姆的《理想国》,Thomas Pangle的《法律篇》,Seth Benardete的《政治家》与曼斯菲尔德的马基雅维利。强调文本的“显白”与“隐微”,要求读者在文本的字里行间发现文本的自足性、连贯性和指涉问题的永恒性。剑桥学术进路的两大支撑:1原典的翻译与整理,即斯金纳与盖斯(Raymond Geuss)的剑桥政治思想史系列2斯金纳主持的“语境中的观念”丛书,已出版四十余种,第三代代表为塔克的霍布斯、塔利的洛克、温奇(Donald Winch)的斯密,维罗里(Maurizio Viroli)的早期共和主义研究。对原典的细读是中国学界最为紧迫的任务。1-2
·Stefan Collini:观念史Idea of history着重于我们心灵中自成一体的抽象物,他们在时间之流中独立航行,偶尔在特殊的心灵中短暂停留,类似德国的“精神史”Geistsgechichte;而思想史关注点是人类活动的某一方面,类似经济史与政治史。5
·Pocock:无论是思想史还是观念史似乎都是一回事,都是关于思想与观念如何找到各自位置的基础上有关历史性质的研究。这一活动有时被称为“政治思想史”,但我宁愿换另一个词,因为它无法概括行动,我更倾向“话语”discourse这个词,即speech和literature的公开言论,可以表示与语境、行动的联系。16-17
施特劳斯:《政治哲学与历史》,洪涛译,
见列奥·施特劳斯:《什么是政治哲学》,李世祥等译,华夏出版社2011年版
阿兰·布鲁姆:《文本的研习》,韩潮译,
【如何教育政治哲学家?】我们总是在问该如何教育下一代的政治哲学家?这句话意思其实是该如何教育下一代哲学教授。因为天才总是可以自我照看,而哲学也不是一种类似医学和制鞋的职业。为了教育政治哲学必须对其内涵达成一致——我们通常认为政治哲学就是寻求最好的生活方式、最广泛的善或正义以及最佳政体的知识;但是我们时代最为有力的思潮实证主义和历史主义都否定了这两者的存在。
【政治哲学教育的关键在于品格】我想指出政治哲学的教育需要形成一种品格,它必定是存在的,要尽可能去激励它而不是刻意去创造它。这一品格首先是对正义和真理的爱,不过两者的结合极为少见;因为对于正义的爱包含着某种义愤,这会压到科学所需要的冷静与中立,另一方面对于真理的爱又会打消正义所需要的对于特殊事物的关心——政治科学既包括理论也包括实践,因此任何一种极端视角都是科学的,尽管这是一种极端的诱惑。这也如帕斯卡所说几何学精神(geometrie)与敏感学(finesse)精神的不可能的统一。43-44
【学习的方法1:细读文本、细读最遥远的文本】这样的性情需要什么样的正确教养?答案是仔细研习文本、经典的传统文本——这就足够了。这永远是必要的——尤其是在我们这个时代。44
哪些人物必须被严肃对待?可以从基本达成一致的伟大哲学家那里开始,尤其是时间上最为遥远,最为时下所忽视的那些,这不是教条布丁好坏一尝遍知。51
【对文本关注的理由】1首先在于我们很难想象严肃的思考会推倒重来。2伟大的哲学家都是伟大的学者,他们就是研习者;尽管现代自然科学的进步为其他学科提供了一个范本,正如科学不需要科学史一般,学者也不再需要哲学。3对政治哲学的挑战从未如此强大,已经接近了虚无主义的边缘,我们的时代尤其需要文本的研习;寻求一个清除成见的范畴需要回到思想的起点,回到前科学的、前哲学的或者说自然的世界,否则我们只能透过联结现象的屏幕看世界,只能被一个人所愿意提出的解释所限;当科学卷入世界改变这个世界之后(如经济学家假定人是被利益驱动的,政治也是)这不仅丧失了那些挑战我们所钟爱信念的对手,也失去了能给我们的信念以最好的支持的人。44-48
【批判罗尔斯:没有讨论平等作为前提、对传统的无知】对我们的自我意识的威胁集中体现在这些年英语世界最富盛名的著作中——也就是罗尔斯的《正义论》,他为自由民主提供了新的理论基础但是对于其平等主义的前提从来没有讨论,但平等真的是正义吗?这本书另一个特征是对于政治哲学传统的极端无知:罗尔斯试图更新传统自然状态的契约理论却放弃了他们对于自然的坚持。现代的哲学家已经不是唤醒我们,恰恰相反,他们是在给我们催眠,罗尔斯已经完完全全落入了流行的意见的漩涡,因为他已经彻底拒绝接受任何来自外部的东西。49-50
【细读的障碍:不爱读书、矛盾的倾向、谬误社会学、一般化的倾向】我的处方就是尽可能细读作品,不过仍然存在一些障碍:
1从托克维尔对美国的智性倾向的分析来看,我们并不是一个注意理论的民族。
2我们的学生还有两种相互矛盾的倾向,足以摧毁他们对真理的追求:价值是相对的,这一信念有益于民主与宽容;而对于平等原则的真理则从未有过怀疑。
3所谓的“知识社会学”完全名不副实,它应该叫做“谬误社会学”才对,他们的看法是经济、心理以及历史的因素已经决定了哲学家的思想过程,对他们来说重要的是柏拉图是贵族、霍布斯是资产阶级、尼采和卢梭是疯子53-54。
4“一般化”其实是一种障碍,对于伟大哲学著作的研习往往堕落为一种抽象,因此小说家和诗人对我们理解哲学的智慧极为有益。因此文本的研习表面上看来与现象学运动相距甚远,但他们的动机是相似的,都是对一般观念导致的经验世界枯竭化的反动,同时对经验世界的再发现导向一个更为完善的一般观念。55-56
【研习的方法2:学习语言(virtu的例子)、借助作品内在表述的历史(托克维尔)
1作为学生首先注意到的是马基雅维利用意大利语写作,如果你不懂意大利语,你必须去学,即使有英译本也几乎是完全无法信任的。比如马基雅维利用virtu这个词表达了美德virtue、能力ability、才识ingenuity等意思,借助这个词的传统用法表明了他对价值的重估,他甚至用两句话使用了三字,不同分别指向完全不同的东西;但翻译往往翻译成不同的名词,那么马基雅维利的教诲当然也就被毁掉了。不过对于语言的学习必须以哲学关怀为指引,而非迷失在无望的语言学迷宫中。58-59
2不能从表面进入作品,必须借助于作品内在表述的历史。《君主论》中存在被内在建构的历史,如费拉拉公爵;他的作品中也提到了其他著作,尤其是《圣经》与色诺芬,马基雅维利期待的是远远比今天更有教养的读者,我们必须努力达到他的要求。
这还可以以托克维尔为例。一般认为托克维尔与卢梭相反,但是最近在讲到同情在民主制的一段时,我才认识到托克维尔的论述是建立在《爱弥儿》的基础上,二者不仅论证相同,而且材料也相同(拉封丹)。在托克维尔看来,现代人面临的选择要么是平等主义的民主制,要么是平等主义的僭主制。而这恰恰是卢梭的教诲,对这两位思想家来说,贵族制已经消亡了,贵族制是不正义的,却包含着某种真正的高贵,而现在高贵在民主之中似乎正趋渐消失。托克维尔与卢梭的政治规划就是要在平等中保有自由,在民主制中保有一种高贵的色调。61-62
以这种方式研习文本是一个永无止境的工作,对自然的研习也是如此,两种研习需要结伴而行并且融为一体,这是真正自由的研习,当然通过这样的研习,一个人最终会由学有所成,但此种学养需要一种坚持不懈的真正的品格,一种与生命的最高目标相关的品格,伟大的著作总是充满隐蔽的指引与含义,只有进入其中的人才能够理解。61
所有制度性的东西都阻碍着对作品的研习,无论怎样,我们的教育至少会给学生带来一种人性伟大的可能经验以及一种分享思想的共同体,这个共同体或许会改变他们对政治的期望。63
昆廷·斯金纳:《观念史中的意涵与理解》(Meaning and Understanding in the History of Ideas),任军锋译,
原载于History and Theory,1969
【错误的“研读”观,是“历史性谬误”,是一种神话】观念史家的任务应该是研究和诠释经典文本,这些文本由于其“普遍观念”是“经得起时间检验的智慧dateless wisdom”,读者可以从中研读而受益匪浅;而阅读的最佳途径就是将注意力集中于这些“基本概念”。← 我接下来将对这些预设进行质疑与批评,如果有可能,使其信誉扫地。 对于经典作家的各种研究不可避免会陷入各种形形色色的历史性谬误historical absurdity的危险;通过这些途径得出的结论是神话,不是历史。95-99
一 学说的神话历史学家们创造了“学说的神话”mythology of doctrines,即认为每一位经典作家必然在某一主题上形成了某种学说体系。这一神话的形式有:
1将经典作家的零星或即兴论述转化为现代人期待主题的学说
这进一步导致两种历史性谬误:
1)时代误置anachronism的思想传记,即认为某一作家持有某一论点,而实际上他只是碰巧使用了类似的术语,如马尔西里奥的《和平的守卫者》中就统治者的行政角色与人民的立法角色做过亚里士多德式的论述,当代著述家会将这一论述追溯到罗马共和国的蜕变,但实际上马尔西里奥并不知道这段历史知识;再比如柯克大法官的邦汉姆医生案(Dr.Bonham’s Case)的判词认为英格兰的习惯法有时超越成文法,这被当代评论家认为是司法复审的前奏,但其实他的意图仅仅是向詹姆斯一世表明法律的特征是习俗而非主权者的意志。
更危险的行为是从经典文本中找到期待的学说,如胡克的《论教会政体》区分教会的神圣起源与公民联合体的世俗起源时,现代评论家会将其视为“社会契约”;洛克《政府论》中对委托权trusteeship的零星评论被整理成了“基于人民同意的政府”(如Gough)。
2)观念单元unit idea。这一方法的目标用其开创者洛夫乔伊的话来说就是,确立某一学说的理想类型之后在一切历史领域追溯这一类型的形态学。这一方法的危险之处在于:被考察的学说成为一种实体,而言说的主体消失了,代之以观念之间的格斗——分权学说内战期间几度出现,到了一百年后三权分立才完全建立。这一具象化导致历史谬误:对于理性类型近似物的观察到了某种学说因为“预见”到了而具有价值。如马尔西里奥之所以值得关注是因为他预告了马基雅维利,而马基雅维利之所以值得关注是因为他为马克思奠定基础;言下之意就是作家的伟大程度取决于他们与我们一致的程度。99-104
2经典作家若未能就主题提出认可学说则不称职 表现形式为:
1)鬼魔学版本。如霍布斯马基雅维利因为最早鼓励人们不服从而倍受谴责(Allen Bloom、 Harry Jaffa、Leo Strauss自然权利与历史、关于马基雅维利的思考、什么是政治哲学),在这里范式决定了历史研究,只有抛弃这一范式本身我们才能对历史做出重新诠释。
2)将现代的主题赋予经典理论家,尽管他们实际上并未讨论,如马尔西里奥一定会赞同民主,因为他主张主权在民。在历史的面具之下历史学家将自己的偏见强加在死人身上,历史成为了我们捉弄死人的把戏。
3)更普遍的策略是:抓住理论家未言及的学说然后批评其不足。如批评柏拉图忽略了公共舆论,批评洛克忽视了家庭与种族(Sabine、Aaron、Russell、Dahl、Richard cox)104-108
二 连贯性的神话(the mythology of coherence)
1文本连贯性。不难发现某些经典作家前后并不一致,但是后世会想当然地赋予文本连贯性,以获得对于著述家理论体系的连贯性认识。有时某一著述家的目标变动不居时就难以找到这样一个体系,便声称马克思从未试图提出“自己的”基本理论(sabine);或者将洛克的政治思想视为一个观念整体,索性称为“自由主义”的著作,这样一来三十多岁采取反对立场的洛克显然还不是“洛克”(M.Seliger)
2内在的连贯性。这一视角关注如何解释表面的矛盾之处?在这一点上奥卡姆的剃刀原理(表面的矛盾可能就是矛盾)被抛之脑后。这一信念见于施特劳斯的笔端,他认为这些矛盾是迫害的威胁。这一辩护以两个先验预设为基础:原创性就意味着颠覆性、且解读言外之意的基础是无懈可击的,能洞穿言外之意的人值得信赖与聪明的。我们得到了一个循环论证——如何确定一个时代属于迫害的时代?答为这样的时代是非正统著述家探寻特定写作技巧的时代。这一技巧是否一直在发挥作用?答曰当不得不这样表达思想时需要这样做。109-114
三 预期的神话(the mythology of prolepsis)这一神话将观察者特定历史时期的意义与研究历史时期的意涵的非对称性生硬地合并到一起。如经常有人说当彼特拉克登上旺图山Mount Ventoux时便拉开了文艺复兴的序幕,这种浪漫主义口吻的描述不可能是彼特拉克的真实意图;再如人们将柏拉图和卢梭的政治主张概括为“极权主义”(K.Popper, Alfred Cobban, J.L.Talmon).这一神话将会带来两种偏狭parochialism:
1一部著作会让历史学家想到另一部或更早著作中类似或相反的论证,于是认为后来者是有意针对早期著作而大谈早期著作的影响:如伯克对柏林布鲁克作出回应,而后者受洛克影响,洛克又受霍布斯影响,霍布斯又受到马基雅维利的影响。这都是神话的解释,这需要考虑以下条件:首先B研读过A的著作;除了A,B不可能在任何著作家那里找到相关学说;B不可能在没有受到任何读者的影响下找到相关学说。马基雅维利对霍布斯、霍布斯对洛克的影响甚至连条件一都无法满足;而以上的结论都无法满足条件三,甚至说我们不清楚如何满足条件三。
2历史学家描述著作意义时会误用他们的视角。比如将“民主”范式引进研究,在平等派的思想中找到“福利国家”。
最后值得强调的一点,涉及到思维活动的本身,我们需要认真对待如下事实:思考过程是一项需要投入相当精密的活动···我们经常与语词和意涵鏖战···我们时常发现,我们力图综合我们观点的过程中所暴露出概念的混乱,并不亚于那些系统的学术体系。诠释者们常常会忽略这一点,他们会将珍贵的碎片系统的呈现出来,或者试图去发现某种程度的连贯性,在这里经常表现在思维活动中的煎熬与迷惑不见了,所有的激情都被耗散殆尽。115-122
结论如果我的论证成立,我们可以从中得到两个肯定性的结论。第一个涉及到观念史应当采用的适当方法,即考察特定言论与更为广泛的语境之间的关系来揭示特定作者的意图。第二个牵扯到观念史研究的价值,即哲学分析与历史证据有可能实现对话。试图从经典文本中找到“恒久问题”提供答案作为学科的基础是完全站不住脚的,我们不是要在哲学史上寻找直接可借鉴的“教训”,而是要学习如何更好地思考;经典文本关注的是他们的而不是我们的问题。历史本身就能够提供一种教训,使我们有自知之明(self-knowledge)。131-13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