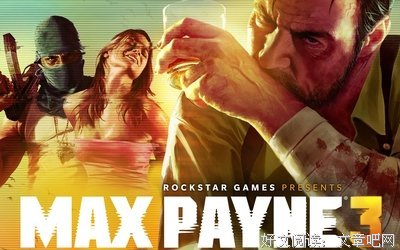
《韦伯与马克思》是一本由【德】卡尔·洛维特著作,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的精装图书,本书定价:88,页数:512,特精心从网络上整理的一些读者的读后感,希望对大家能有帮助。
《韦伯与马克思》精选点评:
●
●翻译真的差
●啥时候能买到啊
●洛维特再难读,也不能翻成这样吧……
●韦伯和马克思的根本区别在于,马克思通过异化概念将之解释为“自我异化”并与之做斗争的东西,在韦伯那里却被认作是理性化这一无法扬弃的命运(p.114)。韦伯在各种论文中都毫不妥协地坚持社会科学中的“价值中立”的意义,并且坚持客观科学和主观价值、关于事实的普遍联系的知识和互相无关的个人态度直接的截然区分(p.123)。对我们来说,最后的前提、相应的手段和设定目标后的可能的后果的基础,都显然在于人怎样“从自己出发”理解自己的生活,也就是说,它与“超验的东西”没有任何联系,人们必须自己选择和决定生活的各种可能的立场(p.135)。结合雷蒙·阿隆对韦伯的描述来看,“韦伯以伤感的目光注视着理性化的社会和对宗教信仰的需要的矛盾。世界的幻想破灭了。”
●韦伯是长于融合的。马克思是矢心撕裂的。
●作为一个不挑剔翻译,读中译本得过且过的人,也不得不指出本书有严重的翻译问题。尤其从书名,人名等错误上看,这更多是译者态度上的问题。
●完全看不懂的书有很多,比如费恩曼的物理学教材,我的感觉是痛恨自己没有好好学好数学和物理学基础。这一本看不懂给我的感觉不太一样,具体来说我生出一个疑问:为什么要研究哲学?这玩意儿到底有啥用?如果说原典(比如本书涉及的韦伯,马克思和黑格尔)之类的还多少有点感觉。那对于在原典之上的抽象分析那真的是要人命。真道不同不知所云…只能放弃了吧。
●正在翻,印象上译得不错,可读性比较强,可以放心购买。我真不明白了,科维纲那本《现实与理性》译得连亲妈都不认识,也能那么卖座叫好。
●译者毁掉一本书,唉……可惜了
《韦伯与马克思》读后感(一):勘误贴
随便翻了几篇费尔巴哈相关的文章,感觉译者有点偷懒。一是人名、书名不去核对,经常让人莫名其妙;一是注释做得不够扎实,分明是大段引用,居然没有脚注;三是沿用的译文版本太旧,都9102年了,居然还用马恩全集第一版。
摸着良心说,人名虽然都是音译,但也有惯例不是吗? Chiang Kai-shek 译成“常凯申”固然没有错,但学界惯例还是叫“蒋介石”的吧?!
随便举几个例子:
第220页,“胡格”,应为“卢格”
第222页,“宇宙主义”,应为“世界主义”
第229页,“《德国唯心主义》”,应为“《德意志意识形态》”
第238页,“卡波特”应为“卡贝”;“怀特林”应为“魏特林”
第223页,“《黑格尔法哲学批判》”,疑为“《<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
《韦伯与马克思》读后感(二):韦伯与马克思
https://athenacool.wordpress.com/2019/12/02/%e9%9f%a6%e4%bc%af%e4%b8%8e%e9%a9%ac%e5%85%8b%e6%80%9d/
韦伯与马克思:以及黑格尔与哲学的扬弃 【德】卡尔·洛维特 / 刘心舟 / 南京大学出版社 / 2019-9
子扉我 2019年秋 季风异次元空间二世
原载回响编辑部微信2019年12月3日
《韦伯与马克思》读后感(三):笔记 | 马克斯·韦伯与卡尔·马克思
《韦伯与马克思——以及黑格尔与哲学的扬弃》,卡尔·洛维特著,刘心舟译,南京大学出版社2019年出版,三辉图书出品。关于本书的更多的介绍,可点击公众号“三辉图书”的推送:《韦伯与马克思》:对现代社会的犀利批评 | 新书。我读了这本书的第一部分,第二部分准备先补充阅读一些黑格尔相关研究著作再进行阅读。这里的笔记是对第一部分第一章节的梳理,关于第二章《马克斯·韦伯和他的后继者》第三章《马克斯·韦伯的科学观》也推荐阅读。(可查看相关推送:马克斯·韦伯的科学观)
问题的提出与其相似性
卡尔·洛维特认为关于我们的现实社会的科学有两种,一种是市民社会的社会学,另一种是马克思主义的社会学。他将韦伯视为市民社会的社会学的代表人物,而马克思则当然是马克思主义社会学的开创人。虽然这两个人严格说来并不处于一个时代(马克思,1818-1883;韦伯,1864-1920。在马克思成就最辉煌的时候韦伯还没有成年,还没有正式成为一名学者),但是两个人着力研究、处理的问题却是相似的,两人都着力研究现代经济和社会的“资本主义”形式。并从以下的特定视角出发:把以这种形式而非别的形式不断经济化的人当作问题的主线;并且这种分析作为一种对人的经济和社会的批判式的分析,它同时也是对和事实不同的关于人的“理念”所进行的批判。
洛维特通过对韦伯和马克思的基本研究动机进行比较性分析,指出他们对于作为经济和社会之基础的人的理念之看法的共同点和区别。他们都着眼于同一种“市民的”人,尽管他们所做出的批判截然不同;也就是说,他们两人的批判都涉及处于我们的历史规定性中的我们自己。 在韦伯与马克思的学术生涯中,他们都试图对“资本主义”的发展作一个科学的研究。就他们原初的研究动机而言,他们看到了我们人类此在的实践问题,并以此出发对当代的生活方式之整体提出了质疑,而整个质疑的总标题就是:“资本主义”。他们都——马克思是直接地而韦伯是间接地——以市民-资本主义为红线,对生活在市民社会中的当代人做出了一种批判分析。他们的分析是基于这样一种经验,即“经济”已经变成了人的“命运”。针对这一问题,马克思提出了“疗法”:人们应当“重新支配他们相互交往的形式”;而韦伯则只是提供了一种“诊断”,而反对提出“疗法”的行为。他们对资本主义的解释就体现了他们的这种差异,也就是说,对韦伯来说,资本主义本身是一种中性的东西,但他对它的价值评判采取了一种双重的立场,即韦伯将它分析为一种普遍的同时又不可避免的“理性化过程”;而马克思则相反,他的看法完全是消极的,即资本主义是一种普遍的然而必须加以革命的“自我异化”(当然,马克思还是肯定了资本主义巨大的历史作用)。
英文版只有第一部分《马克斯·韦伯与卡尔·马克思》(Taylor & Francis e-Library, 2003)。理性化:韦伯的方法与研究
在韦伯那里,其所探索的原初的和整个问题,就是我们周遭的现实性的根本特征,我们就是被置于这样的现实性之中的。他的“科学”研究的最后动机则是趋向于此岸的倾向。而韦伯将我们的现实性本身的总问题归结到“合理性”(理性化)这一标题下。 对韦伯来说,理性化从根本上意味着西方生活方式的基本特征以及我们的整个“命运”——尽管我们对于这同一个命运可以有不同的对待方式,例如韦伯和马克思的方式就不同,与之相应的,对这个命运也可以有不同的解释方式:韦伯采取了宗教-社会学的解释方式,马克思采取的是社会-经济学的解释方式。在韦伯看来,合理性不仅是资本主义经济的特征,也是一种西方特有的“生活行动”和“生活方式”——是一种新的市民-资本主义-新教的“伦理”与“精神”。新教“伦理”和资本主义“精神”之间具有内部的——经济的态度和信仰的态度之间的——亲和力,并塑造了西方国家中的市民——他们也自然而然成为其“杰出承载者”。
韦伯认为,合理性是和行动的自由一起出现的,它是一种作为“目的论的”合理性的自由:是一种在对适当的手段的自由斟酌中,根据最终的价值或生命的“意义”所预先规定的目的。这种目的理性的行为将自己的“人格”塑造为一种向着最终的价值进行的持续不断的人类行为。作为自由的个人行为,它意味着以目的为导向,也就是说,是对某种给定的手段是否能够达到预设的目标所进行的理性测量,并由此而进行连贯的或“为了某种结果的”行为。而手段和目的之间的伦理“张力”(也就是说对某种“善的”目的之达成可以依赖某种可以的手段)使得责任的合理性本身变成了一种特定的伦理。但是,却往往产生这样一种不容忽视的结果——一开始只是单纯手段的东西——是实现另一个具有价值的目的的手段——自己却变成了目的或者自身的目的,于是,本来是手段的东西就独立为一种目的性的东西。在马克思那里,类似的分析是“拜物教”——物对人的统治的形成;在齐美尔那里,是一种“文化的悲剧”,是人“栖居在了桥梁之上”。
怎么在合理性与“人形机器”之间寻找人的价值与生活世界的意义?怎样拯救个人的行动自由?怎么在普遍从属性中的个人中寻求自由的自我负责的条件?如何解决人和专业人之间的矛盾?这些问题都是韦伯着力思考的点,韦伯并没有对这些问题都给出一个具体明晰的答案。对于最后一个问题,古典社会学家都有过阐述:这一问题在涂尔干那里不成为问题,他反而认为人要想获得自由必须依靠职业群体所构筑的道德规范与集体表象;而在马克思那里,这涉及到人的自我异化,必须实现人的真正的而解放。而在韦伯看来,人需要找到一项事业作为其“天职”,在价值领域寻找自己所信奉的“神”并“侍奉”之。
在本书中,对《韦伯方法论文集》的引用采用了这一版本的中译:《韦伯方法论文集》,张旺山译,联经出版事业股份有限公司2013年出版。已列入小编计划阅读书目,相比大陆出版的《社会科学方法论》这本方法文集内容更多、翻译更好一点。 自我异化与人的解放“自我异化”与人的解放
我们可以看到,对韦伯来说属于“不可避免的命运”的东西,对马克思来说无非是人性的一种“史前时期”;而马克思认为真正的历史所开始的地方,在韦伯看来却是一种不负责任的“信念”之伦理开始的地方。比较韦伯与马克思的世界观和关于人的理念,区别也体现为,他们对现代市民-资本主义世界的解释也采取了不同的视角,而这种视角是某种提供标准的东西:在韦伯那里,阐释的视角是“合理性”;在马克思那里则是“自我异化”。 对马克思“自我异化”观的考察,则要进一步研究马克思的思想脉络——尤其是他对黑格尔与费尔巴哈哲学思想的继承、批判与颠覆。
洛维特简要总结了马克思思想的发展道路:它首先是对宗教的哲学解读,然后是对宗教和哲学的政治解释,最后是对宗教、哲学、政治和其他所有意识形态的经济学批判。 马克思所关注的基本问题同韦伯一样是围绕我们周围的现实性,我们被置入这种现实性之中,并且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生产过程的批判性分析一开始所采取的形式就是以生产过程中人自身的异化为红线而对市民的世界进行批判。马克思的思想发展之路的起点和终点都是作为人本身的具体的人,并且,他相信他已经在无产阶级身上发现了一种“新的”人的可能性。他最后想达到的是(并且始终都是)“对人的人性的解放”——“真正的人道主义”。马克思对黑格尔的“绝对精神”进行了批判,又对费尔巴哈的“抽象的”人进行了严厉批判。马克思对处在整体的特殊性当中的单个的特殊性,也即对作为市民的人本身进行描述。为了解放处在他的整体的人之特殊性当中的人,并且为了扬弃人之特殊性本身,马克思要求一种对人的“属人”的解放。因此马克思将对市民世界中的人的批判贯彻为对人的社会和经济的批判。在马克思那里,异化问题在经济上的表现就是商品的世界;在政治上的表达就是市民的国家和市民的社会之间的矛盾;它的直接的人的社会的表达就是无产阶级的存在。
在蛰居英国的一段漫长的岁月之中,马克思着力于对资本主义的政治经济学批判。不过,我们也应该看到,马克思的集大成之作——《资本论》——并不是单纯的政治经济学批判,它同时是以其经济学为红线而进行的对市民社会中的人的批判。马克思在其中,着力研究了“商品”中所体现的自我异化在经济上的表现。 除此之外,马克思对市民社会中人的自我异化的政治表达也进行了大量的论述。在马克思看来,对人的自我异化的特殊的政治表达是:现代国家和市民社会之间的矛盾,以及市民社会中的人和市民国家中的人本身之间的矛盾。在这样的社会中,作为与公共的普遍性有区别的私人的人,这种人自身只是人类存在的一种私人方式。在马克思所阐述的共产主义社会的共同体里却相反:在其中个人是作为个人(即最高的人格)参与到作为属于他的“共同之物”的国家当中。
在马克思看来,所谓的资产阶级的政治解放一方面把人变成市民社会的成员,变成利己的、独立的个人,另一方面把人变成公民。而只有当人认识到自己的“原有力量”并把这种力量组织成为社会力量而不再把社会力量当作政治力量跟自己分开的时候,只有到了那个时候,人类解放才能完成。因此,在马克思看来,只有在人作为其本身而相遇的共同体中,也就是说,通过对人的存在的社会改造和在人的自我意识中,真正个人的自由才有可能。与此相反,市民社会中的私人只是根据他自己的想象才有某种特殊的自由——而在事实上,他却是全面依赖和“隶属于物的力量的”。而马克思认为,无产阶级是对人的自我异化的社会性的突破,无产阶级是实现人类解放的主体力量。
韦伯对唯物主义历史观的批判
与其说韦伯不遗余力的坚决批判马克思、马克思主义,不如说韦伯批判的是一种经济决定论的所谓的“历史唯物主义”的庸俗马克思主义。韦伯反对历史做一种同一的和单一的解释,这在韦伯的宗教社会学研究中,也被反复指出。韦伯在其宗教社会学研究中,并不是与唯物史观相反以一种精神主义的方式处理问题,而是通过放弃任何一种形式的单义的还原,并代之以对历史现实性的所有因素中互相对立的条件进行一种“具体的”历史学研究。韦伯并不是希望以片面的唯心论与历史因果解释,来取代同样片面的‘唯物论的’文化历史观。
韦伯将自己的方法与马克思主义方法之间的不同描述为一种“经验的”方法和“教条的”方法之间的不同。而他的“经验的”方法之优越性的根本意义却只在于,这种方法好像从专门学科的观察中必然的“片面性”走向了专门学科式的“多面性”,这是和关于世界的陈述中的教条主义单义性相对立的。事实上,它更多的还在于,韦伯想要通过放弃了“全面的人性”和包罗一切的“对世界的描述”,而消除对随便那种特定的给定内容的任何一种论断,放弃了由此产生的向着一种幻觉的“整体”的扩张。他事实上所想反对的,并不是存在和观察的总体性,而是将特殊性向着整体性的可能的固化。
《韦伯与马克思》读后感(四):【转】李哲罕:克服现代性-虚无主义的一种尝试——论卡尔·洛维特对该问题的思考
原载于:《现代哲学》 - 2015
卡尔·洛维特(Karl Löwith,1897—1973)卡尔·洛维特(Karl Löwith,1897—1973)出生在慕尼黑一个改宗新教的犹太人家庭,父亲是一位富有的艺术家。早年深受尼采和德国青年运动的影响,在一战爆发后,他毅然参军,后负伤被俘。在战后的1919年,他在慕尼黑聆听了马克斯·韦伯“以学术为志业”的讲座,并受到托马斯·曼的《一位非政治人物的反思》影响,决心投身学术事业,后因慕尼黑政治局势动荡,转学弗莱堡跟随胡塞尔,1923年以《论尼采的自我解释和对尼采的解释》获得博士学位。像当时很多年轻学者一样,洛维特被海德格尔所吸引,1928年他在海德格尔的指导下完成了关于“主体间性”问题的《人的共在中个体的角色》的就职论文,在马堡任教。因为犹太人的身份,洛维特的学术事业并非一帆风顺:1934年离开德国去意大利做客座教授,后局势恶化,在1936年去日本任教,并在珍珠港事件前的1941年前往美国任教,最终于1952年在伽达默尔的帮助下回到海德堡大学任教直至退休。
虽然洛维特学术黄金期的十几年都是在颠沛流离中度过,但他在这个时期仍然完成了多部非常有影响力的学术著作。
他的著述涉及非常广泛的主题,在此仅将考察线索限于他对现代性-虚无主义问题的思考上。
一、现代性-虚无主义问题
在一战后德国的衰败气氛中,尤其是严重的经济危机和洛维特父亲的破产等原因,使得洛维特直接体验到物质的贫乏和精神生活-日常伦理的崩溃,开始直面现代性-虚无主义问题。
因为现代性和虚无主义是相伴随的,所以总是被联系在一起称为现代性-虚无主义问题。对前现代的人而言,很难设想虚无主义问题。现代性-虚无主义问题是指在现代社会中,社会失去了原有支撑其的坚实基础:虚无主义源于拉丁词汇nihil,意思为“无”或“没有”。经过启蒙运动、宗教改革和文艺复兴以来的现代欧洲人,放弃了原本构成本体论基础的古希腊宇宙论和基督教神学理论,形成了基于(人的)理性的理论。但在后启蒙时代,启蒙理性被贬斥到只局限在“工具理性”层面上,人们对于“价值理性”存疑的时候,虚无主义作为极端的相对主义-怀疑论的产物就应运而生。简言之,虚无主义即是从本体论基础上被剥离到伦理学上价值或意义的丧失:旧的业已崩溃,新的还未到来。
现代性-虚无主义问题在德国思想传统的土壤中获得了最为充分的发展,并走向完全对抗西方式现代文明的激进化。不过对洛维特以及和他同时代的德国思想界来说,现实问题只是哲学问题的实现或结果,因此对现代性-虚无主义问题的考察必然是指向对其背后整个西方哲学发展史的考察。
在1932年的《马克斯·韦伯与卡尔·马克思》这本书中,洛维特通过考察马克思和韦伯这两位现代-资本主义社会的批判者,尝试考察现代性-虚无主义问题。他之所以选择韦伯和马克思,是因为他们两人所考察的领域都指向“一个在现代经济和社会中的‘资本主义’组织”Karl Löwith, Max Weber and Karl Marx, edited and with an inrtoduction by Tom Bottomore and William Outhwaite, London and New York: Routledge, 1993, p.42. 。洛维特如是刻画其研究目的:“对马克思和韦伯的科学考察的非常明确的主题乃是‘资本主义’,然而这项研究的动机则是人——他们不确定的本性是被‘资本主义’这个词汇所刻画的——在当代人类世界中的命运问题。这个蕴含在资本主义问题中的问题,是关涉当代人类世界的,并反过来蕴含着在资本主义世界之中人之为人的条件——即何者构成了在这样一个世界里人的人性——的一个明确定义。”Ibid, p.43. 洛维特分析,对于资本主义文明化所带来的负面效应,马克思是通过“异化”的概念,而韦伯是通过“理性化”的概念来诊断的:马克思对此是乐观的,即通过对“异化”的克服达致“自由王国”;而韦伯对于“理性化”的“铁笼”则多少有些悲怆感,但也没有放弃以克里斯玛式的人物来拯救这一切。洛维特认为马克思的普遍世界历史趋势的实现和韦伯的这种个体存在式的相对主义并不能解决他所要解决的现代性-虚无主义问题,因为他们都陷于现代思想的主体性思考之下来考虑人性,并将自然-世界看作是一个与人相异在的对象,而非将之作为构成人性根本的基础。
《马克斯·韦伯与卡尔·马克思》揭示了洛维特所关注的主要问题,他之后的主要工作便是在整个观念史上揭示现代性-虚无主义问题。不容否认的是,这个问题对近现代德国思想界影响巨大:对尼采、海德格尔、洛维特和施特劳斯等都有恒久的影响。在面对这个问题时,上述四人都认为是西方哲学传统的发展出现了问题,并试图通过对这个传统在现代意义上的转折或断裂的揭示和批判,回到在这之前的古希腊-罗马(或犹太)的思想中去寻求“权力意志”、“存在”、“自然”或者“自然权利”,来矫正现代性-虚无主义问题。
二、尼采:现代性-虚无主义问题的
洛维特将现代性-虚无主义问题研究的焦点放在了尼采身上。因为正是尼采在现代性-虚无主义问题完全展现自身之前预见和开启了它:“‘欧洲虚无主义’只有在一个德国人,即尼采那里才被认为是一个真正的哲学主题,而它也只有在德国才有能力变得如此活跃。”Karl Löwith, Martin Heidegger and European Nihilism, Richard Wolin (ed.), Gray Steiner (trans.),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95, p.224. 洛维特通过尼采指出虚无主义的本质是:“他(尼采——笔者注)预见到了‘欧洲虚无主义’的兴起,这种虚无主义认为,在基督教对上帝的信仰以及随之而来的道德的没落之后,‘不再有真的东西’,而是‘一切都被允许’。”〔德〕卡尔·洛维特:《从黑格尔到尼采》,李秋零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6年,第255页。
洛维特认为,德国哲学传统是在黑格尔和歌德之间的岔路口走向了滑进虚无主义深渊的道路:“在黑格尔按照自己的基督教神学出身把历史理解为‘精神的’,并把大自然仅仅看做是理念的‘异在’的时候,歌德在大自然自身中看到了理性和理念,并由它出发找到了理解人和历史的一个入口。”同上,第304页。 他指出,尼采的观念实际上是自黑格尔和青年黑格尔学派以来德国哲学的一系列衰败的最终结果:“经过青年黑格尔学派从黑格尔导向尼采的道路,最清晰地与上帝之死的观念相联系表现出来。”同上,第253页。
但是尼采的思想并不止于此。在洛维特看来,虚无主义分为两类:“一个是被耗空了的存在意志的衰弱征兆,但是另一方面,它也可以是意志的和一个意欲毁灭的力量的第一个信号——即一种消极的衰弱的或一种积极的强健的虚无主义。”Karl Löwith, Nietzsches Philosophy of the Eternal Recurrence of the Same, Translated by J. Harvey Lomax, Foreword by Bernd Magnus, Oakland: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97, p.50. 尼采无疑属于后者:他在揭示虚无主义问题之后,试图通过超人的权力意志“重估一切价值”从而完成对于虚无主义的自我克服。不过,洛维特认为尼采的思想中存在尼采自身无法调和的两个矛盾的方面:一是上帝之死,为了“重估一切价值”的超人的权力意志,二是一种永恒的轮回——“尼采真正的思想是一个思想体系,它的开端是上帝之死,它的中间是从上帝之死产生的虚无主义,而它的终端则是对虚无主义的自我克服,成为永恒的复归”(〔德〕卡尔·洛维特:《从黑格尔到尼采》,李秋零译,第261页)。
洛维特正是从尼采的永恒轮回说中获得了一种克服现代性-虚无主义问题的进路,当然他同时也借助经现象学-存在主义的“生活世界”概念所重构的自然,克服尼采思想中所存在的矛盾。按照洛维特的解释,尼采的这种拟制的“永恒轮回说”的设想本身已经存在于古希腊的自然观之中:“尼采因此不仅怀疑对世界不满意的人(‘反对世界的人’)对世界的反对,也怀疑对两者(‘人和世界’)的并置。我们自身已经是世界——但这并不是因为我们作为我们周围世界的一部分而存在,或世界只是人类存在的一个决定因素,而是因为所有的包含、反对和并置一直被存在着的、物理的世界之包罗万象的存在(它是一个存在和消失与创造和毁灭的永恒轮回)所超越。”Karl Löwith, Nietzsche’s Philosophy of the Eternal Recurrence of the Same, p.189.
同时尼采的思想在消极方面——即“超人的权力意志”——也影响深远,但是他自己却和俾斯麦德国保持着足够的距离。正如洛维特所说:“尼采现在是、也将一直是德国的反理性特质或德国精神的总结。在他与其肆无忌惮的宣扬者们之间虽隔着一道深渊,可是他却为他们开了一条路,尽管自己并没走上去。”〔德〕卡尔·洛维特:《纳粹上台前后我的生活回忆》,区立远译,上海:学林出版社,2008年,第10页。
三、海德格尔:贫瘠时代的思想家
海德格尔则彻底走上了尼采所开启的道路,并且这在他与纳粹的关系中得到完全的显露。在二战结束前,洛维特很少有直接针对海德格尔的批判,毕竟他跟随这位“梅斯基希来的小魔术师”十多年,深受他的影响。但正是洛维特在二战后对海德格尔的一系列批判使得某些问题得以澄清:海德格尔在后《存在与时间》时期的思想都是他的《存在与时间》中所暗含面向的发展。
在展开对海德格尔的直接批判前,洛维特在1935年(一说1936年)匿名发表了一篇对卡尔·施米特的批判文章,并提及了海德格尔在“政治时刻”的思想转变。在这篇文章中,他指出施米特的政治决断论是通过将各种决断论的理论来源去除构成它们自身本体论基础的基督教神学思想,并将自身置于虚无之上的理论。洛维特认为,施米特的这种除自身外不受他物约束的“机缘决定论”一致于海德格尔的存在决定论:“如果海德格尔的存在的决定论是一致于卡尔·施米特的政治的‘决断论’——将一贯以来的个人本己的此在的‘为了整体的存在的能力’替换为一贯以来的个人本己的状态的‘整全性’——则是毫无意外的。在战争的政治紧急状况中,一个人本己的此在的自我主张是一致于政治存在的自我主张的,而‘面向死亡的自由’则是一致于‘生命的牺牲’。在这两人的例子中,原则是一样的,即‘本真性’,也就是去除了所有生活的内容之后所留下来的生活。”Karl Löwith, Martin Heidegger and European Nihilism, Richard Wolin (ed.), Gray Steiner (trans.), p.215.当时德国的现实政治或纳粹运动却给他们提供了自身理论所需要的“内容”,因此他们投身于其中便可以得到理解。
海德格尔深受尼采的影响。他希望复归到古希腊,以扭转几千年来遮蔽了存在的、主导欧洲的形而上学传统,恢复存在的本身面貌,并以此来克服在这个意义缺失的时代里的现代性-虚无主义问题。对他来说,虚无主义是“在世的沉沦”,同时也是获得拯救的可能。按照洛维特的理解,海德格尔虽然以“在世之在”的方式试图消除笛卡尔式的两个实体(即人和自然)之间的区分,但是却依旧没有为此在找到基础或内容,而需要在一种直面死亡(未来,或绝对的虚无)的时间性和历史性的开放性中去寻求可能性或意义,即是走向了尼采所开启的虚无主义之路。
洛维特对1933年海德格尔当选弗莱堡大学校长时的致辞《德国大学的自我主张》——这篇文献是关于海德格尔与纳粹关系的问题上最重要的文献——的评论是十分切中要害的:“这篇演说将海德格尔的历史存在的哲学移植到德国局势之内,第一次给他意欲发挥影响力的意志找到了立足的基础,以使得存在范畴形式性的轮廓得到了一个决定性的内容。”〔德〕卡尔·洛维特:《纳粹上台前后我的生活回忆》,区立远译,第44页。 即海德格尔“为了将存在的历史性的本体理论置于现实历史,也就是政治所发生的本体性的土壤之上,将其最为明确的自我的此在转换为‘德意志的此在’”Karl Löwith, Martin Heidegger and European Nihilism, Richard Wolin (ed.), Gray Steiner (trans.), p.75. 。洛维特指出,《德国大学的自我主张》正是海德格尔之前在《存在与时间》中思想的发展:“从整体上说是一个剧烈转变和被唤醒的存在的哲学,它已经成为政治的。”Ibid. 洛维特的上述观点也得到了海德格尔自己的承认,1936年在罗马意大利暨德意志文化中心讲座后,他对洛维特指出,自己之所以选择支持国家社会主义,原因根植于他的哲学本质。“海德格尔毫无保留地表示同意,并且对我解释,他的‘历史性’的概念正是他‘投身’于政治的基础。”〔德〕卡尔·洛维特:《纳粹上台前后我的生活回忆》,区立远译,第72页。
根据洛维特对海德格尔内在的、连贯的哲学上的批判,海德格尔这种基于历史性的思想正是黑格尔以来德国哲学衰败的结果;“它们不是对永恒的和自我同一的实在的表达,而是对变化着的时代要求的(表达)。”Die Hegelsche Linke, (Stuttgart: 1962), pp. 9 ff., im Jürgen Habermas, Philosophical-Political Profiles, Frederick G. Lawrence(trans.), Cambridge: Polity, 2012, p.90. 所以,洛维特将海德格尔称为“在贫瘠时代的思想家”:“在事实上他(海德格尔)是在时间的基础上思考存在,作为‘在一个贫瘠时代的’一位思想家,他的贫瘠是因为他处在一个双重的匮乏之下(依照他对荷尔德林的解释):‘那些消失的神明已经不再存在,而将要到来的那一位还未出现。’”Karl Löwith, Martin Heidegger and European Nihilism, Richard Wolin (ed.), Gray Steiner (trans.), pp.38-39.
四、历史与自然
洛维特克服现代性-虚无主义的方式是通过对历史哲学的思考,剥离救赎历史与世俗历史的历史意识,回到古希腊人的自然观之中。
在1933年1月8日致施特劳斯的信中,洛维特已经基本形成了自己对于克服现代性-虚无主义问题的看法:“克服历史主义不可通过任何历史的绝对化和教条的时间性(海德格尔),而应藉助自己的历史环境之向前推进的命运,人们正是在这个处境里进行着哲学思辨而一起前进的,并且与非常不自然的文明联袂而行……被还原迻译为非在于人的天性,即唯一完全自然的天性的人,并不是自然的人,因此,我使人的天性的规定性先验地附丽于——始终具有历史性的——人性。”〔美〕施特劳斯等著,〔德〕迈尔编:《回归古典政治哲学:施特劳斯通信集》,朱雁冰、何鸿藻译,北京:华夏出版社,2006年版,第70—71页。 在同一封信中,他谈及和施特劳斯的观点上的差异:“为着眼于未来,绝对的历史的正当性始终应属于当今。然而,您却将恰恰不再是我们的历史的一个历史绝对化,并以绝对的古代取代绝对的基督教……基于一种彻底历史的意识,我却已经完全非历史地进行着思考”同上,第72页。 。
在1935年4月15日致施特劳斯的信件中,洛维特指出:“您为此提出的解决办法,即彻底批判‘现代的’前提,从时代历史上和内容上看,对于我都是遵循着尼采‘进步’方向:这就是说,将思考进行到底,一直到现代虚无主义,而我本人既不从这种虚无主义跳进基尔克果悖理的‘信仰’,也不跳进尼采同样荒诞的重现说,而是……将这类‘彻底的’颠倒从根本上看成错误的和非哲学的,并离开这种毫无节制和绷得过紧的东西,以便有朝一日也许能够以真正古代晚期的方式(斯多阿的-伊壁鸠鲁的-怀疑论的-犬儒的方式)达到现实中可以实践的生活智慧,达到‘最切近的事物’而非最遥远的事物。”同上,第235页。
在古希腊人看来,对于自然而言,并没有历史,因为它一直在进行生成、变化和毁灭的永恒的循环;对于人而言,才有历史,即过去发生过的事情。古希腊人的这种历史观和后来所指向“未来”的,以及要寻求“终极目的”的“历史意识”相比,相距甚远:因为古希腊人从自然中所理解的仅仅是“命运”,而非其他。
洛维特在《世界历史与救赎历史:历史哲学的神学前提》中运用一种“还原”式的方式倒叙欧洲历史哲学的发展,正像该书的英文版标题《历史中的意义》(Meaning in History)所指明的那样,洛维特尝试回溯过往的思想史以寻找历史中的意义:“无论是异教,还是基督教,都不相信那种现代性的幻想,即历史是一种不断进步的发展,这种发展以逐渐消除的方式解决恶和苦难的问题……认真地追究历史的终极意义,超出了一切认知能力,压得我们喘不过气来;它把我们投入了一种只有希望和信仰才能够填补的真空……(在这个问题上——笔者注)希腊人比较有节制。他们并没有无理地要求深究世纪历史的终极意义。他们被自然宇宙的可见秩序和美所吸引,生生灭灭的宇宙规律也就是解释历史的典范。”〔德〕卡尔·洛维特:《世界历史与救赎历史:历史哲学的神学前提》,李秋零、田薇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2年,第7—8页。 洛维特指出,晚期基督教和现代人则彻底改变了希腊人的自然-历史观:“从犹太教的预言和基督教的末世论中,教父发展出一种根据创世、道成肉身、审判和解救的超历史事件取向的历史神学;现代人通过把进步意义上的各种神学原则世俗化为一种实现,并运用于不仅对世界历史的统一,而且也对它的进步提出质疑的日益增长的经验认识,构造出一种历史哲学。”同上,第25页。 不过,这种进步论的历史哲学在现代社会却变成了衰退,变成了虚无主义:“时间本身在‘进步’之中断丧,只有在‘永恒’作为存有之真理现身的那些片刻里,‘进步’以及‘衰败’的时间性图式才会展现为历史性的虚像。”〔德〕卡尔·洛维特:《纳粹上台前后我的生活回忆》,区立远译,第167页。 洛维特的结论是:“历史问题在历史自身范围内是无法解决的。历史事件自身不包含丝毫关于一种全面的、终极的意义的指示。”〔德〕卡尔·洛维特:《世界历史与救赎历史:历史哲学的神学前提》,李秋零、田薇译,第229页。
正是从这种历史哲学出发,洛维特高度赞扬了和尼采同一时代的历史学家布克哈特:“布克哈特抛弃了神学的、哲学的和社会主义的历史解释,并由此把历史的意义还原为纯粹的连续性——没有开端、进步和终结。”同上,第230页。
五、小结
洛维特对现代性-虚无主义的克服方式,是回归到一种古希腊的完满的自然-人性中,不再意欲或追求终极的目的或意义。这也至少部分地解释了他和现实政治之间拉开距离的原因。正如洛维特在1936年的《布克哈特,在历史中间的人》中剖白似地评价布克哈特所言:“文化是不受宗教约束的和不关心政治的人(在躲避国家和无能的宗教期间)的主要世界。关心文化是他们不关心政治的结果。这些人不能够,也不愿意参与政治事件,他们的自由是以退出在国家中的不自由生活为前提的。”〔德〕卡尔·洛维特:《雅各布·布克哈特》,楚人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13年,第170页。 他的这种固守象牙塔并将被认为是洪水猛兽般的现代性-虚无主义拒之门外的思想,的确让他免于像海德格尔一样参与到纳粹运动中去,并对现实政治保持一分有距离感的冷静;但同时这种表现又是德国学者在现实中失意时所表现出来的“非政治”的典型特征。我们不禁要问,又有多少人能像他这样在这个不会回头的、已然现代化的社会中,复归于古希腊自然-人性的思想呢?
同时,洛维特对现代性-虚无主义问题的这种克服方式,又是在典型的德国思想传统的语境内实现的。但是,在这个思想传统中的思想家都“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一般都没有能够设想到是否是德国自身存在的问题(或所谓德国的独特性),才是导致其无法安适于现代社会的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