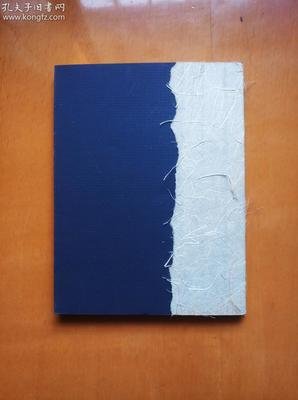
《奥州小道》是一本由[日]松尾芭蕉著作,北京联合出版公司出版的精装图书,本书定价:49.80元,页数:256,特精心从网络上整理的一些读者的读后感,希望对大家能有帮助。
《奥州小道》读后感(一):待到归来时
游记或纪行文这一类的书籍我向来是有一点疏远的态度,所接触的中国古代有名的游记文章全在中学时的课本上,故而我对“奥の細道”的印象只是停留在首句“日月乃百代之过客”上,没有再往下深读。
直到去年秋读完了松尾芭蕉的俳句,最喜欢他那句“暂悬于/春花之上——/这月夜”,有一种清清冷冷的喜气。可能是受唐诗的影响,松尾芭蕉俳句的意象和氛围更为高远,譬如另有“梅花如此白——/昨天白鹤被/偷了吗”,化用白居易“偷将虚白堂前鹤,失却樟庭驿后梅”句,此番读《奥州小道》陈德文先生的译本,在开篇《野曝纪行》中也有此句,是“访三井秋风鸣瀑之山家”时所作,译作“梅林一片白如雪,谁人昨日盗鹤去”,渐渐于纪行文中找到了俳句的对照,觉得也是有意思的事情,方才带着愉悦读下去。
可能因为经历的事情尚少,松尾芭蕉俳文中那些人生的道理我知之甚浅,自然也不如别人讲得透彻,倒是文中的人情十分可亲。《野曝纪行》中就有芭蕉为茶店女主人写俳句的片段,因为女主人的名字叫“蝶”,因此在其白色的绢袖上写下“兰香熏蝶翅”,还在俳文《兰之香屋》辞中补充说“犹如庄周之梦”。关于名字在《奥州小道》中也有一则,是一位村夫六岁的女儿名“重子”,曾良作俳句“重瓣抚子花”咏之,松尾芭蕉也作了《贺重子》的俳文,还与曾良笑谈“我若有子,当用该名”。似乎都是很小的事情,却也可见人情的贞亲。
除了芭蕉与乡民,僧人之间也有深厚的情谊。俳文《竹中梅》里说:
先年旅宿京华,与行脚僧相识于道中。今年春,此僧欲赴奥州一游。行前访我草庵。芭蕉还为之作“待到归来时,再赏竹中梅”。萍水相逢的两位僧人分明行踪无定,却能够许下来年共同赏梅的约定,无论那位行脚僧是否能够践诺,这都是人生的一桩美好回忆了。
以前读俳句时有“欲知我的俳句——/秋风中/在旅途上过几夜吧”,循着注脚找到了《野曝纪行绘卷》跋,陈德文先生译作“口中读我句,心上秋风起”,使我想要追随松尾芭蕉的脚步去走一走他经过的路了。
《奥州小道》读后感(二):芭蕉诗文随笔下的六朝风韵。。。
芭蕉的散文,我的书架上原就有一本,最近拿到手里的这本最新译本,雅众出品的,更值得细细品读,仅仅因为这个译者,陈德文老师。
他翻译的芭蕉,有一种古典的契合感,读来让人踏实,令人惬意。
松尾芭蕉作为日本古典文学的一个高峰,一个象征,一面旗帜,他在诗歌(俳句)和散文(游记俳文)双领域都有卓著的成就,当然还有他那传奇而孤绝的人生经历,令众多后辈诗人望尘莫及。
松尾芭蕉的散文集,中文市面上整体比较少见,之前见过较早的一个《奥州小道》,译者是另一位老师,不太熟悉,深蓝色封面挺别致,可惜早绝版了,没买到。去年出了一个彩色图文版,书名翻译为《奥之细道》,似乎有点过于拘泥于原文,有点别扭。不过里面的浮世绘风景插图是个亮点,引诱我买了一本,绘画果然让人享受。
不过,陈德文老师的这个译本似乎更值得信赖。
很久以前买过一本日本散文集,《自然与人生》,德富芦花的代表作之一,文字古雅,简净,清逸,隽永,颇有意境,读来所获匪浅。当时极为震惊,这简直不像是翻译作品,就是原创的汉语散文集嘛。一看译者,第一次知道“陈德文”这个名字。从此在心目中,将陈老师视为当今一位不可多得的翻译大家。
所以,看到本书是陈老师所译,就觉得这个译本是很好的选择。
看目录(习惯了读书先看目录或序言),本书中收录了两个部分:游记和俳文。基本涵盖了芭蕉的大部分重要的经典散文。游记中除了六章游记(日记)代表作,俳文的篇幅占据三分之二,这是之前很少了解的。读完整本书,算是对芭蕉的散文有了较全面的认知。
芭蕉的散文,无论是游记还是俳文,都有一个特点,就是文中或多或少夹杂着零零散散的优美俳句,诗与文相得益彰。这种格式让人容易想到中国古典章回小说中时不时穿插的写景诗(如“有诗为证”“有道是”云云),所以本书可以说是一部诗文集。
这部散文集,可以说是芭蕉一生不断在旅行和隐居度过的行居轨迹——一竿踽踽独行的身影(尽管他的身边有时也会有追随的弟子),拄着木杖,走向寂冷的幽径深处,或结庵于芭蕉之下,或寄宿于古刹之中,看云,听雨,冥想,写诗……这本书便成了他在旅行和结庐隐居中的孤寂的点滴体验,独特的见闻和感受,他用韵散结合的游记文记录了下来。也是他日常生活和深刻生命体验的一部文学浓缩。
之前读芭蕉的俳句多一些,散文读的少,不过这本诗文集,可以看出,芭蕉的文与诗的风格是高度一致的,简洁,幽寂(也有人说玄寂),加上译文的古雅,更显得作者惜墨如金,没有多余的口水和废话,有如精简的诗意随笔。这又很容易让人联想到《徒然草》和《方丈记》,不论是文笔还是风格,这两部日本古典随笔深受过芭蕉的影响。
还有俳文,书中多为跋文或序辞,文体骈散结合,文字凝练而颇有六朝风韵,古朴雅致。比如其中的《洒落堂记》《乌之赋》《虚粟辞》等诸篇,字字珠玑,堪称绝妙好文。
再如《银河序》中略选末尾一段:
“推窗远眺,以慰旅愁。日既沉海,月犹黯淡。银河半天,星光闪闪。海上涛声阵阵,魂消肠断。旅梦未结,墨衣渗泪,以手绞之。”读之朗朗上口,而又婉媚动人。
文中穿插诗句琳琅满目,应接不暇,感觉与中国的五言绝句重逢。如:
“春去鸟空啼,鱼眼浮泪滴。”
“月阴云气重,钟沉海水深。”
“水上山花落,波间鸥鸟浮。”
“千千绿岛翠,片片烟波明。”
……
最后稍稍挑一个小小的瑕疵吧,这个版本唯一的缺点,就是没有插图,纯文字。毕竟,译文不好的,插图可以作为弥补;译文优秀的话,添些插图(比如东山魁夷的风景画,本人比较喜欢),可谓锦上添花。
《奥州小道》读后感(三):俳圣の旅途
文| 伊达政宗疯了 【本文会同步发布到全网,全网唯一ID:墩蛋探险记】
《奥州小道》被翻译为多国文字,持续感动着全世界。而“奥州小道”也逐渐成为环游日本的一条重要路线,备受各国文艺青年的推崇。芭蕉行脚所经的是江户时代陆奥国(奥州)与出羽国(合称“奥羽”,略称为“奥”)之间的小路,“奥”又有“深远的意思,故“奥の细道”的英译为“Narrow Road to a Far Province”(“通往远方的小径”)。
我曾跟小师妹说,除非你对日本文学有着不同寻常的热爱,不然还是不要去读什么“俳句”,“俳文”,“连歌”了。倒不是说这种东西有多难理解有多深奥,而是你愈是了解中国的古诗词,就会越分辨不清“俳句”和汉诗的差别。就连在芭蕉本人的头脑里,“俳文”一词也是一个模糊的概念。谁都不知道,什么样的文章算俳文,什么样的文章不算俳文。我对俳句有一种简单的理解,那就是把中国某首古诗词中摘出两句或三句,就可以视为一个俳句作品。比如说柳永的《雨霖铃•寒蝉凄切》,"寒蝉凄切,对长亭晚,骤雨初歇。"可以视为一个俳句作品;"念去去,千里烟波,暮霭沉沉楚天阔。"也是个俳句作品;"多情自古伤离别,更那堪,冷落清秋节!"是一个;"便纵有千种风情,更与何人说?"也是一个。俳句好像是一首歌的副歌,或诗篇中最精妙的一句,它就像一个快餐品,或是给来不及细细品味者的猛料。
我自认为自己跟这本书有着莫大的渊源。我大学的专业是日本语科,对松尾芭蕉的俳句有过学习。恰逢大学期间《搞笑漫画日和》正流行,里面也有这个“俳圣”芭蕉的角色,从认知上讲,我对这个人物很亲切。我爱玩KOEI的太阁立志传Ⅴ,这个游戏对我的日本战国史功课起到了极大的帮助作用,室町时代的武士家臣我都烂熟于心,对于那时的日本地理称谓也很了解,松尾芭蕉走过的路,我脑海里都有风景的画面。我和芭蕉都喜欢旅行……以上种种可以确保我,读起《奥州小道》不存在知识上的障碍。
但当我真的开始细品这本书时,却发现还是有一些心理上的隔阂在阻止我静下心来欣赏。
我想了很久,才发现是文化认同感。就像我文章开头所说,我本人对唐诗宋词非常热爱,对于遣唐使的典故也颇为了解,自己又是学日语出身,对中日文化的交融很熟悉,所以打心底对日本古时候的俳句,俳文之类的有一种“心理上的蔑视”。
松尾芭蕉对中国唐宋两朝文人十分推崇,经常在行记中化用他们诗词。“国破山河在,城春草木青”,把“深”改为“青”,这韵味真是天差地远咧。
“俳句”是对绝句诗的模仿,这种念头在我脑海里挥之不去,就如同千利休之于陆羽,日本的茶道之于中国本土的茶经。我知道带着这样的成见,继续读下去意义也不大,索性放下书,搜索起松尾芭蕉的生平事迹。我一向认为作者的人生履历对其行文风格的影响很大,了解作者能帮助我更好的了解作品。
芭蕉死于1694年,享年51岁,即使放到那个年代看,也算不上长寿。在他生命的最后10年,只有俳句和他的弟子曾良陪伴着他。芭蕉一生无妻无子,半生都是穷困潦倒。他曾在贞亨4年(1687年)仲秋为了欣赏中秋满月特地到鹿岛神宫(位于鹿嶋市一游。也因此写了篇游记提作《鹿岛纪行》。同年10月在举行如同达官显要般的饯别宴会后松尾芭蕉开始向另一阶段的长途旅程出发。 旅程经过了上野、大阪、须磨、明石、京都、名古屋、日本中部地方山区。此外并前往更科里欣赏姨舍山(今长野县千曲市的冠著山)的中秋满月。这段从上野到明石的旅程详细叙述在《笈之小文》或《笈中小札》。松尾芭蕉对寄情于山水之间的中国古代文人很是推崇,在旅途中,奥羽国的山川美景也激发了他俳句的创作欲。其中,更是诞生了六篇纪行•日记。芭蕉评价自己的纪行文章:“似醉者之呓语,梦者之谵言。”他认为,自己并非常人,而是一个狂人,大可不必局限于一草一木、一山一水的具体记述,他写的是“意象的风景”“山馆野亭的苦愁”。他是为了记下一个“在风雅的世界里徘徊”的自己的影子。临终前他留下了最后一句俳句:旅途罹病,荒原驰骋梦魂萦(行旅中病了,梦在枯槁的荒野上回荡)。
至此,我已释然,我决定把《奥州小道》当作纪行文来读,谁让我是那么的喜欢在路上的感觉呢。下面我将结合日本的历史和地理给大家讲解,在路上边走边吟诵着的芭蕉之路。
篇一:《野曝纪行》
芭蕉于贞享元年(1683年)秋八月离江户,回故乡伊贺上野,为前一年去世的母亲扫墓。其后,游历关西各地,包括被誉为日本的温泉之乡和疗养胜地的箱根,富士山畔,伊势神宫,大井川。于名古屋出席《冬日》连句诗会,收揽各地新弟子,经甲州返江户。此文当执笔于回到江户处理完杂事之后的一段时间。《野曝纪行》是芭蕉最初的一部纪行作品,不免有尚未成型之憾。内容由前后两部分组成,其结构和《奥州小道》类似。
如今的关西地区,即关西地方(日语:かんさいちほう,与关东地区(东京都、茨城县、栃木县、群马县、埼玉县、千叶县、神奈川县)相对,是指以关原为界以西的地区,包括:大阪府、京都府、兵库县、奈良县、和歌山县、滋贺县、三重县。关西地区拥有日本三大都市圈之一的大阪都市圈。在松尾芭蕉所处的年代,早在1496年,本愿寺莲如在大阪修建石山本愿寺。石山本愿寺附带有庞大的寺内町,聚集有众多人口。当时,上町台地尖端有一个称为小坂的地名,这就是“大坂”的语源。其后,御坊周围发展成为寺内町,奠定了现今大阪的基盘。在战国时期,大阪是兵家必争之地。1570年开始,织田信长和石山本愿寺之间爆发了长达10年的石山合战,最后两者讲和,信长退出本愿寺。不过信长在退出本愿寺之前烧毁了本愿寺的建筑。1583年,丰臣秀吉在旧石山本愿寺的土地上修建大坂城,以大阪作为其统治的中心城市。
富士山,代表日本的名山。随着季节其美丽的景色会呈现出不同的面貌。在有史之前就被视为灵峰而为众人信仰及喜爱,为日本之象征。位于骏河国(东海)兴国寺城西北。
伊势神宫,寺社,由于祭祀天照大御神与丰受大御神,因此从全国各地前来【伊势参拜】的参拜者络绎不绝。供奉著三种神器之一的八咫镜。位于伊势·志摩国(东海)鸟羽城正北。
大井川:是日本铁道迷里人气很高的秘境。
篇二:《鹿岛纪行》
贞享四年(1687)秋八月,作者离江东深川之芭蕉庵,到鹿岛赏月。先从住居附近搭便船,沿小名木川溯流而上,穿中川,入船堀川,再沿江户川到行德。接着,步行三十公里,于当天傍晚到达利根川的布佐码头。然后乘夜航船抵鹿岛。翌日,十五日,参拜鹿岛神宫,同时拜访根本寺前住持、禅师佛顶和尚。文章里,因为雨潇潇下,芭蕉没能看到十五的月亮,但他并没有懊恼,而是去拜访了佛顶和尚,“欲觉闻晨钟,使人发深省”。过一会儿始得清净之心。东方既白,和尚叫醒了我,人们也相继起床。月光,雨音,景象清幽,心情激动,无可言状。不远千里,前来望月,实乃令人遗憾。此时无法觅句的我,正好寻到了一位知音。
松尾芭蕉的心态我是很佩服的,他不远千里来到鹿岛只为赏月,却不想天公不作美没看成。我也有过羊年去梅里雪山转山未遂的经历,那感觉真是糟透了,真感觉还要再等个12年一轮回。但芭蕉话锋一转,说自己能在这深山中觅得一知音也不错。这心态还是值得我学习的。
鹿岛神宫,寺社,相传于纪元前660年建立,为东国三社之一。所祭祀的神祗为武瓮槌大神。有著壮丽的朱色樱门。位于常陆国(关东)鹿岛之町正南海边处。
篇三:《笈之小文》
贞享四年十月至翌年初,芭蕉到关西做了一次探访“歌枕”(和歌所吟咏的名胜古迹)的旅行。十月二十五日离江户,经东海道,在故乡伊贺上野迎来新年。然后,在杜国的陪同下,游览吉野、高野山、和歌浦、奈良、大阪、须磨、明石等地。四月二十三日进入京都。《笈之小文》便是以此次旅行为素材的纪行文。这是一篇未完成稿,作者殁后十五年始刊行问世。
松尾芭蕉首次提到了他对于纪行文的看法,“此种平常事谁都可为之,然而,若无黄山谷,苏东坡诗中的奇闻异事,则无须写成纪行文。”所以芭蕉的纪行文,对意境的描写远多于实景的描绘。
高野山,为真言宗开山始祖·空海创设金刚峰寺之场所。与北方的比叡山延历寺同为山岳佛教的中心地,深受人们的信仰。位于纪伊国(近畿)根来之里正东不远处。
篇四:《更科纪行》
贞享五年(1688,九月三十日改元元禄)八月,漂泊于名古屋、岐阜之间的芭蕉,在名古屋的越人及其仆人陪伴下,经木曾路去信州更科观赏中秋明月,之后由长野经碓冰山口返江户。这次旅行既是《笈之小文》之旅的延长,又是一次富于独特风情的览胜。
篇五:《奥州小道》
更科之旅结束后,芭蕉于江东深川的芭蕉庵迎来元禄二年的新年。此时已有作一次奥州之旅的打算。三月二十七日,芭蕉在曾良陪同下离开江户,徒步巡游奥羽、北陆各地,八月二十日抵大垣。旅期五个月,行程二千三百五十公里。以此次旅行为素材写成的《奥州小道》,最能反映作者那种“狂人徘徊于风雅之世界”的创作理想,是芭蕉纪行文中的代表,也是古代日本记游文学的巅峰之作。
这次是松尾芭蕉旅途最长,历时最久的一次旅行,一路见闻颇多,也诞生了“日月乃百代之过客,去而复来的旧岁新年也是旅人”这样的佳句。
奥州小道旅程图最后附上几段书中我爱的句子吧。
马上吟
道旁木槿花,马儿吃掉它。
于海滨度过一日
日暮海水暗,但闻凫声白。
南宋禅僧慧开《无门关颂》
大道无门,千差有路,透的此关,乾坤独步。
《奥州小道》读后感(四):译者序:送您一个完整的芭蕉
一
日本三重县的伊贺上野是一座小城,距离名古屋不算远,乘关西线快速电车西行约两个半小时就能到达。这里是传统文化气息浓厚的古城,十七世纪中叶,就在这座上野古城里,诞生了一位伟大的俳人(俳句诗人)、散文家、文坛一代宗师松尾芭蕉。松尾芭蕉(1644—1694),幼名金作、半七、藤七郎、忠右卫门。后改名甚七郎、宗房。俳号宗房、桃青、芭蕉。蕉门弟子在其编著中,敬称他为芭蕉翁。别号钓月轩、泊船堂、夭夭轩、坐兴庵、栩栩斋、华桃园、风罗坊和芭蕉洞等。芭蕉十三岁丧父。随后入藤堂家,随侍新七郎嗣子主计良忠。良忠长芭蕉两岁,习俳谐,号蝉吟,师事贞门俳人北村季吟,芭蕉亦随之学俳谐;同时,作为蝉吟的使者,数度赴京都拜访季吟,深得宠爱。宽文六年(1666)春,蝉吟殁,芭蕉返故里,所作发句、付句散见于贞门撰集中。宽文十二年(1672),著三十番发句合《合贝》,奉纳于伊贺上野的大满官。是年春,下江户(一说延宝二年,1674),居日本桥界隈。当时,正值谈林派俳谐全盛时期。芭蕉和谈林派人士交往甚密,逐渐崭露头角,成为俳坛宗匠。然而,芭蕉虽属江户谈林,但比起锋芒峻厉的田代松意和杉木正友等人,讲究自制与协调,作风较为稳健。延宝末年至天和初年(1681前后),谈林俳谐渐次式微,过去热衷于此派的俳谐师们,纷纷暗中转向而寻求新路。
延宝八年(1680)冬,芭蕉蒙门人杉山杉风之好意,移居深川芭蕉庵。天和二年(1682),芭蕉庵遭火焚,遂流寓甲州,翌年归江户。其间,芭蕉逐渐将俳谐改造成一门崭新的艺术,创立了具有娴雅、枯淡、纤细、空灵风格的蕉风俳谐。他在天和三年(1683)出版的俳谐集《虚栗》的跋文中说“立志学习古人,亦即表达对新艺术的自信”。贞享元年(1684),作《野曝纪行》之旅,归途于名古屋出席俳谐之会,得《冬日》五“歌仙”(连歌俳谐的一种体式,每三十六句为一歌仙),此乃蕉风俳谐创作成果的一次检阅。此后,芭蕉于《鹿岛纪行》《笈之小文》《更科纪行》等旅行中,进一步奠定了蕉风俳谐的文学地位。元禄二年(1689)芭蕉的《奥州小道》之旅,可以说是蕉风俳谐的第二转换期。他倡导所谓“不易流行”之说,主张作风脱离观念、情调,探究事物的本质,以咏叹人生为己任。其后出版的《旷野》《猿蓑》等,更集中体现了蕉风俳谐的显著特色。元禄七年(1694),芭蕉赴关西旅途中,于大阪染病,于当年十月十二日辞世。
二
本书内容包括纪行•日记和俳文两大部分。
从艺术表现角度来说,日本的纪行文学就是富有文学意味的游记,作者的主观感情色彩强烈,而所见所闻只是作者表达思想和见解的舞台和道具。行文注重结构,语言讲究文采。芭蕉的俳谐纪行,尤其具有深刻的文学意义。
日本的纪行文学,最早发轫于记录旅程顺序、带有“序”的短歌,芭蕉的纪行最初也缘于此种体式。总起来看,芭蕉的纪行文创作,是由以发句(俳句)为主体渐次转向以文章为中心的探索过程。但是,这并不意味着他已经舍弃“歌”的要素,相反,芭蕉的纪行文学始终保持“歌文一体”的风格,洋溢着丰盈的诗意。他明确宣言:诸如“其日降雨,昼转晴,各处生长松树,彼处有一条河流过”般的记述,只能算是旅行记,不是文学纪行,至少这不是自己所要写的纪行。芭蕉评价自己的纪行文章:“似醉者之呓语,梦者之谵言。”他认为,自己并非常人,而是一个狂人,大可不必局限于一草一木、一山一水的具体记述,他写的是“意象的风景”“山馆野亭的苦愁”。他是为了记下一个“在风雅的世界里徘徊”的自己的影子。
元禄三、四年(1690、1691),芭蕉打算在《笈之小文》中贯彻这种理想,但此文半途而废。《笈之小文》所未能表达的风雅的理想图,终于在后来的《奥州小道》里实现了。在这部作品里,出于表达主观意识的需要,芭蕉更改和省略了一些旅途中的客观事实,使得一些章节含有虚构的内容。因此有人说,芭蕉的纪行实际上是借助于纪行文学形式的“私小说”。
芭蕉唯一的日记《嵯峨日记》,也和纪行一样,是当作文学作品写成的,和同时出现的纯粹记述旅途经历、气象天候的《曾良旅行日记》迥然各异。
图片来源:NHK节目《100分de名著·奥州小道》三
《野曝纪行》
芭蕉于贞享元年秋八月离江户,回故乡伊贺上野,为前一年去世的母亲扫墓。其后,游历关西各地,于名古屋出席《冬日》连句诗会,收揽各地新弟子,经甲州返江户。此文当执笔于回到江户处理完杂事之后的一段时间。作品题目还有过《草枕》《芭蕉翁甲子纪行》《野晒纪行》《甲子吟行》等称呼。这些都不是芭蕉本人的命名。
《野曝纪行》是芭蕉最初的一部纪行作品,不免有尚未成型之憾。内容由前后两部分组成,其结构和《奥州小道》类似。
《鹿岛纪行》
贞享四年(1687)秋八月,作者离江东深川之芭蕉庵,到鹿岛赏月。先从住居附近搭便船,沿小名木川溯流而上,穿中川,入船堀川,再沿江户川到行德。接着,步行三十公里,于当天傍晚到达利根川的布佐码头。然后乘夜航船抵鹿岛。翌日,十五日,参拜鹿岛神宫,同时拜访根本寺前住持、禅师佛顶和尚。
《笈之小文》
贞享四年十月至翌年初,芭蕉到关西做了一次探访“歌枕”(和歌所吟咏的名胜古迹)的旅行。十月二十五日离江户,经东海道,在故乡伊贺上野迎来新年。然后,在杜国的陪同下,游览吉野、高野山、和歌浦、奈良、大阪、须磨、明石等地。四月二十三日进入京都。《笈之小文》便是以此次旅行为素材的纪行文。这是一篇未完成稿,作者殁后十五年始刊行问世。
《更科纪行》
贞享五年(1688,九月三十日改元元禄)八月,漂泊于名古屋、岐阜之间的芭蕉,在名古屋的越人及其仆人陪伴下,经木曾路去信州更科观赏中秋明月,之后由长野经碓冰山口返江户。这次旅行既是《笈之小文》之旅的延长,又是一次富于独特风情的览胜。
《奥州小道》
更科之旅结束后,芭蕉于江东深川的芭蕉庵迎来元禄二年的新年。此时已有作一次奥州之旅的打算。三月二十七日,芭蕉在曾良陪同下离开江户,徒步巡游奥羽、北陆各地,八月二十日抵大垣。旅期五个月,行程二千三百五十公里。以此次旅行为素材写成的《奥州小道》,最能反映作者那种“狂人徘徊于风雅之世界”的创作理想,是芭蕉纪行文中的代表,也是古代日本记游文学的巅峰之作。
这部作品目下流行若干版本,简要介绍如下:
1.芭蕉手稿本——此稿本为樱井武次郎和上野洋三两人于1996年11月首次发现,一时震动学界。据考证,此稿本原系作者的定稿,但写作过程中又经反复推敲,多有改动,稿中“贴纸”达七十余处。由此可知,这不是誊抄稿,但因为是作者亲笔所写,最为珍贵。尤其可窥知作者推敲的过程,和下述的曾良本,都是研究芭蕉不可或缺的原始依据。
2.曾良本——此本系芭蕉责成门人曾良据底本所誊抄,并亲自对原文做了认真的补记和订正,推敲之痕达于全卷,是最可信赖的本子。本书译文即采用此本。曾良本当在下面所述的“西村本”出现之后,曾良由芭蕉手里获得。曾良殁后,同《曾良旅行日记》共为其侄河西周德所有。现藏于天理图书馆绵屋文库。
3.柿卫本——这是出现于西村本之前的另一种抄本,假名部分较多,固然有助于阅读,但有不少误写。此本为伊丹市柿卫文库所藏。
4.西村本——芭蕉将推敲和补正过的曾良本,委托书家素龙誊写,完成于元禄七年初夏。封面中《奥州小道》的书名题签,为芭蕉亲笔所书,名为《素龙誉写芭蕉保有本》,随身携带。到达伊贺之后,赠给了兄长半左卫门。芭蕉殁后,遵照遗嘱,送给了蕉门弟子向井去来。现藏于福井县敦贺市西村家。文中有若干误抄之处,因为是作者保留本,至为尊贵。
此外还有各种传抄本,为节约篇幅,恕不一一记述。
《奥州小道》旅程图《嵯峨日记》
奥州之旅结束后,芭蕉于元禄二年秋至元禄四年秋,辗转于故乡伊贺上野、京都、湖南(琵琶湖以南)一带。其间,元禄四年的四月十八日至五月四日,停居于京都郊外嵯峨野去来的别墅落柿舍,此时写的日记称为《嵯峨日记》。然而,虽称日记,但并不是记述每天细小琐事的流水账,而是深含艺术美感的文学作品。
四
下边谈谈芭蕉的俳文。
什么叫俳文?要下个确切的定义,实属不易。其实,在芭蕉所处的元禄时代,在芭蕉本人的头脑里,“俳文”一词也是一个模糊的概念。谁都不知道,什么样的文章算俳文,什么样的文章不算俳文。元禄三年八月,芭蕉致信去来之兄向井元端,请求修正《幻住庵记》草稿,信中说:“实不知何谓俳文,因异于实文,深感遗憾。”在芭蕉看来,自己是俳谐作家,所写文章自然就是俳文了。因为和一般文人的文章不一样,所以感到遗憾。
据堀切实《俳文史研究序说》统计,江户时代,日本出版俳文集一百一十部,其中使用“俳文”一词做书名的只有《俳文选》(1751—1764,三径编)、《桃之俳文集》(1767,桃之编)、《俳文杂篡集》(1788,梅至编)等少数几种。所有关系到芭蕉本人的著作以及芭蕉著述的结集,如《芭蕉庵小文库》、《蕉翁文集》、《本朝文选》(后改为《风俗文选》)、《本朝文鉴》、《芭蕉翁文集》、《蓬莱岛》等,都不使用“芭蕉俳文”之类词语做书名。
芭蕉为何不愿将自己的作品称为俳文呢?这是因为他不满足于贞门谈林俳谐,决心创立蕉风俳谐的缘故。芭蕉把自己的文章叫作“实文”即“诚实的文章”而不称作俳文,正是出于此种想法。
其实,照现在的观点,所谓俳文,就是俳人所写的既有俳谐趣味、又有真实思想意义的文章。这种文章一般结尾处附有一首或数首发句。本书所收芭蕉俳文,均属此例。芭蕉不屑于一味玩弄词藻、夸示技巧的季吟、元邻派的所谓俳文,自称自己的文章为“实文”。同唐代大诗人杜甫一样,芭蕉一生遍历全国,放浪于山水之间,独步古今,俯仰天地,参禅拜佛,访师会友,一路上歌之哭之,咏之叹之。丰富的阅历、深湛的学养、崇高的情操、博大的胸怀,使得他的每一篇文章都有着特殊的艺术感染力。这是一位智者回望人生、检点自我、反省过去、启悟未来的一组组热情的话语。对于只欣赏过芭蕉俳句的人们来说,再读一读芭蕉的俳文,就会发现芭蕉文学的另一半精彩,从而获得一个“完整的芭蕉”。
退隐江户深川以后的芭蕉,不愿乘当世之流风,只想抒写胸中之块垒。于是,中国历代贤哲文人庄子、孔子、李白、杜甫、白居易、苏轼等,一一走进了芭蕉的文学世界。俳文中除了引用本国贤哲诸说之外,中国古典文史歌赋的光芒随处闪现。据日本学者井本农一考证,旅行中的俳文大都是芭蕉应对之作。《奥州小道》中的俳文则全属此类。例如,本书俳文编的《对秋鸭主人宅之佳景》、《夏日杜鹃》、《〈横跨原野〉辞》、《高久宿馆之杜鹃》、《奥州插秧歌》(两种)、《染色石》(九种)、《〈笠岛〉辞》(五种)、《天宥法印追悼文》、《银河序》(六种)、《〈药栏〉辞》、《温泉颂》、《在敦贺》等,一看就是为他人题字而作的(参见日本古典文学全集《松尾芭蕉集》解说)。
俳谐文学本来就是与人对话的文学。其中的发句近似独白,是向主人的问询,有着潜在的等候回应的意思。旅行中以句会友,以文赠人,正是芭蕉意所愿为。抑或,这正是俳谐文学的本色。
图片来源:NHK节目《100分de名著·奥州小道》五
本书根据日本小学馆1999年4月出版的《松尾芭蕉集》第二卷译出。原文有关中日文史典故的说明与注解甚为详密,翻译时考虑我国读者实际情况,对中国方面酌情有所减削,而对日本一方尽量保留。引用典籍的部分全部查对了原始资料,力求做到准确无误。此外,芭蕉的俳文通常于右上角钤有关防印,末尾有署名,即落款,其下盖印,称款印。关防印原属明代朝廷官府公文上的防伪印鉴,是纵长形状的骑缝印,后用于书画之右肩,以表示起点。芭蕉爱用“不耐秋”“杖头钱”等关防印鉴。这些印鉴在译文中都没有一一标出。
在翻译过程中,虽然参考了日本学者现代日语释文,但为保持原文风貌,尽量沿袭原文,采用文白兼备的译语,力求简约、明畅。当然,翻译芭蕉,对于我实为一桩艰难卓绝的文化工程,中译本不足之处在所难免,衷心期待同行师友、专家学者批评指正。
陈德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