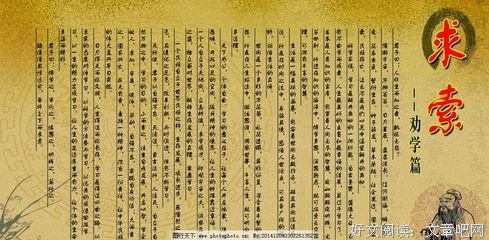
《劝学篇》是一本由(清)张之洞著作,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的平装图书,本书定价:16.00元,页数:148,特精心从网络上整理的一些读者的读后感,希望对大家能有帮助。
●一曰去妄,二曰去苟。
●可怜大厦将倾张老先生苦苦支持。这种中兴名臣看着一个个老古董,其实不知道比那些乱蹦乱跳的高了多少个level。
●眼光毒辣得可怕,博约,体用,绅商,中西风俗,西教之国力基础,早现西方局势与春秋战国类比,王军士师与武备,乃至非弭兵与非攻教,与康梁相比不仅毫不逊色,还多了份冷静持重。
●既不走因循守旧的老路,也不走改旗易帜的邪路——张之洞 #大清药丸#
●“中学(孔孟学说)为体,西学为用”,是民族与世界的统一,也是至理。
●内篇务本以正人心,外篇务通以开风气,忧国忧民,思想丰富,能让光绪和慈禧同时赏识,很厉害。
《劝学篇》读后感(一):国之栋梁
张之洞是晚清的栋梁,那一辈人饱受列强欺凌,一心想要使自己的祖国强大,可惜多种尝试都失败了,张之洞提出的方案还是很好的,不过她好像反对政治改革,而侧重于学习外国的先进技术。难道这就是传说种的阶级局限性?他仅仅是为了保住大清王朝的统治,我感觉不是,他不认为民主可以在我国推行。我觉得他的出发点还是为了国家,民族的。
《劝学篇》读后感(二):读了一遍,感触颇深,要真正了解历史,还是要看当时人的著作
读了这本书,让我对当时的中国有了更深的理解。变法总是易惹来非议,有人支持,有人发对,有人支持变法但认为方法不对。这让我想起王安石变法,就怕最后变成党争,敌人发对的我就支持,敌人支持的我就发对。也有一些地方不知啥意思,如知类第四,本书P29页,有一句:“法、意、日、比为罗马种”,不知这个“日”指哪个国家,请高人指点一下!
读中国近代史,晚请是个饶不开的心结,那里有着太多令人叹息的悲剧——一而再的战败、一而再的割地、一而再的赔款,所谓自通商以来,似乎唯有丧权辱国。对于如此不堪的国是,当时作为晚请一代重臣的张南皮,给重病中的帝国开出了什么药方呢?那就不能不读南皮先生的《劝学篇》。该书当时的印刷量在两百万册,可谓影响巨大。
一、知耻(也就是要了解中国不如其他国家的地方)
一、知惧(也就是要惧怕中国成为那些在当时或灭亡或被瓜分的国家)
一、知变(要知道改变教育,行变法之道)
一、知要(要知道中学致用为要,西学中政治为要)
一、知本(不忘记中国的名教/纲常根本)
其写作目的是希望海内士大夫可以知亡而知强。
内篇包括同心、教忠、明纲、知类、宗经、正权、循序、守约、去毒九篇——其实质还在于维护中国的名教和纲常,这也体现了南皮所倡导的“中学为体,西学为用”,要用西学,必须先学好中学。
外篇包括益智,游学、设学、学制、广译、阅报、变法、变科举,农工商学、兵学、矿学、铁路、会通、非弭兵、非攻教十五篇——个人比较推崇外篇,主要说的是如果改良中国:希望可以开化民智,鼓励士子游学海外(南皮推崇旅日),奖励开办新式学堂,改革学制,多翻译外国著作,鼓励士民多阅读新闻报刊来了解天下事,倡导有节制地变更中国的制度(但是他主张君权而反对民权),改革科举的内容使通过科举的人才能适应时代的要求,奖励工商和农业来振兴中华经济,倡导新式的武备学堂和矿业学校,主张广修铁路,各省要互相交流,不要过多指望在自身军力不足的情况下弭兵,反对攻击孔子学说等等。其中不少建议,在当时有着深远的意义,并被不少人所采纳——比如游学日本。
最后附南皮先生的简介:
张之洞(1837年-1909年),字孝达,号香涛,别号壶公、抱冰,直隶南皮(今河北南皮)人,生于贵筑县(今贵阳市),7岁时随父到兴义府城就读,13岁始回河北原籍应试,考取秀才;15岁时赴顺天府乡试中举人第一名,成“解元”;26岁考取进士第三名,成为“探花”,授翰林院编修。1867-1873年任湖北学政。1874年起任四川学政、山西巡抚。1883年中法战争爆发,因力主抗争任两广总督。1889年7月调任湖广总督,并多次署理两江总督。1906年升任军机大臣。其与曾国藩、李鸿章、左宗棠并称晚清“四大名臣”。
《劝学篇》读后感(四):世人莫忘张之洞
近读张之洞《劝学篇》,颇有感触。
张之洞(1837—1909),字孝达,号香涛、香岩,又号壹公、无竞居士,晚年自号抱冰。直隶南皮(今河北南皮)人。咸丰二年(1852)十八岁中举人,为顺天府解元,同治二年(1863)二十六岁中进士,为该科探花。点庶吉士,历任翰林院编修、湖北学政、四川学政、内阁学士等职,后升任山西巡抚、两广总督、湖广总督、署理两江总督、军机大臣,累官至体仁阁大学士。他一度是清流派健将,后期转化为洋务派的主要代表人物,大力倡导“中学为体,西学为用”,曾创办汉阳铁厂、大冶铁矿、湖北枪炮厂等。他任督抚期间,注重教育和治安,对清末教育和社会发展有很大影响。因为他在中法战争和中日甲午战争期间是主战派健将,一度赢得“天下之望”;而他主持的“湖北新政”的实绩,更使他声名大振,曾被舆论界推重为“朝廷柱石”。1908年11月,以顾命重臣晋太子太保,次年病卒,谥文襄。有《广雅堂集》。他与曾国藩、李鸿章、左宗棠并称为晚清“四大名臣”,而他是最后的殿军。
他饱读诗书,精通以儒家经典为代表的中国古代文化。
他视野开阔,对发展变化的国际大势有广泛了解。
他,绝不是倭仁、徐桐那样的食古不化、顽固守旧者——他吸取了大量的西艺和西政知识,并身体力行,付诸实践;
他,也绝非康有为、梁启超那样的大言无当、没有官场历练的书生——他历任督抚,扬厉中外,颇有政绩和人望。
他,更不是袁世凯那样的野心家、乱世奸雄,尽管清室积重难返、难以为继,他却绝没有“彼可取而代之”的念头。
这一切,都可以从这薄薄的一册《劝学篇》里找到证明。
一本探讨社会改革之书,何以名之为《劝学》?这是因为在他看来,“古来世运之明晦、人才之盛衰,其表在政,其里在学。”而且他发现“西国之强,强以学校,师有定程,弟有适从,授方任能,皆出其中,我宜择善而从也”(《序》)。针对历来科举制度的弊端,他殷切告诫学子,无论治何学问,均应以致用为目的,不可流于浮泛,亦不可专意词章:“一为文人,便无足观。况在今日,不惟不屑,亦不暇矣”(《守约》)。
他深知国家民族危机深重,原因出在内部:“吾恐中国之祸,不在四海之外,而在九周之内矣。”(《序》)危机面前,他坚决反对不切实际的和平幻想,指出“苟欲弭兵,必先练兵”(《非弭兵》)。主张“中学为体,西学为用”,“中学为内学,西学为外学;中学治身心,西学应世事,不必尽索之于经文,而必无悖于经义”(《会通》)。“中学考古非要,致用为要;西学西艺非要,西政为要”(《序》)。他反对顽固派的“因循守旧”、“不知通”;也反对维新派的“菲薄名教”、“不知本”,指出“旧者因噎而食废,新者岐多而羊亡”(《序》)。他超越了早期洋务派“师夷长技以制夷”的局限,不再把西学仅限于“西艺”,把西学的范围扩展到“学校、地理、度支、赋税、武备、律例、劝工、通商”以及交通、传媒等各个方面,除了议会选举制度以外,几乎要“全盘西化”了。
以传统的标准评价,他无愧 于忠君爱国的贤臣良相。
就顺应时势、与时俱进而言,他也尽了极大的努力。
他清楚地认识到,不能再走僵化保守的老路;但他也很明确,必须“明纲”、“宗经”,决不走动摇纲常、改旗易帜的“邪路”。这成了他的底线。
但是,他最终没有能挽狂澜于既倒。他死后两年,在他长期经营的重镇武昌,由他训练的新军下层官兵率先发难,引爆了辛亥革命,推翻了满清王朝。
改旗易帜的路是正是邪,姑且不论,但却实实在在地发生了。
是偶然,也是必然;是意外,好像也是天意。
不知他临终之前对此是否有强烈的预感。好在他先走了一步,避免了出席满清皇室逊位的难堪仪式。否则,不知他将怎样应对,发出何等感慨!
“才自清明志自高,生逢末世运偏消”,是《红楼梦》里咏叹贾探春的诗句。用于形容张之洞,愚以为也颇贴切。
看来,历史的局限,有时要突破,也很难。
近来见到有的论者说:如果是张之洞为代表的改良派当时能执中国牛耳,中国极有可能实现君主立宪,后来的许多混乱和灾难就都可以避免了,中国发展到现在应该是很先进、很强大的了。
也许是吧?可惜,历史不容假设,没有“如果”。
但无论怎样,张之洞一干人为探索中国的前进之路,曾经付出过极大的努力,也给后人留下了有价值的经验和教训,并且为中国的近代工业打下了最初的基础,人们不该忘记他们。
而这本当时印数达200万册、曾风靡一时的《劝学篇》呢?尽管其中不少的论点论据都已过时,但它所开启的关于文化的内—外、本—末、体—用、常—变、动—静之辨,关于文化的民族性保持与世界性获得二者关系的探求,都已提出后人无法回避的题目,促人深思。从这个意义上,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在戊戌变法110周年(2008)之际重新出版此书,显然不无意义。
2012年11月25日读后记
《劝学篇》读后感(五):戏说张之洞《劝学篇》
晚上看了一遍张之洞《劝学篇》的内篇。猜想《劝学篇》就好像是1900年版的“中国人,你要自信”,只不过在今日这是一栏电视综艺节目,两个甲子之前的《劝学篇》则基本上是用整齐的四六文写成。
第一篇“同心”:所谓“同心”,张之洞言“保国”、“保教”、“保种”三者“合为一心”,其中又以“保国”为根本。张之洞列举了世界各民族宗教与国家实力的关系(虽然因为时代局限而错误频出),总结出“故国不威则教不循,国不盛则种不尊”的丛林法则:宗教与意识形态的延续与传播都依赖着国家实力作为支撑。与同时代的康有为、谭嗣同等人一样,张之洞力求将“儒家”转化为辅助中国社会整合的意识形态,(“儒教”),与世界各宗教形成对立的同时,增强民族的文化认同,由此实现救国保种的现实目标。
第二篇“教忠”,很明显就是要求臣民在“时世艰虞”之际仍然效忠于满清统治。张之洞列绝了秦汉以来历代的税收制度,为了凸显出大清自康乾以后就不增田税的“仁政”;在随后罗列出的“仁政”的十五个方面中,大清对臣民的恩惠均是前所未有。但稍有经济观念的现代读者读此篇,不禁疑问:又不加税,又整天动用国家力量大兴土木,清王朝中央政府的财政收入究竟从哪里来啊?
第三篇“明纲”可能是现代读者读到后会义愤填膺的一篇:张之洞不仅反复强调“三纲五常”是“天不变,道亦不变”的永恒真理,更用其批驳民权:“故知君臣之纲,则民权之说不可行也;知父子之纲,则父子同最免丧废祀之说不可行也;知夫妇之纲,则男女平权之说不可行也。”但张之洞还需要做出解释的一个现象是:为什么西方国家没有中华的教化也能够社会稳定繁荣?张给出的解释是:“西国故有君臣、父子、男女之伦也”!
第四篇“知类”,强调种族差异,呼吁大清的臣民不要改换国籍。
第五篇“宗经”,批评“道光以来,学人喜以纬书佛书讲经学;光绪以来,学人尤喜治周秦诸子”,强调必须用六经中的道德标准准评判子部典籍,突显“经”的权威性。
第六篇“正权”,接上文继续批驳民权之说,但也试图寻求折衷:一方面张之洞实际上默认了倡导民权者的诉求:变法设议院,兴办工商、学堂等,另一方面坚持强调:所有这些行动都必须从上而下地展开,民间私自进行必将陷入困境。最终,张之洞大喊:“民权之说,无一益而有百害。”
第七篇“循序”,声明学习西学必先坚实中学。
第八篇“守约”,不是“遵守契约”之意,其中的“约”是“简约”之“约”,与“博”相对;自墨子以降,历来对于儒家都有“繁而无用、劳而无功”的批评,因此“守约”是要求研习经学,需要“先博后约”,“致广大而尽精微”,兼顾知识广博与义理简约。
第九篇“去毒”就是要禁鸦片,张之洞提倡广泛建立学堂,培养民众的求知心,以消除吸食上瘾。真富有理想主义!
在21世纪读《劝学篇》,张之洞改造儒学的种种努力难免显得可笑、可悲、甚至可憎,但我们总不能超越历史背景评价人物。若与同时代的一大群经学家相比,张之洞绝对是思想开明者。在儒学的意识形态中长大,在科举中摸爬滚打进入仕途的人,有多少的希望能够不带有偏见地客观评价中学与西学?即便今日,这样的论争中不仍然充斥着民族情感或者盲目崇拜?
我想读历史的趣味之一,正在于反思历史参照下的荒诞,并且与此同时,警醒自己始终谦虚谨慎:我们何以能自信地宣称,百二十年后,当我们的后代考察2020年人们的观念时,我们就一定会比张之洞高明?
美国汉学家列文森在《儒教中国及其现代命运》一书中进行了一个有趣的区分:“儒家的历史”与“历史的儒家”;前者发生在儒家控制下的中国,所有历史都在儒家的标准下被衡量,后者则产生于儒家失去权威后的中国,儒家经典也成为了历史的遗迹。
即便在“儒家的历史”的崩溃几乎已经不可扭转之际,张之洞却更要坚持一种想象中的“原教旨”主义的儒学。(注意,先秦典籍中从未出现过“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这完全是汉儒及以后的解释)当历史上的各种文明将要崩溃之际,都会短暂地出现一种极端的反抗:试图通过放大自身与他者的对立,突出妄自尊大的民族情绪,仿佛是恒星最后的爆炸。列文森:“西学越是作为生活和权力的实际工具被接受,儒学便越是失去其‘体’的地位。这个在没有对手的条件下被视为当然真理的儒学,现在已成为一种历史的遗产,一种不向改变了中国生活基础的西方对手投降的浪漫主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