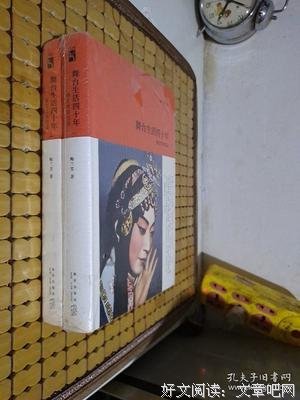
《舞台生活四十年:梅兰芳回忆录》是一本由梅兰芳著作,新星出版社出版的精装图书,本书定价:98.00元,页数:888,特精心从网络上整理的一些读者的读后感,希望对大家能有帮助。
《舞台生活四十年:梅兰芳回忆录》读后感(一):梅兰芳舞台生活的历史还原与细节呈现
梅兰芳是身为我国广大群众热爱的、并享有极高的国际声誉的表演艺术大师,被视为中国一个时代戏剧艺术的杰出代表,为中国京剧艺术留下了空前绝后的巨大精神财富,代表了中国戏剧艺术发展的最高峰。
《舞台生活四十年》是梅兰芳个人艺术生涯的回忆录,也是一部有明确和系统戏曲发展和革新思想指导的艺术实践总结之作。梅兰芳的戏曲理论和主张,来自于舞台实践和革新,也来自于他自身文化、理论的修为和所具有的宏阔的世界戏剧眼光。中国戏曲表演和理论体系具有浓郁的实践色彩,但这种理论总结和提升往往是由学者和理论家们去完成的。而梅兰芳的意义和不俗,正在于他也是中国戏曲表演体系理论的构建者,实践与理论两者的联系和区别,在梅兰芳这里得到很好的体现,这从《舞台生活四十年》亦可以管窥。
《舞台生活四十年:梅兰芳回忆录》读后感(二):绝代芳华背后的事
之前不了解戏剧理论的三大体系,也不了解梅兰芳,连《梅兰芳》这部电影都没看过(可惜的是,后来看再看却也没有带来太多触动了)因为一门选修课的原因接触到梅先生,也进而对梅派艺术,甚至是整个戏曲表演。在此过程中阅读了这本书,虽然略显仓促,但也有许多收获。
这是我读到的第二本访谈对话形式的书,第一本是《我在故宫修文物》。与《故宫》相比,《舞台生活四十年》更有韵味,与叙述者一样,堪称经典。这本书娓娓道来,充满画面感。我似乎看到梅先生唱过堂会,在袅袅的茶香中同执笔者围炉夜话,也似乎看得到小吃店里的梅先生和执笔者亲切闲谈。一般我读书,总是会在手边摊着读书笔记,有些引发思索、或是文法极妙的句子,我总是拿笔记下来;即便是条件不允许,我也是会拿着手机拍下来的。但这本书,或许是因为于我这个外行而言信息量太大,又或者是因为因为叙述太好,竟然让我生出一种恨不能整本书都抄下来作书摘的想法,提起笔又无从下手。大约是因为这本书着实引人入胜,于是放弃了写书摘,而是暗地里觉得,若是再有闲暇,定是要再好好读一读的。
读这本书的时间着实是有写仓促的,以至于我是从梅先生正式叙述,即第一章开始看的,又把下部的书跳了大部分,仅仅来得及挑上最感兴趣的,讲《玉堂春》和《霸王别姬》的来看,其他章节就暂时只能大致翻过一遍。
但即便是这样囫囵吞枣地阅读,我还是有很大的收获,够我暗自里满意一番。大致如下吧:
一是对于民国时期的戏曲创新有了许多新的了解。民国时期,诸多外来元素进入中国,譬如话剧和歌舞,而即便如此,京戏依旧未亡,反而是达到一个新的艺术高度,很重要的原因就在于创新。其中最重要的两个方面,就是改戏创戏和塑造新的行当。改戏,包括将念白、动作、场次、角色进行调整,以达到更好的艺术效果。而创戏,就比如说根据古典小说中的故事改成戏本子再唱出来,比如《黛玉葬花》就被梅先生带到了五舞台上;再比如说加了许多时装新戏,把当时时代的题材也用京剧的方式表现出来,比如说《一缕麻》。
而塑造新的行当,虽然也是改戏创戏的一种,但其影响力实在太大,对于现在的戏曲界也太过重要,因此必须单独拿出来一看。
在传统戏曲之中,青衣和花旦可谓是泾渭分明。青衣注重唱功,一般都着青色或黑色的服装,又因为少动作,素来有“抱着肚子唱”的玩笑话;而花旦注重念白和做工,尤其是眼神和动作。但自王瑶卿先生开始,到四大名旦,事实上是开创了一个新的行当,叫做”花衫“。花衫有青衣的大段唱词,有花旦的念白,甚至还可能有刀马旦的武戏。譬如说《贵妃醉酒》里的杨玉环、《霸王别姬》里的虞姬,都属于花衫于一体,她们都集唱念做打于一身,成为舞台上绝美的人物。正式这样的创新,使得京戏,在保持传统的同时,也不断跟着时代的发展在变化。
二是感慨于这些前辈们对戏的认真和严谨。古代文学史上,有贾岛路上不忘“推敲”的典故,而民国的戏曲界,也不乏这样的例子。或许这不算特殊,而是每行每业,若是想要做出些成就,就必须得深入思考到这些细节中去。《游园惊梦》中的“迆逗的彩云偏”,其中的“迆”是读“tuo”,还是读“yi”,梅先生就曾经和其他名角大家一起斟酌研究过很久,不仅仅是对于这个字本身,也还涉及到地域和语言的演变,他们最终定下来这个字读“yi”。也正是他们自己的功课做得十分到位。当有观众在报刊上发文质疑读音时,他们的回应就快速而有力。
在上述所有的艺术上成就外,梅先生蓄须明智等爱国如家的行为也令人充满敬意。若是没有这样的风骨,他也不会是这个流传千古的梅先生。
可惜,即便现在还有梅派传人,却很少有人能够还原出梅先生的神韵和声韵,我们只能根据少有的,黑白资料片窥见一二。但,谁知道未来会不会再又一个如梅先生的人,出现在中国这片大地上,又是一抹芳华!
此书一定要多读几遍才好啊
《舞台生活四十年:梅兰芳回忆录》读后感(三):千古流芳的戏曲大师
梅兰芳是蜚声国内外的著名京剧表演艺术家,为我国广大戏曲爱好者的喜爱。他在京剧表演上取得的成就,被誉为:“中国一个时代戏剧艺术的杰出代表” ;被视为“代表了中国戏剧艺术发展的最高峰”。 他博采众家之长,自成一家,创立了京剧梅派艺术。 梅兰芳,1894年生人,8岁开始学戏,10岁就登上舞台,一生都是与舞台有不解之缘。梅兰芳的成功是他平时勤学苦练的结果,他对自己奋斗一生的京剧舞台艺术特别钟爱,始终本着精益求精的原则。在童年初学戏的时候,每天早上五点钟就起来,到空旷的地方遛弯儿吊嗓,回来还要再练身段、学唱腔,到了晚上还要背戏本,虽然有着出身京剧世家的影响,经过多少年刻苦努力,终成一代京剧艺术大师。 在上世纪50年代初,学者黄裳请梅兰芳写自传体回忆录。梅兰芳在不影响演出的空隙时间,每天与许姬传谈话2小时,许姬传记下就如此宝贵的回忆录,在《文汇报》上刊登。相继由平明出版社出版了第一集和第二集,书名为《梅兰芳和舞台生活四十年》。第一集出版后,在一年内加印了三次,成为非常畅销的书。 梅兰芳的这本自传,为中国的戏剧保留下近代戏曲发展的许多史实,可以供今后戏曲工作者的参考。所以说,在这本梅兰芳的自传中,都是真实再现中国戏曲表演的历史发展情况,表现出梅兰芳对自己的舞台生活艺术一丝不苟的追求。 梅兰芳的京剧表演艺术是以唯美主义和理想主义作为追求,给人以美的享受。他作为公认的京剧艺术大师,他的为人是为世人所称道的,他平时为人谦和、好学,即使在他成名成家,还是平易近人,没有大师的架子。而且,他在面对国家危难时期始终以民族大义为重、坚持自己的民族气节。在抗日战争时期蓄须明志,数年不为日本人演出,他的可贵品质令人敬仰。 《舞台生活四十年》这部回忆录,时间跨度很长,记录的人和事也很多。是一部内容极为丰富、历史资料非常详实的巨作,也是我国戏曲艺术家的回忆录中篇章最长、影响力最大的一部著作。这部回忆录真实地详细地记录了梅兰芳从小学艺,到成名成家之后的戏剧艺术人生的追求,以及艰辛历程和自身发展的轨迹。再现出中国半个多世纪以来我国京剧舞台的发展和风云变幻。 梅兰芳创造的舞台艺术形象,千姿百态,人物心理刻画的非常细腻,细节处理上,惟妙惟肖,如贵妃醉酒等的舞台形象千娇百媚,独创了了不起的梅派京剧。梅兰芳的舞台艺术的特点是以“美”为标准的。在舞台上表演了一个个非常优美动人的形象。给观众以美为最高的追求。所以,梅兰芳的《舞台生活四十年》书中提供了丰富的戏剧史料,对于如何塑造美的戏曲形象,提供了极为宝贵的经验,深刻地总结了梅兰芳的表演艺术经验,是京剧舞台艺术的结晶。梅兰芳在舞台上创造的形象美给我们留下了非常宝贵的财富,他是美的化身,是对中国戏曲艺术有巨大贡献的人,所以说,《梅兰芳回忆录》确实是一本传世之作。 梅兰芳还是一位具有艺术气质的人,他在其他艺术门径上也非常的有名。他工书法善国画。其书法秀雅隽永,字如其人,他的画更是出名,具有中国传统文人画的风采,每次演出的道具,扇子的扇面都是出自其本人之手。更主要的是梅兰芳把各种的现代艺术理念纳入在戏曲表演之中,对京剧事业做出了卓越的贡献。 梅兰芳还将这个的京剧艺术带到世界,从1930年开始,梅兰芳开始赴美巡回演出,先后在西雅图、芝加哥、华盛顿、纽约、旧金山、洛杉矶、圣地亚哥、檀香山等地,并且使当地的民众了解了中国的戏剧艺术,梅兰芳的表演艺术使京剧第一次登在西方人的舞台上,使外国人真正了解了这一戏剧艺术形式。 梅兰芳的这本记述个人艺术生涯的回忆录,是对我国戏曲发展和革新起到艺术指导的作用,是梅兰芳表演艺术实践的总结。我们通过艺术家的自叙,了解了他的人生历程和艺术征程。梅兰芳的戏曲舞台上塑造美的舞台形象,将千古流芳。
《舞台生活四十年:梅兰芳回忆录》读后感(四):绝代芳华背后的中国艺术改革发展
这本书详细介绍了梅兰芳的经历、社会时代变迁和他为京剧发展作出的改革变化,同时也设计了许许多多当代著名的人物。若想了解现代京剧的形成和发展、梅派艺术的形成等,是最好不过的选择。
梅兰芳对京剧的改革是建立在他对文化深刻的认知、主观上不停的学习和辩证的思维之上。梅兰芳改革的基础在于他对于各种剧种、文化和传统艺术及其熟练的掌握,和对于事物之间关联的正确建立。在京剧界尚禁止一个人学多个行当,甚至不允许学花旦的人去学青衣的时代,梅兰芳——基于一定的世家原因——自小就追随各位大师同时学习青衣、花旦、刀马旦,及昆曲、昆腔等等,甚至在年少成名后开始了解和学习其他行当。在其他演员只能掌握唱念做打其一时,他就利用小时后的时间掌握了大部分动作技巧,和数量众多的成套剧目。如同应试教育的刷题和背诵一样,他的童子功为后期对所有动作的理解和融会贯通打下了夯实的基础。另外,其他学徒专工一门并勤于练习时,他由于生计所迫十三岁便登台表演。那时的他已经在一次次登台中意识到实地表演的经验对于他掌握和体悟剧目的重要性。在候场的时候,他养成了观察他人演出的习惯,这个习惯一直持续到他去世,成为了梅派艺术学习过程中的重要原则。无论何种剧目、哪位演员表演,梅兰芳都能从他们的经验中有所学习和感悟,“透过现象看本质”便是如此。
在梅十七八岁开始到上海表演后,他的善于纳谏和对艺术的尊重与投入让他结识了一批大师,后者为他打下戏子难有的文化底蕴。他与梅雨田、齐如山、孙十爷等人的交往,往往始于他们在梅谢幕后提出的尖锐而有角度的建议。梅本就是常常与观众交流意见的人,因而看到他们如此有批判性的建议,往往邀请他们当面指导,没有丝毫的架子。正是与这些人常年不断的交流,才帮助梅兰芳通过一次次改革逐步完善京剧、完成梅派艺术;同时梅兰芳在国外的交流演出,往往也颇受这一批人指导。现代京剧和梅派美学的根基就基于梅兰芳与他的“智库”们。
梅的辩证体现在他的改革原则中。他从不是为了改革而故作姿态,没有拘泥于传统,也无一蹴而就。他的改革多半以京剧和其他戏曲为根基(这就是他过去博学的重要体现),同时顺应社会元素和意识形态变化(也就是对观众的重视),利用一切传统文艺进行革新。他的改革方式是不断的尝试,不被理论框住,而是从艺术效果和观众反响中进行反思和调整。新的剧本多基于其他戏种的剧本、古籍中的故事/剧目、社会事件和宗教文化故事;服装化妆上的改革有借鉴于古书画和他自身国画的能力;舞台设计和灯光来自于社会变革带来的剧场变化;唱腔身段舞蹈根据人物性格调整塑造;伴奏根据唱腔旋律和韵律进行协调,加入新的唱腔、唱念搭配等等。每一个元素都影响着其他方面的改革,这种对艺术的全局观正是他辩证思维的体现。
京剧是一种综合性艺术,而非单一的表演艺术。在基于昆曲的改革中,京剧逐渐形成了“歌、舞、乐”三位一体的“歌舞剧”形式,形成了独特的“歌舞并重、唱作合一”的梅派特色。为了丰富舞台人物特点、塑造角色性格,梅兰芳打破行当之间的壁垒,让演员从单一的“技巧家”变成需要能够融合、平衡和整合各项功夫的艺术家。他将武打、唱腔和表演的能力结合在一起,形成“青衣、花旦、刀马旦”三位一体的新的表演形式“花衫”。虽然大众只知青衣花旦,但是大部分人所熟知的剧目,如《贵妃醉酒》《霸王别姬》《宇宙锋》等都是花衫作品,而梅派本身代表的“梅八出”也几乎都是花衫。
梅兰芳是一位京剧艺术家、美学家,也是中国文化的传播者。他三次赴日本演出、一次美国之行、另有两次苏联表演和欧洲游学。梅兰芳所到之处无不掀起一股京剧热,虽然隔着文化壁垒,但“东方文化”的绝妙也就在京剧这样一门综合性艺术中才有深刻体现。他与当代多位世界级的艺术家、戏剧家都是好友,深入讨论、学习彼此的文化和艺术思想。在东方被西方文化、政治压迫的情况下,梅兰芳艺术每每让外国人赞叹并反思他们艺术的局限性。梅兰芳艺术甚至影响到了日本歌舞伎发展和“新舞蹈运动”的思路。在演出的过程中,梅更担任着外交的作用。他在日本第三次演出和美国的演出皆在两国建交之前,但是他的访问过后,这几国的文化团体都和中国方面有所往来,进行跨国演出。艺术受社会进步带动,也能够侧面推动时代发展,这是梅之所以能成为中国文化标志性的人物。
关于梅兰芳和京剧,可提及的东西无穷尽。我想引用中国戏曲学院表演系主任王绍军教授的一句话梅兰芳之所以能够成为中国传统文化的符号性、标志性 、象征性的人物,固然跟大家谈的方方面面的浑然天成或者有意追求密不可分,更重 要的是梅兰芳不但是一位传统戏曲优秀的继承者, 一个出色的改革者,更是一位具有前沿意识、具有时尚精神的中国文化和中国戏曲艺术的传播者”。正是这位独特的“时代英雄”构造了中国美学、戏曲和京剧文化。
《舞台生活四十年:梅兰芳回忆录》读后感(五):梅党的意义
《说说梅党》一文分剖详密,作者可谓深知民国历史与梨园典故,我读了很长见识。网络上文章转载大都不注明来源,这是无德的行为。我花了点时间查了查,此文应该来自“民为贵四世”的微博。民国名角大都有“党”,此“党”非政党,而是一种名人雅士自然结成的捧角儿的圈子,源头可上溯自清朝中晚期盛行的对京剧的狂热以及兴起的捧角儿的风气。
“捧角儿的风气虽有改变,但势头未减。一些文人仕宦贤达名流对所喜爱之好角儿给与热捧,既为消遣又算雅好。其中志同道合者渐进形成圈子,由小及大而成迷党。当时坊间对于捧角儿迷党,谑称叫法流行一时。比如“痰迷”(捧谭鑫培者)、“黄病”(捧黄润甫者)、“瑶痴”(捧王瑶卿者)、“羊迷”(捧杨小楼者)、“梅毒”(迷梅至深者。“梅毒”不一定可称之“梅党”)等。“梅党”即是在此时开始形成。” 自《齐如山回忆录》以及齐如山的著作在大陆出版,再经过陈凯歌导演的《梅兰芳》电影的推广,造成一种广泛的误解,而《说说梅党》对此予以辩驳: “翻检近些年的书刊、文章及影视作品,凡言及早期梅兰芳必提到齐如山,认为齐先生对梅先生的帮助影响最大,由此或把齐如山视为梅党领袖。各路方家持论所据材料多集于两点:1、齐先生给梅先生编了几十出戏。2、齐先生给梅先生说戏排身段等。笔者以为上述观点与所据材料均不够准确。首先,即便此两点成立,亦不能得出齐先生对梅先生帮助影响最大并系梅党领袖之结论。其次,上述两点多出自齐如山个人著述,属齐先生“自说”,不能作为确论。 梅党领袖大致应符合以下条件:1、系梅党的发起人,或是具有较高威望的主要决策人。2、梅先生本人诚心认可,其他梅党成员予以承认。3、对梅先生的事业有较大襄助,且始终如一。按此三条衡量,齐先生大体仅符合第三条,且并未始终如一。笔者以为,梅党之领袖当为冯幼伟先生。” 这个论断有梅先生自己的话作为坚强的证据。《舞台生活四十年》里,梅先生谈起自己的朋友,最推重的是冯耿光冯六爷,他的原话是:“我跟冯先生认识得最早,在我十四岁那年,就遇见了他。他是一个热诚爽朗的人,尤其对我的帮助,是尽了他最大的努力的。他不断教育我、督促我、鼓励我、支持我,直到今天还是这样,可以说是四十馀年如一日。所以我在一生的事业中,受他的影响很大,得他的帮助也最多。这大概是认识我的朋友,大家都知道的。” 这话分量是很重的, 据“民为贵四世”的说法:冯幼伟不仅是梅党的发起人,直接参与主持梅兰芳的诸多重大事项,而且付出了极大的人财物力。所谓梅先生早期重大事项有:从朱小芬之“云和堂”脱籍赎身,进喜连成借台习戏,十七岁搭班唱戏,与前室王明华成婚,向王瑶卿等老角儿学戏,向名家学习书画,结识名流,首次赴沪,排演新戏,首次赴日,自己挑班儿,当选“四大名旦”头名,赴美演出,访问苏联,定居上海。。。。。。这些事项均由冯幼伟先生主持决策、给与襄助、提供资金。冯先生煤渣胡同及东四九条的宅院亦常让梅先生排戏及拍摄电影使用。梅兰芳自十四岁结识冯幼伟后,其生活、事业等一应诸事,尤其是梅兰芳事业的几个重要阶段,均由冯六爷把持。梅兰芳对冯幼伟格外信任和倚重,不论搭班唱戏还是生活用度结交朋友等,均听从冯六爷的意见。梅先生在二十多岁时曾说:“他人爱我而不知我,知我者其冯侯乎。” 包括梅先生与福芝芳的第二次婚姻,是冯先生的撮合,娶孟小冬为侧室,也经过冯先生的同意,最后梅先生留福舍孟,也是冯的一句话”孟心高气傲,是人服侍;福芝芳随和大方,是服侍人“而一锤定音。梅先生是个唱戏的天才,他会的是好好做人,好好唱戏,至于其他,就得靠欣赏他的艺术的一帮朋友们--“梅党”出谋划策,出钱出力,百般成全。里面,冯先生最有力量,也最花心思。齐如山先生在法国研究过现代戏剧,回国后帮助梅先生二十年,写剧本、排戏等等,贡献当然很大,这点梅先生多次肯定,齐先生在各种著作里更是念念不忘。但论明面的恩义与支持,论内心的尊敬与信服,齐如山是无法和耿六爷相提并论的。耿先生为了梅的出国访问,自己不惜卖房卖地,过后一句不提,这种风度,也是齐如山万万做不到的。 冯幼伟名耿光,广东人,光绪朝日本士官学校留学生,与蔡松坡、蒋百里等为同学。归国后任禁卫军标统,宣统元年(1909)任军咨府厅长。民国后历任陆军部骑兵司长、总统府顾问、中国银行总裁。这个资历,权势地位,都有。梅党除冯六爷与齐如山之外,核心成员有留日学生兼遗少李释勘、吴震修、许伯明、舒石父;出身译学馆的郭民原、张孟嘉、张庾楼、言简斋、黄秋岳。另外樊樊山、罗瘿公、易实甫、姚茫父、陈三立、陈师曾、张謇、齐白石、张大千、吴湖帆、叶恭绰等均与梅先生有较密切的交往。 侯磊、 杨津涛的《人间不见梅葆玖 梅家再无后来人》讲梅兰芳与梅派艺术讲得极好,但其中说梅党是“艺人与旧文人结盟的先河。艺人向文人学文化,文人向艺人借平台”,我以为不太确实,因为他们拿清末民初的梅党与后来的胡适、鲁迅去比较。当时初起的梅党中坚,或者留日,或者出身译学馆,绝不可说是旧文人。准确说他们是学问亦新亦旧,多世家子弟,旧学有根基,又多留学经历,通晓世界情形。他们文化精英的色彩很浓厚。他们或者在军界有重要影响,或者在银行与实业上,或者在艺术界占据重要位置。他们都热爱祖国文化,热爱京剧艺术,也都认为与接受京剧必须改良跟上世界潮流。他们极欣赏梅兰芳的人格与艺术,以为其为中国文化艺术的中心人物。故不惜精力与代价,帮助扶持其成长。或者在经济上大力支持,或者在学识上予以指点,或者在艺术上加以拓展。梅派能亦新亦旧,传承中发展,移步不换形;能形成中正典雅,博采众长的艺术风格;成为三大戏剧体系之一,这和梅党是分不开的。梅兰芳与梅党,是戏曲艺术家与文化、经济界部分精英的联盟,没有文化的滋养、经济上的支持,梅派是不足以获得如此巨大的成功的。 当然是梅兰芳先生的人格与艺术,吸引了梅党;但另一方面,也是有了这些学养、艺术鉴赏力极高的梅党,梅兰芳才可能广泛吸收中国文化的精华,拥有世界的眼光,产生文化的追求,通过自己的不懈的努力,没有辜负梅党的期望,不但极大地推进、改进和丰富了京剧艺术,而且为中国文化自立民族之林做出了自己的贡献。
梅党看着与当下粉丝团似乎很类似,但其成员学养、地位、品味之高尚,立意、追求的纯粹,寄托的深远,是现在的粉丝团不能梦想的。京剧是中国戏曲文化的集大成者,梅兰芳是京剧的最重要的艺术家,扶持梅兰芳,不仅仅是扶持与关爱他这个人,而是扶持以他为代表的我国文化的极重要的部分。这才是梅党存在的意义与价值。
《舞台生活四十年:梅兰芳回忆录》读后感(六):梅兰芳时代与时代中的梅兰芳(靳飞)
(一)从初出茅庐的黄裳谈起
1936年秋,天津南开中学邀请已经完成两次访日及访美、访苏公演而得驰誉国际的京剧艺术家梅兰芳到校演讲。南开的主持者是著名的教育家张伯苓和张彭春兄弟。张彭春又是戏剧家,曾经担任梅兰芳访问美苏时的艺术指导,且是其中不可或缺的重要参与者。所以,梅兰芳势必是要给南开这个面子的。
演讲当日,正当张伯苓校长亲自陪同梅兰芳走上讲台之际,讲台的幕布后面,突然闪出一个在那里埋伏了许久的少年,冒冒失失撞上前要求梅兰芳签名。梅兰芳原本也没有耍大牌的习惯,他接过少年递来的本子,用清脆的京白客气地问:“您是让我竖写呢,还是横着写?”
这一天,南开中学不知有多少师生会羡慕这个名叫容鼎昌的少年。这些师生里,可能会有黄宗江、周汝昌,他们与容鼎昌是同窗;可能还会有何其芳、张中行、毕奂午与巴金的二哥李尧林,他们都是南开中学同一时期的青年教师。这些后来很出名的人物,多成了梅兰芳的忠实观众,有的还成为梅派艺术的研究家,但与梅兰芳渊源最深的,仍然要说是容鼎昌——他改以黄裳为笔名行世,是现当代名头颇响的剧评家、散文家和藏书家。
距梅兰芳南开演讲约有十年,不到三十岁的黄裳初出茅庐,担任《文汇报》的编辑,同时以剧评家的面目写作“旧戏新谈”专栏,他再次以一种奇特的方式在梅兰芳的视野里闪了出来。黄裳于1947年1月在其专栏里发表了他的名篇《饯梅兰芳》。这次闪出来的黄裳,却没有了十年前的谦恭,而是以敢于不留情面地批评梅兰芳等名角儿,得以名噪一时。舒展《梅兰芳的“粉丝”》文就说黄裳:
他的专栏《旧戏新谈》,各大名伶,一一点评,戏里戏外,一天一篇,雅俗共赏,嬉笑怒骂,借古讽今。尤其在知识界,一报到手,先睹为快。1948年由开明集结五十多篇出版,在当时国立剧专的同学们中,黄裳之大名不胫而走。
黄裳在出版《旧戏新谈》之前,还出版过散文集《锦帆集》,但影响不大。可以说,黄裳之成名系由这册《旧戏新谈》,而《旧戏新谈》的点睛之笔,正是这篇《饯梅兰芳》。
黄裳在文章中毫不客气地说道:
我想到梅浣华五十余年的舞衫歌扇的生涯,垂老还在舞台上作戏娱人。然而他的嗓音的确大大不如从前了,全失了低回婉转的控制自由,时时有竭蹶的处所。
他更甚一步地咄咄逼人说:
时至今日,梅恐怕又将有留须的必要了,为了那些外来的殷勤,还有一个理由,嗓子的确不行了,为了保持过去的光荣,梅有理由从此绝迹歌坛。
坦诚地讲,黄裳所说的未尝不是事实,只是文字上过于夸张渲染而已。众所周知,梅兰芳在抗战期间蓄须明志,辍演多年;他生于清光绪二十年甲午九月二十四日,即1894年10月22日,到抗战胜利时,已年逾半百之龄的梅兰芳于1945年10月10日重新登台,恢复演出。这时的梅兰芳,理所当然是难与先前相比照的。
此外还有一个情况,极有可能就是发生在黄裳观看梅氏演出而大发议论之日,梅兰芳恰逢突如其来的变故。1947年1月5日,他最为心爱的弟子李世芳因飞机失事而罹难。梅兰芳在《舞台生活四十年》里记述说:
回想四年前在上海中国大戏院,李世芳陪着我唱青蛇,这还是我演《金山寺》带《断桥》的初次尝试。他并不是我们剧团的人,临时约他参加帮忙,前后演了几场,我都觉得满意。我记得1947年1月2日的晚上,我们演完了最后一场,他在5日早晨坐了飞机回北京。飞到青岛,半路上飞机出了事,把他牺牲在里面,我们师生从此就永别了。我那天正在后台扮戏,听到这个传说,差一点要晕过去。旁边有人安慰我说,“这消息不一定可靠”。我还希望这不是事实呢。谁知道第二天我接到飞机场的电话,竟证实了这件惨事。我大哭了几场,从此就不愿意再演这两出戏。
年仅二十六岁的李世芳,夙有“小梅兰芳”之称,位居“四小名旦”之首,是公认的梅兰芳艺术的继承者。李世芳之死,对于梅兰芳的打击是相当沉重的。而黄裳的那篇不顾实际情况,并且不合时宜的批评文章,客观上不能不说是对于梅兰芳的伤害。黄裳却始终不肯认这笔账,晚年犹是嘴硬,写文章为自己辩护说:
我写过不少评梅戏的文章,大抵喜欢的多说一点,不大喜欢的少说一些,但从未放过冷枪。对他早年的反串戏,我也并不认为是他的代表作,未能一律吹捧。就在《饯梅兰芳》一文中,也指出了他的一些缺点,如笑场,未曾恢复盛年原样的嗓音、身段等。我觉得这是剧评作者的权利也是义务。
黄裳不肯服软的另一个原因,是因为他的这番自辩,针对的根本就不是梅兰芳,而是他的老上司、《文汇报》重量级的元老柯灵。
同样是已到风烛残年的柯灵,于1993年3月21日写作了《想起梅兰芳》。柯灵在文中重提黄裳的那篇《饯梅兰芳》,直截了当批评说:
这篇名文,清楚地表现出作者的才华,也鲜明地反映出作者的性格。当时此文很受赏识,似乎没有人想到这样对待梅兰芳是否公平,这样的强行送别是否过于霸道。
柯灵又说到在《饯梅兰芳》发表后,黄裳还有其他表现:
其实继《饯梅》之后,这位作家对梅放冷枪,就不止一处,例如说:“贤如梅博士,偶演《木兰从军》,武装扮一下赵云,虽然所谓梨园世家见多识广,也看不得,正如在台下梅博士说话一般,总有些不舒服。”原来不但在台上不行,连在台下说话也令人看不惯。甚至与梅毫无关联的题目,也要扫横一笔“孟小冬与梅兰芳的桃色新闻”。即使用最新式的精密仪器,大概也检验不出丝毫的善意来。
这就是前面所引黄裳自辩文中的“冷枪”的出处。柯、黄暮年剑拔弩张,与其说是为梅兰芳,不如说是缘自二人间之宿怨。稍后在香港披露出来的柯灵致古剑函即云:“我和黄裳的笔墨官司,事实极简单,内在原因,则可以说由于我深鄙其人。”暂且放下柯黄之争不论,回到他们争论的焦点《饯梅兰芳》一文。今天看来,黄裳所说内容未必不是真实的情况,写法上则未免不够厚道——当然,喜好京剧者历来有这个毛病,说话嘴损,喜欢阴阳怪气,这一点似是不好京剧的柯灵所难以了解到的。至于黄裳晚年的自辩,其既以资深剧评家自居,却说出“恢复盛年原样”这样的外行话,实在是够不上一个职业剧评家的见识,复何谈“这是剧评作者的权利也是义务”呢!
然而世事难料,大概是黄裳自己也未想到,在他发表《饯梅兰芳》文之后,其与梅兰芳不仅没闹翻脸,渊源反而愈结愈深。他居然能够神奇般地第三次在梅兰芳跟前闪出,而且成了梅兰芳最重要的著作《舞台生活四十年》的第一位责任编辑。
梅兰芳署名的《舞台生活四十年•前记》文说:
我事毕回沪,小住一月,正预备到天津演出,《文汇报》的黄裳同志要我写一个回忆舞台生活的长篇,在报上连载发表。我告诉他,我们本有这个计划,不过要报上连载发表,是相当困难的。因为中央人民政府要我担任中国戏曲研究院的工作,我想此后任务繁重,我自己还要演出,恐怕不能有固定的写作时间。再说我早期不曾写过日记,后来零碎记了一些,也不成篇段,这几十年来往事的回忆,全凭脑力追索,要没有充分的时间准备,是很难做有系统的叙述的。等我稍稍清闲一点再动手吧。他听了却不以为然,他说:“你以后只有更忙,不会闲的。现在不赶着写出来,将来一定更没有机会了。”他这句话,给了我很大的启发,我向他表示,让我考虑一下,再作决定。
我和几位老朋友商量的结果,他们一致认为这部回忆录,不但能总结我个人四十年来舞台生活的经验,也会保留下近代戏曲发展的许多史实,是可以供今后戏曲工作者的参考的。他们都鼓励我,勉力完成这个任务。并且答应帮助我回忆,供给我资料。我得到了他们的鼓励,就与黄裳同志约定,等我到津以后立即开始写作。写作的方法,是由我口述,姬传笔记,稿成寄给他的弟弟源来,由源来和几位老朋友再斟酌取舍,编整补充,最后交黄裳同志校看发表。
《舞台生活四十年》的主要记录者许姬传晚年撰写的《〈舞台生活四十年〉出版前后》,谈得更为详细:
1950年春,上海《文汇报》黄裳同志约梅兰芳先生写自传式的回忆录,梅先生说:“我现在很忙,没有时间写文章。”黄裳说:“您的艺术经验是丰富多彩的,应该写出来,给后辈留下珍贵的资料。”黄裳接着说:“您以后比现在更忙,如不抓紧时间,更难着手。”梅答:“让我考虑一下再决定。”
过了几天,梅葆玖带了剧团到苏州演出,我同去。有一天在老朋友沈京似家里吃饭,饭毕,梅夫人、梅葆玖都到剧场去了。沈留我下榻夜谈,沈君喜收藏书画,出示所藏,共同赏玩。第二天早晨主人准备了精致的西式早餐,正在边谈边吃,剧团有人来通知我说:“上海有姓黄的找您,并约您到一位朋友家里吃午饭。”我准时前往,原来是黄裳。他说:“我是专程从上海来奉访的,关于梅先生写稿的事,编辑部开了好几次会,最后决定题目叫《舞台生活四十年》,由梅口述,你笔记,这样分工,不致太紧张。你返沪后,务必善为说辞,得到梅先生同意。”我说:“我还没有写过长篇连载的文字,负担不了。”黄说:“这是近代戏曲史上一件大事,你要打起精神,担起这个责任,至于文字方面,我在审稿时可以帮忙。关于调查研究,核对事实有令弟源来在沪可以和梅先生的老友商量着办。”我说:“返沪后,打电话给你,你把这番话,当面讲给梅先生听,写与不写,由他决定。”返沪后,我把他的意思摘要告诉梅先生,就把黄裳找来,黄裳又重复述说了在苏州说过的话,还补充说:“像您这样享有国际声誉的艺术家,没有一部完整的著作,是非常可惜的。趁现在你们精力还旺盛,挤出一部分时间,细水长流地搞下去,这是总结梅派艺术继往开来的一件极有意义的事,您就不必犹豫,要下决心干,现在不干,将来一定后悔。”
梅兰芳与许姬传的话,都具有足够的权威性。他们两位一起肯定黄裳对于《舞台生活四十年》的贡献,这个分量是非常重的,几乎也就可以作为定论了。
不过,仔细辨别,梅兰芳与许姬传所谈虽然大同小异,但在时间及细节方面,还是有着较大出入,或许是许姬传晚年回忆时记忆有误也未尝可知。更大的一个问题是,梅许两文都没有交代黄裳是怎么突然就现身出来的,这令人难免要感到有些蹊跷。第一是,黄裳本有《饯梅兰芳》的前科,何以就能一笔勾销,如同没事人似的闪现在梅兰芳面前约起稿来了呢?第二,梅兰芳与黄裳的年纪地位均不相等,两人亦无深交。黄裳的话,多少有些交浅言深的味道。梅氏仅凭黄裳这三言两语遂决定写作回忆录这种大事,完全不合梅氏向来谨慎行事的风格。第三,黄裳在《文汇报》并无过高职位,《文汇报》要刊载梅兰芳的长篇回忆录,仅是委派黄裳去与梅兰芳商谈,这岂不是过于不把梅兰芳当回事了吗?这些个问题,在梅兰芳、许姬传的文字里,却是找不出答案的。
(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