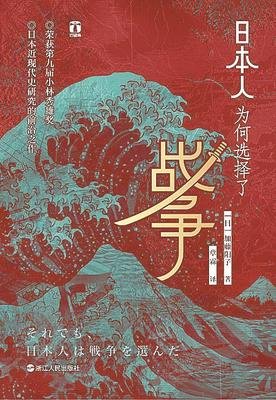
《近代的超克》是一本由[日] 竹内好著作,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出版的平装图书,本书定价:24.80元,页数:360,特精心从网络上整理的一些读者的读后感,希望对大家能有帮助。
《近代的超克》精选点评:
●竹内好太浪漫了,他在学界只能是失望和孤独的。
●亮点是对鲁迅的研究
●弯弯绕绕,在做笔记
●不知道是翻译的问题还是语言本来就有点绕……
●读学术研究 读文学思路 读他人 读他人的他人 最后读到了我自己 哭唧唧 受语言和材料所限 不免偏颇和臆断 这并非缺陷 反而使人惊诧竹内好的直觉和共情力 毕竟 他只是想从鲁迅那里 抽取自己的教训
●大概是八年前读的,那个时候大概既不懂鲁迅,也不懂竹内。不懂的并非否定的部分,而是否定之后生长的部分,是自觉到无力之后该往何处去的部分,我想这便是我褪掉的年轻的皮。即便是将回心放在一个“罪”的角度讲有过分阐释之嫌,依然是极好的、拒绝纯粹的知识关照的文学阐释最出色的示范。
●有的人在书里读出了德里达,有的人读出了李卓吾,也有人读出了福柯和辩证法,而竹内好心心念念的“自我否定”就是在这样不断的解读和误读中假他人之手实现了吧。无论是谈鲁迅还是谈近代,他自己的“回心”一直都是对形而上主体和客观化知识的拒绝。这样的想法在四十年代表现为“在文学中实现十二月八日”,到了六十年代则具象为“亚洲作为方法”——这大概就是竹内好自己投身于历史进程的生活态度。
●没读完
●竹内好真是一个,极为纠结又极为浪漫的人。读到近代的超克结尾仿佛觉得他自己就成为了矛盾的日本的缩影。串联起历史与现在,亚洲与欧美,民族与世界,在此中越发彰显的二重结构性和现代性根源上的危机。(但是我真的好怀疑我到底看懂没有啊)
●竹内好倒像个萨义德式知识分子,在西洋—东洋的结构里结构自己的“精神”。在近代的超克——即拆解近(现)代化过程中二元结构的禁锢——中,他多次与鲁迅相遇(谈文学就是谈政治),找到的方法是“回心”——向内否定,而非向外(西方)否定。试图在固化的西方现代化话语中找寻东方的逻辑。而他自己则是同鲁迅一般,针对主体内部的缺陷解决“主体性”问题,身处历史之中,不去做历史的先觉者。论述复杂,结构时而明显时而混乱,但还是盖不住文字里的独立以及绝望,力透纸背啊。
《近代的超克》读后感(一):关于《何谓近代》
第一,我同意竹内好对欧洲、日本和中国的观察。
欧洲文化是扩张性的,因为理性本质上是扩张性的。日本会迅速有样学样,而中国比较固执。
第二,我不同意他对鲁迅的判断。
竹内好说鲁迅绝望,其实鲁迅说的是“绝望之为虚妄,正与希望相同”。日本人自己喜欢绝望就行了,不要拉上中国人。
鲁迅是一个人道主义者。好的中国作家都是人道主义者,中国人也向来以这个标准来评判作家。我们最好是保持这个传统。除了人道主义,我还不知道有什么别的可以站在和理性相同的高度。
但现在的情况是,西方已经把人道主义拿过去了(是不是从我们这儿拿的也未可知),而中国没有把理性拿进来。于是人道主义正在西方变成现实,在中国却仍然是个梦。
《近代的超克》读后感(二):近代的超克与当代的日本和非西方
《近代的超克》读后感(三):近代的超克 书评
竹内好对鲁迅一生的阶段划分是以地点的辗转为标准的,从这个角度来说,他更侧重于鲁迅本人的转折,而李长之更侧重于鲁迅作品的转折。他却说“和李长之不同,我不在发展中看鲁迅,所以传记的划分也只取方便。”竹内好作为研究鲁迅的专家,显然不至于持文学进化论的观点的,李长之同理,所以“在发展中看鲁迅”,是不是翻译上有失偏颇,这一点存疑。
竹内好对鲁迅提出三个最主要的疑问,在之前读这本书的时候就给我留下很深刻的印象。
第一,鲁迅和周作人对待祖父的态度相左甚远,前者讳莫如深,不轻易提起,后者颇有感怀,回忆富有文学性。祖父对鲁迅究竟产生了怎样的影响,又是什么原因导致兄弟二人的态度不同?
第二,鲁迅的第一次婚姻问题。竹内好将鲁迅的文学基调定在“赎罪”上,因此其恋爱不足以赎清错误婚姻带来的罪过。
第三,兄弟失和真实性的质疑。骤变发生得太过极端,且根据二人性格特点的推测来看,失和是无法理解的。每一个疑问都可以被偷懒的学者捡去做做论文(切口偷懒,收集资料不可偷懒),此处不再赘述。
进入第二章《思想的形成》,竹内好引入了一个“回心”的概念。根据译者的注释,回心指基督教中忏悔过去的罪恶意识和生活,重新把心灵朝向对主的正确信仰。这个概念在本章中非常关键。首先,它指向竹内好对鲁迅文学作品的理解,其性质是赎罪,和基督教的赎罪有相通之处。诚然,即使有类似于原罪意识的鲁迅也依然是非宗教的,这一点在九月十五日的读书笔记中已有阐释。此后,竹内好开始探讨鲁迅回心行为所围绕的关键点,也就是所谓“回心之轴”是什么。竹内好认为,“一个人,到了获得对他一生来说都具有决定意义的时机为止,恐怕会有无数个堆积起来的要素,但在他一旦获得自觉之后,那些要素反过来又要任他选择。”也就是说,在竹内好苦苦找寻的关键时间节点之后,鲁迅幡然醒悟,他获得了“鲁迅思想”的自觉性。这种观点未免有些扁平化,将人生看作小说式的开端-发展-高潮-结局,前期的准备都是为了高潮做铺垫。我想,鲁迅的思想并非有一个可以回望,萌生自觉的时间点或者事件,而是在他每记录一件事,都有意地回忆着这件事当年如何产生影响,现今又如何对未来进行观照。这种自觉本身就是逐步形成的,没有一个非0即1的决定性变化。所以竹内好可能无法找到这个答案,因为问题的出发点建立在不够准确的假设上。
但竹内好关于其他问题的论述是有助于我们靠近鲁迅的。“回心”观念所引申出的赎罪的文学,就此打住即可,无需寻找“回心之轴”,这并不影响竹内好在前一部分中琐碎而重要的问题成立。
《近代的超克》读后感(四):很早就想写的鲁迅
虽然只是一篇公选的课程结课作业
一、 历史深处的忧虑
人们总是把鲁迅先生看做那个时代一个标杆式的人物,是直观意义上的“战士”,却很少有人愿意从那张时代的大网中跳脱出来,顺着鲁迅先生深邃的目光,去看穿他骨子里的埋在历史深处的忧虑。
自鲁迅的作品被大量编入中小学教材后,很多学生就对“鲁迅”二字产生厌烦的心态,并默默地在心里将其文章与“枯燥难懂”的标签划上等号。恐怕那是简单应试型教育对原始感知压榨下的产物。竹内好先生也说“难懂毁了小说“。
但在我看来,就鲁迅的创作而言,他本没有企图成为时代的标杆型作家,他的小说是用来叙述,他的散文和诗是用来抒发,他的杂文是用来泄愤。这一切都应该站在先生个人的角度去看。也就是说鲁迅在写作的时候,本就没有以让后世的人读着通俗有趣为标准,他只是站在自我的中心,然后长久而不停歇地朝地底,也是朝他的内心,深深地挖掘下去。与他人无关,更与我们这些后世再来苛责的人无关。
但竹内好先生的《鲁迅》让我最欣赏的是它虽然被归类于学术研究类论文,却处处透露着作者本人最朴素和真实的气息。他似乎和鲁迅先生站在一行之间,去表达他内心的所思所想,而不是将鲁迅置于一个高高在上的位置,然后以小心翼翼谨慎严格的态度去做仰望型的研究。
这正是我所期望的探寻鲁迅的方式。
我生于长于鲁迅的故乡绍兴,所以每次我在阅读鲁迅先生的作品时,都会产生强烈的代入感,尤其阅读小说作品,愈觉得此时故乡环境里的人与物,都仍是鲁迅笔下故事的化影,经历着同样的世俗冷暖、幻想与挣扎。正如竹内好先生在《鲁迅》中所述,“鲁迅是诚实的生活者”,他的文字是现实的生活,是时间也无法改变的属于一个民族的永恒的隐秘人性。而“鲁迅文学的根源,是可以称为‘无’的东西。”我把这种“无”理解为超越在时代之外的“历史深处的忧虑”。正是这种忧虑让鲁迅伏案之间不仅看到了过去的真实,现在的真实,而且还预见了几十年后的今天乃至未来更长时间里的真实。
二、 孤独的理想与死亡
鲁迅信守着那份构成他生命本源的孤独。
很多人都把鲁迅的文字比作锋利的匕首,披荆斩棘,指向社会最黑暗与致命的部位。但绝不仅仅是这样而已。在我看来,鲁迅的文字似乎更像是一面镜子,照出了他自己的生活,也照出我们每一个人的生活;反射了他自己的孤独,也反射了我们每一个人的深刻的孤独。竹内好先生就是之一。
孤独来源于什么?孤独来源于清醒,来源于看清这个世界之后还要去爱它的企图。当一个人没有经历太多也没有了解太多的时候,他往往会更容易被影响,更容易听到一个段子就乐得哈哈大笑,更容易看到一个悲剧故事就泪流满面。鲁迅无疑是清醒的,他早已深刻地了解了自我,看穿了这个时代。他的思想总是不经意间上升到魂灵高度在思考,他知道他的道路在哪里,也明了彼时这个民族和社会从根源上显示出来的未来将如何改变。所以当人群在左右前后来来回回移动的时候,他永恒地站定在那里。他说“这个岛上众生喧哗”,因为他那个平面的世界中一片静寂。他说“一个都不宽恕”,因为宽恕对于改变于事无补。
这便是鲁迅的孤独。因着这份孤独,鲁迅深深地望进了黑暗,甚至“以满腔热情来看待黑暗,并非绝望。”他在黑暗中便这么“顽强地恪守着自己,直到死。”
竹内好先生曾就鲁迅是否做好了死的准备这个疑问做出了探讨,还原了鲁迅死前的情况,但其实,作者在心里早已摒弃了探讨这个疑问的价值。或许鲁迅的确恐惧死亡,尤其当与许广平交往之后生命多了些新的企盼之后。但“鲁迅在晚年超越了死”。——竹内好先生早已看清了鲁迅存在的孤独,并从他的的死中感受到一种行为的意义。
而我同样也相信死亡对于鲁迅来说绝不是最恐惧的事,即使在内心有所情感的羁绊之后也同样不是。忘却才是。这种忘却不仅仅是民众对屈辱历史和惨痛现实的忘却,如无数篇同《纪念刘和珍君》言辞激烈的杂文中所述。忘却更是每一个个体对其个性形象的忘却,这大多体现在鲁迅的小说里,尤以《伤逝》、《在酒楼上》等篇为甚。对鲁迅自身而言,他惶恐有一天他的文字连同思想一道失去那种坚定和锐利的姿态,对于众生而言,他惶恐在复杂的时代背景下会有越来越多的人看不清世界也看不清内心,以致成为一个模糊的人、丧失的人。
那么死又算得上是什么绝望呢。“死孕育生,生又不过是走向死。”
《近代的超克》读后感(五):竹内好眼中的鲁迅
书的扉页上记着我是05年4月1日在前门社科书店买的这本书,却直到两年后才来阅读它,而当初的社科书店老早就消失了。
当初买这本书的缘故是因为他讲了亚洲主义思想,而前天从书架上把它拿下来是因为最近正好连续看了些鲁迅研究的书,于是乘机看看竹内好书写的鲁迅。
《近代的超克》第1页到161页收的是竹内好1943年写的《鲁迅》,战后曾经再版过几次。在1952年的创元文库版后记里,竹内好说“我的《鲁迅》已经旧了,是否有重出的价值还是个疑问。但从另一方面来说,《鲁迅》对我来说又是一本很能牵动怀旧之情的书。怀着被追赶着的心情,在生命朝不保夕的环境里,我竭尽全力地把自己想要留在这个世界上的话写在这本书里。虽还不至于说夸大其辞地说像写遗书,但也和写遗书的心境很相近。我还记得,事实上就在这本书刚刚完成时,征兵通知书就到了,那时我想,真是老天保佑,谢天谢天呀”!竹内好因此说他因为写鲁迅而获得了他的生的自觉。
竹内好腔调,“鲁迅是文学者,首先是个文学者。他是启蒙者,是学者,是政治家,但正因为他是文学者,即正因为丢掉了这些,这些才会作为表象呈现出来”。
“绝望之为虚妄,正与希望相同”,竹内好说“对绝望感到绝望的人,只能成为文学者。不靠天不靠地,不以任何东西来支撑自己,因此也就不得不把一切归于自己一身”。
竹内好认为“鲁迅的文学,在其根源上是应该称作‘无’的某种东西。因为是获得了根本上的自觉,才使它成为自觉者的,所以如果没有了这根柢上的东西,民族主义者鲁迅,爱国主义者鲁迅,也都成了空话。我是站在把鲁迅称为赎罪文学的体系上发出自己的抗议的。
在“政治与文学”一章里,竹内好提到鲁迅在广州有名的那两篇演讲,谈到《魏晋风度及文章与药及酒》中说到嵇康、孔融都被以不孝罪名杀了时,竹内好说“就是这么种关系:杀人者杀批判者,而批判者又因被杀而批判杀人者。政治在政治上是有力的,但在文学上是无力的;无力的文学,作为文学是绝对的,这是因为它的无力”。“批判者被杀了,但被杀却是批判”。
竹内好同意李长之认为的鲁迅的强韧,就在于“人得要生存”这样一种朴素的生活信念。“为了生,他不得不做痛苦的呐喊。这抵抗的呐喊,就是鲁迅文学的本源,而且其原理贯穿了他的一生”。
“鲁迅不能相信善能对抗恶。世界上或许有善,但那是另一回事,他自身却不是。他的与恶的战斗,是与自己的战斗,他是要以自毁来灭恶、在鲁迅那里,这便是生的意义,因此他唯一的希望,就是下一代不要像自己。为灭恶而知恶,只被恶所允许,即所谓恶的特权。或许会在某一时刻实现的善,只有通过恶的自我否定,才会被赋予克服其相对性的基础。鲁迅的这种虚无主义,当然是以一个后进的、封闭的社会为条件的,但是应该注意到,它在鲁迅那里却孕育着一个诚实的生活者的实践,同时,它也显示着现今中国文学的自律性的本源”。
鲁迅“几乎不怀疑人是要被解放的,不怀疑人是终究会被解放的,但他却关闭了通向解放的道路,把所有的解放都看作幻想”。“他把问题看透了,那就是把新道德带进没有基础的前近代社会,只会导致新道德发生前近代的变形,不仅不会成为解放人的动力,相反只会转化为有利于压制者的手段”。
上面我摘抄了很多竹内好论述鲁迅的文字,然而上面那些摘抄只是我个人看书时用笔随看随划的一些文字,并没有自成体系,只是一种感性的择取。说我对那些文字的排列或者选取所表现出来的描述和竹内好不尽相同也是可能的。
我很注意竹内好一些论述,比如他认为鲁迅首先是个文学者,然而对于鲁迅大多数作品,他认为是失败的,或许竹内好之所谓文学者,和作品好坏是没有多大关联的,那么他是在一种什么意义上说出这句话来的呢。还有竹内好把“辛亥革命和文学革命”、“国民革命和革命文学”联系在一起,并且他探讨了孙文和鲁迅思想上的联系。还有,我们的一贯印象是鲁迅是和现代各种风起云涌的思潮联系在一起的,一般是不会想到鲁迅经历的平凡的,不过竹内好说,鲁迅一生经历没什么大波折,除了8年留日学习,短期厦门广州工作经历,其余时间基本都在北京或上海度过,也没什么很多出游的经历,这和郭沫若投身革命是不一样的。
还有,我对竹内好的政治趋向感兴趣。当然我并不会仅凭政治标签就判断了一个人,不过我对竹内好是不是共产党员这点仍然感到兴趣。
以前听讲座时,一个人问一个日本学者关于竹内好的鲁迅研究的问题,台上的日本学者和中国学者腔调,我们应该理解竹内好写《鲁迅》时,有他自己的环境。确实,向我上面摘抄中所言,竹内好应是在鲁迅中得到了他精神上的某种需求与满足感的。
鲁迅研究各人的风格不一,我们最熟悉的就是从小度讼背诵的僵化鲁迅教条。夏志清在他的《小说史》中对鲁迅未免有些掩藏不住的贬抑冒出来,李欧梵就好多了,针对应该算他师叔的夏志清的一些看法也作了修正。以前听汪晖讲座时也听到他的一些看法,不管怎样,每个人有他自己的理解,只要是真心的是这么以为,而不是人云亦云套话连篇,说着一些自己都不信仰的话,我都不会反感,最讨厌的是假话套话满天飞而又根本不能身体力行的鲁迅研究者。
竹内好在这本书中有一段话,让我从他身上真正嗅到了鲁迅的气味,把它录在下面:
“总而言之,我站在了我自己的‘终极之场’。虽然还剩下很多话要说,但走到了现在这一步,我也就不想再回头去捡拾它们了。我只能往前走,为的是抹杀我的研究笔记。这是用以报偿这份笔记之不备的惟一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