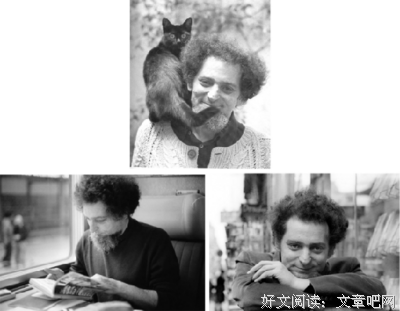
《中國現代小說史》是一本由夏志清著作,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出版的平装图书,本书定价:US$30.00,页数:521,特精心从网络上整理的一些读者的读后感,希望对大家能有帮助。
《中國現代小說史》精选点评:
●错别字多到与出版社的地位很不相符,人名都能印错,编辑不觉得羞耻么?
●宇宙有若干千亿(10的11次方)个星系,每个星系约有千亿个恒星,行星的总数和恒星大致一样。而所有天体加起来几乎只占宇宙的10的33次方之1。 在如此广袤的太空,夏志清先生和黄仁宇先生,都让我看到了不卑不亢认真活着的态度。著书立言,唯其宽而不泛,深而不僻,始觉独到。
●当然,我得承认,我原是抱着一定的眼光——夏是个著名的反gong分子——去读这书的(之前读过,但是有删节的),读了也就,果然,那攻讦的笔锋甚健,戳击的痛点甚酷,甚至因了这立场而时有偏激之论与刻薄之语也不惜了(譬如他对老舍之死的近乎幸灾乐祸的话)。尤其与大陆的现代文学史并读,我最感慨的倒还不是夏洋洋自得的所谓重新发掘了张天翼张爱玲钱鍾书,而是同样一段历史,同样一位作家,只因了立场的不同,居然可以有这样异质,甚或截然不同的看法与写法——而且它们看起来都那么意气风发,那么真理在握,那么自圆其说,噫,套一句话来说就是,史料广大已极,足以占有一个人,谁知道自己已拨掉了障目之一叶之后的眼中的泰山,只不过是另外的一片叶子呢。
●这本一定要读港版,大陆版删减太多,已伤元气。
●读完以后觉得 不想学现代文学了..昨天有的没的扯闲话时 舍友说她觉得现当代文学里的有些作家不道德,所以她不喜欢。本能觉得哪里是说对了的,又想了想如果历时性评价作家,那很多作家都谈不上道德;如果在共时平面看,是不是就能发现不一样的东西。话是总说成熟与否,好与不好,并不是评判是否道德的标准;但是有时候撒泼的文人也不是没有,自知格不高但硬是故作姿态。有时候被我们看作先锋的东西,万一也只是我们给他们带了高帽,这就有点有趣了。原来很多觉得残忍的东西也对,其实人都是要逢迎的,逢迎物质,逢迎人生,逢迎文学乃至艺术,哪一个都不是无为。其实人都是俗人,只不过俗得有没有内味儿,这才好。
●4.5 几乎是完全颠覆的文学史阅读体验,政治立场原因。值得读港版,不然简体版不知道要被削成怎么个前言不搭后语了。/ 这本书令我欣喜的原因是夏的观点不狭隘:行文时不断地跟外国文学作品对比,很有意思;他的文学批评标准是文学价值的高低,所以他的观点态度不随波逐流,说得也更加一针见血,只不过看到后面我已经丧失了辨别公正客观和主观偏激的能力(三观被按在地上摩擦)。读罢最大的感受是文学史是私人的东西,每个人眼中的历史都不同,更何况文学作品。所以夏偏爱张爱玲、钱钟书、姜贵等,而认为“把鲁迅仍视为国家英雄,对于政权是有利的,虽然ZG却极力阻止任何人模仿他的讽刺文体。”并预言随着时代的发展鲁迅地位只会原来越低。现在想想真的是这样。/ 二十世纪的大陆文学往往因为意识形态太强而无法引起我的兴趣,欸,还是好唏嘘。
●太喜欢了
●虽然贬了鲁迅,通篇下来最喜欢的还是鲁迅、沈从文、钱钟书。 不管再怎么表露政治立场,起码此书以文学为主。一本文学史无论怎么样都是有意识形态的,但不为意识形态所掳获即可。
●当大陆文坛被神化的鲁迅和被媚俗的张爱玲被还原成一个普通的作家时,十分有趣。很多读者批评说,作者名义上谓以文学为标准,实则夹带了太多政治性的私货。且不论作者的政治私货才是世界潮流,即便从作品本身来看文学标准也确实是大于政治标准的。
●夏志清在此书里重新评价张爱玲,其实是重估了文学写作的伦理品质,而非艺术性取代政治性那么简单。政治性作为统摄性的标准包含了流俗写作与正统写作、表现写作与思想写作等等,很像亚里士多德把“作诗”的本质从具体的“诗作”样式中提炼出来的方法。包括其他作家在内,都被夏志清纳入整个政治文学的框架下,进行提炼式分析,并以此组成了现当代文学的价值重估
《中國現代小說史》读后感(一):记录。
鲁迅 【叶圣陶】 教育:《饭》《倪焕之》 市民:《孤独》《秋》 农民:《多收了三五斗》 童话:《稻草人》 散文:《两法师》 冰心 【凌叔华】 《花之寺》过渡时期女子的悲惨遭遇(小巧精致,对话心理) 【许地山】 宗教,爱与忍的意义,曲折离奇的情节,寻求一个完美的寓言来表达他对完善的生活之见解。 《缀网劳蛛》《春桃》《玉官》 郭沫若 【郁达夫】 心理和道德,罪恶和忏悔用儒家教化去了解,暴露自己的弱点。 《沉沦》《春风沉醉的晚上》《迟桂花》《过去》 【茅盾】 自然主义 【老舍】 有些人悲愤的激情掩盖讽刺的笔调。 【沈从文】 少女和老头,丰富的想象力和对艺术的诚挚。 《三个男子和一个女人》《大王》《萧萧》 《三三》《边城》《生》《夜》《大小阮》《主妇》《静》 张天翼 【巴金】 有些人无法超越青春期间的文艺修养和领悟能力。拒绝个人意志与罪恶互为因果。 蒋光慈,丁玲,萧军 吴组缃 张爱玲 【钱钟书】。 小说的优劣,不能以主题深浅来评价,关键是主题是否得到适当的处理。孙柔嘉的评价。小说的主题。 师陀 赵树理 对一些作家作品尤其本人喜欢的(准确说是不跟随d或有部分脱离d的),点评到位,有独到见解。对一些作家作品的点评现在依然流传,传世之作。 不是小说史,更像个人点评小说。个人喜好强烈,以及有强烈的政治性偏见。 政治意识形态过重,对党的贬义过于明显,党是一个贬义词并多次提及,推测性谣言写入书中(比如13,24页等)。 说鲁迅自以为青年导师和对杂文的评价,我认为他没怎么读过鲁迅杂文。对鲁迅过于尬黑。
《中國現代小說史》读后感(二):以“偏狭”重构文学传统
正如王德威所说:“在《小说史》一书中,夏也本着类似精神,筛选能够结合文字与生命的作家,他此举无疑是要为中国建立现代文学的‘大传统’。”夏志清有着重构中国现代文学“伟大的传统”的野心,《小说史》的生成样式跟同时代的现代文学史有别:与其说它是一本研究型的文学史,不如说是一本“作家论”。
《小说史》作为在新批评理论浸润下的果实,表现出来的特点有:以文艺作品为本体,着重研究文本;重视作品的内在构成的各种因素的特点,“细读”(close reading)的内部研究方法则确立了审美性为核心评价体系。在这种体系中,挖掘出了被标榜为“反动文艺”的沈从文,写滑稽小说的钱钟书以及被视为“鸳鸯蝴蝶派”的张爱玲。
另一方面,道德关怀是夏志清衡量一部作品的重要尺度,不难发现“道德意识”、“道德冲突”、“道德视景”以及“宗教观”、“人道主义”这类词出现的频率较高。他认为:“现代中国文学之肤浅,归根究底来说,实由于其对“原罪”之说,或者阐释罪恶的其他宗教论说,不感兴趣,无意认识。”实际上,夏所做的工作,即是在宗教信仰与文学发展的复杂关系中,为国内文坛理出一条可供参照的线索和思路。
总而言之,《小说史》为大陆现代文学一度以科学名义作为集体操作的精神模式,展示了一个充满文学性和个性化的风格史写作范式;它也提供了一个跨文化的国际视野,在宏观上厘清与挖掘了那些“优美”的作品,拓宽了中国现代作家的研究谱系。纵然对于《小说史》的批评与争议未曾间断,但我们通过思考不断地完善对历史与文学的认识,使其更加合理、合乎人性,这是《小说史》给予我们的启发,同样是文学研究的初心。
《中國現代小說史》读后感(三):先声与后来人
1.新批评的保守使得这本书问题多多。比如鲁迅一章就有太多地方不敢苟同了。总体不如其先兄夏济安的《鲁迅作品的黑暗面》精彩。张爱玲一章不乏妙语,但张氏小说的毛病,也是显而易见的——夏志清显然没能克制住自己对女神的爱。但这就是夏志清,一个可爱的老顽童。
2.但在我们谁也不清楚到底何为“Modern Chinese Literature”的时候,夏志清为我们提供了一条虽然看上去非常粗暴但其实很发人深省的路径:用英美文学的标准来撞击现代中国文学。火花四溅之余,表面看去,这种做法好像是什么“欧洲中心主义”。可换个角度看,又何尝不是在创造现代中国文学批评多样性的无限可能呢?夏志清抛给了我们很多问题:像communism与现代中国文学的关系,像现代中国文学与世界文学的关系等等,在今天仍然值得我们思考——自本书始,现代中国文学的解读空间只会越来越大,而不会收窄。这想必也是所谓“开山之作”的意义所在:不是说前无古人就不得不要给它位置,而是说它创造了生机,是巨大的贡献。
3.总的来说,夏志清证明了,不同渊源的理论资源之间唯有不断在碰撞中交融,在交融中碰撞,才不失为是一条有希望的出路——带刺的未必是洞见,但真正的洞见一定套着偏见的皮囊(尤其在今天这个漂亮话横行的年代),并能引发新的洞见(否则才真不过是哗众取宠的论调而已)。在这一点上,王德威就显得有点滑头了。
4.在最后也是最值得反复重读的“结论”章中,夏志清表达了自己从祖师爷李维斯那里继承来的“大传统”野心。我想,应该不少人有过同样的想法:即跟欧洲一样,中国也应该有自己的但丁、莎士比亚。不过事实并不如人愿。而“应该怎样看中国文学至今没有自己的但丁和莎士比亚”这个问题,跟2里提到的那两个问题一样复杂。
5.世人每每谈及夏著,总三句不离“保守”、“冷战”、“反动”、“激进”甚至“毁三观”等词,对其中的深意置若罔闻,实乃愚不可及也。
《中國現代小說史》读后感(四):透过小说了解中国
夏志清的《中国现代小说史》匆匆看完。他声称抛开政治、宗教、意识形态,以“文学作品的真正价值”——“文学价值”重新评估中国当代的小说,“发现和评审优美作品”。夏志清(1921-2013)在写本书之前主要研究西方文学,尤其是英国文学。正是受益于长期西方文学评论的训练与艺术理论,他对中国文学的批评提出了新的看法,开创了中国文学批评的新领域。让张爱玲,钱钟书跻身名家之列,也提到了一些大家不太注意的作家及作品。虽说他要抛开意识形态,单以作品的艺术价值来评估作品的好坏。他其实也深受他自己的政治立场和喜好来评价作品,或者说是带着强烈的个人偏见。这应该是他受当时环境的局限。比如对张爱玲的《秧歌》、《赤地之恋》等类似的作品,他对此评价很高。以我愚见,张的这两部作品和她之前的作品风格迥异。感觉张对那时农村的生活并不熟悉,驾驭不了这种风格,与她写城市市民生活的作品比起来味道索然。他对张爱玲钱钟书等评价很高,而对大家熟知的鲁迅,丁玲,矛盾等评价平平,也许因为他把他们的作品归到了宣传工具之列的缘故吧。这也解释了为什么有的作者或有的作品我们见不到甚至很少听说的原因吧。因为他们可能对某些宣传不利。
夏尤其看重以作品的深度,对人心理的剖析来评价作品。他拿来对照的多是西方顶级作家,比如陀斯妥耶夫斯基,乔伊斯,托马斯·曼,福克纳,乔治·艾略特等等。他认为,和他们相比,中国的作家大都过于浅露,缺乏“道德问题之探讨”。他给的解释是中国不是宗教国家,是过于理性的社会。“中国文学传统里并没有一个正视人生的宗教观。中国人的宗教不是迷信,就是逃避,或者是王维式的怡然自得的个人享受”。再者,中国积弱已久,作家们也难以跳出“感时忧国”的思维模式。他们关心的是怎么摆脱贫困,怎么唤醒国民,甚至对民主和科学充满了向往。而西方的作家们则没有面临这样的问题,他们甚至在反思他们的社会,或者从某种程度上说,文学艺术是反理性的。中国的作家们背负如此沉重的责任负担,所以他们没有时间和精力去关心人类普遍面临的问题。因此他们的作品视野狭窄,多为狭隘的爱国主义,无法跻身世界文坛,甚至相去甚远。也是因为他们的这种“感时忧国”(Obsession with China)的使命感,他们写的最多的小说类型就是讽刺。从晚清,到五四,到民国,甚至到现在,似乎总延续了这个传统。此外,中国的作家们还受意识形态的限制,种种题材不能写,可谓枷锁重重,生存空间严重受限。这是中国文学不能繁荣发展的症结所在。本书首次出版于上世纪60年代(1961年),不知道夏先生对莫言的作品作何评价。夏先生对中国文学的评论应该延伸至中国古典文学。结合西方的文学评论,重新评估我们的文学作品。这应该也是夏高度评价胡适工作的原因吧。他的某些论点甚至可以推广到中国社会的各个方面。
读完本书,根据夏的结论,对中国小说的前途我是悲观的。然而再看前面的几篇序言时发现,后来夏本人对他之前的看法做了不小的改变。比如对于宗教观,讽刺等。“大体说来,中国现代文学是揭露黑暗,讽刺社会,维护人的尊严的人道主义文学。”“比起宗教意识越来越薄弱的当代西方文学来,我国反对迷信,强调理性的新文学倒可说是得风气之先。富于人道主义的精神,肯为老百姓说话而绝不同黑暗势力妥协的新文学作家,他们的作品算不上‘伟大’,他们的努力实在值得我们崇敬的。”这可以算是中国文学的可取之处。他甚至说,“只要有人能努力去写,白话文的前途是不容我们去忧虑的。”然而任何事情的发展都不是一蹴而就的。尤其是文学,它需要超脱,剥离,积累和沉淀。
当中国富强以后,也许会摆脱“感时忧国”的责任限制,这一点从逐渐发达的娱乐业可见一斑。然而,严肃文学与娱乐又不一样。富强的中国只是摆脱了“感时忧国”的限制,其它的限制未必能摆脱掉,也许升级为广义的“感时忧国”,或者说不自信,深层的不自信。他们的视野未必会放得很开,至少在较短时间内应没希望看到世界顶级作品的问世。此外,输入国内的外国文学作品类型单一,并不完整丰富,缺少必要的交流和碰撞,无论小说思想,技巧,都大大滞后于国外先进水平。仍需从各方面不断努力。
《中國現代小說史》读后感(五):文学的思想史价值:夏志清《中国现代小说史》读后
一
文学*是更为深刻的思想史。最精深的思想往往难以精确表达,而文学的独特之处在于,可以通过对文学人物及其处境的设计和描述,营造出现实生活中不一定存在但却又十分真实的思考环境,传递一种复杂的情绪和体验,并以此为基础挖掘更为深刻的思想内涵。一部文学史,可以通过对一个时代文学作品的考察,去展示特定社会环境下,特定作家通过特定文学形象传递出的思想内容,从而更加真实、准确和深刻地反映那个时代人们的思想面貌。这是我读《中国现代小说史》的突出感受。
《中国现代小说史》是旅美中国学者夏志清的代表作,一直被认为是研究中国现代小说开创性的经典著作(原书为英文)。确实,此书不仅语言优美,立论诚恳,且每发一论断评鉴,皆言之成理,持之有故,传为经典,非虚名也。在体例上,此书为编年体和纪传体杂糅,以时代分野为经,以作家为纬,其中亦有穿插,可谓兼采中国传统史学体例之长。
夏志清的每一论断不一定都能让读者信服,但却总能反映出其解读品鉴作家及其文学作品的独特眼光和广阔视野,使人耳目一新。加以文风老辣不遮掩,读来可谓酣畅淋漓。夏志清学贯中西的深厚学养及其在东西方生活的丰富经验,更使此书具备了少有的洞察力和穿透力。
二
关于如何认识和对待文学,此书贯穿了两个主题:一是文学的目的在于挖掘人性,二是文学应该“为文学而文学”,去除济世性。
关于第一个主题,夏志清说:
“一个艺术家,只有照实的去描写生命,去探索人心的隐蔽处,去灼照人生中爱的道路,才能够为真理服务。”(页290)
这句话可以说是全书精髓的集中表达。从根本上讲,人性的基础和优缺点是古今一致的,只是面对不同的环境,有不同的面貌。文学的作用,就是挖掘人性的幽暗之处,表而出之,然后指出此种人性对个人和时代造成的影响。因此,文学的根本目的在于反思人性,以便人类更好地认识自己,尽量拓宽人对于美与爱的认知界限,避免落入人性中恶的陷阱,从而使人更加健全,更加丰富,更具备自爱和爱人的能力。
夏志清对于人性的观点是较乐观的,至少在书中主要表现出的是乐观,否则他也不会说“灼照人生中爱的道路”和“为真理服务”了。我却并没有他那么乐观。在我看来,人性的根本困境在于,即使认识到了人性的幽暗之处,以及人性中的恶可能造成的悲剧,人却无力去改变这种人性。爱与真理之不能达成,其原因不是人的认知能力问题,而是人与生俱来且永远无法改变的固有局限问题。
当然其实夏志清在书中也会透露出悲观情绪。例如他说:
“现代中国文学之肤浅,归根究底说来,实由于对原罪之说或者阐释罪恶的其他宗教论说,不感兴趣,无意认识。当罪恶被视为可完全依赖人类的努力与决心来克服的时候,我们就无法体验到悲剧的境界了。”(页383)
结合夏志清一生的经历和他本人的文学创作,我认为他的内心更倾向于悲观,只是在书中掩饰自己的悲观罢了。因为如果彻底悲观,文学创作就无法开展或没必要开展,文学史的意义也就不太大了。
关于第二个主题,夏志清主要是通过批评共产小说实现的。共产小说的宗旨,代表文献是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这篇讲话的精神既是总结性的,又是指导性的,反映的是一个时代的面貌。讲话强调的重中之重是文艺应具有鲜明的济世性,即为工农兵服务。
其实,中国文学的济世传统并非到毛泽东才如此,而是长期存在、渊源深厚,这是儒家济世传统在中国思想史上的压倒性优势所导致的。中国历史上最好的文学作品,似乎主要出自道家、佛家的信徒之手。或者说,即便是一个处于儒家传统下的中国读书人,只有当他从道家、佛家寻找思想资源的时候,才更可能创造出伟大的文学作品。庄子、陶渊明、李白、苏东坡等即是如此。
夏志清对“文学需济世”的观点显然不赞同。他认为文学应该坚持自身的固有传统,不能作为任何其他外在因素特别是政治的工具。夏志清说:
“劳伦斯在他的《古典美国文学研究》一书中,说了这么一句话,对于有想象力的作家,可谓金科玉律:‘勿为理想消耗光阴,勿为人类但为圣灵写作。’照此说法,那么一般的现代中国文学之显得平庸,可说是由于中国现代作家太迷信于理想,太关心于人类福利之故了。……事实上,这些作家往往把理想误作圣灵来侍奉。”(页379)
也就是说,夏志清认为必须跳出人、人性和人类来认识文学,才能创作出好的作品,也就是“为圣灵写作”。这里突出了作家写作的神圣性。可惜任何作家都是深嵌于现实人世,完全“为圣灵而写作”几乎是办不到的。
三
读文学史有一个好处,可以快速了解作家及其作品的梗概,并且借由史家之笔直接认识到作品的内在含义。虽然会有偏差,但也简单直接。大部分文学作品恐怕是没有太大意义通读的。虽然如此,经过夏志清的介绍,我对于一些文学作品倒发生了兴趣,希望可以去读原书。
此书写得最好的部分是鲁迅和张爱玲。鲁迅的文学创作不是太多,我基本是读过的,夏志清的解读令我有拨云见日之感。张爱玲的书我几乎没读过,但看夏志清描述《秧歌》和《赤地之恋》的故事梗概,仍然惊心动魄。我未曾料到文学作品在反思和表现政治中的人性方面能够达到如此深度。
此书广受赞誉的一大原因,是夏志清通过此书的评介,发掘了沈从文、张爱玲、钱锺书等一批此前未受注意的作家,使之成为知名作家。沈从文我很喜欢也更加了解,钱锺书的《围城》则是我读了多次而读不下去的书。我揣想,张爱玲、钱锺书之所以被夏志清发掘,可能因为他们三人生长于于同一地域文化圈(张爱玲和夏志清均生于上海,夏志清祖籍江苏,而钱锺书是江苏人)。夏志清对张爱玲和钱锺书作品的理解,很多是我无法做到的,其原因除了鉴赏能力的高下和人生经验的多寡,部分也由于中国语言和文化的地域差异,与我喜欢沈从文的作品是一个道理。同时,沈从文能得到夏志清的高度评价,也从一个侧面反映出沈从文的作品或许更具有跨越地域的穿透力和辐射力,而这正是好作品最重要的特征。
四
当今时代,小说作为一种艺术形式正面临挑战,其对人的意义很大程度上已被影视剧取代,很多小说家兼任编剧也就不足为奇。李敖曾在《北京法源寺》书后的一篇自叙中说:
“正宗小说起于十八世纪,红于十九世纪,对二十世纪的小说家说来,本已太迟。艾略特(T.S.Eliot)已咬定小说到了福楼拜(Flaubert)和詹姆士(Henry James)之后已无可为,但那还是七十年前说的。艾略特若看到七十年后现代影视的挑战,将更惊讶于小说在视觉映象上的落伍和在传播媒体上的败绩。正因为如此,我相信除非小说加强仅能由小说来表达的思想,它将殊少前途。那些妄想靠小说笔触来说故事的也好、纠缠形式的也罢,其实都难挽回小说的颓局。”(李敖:我写《北京法源寺》)
现在,距李敖写这篇文章(1991年6月)又过了28年,距艾略特咬定小说无可为则快要100年了。在没有电视机、电影院、电脑、网络的时代,读小说是排遣时光的重要手段,现在则是追剧、看电影、打游戏了。这是小说的危机,不过倒不必惋惜。很多艺术形式都随着时代产生,随着时代灭亡的,汉赋、唐诗、宋词、元曲均是如此。小说的前途,恐怕就是李敖所说,需要“加强仅能由小说来表达的思想”。
其实整个文学的处境与小说相差无几。大众中阅读严肃文学的人显然越来越少了。从这个意义上讲,文学在思想史上的价值和意义更值重视。只有在更超拔的层面上描绘和反映现实生活,反思新的时代中人性的独有困境,文学才有可能在人的心灵和历史中占据一席之地。
《中国现代小说史》2016年6月20日
购于香港中文大学
2018年7月31日起读,2019年5月2日阅毕
2019年6月30日写
*本文以文学为题,但主要以小说为例,二者是包含关系。因为只是读后感,为表述简洁方便,未对文学和小说从概念上作严格区分。
(此文首发于微信公众号“丹枫阁文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