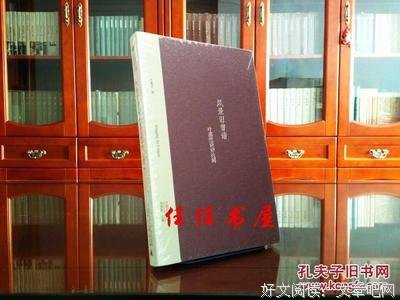
《叶嘉莹说诗讲稿》是一本由叶嘉莹著作,中华书局出版的精装图书,本书定价:38.00,页数:232,特精心从网络上整理的一些读者的读后感,希望对大家能有帮助。
●仍然没记笔记,flag
●(求保佑!)重复还好,内容也挺好。我猜比较适合入门吧……今后我要读出来、读诗了呢。
●叶先生的书真的很适合学诗词入门,特别是让人产生对诗词的热爱,让你觉得这个世界上不会有不爱诗词的人。
●深刻细腻,有自己独到的见解,又能从西方文论里吸收新的思想来指导诗词欣赏。
●同样内容多次重复情况较多,编纂体例问题,序言也承认了。引介西方文论有中体西用之嫌,浅尝辄止,术语阐释个人化倾向明显。热爱古诗词那股劲儿一上来,多少让人有点儿想敬而远之,感赞胜于引导,则过犹不及。《吟诵》一篇最佳,《陈元琛》一篇亦有可观,其余泛泛
●中国诗歌中,最重要的质素,是那份兴发感动的力量。 读叶嘉莹的第一本。 陶渊明是以心托物,杜甫是以情注物,李商隐是缘情造物。
●不如08年的版本,字太小 。叶先生的书是好的,附的讲座录音很好,可以充分感受先生对诗歌的激情。 叶先生是如此美好的人!
●一些讲演的合集,编排得不是很有系统,水平有些参差不齐,多数还行吧。有两篇看得不舒服。还有还有,这个系列内页略显花,个人感觉有些艳俗。
●古诗十九首。老杜越品越觉得好,难得。李商隐再认知。文学历史不分家啊得。
《叶嘉莹说诗讲稿》读后感(一):叶嘉莹说诗讲稿
《叶嘉莹说诗讲稿》,叶嘉莹著,中华书局,2015年1月第1版。叶先生九十高龄,弦歌不缀。并非只有著书立说才是学者,普道弘法功德可能更大。因此,老师在学校里讲课讲得好才是王道,在核心期刊上发论文反而是小道了。不过,正因是讲座合集,难免有重复之处。重点处反复看几遍也是好的。
《叶嘉莹说诗讲稿》读后感(二):兴发感动——中国古典诗歌与生命之联系
版权归作者所有,任何形式转载请联系作者。 作者:陈恰明-(来自豆瓣) 来源:https://www.douban.com/doubanapp/dispatch?uri=/review/9425486/ 读叶先生的书,总感觉读的不只是文字,更不仅仅是一门学问,而是一种生命的状态。就像叶先生的老师顾随先生说过:“一种学问,总要和人之生命、生活发生关系。凡讲学的若成为一种口号或一集团,则即变成一种偶像,失去其原有之意义与生命。”所以,凡大师者,必不全系于知识,而关乎于情怀。读完《说诗讲稿》,最强烈的直接感受是这位老太太和古典诗歌之间有了一座桥梁,他们之间的沟通是畅通无阻的,这座桥是生命之桥、是感动之桥。 在这本书中,叶先生提到了衡量中国古典诗歌好坏的一个标准——兴发感动。钟嵘《诗品》有言“气之动物,物之感人,故摇荡性情,行诸舞咏”,诗的作者首先要能受到外界的兴发感动,其次他要能将这种兴发感动通过诗歌传递给读者,让读者很好地感受到这种兴发感动。杜甫《曲江》二首中有“穿花蛱蝶深深见,点水蜻蜓款款飞”两句,作者对于“穿花蛱蝶”、“点水蜻蜓”的喜爱之情,可以说是溢于言表,作者看到眼前之景而受到兴发感动,又将这种感动写成诗很好地传达给了读者,实为好诗。对于“兴发感动”这一标准的提出,并不是突兀的,而是叶先生对从诗经时代的“赋、比、兴”传统,一直到后世的古代诗歌文论的一个整体的研究,可见叶先生古典文学功底之扎实。 中国古典诗词的兴发感动,体现了古人对于生命、生活强烈细腻的感受,这实在令我们今人感到惭愧。“露从今夜白,月是故乡明”这是诗人对于兄弟和故乡浓浓的思念之情;“山回路转不见君,雪上空留马行处”这是诗人送别友人后依依不舍,望着雪上留下的马蹄印久久不愿离去;“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这是诗人对于弟弟和天下人美好的祝愿。这些是古人对于生命的感悟,对于生活的热爱,这足以引起我们今人的反思。 值得一提的是,在对李商隐诗歌的意象进行阐释时,叶先生引用了大量西方文论,这给我们理解古典诗词提供了一种新的可能。但更需要注意到,中国古典诗词植根于中国悠久的社会历史,有其特殊的成长土壤,所以并不是所有的西方文论都适合用来对中国古典诗歌或者其他古典文学体裁进行阐释。诗中特别提到了“作者原意谬论”这一说法,叶先生则认为这一观点“以为作者不重要”并不适合对于中国古典诗歌的解读。所以,对于古典文学的学习,既要拓展思维吸取西方理论知识,但同时对于不同文本的解读,要能够进行甄别、选择,不能千篇一律、按图索骥。 总体看来,整本书对于古典诗歌的解读融会了中西古今文艺理论,能够拓展读者思维,内容深刻但不深奥,语言深入浅出,唯一不足可能是因为本书是通过对讲稿进行整理而编成的,所以各章有些内容是重复的,但不影响整体阅读,适合喜欢中国古典诗歌的朋友进行阅读。By the way,有兴趣的朋友可以去网上看叶先生的吟诵视频哦,更加能够感受到诗歌与生命之间的联系。
《叶嘉莹说诗讲稿》读后感(三):什么样的诗才是好诗?
“鱼跃练川抛玉尺,莺穿丝柳织金梭。”如果按照我们现在学习写作的方法和观念,这句诗应该算是一句佳作,因为这里面含有丰富、具体的形象和多重修辞手法,语言上又清新华美,不禁让人眼前一亮,感叹其灼灼文采。然而中国古典文学研究专家叶嘉莹先生在《说诗讲稿》这本书中却说:“这首诗不是好诗,虽然大家老说形象思维,但不是有了形象就是好诗,如果你用的都是僵死的形象,你永远写不出使人感动的诗篇。因为这个作品没有生命,作者没有感动,至少他没有把他自己感动的生命传达出来。”
那么判断一首诗歌的重要标准是什么呢?叶先生很干脆的给出了答案,那就是作者是否做到了“情动于中”。“说到一首诗歌的好坏,先要看那作诗的人,是不是内心真正有一种感动,有要说的话,是不是有他自己真正的思想、感情、意念,还是没话找话,在那里说一些虚伪、夸张的谎话。”也就是说诗歌应注重一种兴发感动的作用,而这种作用又是通过“赋、比、兴”这三种手法表现出来的。
1、 应物斯感
《文心雕龙•明诗》说:“人禀七情,应物斯感,感物吟志。”我们人类各种情感,都是在看到世间外在万物的千变万化后引发而来的。如李后主的小词“林花谢了春红,太匆匆。无奈朝来寒雨晚来风。”春天,满林绚烂的春花,婀娜多姿、争奇斗艳,可是它们却禁不起时间的考验,转眼间竟然满树的鲜花都“谢了”,留下一整片的凋零。花期如此短暂,美好的事物如此容易逝去,实在“太匆匆”,太令人惋惜、哀叹!这首词里如果说“林花谢了春红”是外表所见的现象,那么“太匆匆”则是诗人内心不假思索、不假掩饰的悲哀和感叹。
钟嵘的《诗品序》说:“气之动物,物之感人,故摇荡性情,形诸舞咏。”宇宙之间有阴阳二气,就是因为阴阳二气的变化,感动人心,所以就“摇荡性情,形诸舞咏”。北宋欧阳修有诗云“雪云乍变春云簇,渐觉年华堪送目”。春天来了,天空中均匀的雪云化开了。“雪云乍变”成了“春云簇”。“簇”是一团一团的,一堆一堆的,柔软得像一团团雪白的棉絮,在柔和的春风中悠闲地漂浮着、闲荡着。放眼望去,就会发现一年中最美好的季节来到了,最美丽的景象呈现在了眼前。无论是山、水,还是树木、花鸟,还有一切的颜色、一切的光影,都随时在转变,因此,作者说“渐觉年华堪送目”。这同样也是大自然中的物的变化对人的情感产生的作用。
陆机的《文赋》中说:“瞻万物而思纷”。我们自己看到万物的形象就会引起内心情绪的纷纷感动。是什么样的感动呢?是“悲落叶于劲秋,喜柔条于芳春”。我们看到草木的衰落,内心就随之悲哀,看到春天的草木欣欣向荣,内心就随之欢喜。于是,我们的内心就真的有了兴发感动了。作为一个人,我们如果连鸟兽都欣赏、都喜爱、都关怀,并将它们写进了诗里,怎能对跟自己同类的万物之灵冷漠呢?跟我们更切近的,更值得我们关心的是什么?当然是人类!
因此,上述所提到的“物”,在叶嘉莹先生看来,不仅仅是指大自然中的“物象”,比如草木鸟兽,还应指人世间的事物,也可称为“事象”。
2、 赋、比、兴
叶嘉莹先生说,中国的诗歌原是以书写情志为主的,情志之感动由来有二:一者由于自然界之感发,一者由于人事界之感发。至于表达此种感发的方式则有三,即赋、比、兴,也就是诗歌的作法。
《诗大序》说:“诗者,志之所之也,在心为志,发言为诗。”如果我们心里有诗情,有内心的感动,但没把它写出来,那就不是诗。我们要表达内心的感动就需要落笔成诗。
那么,当我们作诗时,就可以用“赋、比、兴”这三种方法。
“兴”是完全自然的感发,是由物及心的过程,是因为听到或看到外物的景象,然后才引起来的一种感动。如《诗经》中的《关雎》说:“关关雎鸠,在河之洲。窈窕淑女,君子好逑。”这里就是听到一对对的美丽的鸟的叫声,看到这些水鸟都有自己的伴侣,于是,就产生了对恋人的思念。
“比”是经过诗人自己的理性的安排,是由心及物的过程,是内心中先有一种情意,然后经由诗人主动安排,找一个形象去表现的。如是《诗经》中的《硕鼠》说:“硕鼠硕鼠,无食我黍。三岁贯汝,莫我肯顾。逝将去汝,适彼乐土。乐土乐土,爱得我所。”这里是借老鼠来讽刺那些剥削的人。诗人内心中先有一种对剥削者的痛恨的那种恶劣的印象,然后才用老鼠作比的。
而“赋”是“直陈其事”,就是平铺直叙,不需要一个外物的鸟兽草木的形象,即心即物。“中国作文法,常常说你要用形象思维。于是大家都用形象思维,没有形象也非找个形象不可,即使那个形象已经死掉了,也要找个形象在那里。”事实上,“写作不在于你用了什么方法,重要的是你用什么样的叙述方法把你的感动传达出来。” 比如《诗经·将仲子》说:“将仲子兮,无逾我里,无折我树杞。岂敢爱之?畏我父母。”这是一首爱情的诗歌,是以一个女子的口吻来写的。这里没有鸟兽,也没有草木,就是铺陈直述。其中,“将”和“兮”都是表示发声的语气助词,没有实际意义。但我们都知道,说话的口气十分重要。诗里用这两个虚字,就将语气完全缓和下来了,表达出了这位女子与心爱的男子分别实属无奈的感慨,亦使读者为之感动。
因此,作诗是要“情动于中而形于言”的,用什么方法不重要,重要的是要有“作诗的感动”,并用言辞来表达这种感动,再向读者传达出这种感动,这才称得上是成功的诗。
《叶嘉莹说诗讲稿》读后感(四):陶渊明、杜甫、李商隐三家诗是如何用“物”的?
钟嵘《诗品序》云:“气之动物,物之感人,故摇荡性情,形诸舞咏。”又说:“若乃春风春鸟,秋月秋蝉,夏云夏雨,冬月祁寒,斯四侯之感诸诗者也。”这是说自然界变化足以感动人心的种种因素,将这种感动传达出来,即可为诗。
中国古典诗歌研究专家叶嘉莹先生也强调:“我们认为诗歌最基本的衡量标准,第一是感发生命的有无,以及是否得到了完美的传达;第二是所传达的这一感发生命的深浅、厚薄、大小、正邪。”叶先生研究诗歌,十分注重“物与心”的关系,即“形象与情意”的关系,因此,在她的《说诗讲稿》第二部分中,深入探讨了中西方关于形象和情意之关系的理论,并以此为依据,对陶渊明、杜甫和李商隐三位杰出诗人的创作特点进行了详细地分析及比较,内容讲解深入浅出,语言表达平易近人,令徘徊在古诗词门外的我们终于“云开见日”,并可以鼓足勇气扣起古典诗歌的大门。
1、 中国诗歌和诗论的特点
1、 中国传统的诗人,他们诗歌的艺术风格,与他们情意中所表现的作者人格,都往往结合在一起,有密切的关系。陶渊明之不同于谢灵运,李太白之不同于杜子美,都是要结合作者的性情人格,才能对其艺术成就与风格作出正确的判断。
2、 中国诗的声律虽然有固定的形式,用字和句法也有习惯的传统,但却并不是千人一面没有差别。真正伟大的诗人便是要在这种相似的传统中,创造出自己不同的风格,传达出个人独特的情意。而好的评赏人也就善于从这种相似而又不同的作品中,分辨出其间精微细致的差别。
2、 陶渊明、杜甫、李商隐诗的特点
1、 从意象与情意的关系上看:
陶渊明的诗是“以心托物”;杜甫的诗是“以情注物”;李商隐则是“缘情造物”。
陶渊明所使用的意象,取材多出于现实中的“可有之物”,但因陶渊明是一位平实质朴中又见深微高远的人,同时也视精神胜过物质的人,他诗中活动着的,常常是事物的概念而非实体,诗中表现的事物也往往只是遗貌取神的抒写。因此,他的诗中没有一句是刻露的写景咏物之作。如他《饮酒之四》中的诗句“栖栖失群鸟,日暮犹独飞”,这只鸟不是一只具体的能叫出名字的鸟,而是一个概念而已,目的在于表达自己的内心感受或体验。所以,陶渊明诗中意象与情意的关系是“以心托物”,是把满怀激情托之于他所选择的事物概念之中来表现。
杜甫则不然,他最大的特色在于极其关心留意现实,以最大的勇气面对现实,以最大的天才叙写现实。他所选写的事物,多取材于现实中的“实有之物”。他不但情感丰富、饱满、热烈,不仅具有强烈的家国情怀,关心人类的命运,也会对大自然的一草一木一花一鸟投注感情,给与他们关怀、给与他们同情,悲它们之所悲,喜它们之所喜。如杜甫的《秋雨叹》中说:“雨中百草秋烂死,阶下决明颜色鲜。”秋风中百草已凋零枯萎,阶下的决明却依然顽强地生长着,在瑟瑟秋风中毫无“褪色”。而接下来,杜甫面对这枝翠花鲜的决明,不禁担忧起来,因为“凉风萧萧吹汝急,恐汝后时难独立”,作者看到了这寒冷的秋风这般肆虐,担心它也会像百草一样很快就承受不住了。但“我”这一介报国无门,自身难保的书生,却又帮不了你,只能临风为你感慨,为你哭泣啊,“堂上书生空白头,临风三嗅馨香泣”。由此可以看出,杜甫诗中的形象与情意的关系是“以情注物”,是因了感情的注入才使事物意象化的。
李商隐是一位形象化、意象化的大师。陶、杜诗中的意象无论如何丰美,对作者来说,仍不过是自然而言的流露。而李商隐的诗却是作者对于意象的有意制造和安排。有时他所表现的,就是一片错综繁复的缤纷意象,这与他先天资质禀赋和后天的遭际经历加之隐约幽微的表现方法均有很大关系。因此,只有那些非现实的,又带有恍惚迷离色彩的事物,才能表达出他那份独特的幽隐之情。比如《锦瑟》诗中“沧海月明珠有泪,蓝田日暖玉生烟”,李商隐就是这种虚幻的,朦胧的意象来抒发内心悲苦和一生的遗憾。因此,可以说李商隐诗中形象与情意的关系是“缘情造物”。
2、 从章法上看:
陶渊明以“任真”为宗,表现于或层次之平叙,或心念之流转、跳接;杜甫是感性、理性兼济,纵使处于感性的联想发为突然之转接,也依然不忘理性上作先后之呼应;而李商隐则往往以一些意象的错综并举为主,有时在首尾发展之际略微作理性之提契。
陶渊明诗的特色是:用最简单的词汇来表达最幽深繁杂的情思。元遗山在他的《论诗绝句三十首》中,就用了这样的一首诗拉埃形容陶渊明,“一语天然万古新,豪华落尽见真淳。南窗白日羲皇上,未害渊明是晋人。”诗人写诗难免不雕琢、修饰,连李白、杜甫尚且不免于用力著迹,只有陶渊明能跳出修饰造作,剥去铅华腻粉,只留下真醇简净,以他本来的质地与世人相见。陶渊明写诗是永远都不用技巧的,这是最高的境界,是他心思意念的自然流转。
杜甫的诗是有安排的技巧的,是有功力的,所以他的诗对后世影响最大。在他的诗中,既可以更清楚地看到杜甫在章法结构方面安排和组织的功力,也可以看到他在形象与情意之间的强大的感发生命的活力。他总能将感性和理性结合得很好。如“堂上书生”和“阶下决明”遥遥相应,这里面既有理性的安排和呼应,同时又有感性的感发和联想。
李商隐诗的特色则是以理性为提纲来组织一些非理性的形象。如《锦瑟》的前两句“锦瑟无端五十弦,一弦一柱思华年”,这是整首诗的总起;而末二句的“此情可待成追忆,只是当时已惘然”,则可以看作是诗的总结;至于中间四句的“庄生晓梦”、“望帝春心”、“沧海月明”、“蓝田日暖”则是四组并列的难以用理念解说的形象。从整首诗来可以看出,李商隐正是以理性为提纲来组织非理性之形象的。
3、 从句法上看:
陶诗多用古诗平顺直叙的句法;杜诗有时只掌握感性重点,在句法上表现为颠倒或浓缩;李诗则以理性之句法来组合一些非理性的词汇。
《叶嘉莹说诗讲稿》读后感(五):为什么李白的《玉阶怨》比谢眺和虞炎的《玉阶怨》写得好?
中国古典诗歌研究专家叶嘉莹先生在说:“评判一首诗歌的好坏,应当看作者是否‘情动于中’然后再“形于言”,这是诗歌孕育出来的一个重要的素质。”叶先生研究诗歌十分注重“物与心”的关系,即“形象与情意”的关系。基于这一点,叶嘉莹先生在《说诗讲稿》第三部分,从“形象与情意的关系”来为我们解读了三首不同诗人创作的同一种题材的诗歌《玉阶怨》,引领我们在赏诗的道路上发现了别样的美。
众所周知,中国古代妇女受传统封建文化的约束和影响,没有地位,没有主动权,一生都在被选择,被统治,她们内心深处潜藏着的幽怨和悲苦无从诉说。因此,古代一些男子写了很多代言体,替她们抒发内心的这种情愫,这就是闺怨诗。
《玉阶怨》即为闺怨诗。“玉阶”是很珍贵、很美好的玉石做的台阶,像大理石、汉白玉,所以叫“玉阶”。“玉阶”是闺中的,她的园庭之内的台阶。虞炎、谢眺、李白都写过《玉阶怨》,但诗作的质量却有着云泥之别。
一、“拂”、“度”本佳字,误用拙文生
虞炎的《玉阶怨》
紫藤拂花树,黄鸟度青枝。
思君一叹息,苦泪应言垂。
叶先生认为这首诗中的“拂”和“度”本是两个非常妙的字,如果用对了地方就会尽显诗情和文采。然而这两个字用在这首诗里却极为不恰当。
法国的小说家福楼拜曾经给莫泊桑写信,跟他说过所谓的“一语说”,就是你要找到你所要传达你的思想感情的最恰当的那一句话,不是最美丽的那一句话,是最能够真诚地表达你的思想感情的那一句话,适合于那个物性的那一句话。
“紫藤”是指紫色的藤萝花,是一种花树里的专类名词,是具体的。而“花树”却是泛称。“紫藤”也是花树的一种。因此,作者把一个专指的名称与一个泛称的名称结合在一起,这在诗歌里面就没有产生一个目的性的作用,更没有一个固定的引导读者去感动的方向。况且,“紫藤”和“花树”之间用了动词“拂”,怎么“拂”呢?“藤”这种植物一般给人的印象都是紧紧地缠绕,一直向上爬,用“拂”显然不恰当,传达不出什么感动,本来也没有什么感动可言。
“黄鸟”是黄莹,在树枝间来回穿梭,飞来飞去,如果用“度”,给人的感觉好像在慢慢地踱步,而鸟在树枝间像散步一样地走动显然不合常理。因此,这个“度”字用得也非常失败。
因为前面两句诗给读者的形象和描述是不恰当的,不能引起读者一种感发的感动,所以后面两句“思君一叹息,苦泪应言垂”,纵使作者用了看似十分悲苦的文字,但却很难把读者带入这种痛苦之中,因此这首诗不是一种好诗。
二、丝线手中走,无语幽怨生
谢眺的《玉阶怨》
夕殿下珠帘,流萤飞复息。
长夜缝罗衣,思君此何极。
叶先生认为,这首诗中的“夕”、“下”、“息”用的非常妙。
古人说“有约不来过夜半”。如果有约会,他早就应该来了,已经到了黄昏——“夕”了,这个人还没有来,所以一直在等待的佳人只能将珠帘放“下”了。
这里的“夕”和“下”都产生了一种要传达他的感情意念的正确作用。诗人要写这个女子的孤独寂寞的怨情,所以用“夕”,也就是“黄昏”。这个“黄昏”就引起了后边所有的长夜漫漫的孤寂之心。这里是有一个方向在引领你的。“下”字用得妙在于,把窗帘打开代表有希望,而将窗帘拉下,意味着天色已晚,希望也随之断绝了,于是这个“下”字就隐约地带领我们向这寂寞孤独的怨情前进了。
“流萤飞复息”中的“息”字,叶先生认为用得十分生动准确。如果是普通的鸟,就应该用“飞复止”了,只有萤火虫的光火才能够一亮一息。而就在这一闪一灭之间,衬托出了那夜的漫长、夜的黑暗、夜的寂寞。所以,每一个光亮的闪动,就都将她思君的怨情引发出来,不禁让人为之感动。
虽然长夜漫漫,但这位女子并未休息,而是继续缝她的衣服。手中那绵长的丝线,那细腻均匀的动作,无不代表了对丈夫无边无尽的思念,因此说“思君此何极”,对丈夫的思念何时才能终止啊?
叶先生认为这首诗好,是因为前三句结合起来归纳到思君的感情。而他前面所叙写的情景是有感发的力量的,是把我们带到感情之中的,所以就比虞炎的诗好多了。
三、阶下寒露侵,秋月意转浓
李白的《玉阶怨》
玉阶生白露,夜久侵罗袜。
却下水晶帘,玲珑望秋月。
叶先生认为李白的这首诗中的“生”字用得特别妙,因为“生白露”,是说这白露的露水越来越多,越来越浓,天气也越来越寒冷,夜也越来越深了。在这样的一个夜晚,如果这位女性没有一直站立在玉阶之上,如果只呆了几分钟,怎么会感受到“生白露”,怎么白露的露水会沾到鞋袜上呢?于是,这一个“生”字就带给读者一种感动,这是一个情意绵绵的女子,这是一个望穿秋水的女子,这是一个让人怜爱的女子。
这首诗当中的“秋月”是和“玉阶”、“白露”结合在一起的,是寒冷的,肃杀的,寂寞的,是秋天的月亮,秋天的月亮带给人一种高远、寒冷的感觉。在这一样的一个秋夜里,一位思君的女子在园庭里久站后,回到寝室拉下窗帘,而这窗帘是“水晶”做的,玲珑剔透、光洁明亮,透过它,这位女子看到了遥远的天空中月亮里边那片光影,如同一块玉雕的玲珑般灵巧通透,多美纯洁、多么美好!
叶先生认为,李白的这首诗,已经从写实进入到一种象喻的境界,已经把这个女子思君的怨情从现实更提高了一步。她自己的怨情,她所怀念的那一个对象的品质,是那样高洁,那样光明,那样美好。整首诗没有一句“思君”之语,但却全篇贯穿着“思君”的怨情。而这一份怨情之中,已经不只是思君的怨情了,还有一种对崇高的、光明的、皎洁的、美好的品质的追寻和向往。李白已经把他的诗提升到了一个更高的层次,因此说这首诗相比而言是最好的一首《玉阶怨》。
由此可见,一首诗的好坏,与诗人的感情、诗的内容、表现形式及表达出的每一个字的作用和质量都息息相关,当然最重要的还是要“情动于中而形于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