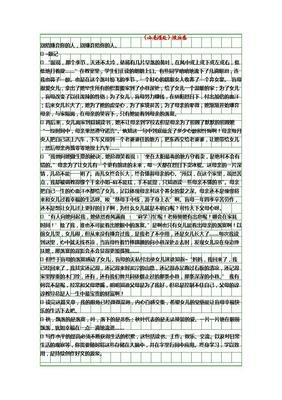
《走向人生深处》是一本由刘再复 / 吴小攀著作,中信出版社出版的平装图书,本书定价:28.00元,页数:248,特精心从网络上整理的一些读者的读后感,希望对大家能有帮助。
●刘先生把他的人生划分成两个部分,48岁前和之后的生活。 第一次知道刘再复先生的名字是3月份在准备毕业论文的时候,读到他的《罪与文学》。“忏悔意识”本身就是一个比较复杂的概念,是宗教和文学杂糅之下的作者情缘,而这个复杂的概念在他的阐释中让我明晰许多。《罪与文学》和《走向人生深处》其实都具有一个相似之处,那就是总会给我一种与刘先生面对面坐下聊天的亲切感。 在这本书里,他就像一个老者一样,娓娓道来。这本书是我半个月以前看的,现在脑海里有一句话还是很清晰。那句话大概是这么讲的,决定一个人的日子其实是大学毕业之后的生活,只有离开学校依然没有放弃学习的人才是最值得敬佩的人。恰好今年大学毕业,虽然还有三年的研究生生活,但是这三年我想做一些自己想做的事,学一些想学的东西。
●刘再复的东西,看多了也容易腻味,但不可否认的是他对文学的理解至少给了我很大帮助。
●好几年前的书了,对于政治文化各方面,很诚恳的发表了答者的观点,很有意思,今天翻出来再看还会有新收获
●如果找我谈话,我比刘再复谈的更深入。整个访谈都是翻来覆去那几个问题,吴小攀也极不专业,根本没问出什么东西。访谈中的提问者应好如解剖刀,切碎切碎再切碎。而那刘再复的回答,基本算是拾人牙慧。李劼、史铁生、李泽厚的话被刘再复扩写加工。于是有个这本访谈者们名利双收的书。
●走向人生深处的那一种精彩
本书用访谈的形式提供了刘再复的一些个人背景资料,以及他的思想走向,有一定的参考价值。近些年来刘再复的部分书得以在国内出版,也可以说明某种氛围。最近还看了他的《师友纪事》,其中有些篇章涉及到中国科社院的一些官员、学者,有一定的史料价值。
《走向人生深处》读后感(二):向往
早前看査建英的《八十年代访谈录》,采访的都是一代文化标杆,其中就有刘再复。可惜当时看完只觉得疏离,似乎过于理性的文字并不能通达人心。又想起柴静很久以前的文章,满满的一片温柔,尽管现在的她已经具备足够的深度和社会关怀,但你会察觉到她骨子里还有一股柔软,可能只有这种感性与理性的结合才能衍生最美妙的气质。
看《八十年代》看不出这种味道,看这部“心灵自传”,才感受到这种美妙。个人觉得这结合必须经历几个转弯才能取得,正如柴静从《夜色温柔》到直击非典,到更后来的新闻调查。对于刘再复,他在这本“心灵自传”里说1989年把他的人生划分成了两个时期,像是“瞬间可以让生命更换一种存在形式”。
好在这一次的更换让他的生命走向了自由和纯粹。什么是自由?刘再复说自由意味着独立地挑起一切重担,意味着自己开车,自己买菜……他也曾想过逃离,想念在群体软翼下“取暖”的日子。
不可否认,对于我们,这日子同样一去不复返了。逃离也并不能获取自由。面对现实的逼迫,你必须走向自觉才能获得重生;一旦自觉,就能摆脱很多繁复而变得纯粹,由此获得一种沉浸的自由。
《走向人生深处》读后感(三):思想者的灵魂不老:要理解这个时代,必须理解刘再复
*转自《信息时报》2011年3月13日C4版*
思想者的灵魂不老
阮直
春节前夕,在网上买到了《走向人生的深处》一书,随意一翻即手不释卷了。这可以说是一部为全面了解刘再复的读者准备的导航之书,更是一部走近刘再复的开卷之书。
《走向人生深处》再复了我的“再复情结”。在改革开放的上世纪八十年代,凡是喜欢文学或从事文学理论研究的,很少有人不知道刘再复。我就是因此成为刘再复做主编时期的《文学评论》的忠实读者,并至今完整保留着1986年至1988年共12本的《文学评论》;1986年买到了2.85元的《性格组合论》,1988年用4.35元买到了《文学反思》。时隔24年,如今又买到《走向人生深处》一书。看到书中刘再复的照片,他已届七旬,但思想者的灵魂是不老的。
“从文明的结晶到社会建构,从文化‘伪形’到人性的异化,从文人立身态度到现代知识分子天职,从宗教情怀到终极认知,从文学的自性到历史的反思,从‘文革’荒唐到事后自审,从大国的风度到中国的崛起,从讲述哲学与贵族精神。”访问者凭借着对叙述者思想的熟知,循着刘再复的人生轨迹,从福建到北京,再从北京到科罗拉多,不仅展示了刘再复截然不同的两次人生,更重要的是揭示了在两次人生中其人生观的嬗变,从而将读者一步步导入刘再复心灵深处。
刘再复第二次生命转移后凤凰涅槃般的再生,接轨到了一种更纯粹的学术境界上,我们看到了一个躲开“斗争场”的消耗,静下心来平静思索的哲人。在人生的最深处,刘再复不仅再次安妥了自己的灵魂,而且源源不断地奉献出一部部独立思考后的精神结晶:《告别革命》、《罪与文学》、《独语天涯》、《共悟人间》、《红楼梦悟》、《双典批判》……
要理解这个时代,必须理解刘再复;要理解刘再复,必须理解他的两次人生。当一个时代淡忘了一个伟大的思想者时,这一定是被欲望主宰的时代;当一个时代还有人去记述思想者灵魂轨迹时,这还算是一个不坏的时代。
《走向人生深处》读后感(四):用八年时间与刘再复“谈”出一本书
*转自《南方日报》2011年4月17日A12版读书周刊*
用八年时间与刘再复“谈”出一本书
吴小攀
2001年的时候,我从一个跑区街新闻的记者转为文化版面的编辑,因为所在部门没有配置记者,因此,虽然是做编辑,但我还是经常主动做一些访谈,这一做法坚持至今。正是在这种坚持中,2002年我偶然得到了采访刘再复的机会——— 在香港大学读博士的我的同学告诉我刘再复在城市大学讲学的消息,这触发了我前往采访的念头。
2002年9月10日,在香港等了三天以后,终于接到刘再复的电话,确定接受我的采访。按一般情况,这样的当面采访最多不过两三个小时,谁知道一谈就是八个小时,中间还吃了一顿晚饭。
刘再复是上世纪80年代文学变革时代的弄潮儿,曾任中国社科院文学所所长和《文学评论》主编,其“文学主体论”、《性格组合论》曾在文化界掀起波澜;出国后,他以《告别革命》(与李泽厚合著)及一系列散文随笔创作,在更广阔的华人世界影响巨大。如今,“八十年代”已经几乎成为一个专有名词,在叙述那一段风云变幻的变革年代时,刘再复是经常被提到的一个名字。
近些年来,刘再复的著作在内地的出版成为热潮,主要有三联出版社、中信出版社、福建教育出版社三个系列数十本书。要了解刘再复的学术思想,可以通过阅读他这些已经出版的作品获得。如果要出一本有关他的新书,必须要有新的视角和价值。几经商量,终于确定,从知人论世的角度,以时间为经,以思想为纬,做一本关于刘再复本人经历的访谈书,以供对上世纪80年代文化及刘再复本人感兴趣者作参考,可以说是一新思路。
刘再复家在美国,经常受邀到欧美及港台讲学,因此,为了完成出这本书的任务,除了几次见面交谈及蒙他赠送一些难得一见的相关著作外,多是他打越洋电话与我联系。基本上,他都计算好了时差,在我刚好在家还没休息的时候,打电话过来。这样的通话忘了有多少次了,一般一聊就是一个小时左右,电话中我会向他请教一些问题,他详细作答,我顺手记下来;还会和他探讨书的架构和细节。他既有老派学者的谦和睿智,也有西方学人的平等民主,每次打完电话,我都禁不住想,读书的时候每堂课是45分钟,觉得很漫长,为什么和刘再复通电话时间却过得这么快?
通过这样的隔空谈话,再加上阅读刘再复的原著,经过一段时间的思考,以及一些朋友的帮忙,删删削削,终于拟定了100多个问题,打印出来,寄给远在美国的刘再复。2009年12月,差不多都忘了这件事的时候,突然又接到刘再复的电话,说是所有的问题都已用笔完成回答,要寄回给我编校。不久,就收到差不多一尺厚的手写复印稿,看得出是用水写笔写的字,一字一句,绝无苟且,整洁从容。
即便如此,刘再复仍精益求精。书稿输入电脑后,经初步编校,再电邮到美国刘再复处,他继续耐心增删修改,再寄回给我二校,稍作修订后,再寄回给刘再复。他说,我们不要随随便便,要出就把书出好。书的出版时间因此一拖再拖。2010年3月,刘再复恰好又应聘到香港城市大学做讲座教授,我便又到香港去和他面谈,再作补充采访。
最后,历经八年的访谈稿交由出版社编辑,经过他们重新设计调整编排,书稿在国内国外来来回回转了几趟,从形式到内容,一改再改,便成了现在的模样。
刘再复在最后成书——— 《走向人生深处》的扉页上题写着:“人格是人自身的乳汁,它取之不尽并会滋润整个曲折的人生。”可见,他对于人格的重视。因为这本书的访谈和出版,我从与刘再复的频繁交往中深受教益,也因此明白,人格的表现不在于你说了什么,也不在于你做了什么,而在于你如何做。
《走向人生深处》读后感(五):叩问刘再复的两次人生: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学术人生,于历史是势,于个人则是命。
*转*
叩问刘再复的两次人生
■ 傅修海 (学者)
翻读刘再复的访谈录《走向人生深处》,第一感觉是“夜阑卧听风吹雨”,唯有倾听方能入耳入心入神。对我这样的小辈而言,刘再复的人生跌宕生涯和学术开阖气势,都只能是一种向往。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学术人生,于历史是势,于个人则是命。刘再复的第一人生,便因此而格外笼上些迷离斑驳的尘烟,不由得令人扼腕惆怅。
然不管这段时光如何,第一人生的苦难与波澜,总归是酿成刘再复此后断裂和超拔的始基了。既如此,作为读者,我所欣赏的便是他的反思深度与平和态度。告别哪些和远离什么,固然是个中应有之意,但毕竟都是一种对待的差别,并非看透。可一旦有所决绝,由此而来的就是更令人欣喜的、对自我此身的发现和坚守,对彼岸的沉思和关照,所谓“天上星辰,地上道德律”一类的敬畏。借用书中刘再复的话说,那便是其“立身态度”的变化,即本书采访者吴小攀关注的“人生观的变化”。
刘再复在磨难之后选择和认定了“存在先于本质”,他说:“既不纠缠于过去,也不执著于未来,不再制造幻想与乌托邦,只充分活在当下,就在当下感悟真理,创造存在意义。”这便是他的放下和舍得,尽管其间饱含着无奈与被动,更粘连着将自我剥离某种母体的血肉相连的苦痛。但唯有如此,他便没有了许多海外潇洒者的摇摆和高明,彻底获得自我放逐和游走的淡定,并不时以独语天涯的明慧而直抵人类基本精神的内囊深处。在我看来,刘再复的这些“闲敲棋子落灯花”式的心灵叩问,无疑是一种精神清洁。
在书中,刘再复说国外十几年的生活,于他而言最大的收获有两项:“一是扩大了眼界”,一是“赢得了一个自由表述的个人创造空间”。他更把收获简括为“三宝”:自由表述、自由时间和完整人格。一种得到的珍贵和喜悦溢于言表。没有种种形态各异的精神文化、现实生活等等的重压,又怎么会有李贽的童心说和六祖慧能的顿悟呢?
重要的恰恰不在于某种得到,而在于如何看待和介入这些得到。以自由为例,刘再复便独具一格地向往和选择了“主体间性”的出处,如在文学艺术中寻找美善,强调其精神内涵和人性深度;于宗教则止于敬畏精神(大慈悲、大谦卑),“喜欢孤独的上帝”;对社会人生注目于关怀,关心思考人间的世事沧桑。然而,如此种种的“间性”,流露的绝不是他的何等悠游,而是展现了他在人世美好的叩问旅途中的温爱与从容。
人生最苦是我执。饱受片面进化论滋养的中国现代人,所执何其多。刘再复从第一人生到第二人生,仍都不免有所执。“写作”与“禅”结合的思想自救,不仅让他明白“梦里已知身是客”的灵动,也由此得以进入“一晌贪欢”的智慧的“挥洒”,返归贵族古典,沉潜原形文化,散淡禅意人生。这便是刘再复的第三人生。
他认为人文学术有两种方式:“一种是主观性的,它是在具体的历史语境下和现实展开对话;一种是客观性的,那是对其精神价值进行具体把握。”进入禅的内核后,作为一个思想者,刘再复不但自觉把人文学术的思考奠基于客观,而且把学禅也基于“一个追求真理的过程”。不仅如此,他还强调破一切执,返归自性。所谓“一切看空了,生命更积极”。
大乘佛学的影响和禅的参悟,无疑是刘再复人生境界飞升的一大契机。但不管如何,真正让他破关而出的,当是《红楼梦》悟。刘再复坦言:“唯有进入面壁的沉浸状态,才能进入深邃的精神深渊。唯有在那里,我才能与曹雪芹等伟大灵魂相逢。”
《走向人生深处》是刘再复的精神传记,而且是一本与众不同的传记。其卓异之处,除却传主的风雨人生与智慧高格之外,还因为这是一本以纸上问答生成的传记。访问者机智、朴素和识见,带着倾听的热忱和富有思想的语言火花,牵出的不仅是叙述者串串珍珠般的智慧挥洒,更引发出了足以辅证一个时代的思想者情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