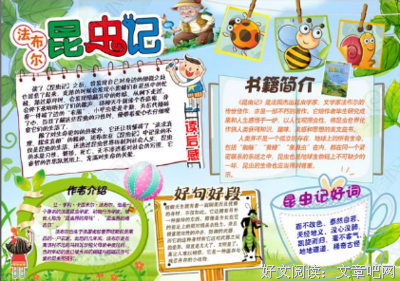
《走出唯一真理观》是一本由陈嘉映著作,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的平装图书,本书定价:58,页数:428,特精心从网络上整理的一些读者的读后感,希望对大家能有帮助。
统一场论也许可能也许不可能,但哲学肯定不提供整全的真理系统,真理是局部的,还可能随时间变化。陈嘉映给的这个判断可能会让很多人失望,多少执念在于斯。
关于陈老师,值得多说一句。这世上有许多聪明而有魅力的人,他们可能从事各种各样的事情,也许是创业、也许是从政。也许是研究经济学,干不同的事情就会有不同的知识和经验源泉,碰巧陈嘉映的源泉是哲学,在这个意义上,可以称他为哲学家,但其实,哲学家是个次要的身份。
《走出唯一真理观》读后感(二):走出唯一真理观
本书是陈嘉映先生选编自己于2007—2018年间所作演讲、访谈与评论结集。 有不同的道,从前有不同的道,现在有不同的道,将来还有不同的道。重要的问题不是找到唯一的道,而是这些不同的道之间怎样呼应,怎样交流,怎样斗争。你要是坚持说,哲学要的就是唯一的真理体系,那我不得不说,哲学已经死了。 哲学,尤其今天的哲学,不是宣教式的,不是上智向下愚宣教。我们之所求,首先不是让别人明白,而是求自己明白。 “我个人想要的是,认真思考,认真表述这些思考,召唤爱思考的人来一道思考。
《走出唯一真理观》读后感(三):短评写不下了
“用厚重的生存托起反思。”关于反思和过度反思的讨论对我挺有启发的。还有一个困扰我蛮久的问题,大概是如何把很专业的知识普及到大众面前来减少歧义/不当的隐喻,但现在看来好像是个伪问题,往通俗方向发展和往专业性更强的方向发展本就不能混为一谈,专业领域自然有一套自己的评判标准,两者的目标不同,最关键的还是要真诚,对自己诚实。(而且“吾生也有涯,而知也无涯”,有限的人怎么能要求无限的知识呢)有一篇里陈老师谈到自己的一个学生从他身上得到的最大的东西是“您一直对我很宽容”,我也有感受到宽容。(对他人宽容太难了)“我愿补充说:没有人拥有无限的同情心、爱和耐力,所以我们要珍惜这些美好的东西,善用它们。”关于海德格尔的两篇导读好棒,准备把海德格尔的书提上日程。//关于科学的局限性读来一直很有共鸣,但至少在生物学方面,我觉得没法把研究对象完全客体化,总会牵扯到伦理问题的。
大概花了半个月的通勤时间,把哲学家陈嘉映的《走出唯一真理观》中感兴趣的文章都读了一遍,读完以后觉得陈嘉映老师真的是一个特别诚实的人,他不避讳自身的局限,不避讳哲学的局限,也不避讳人们在这个时代所能达成的事情和所能互相理解的程度的局限,谈了许多在这样一个平民时代、科学时代、信息时代我们该如何继续过一种思想的生活。我拎两个点出来讲讲好了。
1.哲学的重新定位。首先,陈嘉映认为现代哲学已经离开了曾经构建体系,甚至试图建立王国的时代。在启蒙运动时期,哲学把自身的真理观念类比于科学,认为存在一套客观且可以认识的真理体系。然而我们现在知道,作为知识体系的哲学和科学是截然不同的,因此它们的真理观念也无法类比。人类社会过于复杂,我们曾经为了追求社会和历史的唯一真理,付出了惨痛的代价,现在我们必须放下这种唯一性。虽然我们还是要追求真理,但我们必须时时刻刻将人类社会的多元和复杂考虑在内,走出唯一的真理观念。
其次,我们的哲学教育有太大的问题。即便是清北这样的学校,哲学本科院系都有太多的调剂生,很多孩子不想专门学哲学。光读本科,也谈不上有什么专业意义,哲学作为一个本科专业存在的价值是可疑的。有心学哲学,本科先学其他专业,科学类也好,人文社科也罢,借此拓宽视野,并不会耽误哲学的精进。更何况,当哲学成为一个专门领域,只有专业人士思考的时候,哲学离失效也不是那么遥远了,哲学应该吸引大家来思考,才能吸取足够多的东西。从这个角度来说,在大学开设“幸福”“逻辑”等哲学公开课,倒是很有意义的。
2.我们如何说理。我们太习惯于把说理和说服混淆在一起,也太常常把对于道理的辨析和意志的征服混淆在一起。这一点学校里的辩论比赛是非常可怕的影响,因为双方都不存在变更立场、理解对方道理的可能性,这种活动更像是古希腊的诡辩术,注重的是修辞的效果。固然说理和说服不存在泾渭分明的界限,但理清说理的细节对于我们考察思想的碰撞还是有很大的意义的。
陈嘉映提出了几种衡量说理方式的概念,一种是古典意义上“生长”,当道理的“不得不”跟对方的自我相联系,你启发对方看到了他自己身上道理的可能性时,这种说理的内化形式是有效的“服人之心”;另一种是把论证往辩护的路径去理解,不必诉诸说服别人,也就因此杜绝了其中关于影响和力量的部分。在我看来这一路径对于我们如何学会与他人的不同相处尤为重要。
两点讲完了,其实这本书很杂,是文章、讲座、对谈、书评乃至刘苏里的名家大课的讲义。海德格尔研究也是陈老师一个比较核心的关切,但让我讲我也讲不明白,感兴趣就自己去看吧。除此之外,还有些其他主题的文章比较值得一读,比如“教育与洗脑”,这其中的区别有很多大家也都熟悉了,但如果我读本科时有幸听到这样的讲座,会启发我更早地做更多思考吧。
不过也必须指出的是,这本集子里文章和访谈因各种因素有比较大的差距,比如“漫谈人工智能”就显得很业余,不应当收录进来。第三辑的好些书评也略松散,到后面就跳得比较多了。
《走出唯一真理观》读后感(五):说理之为教化
陈嘉映老师这本新书有一个美妙的地方:在这本书里,陈嘉映主张哲学应当是一种对话,他不仅从说理的层面论证了这个道理,更重要的是,书中收录的几个对话本身就在向我们展示,良好恰当的对话应该是什么样子的。好书,尤其是那些洋溢着智性美的好书,很多都具有一种自我指涉性,即它所主张的和它本身的行文风格所展示的是同一件东西,也就是老话讲的“形式与内容的统一”。你论说的是什么,展示出来的同样也是什么——关于做人,我们常说一句“知行合一”,大概也有类于此吧!
本书的几个对话里,我个人从中收获最多的是最长的那篇《“说理”四人谈》,这也是比较贴合全书主旨的篇目。以下是读过四位老师的言论之后生发的一点感想,权当对整本书的读后感。我们普通人往往缺乏条件参与这种高质量的讨论,幸好陈嘉映能把它写到书里供人观摩。我写下这些的想法,算是以某种自己的方式参与这种令人神往的交流。
1.说理与说服
四位老师在讨论中一直围绕着一个观点:说服别人——或者更直接地说,改变别人的观念——有很多方式,除了说理之外,还有宣传、欺骗、威胁等等,如果只从说服效果上着眼,单纯的讲道理其实远不如其他几种方式。这是很平实的观察,道出了人类活动的一部分真相——然而我们在日常生活中总是忽视这一点。我觉得其中部分原因在于我们总是对说理,对理性抱有过高的期望,更重要的是我们总是自以为自己是理性的。当我们采用说理以外的方式试图说服别人时,经常打着“讲道理”的旗号,以此获得正当性。网上的发言很多都以“理性讨论”开头,说出的话却少有理性的成分,这样的理性声明和教徒口中念诵的经咒没什么两样。
我总觉得,把求真性的说理看成一种说服方式,本身可能就有误解。我们把以理服人和以情动人,以权力压服人并列,仿佛道理和情感、权力一样,只是我们用来改变别人想法的工具。但这里的区别在于,情感、权力属于私人性质的事物,人可以实在地占有它,而道理是公共的,不是任何人能宣称可以独占的东西。陈嘉映在别处说过:我们并不掌握真理,但如果我们以开放真诚的心态求真,真理会降临下来掌握我们。以理服人,不是我用道理来说服你,而是我们共同服膺于道理本身,前者是在争胜,而后者才是求真。
说理不是争胜,尽管当两个人进行理论争论时看起来像是在互相较量,实际上并不是如此。求真的论辩和争胜的论辩之间的区别有点像体育比赛和战争之间的区别。我们踢足球,踏入赛场的那一刻脑子里想的就是怎么赢得比赛,但这不是我们踢球的终极目的,否则如果单纯地想打败对手有无数手段,没必要非得选择二十二个人追着一个球跑这种方式。说起来,哲学和竞技体育都是古希腊人带给人类文明的伟大贡献,它们之间本身就具有联系,并且这种相似性还能扩展到希腊文明的其他成就上——纯数学、民主政治等等——这绝对不是一个巧合。
2.说理与平等
讨论中慈继伟提出了一个挺重要的观点:我们进行说理论证,主要是为了“表达了人与人之间的平等关系,以及人们对这种关系的认同”(P171)。的确如此,这一点,即使不说是说理活动的全部内涵,至少也说出了它很重要的一个方面。我们现代人说起平等,总觉得它是启蒙和法国大革命的产物,其实平等的概念主要来源于基督教——我们的灵魂是被上帝平等创造的,尘世的不平等只是假象——而这又可以追溯到柏拉图的理念论和灵魂回忆说。柏拉图笔下的苏格拉底通过辨证的方法诱导小孩子解出几何题,意在证明小孩子和大学者在智识上其实是平等的,只不过这种平等被尘世所遮蔽和“遗忘”了。现代人理解的平等是财产和权力的平等,然而在柏拉图和中世纪人看来,这种尘世的物质的平等恰恰是虚幻的,真正的平等是灵魂和精神的平等。
说理体现的平等是一种柏拉图式的平等。我和你讲道理,是因为相信我和你一样都是理性的人。尽管我们在天资禀赋和社会关系上具有很大的不平等,但我们怀有这样的信念(毋宁说是希望):归根到底,我们是一样的。尤其当强势者面对弱势者,明明可以利用强力压服对方达成目标时却仍然选择讲道理,就是为了表达这样的企盼。尽管这样的希望大多数时候都不能实现,世俗的种种总是不免玷污说理的纯洁性,但这不代表我们要放弃希望。诚然,人与人之间有着智识上的不平等,说理虽然是通达平等的途径,但说理能力本身是具有高下之分的。有些经过说理训练的“专业人士”经常借着说理逞其才学,以智力压服人,形成“理性的专制”,而这恰恰背离了说理的初衷,是需要警惕的。
3.“专业”的说理
这就引出了一些难缠的问题:我们需要具备什么程度的说理能力?说理是越专业越好吗?或者说根本就没有“专业”的说理?《“说理”四人谈》当中,四位讨论者都是专业人士,但言谈中似乎都对学界的过度专业化倾向深感忧虑。现代生活纷繁复杂,说理时不免碰到一些知识和概念,只为专业人士所熟知,普通人很难准确地运用它们。不久前一位网红刑法教授,因为不严谨地使用了几个哲学专业相关术语,因此被不少哲学从业者(以及一些自诩哲学专家的人)批判了一通。的确,像“功利主义”这样的词,哲学专业的说法跟老百姓的说法不一样,前者显然更严谨,内涵更丰富;但如果由此就认定专业人士的说法比老百姓高明,乃至应当用前者消灭后者,实在欠妥。语言是公共的,一些概念上汇集的不只是某个专业圈子内部积累的知识,更多的是我们所有人对事质问题的关心。边沁和穆勒的功利主义观点异同是哲学课上的专题,操心禁食狗肉立法的普通人有着更紧迫的需求,这是需要体谅的。正如前面所说,虽然实际操作中未必可能,我们应当保留平等交流的信念,这样面对非专业人士不严谨的说法能多一些宽容。“我觉得你说的可能是这个意思,这里我可以帮忙澄清一下。”显然要比“你这个词用的不对,回去看书!” 更开放,更有建设性,更少学阀做派,不是吗?
我们常说说话要严谨,能够把话说得滴水不漏,让人抓不到把柄,被看作是一种优秀品质。我个人以为这一点有时被过分强调了。且不说人能不能做到说话完美无缺,就算真的把一切都说到位了,你让别人说什么?怕是除了给你鼓掌叫好就没别的了。有时候,正是语言中那些暧昧、模糊的地方激起人想要说清它的欲望,因此使得对话成为可能。借助人们描述理论时常用的建筑隐喻:言语要是严密到密不透风的地步,就会成为一座坟墓。真理性的言说则是敞开的,它邀请人们自由进出。假如真有正面意义上的“专业”说理,我觉得应该是后一种。
4.说理之为教化
四位老师最终都认为,说理论证本身很难让人们达成共识,现实中的共识往往是利益博弈乃至暴力导致的结果。通过说理,将不同群体的信念进行整合,最终融合成一个终极真理,这种想法应当被抛弃。这不免让人怀疑说理活动对现实生活到底意义何在。其实陈嘉映在对话开场白里就已经说了,说理的最大功能是一种教化。我们争论一件事的道理,不光是为了争出一个对错是非出来。庄子云,是亦一无穷,非亦一无穷,是非永远都有,重要的是参与这个过程能学到什么东西。学习哲学,乃至一切和论理有关的学问,应当修炼这样一种虚怀若谷的心态。有些人不是这样,读书把自己培训成了斗鸡式的辩者,逢人必辩,逢辩必想赢,实在是可气又可悲之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