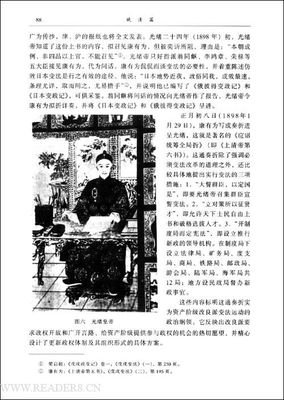
《庚子勤王与晚清政局》是一本由桑兵著作,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的精装图书,本书定价:75.00,页数:624,特精心从网络上整理的一些读者的读后感,希望对大家能有帮助。
●難得在庚子勸王的話題上有部如此豐富的專著。誠然,此書蒐羅廣博而有瑣碎之嫌。庚子勤王中在野政治力量的視角基本都被說盡了。要在這題目上再進深,不靠新史料就只能靠轉換視角。從各地督撫及督撫幕僚入手或許能再做出什麽成果來。
●#t# 详尽分析保皇会庚子勤王的活动,剖析保皇会内部矛盾、与各方势力的关系与相互影响;绪论中讨论了治学门径,切中肯綮。
●虽然保皇拥帝充满了时代的局限性,在进入二十世纪后无人不言革的大时代下更是显得沧海一粟,其内部的分歧龃龉导致的一事无成更是引人可恨叹息,但其人救国存亡的愿景还是值得称道,能动员起全球华人一齐捐款勤王,可见维新派虽然保守软弱,但终是在倔强的昂首前行着
●自以为述而不作,其实质失于琐屑,改名为史料长编更为妥帖——史有精有细,庚子勤王本就为潮流一瞬,如此宏篇,未免贪大求全,故燕赵多秦舞阳之流,但能乡野之间杀人不惭,却不能立朝堂之上。
●相比茅写的太不友好了(也有可能是题材原因),然而我蛮喜欢并献上膝盖KKK
●琐碎一点,内容很大,格局有限。 不过保皇会数年间的事,于历史不过短短一瞬!
●打开了康党后期活动新世界的大门,了解了自立会,保皇会,华侨,秘密会社的诸多关系,但属于学术中的晦涩品,有格局有观点,多处自我解释不到位给读者或有迷惑,人物介绍也不到位,一般人很难下咽。
●把极短的时间跨度内各派势力如革命党、保皇派等勤王过程中的博弈与角逐、合作与竞争给理清,是一件非常细致入微的工作,也就决定了它的难度。 桑兵在整理新旧史料,转换历史叙事,重构历史现场做的很好。也有缺陷,就是文法问题,文白交织带来的阅读体验...
《庚子勤王与晚清政局》读后感(一):另一种视角下的庚子年——评《庚子勤王与晚清政局》
桑兵先生开篇就谈:“治学途则,一为先因后创,一为不破不立,前者可以得道,后者易于成名,恰如武侠小说中练习正宗武功与旁门左道之别。”桑先生此言固然矣!在他看来,治史难,治近代史尤难,治史者不仅面临着浩如烟海的史料档案,还应该字斟句酌地揣摩史料之间的真伪含义,要有着穿越时光的敏锐眼光与数十年如一日的钻研积累。然而大多学者舍近求远,往往放弃对已有材料的深度理解,或是去追逐只言片语的零碎史料,或是去套用国外昙花一现的史观范式,这不过是畏难逃避的歧路。
桑兵先生此书便是他数十年来对已有的相关史料进行透彻研读后,从宏观方面全方位把握庚子年政局而写成的恢宏巨著。全书虽只写一年的政局,却以康梁保皇派为主线,对当时国内外各个党派(保皇派、革命派、国内改良派、会党、地方实力派、满清贵胄等)进行了详尽地分析,不受以往标签式的影响,更加深入到每个人不同时期不同的心理状态(如庚子年梁启超强烈的革命思想),各个派别之间复杂的利益关系(地方实力派李、张与革命派、保皇派的羁縻利用),展示不同以往传统叙述的庚子政局。
二、虎头蛇尾的庚子勤王
庚子勤王可以说是全书的中心,而康梁的保皇派则是本书的主角,作者的叙述开篇便是保皇会的救上勤王。
戊戌之后,西太后及不少满清贵胄对伤及自身利益的康梁等人自是恨之入骨,有公然另立新君之心。然而在地方实力派刘坤一、士绅代表经元善以及外国列强的反对下,废旧立新只能以暂时立储而告终。保皇派借此打出了勤王救上(光绪帝)的招牌,而让他们大喜过往的则是京师义和团的兴起与八国联军入侵所造成的混乱状态。
保皇派的战略与革命派相近,均为立足两广,经略湘鄂,之后或是直捣京师,天下传檄而定;或是划江而治,另建维新之国。在海外华侨大力资助之下,康梁广泛发动地方会党 (诸如哥老会、三合会),一时间也颇有成效。然康派万木草堂师徒弟子终是文人书生,带兵打仗实非其能胜任,加之会党众人名为救上保皇,实为枪械资财,一贯骑墙观望,绝不肯出死力。结果,康梁领导下本应轰轰烈烈的勤王运动在耗尽华侨数十万资产后便悄无声息了。从此,保皇派不再言兵,亦不敢、不能言兵。
三、复杂微妙的庚子政局
八国联军攻占北京,慈溪光绪逃奔西安,北方大乱,东南互保下的江南似有隐然割据之局。倡言革命排满的革命派、致力勤王救上的保皇派、试图渐进革新的江浙派、徘徊观望的地方督抚构成了左右此时政局的重要力量。
四派之中,实力最强的莫过于手握重兵又享有时往的地方督抚(如张之洞、李鸿章)。他们成为各种势力拉拢以实现自身政治目标的对象,当然革命派、保皇派之间之于督抚同样是拉拢利用的关系。
《庚子勤王与晚清政局》读后感(二):戊戌政变后清廷中枢政局演变以及革命派和改良派的分合离疏
桑兵老师的《庚子勤王与晚清政局》梳理了戊戌政变之后清廷中枢政局演变以及革命—改良二派的分合离疏,有助于增强读者对“历史空白之处”的认知,可谓受益匪浅。
一 戊戌—庚子年间朝野政局变迁
历时百日的戊戌变法被拦腰斩断,慈禧太后重新当政。西太后及后党人员最重要的目标便是清除异己,既包括最高权力象征的光绪皇帝,也有拥护皇帝的帝党官员以及鼓动变法的维新人员。
首先,光绪皇帝被剥夺实权,囚禁于瀛台,形同傀儡;接着,清廷密令各省督抚捉拿新党人员,戊戌六君子血洒北京菜市;康梁在英日两国的帮助下得以出逃,而清廷便开始与向康梁等流亡者提供政治庇护的英日等国交涉,使之不再提供保护或迫使其离境,以便实行暗杀绑架。
慈禧与光绪关系急剧恶化,故欲废黜光绪。殆1900年,慈禧太后接受荣禄意见,以光绪皇帝名义发布诏书,立端王载漪之子溥鐫为大阿哥,是为“乙亥建储”。在立储工作进行的同时,慈禧太后下令加紧镇压保皇会和国内维新人士,诛杀戊戌被贬的帝党大臣以绝后患;
然立储遭到了外国公使团的强烈反对,立储没有得逞,慈禧太后迁怒于保皇党人鼓动外国横加干涉,于是设计排外。清廷默许甚至支持义和团的排外运动,未料想形势恶化,引发八国联军侵华之乱。之后,便是慈禧太后的宣战与奕劻、李鸿章的签约,上演了一幕庚子国变。
二 康梁等维新派:在保皇与革命之间
康梁出逃,其保皇之志不变。康梁欲借助英美德等国的力量,通过暗杀或外交途径以达到光绪皇帝复辟的目的;然而慈禧太后很快控制政局,并没有采取排外政策,故各国拒绝了康梁的请求。
1899年康有为在美洲成立保皇会,开始动员海外民众,向清廷施加压力以求达到保皇复政的目的;梁启超流亡日本,暂时与革命党的关系渐趋缓和,目标走向一致。 戊戌变法的失败使得梁启超初步认识到流血斗争对于政治变革的作用,思想一度转向激进,提倡“破坏主义”,曾言“名为保皇,实则革命”,此言不虚。
1900年乙亥建储在趋势人士中引起轩然大波,以电报局总办经元善为首的上海士绅,合计1231人联名上书向清廷施压,成为清廷作出让步的原因之一。
三 孙中山等革命党人的选择
庚子年间,湖南浏阳二杰之一的唐才常决心为好友谭嗣同报仇,与康有为约定武装勤王,在上海成立中国议会,鼓吹建立光绪皇帝领导的的君主立宪政府;然,自立军汉口总机关被张之洞破获,唐本人亦被抓捕旋即就义,
革命党的先期起义接告失败,孙中山为了将反清活动推向全国,尽可能地结交各方领袖人物。由于孙自感实力不足,于是接受梁启超的联合意见,积极支持自立军的中原大举,而且争取与保皇会、中国国会合作,与李鸿章等合谋两广独立,上书港督卜力寻求援助,向法国、日本示惠。
所有的一切终结之后,历史的线索便渐渐汇合于庚子拳变——联军侵华——东南互保——战败签约的历史当中去。
《庚子勤王与晚清政局》读后感(三):“重估”近代史
1923年5月6日顾颉刚先生将《致钱玄同先生论古史书》一信发表在《读书杂志》上面,其在这封信当中提出了著名的“层累地造成的中国古史”的观点,当时这一观点在先秦史研究方面引发了轩然大波,一时间史学界为之大震。这为当时古史研究提供了方法论上的指导。这一方法论对我们今天的历史研究依然有指导意义。近代史史事复杂,史料繁多,众说纷纭,各种玄秘之说反而掩盖了事实的真相,庚子以后的晚清政局,更是风云变幻,千人千辞,史事与谬说相互叠加,而当事人由于后来的种种考虑反而对当时之事加以遮掩,反而使我们陷入镜花水月之中。而桑兵的这本书铺排史料,考证诸说,层累地揭开近代史的面目,摆脱过去庸俗的一分为二非黑即白的史观,为我们重新勾勒庚子之变后的晚清政局。
勤王秘事
庚子之变,异端突起,清政府借助传统之外的异端进行自救,东南的封疆大吏与中央各怀异心,保皇党与革命党既相互利用又相互斗争,勤王与救亡之势力相交织。其中最玄最密者莫过于中国国会,其纠结各方实力既有保皇党人又有革命党人,既有外人之势力又有封疆大吏之参与,而后人往往只关心自立军之起义,而忽视中国国会各种势力的纠缠,忽视保皇会最初的密谋。康有为的保皇会同革命党人相联系,意图在两广,江浙,闽越一带反动起事,以期废后勤王,康有为书生之气失之迂阔,期望借助秘密社会力量进行勤王,不料反折费筹款,与海外最主要的华侨邱菽园反目。
“革命”的知识考古
康有为对革命的恐惧,他在陈奏光绪的著述中就屡次强调革命的破坏性借此来推行君主立宪制,他的观点也代表此时中国人对革命的理解。陈少白在回忆其革命经历时层言:“(1895年)到了神户就买份日报来看看。我们那时,虽然不认识日文,看了几个中国字,也略知梗概。所以一看,就看见‘中国革命党孙逸仙’等字样,赫然耀在眼前。我们从前的心理,以为要做皇帝才叫‘革命’,我们的行动只算造反而已。自从见了这样报纸后,就有‘革命党’三字的影像印在脑中了。”“革命”一词还没有摆脱汤武革命改朝换代的历史语义。随着个人阅历的增长和时势的发展,保皇党内部就革命的语义发生了变化,以今日之我攻昨日之我的梁启超最早在对革命的理解上与康有为发生冲突,梁启超在《释革》一文中将Reform与Revolution进行比较,“革命者,天演界中不可逃避之公例也”。不再将革命视为洪水猛兽,言革命之主张则光绪无地安放,当然不能另康有为所接受,理论主张分歧上升至组织之分裂,保皇会宗旨与组织的分裂在所难免,虽最终理论的分歧以梁启超的负荆请罪而终结,但间隙已有不心服难以补缺。
保皇会与革命党
时事的急剧变化,各派力量趋于整合。康有为虽然抗拒与革命党的合作,但是其弟子却依然与革命势力相交通,梁启超与孙中山的会晤,唐才常自立军中的革命党势力。时代的风云际会,秘密社会的兴起,传统官神互补体系的瓦解,游侠刺客之风兴盛,这些混杂的势力更加凸显变革转型社会中的各种可能性。
传统与变革之间
康梁的革命之辩与台湾民主国内渡士绅对武装勤王的积极参与,他们一只脚踏在传统之上,另一只脚又向传统迈进。台湾民主国内渡士绅在经历清政府的无能之后,转而在传统与现代之间选择思想资源,一边是传统的民本思想,另一边是近代的民主与自由,这共同造就了他们的异端思想。唐景崧、俞明震、易顺鼎等人积极参与变革,无不是时代变革的见证。
《庚子勤王与晚清政局》读后感(四):读《庚子勤王与晚清政局》
桑兵《庚子勤王与晚清政局》(2015,北京大学出版社)内容上大体沿袭了2004年的第一版,以大量史料来钩索庚子年间勤王运动所涉及的各方人物和事态发展。这场终无下文的勤王运动,除了为之前后奔走的保皇会外,革命会党、秘密会社、海外华侨、清廷大员乃至台湾民主国内渡官绅等团体、人物,全都牵连其中。正因其牵连甚广,有关勤王运动的资料驳杂繁多,头绪梳理不易,要从事相关研究,必须要有一定的方法,因此,正文之前的绪论,很合事宜地在简短概括本书的叙事线索外,着重论述了作者几十年治近代史的经验和方法,这些方法在他的另一部著作《治学的门径与取法》(2014,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中已有详尽发挥,而本书则是这些方法的具体成果。
戊戌变法失败之后,仍致力于政体变更的人物,在今人的政治光谱分类中多以“革命党”和“保皇党”两类称呼为之命名,然而揆之历史资料,将他们划作两类界限明晰、截然两分的团体,或许稍显武断,也无益于我们理解历史人物和历史事件的复杂性。事实上,为了获得足够的组织资源以进行政体变更,也为了能在政坛上从容进退,政治人物往往会构造起一套错综复杂的关系网络,即使是观念相左的人,如果有可资利用的必要,也会保持密切的联系。同理,如果观念相近的人与自己有利害冲突,也很难宽容相待。在策划勤王运动的过程中,维新派系之间,乃至派系内部,就因种种人事纠纷和利害冲突,相互倾轧:正气、自立两会汪康年、唐才常两派的分歧;康门内部派系纠纷不断,大弟子梁启超的思想也与老师渐行渐远,被康有为斥为“妄鼓革命”,梁启超最终因对老师的敬重和游美后的失望,“不敢复倡革命”。还要注意的是,虽然勤王计划的具体落实之中,保皇诸人之间关系并不融洽乃至剑拔弩张,但这只是实践层面上的摩擦,无关乎思想宗旨,我们应该把这些内部的事务纠纷放在观念上总体一致的大背景下,以更全面地了解复杂的政治生态,而非对局部的过分夸大。即使是对被当做历史丑角的一些“顽固派”,他们也并非全是冥顽不灵的人,当时《知新报》转载香港《士蔑报》的一则报道,对此有很精要的概括:“西后本非守旧,亦非维新,只求权势平稳逸乐”,经几十年宦海沉浮的老人,是不会放弃自己安定舒适的生活而轻易冒险的,度之人情,历史人物的活动,既有关于思想认同与观念冲突,也有关于人际关系和个人利益。
就像章太炎说的那样,保皇党人之间的冲突“所争不在宗旨,而在权利也”。保皇会以广东人为中心,坚持两广发难,康有为更是不肯北上,甚至以地域定亲疏,激化了内部矛盾;他们招来的武勇头目,多是为了求利;与保皇会有交往的官绅,对他们也是若即若离。诸如这类战略失误、调度错误和同门之间的抵牾,已使勤王运动艰难重重,而且“保皇会奉行办事同门人、打仗子弟兵的封闭式组织方针,以君、亲、师的旧式纽带定亲疏”,主要成员是一群饱读诗书的秀才,难免对实际事物有所隔阂,康有为知道这点,但他也不能改掉多年来的习惯,他指示总局健全文书制度,“今日军谋即为他日考据”。随着形势的变化,康有为依然寄希望于光绪复辟,梁启超、唐才常和江浙维新士人如汪康年等人,却以为尊王不过手段,自立才是立国基本。唐才常希冀“南方立国”,汪康年主张“各省自行治理”,并联合民间秘密会社,“保卫一隅,立自主之国”,虽然他们的观点都建立对光绪帝位的认同之上,但对政治改革的具体实践方法上,歧异与分裂已经非常明显,相互之间的关系,也随着勤王运动的筹备而渐渐疏离、紧张,这类内部的人事纠纷就已治丝益棼,勤王运动远没有做好准备。在庚子年紧张的政治氛围中,各种谣言也开始散播,报纸上刊登完全相反的政坛消息,在一片混乱中,还没有完全筹备好的庚子勤王运动,落得一个“汉口自立军未起先败,保皇会两广草草收场,雷声大雨点小”的结局。
保皇会既已流亡海外,只能徐徐图之,伺机勤王,摆在他们面前的首要难题就是如何解决活动资金的来源问题。在这方面,海外华侨的爱国热情,解决了活动资金的来源问题。也正因为华侨群体的捐助是保皇会,也是革命党的活动资金来源,所以保、革二党在争取华侨方面必定互不相让,孙中山和梁启超由一起倡言革命到“划清界限,不使混淆”,就有争夺华侨捐款的因素。各地华侨在舆论上,也起到了保持光绪帝位的作用,新加坡华侨在其中的作用尤为重要。保皇党人、各地华侨和本土士人在国内外奔走呼号,一方面劝阻当局废光绪,一方面吸引外国对废立问题的关心乃至干涉,最终连同朝廷重臣一起,施加舆论压力,迫使慈禧打消废黜光绪的念头。从废立一事可见光绪在中外臣民中的份量,其中固然有忠君思想的影响,但光绪受人牵制终身,他的名望却日益增长,不得不说这是与他的“贤明”形象分不开的。有意思的一点是,当时的报纸把废立的主谋指向荣禄、刚毅等人,完全不提慈禧的责任,这当然是出于政治伦理和政治权力的敬畏,但在康有为的回忆里,事件的始末,也出现了一定的误差。领头谏阻废立的南方士人经元善,在康有为的追述中,只是粗略提及,而且还当他是受了保皇会的激励,并用大量的笔墨叙述了保皇会人的活动运作,事实上,保皇会人在其中起的作用,至少远没有他所说的那样重要,经元善的作用,也被他一再无视乃是扭曲。后来,康有为在对此事的描述上,变得越来越放大自己与保皇会的作用,桑兵分析当时的具体史料,以为“很难说清楚康有为到底是记忆有误还是故意为之”,按照康有为的一贯作风,我们有理由怀疑,他是在故意制造偏颇的史料。
在这类事后的追述中,康梁师徒“有意掩饰和放大”一些相关史实,给后来治史者造成不小的麻烦。言行不一的情况在实际活动中屡见不鲜,保皇会人在暗中联络并利用秘密会社和盗匪势力的同时,又公开保持距离,洗刷自己与盗贼会党这类边缘人物有联系的嫌疑,在暗中谋划刺杀行动的同时,又要维护表面上正人君子的形象。这种政治形象的塑造,在当时是常见的现象,孙宝瑄分海内党派为四:变法党、革命党、保皇党、排满党,这四类党派或多或少都希望与外国势力联合,借助外国列强的力量,达成自己的政治目的。在海外强国中,日本极受时人的青睐,夏曾佑说:“谓满不同种乎?则满亦黄种也。日本可联,安在满洲不可联?”虽然这段话是议论“排满”风潮的,但我们要特别注意“同种”、“黄种”的概念,这种概念是在西方白种人的侵入下,吸收了经过翻译改动的种族与文明理论后才出现的。简单来说,就是以地理方位(亚洲、欧美)和肤色(黄种、白种)来定义亲疏,这与原来的“朝贡体系”是不同的,“朝贡体系”中的文明优越者是新体系中文明“有待提高”的国家,这种“同种”观念,是在文明发达的欧美诸国的冲击之下,一种寻求安全感和认同感的行为,日本从受外国侵略的蕞尔小国,到维新后跻身强国,又与中国文化相近,清末人士有的以日本作为模板,将自己的理想投射到东邻,加上留学与流亡生活,难免产生“同种”的深切感情,后来宣传“大亚洲主义”的人,也未尝不是延续清末的思路。
虽然本书主要内容关乎勤王运动,但清末的整个政治氛围也包含其中。戊戌以前,康有为和大多数人对和平变法深抱希望,百日维新期间他们急不可耐地推行新政,除了读书人不熟悉实际事物之外,也体现出变法派的热切希望。庚子勤王失败之后,鉴于清廷的强硬态度,更多的人产生了革命的倾向,孙宝瑄说:“国家不变法,则保皇者忠臣也,革命者义士也。”这是他的肺腑之言,后面还有一句话:“国家果变法,而此辈党人犹不解散,则皆乱民也,可杀。”变法派希望以变法消除革命,但形势比人强,在内外交困之下,大清只能靠一些有能力的糊裱匠勉力支撑。孙宝瑄自述对李鸿章的态度“甲午以前每每痛诋之。自审知中外政务以来,始不敢厚非,稍稍了和敬重之。”陈寅恪认为同光时代的清流,中举时年纪尚轻,对国内国际形势不太了解,“务为高论”。庚子年中外之间种种矛盾的激化,还有南北朝野之间政治势力分化组合这种复杂情态演生,酿成了北方拳变、东南互保和勤王运动,对晚清政局造成了巨大影响。
作者通过蒐集大量资料,试图还原历史现场,但在资料的收集过程中,问题随之出现。近代史的资料繁多,但往往真假掺杂,未可尽信。就拿书中经常引用的报刊报道来说,如果涉及内廷机密,只能发挥想象力,用坊间传闻猜测实际政局,其中真假掺半,让人如堕五里雾中。还有日记和书信这类私密文件,虽然为我们研究近代历史提供了一手资料,但也并非尽善尽美,重要人物留下的日记,涉及一些内廷机密时,往往避而不谈或闪烁其辞,当事人如果在书信中有所避忌,相关资料必遭删改或毁弃,让人头疼的是,日记和书信的叙事中又夹杂大量隐语代码,让人不知所云。熟谙世故宦情的大吏,往往千人千面,惯使虚虚实实的招数,真话假话一起说,什么该说什么不该说都想得清楚,近代政治史中的人际关系就足够让人费神,本书将对史料的爬梳剔抉和对事件的深入思索结合起来,其中的旁文剩义也有可以发挥之处,最重要的是,通过对史料的搜集和分析,为我们展示了一个复杂而有理解深度的历史面相。
《庚子勤王与晚清政局》读后感(五):《庚子勤王与晚清政局》一书读书报告
经历了戊戌到庚子的一系列政治风波,鼎足而三的政治格局逐渐形成,庚子年南北朝之间政治势力的分化组合,北方拳变,东南互保和勤王运动局面的出现,正是那一历史时期错综复杂的政治生态演化的产物。
——桑兵《庚子勤王与晚清政局》
《庚子勤王与晚清政局》一书共分为十三章,桑兵并不将庚子勤王看作一个简单的历史事件加以叙述。从题目也可知晓作者试图将“庚子勤王”作为一个研究晚清政治生态的切口而不仅仅是叙述事件本身的历史说明。从书的整体架构来看,作者也将这层意思表达的淋漓精致,达到了作者“截取历史的一个断面,从不同角度展开对同一事件的多方位、多层面探究”(绪论第25页)的写作意图。这样的书写结构虽然作为切口让我们透过历史事件本身看到更为广阔的历史潮流与趋势,但是同时本书中的许多内容出现了不可避免的前后折叠。
本书的史料运用可谓娴熟,作者运用了大量的书信、日记、学人论述来证明自己的观点,作者也说“有关史料必须前后左右互为参证,跳跃联想”(P25),但是也存在堆砌史料之嫌,对读者的观感而言,往往使人囿于史料而不能“跳跃联想”。作者浓烈的实证主义意识,还是很值得学习。
01
戊戌政变之后,光绪帝被慈禧幽禁于瀛台,康有为等人试图积极拉拢日、英两国通过外交手段救出光绪。但外交政治并不是康梁师徒所幻想的那般简单,毕竟统一、强悍又不受列强控制的中央政府并不符合列强的要求。《庚子勤王与晚清政局》(以下简称《庚子勤王》)这部书中也列举了康有为、梁启超等人试图通过日、英、俄之间的矛盾来达到列强干涉政治时局的诸多史料。从保皇会的角度看这个问题自然是没有问题,可是将满清贵胄对光绪的矛盾情绪不免有所忽略。近来马忠文《荣禄与晚清政局》一书,则涉及荣禄在戊戌政变之后积极调和两宫矛盾的做法,这显然是保皇会众人所未料及的,因为荣禄就是推动戊戌政变的幕后推手。但是保皇会诸人对于荣禄的成见,影响了我们对于戊戌政变后庚子勤王整个局面形成的认识。督抚中虽然仅有刘坤一积极希望“两宫相孚”,但在满清贵族中间对于光绪的废立问题的不同意见也成为光绪废立的牵制。
废立问题的次生问题就是建储问题,正如《庚子勤王》一书提到的“立储使得保皇会复行新政的期望几乎完全破灭,清政府与维新派的矛盾急剧激化。”(P71)在保皇会看来清廷是以立储为踏板,试探各方反应,适时再行废立。作者通过刚毅、赵舒翘这类清廷内部极力反对变法的守旧党和荣禄以及地方督抚相对温和的“革政派”之间的矛盾来论述“鼎足而三的政治格局形成”的经过。建储问题实际上是清廷对于保皇会镇压的一次反弹,所以建储问题“终于将保皇会筹划年余的勤王推入实际运行的轨道”。(P80)
02
关于勤王运动,作者指出“受康有为、梁启超等人有意掩饰和放大相关事实的影响,都以唐才常为主”(P80)。作者对于保皇会内部对于勤王运动和自立军运动叙述的史料抱有很大质疑的态度,从全书来看,作者对于这一时期的康梁所著的论述基本持否定态度,更多地是从当事人的书信中发微钩沉,还原历史真相。作者指出,康有为其实重视的两广的勤王运动,对于唐才常的自立军一直并不予以重视,作者从保皇会的资金分配合保皇会内部的书信往来中得出“武力勤王计划动议与唐才常,湘鄂又最具声势,但在保皇会的战略框架内,自立军只是‘数路大军’中的一路,而且不是主力正军”(P81)的结论,完全推翻了康有为的说辞。作者对于康有为对唐才常的“长江大举”不以为然的态度颇有意见,作者借人之口评价康有为是“有救世之力,而无救世之勇”,只知“舞文弄墨,视中国濒危于不顾”。(P109)
03
保皇会之外的勤王运动依然是值得注意的事件,作者中国议会一章中首先考证了中国议会的组织和人员构成。从中国议会的人员构成方面侧面印证出“唐才常由北上勤王转为南方立国”是因为“南方党人不仅有联合之意,而且出现了联合之机”(P125)。正气会是中国议会前,唐才常与汪康年的政治联合团体,但是因为汪康年等人不满唐才常架空,所以唐才常放弃了对正气会的领导,与梁启超等人合议成立自立会。唐才常“将自立会与国会纽在一起”(P158),这一举动又招致汪康年等人的不满。作者通过透析“唐汪之争”反映出中国议会内部也有很多隔膜,同时作者也指出“国会内部分歧主要不在宗旨手段,而在人事派系。”唐才常作为庚子勤王运动中长江流域最有力的实施者,他也积极撮合革、保两派的联合,并得到了梁启超的支持拥护。1900年5月,孙中山接受梁启超的劝说,同意联合阵营顺应时势,使用借勤王以兴民政的旗号。(P171)作者积极评价中国议会是“政治打乱的特定情况下民意浮升、民权提高的表现”(P176),“国会存在的时间虽短,但反映出新学士绅对欧美近代民主宪政的接纳,显示出由他们代表的民权力量的增长。”(P181)
04
庚子勤王,从表面上来说是于革命党没有关系的,因为革命党并不存在“勤王”的主张。以介绍兴汉会为线索,引出了兴中会与哥老会、三合会秘密社会的合作。在这条线索中起引导作用的是毕永年,但是毕永年后来与康有为交恶,遂完全转向孙中山革命派,在兴汉会的成立中也是毕永年在具体操作。可见在兴汉会和保皇党中有些人员是一定重叠,并存在政治转向。
甲午之后,开明士绅开始寻求与下层秘密社会合作。对于会党,尤其是哥老会的争取,成为革命派和保皇派长江大举的关键。兴中会比保皇派抢先一步成立兴汉会,使康有为心中不悦,便暗中破坏。但是孙中山与梁启超却有意合作;唐才常与毕永年又有深厚的交谊,同为谭嗣同挚友,所以两派的关系就出现交织。唐才常因为在上海利用正气会筹到巨款,哥老会首领就开始依傍唐才常,但是唐才常与汪康年的派系倾轧使得唐才常另组自立会,并且设立中国议会联络开明士绅。汪康年自行其是,在川、鄂、皖、江联系会党。与盟兴汉会的哥老会成员还是和唐才常联系与江浙士绅的关系相对较少。毕永年死后革命派与湘鄂会党联络减少,但是孙中山还是对在汉口的林圭和容星桥有信心,所以亲赴上海准备参加自立军的长江联合大举。文章最后将主旨落在孙中山成立兴汉会的意义上来,认为孙中山组建兴汉会并非权宜之计,而是始终给予一定程度的重视,并几乎使之发生实际效用,将兴中会的活动与革命风潮推向长江流域。从本文中,我们可以看出兴汉会中兴中会、哥老会与三合会的结盟,与自立军的关系最后都是开明士绅与下层秘密社会积极的合作,他们虽然宗旨不仅相同,但是并没有囿于政见,而罔顾国家前途。
05
革命党人与唐才常的联系以及和哥老会以兴汉会为形式的结盟,革命党也被卷入并不符合自己宗旨的“庚子勤王”运动中。因为孙中山在兴汉会中的地位举足轻重,哥老会也服膺孙中山的地位,所以兴汉会与自立军的关系在一定程度上就代表了革命党在“长江大举”中的作用,加之林圭和容星桥因故停留汉口成立义群公司“专办湘汉”所以革命党对于长江流域的影响力也不可小觑。作者指出“兴汉会成员积极参与自立军的活动,正是孙中山与湖南维新派合作战略的重要体现。”(P226)作者又通过孙中山亲自去上海参加长江大举,分析出“孙中山赴沪可能是自立军的邀请。说明孙中山视自立军为本派参与的联合反清大举。”(P227)
最后唐才常领导的自立军运动失败,“康有为为了应付华侨的追究,将失败的责任归咎于长江、广西、广东方面担当大任的唐才常、陈翼亭、梁炳光等统兵之人,其实保皇会真正重视和全力投入的还是两广,尤其是以陈翼亭一路为主力军。”(P233)作者将兴中会的“举义”与保皇会“勤王”做以对比,认为“保皇会勤王虎头蛇尾,兴中会举义虽败尤荣”,一褒一贬态度鲜明。与维新派的联系,孙中山通过梁启超创办的东京高等大同学校开始与留日学生接触,留日学生是后来革命的主力军。孙中山还充实和完善了革命理论,扩大了与趋新人士的联系交往。
作者对于革命与改良的定义去完全区分正气会和自立军其实有所疑虑,他指出:“用革命与改良的概念去看围绕正气会与自立军的宗旨矛盾与争论,无法全面观照革新人士具有广泛共识的反清变政意向与活动,不仅将大批改革人士划归保皇或改良,甚至疑及孙中山的反清立场。”(P261)确实是这样,这类标签使得历史相对来说更加“鲜明”但是于此同时我们也牺牲了模糊地带的历史事实。
06
1895年的台湾民主共和国,被认为是洋务与维新运动的交合点,而非孤立的偶发事件。今天的学者对于台湾民主共和国的研究常常带着意识形态的偏见,作者也说“后人分析台湾民主国的政治取向时,从维护统一的立场出发,强调官绅们的忠清意识,而多少忽略了他们对清廷怨恨离异倾向。”(P279)其实是我们太过敏感,实际上台湾民主国官绅是“宁可违抗朝廷旨意,也要力求保全社稷。”台湾民主国的官绅可以说是,民主觉醒比较早的,他们与康有为的保皇派联系密切,并且很多人是姻亲关系。台湾民主国官绅的影响范围又和康有为所主张的两广首先举义的想法契合。
但是总体而言,台湾民主国对于庚子勤王的影响有限,更多地是反映出“甲午和庚子,清政府两度恣意妄为,在局部或整体上触犯规则,以牺牲百姓社稷为代价,保家财逞己欲泄私愤,引起士绅的激烈抗争,甚至不惜诉诸武力。”清廷在国家社稷危若累卵之际,还不推行改革,使得政权统治的合法性开始丧失,许多官绅开始转向暴力革命。
07
新加坡华侨对于庚子勤王可以说起着决定性作用,因为保皇会所募资产,一大半以上是由邱菽园捐赠。邱菽园的捐赠可谓是毁家纾难之举,不仅如此,1899年在光绪废立的关键阶段,邱菽园联合侨民500余人致电总理衙门恭请圣安,并恳请归政。新加坡因此被视为“我四百兆同胞之云霓”。邱菽园和唐才常私交甚好,还寄专款给唐才常支持长江联合大举。
但是康有为确是心有余而力不足之辈,知道勤王事不成,对邱菽园极尽敷衍。作者指出保皇会“勤王与筹款的位置互易,即勤王由目的变为手段,筹款则由手段变为目的。”(P312)最后邱菽园决定放弃资助康有为转向支持梁启超,作者指出邱菽园此举“绝非仅仅出于财务纠纷或个人的关系不恰,而是宗旨倾向变化的表征,亦即由康有为的保皇转向梁启超、唐才常等人的民政。”
08
八国联军侵华之后,两宫北狩途中发出了勤王的旨意。接到旨意的甘肃布政使岑春煊马上行动了起来。作者认为,岑春煊确有借清廷勤王之名行保皇会勤王之实的可能。康有为一直认为岑春煊是自己同道中人。康有为之所以把勤王运动的重心放在广西,也是因为唐景荪主持广西,而岑春煊家在广西又极有势力。但是庚子的形式复杂,岑春煊“审时度势,终究选择了‘戴后’而非‘助帝’。”(P333)康有为听闻岑春煊依靠慈禧青云直上的消息时,不忧反喜,认为在保皇会的劝说下,岑春煊肯定能帮他成就大事。
通过这章,作者其实重点论述地方督抚与海外保皇会的联络。作者在第十一章就曾提到李鸿章因为北方局势不稳,为留有后路就积极和保皇会联络,保皇会于是将李鸿章移除在暗杀名单之列。不仅如此,李鸿章在抚粤之处有联合孙中山擒拿康有为的意图。地方督抚与保皇会与革命党的关系并不是多么泾渭分明,作者指出,“实际上疆吏乃至王公亲贵暗中结交保皇党,在当时已是公开的秘密。他们有的本来就是维新变法的同道,新政复行,官府与新党的政见隔阂渐趋模糊,而相互利用处日见增多。”(P336)作者在描述这一“在朝”和“在野”貌似大逆不道的模糊关系时认为“以政治派分人为划界的做法,必然导致牺牲历史真实以曲就理论观念的荒谬,实在是治史的大忌。”诚如斯言,如果史学概念只是历史事实的简单填充,无异于是削足适履。
09
庚子勤王运动,保皇会以武力用兵为行动方略的重心,除试图争取清军将领外,主要是利用秘密社会现成的组织和武装,“从草泽而与朝廷抗”。以区新为首的广东匪盗虽然与康有为等人的联系热络,但是作者并不仅仅将研究视角定位在两广匪盗与保皇会的关系,而是从基层社会的权利分派来认识庚子勤王中的秘密社会。作者指出“区新个案反映出晚清地方社会权力资源分配经历了大幅度的复杂运动,盗匪势力过分膨胀,但并不完全脱离地缘和宗教联系,破坏了原来官权与绅权互为协调补充的机制,社会控制乃至整个统治秩序陷入紊乱。连官场中人也明确认识到,如果不能进行根本性地变革,清政府将无法继续对社会实行有效控制。”(P346)
可以说清政府在庚子前后基本上对于两广的控制已经很微弱了,盗匪开始明目张胆地收“行水”,当时的情形成为“商人纳厘税于官,而官未能保,反或为之扰者;纳行水于盗,而盗保其不失,且能赔偿,是商之信官不如其信盗之足恃也。”两广对于清政府几成法外之地,所以清政府不得不持续用兵镇压。这些匪盗毕竟是一支有生力量,康有为的保皇党积极与之联系,但是同时又否认自己与秘密社会有染,以防有损自己的形象。其实两者之间也是相互利用,保皇会想利用匪盗对抗清廷,匪盗也想通过保皇会获得枪械银两。港澳总会对于此不审慎,所以邱菽园等华侨的捐赠竟被这些绿林匪盗骗取。最终的结果就是“保皇会的取粤计划,除耗费大笔海外筹款外,几乎一事无成。”(P365)
10
戊戌变法失败后,东亚会成员积极设法营救康、梁,并且允许流亡日本的康、梁加入东亚会。除与维新派的关系密切,一些会员与孙中山的关系也十分密切。1898年因为寻求政府支持的现实需要,东亚会与同文会合并成立东亚同文会。东亚同文会的资金仰给,所以其代表的利益团体不言而喻。1900年8月15日,东亚同文会在江东中村楼召开临时大会,针对义和团事变以来中国政局的变化,重新检讨该会一贯主持的保全中国的主张,以及如何在新的形势下更好地贯彻宗旨的策略,提出公开发表保全中国的宣言案,大张旗鼓地向社会提倡保全主义,一方面抗衡欧美列强乃至日本国内日见抬头的分割主张,一方面解除中国人对日本对华态度的疑虑,使之由感激而更加信赖自己的邻国,令日本对华处于有利地位。(P383)
在本章中,作者主要关注的是东亚同文会在广东的工作展开和撤销。康有为和孙中山都是广东人,而且康有为的保皇会组织的庚子勤王运动的重心就在两广,而孙中山则在积极筹划惠州起义。而这些事情,东亚同文会都与闻。但是东亚同文会高层顾及会员卷入没有把握的革命党的密谋太深,影响全局,所以撤销广东支部。后来因为庚子勤王和惠州起义均告失利,所以东亚同文会就放弃了恢复广东支部。
近代日本对中国影响至深,日本通过官方和民间的多方位外交,意图与列强在未来争夺中国的斗争中胜出。但也不能抹煞部分日本仁人志士为了中国之前途做出的贡献。
11
暗杀活动一直是近代中国打击政敌的一种重要方式,也因为暗杀许多也改变了中国历史。保皇会的暗杀是“处于在野地位乃至被迫流亡的康、梁缺少正统性依据,行动更为隐蔽,以后又秘而不宣,借以保持忠正形象,编织道义战胜权奸的神话而已。”保皇会与暗杀对象的关系很暧昧,时而是暗杀对象时而有成为拉拢对象。并且为了暗杀,保皇会往往所托非人,靡费颇多。保皇会自己的同志亲自参与的暗杀,又是枉送性命,暗杀也终是一事无成。作者认为暗杀活动有很强的士绅代行社会主导职能的内涵,“传统绅权既有接续官权传导皇权的功能,又有代表民意制约皇权的责任。一旦朝廷官府置国家社稷的兴亡安危于不顾,士绅便会起而代行社会主导职能。”
最后作者揶揄保皇会的作者道:“圣王之道毕竟两歧,保皇派只好在致圣的幌子下,大行争霸之道。只是他们缺乏这方面的人才功力,没有值得炫耀的业绩,不得不避讳遮丑罢了。”
12
保皇会内部对于是否进行暴力革命也有争议,并不和我们之前想象的一样。作者认为y有几种因素促使维新派与革命党相互呼应,“其一,兴中会持续主动寻求合作。其二,日本人士的压力和影响(东亚同文会部分人士认为,根据中国各方面的实情,改革比革命更加困难)。清政府血腥镇压变法激发了维新派的反清意识。”(P438)但是康有为对于弟子“言革”一直极力反对,欧榘甲因为积极“言革”差点被康有为逐出保皇会。康有为告诫保皇会中人说:“仆受圣主衣带之诏,愧不能救,誓死救上,岂可他论。故革命扑满之言,仆不愿闻也,亦望同志俯鉴仆心,俯采仆言”。还动辄以逐出师门为要挟,使得弟子不敢妄议。
梁启超远游美洲筹款之后,才逐渐放弃了“言革”思想。梁启超之所以有悖于业师康有为的思想,是因为担心光绪如果发生意外,保皇运动的趋向将不明了。加之海外各阜侨民支持革命者日多,“革命党与保皇会均视海外华侨社会为生命线,权力基础此长彼消,争夺自然格外激烈。”但梁启超在美洲认识到暴力革命之后,就幡然悔悟,继续支持康有为的主张。
13
本书中作者对港澳总局的批评处处可见。港澳总局是保皇会的执行机构,是勤王大业的具体操作者。但保救大清皇帝公司又以横滨《清议报》为总公司所在,与澳门《知新报》同样具有收集各地捐款的职能,令两地组织机构之间容易产生矛盾。港澳与横滨之间的矛盾冲突屡起,捐款问题、组织人事问题、商会问题都将整个保皇会重要成员牵扯其中。这种无意义的内耗,加之港澳总局办事不力,捐款多为两广绿林所骗,亦或是被挥霍殆尽,终于一事无成。保皇会中人尚未掌握政权就内耗不止,始知庚子勤王败局已定。
余论
《庚子勤王与晚清政局》这本书还是给人以许多启发之处,在描写各地督抚与保皇会的接触上,作者敢于澄清事实,不让历史被带有鲜明标签意味的史学概念所限制,使处于模糊地带的历史被我们所认识。在这本书的时候,我们不得不由后想到辛亥革命,辛亥革命似乎在一夕之间取得成功,其实不然。对比庚子勤王和辛亥革命,我们就知道在政府不顾国家社稷,而在乎一姓之荣辱的时候,地方士绅便会代行社会主导职能,使政府失去其执政的合法性。广东的宗族社会被匪盗所颠覆,江浙士绅与秘密社会的交往,保皇会采取的暗杀行动,中国议会针对清政府的行为,康梁师徒关于宗旨的争论,其实一定程度上都说明了这个问题。庚子勤王运动,尤其是唐才常的长江联合大举,将孙中山、梁启超、林圭、容星桥、容闳等人联合在一起,说明无论保、革在民族大义面前就不在乎宗旨的分歧。相比较后来的辛亥革命中革命党与立宪派的联合,多有相似之处。无怪乎桑兵感慨:“如果不是康有为从中作梗,求同存异、互相呼应的中国革新派未必没有乘乱取胜的机会。”(P261)
是清末新政加速了清政府的灭亡,还是延缓了清政府的灭亡?庚子年南北朝之间政治势力的分化组合,北方拳变,东南互保和勤王运动局面的出现,从南到北再到海外,清政府与地方的分离已经开始显现。如果不推行新政,只怕清政府的灭亡只在朝夕间。武汉新军枪响,一个王朝落幕。但是推翻这个王朝的各项条件在庚子年已经具备,可以说庚子勤王是辛亥革命的发萌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