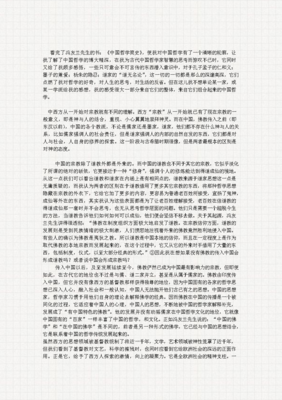
《新编中国哲学史》是一本由劳思光著作,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出版的平装图书,本书定价:159.00,页数:1284,特精心从网络上整理的一些读者的读后感,希望对大家能有帮助。
●2018.12.30重读。叙述事实,但更注重用逻辑分析和考证的方法反溯理论的根本意向。整体以“主体性”为基准,为儒家总结一“价值自觉”,为道家总结一“情意我”,为佛教总结一“主体自由”。 每章总论与理论难题的部分都非常好。在具体介绍学人思想时,有些未形成系统,只剩一条条主张。第一卷最好。第二卷对汉代哲学否定态度甚明,未免于理论本身论述不精,佛教部分论述清楚。三卷上第二章理学总说极好,哲学性较强。其余部分未细看。三卷下也还行。
●清而要,胡、冯书较之如泥
●最哲学性的哲学史
●尝试读了几本不同作者的中哲史,还是劳先生的最读得进,也最受益。通读中国哲学史最大的收获是,终于能从头到尾叙述中国的历史朝代变迁了…
●比国内的教材好很多,有个人风格,我没看过冯友兰的哲学史,不知与冯友兰的相比如何
●等考完,再读一遍...修正了我对儒家的态度。。原来自己一直也是媚俗的,不懂就人云亦云,多加批判...这本书在我看来,很严谨,各种考据都有,读起来,有点难度,就孔子和孟子的“仁”,反反复复,还是不懂......也是一本扫盲的书
●这算劳先生中期的学术著作。早岁集中在《思光少作集》和《思光学术论著新编》,晚岁则有《思光近作集》和对文化哲学的探讨。 劳先生此书最大的特色在于基本秉持康德哲学的立场,截然划分应然和实然,存有与价值。整体上,劳并不认同港台新儒家所谓的天道性命通而为一的道德形上学模式。以存有和活动两个范畴来看,对中哲和儒学的理解上,劳先生是摄存有于活动,牟宗三先生是即存有即活动。 劳先生持心性论中心的学问观,以为先秦心性论不需要亦不必要发展至形上学,这和高抬天道论的新儒家学者迥异。 全书思路清晰,论证严谨,方法论特色尤其突出。有所谓的基源问题研究法,但此方法在具体运用上尤其是处理宋明理学问题时并不凸显,而似乎被劳先生一系说的理论取代。 劳先生业已作古,现长眠于台湾宜兰公墓,惟此思想事业并日月不朽矣。
●挺不一样的。
●说实话,并不适合初学者,不了解台湾叙述风格的,看不到本书许多论述背后的东西,容易先入为主。
《新编中国哲学史》读后感(一):劳思光及其“中哲史”中透显的人生价值
劳思光先生认为一部“哲学史”不光要有“史”的成分,还应有“哲学”的成分。 也就是说“哲学史”不光要阐述事实,更要解释理论,展现各家思想精髓。 先生认为胡适的“中哲史”不能算作是“哲学史”,仅是“史”而已;而冯友兰的“中哲史”虽有“哲学”成分,却很遗憾地没有触及中哲的特性所在,冯一直试图用纯粹西哲的眼光去解读中国哲学。 对哲学有些了解的人都知道,“哲学”一词是舶来品,中哲与西哲是有区别的。
有感于中国居然没有一部较为合格的“中哲史”,劳先生就开始了自己的中哲史著书之路。
劳不满意一些今人对中国某些思想的误解,亦不满意某些先哲对更古的思想进行继承却又改变其本来的精神方向。
劳非常推崇孔孟儒学,使用了一些特别的角度去解释儒家思想,同时也客观点出了儒学思想存在的问题。 孔子思想并不迂腐。 孔子在几千年前就能强调人的自觉,认为人与其他存在物的区别在于人有价值意识,有道德判断力,而动物只有本能。 孔子认为“礼”存在主干和末节,主干就是“义”,表“正当”,末节乃具体表现。一位有自觉心的人心中自然有一套规则,同时不拘泥于形式表现。 劳认为孔子思想存在两大问题: 一是未能对自觉性予以证立。 二是既然各种身份的人需要尽其理分,若君不君,可否转移政权?
劳认为继承了孔子思想且没有改变其精神方向,同时解决了孔子思想两大遗留问题的,唯有“亚圣”孟子。
对于问题一,孟子提出了“性善论”。 容易被误解的“性善论”并不是指人一开始便有程度达至完成的终极德性,不然便理不可通。 此论实指正常人都具备“善”的微光,区别只在于程度之多少。 与此对应的有“四端说”。 “四端”即为人之四种体现“性善”的自觉心。它们分别为 “恻隐”,“羞恶”,“辞让”,“是非” 。 觉事“不应有”,为“恻隐”;觉事“不应有”而显现拒斥割离自觉为“羞恶”;有“应得”与“不应得”辨认之自觉为“辞让”;对事能有“合理”与“不合理”辨认之自觉则为“是非”。 正常人都具备这四种自觉心,区别在于多与少,这便是“性善”的体现。 对于问题二,孟子提出了“民本说”。 孟子认为合格的君王应该顺应民意。天下得失系之于民心之向背,如若君暴政,则民可推翻之。 此外,孟子还倡导“仁政”。 劳认为思辨性不足乃儒学一大缺陷。孔孟认为重要的是当机教化,扩大“仁”之覆盖面,故辩证不应是儒学需要主要考虑的东西。 劳在论述孔子思想中的“自我问题”时,设立了“四我”。 一、形躯我。 二、认知我。 三、情意我。 四、德性我。 劳认为孔子所推崇的是最后的“德性我”,这个才是人生的终极追求。 不光需要物质生活满足的“形躯我”需居其下,连体现求知精神的“认知我”和体现艺术追求的“情意我”都应该在“德性我”下面。
真乃凡人无望的境界。
《新编中国哲学史》读后感(二):读劳思光《新编中国哲学史》序言&第一章所感---对“中国哲学史”一词的粗浅理解
首先说明,以前的我一直对“哲学”和“历史”这两门学科都是敬而远之的,参加工作后,多亏了和读书会的小伙伴们一起,在2014年左右开始读了一点西方哲学、中国哲学的通识读本,前者主要指斯通普夫《西方哲学史:从苏格拉底到萨特及其后》,后者指冯友兰先生的《中国哲学简史》;在2017年也是和大家一起,阅读了钱穆先生的《国史大纲》。回忆中这三本书都是很愉快的阅读体验,尤其是当时大家的意气风发、交流碰撞让人怀念,钱穆校长的“温情与敬意”也让人心有戚戚焉,同时我也算在这个过程中收获了一些基础知识和感性认识。
2018年3月,读书会要一起读劳思光先生的《新编中国哲学史》一书了。我是犹豫的。固然我知道自己对“中国哲学”的学习还需要加强,能和小伙伴一起精进机会难得。但因为这段时间的我,对“中国”充满了某种偏见,想想又要接触孔孟那一套,实在觉得是某种枷锁上身。此外,读了劳先生该书的序言和第一章,我发现自己对他的写作风格不太感兴趣(呼,是有些不敬了),这更让我纠结。
最终让我下定决心试一下的原因是我突然想到了一个问题:“如果要写19、20世纪的‘中国哲学史’,该怎么写?”这个大命题下面的一个子问题可以是,比如,“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演变和现状是什么?它对中国自下而上、各方各面的影响是怎样的?它如何推动或阻碍了中国历史进程?”……
所以,我想在读这套书的过程中,一直要记着问自己这个问题,这至少意味着: 第一,我要特别留意“中国哲学史”的内容和方法论;第二,我要特别留意书中对“佛教”这一外来思想的解读。
今天是读书会的第一次上课,读序言和第一章。晚上骑车回家的路上,我又开始想如何理解“中国哲学史”这个概念的问题,现记录一点想法如下,作为备忘。当然,我的这些想法应该全部是抄袭的,它们最初都是别人的,我所景仰的那些人的,只不过在我这里落了根,而且就像插花一样,在我这里集合暂时成了“一小盆像点样的整体”。
首先是关于“史”。我自己现在对历史最基本的三点理解是,第一,历史是一种“古今对话”,正如钱穆先生在《中国历史精神》等书中强调的那种“持续”,这种“持续”的意涵其实是多层次的、丰富的。第二,就思想史、文化史、经济史、政治史、军事史、阅读史、戏剧史等等这些分类别、分学科的史学看,我觉得历史也是“各领域之间的对话”、“上与下之间的对话”,即那种一讲历史就是“帝王轮替”、一讲思想史就是“精英经典”的传统固然也是重要的,但在每一个时间切片下,我们对当时不同人群的理解应该有更多的层面和视角,并且注重他们之间的相互关联。就思想史而言,也许正如葛兆光先生在《中国思想史•导论》中所说的“还有一种近乎平均值的知识、思想和信仰,作为底色或基石而存在,这种一般的知识、思想与信仰真正在人们判断、解释、处理面前世界中起着作用”。是的,我大概是“新社会文化史学”的一名小粉丝。第三,其实是第二点的延续,历史不仅仅是史书中的文字,还有考古学者许宏先生所说的“无字地书”,不仅仅是远古需要考古学的助力,就是博物馆那些历朝历代的文物都会说话。此外,中国历来被认为是重视历史的民族,就我浅薄的常识,世界其他各国也都或多或少有历史记载,并且可以大体认为,中国“经史子集”中的“史”与英语世界中的history一词基本含义应该相差不多,可以直接对话。这就与下面要解析的“哲学”一词所处的情况非常不同了。
上面先谈“史”,是因为我认为“哲学史”应该放在“历史”的大背景下来理解。这就要求我们:第一,它属于历史范畴,因此要注重其内在的持续性。第二,注重其与其他历史方面的双向联系,即某种“哲学”思想既可能由当时复杂的社会背景催生,也可能对当时的社会各方面产生实际或潜在影响;并且注重“精英”的哲学思想在帝王、知识分子、普通大众等之间的传播。
“哲学”一词是我们现在通用的中文,比如北大有“哲学系”,而且其更多地源于西方文化,或者说源于希腊,但对20世纪以前的中国人来说,这个词几乎是没有意义的,比方说孔子应该不会自认为是“哲学家”。
因此,当我们说“中国哲学”一词时,我觉得,一方面,我们是在用“我们现在、当下定义或理解的哲学”来“衡量”中国传统思想历史中“类哲学”的内容,即就“哲学”一词而言,这里有一种“古今对话”。具体来说,我们现在对“哲学”的理解虽然肯定是有各家之言,但比较朴素的,按劳思光先生的说法,可以是“整个哲学史的功能,在于描述人类智慧之发展,内在的心灵境界、外在的文化成果,都要统摄于此”,然后,我们可以从中国传统思想中寻找“智慧、心灵境界和文化成果”,把它们在某种程度上叫作“中国哲学”。另一方面, 由于“哲学”一词最初源于西方文明,而且对西方世界是极其重要的,因此“西方哲学史”对他们而言是“自然的成体系的传统”,西方哲学的各种概念、学说和理论体系在某种程度上也更加自觉、多元、成熟,至少对中国人理解“哲学”一词而言,是“先入为主”的,所以,当我们说“中国哲学”一词时,不可避免“中西对话”,即用“西方哲学”来衡量中国传统思想,所以,劳思光先生也说到,做中国哲学史研究,要对西方哲学理论有所把握、有所造诣。与哲学的“古今对话”相比,哲学的“中西对话”似乎是两个文明的对话,找到如何走出更大范围的“词语迷阵”以开展交流的路径,应该不是一件容易的事,甚至有些强人所难,也许就像中西医对话那么难。
所以该怎么结语呢?该怎么读中国哲学史呢?我感觉,如果不得不舍弃什么才能前进,那还是不要在“哲学”一词上太过纠结了,某种程度上就像我们根本不会纠结是否应该有“中国科学史”、“中国物理学史”一样。就我个人功利的目的而言,读“中国哲学史”一方面是为了更好地理解中国传统思想和历史源流,另一方面,是为了加深对“哲学”即人类智慧的理解,而这两方面,应该都将有助于我认识今天的中国社会,以及自己的生活。
希望能坚持和小伙伴们读完劳思光先生的《新编中国哲学史》第一卷,那时对“中国哲学史”一词的理解或许就有所进步了,希望过程快乐。
2018.3.24
《新编中国哲学史》读后感(三):《新编中国哲学史》第二章古代中国思想
第二章古代中国思想 本章所要讨论的是孔子之前的中国思想。古代中国,指孔子之前的中国而言。以孔子为第一个有系统的哲学理论体系的哲人,此前的思想只能算作是中国哲学未出现之前的零星思想。 以哲学史的治学态度,只能考察古代中国与哲学有关的观念,其他的概不能涉及。 古代中国与哲学有关的观念分为两种,其一是与哲学问题相关者(理论意义),其二是与哲学史进程有关者(历史渊源)。这一划分的依据在于本质问题与发生过程问题的区分,哲学史工作者需兼及两者。 案:本质问题是就哲学问题自身的内在逻辑地展开和发展而言,不涉及具体的客观在外的诸如经济政治地域等影响因素,纯就哲学理论而言,如考察孔子思想,其基本的三大哲学观念是仁义礼,只单纯的考察这三者之间的哲学的逻辑关系,以礼作为外在的具体秩序规范,进而推论其内在的正当性,再进一步探寻其正当性的来源和基础。发生问题则要涉及外在的具体因素,要考察当时的具体的历史背景、地域特色、宗教信仰、政治关系、经济变革、阶层升降等等方面,其可以作为哲学思想史发展的渊源。 一个文化传统的特性并不与其早期观念(文化精神定向以前的观念)是一回事。文化精神的定向与形成,以自觉的价值意识及人生态度为标志。一个民族在不可考的远古必有各种非自觉的早期原始风俗、信仰,文化进入自觉阶段之后,这些非自觉的观念即被动的被容纳或者淘汰,本身不具备主动性。中国文化精神的特性是在自觉期才出现的,不可以认为凡是在历史上出现过的观念都能代表文化精神,不可以认为凡是最早出现的即能代表文化精神的特征,尤其不能在一群原始观念中找出中国文化精神的方向。 案:原始观念涉及一系列的风俗、宗教信仰(观念、仪式)等等,本身不能作为自觉的文化精神方向,而是文化进入自觉期之后接受自觉意识的容纳和淘汰的中性的资源。文化精神的定向的完成一方面涉及理据(价值意识)如追求仁,另一方面涉及人生态度,这方面是价值意识落于具体的个人生活之中,如追求道德生活的完满。总之,文化的定向本身就是文化精神理性地自我选择的结果。 第一节有关原始观念之问题 原始观念:文化精神定向之前的杂多观念。基本上只能反映各民族的一般性观念,当然也有一些特殊观念为其他民族所没有,而这种特殊观念是不同民族之间比较所得与文化定向之后的特殊方向并非一事,二者之间没有必然联系。 原始观念之存在为一事实,在自觉的哲学思想出现之后,其并未立即消失。表达原始观念的词语仍然存在于哲学理论之中(词语的移义和复义问题),比如天范畴在原始观念中以表达人格神意义为主,孔子之后人文精神日益显露,天范畴的人格神意义基本丧失,而天范畴在儒家思想的框架之后又呈现了另一种意义。原先表达原始观念的词语在哲学理论出现之后被自觉地赋予新的意义,不可执着于字面将原始观念和哲学思想混为一谈。 原始观念的附属性地位。某些原始观念具备零星的哲学理论意义,某一学派的哲学理论也许刚好强调与之相同的问题,其即被引之为同调纳入某学派的理论。这其实是自觉的哲学理论选择了原始观念而非原始观念决定了某一学派的哲学立场,某一哲学理论自有其内在的理论依据。研究某一学派的思想时,原始观念只能作为附属性的资源并没有基础性作用。 第二节古代中国思想的重要观念 中国哲学兴起之前的原始观念,见之于古代典籍。秦汉以下,伪书甚多。自汉代到唐代,学术疏于考证基本认定经书为可信资料。宋以来渐开疑古风气,至清代方能考据经籍中的真伪问题。现所存经书,应首推《诗经》《尚书》(今文)《易》卦爻辞,《春秋三传》尚属先秦作品,《三礼》最成问题。本节所论的原始观念,以《诗经》,《尚书》,《周易》卦爻辞为主要根据。 《诗经》中之“形上天”观念 形上天即将天作为一形上学意义的实体,区别于宇宙论的天和人格神的天。 案:人格天表示某种人格意志的主宰,万物服从此人格意志,强调天意。形上天只表示某种实体(理序或者规律),无意愿性,强调客观运行的天道。宇宙论的天泛指自然,并不强调天道或者天意。 案:关于形上天的有两种说法,一说认为形上天属于先秦道家思想,另一说认为形上天是儒家精神的中心以之为正统。严格地说以上两种说法都不准确。一方面周初即出现了形上天的思想故不可以说此观念必在道家思想中才出现,另一方面先秦儒家思想以道德主体性为中心,形上学天本不属于其理论建构的必要部分,从历史上看,形上天观念要成为儒学的一部分则要始于秦汉至两汉经学大盛,以《中庸》为代表。 《诗经》中的形上天见于《雅》,《颂》。 第一,《周颂-清庙之什-维天之命》 维天之命,於穆不已。於乎不显,文王之德之纯。 案:天之命即天之法则,运行不息。不通丕,至。天道至为明显。以文王之德比拟天道。 第二,《大雅-荡之什-烝民》 天生烝民,有物有则。民之秉彝,好是懿德。 案:天为万物的法则,表示某种必然性,为万理的存有性的根据。人能认知的理皆是此实体的显现,皆是由此实体而来。人所执守得常理和追寻的价值都是以此实体为归宿。 案:以存有解释价值。 《大雅-文王之什-文王》 上天之载,无声无臭。仪刑文王,万邦作孚。 案:无声无臭表示无意愿性,用以描述形上天的特性。天道无所主观作为,一理运行。后两句言文王法天的效果。 《易经》中之“宇宙秩序”观念 《十翼》为后人伪作,其中的观念涉及宇宙论,形上学,方士邪说,古代习俗,极为杂乱。专就《易》卦爻辞而言,以时代论不晚于周初,以意义而论则涉及中国古代思想中德宇宙秩序观念。 宇宙秩序。卦爻组织本身是一种符号游戏,组成六十四重卦之后,予以排列定以名称表示特殊意义,即含有宇宙秩序观念。诸如《乾》表示形式动力,《坤》表示质料,《既济》与《未济》表示宇宙生化过程的无始无终。 卦与爻。卦表示事态,兼及宇宙历程和人生历程。爻则为基本项,表示某卦的某一阶段,以之定吉凶。暗合宇宙历程与人生历程。 卦辞与爻辞。至少有两大特色。其一物极必反的观念。即卦象吉者,最后一爻多半反而不吉;卦象凶者,最后一爻有时反而吉。例如:《乾》之上九,《坤》之上六,《泰》之上六,《复》之上六,《益》之上九,《升》之上六,《丰》之上六。《否》之上九,《剥》之上九,《睽》之上九,《蹇》之上六,《损》之上九,《困》之上六。其二,居中为吉。中的观念为变中之不变,无论各种状态如何变易,每一种状态皆有中在,此中即被视为得正,为吉。此是以存有解释价值。 《书经》中之政治思想 民本观念。 《虞书-皋陶谟》:天聪明,自我民聪明,天明畏,自我民明畏。《商书-盘庚》:呜呼,古我前后,罔不惟民之承。《周书-泰誓》:天视自我民视,天听自我民听。《周书-酒诰》:人无于水监,当于民监。(监通鉴) 2,人才观念。 《虞书-皋陶谟》:在知人,在安民。《虞书-益稷》:股肱喜哉,元音起哉,百工熙哉。《周书-君奭》:我闻在昔,成汤既受命,时则有若伊尹。 第三节附论原始信仰 人格天观念 《诗经》中虽有形上天观念,但大部分资料仍表现人格天观念,以“帝”或者“ 天”专指最高主宰或人格神,此承继古代习俗,并无哲学史上的本质意义。 《诗经》中人格神只是主宰者而非创世者,主要主宰于政权的兴废,以其为人事多不能控制之故。 人格神的主宰性仍需要受到某种形式约束(理序),主宰力的运行受到理的约束,人格天低于形上天。 中国古代之神鬼观念 神与帝比较。神为多数(四方之神,遍于群神,诸神,百神),涉及一神则为天、帝。(王专指尘世统治者) 神并非先于世上而存在,其中一部分为人死而成神,神无超越此世的意义。 神鬼并称。祭天祭祖,如殷墟中卜辞中先王的观念。 神人关系。神的领域与人的领域不分,人解释鬼神的行为依照的是人世的价值观念,神鬼本身并无不可解释的神秘性。过度的神人关系在上古曾一度成为社会问题,后来即有颛顼宗教改革绝地天通(《尚书-吕刑》:乃命重黎,绝地天通,望有降格。《国语》:少皥氏之衰,九黎乱德,民神杂糅,不可方物,夫人作享,家为巫史。颛顼受之,乃命南正重司天,以属神。命大正黎司地,以属民,使复旧常,无相侵渎,是谓绝地天通。),限制人民过度迷信神鬼的倾向。 三、命观念 命在中国古代有两种意义,其一指出令,即命令义;其二指限定,即命定义。前者为命的本义。 命令义。以意志性为内容,半多与人格天相连,涉及意志要求,常涉及价值观念。如天命-人格天-天为权威标准-顺天命为正义。(后世墨家受此影响甚深) 命定义。以条件性为基本内容,不必然涉及意志问题,必涉及一客观限定的观念,亦可不涉及价值问题。 如《郑风-羔裘》:羔裘如濡,洵直且侯,彼其之子,舍命不渝。《召南-小星》:肃肃宵征,夙夜在公,命实不同。 案,此处解释命为命定之环境似有牵强。 命定义的命与人格神分离,表客观限定,对价值问题而言呈中立性。于是命之所决定者,与正义并无关联,反之人生合义与否是另一问题,归另一领域。命只能涉及条件序列而不能涉及自觉意志,客观限定与主观自觉二分。后世儒家思想即继承此命定义的命观念,在自觉领域凸显人的道德主体性,义命分立。 案:此种解释命的观点自然契合劳思光诠释中国哲学严守的心性论中心的立场,至于强调天道性命相贯通的牟宗三的观点,则自然与其不能合。关于命范畴的哲学立场的诠释贯穿了劳思光阐释儒学思想的全部,为其立论根基之一。
《新编中国哲学史》读后感(四):《新编中国哲学史》第三章孔孟与儒学(下,未完成)
第三章孔孟与儒学 (下)孟子及儒学之发展 第二节孟子之学说 心性论 心性论可分为三点,其一,性善与四端说(价值根源与道德主体的显现);其二,义利之辨(道德价值的基本论证);其三,养气与成德工夫(道德实践) 案:明显可见,劳思光是以主体性哲学的进路来诠释孟子的思想,至于天道形上学、宇宙论的部分,完全没有涉及到,因主体性哲学只需阐明价值根源,何为价值,如何实践价值的问题,至于牟宗三所谓的道德秩序即宇宙秩序这样的说法则自然为劳思光所不取,劳思光在《新编中国哲学史》的第三册宋明儒学总说部分详细阐明了三种形态的儒学模型(天道观、本性观、心性论),其所肯定的自然是心性论的模式。 性善与四端说 关于性善的讨论多半见于孟子与告子的辩论,兹以《公孙丑》为总纲。 《孟子-公孙丑上》: 孟子曰:人皆有不忍人之心。先王有不忍人之心,斯有不忍人之政矣......所以谓人皆有不忍人之心者,今人乍见孺子将入于井,皆有怵惕恻隐之心,非所以内(纳)交于孺子之父母也,非所以要誉于乡党朋友也,非恶其声而然也。 由是观之,无恻隐之心,非人也。无羞恶之心,非人也。无辞让之心,非人也。无是非之心,非人也。恻隐之心,仁之端也。羞恶之心,义之端也。辞让之心,礼之端也。是非之心,智之端也。 人之有此四端也,犹其有四体也......凡有四端于我者,知皆扩而充之矣,若火之始然,泉之始达,苟能充之,足以保四海,苟不充之,不足以事父母。 梳理上段材料如下: 先验论进路肯定价值意识为人本有。 孟子所肯定者,乃价值意识内在于自觉心(价值意识为自觉心本有),此内在或者本有,并非指发生历程而言,而是指本质历程。 案:如果将价值意识为自觉心本有理解为发生历程,则会得出人在出生的始点为善,自然于理不通。所谓将自觉心本有价值意识理解为本质历程,是指价值意识本身就是道德主体行为的方式。这个“有”要理解为“主体行为形式(能力)义”。 价值意识为人本有随时体现。 人在自觉生活中,皆会有应该或者不应该的自觉。而这种自觉与利害考虑、所具知识如何、处于何种环境等等均无涉。人之恻隐、羞恶、辞让、是非之心,皆是当前自觉生活随时显现者,皆是价值自觉的表现形式,人对此反省,发现其中蕴含德性的种子,进而可以肯定人本有成就各种德性的能力。 德性完成在于不断道德实践。 端只是始点,自觉心原含有各种德性,如要使得各种德性圆满展开,则必须要有自觉的努力(扩而充之)。德性的完成是自觉努力的成果,是将自觉心本有的德性落成一贯的升进过程。德性是价值意识发展的结果。 心体性用。 心,自觉心。性,自觉心的特性(特有之本性),意义略相当与亚里士多德所言的“本质”、“特性”(essence)。性善指的是价值意识(内在于)根源于自觉心,严格地说善恶问题都以自觉主体为根源,但孟子所谓的恶是善的缺乏(此点与柏拉图学说有相似处),故而只点出性善,以说明价值根源于自觉心(主体)。 义利之辨与驳告子之说 性为人之所以为人的本质特性。 《告子上》: 告子曰:生之谓性。孟子曰:生之谓性,犹白之谓白与?曰:然。白羽之白犹白雪之白,白雪之白犹白玉之白与?曰:然。然则犬之性犹牛之性,牛之性犹人之性与? 性在古文中与生为同一字,故人每以为性即指生而具有者。孟子所谓性指的是特有的本性。若以生释性则一切事物之性皆可以指生而言,于是不能分辨人之所有的特殊之本性。孟子所谓的人之性,指的是人所以与其他存在不同之性(essence)。 2,性为人所本有内含价值意识自作主宰。 《告子上》 公都子曰:告子曰,性无善无不善也。或曰,性可以为善,可以为不善,是故文武兴则民好善,幽厉兴则民好暴。或曰,有性善,有性不善,是故以尧为君而有象,以瞽瞍为父而有舜......今曰性善,然则彼皆非与?孟子曰:乃若其情(训情为实),则可以为善矣,乃所谓善也。若夫为不善,非才(本质)之罪也。恻隐之心,人皆有之;羞恶之心,人皆有之;恭敬之心,人皆有之;是非之心,人皆有之。恻隐之心,仁也。羞恶之心,义也。恭敬之心,礼也。是非之心,智也。仁义礼智,非由外烁我也,我固有之业,弗思耳矣。故曰:求则得之,舍则失之。或相倍蓗而无算者,不能尽其才者也。 分疏如下: 其一,性善之善,指性之实含有实现价值的能力。训情为实。性善即实现价值的能力内在于性的实质中。 其二,才指本质,人不能实现价值,并非人之性中无此能力,而是人为能发挥。 其三,公都子所言的三说,均未能切入价值意识本内在之义。无善无不善乃中性观不可以解释价值,可善可不善和有善有不善指经验事实的状态。价值根源于自觉心是一回事,人在经验之中是否能发挥又是一回事,人能否充分发挥此能力,不妨碍此能力的本有。 人不能发挥价值意识在于溺于物(利)故失主宰力。 《告子上》: 告子曰:性犹湍水也。决诸东方则东流,决之西方则西流。人性之无分于善与不善也,犹水之无分于东西也。孟子曰:水性无分于东西,无分于上下乎?人性之善也,犹水之就下也。人无有不善,水无有不下。今夫水,搏而跃之,可使过颡;激而行之,可使在山。岂水之性哉,其势则然也。人之可使为不善,其性亦犹是也。 此说孟子以水之上下喻价值自觉的有向性,本身是喻而非证。 《告子上》: 公都子问曰:钧是人也,或为大人,或为小人,何也?孟子曰:从其大体为大人,从其小体为小人。曰:钧是人也,或从其大体,或从其小体,何也?曰:耳目之官不思(自觉),而蔽于物,物交物则引之而已矣。心之官则思,思则得之,不思则不得也。此天之所与我者。先立其大者,则其小者弗能夺也。此为大人而已矣。 此说自觉心与感官的差别。感官经验在一组条件下成立,仅表事象关系。自觉心以自觉为功能,其功能的发挥视自身而定。心溺于物蔽于私则不能如理不能实现价值,心不溺于物则如理畅行,即以本有的价值自觉为方向而行。意志选择何种方向,乃是自觉心自觉者。 《梁惠王上》: 孟子对曰:王何必曰利,亦有仁义而已矣。王曰:何以利吾国;大夫曰,何以利吾家,士庶人曰,何以利吾身;上下交征利,而国危矣。万乘之国,弑君者必有千乘之家,千乘之国,弑其君者必有百乘之家。万取千焉,千取百焉,不为不多矣。苟为后义而先利,不夺不餍。 此说循利必生夺取之心,以利必为私。义利之辨即公私之别。 《告子上》: 口之于味也,有同嗜焉;耳之于声也,有同听焉;目之于色也,有同美焉。至于心,独无所同然乎?心之所同然者,何也?谓理也,义也。圣人先得我心之所同然耳。故理义之悦我心,犹刍豢之悦我口。 此说价值自觉本身就要求如理而行,如果感官要求其所欲。 《离娄下》: 孟子曰:人之所以异于禽兽者几希。庶民去之,君子存之。 此说性(价值自觉如理)是人异于其他存在的特性,其自觉能否发挥,又纯依于自觉努力而决定。 养气与成德工夫 1,不动心与言、志、气、体。 《公孙丑上》: 曰:敢问夫子之不动心,与告子之不动心,可得闻与? 告子曰:不得于言,勿求于心;不得于心,勿求于气。不得于心,勿求于气,可。不得于言,勿求于心,不可。夫志,气之帅也,气,体之充也。夫志至焉,气次焉,故曰持其志勿暴其气。 既曰:志志焉,气次焉,又曰:持其志勿暴其气者,何也? 曰:志壹则动气,气壹则动志也。 梳理如下: 其一,得指的是得理(得正)。 其二,言、气、心都是指本己而言,以自己立论,并不是指他者。 其三,告子与孟子的区别在于“不得于言,勿求于心,不可”。告子的养心之道在于断离,以为心不为言所累而求不动心。孟子则持成德之教的立场,认为讲论有得正与不得正者,正须求之于心志,以心正言,方能人文化成。孟子的不动心,在于心志如理自在,非心与事隔之静敛不动。 其四,志与气是一回事,二词只有动静之别。孟子认为人意气应该以心志为主,心志指德性我,内含私端价值自觉,气指生命我或情意我。德性我应为生命我的主宰。体指形躯我,形躯我的活动直接受生命情意的主宰,其以生命力和情意感为内容。以心志统气是成德之境,是应然而非必然,故有存养之道。一方面需要定受其志使价值自觉澄定,二方面勿使其气暴乱不纵生命情意。 其五,公孙丑认为志本能帅气是必然而非应然。壹指定于一,主宰支配义。需要一套工夫论在于持其志无暴其气,义心的升降无必然。德性我如果不能作主宰,则生命情意亦可作主,反制德性我。 其六,综合而言,言指认知我,心指德性我,气指情意我。孟子之学乃成德之教,故必以志帅气,必以心正言。以志帅气,最后境界即为生命情意的理性化,此境界的工夫即孟子所谓的养气。 2,养气之道 《公孙丑上》: 敢问夫子恶乎长?曰:我知言,我善养吾浩然之气。 此说知言是德性我对认知我的临照,养气即德性我对生命情意的转化。 《公孙丑上》: 敢问何谓浩然之气?曰:难言也。其为气也,至大至刚,以直养而无害,则塞于天地之间。其为气也,配义与道,无是,绥也。是集义所生者,非义袭而取之也。行有不慊于心,则绥矣。我故曰:告子未尝知义,以其外之道也。 此详论养气之道。生命情意若能理性化,则经理性化之后的生命力量浩浩然广大无际。此生命力以义为根据,故不可屈不可服(大与刚形容),理性化的生命情意由义理而定向,非寻常的生命冲动能比较(配义与道)。无义理为根的生命情意易竭(绥也)。 训诂问题。 《公孙丑上》: 必有事(事为误写,实是畐即福)焉而勿正心勿忘勿助长也。 经文有误当为:必有畐(福)焉而勿忘(妄),勿忘,勿助长也。此说如理而行必有效果(福),但不可妄求效果,揠苗助长,反为有害。 政治思想 分为三点,其一,民本说,即孟子对于政权转移问题的理论,其二,仁政与王道,其三,仁德效用化及德治观念。 民本说(政权转移问题) 天下之得失系于民心之向背 《离娄上》: 孟子曰:三代之得天下也,以仁;其失天下也,以不仁。国之所以废兴存亡者怡然。此说因仁得民,不仁则失民。 《离娄上》 桀纣之失天下也,失其民也;失其民者,失其心也。得天下有道,得其民,斯得天下矣。得其民有道,得其心,斯得民矣。此说民心决定政权得失,旧说以天命解释政权的转移,孟子直以民心解释天命,唯有将时机和才能归于天而已。 仁政与王道 仁为统一天下者所必须具有的条件,具体为政治设施。 王道即保民。 以尊士为得民之道。 仁之效用化及德治观念 孔子之仁只有纯德性的意义,孟子以为忍者必为天下所归,有效用意义。仁观念的效用化即生出德治的理论。 其他理论 社会分工观念 史观问题 天、性、命之关系
《新编中国哲学史》读后感(五):《新编中国哲学史》第三章孔孟与儒学
第三章孔孟与儒学 (上)孔子与儒学之兴起 就时间次序上说,孔子为第一个建立哲学理论的人(系统性与自觉性),中国哲学史的论述要从其开始。在学说内容上看,先秦儒学虽为其中一家,但汉代以降及至明清,儒学思想一直是中国哲学的主流。 第一节儒学之源流问题 儒学的源流问题可分为儒家的根源和流派的问题,前者涉及两个方面,其一,儒学作为一个学派的演变过程,其二,儒学自身的基本精神和思想与古代的思想、观念、习俗有何种关系。 儒学的学派演变问题。旧说引用《汉书-艺文志》的说法认为先秦各学派出于王官,即每一学派皆由政府中某一部门演变而生。该说确实反映了古代贵族掌握一切知识的史实。但是对于各学派自身的特性和精神不能有明确的陈述,在严格意义上不可取。近代以来另有新说,如胡适《说儒》考证儒学出于殷士。胡适的论据大抵有三点:其一,殷亡国之后为周服务从事礼仪,形成司礼的特殊社群即称儒。其二,孔子及其弟子以礼为业,继承殷士社群的传统。其三,孔子为儒传统的革新者并反映殷民族的复兴要求。胡适的观点只能从外缘方面解释古代儒社群的产生而不能说明作为一个学派的儒学的自身的特性;且孔子继承周文以重建周文为方向,不能说与殷民族的传统直接继承;孔子立说肯定自觉精神透显对普遍性的肯定而无现代民族主义的情绪。 儒学思想和古代观念习俗的关系。首先孔子学说的精神并非承古代观念而来,反有革新的趋向。周人建国以制度为重,主要指两方面,其一建土封君建立一种人为的政治秩序取代部落酋长式的自然政治秩序;其二建立宗法制度将自然血缘关系化入人为的政治之中。周人建立此种政治本意是加强中央集权,但客观上肯定了人的主体价值,表现了一种以人为主的思想趋势。周人的这种精神方向以肯定人的主体地位,是一种由原始信仰进而肯定人文的革新转变。周人表现这种人文精神只在制度方面思想上尚未到自觉阶段(半自觉阶段),真正的自觉要到系统地对人文精神建立系统理论,此一工作即以孔子为代表。 案:本质意义与发生意义。本质意义是哲学理论的内在逻辑的展开,涉及客观的理论与其他外缘无涉,发生意义多半和外缘影响、主观心理状态有关。诸如因迎合帝王提出炼丹术,发生条件是其内在动机,本质意义则是该炼丹术在理论上的客观意义。 儒学的流派问题。大抵分为两种,其一,直承孔子原有方向的;其二,与孔子方向不同者。后者涉及偏离违背孔子精神方向、对孔子理论未能完全继承者等等。 案:牟宗三《心体与性体》综论部分谈及宋代新儒学的“新”涉及两个层面,其一是顺本有者引申发展而为本有理论所涵;其二,在基本处有一定的转向,歧出另一套系统为本有的理论间接地允许而非其本质的直接允许。后者显然是牟宗三所指的程朱一系。 第二节孔子之生平及其学说 孔子之生平(略) 孔子之学说 孔子学说之内容 孔子学说分为两大方面,其一是孔子学说的具体内容,又可分为基本理论和引申理论。其二是孔子所代表精神之方向,可分为自我境界和文化意识。 一,基本理论 礼观念为孔子学说的始点,并由此逐渐升进至仁义诸观念,礼义仁三观念为孔子理论的主脉。 礼有广义和狭义二分。狭义的礼专指仪文,广义的礼则指节度秩序。在孔子之前列国的其他士大夫已经有区分礼和仪的言论。如《左传-召公五年》记女叔齐之言: 晋侯位女叔齐曰:鲁侯不亦善于理乎?对曰:鲁侯焉知礼。公曰:何为?自郊劳至赠贿,礼无违者,何故不知?对曰:是仪也,不可谓理,礼者,所以受其国,行其政令,无失其民者也。 礼取秩序义,与仪文已有本末之分。至于以何解释秩序义的礼的基础,则孔子之前的士大夫普遍将其归于天道,即以天道为礼之本,此承原始信仰而来。如《左传-文公十五年》记载季文子评齐侯之说: 礼以顺天,天之道也。己则反天,而又以讨人,则难免矣。 孔子发展礼的理论,摄礼归义,再摄义归仁,认定礼的基础不在于天而在于人的自觉心或价值意识。一方面继承当时知识分子对礼和仪的区分,另一方面进而肯定人的主体价值,离开原始信仰的纠缠,开创儒学的成德思想。 礼与义 义指正当性或者道理。 《为政》: 子曰:见义不为,无勇也。 《里仁》: 子曰: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 《里仁》: 子曰:君子之于天下也,无适也,无莫也;义之与比。(案:适与莫指赞成或者反对的态度,谓君子无特殊态度惟理是从) 《宪问》: 见利思义,见危授命。 《阳货》: 子曰:君子义以为上。君子有勇而无义,为乱;小人有勇而无义,为盗。 《卫灵公》: 子曰:群居终日,言不及义,好行小慧,难矣哉。 从义的方面论礼义关系。《论语》对二者的关系有明确解释。 《卫灵公》: 子曰:君子义以为质,礼以行之,孙以出之,信以成之。君子哉。 此处“义以为质,礼以行之”。礼依于义而成立,义是礼的实质,礼是义的表现。于是,一切外在的仪文制度,皆以正当性或者理为其基础,人所建立的秩序皆为实现正当而言。至此,一切历史事实、社会事实、心理及生理方面的事实,本身皆不提供价值标准,自觉之意识为价值标准的唯一根源。 从礼的方面论礼义关系。孔子并未全部舍弃仪文的价值,而是追求礼之本。《八侑》: 林放问礼之本。子曰:大哉问。礼,与其奢也,宁俭;丧,与其易也,宁戚。 《子罕》: 子曰:麻冕,礼也。今也纯。俭,吾从众。拜下,礼也。今拜乎上,泰也,虽违众,吾从下。礼之本有两层含义,其一,与仪文相对的本质本然之义,突出礼的生活秩序性意义。其二,礼的基础或根本。仪文的转变不必拘受传统不必顺从流俗,而有其内在理据即孔子所言的义。 (2)仁 1,乾嘉考证问题。 清乾嘉以来,谈儒学者错误的将哲学问题当做训诂问题。哲学家所持的观念的具体含义,不可能通过字源研究而完全了解。哲学家不能自创文字,所使用的词语必是已有文字(至多稍加改变),但哲学家每每使用词语皆有其特殊意并非只是一般使用中的意义,必须要置于其思想系统之内(系统内的约定性)确定其涵义。字源研究只能有补助作用而不能作为解释哲学思想的根据。 2,《论语》中涉及仁的材料。 《雍也》: 夫仁者,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能近取譬,可谓仁之方也已。此以仁为净除私累的境界,不假外求,自我的主宰性。 《述而》: 子曰:仁,远乎哉?我欲仁,斯仁至矣。此说明仁是超越具体条件的大公境界,纯粹自觉自主的活动。 《里仁》: 子曰:惟仁者能好人,能恶人。此说明仁者能立公心,对于外界的事物皆可以依理而立价值判断(好恶指普遍意义的肯定与否定,不指心理反应)。 《里仁》: 子曰:苟志于仁矣,无恶也。此处说明罪恶起于私念,人若能具有仁德,自然可以超越一切罪恶,无私则无恶。 就仁与义的关系说。有私念则求利,有公心则求义,仁为义之本。义为正当性,人之所以能求正当性,在于人能立公心。公心既立,则自然能循理而行,不溺于私欲。 仁与礼的关系。 《颜渊》: 颜渊问仁。子曰:克己复礼为仁。一日克己复礼,天下归仁焉。为仁由己,而由人乎哉?颜渊曰:请问其目。子曰: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言,非礼勿动。此处说明克己即是去私,复礼即是循理。在理论意义上,仁义礼分别为三个层次,礼以义为实质,义以仁为其基础。但就实践程序上说,礼义相连不能分别。故而在上述引文中直接由仁而说到礼。 案:就逻辑思考而言,人必有求严格的意志,在实践中遵循规律进行思考,然后才能在具体的符号演算中求得严格的论果。“求严格的意志”,“思考的严格性”,“演算中的严格论果”三者在理论上显然是三个层次,但在实际的运算程序中,思考的严格性必然借严格的论果才能被体现,不能脱离特定的符号群显示自身。故而可以说在理论程序上仁义礼三观念可分,但在实践程序中义与礼不可分。 礼须归于仁。《八侑》子曰:人而不仁,如礼何?人而不仁,如乐何?此谓仁为礼的基础,无公心则不能建立秩序,因秩序依于正当性,而正当性则依于公心。 引申理论 引申理论分为三部分叙述,其一,正名观念与政治思想;其二,直观念与价值判断;其三,忠恕与成德工夫。 正名观念与政治思想 孔子立说原以解决政治秩序问题为主,礼观念即引申正名思想。 《季氏》: 孔子曰:天下有道,则礼乐征伐自天子出;天下无道,则礼乐征伐自诸侯出。 侵权为政治秩序崩溃的主要原因,重建政治秩序以不侵权为主。 《子路》: 子路曰:卫君待子为政,子将奚先?子曰:必也正名乎。子路曰:有是哉!子之迂也。奚其正?子曰:野哉,由也。君子于其所不知,盖阙如也。名不正则言不顺,言不顺则事不成,事不成则礼乐不兴,礼乐不兴则刑罚不中,刑罚不中则民无所措手足。此说认定为政以正名为本,即说是以划定权分为本。一切政治秩序制度,皆在于决定权利义务。 权分的划定,目的在于使社群中每一分子各自完成其任务。 《颜渊》: 齐景公问政于孔子。孔子对曰:君君,臣臣,父父,子子。此处认为凡是有所名分的人(君臣父子)必须完成其分内的任务,也只能享有其分内的责任。 统一秩序的建立不可以强力征服而为之,强调教化。 《季氏》: 季氏将伐颛臾。冉有、季路见于孔子曰:季氏将有事于颛臾。孔子曰:求!无乃尔是过与?夫颛臾,昔者先王以为东蒙主,且在城邦之中矣。且在邦域之中矣。是社稷之臣也。何以伐为?冉有曰:夫子欲之,吾二臣皆不欲也(此处夫子指季氏)。孔子曰:求!周任有言曰:陈力就列,不能止者......虎兕出于柙(木笼),龟玉毁于椟中,是谁之过与?冉有曰:今夫颛臾固而近于费,今不取,后世必为子孙忧。孔子曰:求!君子疾夫舍曰欲之而必为之辞。丘也闻有国家者,不患寡而患不均,不患贫而患不安;盖均无贫,和无寡,安无倾。夫如是,故远人不服,则修文德以来之。既来之,则安之。今由与求也,相夫子。远人不服,而不能来也;邦分崩离析,而不能受也;而谋动干戈于邦内,吾恐季孙之忧,不在颛臾,而在萧墙之内也。此处是孔子具体政治主张的重要资料,有两点,其一,经济问题以建立公平经济制度为主,有公平制度,自然人民团结,安心工作,自能提高生产。其二,统治者欲得外族拥护,必须修文德以来之,德性指导政治。 反战争,反强力,重教化。 《颜渊》: 季康子问政于孔子。孔子对曰:政者,正也。子帅以正,孰敢不正? 《颜渊》: 季康子问政于孔子,曰:如杀无道以就有道,何如?孔子对曰:子为政,焉用杀。子欲善,而民善矣。君子之德风,小人之德草,草上之风必偃。 《子路》: 子适卫,冉有仆。子曰:庶矣哉!冉有曰:既庶矣,又何加焉?曰:富之。对曰:既富矣,又何加焉?曰:教之。 《卫灵公》: 卫灵公问陈于孔子。孔子对曰:俎豆之事,则尝闻之矣。军旅之事,未之学也。明日遂行。 军队建立在于讨伐有罪者。 《宪问》: 陈成子弑简公,孔子沐浴而朝,告于哀公曰:陈恒弑其君,请讨之。公曰:告夫三子。孔子曰:以吾从大夫之后,不敢不告也。 直观念与价值判断 价值在于具体理分的完成。涉及到两个层面,其一,理分的肯定。抽象的分配不同的权利义务责任显然并不是公平的本旨,而是在于给不同的人依据具体的社会关系角色和情境划定不同的职分。其二,理分的具体性和位阶性。理分的划定要依据于不同的情境中的不同角色,不能彼此逾越和替代,更要重视不同的社会关系之间的价值位阶性。 案:劳思光并没有强调理分的位阶性,似更看重普遍性的观念。 父子相隐与价值问题。 《子路》: 叶公语孔子曰:吾党有直躬者,其父攘羊,而子证之。孔子曰:吾党之直者异于是。父为子隐,子为父隐,直在其中矣。此说正直合理不在于视父子为路人,而在于各尽其父子之理分。 案:举例说一百人从事运石工作,若从抽象的公平来看,则令每一个人从事同样的工作即是合理。但具体地看此一百人之中或老或小或强或弱,各有能力的不同,欲真实现公平而言,则要就具体的条件而决定。 具体理分为义观念的引申。 《公冶长》: 子路曰:愿闻子之志。子曰:老者安之,朋友信之,少者怀之。此说在人生态度方面,以处处尽理分为理想。 案:就政治生活而言,孔子要求尽理分,体现为正名观念,在道德生活方面也要求尽理分,相比较而言道德生活更具有普遍性,后代宋儒大抵先研究道德哲学,再展开其理论,以确定政治生活的价值标准。 忠恕与成德工夫 通过直的观念确定价值判断的原则(依据理分而定),但人之能否对于价值问题作正当的判断不在于对价值的了解,而是关涉意志方向的问题。面对意志本身如何纯化的问题,此是仁观念的引申而有忠恕思想。 孔子以道说仁。 《里仁》: 子曰士志于道,而耻恶衣恶食者,未足与议也。此说道与富贵无关,涉及无私的特性。 《里仁》: 子曰:富与贵,是人之所欲也;不以其道得之,不处也。贫与贱,是人之所恶也,不以其道得之,不去也。君子去仁,恶乎成名。此说要依道而立即是仁,以大公之心进行取舍。 《里仁》: 君子无终食之间违仁。造次必于是,颠沛必于是。此说有德者必须时刻存大公之心。 《卫灵公》: 子曰:赐也,女以予为多学而识之者与?对曰:然,非与?曰:非也。予一以贯之。此说一以贯之的道是指意志的纯化而非零碎知识。道即仁。 忠恕是仁的两方面体现。 《颜渊》: 仲弓问仁。子曰:出门如见大宾,使民如承大祭。己所不欲,勿施于人。此说恭谨诚敬。 《卫灵公》: 子贡问曰:有一言可以终身行之者乎?子曰:其恕乎!己所不欲,勿施于人。此暗合宋儒尽己之谓忠,推己之谓恕。 仁德的达成,必通过忠恕的实践工夫。自处不为私欲所动是忠,处人视人如己不侵人自利是恕。 《颜渊》: 司马牛问仁。子曰:仁者其言也讱(迟钝)。曰:其言也讱,斯谓之仁仪乎?子曰:为之难,言之得无讱乎? 《学而》: 子曰:巧言令色,鲜矣仁。 《雍也》: 樊迟问仁。曰:仁者先难而后获(收获),可谓仁矣。 孔子之精神方向 精神方向,确指价值意识而言,表现在三个方面。其一,文化问题,涉及孔子的宗教观及宇宙观等;其二,自我问题,涉及纯哲学的自觉心的问题;其三,传达问题,涉及孔子对理论学说的看法和学与教等问题。 孔子对文化问题的态度 孔子对文化问题的基本态度。人的主宰性的肯定即人文之学。涉及两个方面,其一,从正面肯定人的主宰性,这部分已经由仁义礼观念加以阐明。其二,对客观限制和主宰性的冲突问题作出解答,这方面的问题涉及到孔子对命的看法,基本观点为义命分立。 义命分立。 《雍也》: 伯牛有疾。子问之,自牖执其手曰:亡之,命矣夫。斯人也,而有斯疾也,斯人也,而有斯疾也。此说命为客观限制与义表示自觉主宰不同。 《宪问》: 子曰:道之将行也,命也;道之将废也与,命也;公伯寮其如命何?此说道之应行和能行是两回事,应行与否归于义(应然),能行与否归于命(事实问题)。人所能负担的只是价值是非问题而不是成败的事实问题。 《宪问》: 子路宿于石门。晨门曰:奚自?子路曰:自孔子。曰:是知其不可而为之者与?此说孔子划定义命的界限,不计成败,惟求理分的完成。 《微子》: 子路曰:不仕无义。长幼之节,不可废也,君臣之义,如之何其废之?欲洁其身,而乱大伦。君子之仕也,行其义也;道之不行,已知之矣。此说肯定人的责任,不计成败,但求尽理分。自觉主宰的领域是义的领域,此领域中只有是非问题;客观限制领域是命的领域,此领域中则有成败的问题。 《为政》: 子曰:吾十有五,而志于学;三十而立,四十不惑,五十而知天命,六十而耳顺,七十从心所欲不逾矩。此说五十之前在于培养个人的主观意志,之后则转向客观方面,知天命即谓知客观限制,于是主客之分皆定,自觉心朗现,人文价值得以肯定。是非与成败区分开来,所谓原始信仰的天命天意观念不再与价值意识相混。 从理论上看对命观念有四种态度。其一,以为天命不可违,故人应努力实现此天命。义命相混。比如以命归于超越的人格神及墨子的天志观念(神权主义)。其二,将命作为事实意义上的必然,没有超越价值,人顺此规律活动。诸如受经验科学影响下的自然主义的立场(物化主义)。其三,承认命的客观限制,并认为自我在此领域中根本无可作为,因而要自求超离。以离命为义。比如道家的无为思想和印度解脱之宗教(舍离主义)。其四,区分义和命,划定各自的领域,然后在主宰性的领域建立价值和文化标准,将客观限制作为质料条件。在命中显义(人文主义)。 孔子对原始信仰中的天神鬼观念皆不重视。 《先进》: 季路问事鬼神。子曰:未能事鬼,焉能事神?敢问死,曰:未知生,焉知死?此说孔子不喜谈原始信仰。 《八侑》: 祭如在,祭神如神在。子曰:吾不与(参与)祭,如不祭。此说孔子更重视人内心的诚而不注重受祭一方的神。 《雍也》: 樊迟问知。子曰:务民之义,敬鬼神而远之,可谓知矣。此说为人文精神日益透显纯粹之后,原始信仰即逐渐失去势力。 宗教的三个特性。其一,人格神,肯定一超越的主宰,以之为最后的决定者。其二,以人格神作为价值根源(一切价值标准的最后根据)。其三,人神关系的酬恩观念,涉及一系列宗教仪式和心理。这三个层面分别涉及必然问题、价值问题和义务问题。 儒家思想涉及的自由和必然的问题。一切事物在性质和关系上都是已经被决定了的(命),无论人是否了解此种事物的性质和规律,皆不影响其已经被决定。在对象界中,人与其他事物同为一被决定者,命的限制性实为一客观事实。若只从人被命所决定的这一层面上看,则人生一切事象皆在必然系列下被决定,进而无所谓是非善恶观念,价值与人文亦不能建立。但孔子在命之外立一义的观念,价值、自由、人生意义等观念运行的领域即由此显出,而这一领域的建立的前提在于断定人能作价值判断。人作为一经验性存在,无论生理心理物理层面上均属于条件系列之中而被决定。但人除了作为一经验性存在之外,还有自觉能力,进而有应该或者不应该的意识(价值意识),此种意识决定人有一内在动力(意志)决定其行为方向(价值选择与价值定向)。人能在此自觉的领域自作主宰,从而凸显人在这一领域的自由与在命一方面的必然被决对区分。人所应该努力的领域亦是此自觉的领域(义),人也只能在求正当性(义)上努力表现其主宰性。 儒家思想涉及义务问题的方面。孔子承认生命基本责任的观念,但此责任不存在神人和人与物之间,而在人与人之间(人伦)。人伦观念起源于人作为一个个体,必须接受各种人的助力,因此,人必须对其他人有某种酬恩的义务。 《阳货》: 宰我问三年之丧,期已久矣,君子三年不为礼,礼必坏;三年不为乐,乐必崩;旧谷既没,新谷既升,钻燧改火,期可已矣。子曰:食夫稻,衣夫锦,于女安乎?曰:安。女安则为之;夫君子之居丧,食旨不甘,闻乐不乐,居处不安,故不为也。今女安则为之。宰我出。子曰:予之不仁也。子生三年,然后免于父母之怀。夫三年之丧,天下之通丧也。予也有三年之爱于其父母乎?此说孔子以三年之丧为孝道的体现,而之所以应该如此又在于子生三年免于父母怀抱,这是一种酬恩的心理。每一个人自出生之日起,即已接受社会的各种直接或者间接的助力,因此人对于社会有一酬恩的态度,此通过孔子的人伦观念体现。人既对社会抱有一种酬恩的态度,则可以说人终身对他人有普遍性的责任,落实在具体的社会关系中,即有具体的内容,此即是理分。 儒家思想对于历史文化的态度。秉持酬恩的态度而来,对于古代的文化成绩皆无仇视的态度。 《述而》: 子曰:述而不作,信而好古,窃比于我老彭(窃比我于老彭)。此说孔子尊重古人成绩。 《为政》: 子曰:殷因于夏礼,所损益可知也;周因于殷礼,所损益可知也;其或继周者,虽百世可知也。此说孔子并不迷信古人,重视文化的传承与升进。 《八侑》: 子曰:周监于二代,郁郁乎文哉。吾从周。此说孔子观前代的成绩肯定周文的精神。 孔子对自我问题的态度 自我问题为哲学的基本问题之一,理论性极高,孔子论及此问题自然没有稍后出现的其他诸家学说,但在《论语》中已有相当程度的态度流露而出。先从仁知勇三观念引出孔子的基本主张。 《子罕》: 子曰:智者不惑,仁者不忧,勇者不惧。 《宪问》: 子曰:君子道者三,我无能焉。仁者不忧,智者不惑,勇者不惧。 《宪问》: 子曰:有德者必有言,有言者不必有德,仁者必有勇,勇者不必有仁。以上以仁知勇合说,认为仁可以决定知和勇,而后两者不能决定仁。 自我境界的设准。大抵有四个层面的设准,其一,形躯我,以生理和心理欲求为内容。其二,认知我,以知觉理解和推理活动为内容。其三,以生命力和生命感为内容。其四,德性我,以价值自觉为内容。 形躯我在孔子思想中无重要地位。 《卫灵公》: 子曰:志士仁人,无求生以害人,有杀身以成仁。此说身之生死不足计,惟求德性实现。 《雍也》: 子曰:贤哉,回也。一箪食,一瓢饮,在陋巷,人不堪其忧,而回也不改其乐。贤哉,回也。此说君子以明德性为本,不以穷困为意。 《卫灵公》: 子路愠见曰:君子亦有穷乎?子曰:君子固(固然)穷,小人斯穷(困顿)滥(无所作为)矣。 认知我无独立性。 《卫灵公》: 子曰:知及之,仁不能受之;虽得之,必失之。此说知识问题不重要。 《子罕》: 子曰:吾有知乎哉?无知也。有鄙夫问于我,空空(通悾,诚恳义)如也,我叩其两端(问题的前和后)而竭焉。此说不重视知识量的储备。 《颜渊》: 樊迟问仁。子曰:爱人。问知。子曰:知人。樊迟未达。子曰:举直(正直的人)错(管理)诸枉(邪恶的人),能使枉者直。此说就知本身而言,其价值亦在于了解人本身。知的作用亦在于辅助德性的完成。 情意我(生命力和生命感,前者指勇敢坚毅等品质,后者表现于艺术活动)依附于德性我,受其制约。 《八侑》: 子谓韶,尽美矣,又尽善也。谓物,尽美矣,未尽善也。此以德性观念为基础评价音乐艺术。 《卫灵公》: 颜渊问为邦。子曰:行夏之时,乘殷之辂,服周之冕,乐则韶舞。放郑声,远佞人;郑声淫,佞人殆。此说艺术受德性制裁。 《阳货》: 子路曰:君子尚勇乎?子曰:君子义以为上。君子有勇而无义,为乱;小人有勇而无义,为盗。此说德性自觉可以生出一种生命力,但生命力不受德性主宰会滋生罪恶。 孔子对理论学说的态度 学指进德而言。 《雍也》: 哀公问弟子孰为好学。孔子对曰:有颜回者好学;不迁怒,不贰过。不幸短命死矣。今也则亡。未闻好学者也。此说好学的学并不指知识,全属于进德之事。 《公冶长》: 子曰:十室之内,必有忠信如丘者,不如丘之好学也。此说好学指德性的升进。 当机立教。教人不以建立某种客观知识论证,而在于改变受教者的意志状态。 《先进》: 子路问:闻(听到)斯行(行动)诸?子曰:有父兄在,如之何其闻斯行之?冉有问:闻斯行诸?子曰:闻斯行之。宫西华曰:由也问闻斯行诸,子曰,有父兄在;求也问闻斯行诸,子曰,闻斯行之。赤也惑,敢问。子曰:求也退,故进之;由也兼人,故退之。此说教人以改变其本有的缺点而不是授予知识,目的在于提高价值自觉,培养意志,理论学说皆属于附属条件。 孔门学派与孔子遗留问题 孔子早期弟子,除颜回早死之外,其他人大抵只得孔子政治思想,以礼乐为主。晚岁成熟思想,由曾子继承。 遗留两大问题:其一,自觉心如何证立。孔子立说的最大特点在于将道德生活的根源归于自觉心,由此凸显主体自由,另一方面将主体性客观化使得价值意识直通生活秩序和制度。但自觉心如何证立的问题孔子并未提及。其二,政权转移问题(是否应转移,以何种形式转移)。孔子以正名思想划定政治生活中的各种职分,但当君不君的时候国家政权应该如何则没有提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