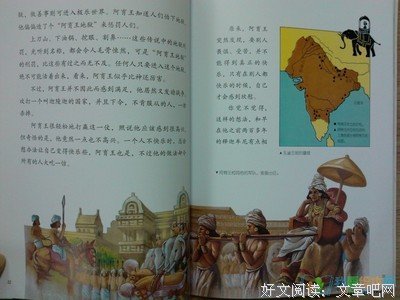
《给孩子的故事》是一本由王安忆著作,中信出版社·活字文化出版的精装图书,本书定价:42,页数:291,特精心从网络上整理的一些读者的读后感,希望对大家能有帮助。
《给孩子的故事》读后感(一):愿我们天天有故事相伴,温暧且精彩
我是个很喜欢看书的人,
从上学到现在,
看了很多很多书。
读书,
确实可以打开一个更广阔的崭新世界,
身体不能走在路上的时刻,
我们的精神,
也要活动一下
.
很不错的故事书,
内容很丰富,
故事有血有肉很生动。
有我熟悉的场景,
会撞击心灵;
也有我陌生的场景,
但我敬畏那份心情。
是一本很适合中高年龄孩子阅读的故事书。
纸质
《给孩子的故事》读后感(二):不仅仅适合孩子阅读,也适合成人~~~
《给孩子的故事》由作家王安忆编选,在中国当代作家作品中,遴选出27篇经典,其中以短篇小说为主,也有数篇散文。在编选过程中,王安忆跳脱出“儿童文学”的概念,在所有的故事写作中,挑选出适合孩子阅读的篇目。
《给孩子的故事》中收入的“故事”以小说为主,但王安忆的编选标准并非从文体出发,而在于给孩子一个有头有尾的文本,其中有几篇散文,也是有人和事,有发展和结局,称之“散文”是因为来自真实的经验,不是虚构,是非虚构,但并不违反叙事完整的原则。这是编者出于一种让孩子的阅读“回到人类的童年时代,漫长的冬夜,围着火炉听故事”的经验期待。
《给孩子的故事》中所选篇目的主题有着鲜明的价值取向,但并不是某种教育或灌输,而是希望营造一个原初而单纯的世界,去烛照孩子的心灵,如王安忆所言,她的编选原则“是一种天真,不是抹煞复杂性的幼稚,而是澄澈地映照世界,明辨是非”。
《给孩子的故事》读后感(三):这些故事
《黄油烙饼》和《大风》,奶奶与孙子,爷爷与孙子的故事,让我想起了爷爷。
我是爷爷奶奶一手带大的,用现在时髦的话儿来说,是个留守儿童。
爷爷不爱笑,很瘦,很节俭,常常被奶奶说铁公鸡,脸上有一道道深刻的褶子。爷爷做什么都很认真,他做的簸箕,竹具都很细致,漂亮。
爷爷还很爱干净,烧得一手好菜,特别是红烧肉。自从他去世后,我再也没吃过红烧肉了。
大概是因为我爱念书,最乖巧,爷爷很疼我,不是平日里什么东西都紧着我的疼,是时常念叨我的疼;是每次知道我回家,都早早的坐在门口假装喂鸡,其实是在等我的疼。轻快的叫一声“阿公!”, 他总是满不在乎的一句,“回来了,饿了厨房有吃的。”
爷爷没有那么幸运,在世的时候没有过上好日子,去世的时候全身插满了管子。
随着时间的流逝,悲痛的情感不再像开始时那般汹涌,那般撕心裂肺,那般占据你所有的情感,侵蚀你的生活。
只是会在不经意的时候袭来,让你怅然若失,让你实实在在的感受到,心底某个位置的空缺这辈子到底是无法填补了。
但是这种悲痛,也会提醒你,让你明白生命中对你而言真正重要的事。
《拣麦穗》里,“我“与卖灶糖的老汉的“婚约”让我觉得很可爱;《高女人和他的矮丈夫》的故事则令人感动而又惋惜。我们的社会发展的很快,每个人都想要抓住些什么,获得些什么,包括一切的情感和关系,我们要先把这些关系打上价格标签,才能衡量值不值得投入。卖灶糖的老汉与“我”,高女人和矮个子之间简单,不带利益关系,让人费解的感情在我们看来总是显得太傻气。然而爱本就是无用的,不是因为你对我有用所以爱你,而是我爱你就是我爱你,不带附加条件,彼此不计较付出。
还有《种在坟上的倭瓜》《孕妇和牛》《驮水的日子》中与自然有爱的互动,草原上盛开的《红花蕾》,《春雨之夜》绽放的耀眼的友谊之花,还有好多好多。
这里面的故事有悲欢离合,有丑陋,有美好,有真情,也有假意,这些故事带给我们最简单的触动,唤起我们去掀开历史一角,去提问的好奇心,也带给我们警醒和思考。
而这些,我想不论是对孩子还是大人来说,都已经足够值得去翻开这本书。
《给孩子的故事》读后感(四):过去的故事,共通的感情
给孩子的系列作品陆续出版,在书店大略翻阅过我便坚信这套书绝对值得入手。由于自己孩子还小,所以我自己先看,准备以后她上小学了再亲子共读。第一本看了《给孩子的汉字王国》,是一位对古文字研究颇深的外国学者所著,篇章分类简单,语言简洁,大人读起来很轻松,可以再口语化复述给孩子。通过了解汉字的起源和发展,帮助给孩子讲解学习汉字。而这本《给孩子的故事》也同样是诚意满满的一部作品。编者王安忆就是我个人很喜欢的作家,所以对于她的文学审美,我也很认同。正如她在前序所说,作品文海浩瀚,孩子的年龄范围广,如何选定颇费踌躇,但无论如何入选的作品都有其值得欣赏的不同之处。
可以看出每篇作品尽量选取不同角度描述了孩子所能遇到的不同感情,例如亲情、友情、爱情。或是温暖、或是酸涩,都是我们在成长中会遇到的,尽管很多故事发生的背景已经离我们现在的时代有些距离,但感情是共通的。比如苏童的《小偷》,把孩子面对喜欢的玩具,想要拥有又背负着偷窃的罪恶感那种挣扎、矛盾的心情描写得非常真实,孩子间不用言说的了解与友谊、背叛与谅解,以及原生家庭对孩子的影响,短短一篇文章中淋漓尽致。冯骥才的人物形象描写自有其特色,以前看过他的《俗世奇人》,每个人物形象都生动有趣,跃然纸上。《高女人和她的矮丈夫》的人物外形描写也延续了他的一贯风格,不过故事却有些沉重,在当时的时代背景下,类似的悲剧屡见不鲜,由此篇可以管中窥豹,历史仿佛滚滚而来不停歇的车轮碾过芸芸众生,我们如同蝼蚁,只能徒劳挣扎。
有人觉得给孩子的应当是美好的童话,不要过早让他们接触到世事无常,可我觉得孩子其实能感知很多事情,通过这些给孩子的故事,他们会知道曾经的历史以及共通的感情。正如郝广才曾经说过:“一本好书未必能找到最完美的解释,也未必能回答孩子的疑问,但它能提供一个‘体会的过程’,让孩子学会打开情感的出口和入口。”
《给孩子的故事》读后感(五):命运中的幸运
“印出来出来的效果还真不赖!
5月初的一个漫天黄沙之后的傍晚,编辑部的小伙伴们一边传递着美编从六环外的北京带回的热乎乎的《给孩子的故事》样书,一边不由自主的赞叹。
而在今年春节前,同事转来王安老师忆定下《给孩子的故事》的篇目,乍看之下,真有些吃惊。专业读了好几年的现当代文学,余华、史铁生、苏童、迟子建等也算自己喜欢的作家,而整整二十五篇选目中,居然除《黄油烙饼》外,几乎毫无印象印象,这可如何是好?
“目标读者能接受这样的‘陌生化’选本么?”
“只选八十年代以来的作品,评论界会不会有意见?”
“ 好几篇都写到死亡,还有关于婚外恋的情节,家长能否放心让孩子读”
基于编辑的职业习惯,脑袋中不免有一个又一个问号冒出来。
而真正进入编辑流程,将这些故事电子版反反复复。认认真真读过好几回后。所有的疑虑都消失不见了。
一边读稿,一边笑,一边哭,甚到孔夫子上出高价买了入选作家的绝版旧著。编辑工作完成后,甚至有种怅惘之感,这是怎么回事?仔细想想,大概是因为王安忆老师的用心与功力,让动人的故事,让文学的魅力,再次击穿一位中年人自以为是的“铁石心肠”吧。
对于这本书,不想制造悲情话题,也不想用传销式宣传,编辑能能感受到的,读者一定也能感受到。
从年纪最长的汪曾祺到1970年代的张惠雯,或多或少,或直接或间接,王安忆都曾亲身接触过,对于这些同时代人,了解他们的道德感情,信任他们的语言文字,才能笃定地挑选出一篇篇来组成这本交织着各种情感、世间万象的故事集。
而这已是“给孩子”系列的第八本了。在北岛、李陀、叶嘉莹、黄永玉、李泽厚、林西莉之后,如何为新世纪出生的孩子们提供真正有益于他们心灵成长、滋养一生的读物,《给孩子的故事》的面世,将让这条探索的道路更加宽阔而明晰。
简•奥斯汀曾经在《诺桑觉寺》中借一位埋头读书的姑娘说出自己对于18世纪方兴未艾的小说的看法:“或者,简言之,不过是这样一些作品,它们展示了最有力量的思想、关于人性最透彻的知识以及对人的复杂性的最精妙描绘;它们用最恰当的语言向世人传达最生动活泼、恣肆汪洋的机智与幽默。”《给孩子的故事》是是这样一些作品,它是我们这个时代最“有情”的写作者们所合力完成一项心灵工程。
在人工智能即将席卷一切,人类文明不知伊于胡底的时代,慢腾腾地,以近乎手工业的方式做这样“人文”的事情,冀望为下一个千年留存一点文明的火种。对于身处“夕阳产业”自己而言,真是名符其实的“命运中的幸运”
无论早还是晚,无论孩子与否,能遇上这些由“蜜与蜡”所浇筑的故事,体会着它们所携带的温暖与光明,品尝着其中种种滋味的人,有福了!
《给孩子的故事》读后感(六):为孩子澄澈地映照世界°
——评《给孩子的故事》
文/蓦烟如雪
幼年我看的第一本书是狄更斯的《大卫·科波菲尔》,虽说那书绘图多过文字,但也从中体会了主人公跌宕起伏的命运,受此启发,我对故事有了新的认识。而当我翻看《给孩子的故事》,在序言中,我对编者王安忆说的‘有头有尾的文本’有了共识,既“你要讲一件事情,就要从头开始,到尾结束,这是‘故事’的要旨。”
《给孩子的故事》是北岛主编“给孩子系列”的第八部,由著名作家王安忆选编出25篇中国当代经典的短篇小说及散文,在编选过程中,她跳出惯常的“儿童文学”的概念,在所有的故事写作中,挑选适合孩子阅读的篇目。这些所选篇目的主题有着鲜明的价值取向,但并不是某种教育或灌输,而是希望营造一个原初而单纯的世界,去烛照孩子的心灵,如王安忆所言,希望追求一种天真,不是抹杀复杂性的幼稚,而是澄澈地映照世界,明辨是非。
这25篇作品,均来自中国当代最具代表性的作家之手,例如汪曾祺、史铁生、贾平凹、莫言、余华等等。作为一个文学爱好者,书中的内容,我大多是首次阅读,编选者眼光敏锐,所选篇目与通常所看到的儿童文学或者青少年文学有很大不同,传达的是一种平起平坐的视角,将社会、人性、欲望、友情等等冷静而又不失温情地展示给孩子。
从《黄油烙饼》中,我们能感受到饥荒年代的特殊,也能从萧胜的内心世界,感触与奶奶不一样的情感升华;《高女人和她的矮丈夫》虽然在题目上显示了差距,但是这篇故事很暖心,高矮没有距离,他们爱着对方,不去辩解什么,矮丈夫在妻子离开后,那雨天撑伞空出的距离,依旧让我唏嘘;《小尾巴》从题目就有一种拖油瓶的感觉,但是在妈妈的眼中,小尾巴珍珍是她的全部,即便打乱农活,影响了收割,她依旧无怨无悔,面对孩子丢失,那种焦急的描述和文字中渗出的母爱,让人记忆犹新;而余华的《活着》那种灰调色差,让人深刻,而书中的《阑尾》却是用一种很调侃式的文风去淡化孩子对父亲造成的伤害,每每翻开,篇篇都有闪光之处。
从《黄油烙饼》理解亲人离世的悲痛;从《小偷》中认识友情的珍贵,甚至能从《爱》中体悟爱意的萌动,一个好的故事必然有触动人心的源点,而这些作品,不仅带着自身的文化印记,更浓缩了作者的才华,讲故事是一个传递的过程,它不仅为孩子打开了想象天地,更为孩子展现了故事中不同人物的命运,孩子能在文学中,体味真实,感触悲欢离合,这不仅是与故事人物同悲共喜的情感共鸣,更是审视自我,塑造心灵的渠道之一。编者打破文体界限,回到文学源头,不仅仅是为孩子,也为我们这些成年读者提供保有美学本能的完整故事,让我们感受到最原初的阅读乐趣。
一个好故事它呈现的不仅仅是真善美,更多是引导性的成长。作为成人,或许我们都该反思,
如何去呈现故事的多元化,如何让孩子继续享受于阅读带来的快感。如果这里的25个故事,给了你启发,让你重新审视人生的意义,或许这个故事就有了价值,有了延续的活力。
《给孩子的故事》读后感(七):故事的魅力
文/
童年时,我家与姥姥家住在一个大杂院里。院子中央有棵粗壮的丁香树,夏日清晨,微风吹过,幽香扑面。姥爷早上有个习惯,就是将半导体收音机放在院中的石礅上,边洗漱边听。长大后才知道,他听的是“评书连播”,里面时不时地传出拟人的兵器相撞声音,偶尔还模仿马蹄由远及近的动静。
上学以后,我也爱上了听评书,中午放学就忙三火四地向家奔。从小方盒子里不仅有我钦佩的英难,还有我想交的朋友。这便是最早故事之于我的魅力。那时家里不富裕,很少买故事书。我是听故事长大的一代。
现在孩子们幸福了,从胎教到早教,再到幼教,从小就有各种各样的布艺书、童话绘本、经典名著。但同时,信息泛滥的时代,势必造成阅读的慌不择食,父母又担心孩子们受到不良书籍的影响。再加上社会竞争激烈,学业繁重,初中以后读故事书几乎是被禁止的。虽然父母用心良苦可敬,却素不知这种举动扼杀了多少故事大王和小说家呀!
《给孩子的故事》,是著名作家王安忆编选的故事集。如何定义“儿童”,她的意见清清楚楚:“十岁至十五岁,抑或十六岁,大概也不排除十七岁,将成年未成年,我们称之为‘少年’。这个成长阶段相当暧昧,不能全当成大人,但要当作孩子看,他们自己首先要反抗,觉得受轻视,不平等”。也就是说,多大年龄应该读什么样的故事,并不完全是家长主导的事情。现代家庭都主张“民主”,在读故事书这件事上,还是要尊重孩子们的选择。
关于选本,王安忆说,第一,她并未拘泥于孩子认知,因为大人也未必比他们精灵。但孩子们是“素人”,希望这些故事带给他们一颗澄明的心,至少要有一种天真,要能明辨事非; 第二,为什么是故事,而不是小说?如果按照之前的“给孩子”系列,从诗歌,散文,自然就该到小说了。但小说可能更关注于技巧和延展,而故事更接近于内核。每个人都有依在奶奶怀里,听故事的经历。围炉听书的夜晚,恍然如梦,当翻开《给孩子的故事》时,那些过去的事情仿佛又回来了。我们都是“有故事”的人,这就是故事的魅力。
书中共选取故事二十五篇,都是当代名家作品。从诺贝尔文学奖得主莫言,到能讲“小说课”的毕飞宇,再到专写儿童文学的曹文轩,个个都是讲故事的高手。这些故事,无论是祖孙情深,还是少年友谊,又或人与动物交朋友,我们都能读到人性纯良的光辉。即便有人年轻无心失错,日后也必会认真改过。如果读者认为这些作家写的都是真的,那必是好故事!因为故事里的人已经走进了你的生活,而你也在故事中找到了自我。这也是故事的魅力。
特别想推荐其中几篇:汪曾祺的《黄油烙祺》,写出了少年萧胜与奶奶的情深意重; 莫言的《大风》,着重描绘与爷爷一起跟暴风雨搏斗的星儿,学会了生命的力量,终生受益。莫言的景物描写堪称绝妙,配合故事情节,读起来别有滋味; 张洁的《拾麦穗》,从故事里向外散发微热,一位卖灶糖的老人,却带给了小姑娘难以忘却的温暖。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是用爱的纽带联系。这仍是故事的魅力。
在故事里,我们都想遇见一个更好的自己。
转载请豆邮联系
《给孩子的故事》读后感(八):给成年人的问卷
如果你以为本书的内容跟书名一样,是纯粹给孩子看的故事,你一定会大吃一惊。因为无论是从内容抑或风格来看,这些“故事”都绝非是一般孩子所能理解的。里面选取的故事,很多都是带有“伤痕文学”的影子。在集体失语,理智丧失的疯狂年代,那些直面人性,素面朝天与生命对话的文字更像是给成年人的一份问卷。就像王安忆在选编故事的时候就说过:
“原来,我要的是一种天真,不是抹杀复杂性的幼稚,而是澄澈地映照世界,明辨是非。”
在这些故事里,让我触动最深的就是迟子建写的《逝川》。同为东北籍女作家,迟子建和她的前辈萧红的文风非常相似。不知道是不是地处苦寒之地,她们的笔触都有一种指触眉骨的凌劲,女性的柔软又让她们对生命的轮回和无常有了更广阔天地的怜悯和洞察。如果说萧红的那支笔是白雪里凄冷的一轮明月,人间悲苦,世态荒凉在月水下无声流淌,冷彻心扉。那么迟子建的一支笔则像是奔流的一条河,严寒会把它冰封,裂痕触目惊心,但她始终用温热的一颗心去等待寒冰消融。萧红看到黑土地上的世常是蝼蚁一样的活命,麻木又寂静无声。迟子建看到这片土地世世代代的女性,都在用一种近乎“宿命”一样的顽强去与自然抗衡,无怨无悔,悲欣交集。
《逝川》的一开篇就是无与伦比的壮阔,
“大约是每年的九月底或者十月初吧,一种被当地人称为“泪鱼”的鱼就从逝川上游哭着下来了。”
什么是“泪鱼”呢?迟子建的这一大段描写为逝川注入寓言一样的悲壮色彩:
“这种鱼被捕上来时双眼总是流出一串串珠玉般的泪珠,暗红的尾轻轻摆动,蓝幽幽的鳞片泛出马兰花色的光泽,柔软的鳃风箱一样呼嗒呼嗒地翕动。渔妇们这时候就赶紧把丈夫捕到的泪鱼放到硕大的木盆中,安慰它们,一遍遍祈祷般地说着:“好了,别哭了;好了,别哭了;好了,别哭了……”从逝川被打捞上来的泪鱼果然就不哭了,它们在岸上的木盆中游来游去,仿佛得到了意外的温暖,心安理得了。”
老渔妇吉喜是逝川生命力最强盛的一个女人,迟子建不去写她年轻时的美貌,只是强调她大口咀嚼生鱼的那股生猛劲子:
“夏天总是穿着曳地的灰布长裙,吃起生鱼来是那么惹人喜爱。那时的渔民若是有害胃病而茶饭不思的,就要想着看看吉喜吃生鱼时的表情。吉喜光锐的牙齿嚼着雪亮的鳞片和嫩白的鱼肉,发出奇妙的音乐声,害病的渔民就有了吃东西的欲望 。”
年轻时的吉喜不仅会捕鱼,还会刺绣,裁剪,酿酒。她爱上了能骑善射的猎人胡会,认为百里挑一的自己会是胡会的新娘,没想到最后他娶的却是一个平平无奇的女子。
“胡会结婚那天吉喜正在逝川旁刳生鱼,她看见迎亲的队伍过来了,看见了胡会胸前戴着的愚蠢的红花,吉喜便将木盆中满漾着鱼鳞的腥水兜头朝他浇去,并且发出快意的笑声。胡会歉意地冲吉喜笑笑,满身腥气地去接新娘。吉喜站在逝川旁拈起一条花纹点点的狗鱼,大口大口地咀嚼着,眼泪簌簌地落了下来。”
她什么也没做错,胡会对她说:“你太能了,你什么都会,你能挑起门户过日子,男人在你的屋檐下会慢慢丧失生活能力的,你能过了头。”
这样直白的一句断言,似乎把吉喜的一生都望到了尽头。吉喜一天天的织网,捕鱼,平静的老去。她开始频繁的为逝川的女人接生,甚至在泪鱼到来的这一天,还在为胡会的孙媳妇儿接生,尽管胡会那时已魂归故土。吉喜不是没有怕过,当地世世代代的传说便是泪鱼下来的时候,如果哪户没有捕到它,那么这家的主人就会遭灾。最终吉喜错过了泪鱼,胡会的孙子喜悦地迎来了一对龙凤胎。看到这里,我的心开始隐隐地疼起来。大自然的迁徙已落幕,欢闹的人潮褪去后,剩下的一个倔强而丰盈的灵魂是这样的孤独和不甘。最后吉喜还是惊喜的发现了木盘里静静游动着的蓝色泪鱼,这是逝川的人们给这个了不起的女人无声的敬意。迟子建的文学世界是充满“灵性”的,无论是奇幻的泪鱼,善良强悍的吉喜,还是新生的婴儿和生生不息的渔村。就算生命有过脆弱和不公,总会在周而复始的自然轮回中得到救赎。迟子建借用吉喜的口吻感叹道:
“泪鱼是多么了不起,比人小几百倍的身子,却能岁岁年年地畅游整条逝川。而人却只能守着逝川的一段,守住的就活下去、老下去,守不住的就成为它岸边的坟冢,听它的水声,依然望着它。”
《给孩子的故事》读后感(九):逐一点评,总体上还是不错的
我一开始也很好奇,王安忆为什么愿意编这个选集?不过,后来看方卫平的书知道,王安忆最早就写过儿童文学,比如她曾在儿童文学刊物《儿童时代》担任过编辑,她发表的第一篇小说是《谁是未来的中队长》(《少年文艺》杂志,1979)。她和儿童文学是有渊源的。
这本集子的二十五篇故事不止是小说,也有叙事性的散文,虽然单看文本,两者也不是那么容易区分。有些故事的主角是儿童或使用儿童视角,有些则远远超出了儿童的生活,包括成年人的工作、父母一辈的婚姻,等等。在序言里,她也表达了对给孩子的故事的观点:“我要的是一种天真,不是抹杀复杂性的幼稚,而是澄澈地映照世界,明辨是非。”
王安忆的视野渊源超出了儿童,恐怕高中生、大学生也不是很好懂。当然,什么叫做懂?有些小说故事性、趣味性强,这自然好读也爱读(比如余华深谙此道),有些则因为其隐喻带来的多义性,不是很好解读(比如铁凝、阿来、迟子建),有些,则淡淡的,需要仔细去品,才能得到滋味(汪曾祺、张慧雯)。另外,这些故事的背景,比如说大跃进、反右、文革,等等,今天的孩子未必了解。对孩子而言,也称得上“大开眼界”了。
汪曾祺《黄油烙饼》 背景是“大跃进”,儿童视角,主人公萧胜的奶奶被饿死了。这篇小说看起很平淡,不以情节曲折吸引人。“黄油烙饼是甜的,眼泪是咸的。”也有对干部的讽刺。
高晓声《摆渡》 作家更给摆渡人什么?真情实意。如果没有摆渡人,那他就自己摆渡。“原来创作同摆渡一样,目的都是把人渡到前面的彼岸去”。
张洁《捡麦穗》“在农村长大的姑娘,谁不熟悉捡麦穗这回事呢?”卖灶糖的老汉老去了。(曾入选北师大版初中《语文》教材七年级上册)四星。
冯骥才《高女人和她的矮丈夫》背景是文革。裁缝老婆这种人,倒是比高女人和矮丈夫还要抢戏。林子大了什么鸟都有,这种人可恶自不必说。可是时代竟然给了她机会,“整人”之卖力程度,好像家里办喜事。(曾入选苏教版高中语文选修教材《短篇小说选读》)四星。
贾大山《杜小香——梦庄记事之二十二》 背景是知青生活。不是很明白为什么选这篇。
张承志《红花蕾》仍然是没有什么起伏的故事,牧区的小女孩巴达玛让我想到了纪录片《雪落伊犁》。“我的心里涌起一阵潮水,一阵对这小女孩和长满红花蕾的草地的眷恋。”四星。
阿成《春雨之夜》老驼是一个诚实的人。不过,作者也有很多闲笔,写他穿过胡同街巷,想到了当年自己开车喜欢溅人泥点子,写老驼找女人(可以写吗?)落脚点是友情和信任。
王璞《捉迷藏》 这个故事的展开,真的是让人出乎意料。印象很深。五星。
史铁生《合欢树》旧文重读。突然想到,史铁生很少写爸爸,我一度误认为他来自单亲家庭。
刘庆邦《种在坟上的倭瓜》还行,好像也没什么可说的。
贾平凹《一位作家》写自己刚辞职,专心搞创作的那段经历。当代陋室铭,有那么一点自得,甚至不无自恋。《静虚村记》相比而言,感觉在心态上可能更沉静一些。
曹文轩《小尾巴》牙碜的很,不知道为什么能发表在《人民文学》上。很失望。
黄蓓佳《布里小镇》是全书25篇中我最喜欢的,真的太搞笑啦,我乐了一天。黄蓓佳是儿童文学作家,多年后重新写起成年人世界。作者辣手。王安忆看到了,问作者,这到底是不是你老公?作者说,不是,不然早就离了。抄一段《文艺报》的文章:“生活是琐碎的,琐碎的生活写出来往往就是荒诞的。年轻人对这样的荒诞未必能够心领神会,要上到年纪,活到风轻云淡的时候,读着这些家长里短的碎碎屑屑,才能如安忆这般乐不可支。”赶快发给朋友们传看,真不错真不错。本场冠军。
莫言《大风》 吐槽:为什么偏要写一下奶子啊?当代男作家没有别的可以写了吗?
铁凝《孕妇和牛》,曾经被选做某年高考语文阅读题,当时高中的我只知道做题,觉得这种小说古怪、看不懂,不知道作者在搞什么东西。如今又看到这篇小说,才感觉到了一点里面的韵味。有一个很有趣的点,我去搜了搜那个怡贤亲王碑,原来还真有,就在河北省涞水县,铁凝曾经工作过的地方。铁凝还写过一篇《哦,香雪》,似乎也是在涞水。五星。
阿来《秤砣》写藏区故事,包袱到最后才抖出来。秤砣大概也有隐喻意味。
余华《阑尾》余华的小说常是有一种黑色幽默在里头。很会说段子,读者很喜欢。四星。
苏童《小偷》“坏”小孩的故事。可怕,想到《隐秘的角落》。抄录一个编者按“按:一场小小的文字游戏,引发了一件尘封许久的童年回忆;这件往事不过关乎一件小玩具的得失,但对于一个小镇男孩来说,无疑是一场对友谊,对道德,乃至对灵魂的终极试探。苏童以冷静而深刻的笔法,为我们描绘了发生在一个孩子心中的战争。”五星。
迟子建《逝川》不知把它归为哪一类。东北少数民族故事,阿甲渔村的吉喜给人接生。逝川也好,泪鱼也好,初雪也好,给故事笼上了一层神秘色彩。这种小说还蛮难把握的。
东西《你不知道她有多美》少年对隔壁嫂子的爱,永远定格在了那场地震。
温亚军《驮水的日子》上等兵,和一只叫做黑家伙的驴。“对付这种犟驴,就得上等兵这样比驴更能一磨到底的人才能整治得了。”军旅文学,简单,向上,美好。虽然终有一别。
鲁敏《在地图上》怎样对抗/应对工作的单调和虚无?这篇我很喜欢。抄一段简介:“这是另一个旅行的故事,在地图上旅行。一个微渺的小人物,他痴迷地图、并试图通过地图来逃避人生的失败、虚无与局限,一个带有象征性的、隐喻普通人精神状态的小故事。”五星。
乔叶《深呼吸》涉及抗日背景。作者自述,从母性的角度,写两个女人之间的对峙。我看,这故事写的够曲折波澜,足以扣人心弦,然后呢?写人性?还是不太搞得懂小说中日本女人的动机,结尾突然拐到文革,是要对比么?质疑历史?我总觉得有些强行深刻。
朱山坡《丢失国旗的孩子》“他够得上枪毙了!”有年代感。
张惠雯《爱》牧区新来的年轻医生艾山,在宴席上偶遇了一位姑娘……爱是多么不可思议!四星。
《给孩子的故事》读后感(十):“要的是天真,不是抹杀复杂性的幼稚”
2016年上半年,身在美国的作家王安忆接到诗人北岛的电话。北岛请王安忆推荐给孩子读的短篇小说,他与出版机构“活字文化”合作,主编了一套“给孩子系列”图书。王安忆手头没有资料,凭记忆列出一批小说。
下半年,王安忆回国,北岛提出直接由她编选。书在2017年春节前就编好了,王安忆起初想到的那批作品,大体保留在书里,书名定为《给孩子的故事》。“故事”含义更广博,有围炉夜话的亲切感,而它的价值又因鲍勃·迪伦获诺奖而被再次确认。书里多了几篇叙事的散文,因为担任编者,王安忆抽走了自己的小说《打一电影名字》。
因母亲茹志鹃同为作家,家里书籍很多,王安忆从小就广泛阅读,不拘于儿童文学。她曾在儿童文学刊物《儿童时代》担任过编辑,时常去学校调查、采写,组织活动。1979年,她的第一篇小说《谁是未来的中队长》发表在《少年文艺》杂志。写过几篇“儿童小说”后,她开始写第一篇“成人小说”《雨,沙沙沙》,并将这篇作品视为自己的处女作。
王安忆很早就反思起儿童文学概念,不认为文学应该分儿童和成人两类。在前言中,她谈及理想的读者:下限是认识汉字,能理解书面表达;上限弹性很大,十到十五岁,也许稍大,将成年未成年,大致可称“少年”。“这个成长阶段相当暧昧,不能全当成大人,但要当做孩子看,他们自己首先要反抗,觉得受轻视,不平等。”她继续写道。
确定篇目也不容易,肯定漏掉许多好作品。几位作者如迟子建、苏童、刘庆邦,王安忆又觉得作品几乎篇篇都可以选进书里,但每位作者一篇是原则。她比较了苏童的作品,选进来《小偷》,小说记述一桩残酷的往事,但孩子间的友谊又留存了些许单纯。她起初选了迟子建的《一坛猪油》,因为太长,换成描绘生机勃勃的渔民生活和女性悲剧的《逝川》。
从1920年诞生的汪曾祺到生于1978年的张惠雯,25则故事大体以作者的出生年份排序,通读下来,仿佛简略的当代文学编年史。在编选过程中,王安忆终于了解到,自己“要的是一种天真,不是抹杀复杂性的幼稚,而是澄澈地映照世界,明辨是非”。
留下的故事,包含了成长的欣慰与酸楚,亲朋逝去的惆怅,世界不可逆转的变幻,男孩对年长女性的倾慕,甚至父母辈的婚外恋情。无疑,在传统观念中,后面两种未必适合孩子阅读。
孩子该读什么,王安忆坚持着自己的想法。虽然毫不因袭传统,但她还是请责编和作者们沟通,去掉故事中的某些粗话,因为“非常不雅,给孩子看不好,容易学坏了”。
2017年5月21日,王安忆接受南方周末记者专访,谈应该呈献给孩子们的故事。
杂乱看书的一代人
南方周末:你在少年时代读什么样的作品?
王安忆:其实我的情况比较特殊,别人肯定不会有我这么好的阅读条件:我家里面有书,可以读很多。我很早就开始阅读,阅读范围挺广,主要是童话、传说、神话。那时候我母亲在上海作家协会,我很小的时候,可能一二年级就到那边的图书馆借书。我记得总是借一大堆回来,很快还回去再借。对我们现在以为的儿童文学,我个人兴趣倒不是很大。
在1960年代,我们是这么分的:学龄前或一二年级的孩子看《小朋友》,以绘画为主,也有文字,是上海的少年儿童出版社出版的;四年级到初一读《儿童时代》,我在这工作了几年,文字多,但有相当大一部分插图;年龄再上去一点,我们还有上海的《少年文艺》和中国少年儿童出版社的《儿童文学》。我们中国的少年儿童阅读,当时基本上就是这几个阶梯。
南方周末:哪些作品影响了你的成长?
王安忆:这倒说不清楚了,小时候看的不一定记在心里面,但是阅读会慢慢积累起来产生影响,很难理性地分析。很难说我受谁的影响,我们就是杂乱看书的一代人。我1978年回到上海,到《儿童时代》工作,看了一些儿童小说,但没有认真分析过它的状态。我们可能继承了苏联当时的“校园写作”体系,把少年儿童、少年队员看成祖国的未来。我编辑和阅读儿童文学,最早时还写过,但是很快不写了,因为感觉有一点把文学幼稚化。我很早就提出,文学不应该这么分类。
南方周末:与你的少年时光相比,现在的孩子有什么特别之处?
王安忆:现在的人阅读少,当年我们不管爱好不爱好文学,读书量都比现在大。图片、电视、电影还有动漫……现在直观的东西太多了,所以阅读量非常低。这肯定是不好的,文字很重要,需要更高的智慧。你先得识字,之后还要有一定想象力,能把文字转换成各种各样的声音、画面。读图一定是很直接的,相对来说简单和表面得多。
但年幼的孩子读绘本,是比较科学的。他们识字量少,看图画非常合适,尤其绘本有专门的风格,非常适合儿童阅读。我个人很喜欢绘本,觉得好的绘本像安徒生童话一样,小孩要读,大人也要读。它有些东西是孩子根本读不懂的。像《海的女儿》,写的不是残酷的故事,而是非常高尚的,那么纯洁、无我的爱情。
西方有些绘本非常深刻。我曾经看过一本叫《阁楼上的光》,好像是“新经典”出版的,真可以称为经典,大人孩子都可以读。它不是一个连贯的故事,只是生活当中小小的现象,配上图和文字。这些现象非常幽默、温馨或严厉,总之很有趣。
南方周末:为编选这些故事,你是否特意观察过当下孩子的趣味?
王安忆:我没有刻意去关心这些,只是觉得现在给孩子看的东西太幼稚了。好像一个人年龄很大,还是这种趣味,30来岁的人也非常幼稚。这是我从生活中观察到的,具体现象非常多。孩子读书少,动漫都那么简单,好像一个人发育非常晚,始终那么天真。从我们周围的文化环境看,现在的电影、电视等都趋向于低龄化,非常简单,整个标准在不断降低。影视作品我现在看得比较少,它们可能更加强调直觉和所谓的视觉冲击力。
南方周末:你在前言中写道,“得让他们把过来人放在眼里”,这句话是什么意思?
王安忆:我不要让他们觉得我们很差,希望能够提高大家的智商。阅历还是很重要的,而我们的阅历和认识肯定比他们丰富。以前过于强调孩子要阅读“低”的,其实不见得。大概四年级的时候,我看课外书,班主任过来说不应该看这样的书,意思大概是在你这个年龄看《红岩》已经到头了。我到现在还记得,那本书名叫《虾球传》(注:黄谷柳的长篇小说,以1940年代中后期的香港一带为背景,描写少年“虾球”在底层社会的流浪历程)。我四年级就看《红楼梦》了,《红岩》不能满足我。《铁道游击队》等“红色经典”我很多都没看过,个人取向不一样。
有些概念,把事情规定得越来越窄。我们现在好像分得非常严密,孩子该看的和大人该看的有分界线。幼儿看看绘本、图画,等到一定程度,就有了所谓“成人文学”。其实不是,文学就是文学,不应该分得那么清,文学本身就是青春的读物。
“不给他看小说,他就不知道死吗?”
南方周末:最初联系你时,北岛怎样形容他的想法?
王安忆:我以前看过他们出的系列书,给孩子的诗歌、散文等,所以大体知道他们的想法,但没想到最后让我来编。有一篇是我向编辑争取的,就是黄蓓佳的《布里小镇》。他们觉得这篇小说好像写和孩子无关的事情,但换个题目,比如“爸爸、妈妈的爱情”,就有了关系。我们不断沟通,他们认为这篇写大人之间的三角恋爱,不应该给孩子看,但是我觉得小说里面的人物都那么天真可爱。他们很尊重我的意见,把这篇小说保留了下来,我感到很满足。
南方周末:你选择汪曾祺的《黄油烙饼》等写到死亡的作品,是希望帮助孩子形成正确的死亡观吗?
王安忆:这又关系到我们对孩子的认识:难道不给他看小说,他就不知道死吗?这是时时刻刻发生在我们身边的事情。有些孩子很就早经历爷爷、奶奶去世,回避没有太大意义。我倒没有考虑死是不是能让孩子阅读。
南方周末:书里的故事还涉及很多重大主题,比如亲情、友谊、成长。这是你个人的偏好,还是文学就植根于这些最重要的词汇?
王安忆:严肃的文学当然要回答一些重要的问题:生命是什么,死亡又是什么,世界是怎么样的,我们应该怎么度过光阴……都是很严肃的问题。我觉得孩子也应该慢慢学习,尤其是我们对孩子的定义,就像我在序里面写的,我大概把孩子、读者的年龄上限放在15岁。15岁的人应该读正常的文学作品了,不要读那些为他们特制的。
南方周末:一些作品有具体的历史背景,比如东西的《你不知道她有多美》以及王璞的《捉迷藏》。但孩子未必了解得那么清楚,你预期这些故事将产生什么效果?
王安忆:《你不知道她有多美》里的大地震完全是隐喻性的,景象很灿烂,是一个男孩子对女性初生的崇拜。大地震给了他一个环境,身上插满玻璃片,玻璃片亮闪闪的,不能拔,一拔就出血。它有隐喻,意象又非常美,非常璀璨。
《捉迷藏》写得很好,一个晚上发生的事情非常丰富,可能值得我们不断地挖掘出来,了解不了解背景无所谓。每个孩子都会捉迷藏,她在外面躲一晚上,回到家以后,显然发生了一件比一晚没回家还要重要的事情,这就行了。你让孩子知道了,这个世界可能发生很多比他的事更加严重的事情。他现在可以明白一点,不断地再详细地明白。读书最重要的是让孩子感情丰富,让孩子更聪明,让孩子了解:世界上可能发生的事情,比实际发生的还要多。
南方周末:这个选本反映了哪些你的特质或价值观?
王安忆:它还是比较鲜明地反映了一些我对小说,尤其对儿童应该读的小说的看法。这些小说写得很特别,文学性很强,本来就不是专门写给孩子看的,没有我们惯常看到的儿童文学那种“娃娃腔”。中国人认为选编是一种文学评论的方式,这很有意思。让我编选,肯定要体现我的选择,每一篇都经过我的阅读和考虑。我们经常碰到编者只排名字,排他觉得有名的作家,这样编不够好。
感觉到难过,说明你的感情还没麻木
南方周末:让孩子读令人难过的故事,是要打“预防针”,告诉他们人生会发生这些吗?
王安忆:不是人生,我们读小说,是要将感情变得丰富一点,得到一些充实。难过是感情的一种表达,如果一个人连难过都不会,还有什么感情可以享受?
南方周末:但大家通常认为该让孩子多看点世界的温存,而少让他们接触残酷的事情。
王安忆:我对残酷有不同的看法。我觉得有些东西是不能看的,比如说比较暴力的,我选的小说没有一篇是暴力的。暴力是外部的东西,内里感觉不舒服,感觉到难过,正好说明你的感情还没有麻木,还敏感。我觉得不能给孩子看太直接、太暴力、太血腥的东西。像电影分级一样,有些东西就是不该看的,连大人都最好不要看。我个人抵触暴力,还有比较庸俗的、鄙俗的东西。我其实是从美和丑来分辨的,特别暴力的东西首先不适合美学,我不太赞成美暴力美学。美学和道德在一起,又和我们对世界的真实认识在一起,但“真善美”这个词被大家用烂了。
南方周末:你希望这些故事能“澄澈地映照世界,明辨是非”,这里的“是非”指什么
王安忆:其实是非不需要我来解释。有一些事情是我们绝对不能去做的,还有一些事情的对错是比较微妙的。比如苏童的《小偷》,里面的是非就很微妙,但又和感情联系在一起,有些事情不是理性告诉你不对的,而是感性告诉的。应该让孩子面临一个比较丰富的环境,再抉择。
南方周末:你选择了一些少数民族或者军队背景的小说,孩子未必经常读到,这是否意在呈现世界的多元性?
王安忆:我倒没有从人的身份上去选择,我觉得它们都很好。阿来那篇《秤砣》特别有意思,其实讲我们给世界各种各样的规定是有变化的,不要觉得世界的规定只有一个。粗看觉得有趣,慢慢会不断发现里面有东西。《爱》的作者张惠雯,是我选编的最年轻的作者,我很关注她的作品。张承志的《红花蕾》也写少数民族的生活。我们现在这个社会,大家能够分清楚物质贵贱和货币的关系。而文中那个女孩的生活和货币完全没有关系,她有一种特殊的价值观,她的世界里面有另外一种评判标准。
南方周末:鲁敏的《在地图上》与《秤砣》很像,也写到了人们对世界的规定和人的生存状态。
王安忆:是的,鲁敏那一篇我很喜欢,我找到它很偶然。我一直记得有这么一篇小说,但以为是苏童写的,还当面问过苏童,苏童说他没写过。我想不起是谁写的,当时鲁敏不是很有名。这次编选,我看了一些以前的年选,才看到这篇是鲁敏的。虽然比较长,我还是毫不犹豫地把它放进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