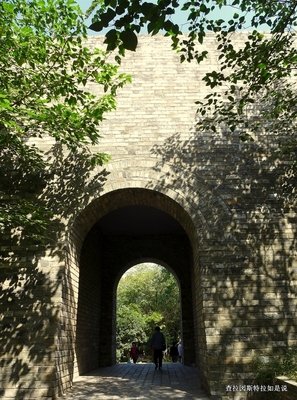
《尼采思想传记》是一本由(德)萨弗兰斯基著作,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的平装图书,本书定价:34.80元,页数:454,特精心从网络上整理的一些读者的读后感,希望对大家能有帮助。
《尼采思想传记》精选点评:
●收获很多,最大的收获是要运用语言自我塑造,这是我下个月的重要内容!萨弗兰斯基写的书都很好看,浪漫主义那本和海德格尔那本都不错。可我觉得这本书对于尼采思想的理路没有整理得很清楚,当然,尼采自身文本的片段式书写给总结增加了很多困难,但至少应该针对每本书按照主题梳理下……或者还是我自己
●只得到一些破碎的思想。
●“我不是人,我是炸药。” 哲学承上启下的关键点。 尼采在思想中走得太远了,而有一些东西是人完全没有一点控制能力的。不断超越已有的认识,探索意识之流的边界,有趣却危险至极。 大多数人的探索会停在虚无深渊的前面安心筑巢,而尼采的个性(求真、痛苦驱力、自由)使他不能停止超越,最后失控了。值得庆幸的是,他的哲学已经差不多完成了。 尼采要活在它被给定同时也是自我塑造成的风格之中,他不与他人共在。他意识中狄俄尼索斯和理性的裂缝,终生在不断使他疼痛,使他不能停止思考。 说人各有命运,对任何人都是如此。先天给定的东西,它一直就在那里。 而事实上,虚无可以被克服吗?这是一个问题,或许我可以这样说,不同的个性导致不同的结果,能不能克服不是穷尽理性所能达到的,而是看这个人愿不愿意至少对深渊保持相当的敬畏和距离。
●读完前9章,205页。 还会再读,但前一个时机已过。
●期待更好的译本。
●这本书很好,可惜的是译者是赶着翻译的,明显很多地方翻译的不够精细
●尼采的生命哲学把“生命”从19世纪晚期那决定论的拘厄里扯出,把它那独特的自由交还给它。那是艺术家面对自己著作的自由。我愿意是我生命的诗人,尼采宣布,而这里也已经描述,对真理的概念来说,这有什么后果。客观意义上的真理不存在。真理是某种幻觉,它证明自己是服务于生命的。这是尼采的实用主义,不过同盎格鲁—撒克逊的实用主义不一样,它指涉一种狄俄尼索斯的生命概念。在美国的实用主义中,“生命”是一件常识的事情,可是尼采,恰恰也作为一个生命哲学家,是激进分子。他厌恶盎格鲁—撒克逊的粗俗,同样厌恶达尔文主义的关于生命进程中“适应”和“选择”的教义。对他来说,这只是一种功利主义道德的投影。这种道德相信,就是在自然中,适应也能获得一种成功的奖赏。“自然”对尼采是赫拉克利特的游戏着的现世享受者,永不止息的创造过程。
●是的,就像一个朋友爱着朋友,我爱你,这谜一般的生活。几千年!可以想象,请用双臂环抱我,要是你不再有任何幸福赠予我,好吧,你还有你的痛苦
●外国人表达的东西,要说的话跟被描述的思想感觉总是混含一起,分不大清是作者的独白还是转述对方的思想,有些累的慌。
●囫囵吞枣式地看。
《尼采思想传记》读后感(一):值得阅读的一本书
这是一本从尼采的思想发展的角度写的一本传记,同时结合了尼采的个人经历。个人觉得是本很不错的书,写得比较有条理,相对于尼采自身那种矛盾而又晦涩的思想来说,能给读者以比较大的帮助。当然把握尼采的思想的确是很不容易的,因为虽然他在不断地批判,但也是站在前人的基础上,所以需要了解的东西很多。
《尼采思想传记》读后感(二):要是读不懂中译本,也许错不在你。
说明:我不懂德文,所以参照的是shelley Frisch 的英译版。英译本和中译本均根据德文2000年第一版译出,但是相差千里。不好说一定是中译本错了,但是。。。大家根据上下文揣测吧。。。
直接上证据:
中译本:(P230)
科学虽然也受到视角的限制,但它们能让自己超越其上:它们扩展自己的视野让整体中自身立场的一种相对化变得可能。之所以这样,是因为科学更接近绝对真理(这句话的意思和英文版完全相反,不是我打错了)。相反的是带着自己有活力的片面的激情。这种激情绝对第投入,不允许任何保留。可是,科学是方法上的距离,所以它让知识的相对性意识保持清醒状态。激情要的是整体,但是科学,如尼采所理解的科学,教导谦虚:我们能够领会个别,但永远不能领会整体。
英译本:(P202)
Although the sciences are also constrained by perspectives, they can be elebated above them. They broaden our outlook and enable us to see our own position in relation to the whole, not because science more closely approximates absolute truth, but for precisely the opposite reason——namely that passion, owing to its vigorous focus, posits itself as absolute and admits of no alternative beyond that focus.Science, however, by dint of its methodical distance, keeps us aware of the relativity of knowledge. Passions aim for totality, whereas science, as Nietzsche understood it teaches reserve. We can grasp particulars, but never the sum at all.
由英文译成中文:
尽管科学亦被视角所限制,它却能超越其上。科学拓宽了我们的视野,让我们明晰自己处在整体中的位置。这并非因为科学更接近绝对真理,恰恰相反,是因为激情专注于强力的焦点,将其自身绝对化了,不允许任何事物超越其外。而科学,凭借其方法的距离,使我们意识到知识的相对性。激情指向整体,而科学,根据尼采的理解,要有所保留。我们能够领会个别,但永远无法领会整体。
这只是一个例子。。。卫茂平先生的译文,文笔出色,看着跟诗似的,可惜看不懂啊。个人觉得是雅而不达,雅而不信的。英文版的确也不一定正确(所以还是建议看德文原版),但是逻辑清晰,易懂,推荐。顺便说下,网上没有英译本的电子版,别找了,大家还是老老实实看纸版吧。
《尼采思想传记》读后感(三):《尼采思想传记》读书笔记
替我说话,这完全没有必要,我也从来不希望,相反,一份好奇,就好像对着一株陌生的植物,带着些许讥讽的反抗,就我看来,这是对我的一个无与伦比的较聪明的立场。
——尼采
真理是个可怕的事物,是能致人毁灭的思维冒险,如果说康德洞察了这一点,在“头顶山的星空”和“内心中的法则”前止步,以避危趋安,尼采却心怀携心自食的勇气,携带决堤奔腾的热情,义无反顾地接受了冒险的挑战,走上了探索奥秘的不归路。
1、尼采与音乐
尼采判断艺术享受的幸福充盈的准绳,是瓦格纳的音乐。
他这样形容他的感受:“我的每根血管,每根神经都震颤不已,很久以来从未有过这样一
种经久不息的着迷。”
在尼采眼中,波浪,音乐,伟大的世界游戏之间具有亲缘性,它是一种死亡和生成,成长和消逝,是由统治和被征服组成的,音乐中迷狂的持续性,使日常世界变得恍惚,而一旦重新恢复意识,世界就显得令人厌恶,从音乐后清醒的狂喜会陷入一种否定意志的情绪。
音乐如此强烈,让人担心可怜的自我,面对纯然的迷狂,在纵情音乐中,有自我毁灭的危险,所以,有必要在音乐和狄俄尼索斯精神敏感的听众之间设置一个有疏理作用的媒介。这是一个由语言,图像,舞台情境组成的神话。谁聆听这样的神话,谁就把耳朵贴向了世界意志的心房,只有前台实体的事件保护,使人们不完全失去个体实存的意识。
音乐只是纯粹器官性程序的功能,尼采以这样祛除激情的论据对自己的激情提出了质疑,尝试着一种试图讥讽自身酷爱的行为。因为人会感到无聊,为了摆脱无聊,就寻找某种刺激,遍寻不得,便发明了游戏。游戏不过是内在冲动自我调节的艺术,音乐会不会就也是如此呢?
艺术是在一个虚无的基底上完成了他那自我刺激的艺术,这几乎是一项英雄的伟业。有坠落危险的人们需要娱乐。艺术是一次张弓,为了是不掉入那虚无主义的松弛状态。艺术帮组生存,否则面对无意义感的侵蚀,生命会茫然无措。
一切都可能是可怕的,不过还好有着与可怕的事物进行协调的音乐,人们还是能够忍受生命,可怕的事物是尼采一生的题目,是他的尝试,他的蛊惑。
1、 尼采和叔本华
尼采从小就不愿虔诚和乖巧,他梦想着,有个扰乱他心绪和给他留下强烈狂热印记的命
运。他拜访自然辽阔的殿宇,喜欢电闪雷鸣。他从小在文本中解释的字就像一道闪电,每每剧烈有力意味深长的击下。他希望自己的语言有使生命震惊的神秘力量。
青年尼采期盼着同他的精神一致,或者鼓励着自我强大。他读书喜欢设身处地的思考,比如他读荷尔德林,读到了软弱无力背后隐蔽的强大,在拜伦那里则是强大的生命力,在拿破仑那里则是政治强权的魔力。在青年的尼采那里,强力变成的事实效果领域的自我命题。
尼采强烈反对将人的命运理解为神的天意,在他看来,命运没有特征,与人无涉,它是一种盲目的关联,我们只有通过自己的行动才能强行取得一种意义。尼采拒绝善的天意,就像拒绝某种臣服上帝意志,这在他看来是一种有辱人格的方式。
谈论宗教和信仰问题,相信一件安慰人的事情比较容易,困难的是直面真理。真理在尼采看来并不是美和善的结盟,真理的朋友眼中不仅有平和,宁静,幸福,真理也可能非常可憎和丑陋。
正是阅读叔本华祛除了尼采眼前乐观主义的眼罩,是他的目光变得尖锐,生命对他来说是有趣的,也是丑陋的。
尼采这样形容自己青年的求学生活:“大学生活看似独立自由,觉得自己想身处梦幻之中,相信自己能够振翅飞翔,但还是由于某些不可理喻的障碍,觉得自己被扯了回来。无法感觉自身,无法帮助自己。尽管心里有高贵而骄傲当然决定,可缺少的是贯彻的力量。最后渺茫地沉入日常工作的世界。片刻之后又会感到恐惧,不愿在狭隘逼仄的工作中沉隐消没。
尼采在当时有对叔本华的新康德主义的批判,比如反对把物自体定义为意志,这是关于世界无法确定自身本质的一个过于确定的说法。但尼采明显同意叔本华哲学的两个基本观点:一是以自身的理性衡量,根据内在本性,世界不是什么理性和精神的东西,而是冲动和幽暗的本能,生机勃勃却没有意义。二是叔本华以否定的意志,描写了一种超越认识的可能。一种意志的力量独自升华进而反对自身。
如果说叔本华的哲学处在拯救的半道上,通过凝神静思,实现了一种与世界的距离。尼采则更强烈地感受到了狄俄尼索斯天性的指引,要更加靠近深渊,他猜想里面有更加诱惑的秘密,他相信自己不会眩晕。
尼采提出了三种可能较好的形象:卢梭,歌德,叔本华。卢梭寄希望于自然修好如初,达到文明的自然化。歌德式人物悠闲好思,以明智而高雅的方式和环境友好相处。叔本华发现了生命的悲剧性和无意义的基本特征,担当起诚实,自愿的痛苦。
使自己的思想成为现实的哲学家是精神的暴君,现实流行的则是乌龟的福音。无数平庸的家伙对古代的伟大真理进行精雕细琢。
3、尼采与悲剧
希腊的悲剧就是这样一个舞场,人被扯入存在的纷乱。
清晰的理想,损害体验的隐晦冲动的准备。在艺术的帝国里,成长和生成都必须在深邃的暗夜里进行。
音乐在希腊人那里的任务,是把主人公的受难在听众那里转变为深切的同情。
但是在尼采眼中,苏格拉底制约了音乐的权力,并用辩证法取代了它,苏格拉底在尼采看来是一个灾难,他启动了置存在的深渊而不顾的理性主义。“似乎人物不是由于悲剧事件,而是由于一种错误的逻辑而走向毁灭。”
悲剧在尼采看来展现了两个基本动力的妥协,热情和音乐是狄俄尼索斯的,语言和辩证法是阿波罗。两者相加,产生出对幽暗的命运之力的明确意识。
尼采认为,希腊人本身具有一种残酷的和老虎般毁灭欲望的特征。比如在希腊神话里“一个厄里斯挑动了糟糕的战争,这个女神来自于漆黑的夜晚,争论变成了不可避免的厄运,被她在人间唤醒。宙斯派去了第二个厄里斯,她促使人类,学会用互相竞争代替相互残杀,由此有效地扭转了不和。
民族之间不断产生出战争的风暴,但是在间隙中,社会有时间和机会,在战争的内聚力的作用下。创造出文化的天才的灿烂的花朵。文化需要残酷的基底,它是令人恐惧的事物的最美妙的终结。文化还需要第二种残酷,就是奴隶制。倘若选择大多数人的自由和幸福,会得到一种民主的文化,这是大众的趣味的胜利。但正如人有肌肉和精神一样,社会也需要勤劳的双手,为享有特权的阶层工作,允许这个阶层,生产一种满足更高需求的新世界。
无穷无尽的现实无法被认识,康德对此警告道,我们穿越了一片纯粹知性的陆地,还确定了在此之上的位置。但这边陆地实际上只是一个岛屿,由一片辽阔汹涌的大海所包围。康德选择了留在岛屿上,汹涌的大海在他眼中是预示着不祥的物自体,叔本华敢于进一步尝试,给这边大海取名为意志,而到了尼采这里,它变成了据对的狄俄尼索斯。
有意识的生命在这两种可能性之间活动,不过,这更像是一个被分裂的活动。为狄俄尼索斯所着迷,不至于荒芜,生命必须与大海保持联系,同时依靠大路上的文明保护机构,以便自己会成为狄俄尼索斯分解暴力的牺牲品。
4、尼采和瓦格纳
尼采本人不反对军事天才的胜利,但在尼采眼中,军事胜利应该涉及的是一种文化英雄主义的振兴。战争对尼采意味着,狄俄尼索斯和赫拉克利特世界入侵政治,形成生命的紧要关头。由此,文化也会正好得到滋润。
尼采依旧寄希望于某种形而上学的慰藉,在《悲剧的起源》中,尼采称神话为一种浓缩的世界图像,通过它,生命沐浴在意义的光芒中。尼采之所以转向神话,一方面是因为无法继续在宗教的意义中信仰,另一方面,也不信任理性可以给定生命的方向。
神话的发现,是一种生命权利的发现,这种生命权利把欢乐的充盈还给存在。瓦格纳和尼采,正是因为觉得他们的时代出于一种危机四伏和意义贫乏的社会状况,而致力于发现和发明新的神话。
经过这开始阶段的意见一致,而以后让尼采和瓦格纳分道扬镳的是,是瓦格纳要求的是一种宗教地位的神话生产,而尼采要求的是一种服务于生命艺术的神话的审美游戏。
在同尼采友好相处的时日里,瓦格纳虽然在政治上心灰意冷,但对自己的艺术充满信心,相信它可以补偿革命的缺失,甚至替代革命。艺术经历应该可以得出生命罪恶得到拯救的短暂瞬间,甚至可以成为时代终结的伟大拯救的先兆。
倘若艺术想要拯救宗教的精髓,必须成功促使人内心的一种持久转变,瞬间的艺术享受是不够的。作为宗教的艺术意志,会遭遇纯粹审美事件的限制。对于瓦格纳来说,这是尼采对他的一个巨大的羞辱。
5、尼采与时代精神
尼采要的是可怕的事物,所以音乐离他很近。他希望的是悲剧性感情的回归。尼采对时代的诊断是这样的:这是一个真实和正直的时代,但是以卑下的方式。
尼采反驳知识庸人们乏味的自然乐观主义,概括了他对自然的狄俄尼索斯的阐释。在自然的形态系列中,从无生命,经过植物性,到动物性和兽性,再到人的身上,最后意识出现。意识首先经历的不是世界的欢乐,相反,意识发现了存在的痛苦。
与叔本华不同,尼采强调人身上有统治那个别样的,烦躁不安的,毫无知觉的非比寻常的强大意志,这就是狄俄尼索斯的智慧。它足够强大,可以承受深渊,而不因此毁灭。相反保持一种神秘的,快活的镇静。
接着与唯物主义的论证之后,尼采开始了反对历史征服的斗争,这是尼采第二个对时代精神进行挑衅的观点。
公众生活中历史主义的泛滥,尼采看到的是一种浅薄的黑格尔主义的后期发展。视历史的强者为理性者,要求对现存者权力的尊重和掌握历史知识的勤勉。历史对黑格尔虽然是理性的,但黑格尔在历史哲学也说过:“没有人不会为历史陶醉而纵酔极乐。”
尼采的路径是回到尚未进行历史思考的希腊时代,用历史来反对历史学,成功地形成一个广袤的视域,创造神话,画出一个圆圈,生命能充实他,也可以在其中实现自身。
那么究竟又是什么队尼采反对时代精神起到了激励作用或者是什么让他相信自己的思想得到了证实。上帝死了,人们破坏了我们存在的彼岸,但还是存在折磨我们的残酷幻象,杀上帝的凶手迫不及待做的,是用一种内心的彼岸来取代古老的彼岸,一方面表现为弗洛伊德的超我,另一方面是在我们心中建立起总体概念的统治。
属于尼采在瓦格纳的影响下自己发明的更高的天性的,是一种形而上学的幻觉意义上的超越历史的思维方式,虽然不召唤彼岸的秩序,不过在次在中发现了永恒和意义相同者的特征。
6、尼采与科学
有一个决定性的思想和一次决定性的经验,导致尼采放弃了他的形而上学和艺术观点。正是1876拜罗伊特的节气演出那令人失望的经历。
尼采接着让一个科学的天才登场,这种科学出于对自然的可探究性,知识是万能治疗力量的信念生存。尼采看来,苏格拉底与学生最后谈话中所说的话,重要的倒不是个别的不朽的证明。单就这种证明来看,显示出了它的可疑性,苏格拉底称其为一艘救生艇,人们尝试用它游过生命。但决定性的其实是把生活作为一个鲜活的客观个体来体验。这种思维的自我体验,在理性和神话之间,在苏格拉底那里,没有任何矛盾。理性精神把他引向自身,他又让神话来证实自己。
尼采看待科学,将其看做同民主的精神叛乱联系在一起的伦理。苏格拉底以其对统治权力的蔑视表达了这种伦理。要是自然可以通过科学变得可以被统治,社会所固有的不平等为什么不能被消除?在苏格拉底文化的怀抱里,民主的精神得到孵化。科学的真理和发明,效用是超越主体的。真理面前人人平等。
但尼采担心的是在底层中间散播知识和认知,会发生可怕的,毁灭文化的暴动。有意识的人类无法忍受一个冰冷的宇宙,人们想要有居家的感觉。在他们那里,哲学不是什么别的东西,而是回家的渴望。
极端的真理意志有可能导致逻辑的世界否定,科学,它否定着过去我们熟悉的世界的价值。与狄俄尼索斯的世界不同,这种否定,不含任何戏剧性的东西。同康德的物自体的情况相同。他在封闭的认知世界起到了一个洞眼的作用,通过这个洞眼,令人不安的气流得以吹入。康德的后人都想窥视莫耶纱巾的背后,即使没有看到,人们也想发明一种咒语。
人类的一种整体意识,同德国的理想主义,特别是和黑格尔的想象不一样,其效果不是崇高的,而是毁灭性的。尼采同样不能满足于浪漫主义诗人的安慰的话语,人们不能有意识地留在谎言中,不应委身于诗人美丽的假象。
尼采一方面只有审美意识上的自我维护,一方面是作为同情后果的绝望。尼采试图第三种可能性,一个泰然自若,几乎是快乐的自然主义。这样灵魂会失去少许重力,像是一种漂浮。尼采把这样一种变得轻松的精神状态,描述为自由和无忧无虑的翱翔。
对尼采来说,如何对待起源,决定了科学还是形而上学的工作。倘若形而上学寄希望于崇高的起源,那么,科学就把关系翻转过来,开始不是什么,仅仅是偶然性和无差异性。
世界非形而上学地站在人们的目光前,作为一种没有意义的开端和没有意义的终结。自然虽然有力地发展,但向前推进的因果关系是盲目的,宗教曾经在一个精神关联的媒介中影响自然,对科学来说,这种关联已经终结,科学相信人们现在有能力,在利用自然规律的情况下,让它为自己服务。
对尼采来说,思维是一种前所未有的乐趣,他无论如何不想放弃他,为此他感谢生命,因为是生命给了他兴趣。尼采和他的思想之间,上演着一个热烈的恋爱故事,带着所有的纠葛。
在尼采那里,道德以自我的分割为前提,尼采思考了人的核分裂,个体不是一个统一体,他也可能成为一个内在世界的活动场所,谁要是探究它,谁就有可能叫做那个人的内在世界的探险家。
尼采实验这这样一个论点,在善恶背后隐藏着古老的高贵和卑贱的区别,从高贵的视角出发,糟糕的人是微不足道的。人们根本无需顾忌他们,因为卑贱者自己都不尊重自己。比如人们为了表示谢意,回赠之物超过接受之物,这种通过债务关系的颠倒,人们想重新获得自由,这在尼采看来是一种温柔的报复类型。
尼采接近韦伯,认为科学无法做出价值判断,但通过对文化的功能网络的解释,科学给活动提供了准则,允许对手段的合乎目的性进行评判。
在宗教的情感中还有什么其他东西可以被发现吗?尼采认为还有,那就是作为感觉到自己有罪的准备就绪。它表现为罗马文化晚期的疲软,负罪感,宗教如同一剂麻醉针,面对角斗场里的搏斗,罗马人已经变得麻木,却开始在禁欲,殉教,修道中获得愉悦。
尼采由此刻画了当时文化需求的一种社会学意义的尖刻草图,之所以不能放弃艺术,是因为不能彻底放弃宗教慰藉,在艺术中听到渐次匿迹的宗教回响。
形而上学,宗教中那伟大的拯救性感觉,被尼采称作一个热带时代,他看到一种温和的文化氛围正在形成,他想加速这种文化的突变,但他也知道,冷却自身也存在的风险。
7、尼采的“永恒轮回”
即使冷却激情是科学的功绩,在尼采看来也不应该走的太远,因为社会不仅受到无节制的激情的威胁,也可能在科学的系统冷却中变得麻木。
1881年,在锡尔斯-玛利亚的锥形岩石旁,永恒轮回的思想在尼采的脑中灵光乍现。年终,尼采在热那亚结束了他的《朝露》,他把自己对于人类精神未知领域的探索,比作是哥伦布发现了新大陆。
意识到底有什么用?尼采的回答是,意识是其间的领域。它是人与人之间的联系网络,其中,语言是沟通的符号。尼采在1882年夏《快乐的科学》的结尾处,小心翼翼的暗示。又过了一年,他让查拉图斯特拉走上舞台。他自己说这是一个需要千年,才能成为什么的思想。
在尼采获得这个转变的思想,即相同的事物的轮回的思想之前,萦绕在他脑海里的是什么?尼采以世界钟的比喻说明了这点,暗示了世界的不停旋转。新的世界时期不是新的,钟面只是表象,新的世界时期将重复这些事件,指针接着指针。
尼采将永恒轮回的思想理解为论题性的真理,也把它作为生命构造的实用手段。以这样的方式,他成功给一种冰冷的意识加热。
一切狂喜,愉悦,的天堂之行,这个以前是被幻想植入彼岸的,现在应该以直接,此岸的生活为准,永恒轮回为内在性保留了超越的力量。如查拉图斯特拉所说,“对地球保持忠诚。”
永恒轮回把宇宙想象为一个封闭的整体,受无情的必然性的彻底控制,这个必然性就是把宇宙成为一个百音盒。我们在盒子里玩耍,其实只是被玩耍。
还有一个尼采不能解决,却无法回避的问题,到底这种意志是服从于自我保存,还是挣脱了自身,到头来反对自己的生命?
我不会失去自己,这可能是个快乐的回答,但可能的惊愕也是,我永远无法摆脱我自己。似乎自己从一个命中醒来,但是带着清醒的意识好,还是继续做梦不被自己毁灭自己好呢?夜游的人必须继续做梦,这样才不至于继续跌入深渊。
8、尼采和莎乐美还有他们的查拉图斯特拉
莎乐美曾经对尼采有过这样一个论断:“尼采会作为一个新的宗教的预言家出现,那时一个为自己的信徒招募英雄的宗教。”
莎乐美不愿成为尼采的信徒,她很好的理解了尼采,但带着她自己的好奇心径直地走向了他人,而没有留在尼采的魔力圈中。把尼采作为自己的教育的站点丢开,抛在了身后。
对此,尼采无法忍受。《查拉图斯特拉》的开头场面,清晰的展示了尼采受到伤害之后的绝望的痕迹。查拉图斯特拉离开了自己的家乡,在大山里归隐了十年,在那里享受精神,直到充盈,直到真正的漫出。但他下山来到人类中间,也就开始了自己的下坡路。
在尼采对于超人的定义中,不涉及任何生物的问题,它是人类精神的力量在上升的过程中的自我控制,自我塑造的力量。但生物学的语调也渗透在查拉图斯特拉的谈话中:“猴子之于人是什么?一个嘲笑或一个痛苦羞辱。人之于超人也是这样,一个嘲笑或一个痛苦的羞辱。”
在《论道德谱系中》尼采向我们展示了一个臭名昭著的“金发野兽”,之所以选择这个例子,是为了证明人内心沉睡的活力,不过,尼采当然不是一个彻底破除心里拘束的鼓吹着,对尼采来说,塑造的原则也一直在起作用。伟大的力量也必须经由一种强大的意志才能获得一种形式。
超人是不受道德指责,在《查拉图斯特拉》中,超人第一次的宣告是,你们正完成由虫到人的过程,但你们在许多方面仍然是虫。“作为群体的人类,为了一个单独强大的人种繁荣而牺牲,这也许是进步的。”
尼采的超人也是对上帝之死的一个回答,让我们回忆一下《快乐的科学》那个疯子在明亮的上午提着灯笼乱跑乱叫:我找上帝!我找上帝!
其实,上帝的凶手或者成为超人,或者坠入平庸。超人体现了此案的神圣,作为对上帝之死的回答。尼采想用超人拯救此岸的神圣力量,针对世俗化的虚无主义倾向。
在《查拉图斯特拉》的第一部,结尾写道:众神死了。在第二部《幸福岛》上,是这样的话:“以前,人们眺望远方的海,便谈论上帝,现在我教你们说:超人。”上帝只是一个假定,而我要你们的假定,不超过你们自己创造的神话。
对尼采来说,超人真正的重要性是自己已经变得成熟,能够把握和承受自己的可怕。这种情况以令人毛素悚然的效果在一个场景中得到描述,一个牧羊人,嘴里往外吊着一个一条黑蛇。查拉图斯特拉,克服自己厌恶和害怕,要求他把爬到他嘴里的蛇的脑袋咬下。于是,一个超人诞生了。
9、尼采的“权力意志”
尼采为《查拉图斯特拉》设计的顺序是:首先勾画一个生活艺术的轮廓,由此让生命和爱情变得显豁。要向太阳一样,带来光明和希望。他在三种变形的讲话中谈到三幅形象的图像,人最初是骆驼,负载着前部的你应。然后变成了是狮子,开始抗争,因为发现了我要。最后成为了儿童,在新的台阶上重新获得某种生灵的自发性。“人们不该把自己牺牲给意见的市场,也不该把脑袋藏到天国的沙子里。”
“权力意志”是查拉图斯特拉的第三项教义,生活需要被生活,而不是思考。查拉图斯特拉和舞女的故事中,他本希望诱惑她们进入自己的生命,但是这样做却赶跑了舞女。因为舞女只想跳舞,并不愿意被人探究。尼采到这智慧又一次呗孤独的抛下,又一次沉入自身的深不可测之中。
什么是权力意志?尼采说“创造一个你们能对此下跪的世界,这是你们最后的希望和陶醉。”
如果说在查拉图斯特拉时代,权力意志还只是自我克服和自我升华的惯用语,如今它已演化成一把解释一切生命过程的万能钥匙。尼采感兴趣的不是防御性的自我保存,而是进攻性的自我升华,冷漠的社会正是体现了一种平衡,这是正义的基础。热泪的社会正是将平衡的位移陷入运动从而导致一种新的平衡并为之斗争。
在尼采看来,基督教为此提供了三大好处:1、赋予人一个绝对价值,不同于生成和消逝的洪流中的狭隘性和偶然性。2、给予痛苦和不幸一个意义,让他们变得可以忍受。3、世界被理解为受到精神的滋润,所以是可以认识和有价值的。尼采承认基督教,但不感谢。因为,对弱者的同情和平衡道德,有碍于一种更高级人类和高贵文化的展开。苦行僧在尼采眼中不过是一个伪装的权势者,针对自己感官和肉身需求的丰富性,建立一种残酷无情的统治。苦行僧是把生命表现成了切割生命,他实质是一个充满权欲的反狄俄尼索斯者。
但尼采自己呢?他有着狄俄尼索斯的天性,可是谁又能说清他不具有苦行僧的天性呢?上帝之死引发的道德革命 是一次价值的全面重估。重估是为有道德教养和豪迈高贵的人分配道德的奖金。
10、尼采之死
1889年1月3日,尼采离开了他的居所,在阿尔贝托广场,看到一个马夫在抽打他的马匹,尼采哭叫着扑倒马脖子上想保护它。尼采最终被同情征服,精神崩溃。
尼采曾这样预言过自己:“面对某一个时刻,我放眼于我的未来,一个遥远的未来,就像放眼于平静的海绵一样,上面丝毫没有卷起一丝渴望的涟漪。我丝毫不想让情形有所改变,我不想成为另一个人。”
方亦元
2015年10月4日完稿于华东师范大学图书馆
《尼采思想传记》读后感(四):一株坟墓近旁的植物
替我说话,这完全没有必要,我也从来不希望,相反,一份好奇,就好像对着一株陌生的植物,带着些许讥讽的反抗,就我看来,这是对我的一个无与伦比的较聪明的立场。
——尼采
真理是个可怕的事物,是能致人毁灭的思维冒险,如果说康德洞察了这一点,在“头顶山的星空”和“内心中的法则”前止步,以避危趋安,尼采却心怀携心自食的勇气,携带决堤奔腾的热情,义无反顾地接受了冒险的挑战,走上了探索奥秘的不归路。
1、尼采与音乐
尼采判断艺术享受的幸福充盈的准绳,是瓦格纳的音乐。
他这样形容他的感受:“我的每根血管,每根神经都震颤不已,很久以来从未有过这样一
种经久不息的着迷。”
在尼采眼中,波浪,音乐,伟大的世界游戏之间具有亲缘性,它是一种死亡和生成,成长和消逝,是由统治和被征服组成的,音乐中迷狂的持续性,使日常世界变得恍惚,而一旦重新恢复意识,世界就显得令人厌恶,从音乐后清醒的狂喜会陷入一种否定意志的情绪。
音乐如此强烈,让人担心可怜的自我,面对纯然的迷狂,在纵情音乐中,有自我毁灭的危险,所以,有必要在音乐和狄俄尼索斯精神敏感的听众之间设置一个有疏理作用的媒介。这是一个由语言,图像,舞台情境组成的神话。谁聆听这样的神话,谁就把耳朵贴向了世界意志的心房,只有前台实体的事件保护,使人们不完全失去个体实存的意识。
音乐只是纯粹器官性程序的功能,尼采以这样祛除激情的论据对自己的激情提出了质疑,尝试着一种试图讥讽自身酷爱的行为。因为人会感到无聊,为了摆脱无聊,就寻找某种刺激,遍寻不得,便发明了游戏。游戏不过是内在冲动自我调节的艺术,音乐会不会就也是如此呢?
艺术是在一个虚无的基底上完成了他那自我刺激的艺术,这几乎是一项英雄的伟业。有坠落危险的人们需要娱乐。艺术是一次张弓,为了是不掉入那虚无主义的松弛状态。艺术帮组生存,否则面对无意义感的侵蚀,生命会茫然无措。
一切都可能是可怕的,不过还好有着与可怕的事物进行协调的音乐,人们还是能够忍受生命,可怕的事物是尼采一生的题目,是他的尝试,他的蛊惑。
1、 尼采和叔本华
尼采从小就不愿虔诚和乖巧,他梦想着,有个扰乱他心绪和给他留下强烈狂热印记的命
运。他拜访自然辽阔的殿宇,喜欢电闪雷鸣。他从小在文本中解释的字就像一道闪电,每每剧烈有力意味深长的击下。他希望自己的语言有使生命震惊的神秘力量。
青年尼采期盼着同他的精神一致,或者鼓励着自我强大。他读书喜欢设身处地的思考,比如他读荷尔德林,读到了软弱无力背后隐蔽的强大,在拜伦那里则是强大的生命力,在拿破仑那里则是政治强权的魔力。在青年的尼采那里,强力变成的事实效果领域的自我命题。
尼采强烈反对将人的命运理解为神的天意,在他看来,命运没有特征,与人无涉,它是一种盲目的关联,我们只有通过自己的行动才能强行取得一种意义。尼采拒绝善的天意,就像拒绝某种臣服上帝意志,这在他看来是一种有辱人格的方式。
谈论宗教和信仰问题,相信一件安慰人的事情比较容易,困难的是直面真理。真理在尼采看来并不是美和善的结盟,真理的朋友眼中不仅有平和,宁静,幸福,真理也可能非常可憎和丑陋。
正是阅读叔本华祛除了尼采眼前乐观主义的眼罩,是他的目光变得尖锐,生命对他来说是有趣的,也是丑陋的。
尼采这样形容自己青年的求学生活:“大学生活看似独立自由,觉得自己想身处梦幻之中,相信自己能够振翅飞翔,但还是由于某些不可理喻的障碍,觉得自己被扯了回来。无法感觉自身,无法帮助自己。尽管心里有高贵而骄傲当然决定,可缺少的是贯彻的力量。最后渺茫地沉入日常工作的世界。片刻之后又会感到恐惧,不愿在狭隘逼仄的工作中沉隐消没。
尼采在当时有对叔本华的新康德主义的批判,比如反对把物自体定义为意志,这是关于世界无法确定自身本质的一个过于确定的说法。但尼采明显同意叔本华哲学的两个基本观点:一是以自身的理性衡量,根据内在本性,世界不是什么理性和精神的东西,而是冲动和幽暗的本能,生机勃勃却没有意义。二是叔本华以否定的意志,描写了一种超越认识的可能。一种意志的力量独自升华进而反对自身。
如果说叔本华的哲学处在拯救的半道上,通过凝神静思,实现了一种与世界的距离。尼采则更强烈地感受到了狄俄尼索斯天性的指引,要更加靠近深渊,他猜想里面有更加诱惑的秘密,他相信自己不会眩晕。
尼采提出了三种可能较好的形象:卢梭,歌德,叔本华。卢梭寄希望于自然修好如初,达到文明的自然化。歌德式人物悠闲好思,以明智而高雅的方式和环境友好相处。叔本华发现了生命的悲剧性和无意义的基本特征,担当起诚实,自愿的痛苦。
使自己的思想成为现实的哲学家是精神的暴君,现实流行的则是乌龟的福音。无数平庸的家伙对古代的伟大真理进行精雕细琢。
3、尼采与悲剧
希腊的悲剧就是这样一个舞场,人被扯入存在的纷乱。
清晰的理想,损害体验的隐晦冲动的准备。在艺术的帝国里,成长和生成都必须在深邃的暗夜里进行。
音乐在希腊人那里的任务,是把主人公的受难在听众那里转变为深切的同情。
但是在尼采眼中,苏格拉底制约了音乐的权力,并用辩证法取代了它,苏格拉底在尼采看来是一个灾难,他启动了置存在的深渊而不顾的理性主义。“似乎人物不是由于悲剧事件,而是由于一种错误的逻辑而走向毁灭。”
悲剧在尼采看来展现了两个基本动力的妥协,热情和音乐是狄俄尼索斯的,语言和辩证法是阿波罗。两者相加,产生出对幽暗的命运之力的明确意识。
尼采认为,希腊人本身具有一种残酷的和老虎般毁灭欲望的特征。比如在希腊神话里“一个厄里斯挑动了糟糕的战争,这个女神来自于漆黑的夜晚,争论变成了不可避免的厄运,被她在人间唤醒。宙斯派去了第二个厄里斯,她促使人类,学会用互相竞争代替相互残杀,由此有效地扭转了不和。
民族之间不断产生出战争的风暴,但是在间隙中,社会有时间和机会,在战争的内聚力的作用下。创造出文化的天才的灿烂的花朵。文化需要残酷的基底,它是令人恐惧的事物的最美妙的终结。文化还需要第二种残酷,就是奴隶制。倘若选择大多数人的自由和幸福,会得到一种民主的文化,这是大众的趣味的胜利。但正如人有肌肉和精神一样,社会也需要勤劳的双手,为享有特权的阶层工作,允许这个阶层,生产一种满足更高需求的新世界。
无穷无尽的现实无法被认识,康德对此警告道,我们穿越了一片纯粹知性的陆地,还确定了在此之上的位置。但这边陆地实际上只是一个岛屿,由一片辽阔汹涌的大海所包围。康德选择了留在岛屿上,汹涌的大海在他眼中是预示着不祥的物自体,叔本华敢于进一步尝试,给这边大海取名为意志,而到了尼采这里,它变成了据对的狄俄尼索斯。
有意识的生命在这两种可能性之间活动,不过,这更像是一个被分裂的活动。为狄俄尼索斯所着迷,不至于荒芜,生命必须与大海保持联系,同时依靠大路上的文明保护机构,以便自己会成为狄俄尼索斯分解暴力的牺牲品。
4、尼采和瓦格纳
尼采本人不反对军事天才的胜利,但在尼采眼中,军事胜利应该涉及的是一种文化英雄主义的振兴。战争对尼采意味着,狄俄尼索斯和赫拉克利特世界入侵政治,形成生命的紧要关头。由此,文化也会正好得到滋润。
尼采依旧寄希望于某种形而上学的慰藉,在《悲剧的起源》中,尼采称神话为一种浓缩的世界图像,通过它,生命沐浴在意义的光芒中。尼采之所以转向神话,一方面是因为无法继续在宗教的意义中信仰,另一方面,也不信任理性可以给定生命的方向。
神话的发现,是一种生命权利的发现,这种生命权利把欢乐的充盈还给存在。瓦格纳和尼采,正是因为觉得他们的时代出于一种危机四伏和意义贫乏的社会状况,而致力于发现和发明新的神话。
经过这开始阶段的意见一致,而以后让尼采和瓦格纳分道扬镳的是,是瓦格纳要求的是一种宗教地位的神话生产,而尼采要求的是一种服务于生命艺术的神话的审美游戏。
在同尼采友好相处的时日里,瓦格纳虽然在政治上心灰意冷,但对自己的艺术充满信心,相信它可以补偿革命的缺失,甚至替代革命。艺术经历应该可以得出生命罪恶得到拯救的短暂瞬间,甚至可以成为时代终结的伟大拯救的先兆。
倘若艺术想要拯救宗教的精髓,必须成功促使人内心的一种持久转变,瞬间的艺术享受是不够的。作为宗教的艺术意志,会遭遇纯粹审美事件的限制。对于瓦格纳来说,这是尼采对他的一个巨大的羞辱。
5、尼采与时代精神
尼采要的是可怕的事物,所以音乐离他很近。他希望的是悲剧性感情的回归。尼采对时代的诊断是这样的:这是一个真实和正直的时代,但是以卑下的方式。
尼采反驳知识庸人们乏味的自然乐观主义,概括了他对自然的狄俄尼索斯的阐释。在自然的形态系列中,从无生命,经过植物性,到动物性和兽性,再到人的身上,最后意识出现。意识首先经历的不是世界的欢乐,相反,意识发现了存在的痛苦。
与叔本华不同,尼采强调人身上有统治那个别样的,烦躁不安的,毫无知觉的非比寻常的强大意志,这就是狄俄尼索斯的智慧。它足够强大,可以承受深渊,而不因此毁灭。相反保持一种神秘的,快活的镇静。
接着与唯物主义的论证之后,尼采开始了反对历史征服的斗争,这是尼采第二个对时代精神进行挑衅的观点。
公众生活中历史主义的泛滥,尼采看到的是一种浅薄的黑格尔主义的后期发展。视历史的强者为理性者,要求对现存者权力的尊重和掌握历史知识的勤勉。历史对黑格尔虽然是理性的,但黑格尔在历史哲学也说过:“没有人不会为历史陶醉而纵酔极乐。”
尼采的路径是回到尚未进行历史思考的希腊时代,用历史来反对历史学,成功地形成一个广袤的视域,创造神话,画出一个圆圈,生命能充实他,也可以在其中实现自身。
那么究竟又是什么队尼采反对时代精神起到了激励作用或者是什么让他相信自己的思想得到了证实。上帝死了,人们破坏了我们存在的彼岸,但还是存在折磨我们的残酷幻象,杀上帝的凶手迫不及待做的,是用一种内心的彼岸来取代古老的彼岸,一方面表现为弗洛伊德的超我,另一方面是在我们心中建立起总体概念的统治。
属于尼采在瓦格纳的影响下自己发明的更高的天性的,是一种形而上学的幻觉意义上的超越历史的思维方式,虽然不召唤彼岸的秩序,不过在次在中发现了永恒和意义相同者的特征。
6、尼采与科学
有一个决定性的思想和一次决定性的经验,导致尼采放弃了他的形而上学和艺术观点。正是1876拜罗伊特的节气演出那令人失望的经历。
尼采接着让一个科学的天才登场,这种科学出于对自然的可探究性,知识是万能治疗力量的信念生存。尼采看来,苏格拉底与学生最后谈话中所说的话,重要的倒不是个别的不朽的证明。单就这种证明来看,显示出了它的可疑性,苏格拉底称其为一艘救生艇,人们尝试用它游过生命。但决定性的其实是把生活作为一个鲜活的客观个体来体验。这种思维的自我体验,在理性和神话之间,在苏格拉底那里,没有任何矛盾。理性精神把他引向自身,他又让神话来证实自己。
尼采看待科学,将其看做同民主的精神叛乱联系在一起的伦理。苏格拉底以其对统治权力的蔑视表达了这种伦理。要是自然可以通过科学变得可以被统治,社会所固有的不平等为什么不能被消除?在苏格拉底文化的怀抱里,民主的精神得到孵化。科学的真理和发明,效用是超越主体的。真理面前人人平等。
但尼采担心的是在底层中间散播知识和认知,会发生可怕的,毁灭文化的暴动。有意识的人类无法忍受一个冰冷的宇宙,人们想要有居家的感觉。在他们那里,哲学不是什么别的东西,而是回家的渴望。
极端的真理意志有可能导致逻辑的世界否定,科学,它否定着过去我们熟悉的世界的价值。与狄俄尼索斯的世界不同,这种否定,不含任何戏剧性的东西。同康德的物自体的情况相同。他在封闭的认知世界起到了一个洞眼的作用,通过这个洞眼,令人不安的气流得以吹入。康德的后人都想窥视莫耶纱巾的背后,即使没有看到,人们也想发明一种咒语。
人类的一种整体意识,同德国的理想主义,特别是和黑格尔的想象不一样,其效果不是崇高的,而是毁灭性的。尼采同样不能满足于浪漫主义诗人的安慰的话语,人们不能有意识地留在谎言中,不应委身于诗人美丽的假象。
尼采一方面只有审美意识上的自我维护,一方面是作为同情后果的绝望。尼采试图第三种可能性,一个泰然自若,几乎是快乐的自然主义。这样灵魂会失去少许重力,像是一种漂浮。尼采把这样一种变得轻松的精神状态,描述为自由和无忧无虑的翱翔。
对尼采来说,如何对待起源,决定了科学还是形而上学的工作。倘若形而上学寄希望于崇高的起源,那么,科学就把关系翻转过来,开始不是什么,仅仅是偶然性和无差异性。
世界非形而上学地站在人们的目光前,作为一种没有意义的开端和没有意义的终结。自然虽然有力地发展,但向前推进的因果关系是盲目的,宗教曾经在一个精神关联的媒介中影响自然,对科学来说,这种关联已经终结,科学相信人们现在有能力,在利用自然规律的情况下,让它为自己服务。
对尼采来说,思维是一种前所未有的乐趣,他无论如何不想放弃他,为此他感谢生命,因为是生命给了他兴趣。尼采和他的思想之间,上演着一个热烈的恋爱故事,带着所有的纠葛。
在尼采那里,道德以自我的分割为前提,尼采思考了人的核分裂,个体不是一个统一体,他也可能成为一个内在世界的活动场所,谁要是探究它,谁就有可能叫做那个人的内在世界的探险家。
尼采实验这这样一个论点,在善恶背后隐藏着古老的高贵和卑贱的区别,从高贵的视角出发,糟糕的人是微不足道的。人们根本无需顾忌他们,因为卑贱者自己都不尊重自己。比如人们为了表示谢意,回赠之物超过接受之物,这种通过债务关系的颠倒,人们想重新获得自由,这在尼采看来是一种温柔的报复类型。
尼采接近韦伯,认为科学无法做出价值判断,但通过对文化的功能网络的解释,科学给活动提供了准则,允许对手段的合乎目的性进行评判。
在宗教的情感中还有什么其他东西可以被发现吗?尼采认为还有,那就是作为感觉到自己有罪的准备就绪。它表现为罗马文化晚期的疲软,负罪感,宗教如同一剂麻醉针,面对角斗场里的搏斗,罗马人已经变得麻木,却开始在禁欲,殉教,修道中获得愉悦。
尼采由此刻画了当时文化需求的一种社会学意义的尖刻草图,之所以不能放弃艺术,是因为不能彻底放弃宗教慰藉,在艺术中听到渐次匿迹的宗教回响。
形而上学,宗教中那伟大的拯救性感觉,被尼采称作一个热带时代,他看到一种温和的文化氛围正在形成,他想加速这种文化的突变,但他也知道,冷却自身也存在的风险。
7、尼采的“永恒轮回”
即使冷却激情是科学的功绩,在尼采看来也不应该走的太远,因为社会不仅受到无节制的激情的威胁,也可能在科学的系统冷却中变得麻木。
1881年,在锡尔斯-玛利亚的锥形岩石旁,永恒轮回的思想在尼采的脑中灵光乍现。年终,尼采在热那亚结束了他的《朝露》,他把自己对于人类精神未知领域的探索,比作是哥伦布发现了新大陆。
意识到底有什么用?尼采的回答是,意识是其间的领域。它是人与人之间的联系网络,其中,语言是沟通的符号。尼采在1882年夏《快乐的科学》的结尾处,小心翼翼的暗示。又过了一年,他让查拉图斯特拉走上舞台。他自己说这是一个需要千年,才能成为什么的思想。
在尼采获得这个转变的思想,即相同的事物的轮回的思想之前,萦绕在他脑海里的是什么?尼采以世界钟的比喻说明了这点,暗示了世界的不停旋转。新的世界时期不是新的,钟面只是表象,新的世界时期将重复这些事件,指针接着指针。
尼采将永恒轮回的思想理解为论题性的真理,也把它作为生命构造的实用手段。以这样的方式,他成功给一种冰冷的意识加热。
一切狂喜,愉悦,的天堂之行,这个以前是被幻想植入彼岸的,现在应该以直接,此岸的生活为准,永恒轮回为内在性保留了超越的力量。如查拉图斯特拉所说,“对地球保持忠诚。”
永恒轮回把宇宙想象为一个封闭的整体,受无情的必然性的彻底控制,这个必然性就是把宇宙成为一个百音盒。我们在盒子里玩耍,其实只是被玩耍。
还有一个尼采不能解决,却无法回避的问题,到底这种意志是服从于自我保存,还是挣脱了自身,到头来反对自己的生命?
我不会失去自己,这可能是个快乐的回答,但可能的惊愕也是,我永远无法摆脱我自己。似乎自己从一个命中醒来,但是带着清醒的意识好,还是继续做梦不被自己毁灭自己好呢?夜游的人必须继续做梦,这样才不至于继续跌入深渊。
8、尼采和莎乐美还有他们的查拉图斯特拉
莎乐美曾经对尼采有过这样一个论断:“尼采会作为一个新的宗教的预言家出现,那时一个为自己的信徒招募英雄的宗教。”
莎乐美不愿成为尼采的信徒,她很好的理解了尼采,但带着她自己的好奇心径直地走向了他人,而没有留在尼采的魔力圈中。把尼采作为自己的教育的站点丢开,抛在了身后。
对此,尼采无法忍受。《查拉图斯特拉》的开头场面,清晰的展示了尼采受到伤害之后的绝望的痕迹。查拉图斯特拉离开了自己的家乡,在大山里归隐了十年,在那里享受精神,直到充盈,直到真正的漫出。但他下山来到人类中间,也就开始了自己的下坡路。
在尼采对于超人的定义中,不涉及任何生物的问题,它是人类精神的力量在上升的过程中的自我控制,自我塑造的力量。但生物学的语调也渗透在查拉图斯特拉的谈话中:“猴子之于人是什么?一个嘲笑或一个痛苦羞辱。人之于超人也是这样,一个嘲笑或一个痛苦的羞辱。”
在《论道德谱系中》尼采向我们展示了一个臭名昭著的“金发野兽”,之所以选择这个例子,是为了证明人内心沉睡的活力,不过,尼采当然不是一个彻底破除心里拘束的鼓吹着,对尼采来说,塑造的原则也一直在起作用。伟大的力量也必须经由一种强大的意志才能获得一种形式。
超人是不受道德指责,在《查拉图斯特拉》中,超人第一次的宣告是,你们正完成由虫到人的过程,但你们在许多方面仍然是虫。“作为群体的人类,为了一个单独强大的人种繁荣而牺牲,这也许是进步的。”
尼采的超人也是对上帝之死的一个回答,让我们回忆一下《快乐的科学》那个疯子在明亮的上午提着灯笼乱跑乱叫:我找上帝!我找上帝!
其实,上帝的凶手或者成为超人,或者坠入平庸。超人体现了此案的神圣,作为对上帝之死的回答。尼采想用超人拯救此岸的神圣力量,针对世俗化的虚无主义倾向。
在《查拉图斯特拉》的第一部,结尾写道:众神死了。在第二部《幸福岛》上,是这样的话:“以前,人们眺望远方的海,便谈论上帝,现在我教你们说:超人。”上帝只是一个假定,而我要你们的假定,不超过你们自己创造的神话。
对尼采来说,超人真正的重要性是自己已经变得成熟,能够把握和承受自己的可怕。这种情况以令人毛素悚然的效果在一个场景中得到描述,一个牧羊人,嘴里往外吊着一个一条黑蛇。查拉图斯特拉,克服自己厌恶和害怕,要求他把爬到他嘴里的蛇的脑袋咬下。于是,一个超人诞生了。
9、尼采的“权力意志”
尼采为《查拉图斯特拉》设计的顺序是:首先勾画一个生活艺术的轮廓,由此让生命和爱情变得显豁。要向太阳一样,带来光明和希望。他在三种变形的讲话中谈到三幅形象的图像,人最初是骆驼,负载着前部的你应。然后变成了是狮子,开始抗争,因为发现了我要。最后成为了儿童,在新的台阶上重新获得某种生灵的自发性。“人们不该把自己牺牲给意见的市场,也不该把脑袋藏到天国的沙子里。”
“权力意志”是查拉图斯特拉的第三项教义,生活需要被生活,而不是思考。查拉图斯特拉和舞女的故事中,他本希望诱惑她们进入自己的生命,但是这样做却赶跑了舞女。因为舞女只想跳舞,并不愿意被人探究。尼采到这智慧又一次呗孤独的抛下,又一次沉入自身的深不可测之中。
什么是权力意志?尼采说“创造一个你们能对此下跪的世界,这是你们最后的希望和陶醉。”
如果说在查拉图斯特拉时代,权力意志还只是自我克服和自我升华的惯用语,如今它已演化成一把解释一切生命过程的万能钥匙。尼采感兴趣的不是防御性的自我保存,而是进攻性的自我升华,冷漠的社会正是体现了一种平衡,这是正义的基础。热泪的社会正是将平衡的位移陷入运动从而导致一种新的平衡并为之斗争。
在尼采看来,基督教为此提供了三大好处:1、赋予人一个绝对价值,不同于生成和消逝的洪流中的狭隘性和偶然性。2、给予痛苦和不幸一个意义,让他们变得可以忍受。3、世界被理解为受到精神的滋润,所以是可以认识和有价值的。尼采承认基督教,但不感谢。因为,对弱者的同情和平衡道德,有碍于一种更高级人类和高贵文化的展开。苦行僧在尼采眼中不过是一个伪装的权势者,针对自己感官和肉身需求的丰富性,建立一种残酷无情的统治。苦行僧是把生命表现成了切割生命,他实质是一个充满权欲的反狄俄尼索斯者。
但尼采自己呢?他有着狄俄尼索斯的天性,可是谁又能说清他不具有苦行僧的天性呢?上帝之死引发的道德革命 是一次价值的全面重估。重估是为有道德教养和豪迈高贵的人分配道德的奖金。
10、尼采之死
1889年1月3日,尼采离开了他的居所,在阿尔贝托广场,看到一个马夫在抽打他的马匹,尼采哭叫着扑倒马脖子上想保护它。尼采最终被同情征服,精神崩溃。
尼采曾这样预言过自己:“面对某一个时刻,我放眼于我的未来,一个遥远的未来,就像放眼于平静的海绵一样,上面丝毫没有卷起一丝渴望的涟漪。我丝毫不想让情形有所改变,我不想成为另一个人。”
方亦元
2015年10月4日完稿于华东师范大学图书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