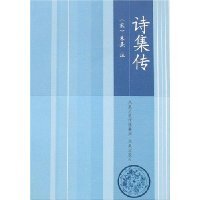
《诗集传》是一本由(宋)朱熹 / 王华宝标点著作,凤凰出版社出版的290图书,本书定价:17.00元,页数:2007-1,特精心从网络上整理的一些读者的读后感,希望对大家能有帮助。
《诗集传》精选点评:
●简体横排太虐心了
●借来的书里有书虫饿...不只一只...严重挑断我的视神筋.遂去复印.B5纸张.放大了看.很爽.
●版本很一般,很多错误没有校勘。
●咦没有蓝皮儿那本?
●印刷错误较多
●朱子注的诗算是好的。
●没想到这种书居然可以津津有味,女曰鸡鸣,士曰昧旦,虫飞薨薨,甘与子同梦,纵我不往,子宁不嗣音,永以为好也,琴瑟在御,莫不静好,殷其雷,在南山之阳,有女怀春,吉士诱之…我的天…觉得自己硕士可能一不小心就被勾去读古代文学了
●小雅的分篇和毛诗经不一样。“因《仪礼》正之?”
●朱子注释的可以
●此书之前打五星是从对于朱熹20卷本《诗集传》的肯定。后来接触了古籍善本和更好的点校本,发现此书在点校中存在一些问题。比如作者仅仅指明了底本,而缺乏对对校本的说明。条目下也没有校勘记。这个点校本可为朱子《诗集传》研究的入门书目,却不适合专业的学术研究。
《诗集传》读后感(一):辱没斯文
为简体横排。
朱熹《诗集传序》的署名竟然是“新安朱嘉序”
一代鸿儒的名字,说改就改了。真是朱子改大学,校者改朱熹。点校者不是清儒派来的“奸细”,就是阳明先生派的“卧底”。
但是想来,点者师从徐复,也算是黄季刚先生的再传弟子。如此改字肯定有所由来,在下不才,还望方家指点。
如果确是笔误,这种错误,真是辱没斯文。
《诗集传》读后感(二):本科二年级的读书小结
笔者总结《诗集传》时的心情是战战兢兢的。《诗集传》实在是学术界太过重要的一部经典,是宋学诗经学的大成之作。笔者也十分钦敬朱熹“无所不用其极”的治学精神。历代学者的研究著作也是不胜枚举。笔者也只不过有两个月左右的阅读经验,只能大概表达自己的一些感受,是万万不敢有所僭逾而轻易评判的。 首先,笔者很愿意阅读,《诗集传》很有文学性。因为朱夫子是从文本自身解读的,不似汉学家依照《诗序》解读《诗经》,有枯燥乏味之感,而且有些解释的确过于牵强,并未有批判汉学家之意,笔者是很钦敬那些治学严谨的《诗经》汉学家的。只不过,朱熹更的解读更富有文学性,而汉学家的解读政治意味过于浓厚而忽略《诗经》文本本身之美了。其次,《诗集传》很有创新意识,而且笔者认为朱熹的创新是成功的。《诗序》是极有权威性的,朱熹的行为必然会遭到很多学者的质疑。可是,《诗集传》仍旧流传下来了。多少典籍都在历史的长河中淹没了,其消失有偶然性而更多的还是遭受淘汰的历史必然性。《诗集传》经得起时间和空间的考验,说明朱熹是成功的。朱熹的创新,体现了中国学术思想的进步。从侧重字词训诂到义理阐发,经历了一个由繁到简和解放文本的过程。学术是需要有创新精神的。而创新的前提是对自己所要创新的东西有深刻的了解。“了解它,才能打破它”,朱夫子对汉学《诗经》是有深刻理解的,所以他才能做出合适的创新。反观五四时期的鲁迅、胡适等人,他们的国学素养是很高的。可是,他们要打破自己所熟悉的体系,这需要勇气,更需要实力。他们了解,所以他们才有发言权。朱熹更是有勇气也有实力的学者。最后,朱熹对《诗经》的解读方法,有利于涵养性情。其实,《诗集传》抛开《诗序》的做法,对于读者提出了更高的要求,读者不能按照一个相对固定的思路解读《诗经》了,需要读者自己反复地熟读玩味文本。在这种反复的体味中,鉴赏力和眼界就渐渐提升了,有利于个人性情的涵养。当然,朱夫子对《诗经》的解读还存在有待商榷的地方。比如:朱熹的“《国风》民间说”和其使用的叶韵系统。人不以一眚掩大德,朱夫子的治学理念和精神很值得后学们学习。 总而言之,朱熹治学的创新意识和涵养性情的要求是很值得赞赏的。
《诗集传》读后感(三):诗无达诂
我们读《诗经》的时候经常要面对众说纷纭的解读,比如毛诗、三家诗、朱子诗集传等等,很多人会执着于某个解读的对错。
孔子说:“诗无达诂”。我想《诗经》诗篇的意义,首先取决于读者,乃至于读者身处的这个时代。所以无论毛公、三家诗传人、朱子,作为儒者,他们在解读《诗经》时首先要为他们身处的时代负责,他们立足于他们的时代,基于诗篇做出有利于时代进步的呼声,那么这种解读就是“中庸”的。而每个人眼中的世界固然有所差异,所以“诗无达诂”。比如,我们这个时代的人群,往往重“爱情”,于是便在许多诗篇之中看到了男欢女爱;而在上古时代,“贤贤易色”的君子们,却往往以类似苏格拉底的男男之爱,表达着对贤君子的渴慕;而在中古时代,或者面临着传统礼法的崩溃,于是诗篇之中便充满了对淫邪的斥责。
这种解诗的态度,就是属《诗》的,或者说“属灵”的。《诗经》诗篇经常以天地之间平凡的万物起兴,而娓娓述说诗人真挚的情感,我们在阅读之中可以感受到诗人的情感被投射于万物之中,令“无情”的宇宙,瞬间变得“有情”了起来。万物之美,与人情之美,浑然一体,这是天地之大美——通过诚挚的倾述,诗人们在诗意中天人合一,这不就是我说的“宇宙圣心”之义吗?
所以,孔子说“诗无邪”,诗的确是无邪的,因为祂是赞美人情的,人情之初,都是无邪的,因为祂至真至深。《三字经》不是说“人之初性本善”吗?阳明先生不是说“无善无恶心之体”吗?无善无恶便是至高的纯洁。人间的丑恶,本不应该怪罪于情,只应怪罪人的愚昧——情之初,固然美,而情之滥,则可以流于痛苦、悲伤、甚至罪恶,这不是有情人的错,正是有情人“不识情趣”——用刀自残,难道是刀的错吗?
《诗经》揭示了男欢女爱的真谛,在“爱情”中我们得到,我们失去,我们欢欣,我们痛楚,这是“爱的宿命”,我想圣人是想用这些“郑声”来度脱我们于情波爱海之中的。所谓“发乎情,止乎礼”,正是在“得”与“不可得”的“中间道”中寻求一种长久的诗性的审美愉悦,我们可以像怀揣世间的珍宝般怀揣着彼此之间的情感,小溪缓缓流淌,我们静静观望。而干柴烈火之后,我们除了失落还剩下什么呢?反而此情绵绵无绝期的淡淡忧伤之中,有一种美,妙不可言。我不是在谈道德或礼法,我在讲如何保有持久的“愉悦”和“美感”,关于男女之情,我想《诗经》想告诉我们的是,我们的愚昧和无知往往留不住当初的美好。
人间的种种得与不得,情欲、渴求、忧愁、哀闵,酸甜苦辣、悲欢离合,在《诗经》的中道智慧之中,都升华为一种宗教体验。这是不是《红楼梦》中警幻仙子的开示?释迦摩尼以此为苦,而圣贤却能苦中作乐,莫不是更高一筹?
所以,读《诗经》,读的是不变的人情,读的是自己的心。那不止是千年前的故事,更是当下的故事,那就是你自己的故事——圣人历历在目,了然于心。谁说圣人不懂男欢女爱,不懂约炮(《诗经》里确实存在约炮的现象),只是祂看穿了一切,所以祂比你我更懂其中的情趣和奥妙。
固然,《诗经》不是专谈男女之情的,但无论如何,祂是一本真正的“情书”,堪为人间无二的典范。此情是遍布三千法界的大有情,是一心开二门的如来藏,是耶稣基督三位一体的爱。《中庸》叫做“诚”,日本人有个词专门形容祂——物哀。
祂是最平凡的,也是最神秘的。鬼神之奥,万物之妙,人间之美,莫过于此。
《诗集传》读后感(四):點校不是一般的差
为避繁琐,本文引此本《诗集传》,一律于引文前标出篇名、章次及正文或注文,引文后注明页码,不再另行出注。
一、底本不误,点校本误录入者
1.《诗经传序》:必有自然之音响节奏而不能已焉。(《序》P1)
按:篇题作“诗经传序”,殊误,当从底本作“诗集传序”。奏,底本作“族”,节族,其实也就是节奏的意思,但此处不当改。
2.《诗集传序》:淳熙四年丁酉冬十月戊子新安朱嘉序。(《序》P2)
按:此《序》乃朱熹自作,亦收于《朱文公文集》,底本正作“朱熹”,此显系点校本误录。
3.《周南•关雎》一章注文:此纲纪之首,王化之端也。(P2)
按:化,底本作“教”,不当改。
4.《周南•桃夭》一章夹注:夭,方骄反。(P6)
按:方骄反,底本作“於骄反”,核《四库荟要》本、《四库全书》本的八卷本《诗集传》,作“音腰”,故亦当以底本为是。
5.《召南•何彼襛矣》一章、二章正文、一章注文及篇名皆作“何彼秾矣”。(P15-16)
按:底本作“襛”。“秾”为讹字,《四库总目提要•诗集传》说陈启源《毛诗稽古编》已揭明此误。[2]今人《诗经》译注本多有误作“秾”字者,均当改。
6.《召南•何彼襛矣》一章注文:康棣,栘也,似白杨。(P16)
按:底本作“唐棣”。正文为“唐棣之华”,此乃注文,不当改动正文。
7.《邶风•终风》一章注文:言虽其狂暴如此,然亦有顾我则笑之时。(P21)
按:“则”,底本作“而”。此显系点校本误录,当从底本为是。
8.《鄘风•桑中》一章正文:爰采唐矣,沫之乡矣。(P35)
按:底本作“沬”,朱熹注音曰“音妹”,可见是从未得声,而非从末得声的“沫”字。底本正是,校点本误录。又,本章注文、二章、三章正文此字皆误。
9.《王风•中谷有蓷》一章正文:有女仳离,慨其叹矣。慨其叹矣,遇人之艰难矣。(P52)注文:慨,叹声。(P52)
按:此三“慨”字,底本均作“嘅”。考阮元刻《毛诗正义》和《四库荟要》本、《四库全书》本的八卷本《诗集传》,此处亦均作“嘅”,故点校本误,当以底本为是。
10.《郑风•遵大路》一章夹注:寁,市坎。(P59)
按:此夹注乃为“寁”字注音,后面脱一“反”字。又核底本,此作“帀坎反”。《毛诗音义》作“巿坎反”,阮元《校勘记》说:“案:《释文》校勘,巿当作帀”。[3]作“市”或“巿”,音切皆与“寁”相异,阮元说是。故当以底本为是。
11.《郑风•子衿》一章注文:青青,纯绿之色。(P63)
按:底本“绿”作“缘”。常森先生《“纯绿”还是“纯缘”:一个〈诗经〉学的误读》认为众家将《诗集传》本篇中的“纯缘”改作“纯绿”是错误的,并对其此有详细论证。[4]拙文《阮元本〈十三经注疏〉误刻六则——兼谈古籍校勘中参校对象的问题》申明常森先生的校勘是正确的,并认为朱熹的注释,实际上是承自陆德明《经典释文》,未必如常森先生所说与朱熹之重礼制相关。[5]
12.《齐风•敝笱》篇注:按《春秋》,鲁庄公……七年,夫人姜氏会齐侯于防。又会齐侯于榖。(P71)
按:“榖”,从木;底本作“穀”,从禾,今简化作“谷”,但此处乃地名用字,可不必简化。又核《左传•庄公七年》,当以作“穀”为是。
13.《唐风•有杕之杜》一章注文:噬,发语辞。(P83)
按:底本作“发语词也”。此虽于义无伤,但改动原文则大可不必。又,点校本中将底本的“词”误改为“辞”者颇多,文不备举。
14.《陈风•月出》三章注文:天绍,纠紧之意。(P96)
按:底本“天绍”作“夭绍”。本诗三章正文作“舒夭绍兮”,此乃注文,亦当与正文同,且《四库荟要》本、《四库全书》本的八卷本《诗集传》亦作“夭绍”,故当以底本为是。
15.《桧风•素冠》一章注文:黑经白纬曰缟,绿边曰纰。(P98)
按:底本“绿”作“缘”,其误当同《郑风•子衿》篇。此说实出自《礼记•玉藻》注文,彼处亦作“缘”,故当从底本作“缘”为是。
16.《曹风•鸤鸠》二章注文:骐,马之青黑色者。(P103)
按:底本无“之”字,点校本衍一“之”字,当删。
17.《豳风•伐柯》二章正文:我遘之子,笾豆有践。(P112)
按:底本“遘”作“觏”,阮元刻《毛诗正义》亦作“觏”,故当从底本作“觏”为是。《四库荟要》本、《四库全书》本的八卷本《诗集传》作“遘”,亦误。
18.《小雅•常棣》首章注文:“故言常棣之华,则其鄂然而外见者,岂不 乎?(P119)
按: ,底本作“韡韡”。 实指蔽膝,则“ ”不辞;而且,这一句是对诗文“鄂不韡韡”的解释:故当从底本为是。
19.《小雅•采芑》三章正文:振振阗阗。(P136)
按:底本作“振旅阗阗”,阮元刻《毛诗正义》同,《四库荟要》本、《四库全书》本的八卷本《诗集传》同。故当从底本。
20.《小雅•我行其野》三章正文:成不以富,亦秖以异。(P144)
按:底本作“亦祗以异”,阮元刻《毛诗正义》同,故当从底本。《四库荟要》本、《四库全书》本的八卷本《诗集传》误作“秖”,亦当改。
21.《小雅•頍弁》一章正文:未见君子,忧心弈弈。(P188)一章注文:奕奕,忧心无所薄也。(P188)
按:此处正文与注文字形不同,必有一误。核底本,作“弈弈”;又检阮元刻《毛诗正义》,亦作“弈弈”。故当以正文作“弈弈”者为是,注文为误。
22.《大雅•皇矣》二章正文:修之平平,其灌其栵。(P215)
按:底本作“修之平之”,阮元刻《毛诗正义》同,《四库荟要》本、《四库全书》本的八卷本《诗集传》同。故此当以底本为是。
23.《大雅•皇矣》四章注文:貂,《春秋传》、《乐记》皆作莫。(P216)
按:底本“貂”作“貊”。这是对正文“貊其德音”进行解释的,“貂”字显误。当从底本作“貊”为是。
24. 《大雅•假乐》一章夹注:假,《中庸》、《春秋传》皆作嘉,当作嘉。(P228)
按:底本“当作”上有一“今”字,点校本脱。当据补。又,此处标点与他处不统一,详下文。
25.《大雅•嵩高》一章注文:宣王之舅申伯,出封于谢,而君吉甫作诗以送之。(P248)
按:底本“君”作“尹”,因吉甫官职为尹,故有“尹吉甫”之称。遍检先秦典籍,并无“君吉甫”这个人,故此处显误。相同的错误还有两处:本诗八章注文:“吉甫,君吉甫,周之卿士。”(P249)《大雅•烝民》八章注文:“城彼东方,其心永怀,盖有所不安者,君吉甫深知之,……”(P251)这两处底本也都作“尹”。
26.《周颂•振鹭》一章注文:言鹭飞于西雝之水,而我客来助祭者,其客貌修整,亦如鹭之洁白也。(P266)
按:底本“客”作“容”,“客貌”不辞,当从底本作“容貌”为是。
27.《商颂•长发》二章注文:牵,循;履,礼;越,过;发,应也。(P287)
按:底本“牵”作“率”。又,本章正文并无“牵”字,此处当时对正文“率履不越”句的训诂。且检《故训汇纂》,“牵”并没有训为循的用例;而“率”则有循、遵的意思[6]。故此当从底本作“率”为是。
二、底本有误,点校本当改而未改者
1.《周南•汝坟》一章夹注:枚,叶莫悲切。(P8)
按:本书注反切,其他的地方都是注“某某反”,唯独此处作“切”。此字底本作“切”,而元刻本作“反”,故当以元刻本改正,作“叶莫悲反”为是。
2.《鄘风•定之方中》二章正文:卜云其吉,终焉允臧。(P37)
按:此处底本作“焉”失误,当作“然”。《四库总目提要•诗集传》说此误为冯嗣京所校正。[7]阮元刻《毛诗正义》作“然”,其《校勘记》说:“唐石经、小字本、相台本同,《考文》古本同,闽本同,明监本、毛本‘然’误‘焉’。案:《正义》云:‘终然,信善。’又云:‘何害终然允臧也?’皆可证。”[8]阮校是,当据改,作“终然允臧”。
3.《魏风•伐檀》一章、二章、三章注文:比也。(P76-77)
按:此处底本作“比也”,但元刻本等作“赋也”。朱师杰人先生点校本《诗集传》于此三处皆改作“赋也”,并出校勘记曰:“原作‘比也’,据元本、明甲本、明乙本改。”[9]本诗一章注文曰:“诗人言有人于此,用力伐檀,将以为车而行陆也。今乃寘之河干,则河水清涟而无所用,虽欲自食其力而不可得矣。然其志则自以为不耕,则不可以得禾,不猎,则不可以得兽,是以甘心穷饿而不悔也。” 细绎其义,朱熹是以为此处为赋,而并非比,故当从朱先生之校勘,作“赋也”为是。
4.《秦風•小戎》三章注文:闭,弓檠也,《仪礼》作“ ”。(P87)
按:此系朱熹误记,《仪礼•既夕礼》“有柲”郑玄注引《诗》“竹柲绲縢”; 乃《周礼•考工记•弓人》郑玄注所引《诗》文。二者任改其一即可。
5.《陈风•泽陂》一章注文:此诗大旨,与《月出》相类。(P97)
按:底本作“大旨”,用在此次,于义不贯。朱师杰人先生校点本《诗集传》有校勘记作:“‘大’,明甲本、八卷本作‘之’。”[10]作“此诗之旨”,于义较顺,可从之而改。
6.《小雅•斯干》六章夹注:寝,叶于检、于锦二反。(P146)
按:此从底本,但是于是云母字,寝是清母字,“于检反”、“于锦反”并不能切出“寝”字的读音。朱子所注叶音,是改动韵部,并未对声纽有所改动。汪业全说此处的两个“于”字均当作“千”。[11]千是清母字,汪说甚是。这大概是由于字形相近致误,此当从汪说,改为“叶千检、千锦二反”。
三、标点不当者
1.《周南•麟之趾》篇注:序以为《关雎》之应,得之。(P9)
按:此“序”特指《毛诗序》,故当加书名号,作:《序》。相同的错误本书还有多处,比如:《卫风•淇奥》篇注:故序以此诗为美武公,而今从之也。(P41)《小雅•雨无正》篇注:据序所言。(P158)
2.《卫风•芄兰》一章注文:容、遂,舒缓放肆之貌。(P46)
3.《曹风•候人》四章注文:荟、蔚,草木盛多之貌。(P101)
按:《诗经》中的“A兮B兮”句式,大多应当把“AB”理解为一个连绵词,除本诗的“容兮遂兮”外,还如《曹风•候人》的“荟兮蔚兮”、“婉兮娈兮”,《小雅•巷伯》的“萋兮斐兮”等等;《诗经》中常见的“叔兮伯兮”、“父兮母兮”,虽不能将“叔伯”、“父母”当成连绵词,但至少是可以当成一个词来看的。而且,我们从朱注运用了训诂术语“貌”来看,朱熹自己也应该是把这个“容遂”和“荟蔚”理解成一个词的,故此顿号皆当删。
4.《卫风•芄兰》一章正文:虽则佩觿,能不我知?(P46)二章正文:虽则佩韘,能不我甲?(P46)
按:据朱熹自己的注文,分别将这两处解释为“言其才能不足以知于我也”,“言其才能不足以长于我也”。很明显,他自己并未将这两句看成是疑问句,而是当成陈述句的。且不管朱熹之注释是否正确,今人标点古籍,当据注家之意以断句,则为通例。这两个问号都应该改成句号。
5.《卫风•芄兰》二章注文:韘,决也。以象骨为之,著右手大指,所以钩弦闿体。郑氏曰:“沓也,即《大射》所谓朱极三是也。以朱韦为之,用以彄沓右手食指将指无名指也。”(P46)
按:“以象骨为之”云云,也是释“韘”,故其前不当用句号,而应该改成逗号。“朱极三”见于《仪礼•大射仪》,故当加引号。将指,指拇指或中指,本句指中指,故其前后皆当加顿号。另,这里的“著”,应该改作简体,作“着”为是。
6.《卫风•伯兮》四章注文:谖草合欢,食之令人忘忧者。(P47)
按:谖草、合欢,均为草名,晋张华《博物志》认为合欢就是萱草,也即本诗中所说的“谖草”。点校者于此未加标点,显然不当,谖草与合欢中间应加逗号。
7.《王风•扬之水》二章注文:《书•吕刑》、《礼记》作甫刑,而孔氏以为吕侯,后为甫侯是也。(P51)
按:《吕刑》为《尚书》之一篇,《礼记•表记》《缁衣》引作“《甫刑》”。故此处当标点为:《书•吕刑》,《礼记》作“《甫刑》”;而孔氏以为“吕侯”,后为“甫侯”,是也。或标点为:《书》“吕刑”,《礼记》作“甫刑”;而孔氏以为“吕侯”,后为“甫侯”,是也。
8.《郑风•女曰鸡鸣》三章注文:来之,致其来者,如所谓修文德以来之。(P60)
按:“修文德以来之”,语出《论语•季氏》,此为引文,当加引号。
9.《齐风•鸡鸣》一章正文:“鸡既鸣矣,朝既盈矣。”“匪鸡则鸣,苍蝇之声。”(P67)二章正文:“东方明矣,朝既昌矣。”“匪东方则明,月出之光。”(P67)三章正文:“虫飞薨薨,甘与子同梦。”“会且归矣,无庶予子憎。”(P67)
按:点校者将三章每两句分别加上引号,并不符合朱熹原意。朱熹于一章注文中串讲章旨曰:“言古之贤妃御于君所,至于将旦之时,必告君曰:‘鸡既鸣矣,会朝之臣既已盈矣。’欲令君早起而视朝也。然其实非鸡之鸣也,乃苍蝇之声也。”可以看出,朱熹实以前两句为君妃所说的话,而后两句则是叙述人的话,并非二人对话。朱熹于二章并未串讲章旨,但说“此再告也”,故当与一章同。因此,这两章当分别标点为:“鸡既鸣矣,朝既盈矣。”匪鸡则鸣,苍蝇之声。(一章)“东方明矣,朝既昌矣。”匪东方则明,月出之光。(二章)朱熹于三章串讲章旨曰:“此三告也。言当此时,我岂不乐与子同寝而梦哉?然群臣之会于朝者,俟君不出,将散而归矣。无乃以我之故,而并以子为憎乎?”据此,三章的四句当都是君妃所言,故当标点为:“虫飞薨薨,甘与子同梦。会且归矣,无庶予子憎。”
10.《曹風•下泉》篇注文:《诗》、《匪风》、《下泉》,所以居变风之终也。(P103)
按:《匪风》乃《诗经•桧风》中的最后一篇,《下泉》乃《诗经•曹风》中的最后一篇,既然都是《诗经》中的篇目,如此标点显然不当。可改为:《诗•匪风》《下泉》,或加顿号作:《诗•匪风》、《下泉》或《诗•匪风、下泉》。
11.《小雅•鹿鸣》一章注文:而其乐歌又以鹿鸣起兴。(P116)又,本篇注文:按《序》,以此为燕群臣嘉宾之诗,而燕礼亦云:工歌《鹿鸣》、《四牡》、《皇皇者华》,即谓此也。(P116)
按:“鹿鸣”是《诗经》中的一篇,“燕礼”是《礼记》中的一篇,故均当加引号。又,“按”乃按语之按,并非按照之按,故本篇注文中“《序》”后的逗号可删,以免割裂文义。相同的错误在本书中多处出现,不备举。
12.《小雅•何人斯》五章注文:《字林》云“盱,张目也”《易》曰“盱豫悔”《三都赋》云“盱衡而语”是也。(P166)
按:此处于《字林》、《周易》、《三都赋》之间不加标点,并不适宜。此处可标点为:《字林》云“盱,张目也”、《易》曰“盱豫悔”、《三都赋》云“盱衡而语”,是也。
13.《大雅•文王》一章正文:履帝武敏歆,攸介攸止。(P222)
按:本句断句一直存在争议,或断同此;或以“歆”此从下句,作“履帝武敏,歆攸介攸止。”此处,我们当据朱熹的注文来断定朱熹所认定的断句情况。本章注文曰:“姜嫄出祀郊禖,见大人迹而履其拇,遂歆歆然如有人道之感”云云。很明显,朱熹的断句是以“歆”此从下句的,故当标点为:履帝武敏,歆攸介攸止。
14.《闵予小子之什》末尾:闵予小子之什十一篇,十一章一百三十六句。(P276)
按:此乃对《闵予小子之什》篇数、章数、句数的统计,故章、句数之间当有逗号。本书统计篇章句数的其他地方于此皆有逗号,独此书缺,可能是手民之误。当补足逗号,“闵予小子之什”似也应加上书名号,故当标点作:《闵予小子之什》十一篇,十一章,一百三十六句。另,全书其他地方的“某某之什”亦未加标点,似有不妥。
15.《商颂•那》篇注文:闵马父曰:“正考父校商之名颂以《那》为首。其辑之乱云云,即此诗也。”(P285)
按:此言“云云”,其后必非闵马父之语,而是朱熹之语。此语出自《国语•鲁语》:“闵马父……对曰:‘昔正考父校商之名《颂》十二篇于周大师,以《那》为首,其辑之乱,曰:……。”[12]故此处当标点为:闵马父曰“正考父校商之名《颂》,以《那》为首,其辑之乱”云云,即此诗也。
四、体例不一,当统一体例者
1.标点体例不一处
(1)本书于“某书作某字”处,一般对某书加书名号,某字都加引号,如《周南•汉广》一章夹注:息,吴氏曰:《韩诗》作“思”。(P7)《小雅•菀柳》一章夹注:上帝甚蹈,《战国策》作“上天甚神”。(P195)但是,也有一些地方于某书处未加书名号,有些地方于某字处未加引号:
《小雅•车攻》五章注文:柴,《说文》作 ,谓积禽也。(P137)为统一体例,此当标点为:《说文》作“ ”。
《小雅•角弓》七章夹注:曰,音越,韩诗、刘向作聿。(P195)又,七章夹注:娄,力住反,《荀子》作屡。(P195)又,八章注文:髦,夷髦也。《书》作髳。(P195)这三处当分别标点为:《韩诗》刘向作“聿”、《荀子》作“屡”、髦,夷髦也;《书》作“髳”。
《小雅•隰桑》四章注文:遐,与何同。《表记》作瑕。(P199)此当标点为:遐,与何同,《表记》作“瑕”。
《大雅•大明》五章注文:伣,磬也。《韩诗》作磬。(P208)又,八章注文:凉,《汉书》作亮,佐助也。(P208)这两处当分别标点为伣,磬也;《韩诗》作“磬”、《汉书》作“亮”。
此外,还可以举出一些,如《秦风•小戎》三章注文:闭,弓檠也,《仪礼》作 。(P87)《小雅•小宛》五章注文:岸,亦狱也,《韩诗》作犴。(P161)《小雅•何草不黄》二章夹注:矜,古顽反,韩诗作鳏,叶居陵反。(P203)《大雅•皇矣》四章注文:貂,《春秋传》、《乐记》皆作莫。(P216)《大雅•文王有声》三章夹注:欲,《礼记》作犹。(P220)《大雅•假乐》一章夹注:假,《中庸》、《春秋传》皆作嘉,当作嘉。(P228)《大雅•公刘》六章注文:芮……《周礼•职方》作汭。(P230)《大雅•民劳》五章夹注:谏,《春秋传》、《荀子书》并作简,音简。(P234)《周颂•维天之命》一章夹注:假,《春秋传》作何。(P208)又同章夹注:溢,《春秋传》作恤。(P208)《商颂•烈祖》夹注和注文均有:鬷,《中庸》作奏。(P285)《玄鸟》注文:何,任也,《春秋传》作荷。(P286)《商颂•长发》六章夹注:曷,《汉书》作遏。(P288)凡此,皆当统一标点体例。
(2)《小雅•常棣》八章夹注:亶其然乎,就用“乎”字为韵。(P120)而《大雅•公刘》四章夹注:君之宗之,就用之字为韵。(P231)二处的乎、之,一处标引号,一处未标引号,体例也不同,当统一为是。
2.避讳字处理方式不统一
汉代习《齐诗》的学者中,有一位叫匡衡,宋代因避太祖赵匡胤的讳,改“匡”为“康”。宋本《诗集传》于“匡衡”一律作“康衡”。这个点校本于《周南•关雎》一章注文及篇末注、《周南•兔罝》二章注文皆回改为“匡衡”,(P2,P3,P6)而《周颂•闵予小子》注文中却又作“康衡”。(P270)按点校古籍的惯例,缺笔避讳字一般改回用正字,而代字避讳的地方,一般则不改。故本书《周南•关雎》篇的两个“匡衡”皆当仍底本,作“康衡”为是。
此為轉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