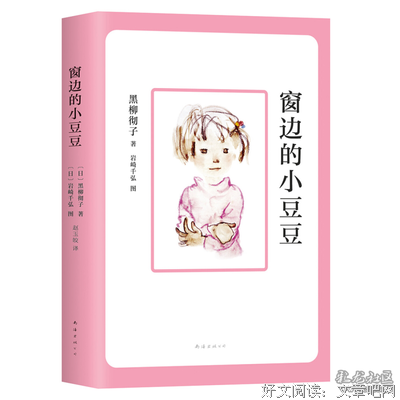
《去年在马里安巴》是一本由(法)阿兰·罗伯-格里耶著作,译林出版社出版的平装图书,本书定价:13.00元,页数:140,特精心从网络上整理的一些读者的读后感,希望对大家能有帮助。
《去年在马里安巴》精选点评:
●“去年,在马里安巴,你记得我们去年在马里安巴的那段爱情吗?”
●我接受影像,不接受这错乱的文字。
●看不懂。。。
●对不起“电影小说”这种新鲜事物我真是接受无能。我以为是文字描写有镜头感,结果却是每个镜头用文字描写!
●汉译本不好看。 用来给搞理论的意淫倒是不错。
●带有分镜头的剧本,抛开摄影机之外的部分其实是很有meta-narrative味道的。银幕表现的是无数“现在”时间片段(也只能如此),而文字却接通了时间的通道,在时间圆环里X与A的一次次相遇与对话,恰好成为一种叙事意义上的完满——当叙述开始,事件一定会在循环中达成,“去年你说过,如果我爱你,那么明年这个时候就来带走你”,当过去与未来连接到一起,所有的时刻就成为了现在。
●94、去年在马里安巴,[法]阿兰·罗伯-格里耶。格里耶远不止一位伟大的作家,他还是美好的画家,杰出的心理学家等。马里安巴也不是某一艳情发生地/假想出来的往事,它是爱情的理想国。我在这个分镜头脚本里看到了那部存在主义的电影,在华丽而冷漠的独家胜地,那迷惘的美丽女人和拯救她的骑士。
●理念不错,过于trick
●已有
●万分谢谢不知名的好心人(ಥ _ ಥ)格里耶的前记最有意思 看脚本的时候更多感觉是在用文字召唤图形记忆……
《去年在马里安巴》读后感(一):光影的碎片
标题听起来有点像印象派,但新浪潮电影,或者说属于其中一个分支的左岸派,还是受了这种艺术风格的影响。格里耶也算是新浪潮电影的一个代表人物,本来是想去找戈达尔的,但找到他了,也就看看吧。他认为电影就是其本身,有其独特的自在世界,并非什么生活的反映和倒影之类。所以他想把电影的特征发挥一下,所以用日常的理解习惯来看这个电影,那就有点不习惯了。
从这个剧本其实看得出,镜头是比较零碎的,绝非一般故事片和传统的小成本文艺片那么的吸引人,这片子容易让人如坠雾中,不知道为什么,不知道导演想干什么,想表达什么,我们关注的问题,片子始终都不予交待。马里昂巴德在哪里,有没有这个地方,导演仿佛并不关注,男主说的是真的么,仿佛也难有定论。这也是一部电影,可能这就是格里耶想要突出的电影自己的特色吧
《去年在马里安巴》读后感(二):谁擦黑板我爱谁
M(伤心,迷惘):您在哪儿……我失去的心上人……
A(犹豫不决):在这儿……我在这儿啊……我跟您在一起,在这个房间里。
M(声音轻柔):不,已经不是真的了。
A(恳切地):请帮我一把吧,我恳求您,帮我一把吧!把手伸给我……紧紧握我的手……紧紧拥抱我吧。
M(他向她伸出手,但手臂又垂了下来):您在哪儿?您在干什么啊?
A(几乎喊出来的):别让我走啊。
M(激动但爽直):您心里明白这已经太晚了。明天我将独自一人。我经过您的房门时,将看到房间是空的……
A(缩紧身子):不……我冷……不!别走呀!
M(爽直地):是您要走啊,您心里明白。
故事里只有这一段算是激烈的对话。在马上要结尾的地方。我一直没看专心,是因为这女人的情绪变化没有清楚。开始的时候她迷茫,中间迷茫,要结束了还是这个死样子。作者太局限于他心目里完美女人的气质了吧。一点成长都不给人家。
一直以为这个地点的名字叫马里昂巴,差不多十年以前,电影课,黄琳老师瞪着眼睛慢慢说出这个地点,重读“巴”这个字。他又继续说,谎言说了一千遍,就变成了真理。
关于他的课,记得很热门很难得选上,巨大的阶梯教室满满的人,而且大多是美女。课间,我跑去把黑板擦了。那时候我总是给各个老师擦各种黑板,如果是和天天一起听课,就我们俩商量着有一个人上去擦。搞得一头一手的白灰。
继续上课,黄琳指着我说,刚才擦黑板的同学,你就是这堂课的班长吧。我记得那时候脸很红很烫。
他又说,坐在班长旁边的那位同学,就是副班长吧。其实是因为那时候我旁边的这位同学很活跃,黄琳是想让他管理的吧。我只是擦了黑板。
他还讲过,毕业以后被分配去审查电影,工作了几天,他觉得这不是人干的事情(大意),就想,我还是回川大算了。
这么说的时候,好象回川大在他是很轻易的。
在家里看电视广告,看得很愤怒,因为喷虫子的广告,镜头打过来一喷,“把观众都当成虫子了”
还有,和马里昂巴差不多同一节课讲的,关于镜头照哪里,看电影的人就被放在了摄象机的位置对着哪里。照一个女人洗澡,观众好象贼在偷窥,照贼拿着刀子,观众就好象在洗澡的女人觉得害怕,又照回来女人惊恐的表情,观众又变成在行凶很紧张。
想到他又想到刘黎明。还有王瑞成。他们最早记得我的作业。
他们在大家之前,之前很久先多我说,你很好。
我才能一直坚持到遇到大家。
你最早会遇到谁呢。如果现在遇到,就不会觉得那么深刻了吧。好象上帝把一个人的信心、勇气、鼓励、希望、幸运星、第2颗幸运星,这样的很多东西分在世界上很多别的人手里。
不知道什么时候遇到谁,谁就那么慷慨地送还给你。
《去年在马里安巴》读后感(三):我们进入了花园,迷失了自己。
拿到出版社送来的一本样书,《去年的马里昂巴》,是我喜欢的,曾认真看过这部电影。于是仔细阅读。
“古典装饰的大房间,安静的客房里,厚厚的地毯把脚步声吸收了,走的人也听不出来,好象走在另一个世界……像是位于远方的陆地,不用虚无的装饰,也不用花草装饰,踩踏在落叶与砂石路上……但我还是在此处,走在厚厚的地毯上,在镜子、古画、假屏风、假圆柱、假出口中等待你,寻找你。”
巴洛克式建筑风格的豪华酒店。沉寂。毫无生气。住在里面的人随时会陷入到凝固的姿态中。戏剧上演。男人X与女人A相遇。他说一年前他们在这里相见,并相约一年后在此重逢、一起出走。眼神严肃而深情。女子摆出嘲讽而不屑一顾的姿态。于是X频频地出现在A的生活里,每次都带着坚定而不可抗拒的口吻向她讲述关于一年前的影像。她惊慌失措,不断拒绝进入他的想象,不断要求“再等一等”,不断阐述着要离开过去的生活是何等困难,直到她被地狱沉重的关门声惊醒,终于开始质疑自己的记忆,开始相信那些乌托邦式真实与梦幻的交织,开始被这个男人所吸引和带领。
这是罗伯-格里耶用文字与影像的虚拟框架构筑出创作迷宫空间的一部电影剧本作品,《去年的马里昂巴》。大段大段的静止场景,人物表情的黯淡冷漠,呓语似的对话,将真实与幻境制造的令人难以分辨。那些潜藏在人心底的欲望缓慢而焦虑的浮动,像宽广而悠长的河流。虽然已经很淡了,但却从静止冰冷的道具编织体的缝隙里庸扰的流淌出来,带着刺目的妖娆。这也是构成典型的罗伯-格里耶式乌托邦的一个要素。
但如同欺眼法的绘画栩栩如生的程度使人看上去并不是图画、而是实物一般,《去年在马里昂巴》里文字与影像铺展出的逼真也让人认为那是真实的世界。现实在这里被抽离,但却在支离破碎的十二音音乐中绽裂着现实与幻象的缝隙,泄漏着文字与影像构筑出的“现实”。X企图利用他的故事将A带进他的叙述当中。他要建构的空间,是一个有阳光、落叶与细碎石子小径的现实空间。可这些与在片中的法国式公园一样,带着玛格利特式的“裂口”谜一般的反复出现,每次都不同,以此来表现X的心理变化:从素描到超现实处理,从黑白倒转的底片到曝光过度。因此,罗伯-格里耶在影片中所想要展示的并非是一段真实的、对过往的追忆,而是建构在逼真虚幻上的真实场景。
X像诗人 ,用法师般的心召唤着那个只有一张床的白色卧房的心象。这个短暂的插入意象重复了十二次,均转瞬即逝。直到第十三次才稍显持久,而A也终于跟随着X看到了这个虚假的白色世界和他一直努力说服A相信的细节:壁炉、镜壁、雪的风景画。于是,他们离开酒店,走入花园,如同影片中多次出现钟声时的预示:“此刻,我属于你。”
“我们进入了花园,迷失了自己。”片尾,X说。犹豫的女子最终跟着她的诗人离开了。离开了那个巴洛克豪华酒店。离开了那些窃窃私语又冷漠的面孔。离开了过去的习惯和固定的身份。没有未来的方向。她像诗人口中曾喋喋不休重复的优美字眼,被统统遗失在过去里,遗失在陈腐的惯性里。她又是诗人竭尽全力都要掳获的读者,却始终带着现实的伤口,拒绝幻想。
“主角用自己的想象与自己的语言创造了一种现实。……在这个封闭的、令人窒息的空间中,人和物似乎都是某种魔力的受害者,有如在梦中被一种无法抵御的诱惑所驱使,而无法逃跑或是改变。……其实没有什幺去年,马里昂巴在地图上也不存在。这个过去是硬性杜撰的,离开说话的时刻便毫无现实意义。但是当过去占了上风,过去就便成了现在。”罗伯-格里耶在《去年在马里昂巴》的自序中这样说。
《去年在马里安巴》读后感(四):我跟罗布格里耶不熟
总共没读过几本书,阿兰罗布格里耶的书读得更少,但这不妨碍我知道他。我知道他的每一部作品在中国都有翻译,他的名气在中国比在法国要大,罗布格里耶这个名字已经是一个名牌,他和法国香水、法国大餐一样让人记忆深刻,在中国,都快成“法国三宝”了。 既然如此,为什么他的小说,我反而会读的那么少呢?我想,要么是我无知,要么,是我知道的太多了。
我确实知道的太多了!罗布格里耶的小说,我能和许多他的中国粉丝一样,随口说出一个名字,但也仅仅是名字。不好意思,《橡皮》:没看过,《嫉妒》:没看过,《窥视者》:没看过;著名的电影《去年在马里昂巴德》:没看过。《金姑娘》,购买过,《幽灵城市》,购买过,大约是1998年,大概是读过,后来忘记了。《反复》,我购买过,也读过,因为时间较近,还有点印象。据说其最后一部作品是85岁时写的《伤感小说》,因为里面有大量恋童癖的色情描写,遭致了广泛的批评,被认为是晚节不保的一个象征。可惜就连这个,我也没读过。这很可能是老罗所有作品中,我最想读的一本书,恰恰是因为这种八卦式的文学书讯刺激了我那卑劣的阅读欲。
是的,对于罗布格里耶,我是个典型的知道分子。既然如此,又凭什么要在这里谈论一位大师呢?大概就是因为我和他不熟吧。不熟就是不了解;不熟就是知道一点,但未必有感情。没有感情而又不了解,正好可以胡说八道。我对格里耶老先生是没有什么感情的,不像那些创造了中国先锋小说历史的作家们,他们很有一批人,把老罗当成了精神之父。说到这里,我就觉得自己很可悲,因为在我还不知道罗布格里耶的时候,就已经读了太多中国的先锋小说,对中国的先锋作家比对老罗有感情多了,但也仅仅是日久生情的那点情,再也没别的,更何况那时有些用情过度,早有些犯恶心。
我对老罗没感情,这倒很符合他一贯“物本主义”的创作理念,我觉得不妨用一种“物本主义”的姿态来表达一个知道分子对他的纪念。老罗的伟大恰恰就在于,他和这个世界一样,“既不是有意义的,也不是荒谬的,它存在着,如此而已。” 也只有这样看待,老罗才是“一个更实在的、更直观的”老罗。我们于是可以“不带任何感情色彩,客观地、冷静地、准确地”纪念他。于是,我们的纪念,也不再是纪念一个大师的死亡,而是一种纪念本身的死亡。
进而言之,对于众多罗布格里耶的知道分子,不必因为知道这个人而感到骄傲,感到悲伤,感到有从尘封的书架上拿一本他的书读的必要;对于不知道罗布格里耶的人,也不用因此而自卑。我们的知识生活里完全可以没有罗布格里耶,没问题的,甚至连法国“新小说”也可以没听说过。不知道罗布格里耶,不会耽误你爱好文学,你也十分有可能写出不错的小说。他是上一代写作者的精神之父,未必是下一代的。我们可以不谈论这个人,在他活了86岁才死去的时候,我们可以不知道他曾经存在于这个世界上。
据说罗布格里耶非常喜欢中国,曾经三次来过这个“世界尽头”的国度。2005年,当他最后一次来到中国时,83岁的他,特地去了他所心仪的江南,他在致中国读者的信中曾经写到:“我喜欢中国南方。我愿意在梦中去那里漫游,坐在一头懒洋洋的黑色水牛上,它最后完全睡着了,而它那梦游者般的沉重、缓慢、颠簸着的移动却没有中断。不久,它也进入了梦中。它想象水波荡漾着它的睡意……”他没有坐在水牛上,而是坐在一条孤舟里,披着围巾,托着他生满整齐的胡须的下巴,做出一种沉思与回忆的姿态,而这个姿态,说真的,在我看来,真的一点也不纯物质,也不那么纯客观。这个感情色彩的拒斥者,完完全全被自己的感情所征服了,而终于在脸上表现出它应有的色彩。
这就是他想像的中国,他那充满感情色彩的沉湎印证了这个想像。他的想像与中国作家对他的阅读和想像是一样的,都获得了自己想要并且愿意沉湎其中的那部分。
《去年在马里安巴》读后感(五):非典型私奔:《去年在马里安巴》
“我再一次——向前走,沿着这些客厅、长廊,在这栋——上个世纪的建筑里,在这座宽大的、豪华的、奇崛的——凄凉的旅馆里,这里走廊连着走廊,漫无尽头——寂静无声,阒无一人,装饰物臃肿:壁板雕、毛粉饰、墙线脚、大理石、黑色镜、暗色画、圆形柱、重帷幔,背景昏暗阴森——框架雕刻的门相连着一间间的房间,一道道的长廊——横跨的走廊通向另外一些空无一人的客厅,这些客厅也布满了上个世纪繁多的装饰,又通向万籁俱寂的房间,这里行走的人他的脚步声被厚实的地毯吸收了,他自己的脚步声一点儿也听不到——好像听觉已消失到离地面、离地毯很远很远的地方去了,已经远离这沉重而空虚的背景,已经远离布满天花板的装饰,复杂的条状和环状的框缘犹如枯死的枝叶,好像地面依然是沙子或砾石似的……”
2003年春夏换季的时候,我在自己开的小书吧里,一遍一遍地看《去年在马里安巴》,手里捧着中译本,跟电视里的黑白片对照着看,一点也不怕烦着客人。因为客人压根儿没有。都被非典型肺炎吓跑了。
“……沿着长廊,穿过空无人影的屋子,我曾来与您会面。我跨过一道道敞开的门来与您会面,好像我经过道道人墙似的,他们的脸呆板、僵化、专注、冷漠,而我始终等待着您,现在依然等待着您,一直瞧着这座花园的入口……”
有一天,是个周末,朋友一家三口过来玩,陪我看了一会,说:不懂。我说:我玩《生化危机》,也是这样一间大屋子,也是一个人跑来跑去,也不懂,也可以一遍一遍玩。他们看着我,不说话。我就说:我的生活,也是这样跑来跑去,也不懂,也可以一天一天过。他们还是看着我,不说话。
我只好说:你们看这个男人,他是X。你们看这个女人,她是A。你们再看这个男人,他是M,是A的男人。每当M不在跟前的时候,X就对A说,一遍一遍地说,你不记得了吗,去年在马里安巴,我们爱得多好,那时你说,如果我真的爱你,今年就来带你走。现在,跟我走吧。
他们看着我,笑起来。
我说:其实我不喜欢这个电影,尤其讨厌这个X。你们看我桌上有副扑克牌。
这是两个人玩的游戏,牌数的分布是这样的:七张、五张、三张、一张。玩者轮流捡牌,捡的数量不限,但每次只许在同一排里捡。谁捡最后一张,谁就输。
我说:这书翻译的有问题。X和M第一次玩的时候,书上是这样写的:第一个回合,X从七张一排中捡一张,M从五张一排中捡一张;第二个回合,X捡起七张一排的全部剩余部分,M从五张一排中捡两张;第三个回合,X从五张一排捡一张,M从三张一排捡一张;第四个回合,只剩一张了,X输了。
其实你拿牌一试就知道书上错了。片子里面很清楚,实际上是有五个回合的,书里掉了一个,第三个回合应该是X从五张一排捡一张,M从三张一排捡两张。
我说:这个游戏玩了好几次,不管谁先谁后,怎么玩,赢的总是M,最后一次的第一步甚至还是X替他走的。我说:太有意思了。有窍门。我一遍一遍地看,要搞清楚的就是这个。
我这么理直气壮地一说,朋友们不再深究,似乎也承认了我在这里一遍一遍做的,到底是件有意思的事。事实上,X一遍一遍地对A说,你不记得了吗,去年在马里安巴,我们爱得多好。A说:不。不可能。您一定搞错了。但是,X还是一遍一遍对她说这个,每说一遍,都有一些新的细节加进来。雕塑,房间,镜子,披肩,手镯,轻纱的花边。
“这个旅馆的大花园是一种法国式的花园,没有树,没有花,没有任何种植物……砾石、石头、大理石、直线条使空间显得刻板,使外表没有神秘感,乍一看,好像不可能在这里迷路……沿着笔直的小径,在姿态僵死的塑像和花岗平板中间……乍一看,好像不会迷路的……而现在您正在迷路,在这静静的黑夜里,单独一人跟着我永远迷失方向。”
这就是结局么?当我终于关闭那家书吧的时候,并不相信。但是今天,再开一家的日子似乎越来越远了,就连关掉的那一家,它的样子我也已经记不起,只剩当年电视机后墙上的两幅书画金汤横轴,现在在我卧室里,每天早上一睁眼,我就可以看见。
善趣
赏鉴家。精舍。净几。明窗。风日清美。水山间。幽亭名香修竹。天下无事。主人不矜庄。睡起。与奇石彝鼎相傍。病余。茶笋桔菊时。瓶花漫展缓收。拂晒。雪。女校书收贮米面果饼作清供。风月韵人在坐。
恶魔
黄梅天。指甲痕。胡乱题。屋漏水。收藏印多。油污手。恶装缮。研池污。市井谈。裁剪折蹙。灯下。酒后。鼠啮。临摹污损。喷嚏。硬索巧赚轻借。夺视。傍客催逼。蠹鱼。酒迹。童仆林立。代枕。问价。
最后“问价”两个字,落笔收笔都有点异常。一定是写时心中犹豫:把问价当恶魔,那还开啥书吧呢?终于还是写了。这横轴上的字,我是从古典艳情小说《贪欢报》里看来的,里面有个男人,就是满壁挂这些,说不出的清高雅致,诓骗寡妇身心钱财。我现在知道我为什么讨厌X了。也许说是嫉妒更贴切。这世上有些人,你也不知道他们到底怎么搞的,可以把私奔做成事业,而我们,即使带着一起私奔的仅仅只是一些书,也不过象一次短暂的休假,一场冒险的电子游戏,一个香甜的梦。假期完了,游戏结束,梦醒了,我们只能乖乖地重新回到现实世界里面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