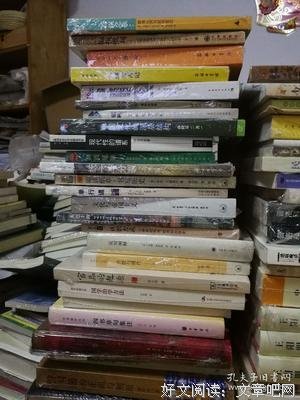
《华盛顿的起床号(1860-1865)》是一本由[美]玛格丽特·利奇著作,东方出版中心出版的平装图书,本书定价:58.00元,页数:521,特精心从网络上整理的一些读者的读后感,希望对大家能有帮助。
《华盛顿的起床号(1860-1865)》精选点评:
●参考已到
●1942年普利策奖。一幅迷人的美国南北战争时期的社会风情画。你大可不必对当前台湾政坛中议员们大打出手大惊小怪,他们的所作所为和1860年左右的美国政客相比不过是小巫见大巫。民主和人一样,需要时间才能长大变成熟。
●散
●晦涩,吃力。
●堪比《光荣与梦想》的历史书,视角很赞,详述和略述之间张弛有度,画面感超强,作者一定会是个不错的导演。重复一下之前想到的一个观点:感觉一个国家历史研究水平的下限是由新闻界水平的上限所决定的……
●一部以首都华盛顿为视角讲述美国内战的经典著作
●太棒了,普利策奖真不让人失望。大片啊,大片!
●细节极其丰富,文笔也很生动。但这本书完全是由海量片段和细节堆积起来的。如果对南北战争本身的进程没概念,拿光靠这本书并不会有太多增益。
●全书以内战为背景其实是想再现社会的各式风貌,穿插了一些并不直接与战争紧关的小人物,像一些女特务,还有女护士的故事。单独一章写总统夫人确实看到了一些不一样的故事。可能因为看的不仔细,而且翻译的原因,会感觉叙事有一点琐碎和乱。主要刻画的林肯形象让我觉得不像之前印象中那个非常有思想和光辉的人,却更虚弱和无力,甚至让我觉得被暗杀对他是某种解脱。片面之见。
●一半是描述性的还有大量的形容词 加的 受不了啊
《华盛顿的起床号(1860-1865)》读后感(一):华盛顿关于南北战争的切片
这书已经买了很久很久了,久到我都忘了什么时候买的了……最近才终于看完了。
南北战争,很早之前就听说过了,如废奴,如林肯。但是却是在看了《葛底斯堡》才对南北战争真正感兴趣起来,之后就稍微搜了一下相关的书籍,然而感人的是……在市面上没有发现什么有趣的……orz
后来看到了这书,看到了简介,于是我觉得我大概看到了不错的书籍,就买了,然而我错了。当我收到之后,翻了开头,发现作者成功用那有画面感(然而琐碎)的叙事劝退了我,我多次拿起又放下,感觉自己实在看不进去,甚至产生了还是放弃这书的念头。
这书就这么在角落里默默地吃了不知道多久的土,终于又被我发掘了出来,我决定再尝试一次,这次我成功了,在熬过了开头(其实是克服了自己的那种阅读惯性和期望,我所期望的是一篇清晰明了的战争故事),我发现我沉浸在了作者给我描绘的那个历史片段之中了。就像短评中有人说的,作者是个很好的导演,她的叙事很有画面感,在阅读中,随着她的文字,你仿佛能看到一幅幅生动的影像在你面前展开,如同一部宏大的电影。
这部电影的主角是华盛顿,而非个人,全书是视角一直钉在华盛顿,这座年轻的城市。它叙述了所有来到华盛顿的政客,军人,护士,间谍,妓女,刺客,演员,诗人,以及男人和女人。给我们提供了一副完美的,关于南北战争时期的美国首都的切片,让我们了解了这个时代的,这个时间的美国首都的样子。同时又让我们从中看到了战争在这座城市中的投影。可能有点奇怪,但是我总觉得在书中,战争并不是主题,虽然这是关于战争的,而这场战争又和这座城市息息相关。这大概是因为作者的视角一直是放在华盛顿的缘故,所以所有的战役仿佛都是从遥远的远方传来的硝烟,虽然难闻,却不真切。
这是一本有趣而又古怪的书,让我十分难以发出对它确切评价。如果你不了解南北战争,那么你读完了这本书,大概还是会一头雾水,所以我无法说这是一部可以入门的经典。
然而若你读完了这书,在书中看到了这么多生动的有关南北战争的人和事,你又怎么可能放下他们,不去进一步了解呢?
:最后一章的最后的大阅兵一段真实太赞了,若是真的拍成影片该多好(话说,我看完后,突然想到了斯皮尔伯格的《林肯》,依稀记得说是根据这书改的,然后去查了,并不是……有点伤心)。
《华盛顿的起床号(1860-1865)》读后感(二):一个国家和一座城
仿佛亲眼看到了1860年代的华盛顿。
看到了载着亚伯拉罕•林肯的马车悄悄地驶入沼泽般的华盛顿,车轮在街道上碌碌作响,碾碎了薄雾蒙蒙的清晨。看到了里士满的独立宣告震动了这座根本不像一国之都的小城。街道上,酒店内,国会里,政府大楼中,分离主义和联邦主义者争吵不休,甚至拳脚相向。无数人离开,去往南方;很多人留了下来,忐忑不安。城市里飘扬的不仅仅是星条旗,《迪克西》的歌声依然在这个联邦首都的角落里回响。
联邦军队中的很多军人奔向了叛乱者。隔着波多马克河是叛乱的弗吉尼亚,围绕特区的是蓄奴州马里兰。毫无防御能力的首都,只有一群业余的民兵在防卫。被敌意环绕的华盛顿发出了几乎绝望的求救声。北方热情地回应了:纽约人来了,宾夕法尼亚人来了,新泽西人来了,马萨诸塞人来了。一群群民兵千辛万苦地穿越马里兰开到了华盛顿,一队队漂亮的制服在军乐声中开过宾夕法尼亚大街。他们高喊着“打到里士满”,斗志昂扬地穿过波多马克河,奔赴前线。
但里士满对这些稚嫩的年轻人还太遥远,没有足够的鲜血和泪水注定无法到达,出征者中的大部分将注定见不到这颗南方的明珠。在联邦的光辉旗帜下,华盛顿被纷争,阴谋,腐败,争权夺利笼罩着。垂垂老矣的将军走了,志得意满的将军来了;色厉内荏的将军走了,志大才疏的将军来了。剧院繁荣,妓业兴旺,白宫的招待会依然宾客如云;威拉德酒店还是人满为患。而从华盛顿到里士满的征途上,躺满了尸体,奔牛溪,杉安道谷地,不会再开口唱军歌的年轻人漫山遍野。华盛顿无比渴望一场胜利,可前线回来的除了战败噩耗,便是川流不息的伤兵。黑暗的日子里,最坚定的联邦主义分子也唉声叹气。可是第二天,更多的新年轻人从北方开来,齐声高唱:“我们来了,亚伯拉罕老爹,你又有了30万人。”
南方的同情者遍布联邦的首都。老国会大厦的监狱里关满了政治犯,间谍和南军的俘虏。美丽的贝尔小姐是监狱里南方军官的女神。她在北军看守的眼皮子底下尽情歌唱讴歌南方。她最喜欢的歌曲是《马里兰,我的马里兰》。每当唱到“欢呼吧!她一脚踢开了北方的渣滓”时,其他男性囚犯就会提供一阵深沉男声合唱作为伴奏,仿佛是一出美国版的《红岩》。国家分裂,同室操戈,道德情操再高尚,趣味再优雅,都只能作为血与火的残酷苍穹下那微不足道的零星点缀。
历史,极少在光明、一帆风顺的大道上勇往直前;而往往是在黑暗、血腥的泥淖中挣扎前行。当所有的苦难告一段落,华盛顿举行胜利大阅兵的时候,带领这个国家走过这一切的总统已经长眠,国务卿也躺在床上奄奄一息。历史大戏在此时进入短暂的幕间休息。而谢幕的演员们,不仅仅是在场的人,也不仅仅是活着的人。所有的人:长眠的,活着的,荣耀的,耻辱的,成功的,失败的人,一起在欢呼声中穿过宾夕法尼亚大道。华盛顿是一个被权力诅咒的城市,注定充满了阴谋诡计和明争暗斗。但是,当游行的人们抬头望向刚竣工的国会大厦顶上,看到长剑入鞘的武装自由女神像时,也许他们会预感到,这个国家已经在血与火中走过青春期,也许历史的下一幕剧情会更光明一些,也许其中会有一个伟大帝国的灿烂黎明。
《华盛顿的起床号(1860-1865)》读后感(三):武装自由女神斜倚在她那把入鞘的宝剑上
小时候读过一部小说《乱世佳人》,其中的“乱世”指的就是1861~1865年的美国南北战争。作者玛格丽特米切尔属于南方邦联的同情者。同样描写美国内战史的,还有这部1942年普利策奖获奖作品——《华盛顿的起床号》,作者是另一位玛格丽特,她为我们提供了一种全新的视角。
这部作品节奏时而紧迫时而平静,很好地调动着读者的阅读情绪。一些章节是纵向时间轴,战争的开始与结束都在线索中,另一些章节是横向时间轴,照亮了华盛顿在战火弥漫中的大英雄与小人物,也照亮了他们的鲜血与光荣、耻辱与梦想。
战争的荒诞感,命运的跌宕起伏,黑帮电影式的危险惊奇……历史本身已有了底本,玛格丽特利奇的笔触冷静中潜藏激情。场景物换星移,英雄小丑走马灯般上下场,真正的主角,还是华盛顿这座城市,它被注入了特有的生命气息。所谓不破不立,四年的战争,残酷摧残了华盛顿,也为它带来空前的蜕变与觉醒。
所谓“起床号”的意义,正在于此。
塑造历史的众生相绝非易事。玛格丽特也无法像小说家那样靠想象力设局让主人公们经受考验。她或用细节、或用故事,淡淡几笔,就点亮了一个人物的内在精神。不是我们熟悉的角度与刻板的印象,那些人物像真实地还魂人间,在华盛顿这个舞台上继续元气充沛地走了一遍。
她写麦克莱伦的自命不凡,拥有拿破仑式的出场:“对于一群强烈需要英雄的人来说,他刚好就是一个英雄。”高调的呼声以后,波托马克军团却长期无所作为,华盛顿居民嘲笑每天早晨用电报发往全国的公告:波托马克河畔太平无事。玛格丽特又讥诮总结,“打从这位年轻的拿破仑走出西部以来,将近八个月过去了,他的头上只有几次小小的胜利的桂冠。他还没有打过一仗。”
她写胡克的色厉内荏,一句话就够了。“他是我所见过的扑克牌玩得最好的人,但这话只适合初期阶段,每当到了他原本能得1000分的时候,他就会丢牌。”
林肯也不再是历史教科书般的形象,而是为了联邦事业鞠躬尽瘁的奋斗者。巨大荣耀背后的挣扎,努力与无力,那么让人感同身受。关于他的场景无比生动,比如前往战争部的路上,急于打探战斗最新进展的林肯像“芦苇荡中的一只鹤一样,昂首阔步于巨大的大理石建筑之间,穿着一身裁剪怪异的灰色套装,一顶毡帽扣在后脑勺上,用一方红手帕擦着脸上的汗。”
作者不写家庭生活中的林肯,却用专门一章写林肯夫人;作者不写福特剧院的林肯遇刺,却写同一夜国务卿西华德的暗杀事件。像所有的大团圆故事,《华盛顿的起床号》的结局也是一场胜利大游行。前线的将军们凯旋归来,政府内阁们在看台俯瞰。在林肯缺席的场合里,他的阴影也有着绝对的存在感。
于是,这时候的华盛顿,就像一座纪念馆,纪念这位伟人存在过。而最终可以欢庆胜利的一刻,他却永远缺席了。内战为华盛顿留下的伤口,没有什么比它更真实刺骨。
在纵向时间轴里,更能直观地感受到四年内战为华盛顿这座城市带来的蜕变。
1861年,华盛顿被称作“宏大辽阔之城”,只是讽刺之辞。在一片沼泽地上建立起来的城市,敞开的下水道把腐烂的垃圾带向波托马克河。尖刻的记者写道,华盛顿是“一个患脑积水的村庄”,是一个“巨大的、急速生长着的、半生不熟的城市胚胎,就像一只躺在7月里的小河滩上的短吻鳄,懒洋洋地晒着12月的太阳”。
战争改变了这一切。政治家们点燃了内战的熊熊火焰,南方叛乱者炮轰萨姆特要塞,那面在炮轰声中飘然坠地的国旗,激发了华盛顿人民的爱国热情。意识到战争的残酷与荒诞之前,市民们聚集在华盛顿的大街上,聚集在酒吧和酒店的办公室里,聆听惊险刺激的战斗故事,充满紧张、激情与无理性,带着隔岸观火的危机感。
然而这样的表情,很快再也不会出现。
日复一日,迎接战败而归的士兵渐渐地成了华盛顿人司空见惯的事情。伤兵源源不断地运到码头,塞得满满的救护车成了街道上壮观游行队伍中单调乏味的一部分。“死亡成了寻常事,每一个仆倒在地的尸体似乎就是联邦本身的形象。从高级军官的镶银红木棺材,到普通士兵的廉价松木板棺材,经营死人的生意就像经营其他任何兴隆的买卖一样。”
华盛顿一次次目送着寄予厚望的英雄们登上舞台走向战场,又一次次迎来失望与幻灭。麦克道尔,麦克莱伦、伯恩赛德、米德、格兰特……这些将军们高调登场,即使用沾满北方联邦军鲜血的双手争取来的胜利也并不彻底。残酷的僵持的战争不得不继续,华盛顿人渐渐不再相信前线传来的虚假捷报。葛底斯堡战役的伤亡超过23000人。渐渐地,这个民族不再抱有天真的幻想,也丧失了盲目乐观的能力;但它学会了坚持,学会了抱定冷酷无情、毫不动摇的决心。
1865年,长达四年的战争终于结束。华盛顿国会大厦的穹顶也已完工。武装自由女神斜倚在她那把已经入鞘的宝剑上。联邦胜利后,大规模集权,于是,一个专门用于政府事务的乡村小镇“华盛顿”转变成为联邦的中枢“华盛顿”。
《乱世佳人》中,那个拥有一双生机勃勃绿眼睛的斯佳丽在南方邦联战败后回想曾经的岁月,塔拉庄园咧嘴而笑的奴隶们、种植园贵族们优雅安逸的生活,都随着战争一去不返,Gone with the wind,而这股时间之风,同样也浩劫在北方,浩劫在华盛顿。胜利游行散去,“活着的和死去的,时间之风把他们全都从华盛顿吹走了。宾夕法尼亚大道上,只有疲惫不堪的人,穿过尘土、垃圾和被踩烂的花环,游游荡荡地回家去。”从那时起,或者更早,华盛顿再也回不到曾经优雅慢跑的步调,起床号吹响了,这座城市在浩劫中觉醒过来。
《华盛顿的起床号(1860-1865)》读后感(四):《华盛顿的起床号》导言——秦传安译
大卫·布林克利在《华盛顿走向战争》(Washington Goes to War)一书中描述了第二次世界大战如何把美国首都从一座专注于新政、每年夏天人去城空、有点偏僻的城市,转变成了一场史无前例的战争动员的神经中枢,以及战后非共产主义世界的司令部。在这个过程中,用约翰·F.肯尼迪的话说,华盛顿成了一座既有北方的魅力又有南方的效率的城市。另有几场战争也对华盛顿产生了重大影响;比方说,在1812年的战争期间,英国人焚烧了尚处于襁褓期的首都。但是,没有任何事件,哪怕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对首都的影响比内战更为深远。这就是《华盛顿的起床号》的中心主题。1861~1865年间的这场冲突,把一个昏昏欲睡的南方乡村从一个权力分散的各州联邦的政府所在地,转变成了一个重新统一的国家的权力之都,这个国家已经通过血与火的洗礼,清除了奴隶制和州主权。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华盛顿的起床号》碰巧出版于美国参加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前夕,它记述了一场更早的战争,围困中的白宫和国会山的居民为之全力以赴。作为1942年普利策奖的获奖作品,玛格丽特·利奇的这本书已经在成果丰硕的内战研究领域成为经典,而且当之无愧。像所有经典作品一样,它也是一部可以在几个不同层面上阅读和欣赏的作品。首先,它是一个写得很优美的故事——故事情节充满了危险和惊奇,峰回路转,柳暗花明,充满了悲剧和喜剧,以及亚伯拉罕·林肯被刺之后,联邦胜利所带来的悲喜交加的高潮。它是一个这样的故事:在林肯身上我们可以看到一个英雄的和悲剧的形象,在约翰·威尔克斯·布斯身上可以看到一个名副其实的恶棍,在乔治·B.麦克莱伦身上可以看到一个自封的救世主,有迷人的叛军间谍罗斯·奥尼尔·格林豪,有惹人怜悯的玛丽·林肯,还有在这里扮演小角色的美国文化巨擘:在军队医院看护受伤士兵的诗人沃尔特·惠特曼和小说家路易莎·梅·奥尔科特;专利局职员克拉拉·巴顿创立了一个由女人组成的医疗队,并突出重围,去华盛顿附近的战场上救助伤兵;安德鲁·卡内基全力以赴,组织进入首都的交通和电报服务。
书名中的“起床号”有多重意义,暗示了本书的某些层面。起床号首先是一次唤醒,把人们从和平中唤醒,走向战争。它不仅唤醒了战争部那些布满灰尘、昏昏欲睡的办公室,使之变得活跃起来,成为一架庞大军事机器的官僚总部,而且唤醒了数量庞大的士兵,蜂拥着进入华盛顿城,涌入周围的山岗与河谷,这些地方成了多次“进军里士满”行动的练兵场和集结地。华盛顿从昏睡中醒来,面对战争的现实,还表现为惊惶和恐慌的形式,这些是敌军对首都的威胁以及想当然的威胁所引发的。这种军事上的活跃,以它全部的壮丽辉煌和莫名其妙的混乱,一一呈现在本书的字里行间。
“起床号”的另一重意义集中于一个崭新首都的出现,它从一个纯粹的符号脱颖而出,成为名副其实的主权实体。美国作为一个现代国家的觉醒,始于内战期间。1861年之前,很多美国人都把他们的联邦看作是各州自愿结成的一个联盟,任何时候都可以主张它们各自的主权,只要它们想这样做。但是,1861~1865年间的事件彻底颠覆了这一观念,使得华盛顿无论在事实上还是在名义上都成为一个主权国家的首都。战前,“合众国”这几个字通常被理解为一个复数名词:合众国are(是的复数形式)一个共和国。1865年以后,“合众国”成了一个单数名词。北方走向战争是为了保全联邦,最后却创造了一个国家。在林肯第一任期的就职演说中,他使用“联邦”这个词共20次,却从未说过“国家”这个词。在1861年7月4日给国会的第一篇咨文中,他22次提到“联邦”,3次提到“国家”。但是,两年多之后,在葛底斯堡,当他援引自由的新生来缔造一种新的美国民族主义的时候,他根本没有提到联邦,却5次说到了国家。在第二任期的就职演说中,林肯回顾4年的战争,把一方描述为在1861年寻求“联邦”的解散,而把另一方描述为为了维护“国家”而接受战争的挑战。在老的联邦共和国,除了通过邮局之外,华盛顿政府很少触及普通公民,而在这场战争期间,它已经让位于一个这样的全国性政府:它直接向人民征税(创立了一个国税局来征收税赋),强制征兵入伍,扩大了联邦法院的管辖权,创造了全国性的流通货币:绿背纸钞,并着手创立一个全国性的银行体系。
在这本书中,玛格丽特·利奇巧妙地把国会大厦的扩建和翻新打造成了一个重要符号,象征着美国民族主义的觉醒。1861年,国会大厦的新穹顶尚未完工,它敞开的屋顶向天空洞开。而在1865年,当联邦接近胜利的时候,穹顶也接近完成。到战争结束时,穹顶已经安装到位,高踞其上的,是胜利的武装女神像,静静地伫立在那里,她的剑已经入鞘。
在另一个意义上,“起床号”标志着华盛顿从南方人统治到北方人统治的觉醒,从地方主义到国家主义的觉醒,从奴役到自由的觉醒。1861年的华盛顿是一个南方社群。哥伦比亚特区被蓄奴州所包围,首都本身也存在奴隶制。尽管这座城市繁荣的奴隶市场由于立法(它是1850年妥协案的组成部分)而被迫迁往波托马克河对岸的亚历山大,可是,当林肯在1861年3月4日就职的时候,买卖人口的生意依然在华盛顿进行。不过,这次就职是改变的先兆。在完全由北方共和党人组成的这届政府中,大量的北方官员涌入华盛顿。在共和党人乘坐火车从北方进入首都的同时,南方人也纷纷坐火车离开,一路向南,加入本州的分离主义运动。华盛顿成了一座既有北方的魅力、至少在一段时间里又有北方的效率的城市。新的共和党多数派最早的行动之一,便是在特区废除奴隶制。在这一行动中,就像在其他很多方面一样,华盛顿就是一个微型国家。在首都废除奴隶制3年半之后,紧接着便是第十三修正案的出台,在整个美国废除奴隶制。
北方人的大量涌入和南方人的结伴离去,预示着所有政府分支控制权的长期转移。1861年,合众国已经在宪法之下存活了72年。在其中49年里(占这段时间的三分之二),担任总统的是南方的奴隶拥有者。而内战之后,要过一个世纪,才有一位南方人当选总统。在1861年之前,36位众议院议长当中有23位代表南方州,36位参议院临时议长当中有24位代表南方州。内战之后的半个世纪里,众议院议长和参议院临时议长没有一个来自南方。内战之前,最高法院先后在任的35位大法官当中,有20位是南方人,而在战后的半个世纪里,新任命的26位大法官当中只有5位是南方人。内战摧毁了老南方的诸多方面,注定要让南方文化沦为地方主义,并确立北方的制度和价值作为国家标准。就这方面而言,这场战争也代表了华盛顿的起床号。
最后,1861~1865年间的这场斗争见证了华盛顿的身体觉醒,它从一个杂乱无章的乡村小镇变成了一座现代城市。同时代人描写这一变迁,仿佛它就发生在自己的眼皮底下。马萨诸塞州一位士兵在弗雷德里克斯堡战役中受伤,当时正在首都康复,他在1863年3月写道:
在几年的时间里,华盛顿会有很多变化,一改它目前肮脏不堪的条件,街道将会增加人行道,对人口自由增长和不断扩大的商业利益的刺激,将会带了一场翻天覆地的变革,这是奴隶制做梦也想不到的。陆军和海军的供应品自战争开始以来便源源不断地通过华盛顿运出,其巨大的贸易量对这座城市外表的改善居功阙伟。在1861年,华盛顿被称作“宏大辽阔之城”。这是讽刺挖苦之辞,因为,除了少数几座公共建筑——国会大厦、白宫、财政部大楼、专利局大楼和邮政部大楼——以及几家像威拉德酒店这样的大酒店之外,朝波托马克河的方向一眼望去,是一片连绵不绝的沼泽。事实上,华盛顿就是在一片沼泽上建起来的,有几条敞开的下水道把腐烂的垃圾带向波托马克河,白宫可以看到这些下水道的尊容,也能闻到它们的气味。一些猪在基本上没有铺砌的街道上拱垃圾,依据季节的不同,这些街道要么是泥泞,要么是尘土,都深及小腿。一群群丑陋难看的窝棚和后院厕所沿着很多街道密密麻麻而建。伦敦《每日电讯报》那位尖刻的记者写道,华盛顿是“一个患脑积水的村庄”,是一个“巨大的、爬行的、半生不熟的城市胚胎,就像一只躺在7月里的小河泥滩上的短吻鳄,懒洋洋地晒着12月的太阳。”
内战期间,所有这一切都开始改变。尽管在某些方面,事情先是变得更糟,后来才变得更好。士兵的大规模涌入带来了一支风味不佳的特遣部队:来自四面八方的妓女、赌徒和酒贩子。直到1863年,被唤醒的市民和宪兵队才着手反击这些罪恶的侵入。战争动员所必须的行政机构的巨大扩张,带来了一次住房危机,最初,它使得一些偷工减料、摇摇欲坠的住宅区成倍增加。联邦军队进入蓄奴地区刺激了“禁运品”(逃亡黑奴)涌向华盛顿那些原本已经人满为患的黑人聚居区。1862年,首都附近的血腥战斗把数以千计的伤兵送到了毫无准备的军队医院,很多人因为缺乏周到的看护和足够的设施而死在了这些医院里。
但是,到战争的最后一两年,政府、军队和一些志愿组织(像美国卫生委员会和各种已解放黑奴的救助协会)使得事情有了一定的秩序。普通医院、逃亡黑奴营和附加住房像雨后的蘑菇一样从沼泽中涌现出来。不远处,锤子和锯的声音与远处战场上的隆隆炮声交相辉映。正当政府和军队在缔造一个新联邦的时候,木匠和砖瓦匠们也在缔造一座新城市。诚然,这两项工作到1865年都还没有完成,但它们都有了良好的开端。本书讲述的就是这个开端的故事——华盛顿的起床号。
玛格丽特·利奇明白晓畅的文字,让读者可以重回美国历史上这个决定性的时期,可以看到华盛顿的情景,听到华盛顿的声音——甚至嗅到华盛顿的气味。像个优秀的小说家一样,她把这出大戏中的人物给写活了,从总统到妓女。但这不是一部小说——尽管它为戈尔·维达尔和威廉·萨菲尔在他们各自的长篇小说《林肯》(Lincoln)和《自由》(Freedom)中对华盛顿场景的虚构叙述充当了一个重要的材料来源。《华盛顿的起床号》是一部优秀而可靠的历史——既精确又有趣——扎根于仔细而透彻的研究。只在一个重要的方面,后来的学术研究修改了本书中的观点。历史学家已经不再像他们在1940年代那样,以一种敌意的眼光来描写共和党激进派,他们还发现,在涉及到南方和奴隶制的相关问题上,激进派与林肯之间并不存在那样巨大的鸿沟。尽管共和党内部确实存在派系之争,正如所有政党中一样,但在一些重大问题上,合作比冲突更为显著。激进派的主要特征不是恶意,他们的主要动机也不是报仇;他们赞成冷酷无情的战争诉讼,赞成奴隶制的毁灭,为的是确保国家实现林肯在葛底斯堡所召唤的“自由的新生”。
尽管从本书的字里行间走过的人物都有着立体的丰富性,但主角是华盛顿本身。这座城市是一个有利的位置,这场战争中所有令人敬畏的事件都是从这个角度去观照。我们了解了一些令人闻风丧胆的战斗,近至奔牛溪,远至维克斯堡——但是,只有当关于它们的传闻和消息渗透进华盛顿的时候,我们才能得知。将军、士兵、州长、参议员、外交官、间谍和战俘,走马灯似地你来我往,但他们活动的焦点始终是华盛顿,至于他们本人,在场也好,不在也罢。本书不仅按照它在华盛顿塑造的样子以及它从华盛顿看到的样子来记述内战,而且还给这座城市注入了生命的气息,使之成为一个有生命的、有感知力的存在,而不仅仅是一个地方。历史是随时间而变化的故事,本书所讲述的,就是华盛顿在其历史上最具决定性的4年时间里不断变迁的故事。
詹姆斯·M.麦克弗森(James M. McPherson)/文
秦传安/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