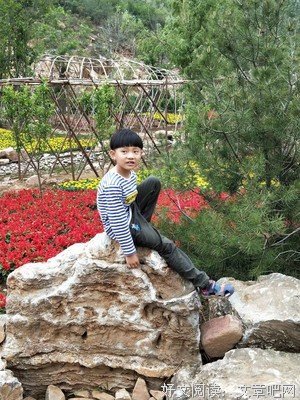
《域外长城》是一本由杨海英著作,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的平装图书,本书定价:66.00元,页数:356,特精心从网络上整理的一些读者的读后感,希望对大家能有帮助。
《域外长城》精选点评:
●壬辰倭乱的细节问题的一本专著,可以说戚家军研究的最新高度,对于关注这段历史的学人来说是必读的。关于战争期间南北兵,朝堂之上乃至后世党争端倪都能秉笔直书,但不知为何没有涉及南兵群体最终的命运"天启元年浑河血战"(民族河蟹不应建立在对历史的遗忘上,明清鼎革问题必须要有个官方明确的论断,希望以后的修订版补上。)
●东征往事,偏细节。阅读体验不如洪承畴那本,四星。
●很难淘到的书,内容详实。义乌矿工被称为最适合从军的群体,于书中战事记载可见一斑。
●运用了大部分的朝鲜史料,但日方史料乏善可陈
●此类题材实在是少之又少,史料详细,前篇可做白眉将军吴惟忠的传记,缺点是史料依赖汉语文言文过于严重,对于中方和朝方尚可,而没有运用日方史料,难免不够全面。这书市面上买不到,只能去二手书市或某宝碰碰运气吧
●此书虽是受地方所托撰写的《义乌丛书》系列著作之一,但是其质量甚至高于一般的学术著作。万历朝鲜战争横跨三国,任何人动笔之际都要博观约取,慎之又慎。杨先生对朝鲜史料的发掘和研究,确实在国内学界都属罕见。虽然囿于语言隔阂,对日本资料的引用不多,但是依旧是一本不可不读的著作。不过某些地方有溢美南兵之处,在所难免。 但愿有生之年,杨先生大声疾呼的“编纂一部全面的、综合性的、全球化视野下的《万历壬辰战争史》”之梦想,可以化作现实。
●本书分为前后两部分,上编以戚继光一手提拔的吴惟忠为主角,考订了他从军缘起、平壤之战、安康之战、蓟镇兵变、驻守忠州、蔚山之战几个历史片段,将吴惟忠治军有方、严己宽人并且深受朝鲜尊敬的影响描绘的栩栩如生。下编则是多为参与东征的义乌籍功臣的史实考订,包括胡大受战时战后安抚女真的行动、楼必迪与柳成龙的交往、毛国科在议和中的作用与滞留日本的经历等等。由于顶着“中国第一部壬辰战争专著”的帽子,本书的压力很大,但其实,以明代军事人物研究的名义去审视这本书更为合适。杨老师专长在于晚明清初军事人族研究,本书利用的诸如《唐将书帖》、各类族谱,都数首次,从这个角度上看,学术价值极大。本书缺陷就在于对日军情况的不熟悉,利用日本史料也比较少,这是中国学者的通病。若不受“义乌丛书”的限制,作者能写出更有体系的军事史作品
《域外长城》读后感(一):【壬辰倭乱】浙江兵和日军在朝鲜庆州、安康一带的数次交锋
转自:https://zhuanlan.zhihu.com/p/21452482?f3fb8ead20=21faa2fc336748e093412893061258e7
《域外长城》读后感(二):《历史意识与现实交响》(杨海英)发表于【光明日报·理论·史学·读史札记】
今年是抗日战争胜利70周年。对于这场战争,国人都有刻骨铭心的记忆和感受。如此惨绝人寰的战争,究竟有没有历史源头?又是如何演变、发展的?将来还会不会重演?相信这是每个国人,也应包括日本人以及世界上所有爱好和平的人,都在思考的问题。从这一角度来说,历史关怀与现实变奏无时无刻不在交响上演,它们的内在交集,凸显出追索这场战争的历史意识起源的重要性。
这场战争的源头当系于1592年万历壬辰这个时间点。在这一年所发生的日本侵略朝鲜的战争(朝鲜称为壬辰卫国战争,韩国称为壬辰倭乱,中国史称万历援朝战争或“东征”,日本则称文禄·庆长之役),被视为日本发动海外侵略的起点。在这之前,唐宋时代的中国还是日本的老师,日本社会中尚未产生学生打老师的念头。但到明朝万历时期,日本丰臣秀吉政权完成统一之后,野心开始膨胀。虽然当时日本的社会发展程度,要远远落后于明朝——这个当时世界经济中心之一、被誉为世界白银“终极秘窖”的大国,但丰臣秀吉的狂热,已经超越后世学者以先进、落后来区分文明发展程度的限定,执意“一超直入大明”,妄想用武力使拥有“四百余州”疆域的明朝臣服。为此,日本欲先征服朝鲜作“先驱”和跳板,悍然发动了壬辰战争。丰臣秀吉的观念,不易被熟悉“落后就要挨打”这一通行标准的人们所理解,而这也是甲午战争后颇为流行的观察角度。从这样的角度来看待万历壬辰战争,不仅完全凿枘不合,而且会越看越糊涂:丰臣秀吉时代落后明朝很多的日本,何以就能产生入侵大明的意图?
历史意识一旦产生就会具有生命力。目前有一种流行的说法:因为雕版印刷不发达等因素,日本文明自宋朝以后就走上了“与中国正好相反”的道路。既然日本社会“与中国式社会180度相反”,那又如何产生对尊王攘夷、逐鹿中原这些在中国延续了2000年的传统观念情有独钟的意识、思潮和人物呢?虽然在江户幕府时代,德川家康作出了与丰臣秀吉彻底“告别”的姿态,但发展到明治时期,日本社会思潮又一次折返:对1592—1597年的壬辰战争研究,开始被定位为国策论证的重要工具。1705年马场信意的《朝鲜太平记》31卷和佚名《朝鲜军记大全》38卷刊行,表明18世纪初,日本对壬辰战争的重视已超越中国和朝鲜,并在收集三方资料基础上产生巨著。此外,无论是福泽谕吉的“恶友”论,还是甲午谍战巨头荒尾精对“四百余州”中国的念念不忘,也与丰臣秀吉没有本质区别。到了1898年,丰臣秀吉去世300周年之际,明治政府更致力于把丰臣秀吉塑造成为民族英雄,而松本爱重的《丰阁征战秘录》,甚至起了甲午战争动员令的作用。一些人将壬辰战争作为日本宣扬国威并向东亚炫耀的重要历史背景,其后并吞朝鲜、侵略中国乃至发动太平洋战争,都被塑造成是在完成丰臣秀吉的遗业。
历史意识与现实变奏的关系,虽然或明或暗,仍可求而索之。丰臣秀吉时代的历史意识,虽然一度在江户时代泯灭无闻,但就像一颗种子,一旦有了适合的环境和刺激,就会萌芽——历经明治维新,这种意识,就乘甲午战争的刺激,引导日本吞并朝鲜、赶跑俄国、侵占中国东北。所以,甲午战争远非一些研究者所认为的是日本帝国主义的一个“起点”或“开端”,早在300年前的明朝万历时代,这种侵略意识就已经“萌芽破土”,这是历史意识与现实变奏间可以触摸的一些关节点。
从东亚关系的角度探讨日本500年来历史意识的发展道路方面,韩国学者已经走在了我们前面。而与之相反的是万历援朝东征战争以毋庸置疑的实力,遏制了日本的侵略势头。如此重大的历史事实和历史问题,却在我们的研究中几成空白。因此,郑重指出以下两个事实,或许并非没有意义的事情。
首先,400余年前,面对日本突然发动的战争,万历皇帝和他的大臣们,经过反复争论,鉴于唇亡齿寒的教训,最后下决心御敌于国门之外。这样的超前观念和卓越见识,却从未得到过肯定:自清修《明史》开始,便断言明亡于万历,这不仅已被史家指出可能是一种“误读”,更有可能是一种“误导”:出自塑造清朝统治正统的需要,有意无意将万历皇帝和他的大臣都置于负面评价之中:无论是阁臣张位还是督臣孙鑛,或是前后几位经略宋应昌、杨镐、邢玠等,虽都不乏各自的问题,但苦干实做这一点却非常鲜明:他们在重重矛盾中尽量权衡轻重利弊,选择符合时代要求的建议并努力付诸施行,只是所有这些努力都因清修《明史》时对不利于己的前尘往事厉行禁毁而被长期忽略。
其次,在东征明军中,最有战斗力的南兵,正是戚继光在蓟镇训练新军十余年的成果展现,其三大“创新”表现,完全可在世界军事史上占据一席之地。一是创新的精兵“混成旅”。他们不仅配备轻型车载火炮(佛郎机炮),也有重型的“大将军炮”,具备“三手”(即射手、杀手和炮手)技艺的南兵和北方骑兵,配合完备的阵法、战法,使这支处于冷热兵器时代之交、掌握冷兵器精髓同时也熟练先进热兵器的新军,面对擅长于近战的日军步兵“足轻”和他们穿透力极强的鸟铳,也从未失却过敢战的本色。明朝东征军进入朝鲜后,平壤首战出手,就打掉了日军的信心。即使在万历二十一年(1593年)那个漫长严寒的冬季里,经历持续数月、规模大小不一的安康战役,固使明军蒙受了不少的损失,但吴惟忠等所领导的留守南兵,以敢战精神与不惧牺牲,博得了朝鲜朝野的一致称赞,“剑阁精兵”之誉就出自朝鲜国王之口。而朝鲜相臣柳成龙对南兵形象的解释,也给历史留下一个铁证:“所谓南兵者,乃浙江地方之兵也,其兵勇锐无比,不骑马,皆步斗,善用火箭、大炮、刀枪之技,皆胜于倭。头戴白幍巾,身以赤白青黄为衣,而皆作半臂,略与本国罗将之衣相近,真皆敢死之兵。”尤其是他们的优良军纪,更是竖起了一面旗帜:南兵统领吴惟忠驻守蓟镇时,就是戚继光的左膀右臂;他与参将骆尚志、陈蚕、游击胡大受、叶邦荣、陈寅等人所率的南兵,无论是作战能力,还是严格的军纪,都受到朝鲜朝野的一致肯定。这支明朝用重饷所练的精兵部队,在异国大放光彩,却在中国史书上缺乏记载,令人遗憾。二是创新的“三手”朝鲜军队。明朝东征军中的南兵与军中教官,利用戚继光的《纪效新书》,通过“三同”训练法,前后共用十余年时间,在朝鲜复制了一支近代化的新式“三手军”,不仅为最后战胜日军奠定了坚实的军事基础,也使这支掌握“戚家军”战术精华的朝鲜军队,成为明朝“剑阁精兵”在海外的嫡传正版。朝鲜这支拥有精良火炮技术的新式陆军部队,后来还在明清易代中发挥了重要作用——被清朝掌握之后,成为对付明朝的利器。事实上,在戚继光死后的第五年,朝鲜战场就已成为戚继光在蓟镇所练新军的最好检验场,“戚家军”的老军骨,吴惟忠、胡大受、骆尚志等人,都是朝鲜军队训练的直接领导者、指挥者和设计者。只是这些“剑阁精兵”的将领命运坎坷,不是在后来遭遇诬陷,就是在历史上被忽略。三是创新的“海上长城”。虽然明朝万历援朝东征战争,消耗了明朝的国库,一定程度上导致天翻地覆的明清易代,这正是造成对东征评价出现歧义的主因;但另一事实也同样显而易见:这场行动及其相关举措,为中国铸就了一道“海上长城”,也对朝鲜的政治、军事、经济、社会、文化各方面产生了全面、深刻的影响。
拥有三大创新的明朝军队和明末历史,却不广为人知,更不用说产生现实影响了。从这个角度看,日本早自明治时代就充分、广泛利用这场战争做文章的意识和观念,确实与中国呈“180度相反”的景象。那么,如何找准历史意识与现实变奏的关节点与焦点?相关历史意识的产生、发展与付诸实践,早已超出单纯历史问题的范畴,而成为与现实问题息息相关的政治、社会、军事、外交的各种具体问题的综合体,但解决问题的基础——历史事实本身的求索与探讨,恐怕是一个更重要也更需学者首先安静下来、花工夫、下力气去做的事。而由有关部门出面、组织各方面人力、物力,编纂一部全面的、综合性的、全球化视野下的《万历壬辰战争史》,应该被提到议事日程上来了。
《域外长城》读后感(三):杨海英:历史意识与现实交响
今年是抗日战争胜利70周年。对于这场战争,国人都有刻骨铭心的记忆和感受。如此惨绝人寰的战争,究竟有没有历史源头?又是如何演变、发展的?将来还会不会重演?相信这是每个国人,也应包括日本人以及世界上所有爱好和平的人,都在思考的问题。从这一角度来说,历史关怀与现实变奏无时无刻不在交响上演,它们的内在交集,凸显出追索这场战争的历史意识起源的重要性。
这场战争的源头当系于1592年万历壬辰这个时间点。在这一年所发生的日本侵略朝鲜的战争(朝鲜称为壬辰卫国战争,韩国称为壬辰倭乱,中国史称万历援朝战争或“东征”,日本则称文禄·庆长之役),被视为日本发动海外侵略的起点。在这之前,唐宋时代的中国还是日本的老师,日本社会中尚未产生学生打老师的念头。但到明朝万历时期,日本丰臣秀吉政权完成统一之后,野心开始膨胀。虽然当时日本的社会发展程度,要远远落后于明朝——这个当时世界经济中心之一、被誉为世界白银“终极秘窖”的大国,但丰臣秀吉的狂热,已经超越后世学者以先进、落后来区分文明发展程度的限定,执意“一超直入大明”,妄想用武力使拥有“四百余州”疆域的明朝臣服。为此,日本欲先征服朝鲜作“先驱”和跳板,悍然发动了壬辰战争。丰臣秀吉的观念,不易被熟悉“落后就要挨打”这一通行标准的人们所理解,而这也是甲午战争后颇为流行的观察角度。从这样的角度来看待万历壬辰战争,不仅完全凿枘不合,而且会越看越糊涂:丰臣秀吉时代落后明朝很多的日本,何以就能产生入侵大明的意图?
历史意识一旦产生就会具有生命力。目前有一种流行的说法:因为雕版印刷不发达等因素,日本文明自宋朝以后就走上了“与中国正好相反”的道路。既然日本社会“与中国式社会180度相反”,那又如何产生对尊王攘夷、逐鹿中原这些在中国延续了2000年的传统观念情有独钟的意识、思潮和人物呢?虽然在江户幕府时代,德川家康作出了与丰臣秀吉彻底“告别”的姿态,但发展到明治时期,日本社会思潮又一次折返:对1592—1597年的壬辰战争研究,开始被定位为国策论证的重要工具。1705年马场信意的《朝鲜太平记》31卷和佚名《朝鲜军记大全》38卷刊行,表明18世纪初,日本对壬辰战争的重视已超越中国和朝鲜,并在收集三方资料基础上产生巨著。此外,无论是福泽谕吉的“恶友”论,还是甲午谍战巨头荒尾精对“四百余州”中国的念念不忘,也与丰臣秀吉没有本质区别。到了1898年,丰臣秀吉去世300周年之际,明治政府更致力于把丰臣秀吉塑造成为民族英雄,而松本爱重的《丰阁征战秘录》,甚至起了甲午战争动员令的作用。一些人将壬辰战争作为日本宣扬国威并向东亚炫耀的重要历史背景,其后并吞朝鲜、侵略中国乃至发动太平洋战争,都被塑造成是在完成丰臣秀吉的遗业。
历史意识与现实变奏的关系,虽然或明或暗,仍可求而索之。丰臣秀吉时代的历史意识,虽然一度在江户时代泯灭无闻,但就像一颗种子,一旦有了适合的环境和刺激,就会萌芽——历经明治维新,这种意识,就乘甲午战争的刺激,引导日本吞并朝鲜、赶跑俄国、侵占中国东北。所以,甲午战争远非一些研究者所认为的是日本帝国主义的一个“起点”或“开端”,早在300年前的明朝万历时代,这种侵略意识就已经“萌芽破土”,这是历史意识与现实变奏间可以触摸的一些关节点。
从东亚关系的角度探讨日本500年来历史意识的发展道路方面,韩国学者已经走在了我们前面。而与之相反的是万历援朝东征战争以毋庸置疑的实力,遏制了日本的侵略势头。如此重大的历史事实和历史问题,却在我们的研究中几成空白。因此,郑重指出以下两个事实,或许并非没有意义的事情。
首先,400余年前,面对日本突然发动的战争,万历皇帝和他的大臣们,经过反复争论,鉴于唇亡齿寒的教训,最后下决心御敌于国门之外。这样的超前观念和卓越见识,却从未得到过肯定:自清修《明史》开始,便断言明亡于万历,这不仅已被史家指出可能是一种“误读”,更有可能是一种“误导”:出自塑造清朝统治正统的需要,有意无意将万历皇帝和他的大臣都置于负面评价之中:无论是阁臣张位还是督臣孙鑛,或是前后几位经略宋应昌、杨镐、邢玠等,虽都不乏各自的问题,但苦干实做这一点却非常鲜明:他们在重重矛盾中尽量权衡轻重利弊,选择符合时代要求的建议并努力付诸施行,只是所有这些努力都因清修《明史》时对不利于己的前尘往事厉行禁毁而被长期忽略。
其次,在东征明军中,最有战斗力的南兵,正是戚继光在蓟镇训练新军十余年的成果展现,其三大“创新”表现,完全可在世界军事史上占据一席之地。一是创新的精兵“混成旅”。他们不仅配备轻型车载火炮(佛郎机炮),也有重型的“大将军炮”,具备“三手”(即射手、杀手和炮手)技艺的南兵和北方骑兵,配合完备的阵法、战法,使这支处于冷热兵器时代之交、掌握冷兵器精髓同时也熟练先进热兵器的新军,面对擅长于近战的日军步兵“足轻”和他们穿透力极强的鸟铳,也从未失却过敢战的本色。明朝东征军进入朝鲜后,平壤首战出手,就打掉了日军的信心。即使在万历二十一年(1593年)那个漫长严寒的冬季里,经历持续数月、规模大小不一的安康战役,固使明军蒙受了不少的损失,但吴惟忠等所领导的留守南兵,以敢战精神与不惧牺牲,博得了朝鲜朝野的一致称赞,“剑阁精兵”之誉就出自朝鲜国王之口。而朝鲜相臣柳成龙对南兵形象的解释,也给历史留下一个铁证:“所谓南兵者,乃浙江地方之兵也,其兵勇锐无比,不骑马,皆步斗,善用火箭、大炮、刀枪之技,皆胜于倭。头戴白幍巾,身以赤白青黄为衣,而皆作半臂,略与本国罗将之衣相近,真皆敢死之兵。”尤其是他们的优良军纪,更是竖起了一面旗帜:南兵统领吴惟忠驻守蓟镇时,就是戚继光的左膀右臂;他与参将骆尚志、陈蚕、游击胡大受、叶邦荣、陈寅等人所率的南兵,无论是作战能力,还是严格的军纪,都受到朝鲜朝野的一致肯定。这支明朝用重饷所练的精兵部队,在异国大放光彩,却在中国史书上缺乏记载,令人遗憾。二是创新的“三手”朝鲜军队。明朝东征军中的南兵与军中教官,利用戚继光的《纪效新书》,通过“三同”训练法,前后共用十余年时间,在朝鲜复制了一支近代化的新式“三手军”,不仅为最后战胜日军奠定了坚实的军事基础,也使这支掌握“戚家军”战术精华的朝鲜军队,成为明朝“剑阁精兵”在海外的嫡传正版。朝鲜这支拥有精良火炮技术的新式陆军部队,后来还在明清易代中发挥了重要作用——被清朝掌握之后,成为对付明朝的利器。事实上,在戚继光死后的第五年,朝鲜战场就已成为戚继光在蓟镇所练新军的最好检验场,“戚家军”的老军骨,吴惟忠、胡大受、骆尚志等人,都是朝鲜军队训练的直接领导者、指挥者和设计者。只是这些“剑阁精兵”的将领命运坎坷,不是在后来遭遇诬陷,就是在历史上被忽略。三是创新的“海上长城”。虽然明朝万历援朝东征战争,消耗了明朝的国库,一定程度上导致天翻地覆的明清易代,这正是造成对东征评价出现歧义的主因;但另一事实也同样显而易见:这场行动及其相关举措,为中国铸就了一道“海上长城”,也对朝鲜的政治、军事、经济、社会、文化各方面产生了全面、深刻的影响。
拥有三大创新的明朝军队和明末历史,却不广为人知,更不用说产生现实影响了。从这个角度看,日本早自明治时代就充分、广泛利用这场战争做文章的意识和观念,确实与中国呈“180度相反”的景象。那么,如何找准历史意识与现实变奏的关节点与焦点?相关历史意识的产生、发展与付诸实践,早已超出单纯历史问题的范畴,而成为与现实问题息息相关的政治、社会、军事、外交的各种具体问题的综合体,但解决问题的基础——历史事实本身的求索与探讨,恐怕是一个更重要也更需学者首先安静下来、花工夫、下力气去做的事。而由有关部门出面、组织各方面人力、物力,编纂一部全面的、综合性的、全球化视野下的《万历壬辰战争史》,应该被提到议事日程上来了。
发表于【光明日报·理论·史学·读史札记】
《域外长城》读后感(四):豆瓣对这本书过于神化了,其实错误很多
此书是我在2015年购买的,书刚出来就买了。此书上架没多久后就下架了(不知什么原因),后来很多网友反映买不到了,只能买到复印版的。对此,我感到比较幸运。 《域外长城》全书一共分为十四个章节,我认为最有价值的章节是第十二章「军中间使毛国科」,揭露了东征军高层在泗川之战以后与日军议和的一些内幕,很有启发性。 本书比较不足的地方是缺乏日本史料的运用,不过目前国内基本都是如此,即便陈尚胜、孙卫国教授也是,所以这一方面也不必太苛责杨海英教授。
但是,本书即便是对汉文史料的运用,也不是很充足,也时常在汉文史料的解读上犯错。本书也存在一些过于明显的硬伤错误。比如前言P6,杨海英指出:
如松之妻,乃郑贵妃(万历皇帝的宠妃)之弟也。然而李如松的妻子和郑贵妃存在什么血缘关系呢?即便真的有,为什么他妻子又是郑贵妃的弟弟?
31,杨海英指出:
明廷先后三次派出军队,到朝鲜半岛及其附属岛屿作战,战事前后绵延七年之久(中间有过短暂修整)——这是十六世纪东亚乃至整个世界规模最大的一次战争,即万历壬辰东征战争。但所谓的中间有过短暂修整,其实表述得并不是十分正确,因为修整的时间并不短暂。从1594年九月刘綎从朝鲜撤兵(标志在文禄之役渡江入朝的明军全部撤兵回国)开始算起,直到1597年三月杨元再次率领援军渡江援朝(标志明军在庆长之役出动第一批援军)为止,明朝都没有驻兵在朝鲜,修整了大约有两年半的时间,占了整个壬辰战争的大部分时间,并不能说是短暂修养。
而对于明廷先后三次派出军队,杨海英在P31的注释中指出:
第一次只派了五千人的辽东地方部队,惨败而归;第二次派出四万多人,以陆军为主,战和;第三次才派出10多万人……最后战胜了日军。但事实上第一次派遣到朝鲜的辽东地方部队人数一共是2854人(《宣祖昭敬大王实录》),不到5000人。第二次派遣的部队,是李如松所率38537人( 《经略复国要编》卷六《益乞增兵益饷进取王京疏》),以及刘綎的后到援兵约5000人(《经略复国要编》、《宣祖修正实录》),加起来是43000多人,没有说错。第三次是约98000人(《东征记》),但没有到十万人,还差了一点。
在兵力数字方面,只能说目前大多壬辰战争的研究著作都没有写对。
31,杨海英又指出:
因粮饷不济,明、日之间开始和谈,派出嘉兴人沈惟敬为和谈使,前往日本谈判,前线进入休战状态。杨海英这句话应该是指1593年的名护屋谈判。但是根据《永哲赴朝鲜记》,沈惟敬在当时并没有渡海前往日本,只是留在了朝鲜釜山浦。前往日本谈判的是宋应昌的部下谢用梓、徐一贯。
31,杨海英又指出:
丰臣秀吉也恰在万历二十六年战事正酣时死去。这话说得也不太准确,丰臣秀吉死亡于1598年的八月,此时距离第一次蔚山之战结束已经过去八月,距离明军发起四路总攻还有一个月(也就是丰臣秀吉死亡后的下个月),他正好死在中间这段时间,也就是明、日两军没有激烈交火的时间段里。
36,针对第二次平壤之战,杨海英又指出:
吴惟忠进攻牡丹峰,攻入普通门,“中铅洞胸”、“功最高”。但根据《宣祖昭敬大王实录》的记载,实际上明军分工明确,吴惟忠打的是牡丹峰,李如柏才打的是普通门,两者位置不同。吴惟忠也根本没有攻入普通门。
36,杨海英又指出:
朝鲜李德馨记载:“提督進圍平壤。先攻普通門,七星門。賊登城拒戰。槍刀下垂城堞如蝟毛。鉛丸雨飛。天兵以火砲,火箭攻之。賊不能支。退入內城。南將駱尙志,吳惟忠。一躍登城。勇士隨後。我將金應瑞,韓明璉。亦一齊踊上。倭賊大敗。走入土窟。”以上这段记载出自《汉阴文稿》附录的李德馨年谱,其实是由他人编纂的李德馨年谱,而不是李德馨自己记载的,杨海英标注错了作者。
37,杨海英引用《芝山先生文集》的《附壬辰事迹》,提到朝鲜将领曹好益跟随骆尚志、吴惟忠攻入平壤普通门。然而事实与此大有出入,根据《宣祖昭敬大王实录》,骆尚志打含毬们、吴惟忠打牡丹峰,都不打普通门,负责打普通门的是李如柏。又根据柳成龙的《平壤贼遁形止状》,曹好益领兵结阵在平壤城东面的大同江,谋求截断日军退路,根本就没有参加攻城的战斗。
39、40、41,杨海英声称宋应昌之所以将第二次平壤之战的头功给杨元,是因为杨元背后的靠山是辽东李成梁家族,宋应昌要平衡南北兵关系。又说杨元是李如松安排在宋应昌身边的耳目。
这些说法可谓大错特错,宋应昌偏爱杨元,将头功安给杨元,实际上就是因为杨元是他的亲信(而非李如松的人),自然要特别对待。而杨元和李如松的关系甚至还是比较差的,后来杨元把碧蹄之战脱围的功绩算在自己身上(但实际上杨元与李如松碰上的时候,李如松已经突围了),引起了李如松不满。可见《宋经略书》对三人的关系叙述:
杨副总兵,号菊崖,定辽左卫人。总兵官右都督四畏之子。初以宋经略中军移授中协副将。经略常言:他将于我,或有所诋讳,杨元则当不我欺。盖以尝为标下中军,而亲信之也。及碧蹄之败,乃以为:提督兵败,为贼所蹑,殆不免,我整众而进,贼见我兵乃退去。经略即上本,以为若非杨元领兵赴救,如松几不免虎口云。杨元当如松败回之日,其众实不来。回军到三十里地,始与元军相值,以此与如松相失。后来杨元在丁酉再乱再来朝鲜,还因为嫉妒李如松,很不满地责问朝鲜人:
你国只知有李提督,不知有我。47,杨海英指出日军在明日和谈期间,攻陷朝鲜晋州,屠杀六万多军民。但根据日本史料《大和田重清日记》,日军实际上只杀死了三千多人,没有六万多人。
48,杨海英指出日军在万历二十一年的十月至十二月,接二连三侵袭庆州安康。十月,日军偷袭安康,驻守庆州的南兵将王必迪营出战,阵亡官兵二百六十人。
但实际上,王必迪隶属于吴惟忠营,并没有王必迪营。而且日军并没有在十月袭击过安康,只在十一月三日大规模的袭击过。杨海英之所以产生这种误解,是因为《唐将书帖》收录的王必迪在写给柳成龙的信,误将十一月三日发生的安康之战写错成了十月三日。
49,杨海英指出宋应昌报告了一场发生在闰十一月的安康之战。但其实宋应昌报告的也是十一月三日的安康之战,只不过他做了与事实不符的报告。杨海英在安康之战的日期判断上,可谓接连犯错。
50、51,杨海英引用《五峰集》,又提到在十二月二日还发生了一次安康之战,数万日军分三路进犯安康。但是这其实是《五峰集》对十一月三日安康之战的日期误记,杨海英又多附会了一战。
52,杨海英对安康之战总结说:
日军进犯安康不止一次:从十月初王必迪迎战一次开始,十月、十一月吴惟忠迎战二次,闰十一月“倭贼五六千,距庆州五十里地来屯”,至此十二月初又三路进抢安康。但实际上安康之战只在十一月三日发生了一次,其余多出来的几战,都是《唐将书帖》、《五峰集》的日期误记,杨海英误引了,结果就是画蛇添足。
52,杨海英指出:
晋州惨案之后,日军八万余人已分期渡海返日,留下四万余人驻守庆尚道东南沿海……但这一说法是错误的,根据中野等《 秀吉の軍令と大陸侵攻 》引用的山崎文书,日军在攻破晋州以后,渡海回到日本的只有49719人,远远没有八万人之多。
72,杨海英认为丰臣秀吉发起第二次侵朝战争的目的,仍然是要与明朝一决高低,再争雄长。但是这种观点是错误的,实际上丰臣秀吉早就已经不敢打明朝的主意了,他二次侵朝的目的,只是追求面子上过得去,让朝鲜主动向他乞和(此前朝鲜不肯派王子、大臣渡海赴日,让丰臣秀吉感到脸面无光,唯一仅有的要求也得不到满足)。小西行长对朝鲜庆尚道右兵使金应瑞透露丰臣秀吉这次出兵目的是:
关白之意,非战斗、欲夺朝鲜之地方也。朝鲜不肯相和,故欲示兵威而取和也。今此之举,只犯全罗而还兵。从《宣祖昭敬大王实录》收录的丰臣秀吉军令,也可见丰臣秀吉此次侵朝的真目的,已经不敢窥伺明朝,只是希冀示以兵威以后,朝鲜能主动乞和,让丰臣秀吉体面地结束这场战争。
朝鲜每此欺我,吾不忍忿。朝鲜所恃而不听我言者,全罗、忠淸二道尚完故也。汝等八月初一日,直入全罗等地,刈谷为粮,击破山城。有可保之势,留屯二道,仍击济州。不可则还兵,自固城至西生浦,相连屯结,以待朝鲜之乞和。85、86,杨海英引用了朝鲜野史《无名子集》,认为稷山之战是人猿大战,并大胜日军:
鞑将解生、攞贵、赛贵、杨登山等四人率铁骑四千、挟弄猿数百骑,狙伏於素沙桥下,望见倭自稷山如林而北。未至百余步,先纵弄猿。猿骑马执鞭,鞭马突阵。倭国本无猿,始见猿似人非人,咸疑怪驻阵眄望。既逼,猿即下马入阵中。倭欲擒击,猿善躲避,贯穿一阵,阵乱。解生等急纵铁骑蹂之,倭不及施一铳矢,而大崩溃南走,伏尸蔽野。但这一段记载纯粹就是胡扯,首先明军将领的名字就搞错了,没有所谓的攞贵、赛贵,正确应是颇贵、摆赛。而且从《宣祖昭敬大王实录》的记载可以看出,明军兵力实际出战兵力是二千人,麻贵后续派遣摆赛的二千五百援军没有实际参战,并不是四千人。明、日两军交战的地点是在稷山,不是在素沙桥,素沙桥是在稷山的北面。(不过较晚成书的朝鲜史料确实附会出了一场素沙坪之战,《无名子集》应该就是在朝鲜野史基础上进行再创作)。
86,杨海英声称杨镐在稷山之战亲自上阵,砍下了两颗日军的人头。这个说法简直太搞笑,杨镐当时在王京,根本就没上前线。杨海英对稷山之战的理解太错乱,又是人猿大战,又是杨镐亲自上阵。
87,杨海英引用《西厓集》,认为杨镐组织七万人马进攻蔚山。但是根据《两朝平攘录》列出的具体动员名单,实际上明军只不过动用了47826人。
88,杨海英提到杨镐、麻贵进攻蔚山的兵力部署:
左协李芳春部从左路、中协高策部由中路、右协彭友德部由右路,同时前进。但这个说法是错误的,根据《经略御倭奏议》、《两朝平攘录》的记载,左协大将是李如梅,不是李芳春;右协大将是李芳春、解生,不是彭友德。彭友德实际上是作为游击军。
88,杨海英又提到:
中协高策屯军宜城,东援庆州,西扼全罗,以余兵会朝鲜合营,诈攻顺天等处,牵制小西行长等应援日军。但这又是对史料的误读。根据《两朝平攘录》的记载, 邢玠摘发中协兵马的一队(只是中协的部分人马,不是杨海英说的高策全军)屯驻于庆尚道的宜宁(同样不是杨海英说的宜城),西防全罗道的日军出兵救援加藤清正,东援明军左、右两协。至于诈攻顺天的小西行长,也不是中协高策的任务,而是专门从三协中抽调出一千五百骑兵,让他们负责完成这一任务。
88,杨海英声称杨镐、麻贵在1597年的十二月四日就已经发兵攻打蔚山,俘斩日军将校一千三百多人,加藤清正仅以身免,逃入岛山,然后二十三日、二十四日再次发生大战。这一个说法又是大错特错,实际上在十二月二十二日,明军才从庆州南下,向蔚山进兵。从十二月二十三日开始,才打响第一次蔚山之战,根本就没有也不可能在十二月四日交战。
88,杨海英提到明军包围蔚山的部署:
经理杨镐、都督麻贵屯于城北,高策屯于东,吴惟忠屯于南,李芳春屯于西,李如梅、摆赛把截西生浦的江边,祖承训、颇贵把截釜山日军。从这一段描述来看,杨海英没有基本的朝鲜地理概念。西生浦是当时日军援军集结、准备去救援蔚山的地点,其实离蔚山战场还是有一定距离的,明军当时的围城部署根本就够不着那里。李如梅、摆赛是负责把截从西生浦海路方向驶向蔚山的日本水路援军,而不是把截西生浦的江边,这两个概念是完全不同的。杨海英之所以出现误读,是把史料中的把截西生浦日军,望文生义地理解为了在西生浦把截日军。
90,杨海英引用《龙湾闻见录》、《宋经略书》,说郑琢(前面一本书的作者)记载了第一次蔚山之战的细节。但实际上《龙湾闻见录》根本没有记载这些事情。
总之,本书的论文选题还算是不错的,但是在细节上犯下的错误颇多,有些是不应该犯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