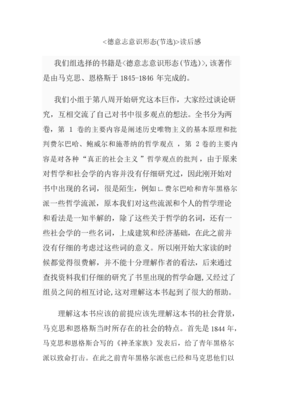
《德意志问候》是一本由提尔曼·阿勒特著作,江苏人民出版社出版的平装图书,本书定价:12.00元,页数:150,特精心从网络上整理的一些读者的读后感,希望对大家能有帮助。
《德意志问候》精选点评:
●翻译者是我们尊敬的可爱的Hans Meng
●不知所云
●好枯燥
●某人替我读过了。
●法西斯的意识形态总是惊人的相似…
●飞机上看的一本小书。读完书中描写希特勒时代人民疯狂的个人崇拜,抬头看到飞机上屏幕播放着的红色恐怖片,倒吸一口凉气。
●七万多字的小书来介绍德意志问候礼这样一个符号化的礼仪形式如何产生、发展、扩散、消亡和其历史影响的。虽然篇幅很短,但是这个问题绝对值得长篇著述的,本书应该只算个开始。这一“希特勒问候语”实质上也是种影射,日常生活中的少先队敬礼、各国军礼中的含义如何呢?出于对德国当时“激进现代性”的分析,那么当下如此多的第三世界国家都在经历这个阶段,是否也都广泛存在于这样的符号化问题。受不同时代的制约吗?是否这个“礼”也有所变化:比如抬高的角度,有无专门的机构或人员进行矫正?其手礼的独特性,是否这样一种“德意志问候”也排除了其他惯例实践的具体形式的可能性?
●2009-08-09 借于南京图书馆 --- 一种具体的反省
●首先,必须对封面吐个槽
●: K516.44/7242
《德意志问候》读后感(一):总觉得这是红史
1. 纳粹统治时期,行礼被视为一种示忠,希特勒问候的贯彻与推广标着着人际交往只需发生的重大转变。同时又清晰地说明德国人地集体退化。他们沉寂在[罕见地前现代仪式所营造地幸福]当中。
2. 当人们决定集体舍弃自己的道德审判标准,并且当人们通过认同纳粹政权来表达这种舍弃,那么它同时也撼动来人际交往当微观社会。
3. 即将陌生人视同为敌人当血淋淋当疯狂。
4. 道德伦理的崩溃——诚如我个人的浅见——不是突如其来的,也不是偶然发生的事件。它是社会个体丧失对个体存在感对控制,无法形成个体存在感感的必然结果。建立自我联系的失败使人们低估来社会缓解变化的真实行,并最终导致神授魅力——获得急剧膨胀。
社会学家 马克斯`韦伯:这种神授权利足以颠覆规则/传统和一切其他圣洁的感念。
此外,它对人与人之间对交往后果也产生来严重对影响,人们对于人的行为的的认识将变得极为狭隘,并形成一种错觉:他们当下所有感知,包括问候行为在哪,并非来源于他们直接面对的行为本体。随着[感知丧失]的出现,构成基本人际交往的标准也变得模糊不清。
5. 这种[问候]无形中使得[最高领导人]无形中成为万能主宰的化身或者代言人。
6. 古以有之。今犹不绝。
7. 问候着将自己托给上帝,让上帝主宰相关的关键时刻[推卸责任,逆来顺受]我在问候的时候臣服于上帝示范性的抚慰力量,并把这种对上帝的信任感加于对方。
8. 军礼的特质在于所有动作集中反应出一种高度的专注[专制?纪律]:最大限度集中注意力,排除其他动作大干扰/清晰体现出上下级之间大服从关系[控制govern关系]/具有明确大先后行为顺序。在军礼中,身体的姿态意味着对地位等级对强调。
军礼行问候折射出一种制度化对全身心对战备。甚至蕴含献身对可能。正由这一切,产生来专一性和身体的紧张感。当人们穿上支付,整个人一下子完全进入x兵当角色,特别是帽子[手中的红宝书和袖标?]更能清晰地感受到这种普通人与士兵到合一。
9. 它在日常生活中重塑了一种相互间到呼吁,要求对方[效忠][疯狂]做好准备[消灭阶级敌人]。作为一种誓言,它要求人们无条件忠诚,基于一种原则上具有可能性/出于道德软弱和怠慢形成的约束力的模糊不清,构筑更为坚固,不让人失望的相互关系。通过宣誓,给自己承担的义务[犯下的罪行]套上了神性的光环,从此再不用在具体的场合检验自己行为意图的合理性,更不用提及这种合理性。
10. p85注释(1):没有人可以预料怠慢行礼或者根本不行礼会导致怎样的下场。这种前途未卜足使热门对此产生一致接受。
11. 纳粹上台后,德国对教育机构争相向学生灌输问候规则。
12. 反应社会制度的强制性同构成自尊的道德准则之间醒目的被撕裂状态。
13. 维克多 施瓦尔布洛克 :“因恐惧造成的沉默/人与人之间的猜忌以及令人不堪重负的强迫” 1934-6-13
14. 几乎百分之百的儿童和青少年都加入了纳粹的青年组织
15. 在青少年组织中,人们打破了以共同体模式渗入家庭环境的父权主义,建立起一个神圣化的公共空间。
16. 用集体行为代替个人责任。
17. 由独裁产生的语言变化:(1)文字狱、(2)帝名讳、(3)简化语(《1984》)
18. 社会被各种共同体取代,共同体被认为地神圣化,承担社会义务变成了一种英雄行为。
19. 冷漠、无动于衷和道德规范的缺失
《德意志问候》读后感(二):从一个手势透视德国的灾难
1933年,德意志帝国内政部长在一份传达给帝国最高机构的备忘录中写道:“在推翻了多党派的国家之后,希特勒问候语已经成为全德意志的问候。”所谓“希特勒问候”,就是我们在电影中听到的高呼“Heil Hitler”,同时摊开手心、伸展右臂举至眉梢的动作。
很多人一直把这句话听成了“Hi,Hitler”(嗨,希特勒),其实Heil Hitler的意思是“万岁希特勒”。这个问候礼被称为德意志问候或者希特勒问候。在12年的时间里,德国人在相遇的最初和最后,无数次使用这一问候礼,不论行礼的人是欣喜、敷衍、犹豫还是勉强,无论是低语还是高声疾呼,它已经成为一段野蛮时光中的一个灾难性的姿势。即使在战后,仍然是德国人心头挥之不去的阴影。执着于反思的德国人对此久久不能释怀,法兰克福大学的社会学教授提尔曼•阿勒特就此写了一本书,书名是《德意志问候——关于一个灾难性姿势的历史》。
对于问候,阿勒特是这么定义的:“问候是最短暂的一幕社交,人们以无休止的美轮美奂的动作表演着他们的相遇,而问候替他们拉开大幕、分配角色、安排出场,也为历史和创新预留了空间。在每一声问候中——即便是拒绝的话语——都映射出参与者的自我感知和他们感受相互关系的方式。”在阿勒特看来问候产生相互往来的义务,迫使双方互相承认,互相体谅,并催生合作。问候将交往的双方带入当下的时间性层面中,“你好”,“晚安”这样的问候行为使双方获得了社会空间和社会时间上的共性。
希特勒问候据说来自古罗马敬礼,墨索里尼在意大利早于希特勒创造了一个类似的问候礼——“salute romano”(向罗马致敬),其伸展的右臂被视为一种故意的、反市民的姿势(但它只有肢体上的动作,没有配套的语言)。墨索里尼曾这样说:“不是我们在学德国人,相反,是那些德国人,无论过去还是现在,都在抄袭着我们的罗马祖先。”希特勒问候虽然自称为纯正的日耳曼血统,但是却不断遭到质疑,连纳粹党员们也把它看作非德意志性质的法西斯问候礼。
在德意志问候之前,德国人的问候行为具有鲜明的地域性、行业色彩和地区民族文化特征。在北德奥登堡地区的小酒馆里,晚上同别人打招呼时,用的仍然是白天打招呼的问候语“moin moin ”(你好,包含有“日安”的意味)。还有些问候语体现出德国典型的诸侯割据的宫廷特征,“请允许我吻您的手”,“请准许我”,“我是你的仆人”等等。还有一些套语多少包含着基督教的普世思想。在南德天主教地区,日常问候语是“问候上帝”,或者是“上帝问候于你”。在人与人的相遇中,把第三者牵扯进来,问候者通过这样一个想象中的主宰,消除了陌生感。而在“万岁,希特勒”中,希特勒变成了上帝。
1937年,周游德国的作家贝克特途径累根斯堡的多米尼加教堂,他发现北门的一块牌子,原来写着“问候上帝”,现在被划掉了,取而代之的是“希特勒万岁”。在语言的替代中,尘世规则完成了其神圣化的过程,希特勒变成了交往的保护神。借助这种方式,充满神授魅力的希特勒的形象成为人们日常世界中的富有意义的存在,充当着人际交往的基准布景,同时又让他的形象存在不可企及的意念中,让人无限神往。德意志问候礼体现出纳粹宣传攻势的核心:让希特勒无处不在。
人们很快发现,新的问候语已经成为了用来测定社会成员对纳粹政权认同程度的地震仪,每个震相都成为评判忠诚度的工具。在长达12年的时间里,希特勒问候语仿佛一个幽灵,成为在象征意义上和身体姿态上覆盖开场白和道别语的一种绝妙伪装,但它以非凡的魔力渗透到人与人之间的相遇中,它从两个方面见证了人与人之间礼仪的消失。首先当人们使用希特勒问候语的时候,他们的相遇根本没有相互问候,其次从历史层面上,它又成为纳粹对人的身体姿态的占领,纳粹思想在人际交往的脆弱缝隙中大获全胜。
问候者和回礼者手臂无限接近的同时,他们的内心却远隔千山万水,相遇者不但没有彼此接近,反而更加疏远。他们陷入一种自我制造的魔力之中,成为神圣之地的陌生者。仿佛有一种无形的孤独的内聚力作用在他们身上。
阿勒特认为,造成德国民族生存心态发生改变的元凶,即不是集体的道德异常,也不是一个民族内在化的反犹太主义,更不是“被追踪妄想”或家长制。相反,德国人自我联系的断裂和随之而来的安全感的丧失使人陷入了周而复始的,不断刺激自己的自我动荡中,这种自我能动严重阻碍了同他人的交流,因而对周围的一切变得越来越漠不关心。历史存在于细节中,从这个角度来看,德意志问候正是德国灾难的根源。
《德意志问候》读后感(三):自由始于不服从
所谓“德意志问候”,指的是1933-1945年间渗透整个纳粹德国的社交规则。大多数人应该都从电影中见过这一令无数人谈虎色变的姿势:即像机器人一样直挺挺地立正,右手斜向前伸,高喊:“嗨!希特勒!”作为纳粹秩序的外在标志,它无疑是那个黑暗时代的社会与政治的最突出的象征之一。
德国学者提尔曼·阿勒特对纳粹秩序的拷问就是围绕着这个姿势展开的。二战结束以来,德国人以其深刻的赎罪意识重新赢得了世人尊敬,这种沉痛的反省也深深地铭刻在这本薄薄的小册子中。在作者看来,这一简单的问候语,有着深刻的社会政治背景,是那个时代国家性的象征与建构,它以最简单的外在形式抹杀了社会个体的思想自由。
问候本是一种最平常随意的社交形式,连这种最基本社会交往也要由政治性规定来指导,本身就昭示着国家权力无孔不入的干预。任何拒绝希特勒问候语的人,都会面临不爱国的指控——它成了判定社会成员对极权政府认同程度的指示性工具。在这里,不服从的权利被取消了,任何人要想不被怀疑,就必须无休止地通过这一问候语来明确表达自己的忠诚。问候语变成了一种严厉的社会控制手段,使人际关系发生了重大转变。
希特勒问候礼是近代一系列历史进程的最终结果。在西方现代化的过程中,身体管理逐渐成为行为规范的必要组成部分,它与礼仪、权力关系、政治行为的结合产生了文明规则。欧洲文化将这种礼仪中的限制性规则变成了人们的思想方式,社会组织化程度越来越高,对个人内心的压力就越来越沉重。这种技术主义和工具理性发展到一个极端,就产生一种布克哈特所说的“可怕的单一化”(terribles simplificateurs),纳粹在思想上推行的强行一致化(Gleichschaltung)就是其登峰造极的阶段。这样一个将日常生活都彻底组织起来的国家,必然造成精神视野的急骤狭隘化,国家无情地指导着所有人,毫不关心地对待个人生命,人们必须无条件地放弃对自由的热望,学会成为一座庞大机器无数齿轮中的一个。
人们并不都是被迫行纳粹礼的。事实上,当时它还被神圣化为民族共同体成员专享的特权之一(犹太人就被禁止这样行礼)。许多人自觉自愿地、狂热地通过它来表达自己对纳粹体制的认同,在某种程度上是因为当时德国强烈的民族自我意识危机。历经近代史上的多次磨难,德国人的自尊心惨遭打击,形成一种固执、片面谋求国家强大的心理——从心理学角度来看,渴求权力其实植根于软弱而非力量。纳粹宣传机器通过将希特勒描绘为将祖国从濒死的沉睡中唤醒的英雄,极好地迎合了这一心理,希特勒问候礼成为克服这种危机和潜在不安全感的力量源泉。
通过逃避自由和放弃个人自我的独立倾向,大批的德国人在这种弥漫社会的整齐敬礼之中,使自我与一个更高价值合为一体,使他们产生一种获得自我所缺乏力量的幻觉。个体自觉地将主权让渡给超个人力量,而凌驾于他们之上的整体权力则不断加强,这种不受任何约束的力量将所有人牢牢凝聚在一起,既是一个顽强坚固的集体,也是一种最可怕的控制。个人的心灵在这一整体中黯然失色,丧失了它的内在价值和独立判断,在精神上无法独立自主。
德国人的这一悲剧可以追溯到路德。在他的思想中,臣服是被爱的先决条件。通过消灭孤立的个体自我,通过与超人力量合为一体(即成为其工具),来寻找肯定。这产生了几个严重的后果:既然个人道德感已被转移给一个超个人机构,人们也就不再对个人行为负道德上的责任;其次如书中所引的一个例子,那种对领袖的狂热,“需要多少对自己的恨才能铸就?”——充斥于现代人生活中的“义务感”,实质上都带有浓厚的敌视自我色彩。纳粹礼推行的迅速和遭遇抵抗之微小,正是因为当时的德国人已经在精神上做好了准备。
“德意志问候”并不仅仅是德国历史的一次意外,它实际上为所有世人敲响了警钟。个体自我的理性和自由,是整个社会理性和自由的基础。而不服从的权利作为一种自由行为,则是理性的开端。如果没有自己独立自主的思想,那么“表达思想的权力”也将毫无意义。一个美好的社会,国家的强大应当与个性的自由同步展开。
纳粹礼已经远去,但催生它的现代文明仍在世上。商业社会同样通过各种媒体和信息渠道,无情地指导着人们的生活:在女性减肥中最能辨认出那种高度自我控制的身体管理与自我否定(厌食症)。只不过现在,社会控制手段变成如此柔软而不具强制性,以至于被控制者不知不觉地忘记了不服从的权利。正如托克维尔曾提醒的,下一次,社会控制也许将像睡梦一样无声无息地到来。
《德意志问候》读后感(四):纵欲的问候
【读品】成刚/文
假如希特勒没有朋友这个说法确凿,我们就不得不面对两个现象:首先,一个社交失败的人竟然深谙社交密码,借助德意志问候主宰德国人际关系长达十二年之久,彻底颠覆了传统交往规则;另一方面,我们将对这种强制性问候的恶果做出合理解释,正因为希特勒不善处理人际关系,才将人们拖进冷漠、猜疑的泥沼。这两种观点看似矛盾,却无疑指向同一处,即德意志问候在纳粹统治体系中的地位。这在以往的德国历史研究中并没有受到足够重视。
法国社会学家提尔曼.阿勒特的研究及时填补了这一缺口,给予开启对话的问候(“象征中的象征”)以应有的关注,并将它扩展至历史、社会、家庭、心理、文学等多个领域,以狂热的口号“希特勒万岁”为主轴,从另一维度,为我们展开了一幅飘摇于悲剧中的德国全景图。他的独到更表现在,于臭名昭著的德意志问候与隐匿在当代大众媒体后“饶舌的恶言相向”、“疯狂的自我表现”的时空差中求得关联,在丰饶多姿的现代语言中窥见冷漠、无动于衷和道德失范的端倪及危险。正如在前言中他附身法国作家塞缪尔.贝克特旅德经历展开自己的研究,回溯“希特勒万岁”历史时他对当下忧心忡忡。
德意志问候是什么?一个偷天换日的概念,希特勒个人设定的礼节入侵伦理道德的秘密通道,希特勒问候的伪装。在纳粹德国,人与人相遇时以“希特勒万岁”互致问候,伴以夸张的姿势:摊开手心,伸展右臂举至眉梢,右臂残废者,举左臂致意。所有传统问候礼数一夜间销声匿迹,如“日安”、“你好”、“再见”;所有面向个人的祝愿和祈盼被一个不在场的第三者暴虐地掠取;所有私人情感交流的途径都被某种宣誓生硬截断;信任、友好、规则、传统与一切神圣被埋葬,猜忌、冷漠、反常与排斥丛生密布;“人参与了交际,同时被排除在交际之外;人与人相遇在一起,同时又互相远离。”在自我联系断裂的一瞬,陌生人更陌生,甚至对立为敌人,血腥气在德国上空开始蔓延。
把日历翻回1933—1945年之间的任一天,在柏林、法兰克福、或者德国其它地区,你将会迷失在由亢奋的 “希特勒问候”搭建起来的语言迷宫:“希特勒万岁——我能为你做点什么?”的服务用语结束后,售货员与顾客开始进行商业活动;在起立并喊“希特勒万岁” 后,学生才上下课;认真写完“向您致以希特勒问候,希特勒万岁”,才能够在工资单、银行汇款单上签名;“希特勒万岁”声中,情侣和夫妻们拥抱接吻;家家户户的客厅里悬挂着摄影师霍夫曼拍摄的希特勒肖像照。希特勒无处不在。希特勒仿佛是使世界运转起来的动力。天主教和新教日渐萎缩,取而代之的是希特勒,他拥有神授魅力,似乎还具备光源的作用。
如果仅仅是复原与展示,只能说提尔曼.阿勒特视角别致。如果说希特勒问候语的广泛接受源自大众急切期盼社会治愈和走出凡尔赛条约的阴影,或者因纳粹在暴力胁迫下的强硬推行,又如何解释这一现象:战争结束后,纳粹政权幽灵一样消失后,许多个喉咙仍然发出“希特勒万岁”的音节,许多只胳膊依然直直挥起至眉梢,以至于不得不出台严厉的律法来加以限制清除。如果十二年的积聚的惯性能够做出解答,又该怎样看待今天德国某些社会现状:“Heil Hiter”(“希特勒万岁”)的缩写无声地出现在车牌上、代表第八个字母“H”的8的连写88印刷在T恤衫图案上,这岂止美学原理和时尚所能概括。
不能草率地归结为纳粹崇拜,尽管它的确存在,存在于别的国家。也不能盲目指称为纳粹后遗症,接下来我们将会知道其间某些社会心理在纳粹政权之前已经存在。在这一问题上,提尔曼.阿勒特从微观社会学和家庭社会学着手,把德意志问候和父权相结合,“在国家社会主义神话色彩下的家庭,始终处于对父权的怀疑之中,权威被抹杀,两性关系经历了一种伪现代的平等化过程。”这种对亲属关系的质疑,来自希特勒问候的政治共同体性质对血缘的扼杀。接受希特勒问候,又是因为人们无法分辨、拒绝承认人类生活的多样性,换言之,抵制社会秩序的多元化和机构分工的多样化的冲动与希特勒问候的不谋而合。
总之,传统行为规范被摧毁了,“我再也没有任何地方可以从头开始重建我的生活。”(茨威格语)。不少人将希特勒问候这简陋的仪式当作浪涛中一根稻草,紧抓着,不松手。从那以后很多人开始沉默不语,从那以后脱口秀节目开始疯狂,这看似悖谬的双方实为硬币的两面。“倾全力演出的摔跤,其本质是一种纵欲现象。”(罗兰.巴特《摔跤世界》)
《德意志问候》【法】提尔曼.阿勒特著,孟翰译,江苏人民出版社 2008年1月
本文刊登于《南方都市报》2008年3月2日阅读周刊.历史.GB27版 有删改 请勿私自转载
《德意志问候》读后感(五):嗨!德意志
1554年马丁克鲁西斯在他的《年代记》中举了一个奇特的例子,而这个故事引自更古老的编年史。那时在士瓦本乡下游荡着一些云游者,他们在海边把黄色的网悬挂在肩上,声称可以司掌农产品的价格,拥有强大的力量……或许他们就是本南丹蒂(benandanti)。
当1525年上士瓦本地区的起义者团结在十二条款的号召下,这场运动就不仅仅是造反、暴动、动乱。旗帜鲜明地争取自己的政治经济权利,才是他们真正的目的,纵使这场运动间或披着神学的外衣。
幸福不仅仅是上天赐予的,坚信上帝抛弃犹太人正拣选新选民的中世纪人对于基督教的热情是无与伦比的,加尔文和路德代表的新教伦理正是激励他们前进的天使。彼得•布瑞克则建议我们先放下宗教,其对1525年德国农民战争的这一种阐释对于当下的中国三农问题是不是确有实效,尚不得而知。但译介者在译序中表达的感情却是直露滚烫的:“现代化不是以牺牲农民为代价而发展起来的现代化过程……它是农村与城市的互动……农民具有改革农村秩序的能力”。
这一对1525年德国农民战争的“新透视”究竟折射出怎样的光彩?诞生于二十世纪七十年代的东西德对峙情势之下的此书,不可避免地侧身于两大阵营的对立中。一方是马克思主义史学家们坚持的经济社会分析和阶级斗争说,另一方则是西方“政治运动学说”;两派的观点皆有理,也都有缺陷:“政治运动学说”下的农民战争发端于领主统治权的兴起,并非是宗教改革的附庸;而马克思主义者固然把农民大众看作是推动历史发展的力量,但在其整个社会衍化的庞大框架之下,个人的力量显得格外渺小卑微。
布瑞克的观照在第七和第八章的命名上表露无遗:“作为普通人起义的农民战争”与“作为一场革命的普通人起义”。对于革命,汉娜•阿伦特直言“只有出现同情新事物并且这些新事物和自由的思想相关联,我们才有权谈论革命”,没有群众基础、使用武力、形成未来国家和社会的新思想就难以称其为“革命”,就这一点而言,1525年革命当之无愧,十二条款每一行都指向着民主、自由与平等。
相较而言,四个世纪后发生在德国大地上的另一次运动,就很难称之为“革命”,即使其具有“革命”的某种表相:迅捷而激进。
1933年,纳粹帝国内政部长在一份传达给帝国最高机构的备忘录中写到:“在推翻了多党派的国家以后,希特勒问候语已经成为全德意志的问候。”1934年的柏林奥运会上法、英两国的代表团在开幕式入场时也伸出右臂向东道主致意,1935年的《图解杜登德语大词典》中,希特勒问候语赫然在“问候方式”图解中位列第一。
不使用希特勒问候语的结果是谩骂和羞辱,拒绝行礼的人即使侥幸逃脱逮捕,也很难不被周围的群氓围攻。“上帝问候你”、“上帝祝你早上好”被极权的铁手一把甩开,连最常用的缩写形式“祝你早安”、“早安”、“早”都被那一只只升起的右臂所取代,当然,偶尔也有些人性的未泯,对于右手不便的人来说,宽宏的方式是换左手。
如此规模巨大的“唯名”规定和语言政策上的变革在历史上仅有一例。然而它的徒子徒孙却绵延不绝,原先交往场景中的第三方——上帝,现在可以堂而皇之地换成任何一个制裁者的名字:“以XX的名义发誓”、“向x主席保证”、“xxx万岁”,分明遥远而又熟悉。
但最可怕的不是这个,原先将上帝作为相遇的保护者的社会契约,慢慢演变成了“希特勒——保护者/距离”这样的吊诡形式,问候既是克服距离的手段,又变成了保持距离的工具,好似塔利班掌控下的电信部门的职责:严防互联网在阿富汗境内的使用!
不信任和告密是黑死病一样的灾难,“小心,敌人在偷听”不仅写在公共场所的墙上也深深地刻在每一个德国人的心里,单凭一种意识,觉得自己可能遭受怀疑,就足以使大众交往环境充满“自我审查”的空气,而作茧自缚之后则是圈子越走越死,自我审查的愈发严格,杯弓蛇影,最后崩溃。
爱弥尔•涂尔干在《自杀论》和《职业伦理与公民道德》中探讨了自杀与杀人等犯罪的关系,并非所有的自杀都跟杀人有关。因失范导致的自杀则有两种可能,向内坍塌是自杀,向外坍塌就有引发犯罪的危险。杀人作为犯罪的极端化变相,实际上与利他性的自杀颇有相通之处。当一个人不重视自己的生命的时候,他是不可能重视别人的生命的,而自戕和杀人与否都和整个社会的道德风气有很大的关系。当社会整体性失范的时候,犯罪的存在就变成了替罪羊,它转移了大众的视线和怒火,能使得人群凝聚——在这点上犯罪的效果跟外敌入侵极为相似——促进凝聚力的加强和人群内部认同的深化。当人们去处置犯罪者给予刑罚的时候实际上凸显了自身的道德优越性。
以这样的观点再来看民众对于推行希特勒问候语的反应就可以理解为,抗拒行礼者即越轨者让群氓认识到彼此的不同,由此产生的打击和谩骂实则意在藉此重申倚靠政权后取得的“道德优势”与社会上的优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