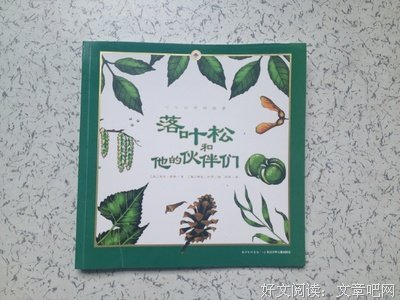
《讲故事的人》是一本由John Berger著作,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的平装图书,本书定价:29.80元,页数:392,特精心从网络上整理的一些读者的读后感,希望对大家能有帮助。
●故意拖着,一天看一篇,今天才读完这本,算是读完伯格所有的中译本了,竟有一阵空虚。用@肖水 翻译的诗讲,就像搭顺路车旅行/在深夜/进入一个陌生的城镇/那里寒冷/下着雨/你又一次孤身一人。感谢约翰伯格。
●约翰·伯格是我今年最幸运的相遇
●和本雅明《讲故事的人》谈理论不同,John用一个画家的视角来记录生活中的旅居和梦想,或是画评与灵感,还是挺有意思的。挺厚的一大本,不知道多年之后我会不会记得这是在T大看过的最后一本书。不知道是否因为翻译的原因,有些描述会有点隔的感觉。
●读约翰伯格的第二本,一样讲艺术观看,相较前一本《观看之道》,读来爽很多,毕竟《观看之道》只是一本照顾大众的盛名在外的小册子
●关于旅居梦想绘画 囊括很多,要么有理论,要么有趣味,甚喜欢。就是诗歌翻译烂得完全无可读性。
●好听~
●任性,就想评五星。
●✈️
《讲故事的人》读后感(一):《讲故事的人》中最美的故事
《恩斯特。菲舍尔:一个哲学家的死亡》,是这本书中最美的一篇。是乡村景色、雨、时间、精神与存在的完美融合。我在零敲碎打的时间碎片里完成了这个故事的阅读,基本都是在上下班的城铁上。
即使是约翰。伯格这样擅长用视觉方式(心理?)进行叙述的人,也需要在故事,和时间的穿梭中完成最终的创作——只有故事才能创造成永生的形象和精神。否则都是雾里观花。
《讲故事的人》读后感(二):这是多么坏的一种习惯
quot;路遥遥 水迢迢 旅途。个人喜欢顺手在书架上拿了两本约翰伯格的「我们在此相遇」和「讲故事的人」丢进袋子里面。时常由于各种冲动,短时间集中阅读和过渡的储备,甚至有些年头都没曾动过开过塑封包装,这只是在等待偶然的开局状态把它们一并衔接。翻看"讲故事的人"愣了一下,多少对画作语言方式表达如此熟悉,或者说疑虑于自己的思维深处有某些约翰伯格看待事物方法的痕迹,就象影片"盗梦空间"一样,兴许约翰伯格套着赖声川接着苏珊桑塔格或者文道、侯吉量孙行者白龙马堂吉柯德等等一系列感兴趣的思维层层叠叠,象吸血蚂蟥潜藏在记忆深处不断延展与裂变。最终象训练有素的侦探用清晰的思维导图组合成每个人不相同的巨大思维魔方。突然想起曾看过这样一段话:"如果每个人死后,身体都能自动变成一本书,书的内容就是死者的生平。有人会变成名著,有人成了禁书,有人变成菜谱,有人变成地图,有人是photoshop使用手册,有人是小旅馆的开房登记簿…"。有点可笑的是:个人又去在一些读过的要当垃圾丢掉的书中,找回了约翰伯格的书。发现他的小说、艺术评论、摄影评论和随笔集各方面大部分作品都曾读过。有点违背原则味道的是,又把它们放回了书架上,也许读过一次书真的可以值得在读一次,这是多么坏的一种习惯啊。
《讲故事的人》读后感(三):书边闲话
前两天去三联,在底层文学类的书堆里见到这本书,灰暗地待着。心里有些难过,这样子的封面摆在书堆里,是太暗了。平常在家里灯光下摩挲时还是喜欢的,除了字体。
只是……这是怎样一本书呢?封面没有传达出清晰的信息。甚至分辨不出时间来。仿佛是一本八十年代的书。在另一种纸上印刷的时候,它更其晦暗,仿佛《静静的顿河》。可它不是。它有点迷失在时间里了。
封面上的小字:
“约翰·伯格随笔代表作,定居的耕作者和从远方而来的旅者特质的融合辉映,
行走成就的无界书写,故事引导的纸间旅行”
我怀疑是不是该重新弄弄标点。措辞足够迷离,也是时髦样式的鼓吹,它说到旅行,与这封面倒是呼应的。
随笔究竟是什么样的一种文字呢?它不似小说,带我们进入另一个人生。它只是撩开帘幕的一角,迅即落下。它甚至不屑于论证,有时是因为促迫,有时因为倦怠。
在我生命的这个阶段,读随笔竟是一桩困难的事情。躺在床上或伏在桌案,想的都是彻底的离开或者全然的安顿,只是在二十分钟的地铁上,或许能读完一个故事,读完半篇文章。
轻咬着这些字,囫囵吞咽。有精彩的译笔,也有潦草的。认得译者,所以文字跌宕处,格外心惊。
在地铁上读这本书的时候,我巴望着人们都看见这本书。
封面太容易磨损了。可是,能够指望拥有一本时间之外的书吗?
《讲故事的人》读后感(四):敬土地者近神明
这条街的树木在盛夏的半空连接成道道拱门,两边一层房子临街的窗户统统被凿开,粗拙的铁艺围栏勉强圈出了庭院,灰空间的过渡在这里丝毫不起作用,商品将生活汹涌地带上街头。它暗示着这必定是条暮年的街道:血糖仪、血压计、无糖食品……人们把蔬菜、水果、成箱的牛奶、卤味和糕饼的香味散播到人行道上,他们坐在其间,用锃亮的不锈钢盆装着可以从早上吃到傍晚的菜,嘴里含着咀嚼的饭菜招呼买东西的客人,也咒骂自己的孩子。老人们把日子过得很长,他们早起,把所有延时的动作都暴露到日光下,所以晚上的时候这条街道就剩下昏黄的灯光。当然,有些房子的营生属于夜晚,她们通常在早市初开之时结束工作,然后向街坊买一天里最新鲜的食物。
方言和街巷有种天然的亲密,样本的不可复制性来自于这些顽强存在于城市夹层中的街道。一天早上,一个戴老花眼镜的老人拎着刚买的一捆芹菜回到摊位前,固执地要退了它,因为他发现再走几步的另一家比这家便宜。老板娘是南方人,强壮精干,黝黑的脸膛,沙哑的嗓门瞬间嚷嚷得一条街都听到:“笑话!八毛钱的物什你也有面孔来退!你活到这么大岁数饭都白吃了嘎!”那老人一遍遍地重复着“我想退了它”,就这样僵持。摊位边的那只杂毛狗瞎了一只眼睛,看起来好像时刻对你眨眼,四仰八叉地吐着舌头,不吠不跑。各种方言再夹杂进来,有劝说老板娘退给他的,有劝说老人算了吧的。我经过,知道新的一天又开始了。
1962年,约翰•伯格离开英国,足迹遍布世界各地;1970年代中期,他选择定居于法国上萨瓦省一个叫昆西的小村庄。这本随笔的大多数文章都写于他定居昆西之后,但也留着那十数年漂泊的印记。伯格与英国某种意义上的“决裂”,是他自省地对从前自己的背离,至少,他之后终于从“不得不以艺术批评的方式表达对任何事物的想法或感觉”的境地逃脱。感谢逃脱,我看到行走的旅人书写于土地之上的文字,理性的爱亦能生发柔情。
我不明了这种情感由何而来,我离西西里采牡蛎的天主教徒很远,也同博斯普鲁斯海峡渡船上的卖针人没有交集,更和阿尔卑斯讲山地法语的牧牛人无缘,但那些故事却在我心中回荡,渗入我观看的意识,我日常的情感。伯格致力的事业,是希望的宗教,感动总来得神秘而不可知,但希望这种状态,关于相信,因相信而行走,因相信而观看,因相信而记录,因相信而书写。
这片土地上,每天都有人或平淡或离奇地生老病死,当漠视遭谴责的同时,更需要当心的是怜悯。伯格曾经称好的小说作家是“死亡的秘书”,其实他本人亦是一位好秘书,他记录观看,而从不随便发表观点,“这就是我看到的世界”,它生猛而直接。他将自己的行走付诸笔端,我们将他的文字反转为观看,在辽阔的幅员上,到处是和我们一样普通的人们,不管他们肮脏而狡黠,只要相信,就能变为力量。这种乐观亦根源自马克思,人们不再相信乌托邦,退一步,1968年之后的左派,“去战斗”转变成“去希望”,虽谁都知道遥不可及,却鼓鼓在心头。
所以,伯格将希望归还给土地,如果这也算一种信仰,那么神明就在观看的同时被我们接近,这更像是一个原始的神话,人们被泥土捏造出来,人本主义的柔情就是关于创世的神话,神明在观看中,上帝之眼,为希望而开启。这也解释了为何本书的书名原文为“THE SENSE OF SIGHT”,不管伯格在谈论的是莫迪里阿尼的爱情还是土耳其庭院与自然的关系,他们最后都是“观看”统摄下的某种对土地,以及生长于土地之上的人们的崇敬,而它不至于跌入民粹主义漩涡的原因也正在于此,没有人会诟病一位摄影师或者一位画家是“民粹主义的”,如果真有龃龉,那么首先需要反省的反而是诟病者本人。
“有时候,我在夜里看到星星,特别是当我们出去抓鳗鱼的时候,我就在脑子里开始想,“这个世界,它真的是真的么?”我,我可不信。要是静下来的话,我会相信耶稣。坏嘴巴的耶稣基督,我会杀了你。不过,有时候我甚至不相信上帝:“要是上帝真的存在,他为什么不让我休息一下,不给我个活干?”
然后我记得我有了孩子,不能松懈了。可是,有些时候……找不到活干的时候,我的头就痛啊……
给青蛙蜕皮的时候,我觉得他们挺可怜的。可是我能怎么着呢,只能杀了它们。我可怜它们,但是它们得死。那青蛙瞪着我,知道死期到了。我把它抓在手里,跟它说,它没错。我怎么晓得咧?抓住它的两条腿,还没下剪刀,它就在你的手里撒下一泡尿——就像我们要碰上这样的事,也会这么做——还不止一泡。我就是这么知道它是怎么想的。”
我想伯格在观看和倾听的同时,内心还有“保佑”二字,保佑,不好不坏,它跟希望一样,没有即时降临,但也令人盈然。那天突兀地哼起张楚的老歌《上苍保佑吃完了饭的人民》,暗自思忖,其实这希望即爱。
《讲故事的人》读后感(五):听约翰伯格讲故事
一
约翰伯格的书,这是读过的第三本。第一本是《看》,第一篇描写动物和人的关系的文章就把我秒杀了。关于此本书,已经有写文章专门谈过,这里就不再赘述。很多的时候,我觉得,约翰伯格的书可以拿来背诵。第二本是他的成名作《观看之道》,先看了一半的英文原版,又去图书馆保存本室找中文版的看。记得最深的一句话是:“女性的风度在于表达她对自己的看法,以及界定别人对待她的分寸。女性的风度深深扎根于本人。”这句话,我想了很久,吃饭的时候,散步的时候,总之,在很长一段时间里,只要我不需要交谈,无需上网,即便我插上耳机,我都在想这个问题。有一刻,我终于想明白了。实际上,我们每天在遇到陌生人,自我介绍的时候,我们(指女性)是不是有可能不带任何偏见,不加任何修饰的仅仅叙述事件本身。比如说:我叫XXX,我来自武汉大学汉科高院。(就此打住!什么都不说,没有修饰,没有限定)而不是说:我叫XXX,我的学校不是很好。。。是个三本。。。我的家乡不是很好,很穷。。。结果,等你说了一大堆,糟糕的修饰涵盖了所有的陈述,却没有道尽事实真正的原委。你的过去到底有多不堪??
二
等我终于抽的开身开始读《讲故事的人》的时候,是在今晚,但也就是在一晚上的欢愉之后,发现,今天也同时是还书的截至日期,结果,我超期了。but who cares??
我读了其中的《伦勃朗的自画像》、《自画像》、《白鸟》、《索多玛城》、《大洪水》、《克劳德莫奈的眼睛》、《艺术的工作》、《绘画和时间》、《列奥帕蒂》、《每一天更红》、《讲故事的人》其中有一些是诗,有一些是艺评,相对来说,诗被译为中文,其原本的意蕴保留的就很少了。艺评就不一样,深刻的见地依旧还在,读着读着就油然升起一股佩服,这个世上,观察力强健,能深谙事物之间多重关系交织的核心的人不会太多,约翰伯格就是其中的一个。
三
留在记忆里最为深刻的一篇文章是《克劳德莫奈的眼睛》,因为莫奈(Claude Monet,1840年11月14日-1926年12月5日)是我所知道的为数不多的画家的其中一位。有很长的一段时间,我将莫奈的画作下载下来,作为桌面,但是每一幅画作停留在桌面上的时间都不长,从 《印象·日出》到《睡莲》,因为我发现长时间的盯着电脑屏幕看,我不会觉得有多开心,相反,有一种忧郁,不断的向你袭来,我想,大抵正是由于“不轻松”,我的潜意识就不断的帮我做出选择,不由自主,不断的更替,直到最后,决定不再选择任何一幅莫奈的画作作为桌面。
约翰伯格说,忧郁来自莫奈的眼睛,作为印象主义最执着、最不妥协的领袖,莫奈将一切颜色相对化,虽然场景是在广大市民的经验之内,但是场景却是临时、陈旧的、破败的。这是五家可归的景象,在其中不可能建立庇护所。
毫无疑问。莫奈描绘的是印象,是记忆,这是莫奈所有作品非公认的轴心。约翰伯格对于“印象”的解析实在是精辟:“对于非常熟悉的景物,你对它们没有印象。印象或多或少是短暂的,因为景色已经改变或者消失,印象是余留的。知识可以和未知共存,而印象,却只能独自娉婷。不论印象在当时是何等激越地、何等经验地被观察,它随后便无从验证。”这或许也解释了为何在长时间的凝视莫奈的画作之后,油然而生的是痛苦。
莫奈擅长使用光与色,但是,画的光与真实的光又有多么的不同,画的光不是透明的,画的光包围、埋藏所画的对象,宛如白雪覆盖的大地。于是,在画作中,真实是存在的,但同时,真实也被掩盖了。并且,很多时候,他所关心的不再是光所揭开的瞬间景色,而是被光缓慢融化的景象。一方面,莫奈用场景的精确性引发你的形象记忆,另一方面,以模糊性的承迎,容纳你所召唤起的记忆。这实在是狡诈?!一不小心,你便掉入了记忆的漩涡,你的所有感官的相宜的记忆都参与进来,你坠入某种感官记忆的漩涡,趋向于一个总在后退的愉悦时刻,一个彻底重新认知的时刻。
莫奈说:“主题对于我来说完全是次要的,我想要表现的是主题和我之间存在的东西。”有意思的是,作为观者,我们也只能孤零零的站在那儿,我们看印象主义者的画作,我们只能“被迫的承认它已经不在那儿了。”我们不能进入印象主义者的画,相反,它提取了你的记忆,deeply。
莫奈想要描绘的是记忆里的全部,因而它的画作是一遍一遍的不断画,颜色叠加的极为厚重,他想挽救的是所有近乎绝望的愿望,所以它的画时常是杂乱的,单调的,尽管回忆本身的内容是如此的丰富.
画家和观者都发现自己比以往的任何时候更加孤单,更加忧虑自己的经验是短暂的,毫无意义的.只有塞尚例外.下次,再论塞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