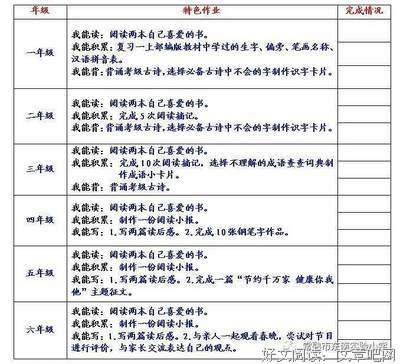
《明亮的泥土》是一本由[英] 菲利普·鲍尔著作,译林出版社出版的精装图书,本书定价:88.00元,页数:471,特精心从网络上整理的一些读者的读后感,希望对大家能有帮助。
《明亮的泥土》精选点评:
●颜色史,艺术史,科学史。就我读过的颜色论著,这部资料翔实,论证较严谨。延展书单:《颜色的故事》;米歇尔·帕斯特罗“色彩列传”三部曲《黑色》《绿色》《蓝色》与《善变的色彩》;《幽蓝之神》。另,文艺复兴与印象派、现代艺术(乔托、三杰等,所有的印象派画家,梵高、马蒂斯、毕加索、马克·罗斯科)。理论可参考康定斯基《艺术中的精神》。
●简直太好看了,虽然里面很多内容上课的时候都曾经听过,但是系统的看一遍效果完全不同。10/10。不一定赞同里面的某些观点,但是这类的书越多越好!
●用了大量的文字描述画作的颜色,不如多配几张图,说了很多废话
●历时一个月读完 值得认认真真每章写笔记
●唤醒并补充无数高三理化生知识……好枯燥但还是被科普了许多知识,特别是美丽的颜色名称。
●一部关于色彩的历史,作者试图从科学与绘画两个角度,来展现各种颜料的相关史实。两个方面平均用力,显然却两边也难讨好。
●颜料的制造需要技术,购买需要成本,用的时候需要调配,这些基本的物质属性,其实都是一个艺术家在创作时考虑的因素。
●非常专业也就是读起来吃力的意思
●整体这本书很不错,包括排版、插图一类的。但内容对于我来说太深奥了,没有很大的兴趣看下去。
●也是画师和颜料关系的演化史,依赖和摆脱同时存在,相互角力。
《明亮的泥土》读后感(一):无题
《明亮的泥土》这本书虽然从色料,化学(炼金术),艺术史的角度讲述,对于我获益良多的是带来了技法的启发,让我了解了罩然技法,以及以前的画师们都如何对待造型和颜色问题的,以及对于目前我们所见的真迹可能以前并不是那样,让我在进行艺术分析的时候,更加全面的考虑各种因素。
通过这种透彻但简要的语言,若不是对艺术史相当之了解,也绝不能写出这样的文字。
《明亮的泥土》读后感(二):2020-2
一本越读越枯燥的书…内容倒还好,按年代顺序书写颜料的发明与诞生,主旨在于科学创新与艺术表达之间的关系———更明确点,技术进步带来的艺术变化。里面的科学涉及化学、物理、医学,但是很多描写让文科生如我越读越困,越往后越触及我的化学盲区…知识不够,瞌睡来凑。
除了科学,颜料与艺术表达还涉及观念、语言。如:对古希腊人来说混色比原色低人一等(可能是因为偏灰偏暗的原因。
还探讨了黏合剂对色料的影响(水—湿壁画、蛋黄—坦培拉、蜂蜡—蜡画法
其实涉及了很多有趣的冷知识(比如湿壁画的画法、什么年代才有什么颜色、画作如何修复、摄影的原理、不同染料色料名字的由来……
但是因为插图太少、原理不解这本书我啃的很痛苦。
怎么撑过去的呢,全靠边看书边把看过的颜色罗列了一哈(足证我有多无聊):
❤️红:辰砂,红铅,胭脂红,茜草红,巴西红,洋红,刚果红,
《明亮的泥土》读后感(三):“色”艺双全 | 评菲利普·鲍尔《明亮的泥土:颜料发明史》
在文博探索节目《国家宝藏》里,第一件与观众见面的国宝是《千里江山图》。北宋天才少年画师王希孟采用了极其复杂的“青绿法”,细腻描绘出江山色彩幻变的绚丽景象,观之令人着迷。这幅画的颜料来之不易,基本都是从宝石、矿石以及中药材中研磨、清漂提取而来。红色来自赭石,绿色来自孔雀石,青色来自蓝铜矿,白色来自砗磲。这些源自矿物质颜料的装饰在历经千年之后依然夺目,一时竟分不清首先看到的是“色”的美,还是“形”的秀;画作的色彩和形式在此时难分伯仲。
然而,在中世纪的西方,绘画被视为一种低下的手工技巧;在古典时代通常由奴隶完成。即使在达芬奇与他的画家同行们强烈申辩着应将用颜料创造的美丽图画,像诗一样归入博雅艺术时,艺术家仍然有别于创造和研磨颜料的匠人。英国化学家兼科普作家菲利普·鲍尔在自己的著作《明亮的泥土:颜料发明史》里结结实实地为颜料的发展摇旗呐喊,“让调色板上的无名英雄列队登场”。
在19世纪,化学合成颜料出现之前,艺术家们就是靠着研磨从地下挖出的包含金属元素的矿物获取颜料。创作之前为找齐颜料东奔西走乃是常态。“铁是红色的,在血液和铁锈中,在石器时代以来的画家们涂抹的红赭石中,都有着夺目的红色。铜为自己选定的是与铜这种矿物相近的绿松石色,这一点从老化的铜器上微绿的铜锈中便可窥见一斑。富丽的深蓝色让人想到钴,镍是海绿色;铬则让人有些拿不准,它是元素中的变色龙”。时光流转,彼时难觅的珍稀颜料随着化学工艺的蓬勃发展,到现在几乎都是合成的有机分子。在古代和中世纪,只有区区十几种天然染料具有足够的稳定性而适于应用,到了今天,已有超过4000种合成颜料。如果现下闲来想作幅画,再也不需要家里有矿般奢侈了。
从颜料制作的发展可以窥探艺术与科学并非截然不同。而众多颜色经过艺术家所在时代观念和文化的加持,呈现出更加富余的意象。就如圣母画中无所不在的蓝色长袍,是德行的象征。而黄色,在中国文化里是帝王的颜色,是皇权的象征。作者在本书中倾囊相授,把颜料涉及的科学、艺术、文化领域面面俱到;倘若能耐下性子,细细读来,想必能使每一个领域的爱好者都能有所收获。
《明亮的泥土》读后感(四):明亮的泥土,淡淡的忧伤
颜料,无论是拿来绘画还是染色,作为材料,“利用它创作”的多半是有一定专业技能的人士。不过,最终欣赏和使用其“成果”的,却是我们普通百姓。
当“成果”摆在我们眼前的时候,作为材料的颜料已经面目全非。
比如一件颜色漂亮的衣服,或一幅色彩美妙的画作,当我们面对它时,最多的是惊叹它制作的技艺,却很少去思考背后那些已经“变了形的”颜料,因为我们已经“看不见”也“认不出”它来了,更不要说去思考发明材料制作材料的人了。(就连分析艺术史的书籍也往往对此忽略。)
《明亮的泥土》就是菲利普·鲍勃给这些“背后英雄”立的传。它是一部讲述颜料发明史的艺术类科普读物。除了讲述颜料的身世,还讲了“和颜料发明制作相关”的人。
作者没有以自己化学家的身份,生硬地给我们灌输化学公式,也没有单纯地把颜料拎出来跟大家分析。
作者从我们熟悉的绘画作品入手(偶尔穿插染色),一边带我们“看”画,一边以讲故事的形式给我们说什么是颜料,是谁最先发明的,哪种颜色被最先发明,颜料怎么被运用,颜料的辉煌时刻以及古今颜料的成分变化等等,一直讲到20世纪的创新颜料。
跟随作者,我们从古代洞穴壁画一直“看”到当今新材料创作艺术品,把整个西方绘画史都重温了一遍,而且是加了“化学眼光”去温习的,这真是一个奇妙的经历。
但是, “看着看着”,心情也低落起来。“没有哪位艺术家画过在时间中凝固的图像。”“时间这个画家,它不停变化的画布。”面对几百年前的画作,其实“我们没有看到艺术家画的是什么。”颜料随着时间的流逝变化了,掉落了,无法修复了。
《寓言人物》里的人满脸开裂,像拼图一样。《阿尔伯马尔伯爵夫人安妮》中伯爵夫人苍茫的面孔。
虽然作者以化学有段,通过“样品吸收的波长”,通过测光拍照法,通过“湿式”法,通过显微镜等等,“看出”破损变色的颜料最初的模样(他应该就是用这样的手法才能跟我们分析颜料发明史)。在我们的眼里,它还是脏兮兮,充满裂痕,只能脑补它刚出画室时的绮丽。
画家准备好了而颜料的制作技术没有跟上,这真是一件让人忧伤的事。
留下画作的画家已经不知道这些遗憾,尽管很多画家创作当时也再努力避免这事。作为后世的颜料制作者(或化学家)却依旧把它当回事。
20世纪,艺术家们已经把目光投向各自新材料,用新材料去创作。但是颜料的研发始终没停步,制造商们仍在努力,就算现在的颜色名称已经从成分标记变为色相标记。
“20世纪制作的钛白,覆盖能力比铅白强两倍,并且极为稳定。它还降低了制备铅白导致的中毒发生率。”“色彩丰富且高度稳定的有机化合物”被发明,“再也不用担心红色的未来了”,“工业领域的更大关注会最终把这些颜色带入艺术家的市场。”
这本来听起来很振奋人心,但是,发明了成百上千种颜料,也只是“用种类上的多样性弥补应用广度的不足。”各种新材料被发现,各种创作方法被应用,颜色退居二线,20世纪的最后几年里,我们已经无“画”可看。颜料制作已经准备妥当,而画家缺席,这又是一件令人忧伤之事。
尽管作者说,“20世纪绘画中有太多的伟大之处,世纪末的几年暗淡下来又有什么大不了的?”“艺术之道就是找到途径来利用技术所提供的东西。”
就算近几十年画画的人很少,技术总是在为艺术家准备着,“技术为艺术家打开了新的大门”,他们时刻准备“把闪烁着光亮的新工具献入梦想家手中”。
梦想家们会怎样先不去预设,就这一点,让我们忧伤的心上抹了一点明亮。
(晚了一天无法上传的习作,郁闷的放这里,等有心人帮批~谢谢!)
《明亮的泥土》读后感(五):时间这个画家
面对一幅年代久远的名画,我们为之所动的,除了所画的内容、画中的色彩、画家的技法、投注的情感和秘而不宣的寓意,无疑还有观看者对当年作画场景的想象以及时间在画作身上的留痕。尤其是,某些画作历经千百年,辗转于多人之手,几番遗失又复面世,命运流转曲折离奇,让人感叹不已。本书讲述的主题是颜料发明以及偶然发现的历史,更是在讲述位于颜料、画作和画家背后,无声而有力的时间的故事。在时间的舞台上,画家的调色板、炼金术士的坩埚、科学家的棱镜,以及艺术家与画材商的歧见、梦想家与手艺人的协作,乃至科学与艺术之间的相互辉映,无不跃然纸上。
作者菲利普·鲍尔在书中说,“没有哪位艺术家画过在时间中凝固的图像”,所有绘画都是永恒的过程。当画家放下画笔、收起颜料,在完工的画作上签下名字时,时间的工作就开始了。即便在画家谢世,归于尘土之后,时间仍像一位热心的修复者,不辞辛劳地重塑着色彩,改变画作的色调对比,甚至遮掩起画家运用色彩的本意。表面显而易见的污垢、斑驳与龟裂,只是在外观上打下的印记。更为深入的,是具有不同化学性质的颜料承受时间的能力,或者说是它们的耐久性。
在绘制于1440年前后的《炉栏前的圣母子》中,圣母那宽松的长袍曾经是紫色,由于所用的色淀颜料褪色,现在变成了白色。使中世纪和文艺复兴时期的画家暴露在这种危险中的,除了色淀,还有朱砂。朱砂的变暗“早已为古人所知”,所以,庞贝古城的朱砂墙板上覆盖着蜡来提供保护。红铅则更不可信,暴露于空气中时,如果不用上光油加以保护,则会迅速变暗。即使是身为画家宠儿、性质极为稳定的群青,有时也无法避免衰变,使祭坛画中的长袍变成不祥的蓝黑色。随着年代增加,铜绿也会变暗,甚至如丹尼尔·汤普森所说,是“灾难性”地变暗。普鲁士蓝曾被寄予厚望,结果同样表现出明显的褪色倾向。
时间不仅会改变画作,使其失去最初的荣光,另一方面在时光的长河中,也有更多的颜料涌现,大大地丰富和扩展着画家们的调色板,虽然它们有时只是某些化学过程的副产品,甚至与炼金术士不无关联。在作者的笔下,颜料诞生的故事徐徐展开,引人入胜:公元前2500年左右,埃及人将石灰、氧化铜和石英按严格的比例混合,制成流传至今的埃及蓝。中世纪的炼金术士发明出工艺,极为艰难地从蓝色矿物青金石中制成了浓郁的蓝色群青。16世纪,银矿工发现在白垩上洒下硝酸铜溶液,白垩会变成绿色,于是就有了碳酸铜蓝。18世纪初,出于节约,迪斯巴赫使用被动物油污染过的钾碱来制作胭脂红色淀,结果偶然发现了普鲁士蓝。19世纪,锌的冶炼又为艺术家带来了锌白。20世纪30年代,单星蓝和锰蓝登场,曾经身为中世纪色料女王的群青一朝失宠,黯然落魄。
除了颜料,还有属于不同画派,风格和性情迥异的一代代绘画大师们,在时间里、在这本书中来来去去。在这里,传说中古希腊的阿佩利斯用色朴素,调色板上只有黑、白、红、黄四色;在这里,达·芬奇和他的同行们努力为绘画正名,想让绘画成为与几何、音乐、修辞平起平坐的博雅艺术;在这里,偶像破坏者梵高的内心世界涌动着“人类的可怕激情”,用色彩表达出令人晕眩的力量;在这里,友善的毕沙罗第一次见到梵高时,就断定这个荷兰人“要么会走向疯狂,要么会把印象派远远地甩在身后”,最终这两点梵高都做到了,随后安息于一片阳光明媚的玉米地;在这里,莫奈作画时同时在几件作品之间飞奔,直面风雪和潮汐,想要抓住珍贵的瞬间;在这里,高更远赴热带,停留于塔希提岛,希望在“狂喜、平静和艺术”中生活,尽管那里颜料匮乏;在这里,多亏了一张颜料订单,仅此一次,毕加索调色板上的那些无名英雄从暗影中列队走出。
人是一种特殊的动物,时光的流逝会在其内心堆积起惆怅和伤感,又或者召唤出温柔和喜悦。不仅是个体人生中的往事,人类整体的遥远历史亦然,这大概就解释了人在发现童年旧物时内心中难平的心绪,以及摩挲钟鼎、亲见商周时那浓郁的怀古幽情。这也解释了画作真迹的不可替代,解释了为何如作者所着力描述的,今人如此不避繁难、殚精竭虑地去修复原作。如本雅明在《机械复制时代的艺术作品》中所说的,复制的艺术品,无论如何完美都缺少一种成分:艺术品在那个时间和那个地点,在它问世之处的独一无二、无可替代的性质。那是艺术品反身在时空中打下的烙印。
滚滚的时间长河,多少帝王将相运筹帷幄、征战杀伐,妄图“江山永固”,如中文版序言中所写,甚至有人想通过服用辰砂而长生不老,如今都已化作青烟,落入尘土。而艺术家们的那些画作,却有相当的比例流传了下来,珍藏在世界各地的美术馆或博物馆中,由专门的团队修复和保护,供人观看和遥想。当你了解到,为了让这些艺术珍品有机会在不同的地方展出,各收藏机构之间为“借展”而在保险、人工和协调方面所付出的巨大努力时,更是不由得肃然起敬。走笔至此,脑海中蓦然跳出一句话:“天上的神明与星辰,人间的艺术和真纯,我们所敬畏和热爱的,莫过于此。”
(刊于2018年6月2日《晶报·深港书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