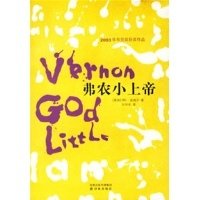
《弗农小上帝》是一本由[英国]DBC·皮埃尔著作,译林出版社出版的平装图书,本书定价:25.00元,页数:313,特精心从网络上整理的一些读者的读后感,希望对大家能有帮助。
《弗农小上帝》精选点评:
●守望者弗农
●语言很有个性,属于典型西方风格,拉拉杂杂
●2003年布克奖获奖作品
●看了三分之二依旧不知所云,翻译很差,那些出彩的句子也提不起再读下去的兴致
●这书...很粗糙.我不知道是不是翻译的失误.最后扭转命运的竟然是一泡大便.哈哈哈
●真复杂。
●看不下去
●每页都是黄幽默和冷嘲讽……不是我喜欢风格,没读完……
●只要扒开那些撩拨人的比喻句,其实你会发现作者和他所嘲弄的那帮人在某些程度上有着惊人的相似。仅仅由自身去想象他人,还带有相当多的(但隐蔽得尤为巧妙的)自我可怜。关注我吧!关注我吧!我似乎从头到尾都听见这样嘎吱嘎吱地叫喊!关注我吧!而且***只能关注我一个人!——虽然这样说,但我还是心甘情愿地被作者写下的每一句话给诱奸了!(在邻近结尾的时候放弃了这本书。)
●弃书
《弗农小上帝》读后感(一):劣迹斑斑的小伟大
年纪不大的皮埃尔依靠这部小说得了布克奖
他很乐意暴露自己的劣迹
四处流浪
吸毒,赌博,欺骗朋友的房产
小说的主人公弗农仿佛来自《麦田里的守望者》
谁叫《麦》是我的最爱之一呢
果然,当我看完第一页,我就知道我会喜欢
“我在学习这个世界的处世之道上是不遗余力的,我甚至隐隐觉得我们会有灿烂辉煌的日子,这真是天知道。然而厄运终究临头了,我原有的隐隐的预感不复存在。我的意思是——这是***什么生活?”
昨天刺梨向我推荐日剧《在世界的中心呼唤爱》
他说日剧远远超过韩剧和国产
因为日剧走现实路线下手也很残酷
他说,你赶紧看完,然后告诉我你写不写那个偶像剧
我目前正在看《弗农小上帝》
这消息真不知是好是坏
吸收了这么多又残酷又愤怒的东西之后
还写得出中韩合作的呕像剧吗
其实都是废话
为了肉体和精神需要
人什么整不出来
《弗农小上帝》读后感(二):侏儒的拳王金腰带
西闪/文
忽然觉得手中的几本新书有某种相似之处。一本是《弗农小上帝》,小说,译林出版的。一本也是译林出版,卡尔维诺的《为什么读经典》,可称之为随笔。另一本是曼古埃尔的《阅读日记》,和《为什么读经典》有些类似,华东师大出版社出版。可是这三本书究竟有何共同的地方,我一时不知道是什么。待我拆开《为什么读经典》那可憎的塑胶包装,我才明白,这三本书为何相似:腰封。它们都在封面上缠着一条腰带式的纸条,据说,这叫腰封。
《弗农小上帝》的腰封上写着:“《弗农小上帝》注定要成为《在路上》和《猜火车》这些小说中的一员,它是另一本《麦田里的守望者》。”“注定?”这种语气真是古怪,古怪得像一个相信宿命论的广告商人。
卡尔维诺则围上了“回车诗”的腰带:“经典是/每次重读都像初读那样/带来发现的书/经典是/即使我们初读也好像是/在重温的书”,看来作者是一个中学时深受格言毒害的“梨花教”外围成员。
相对而言,《阅读日记》的腰封上所写内容和华东师大出版社的定价一样朴实:“阿尔维托·曼古埃尔的私人阅读,继《阅读史》之后又一力作”。可是,为什么现在的书都莫名其妙地有了这么一个玩意儿:腰封?起广告的作用?难道一个理智的读者会通过它,而不是通过翻阅书中内容来决定买或者不买一本文学类书籍?
在我看来,这毫无必要的腰封就像一条镶金嵌银的皮带,只会让人显得粗俗。我记得有一本《相约星期二》,那腰封太宽了,已不能以皮带来形容,上书几个大字:“余秋雨教授推荐及作序”,让我联想起壮阳益肾的神功元气带。而另一本名为《千年悖论》的书腰封上偏还腆然印上:“新生代挑战余秋雨”。这样的书,不知道在书架上能不能立起来?
也有些书的腰封不像暴发户的皮带,倒像威风凛凛的软兵器。比如《揭密红楼梦Ⅱ》的腰封上就写满了刘心武的言论:“上央视是我决不放弃的公民权利”、“讨论《红楼梦》请不要以专家身份压人”等等,很有点“小心,地雷”的意思。
还有的书腰封就更加难看了,有的标榜“与朴树的第一次”,整本书却几乎与朴树无关。有的则赫然印着“韩寒迄今最满意的里程碑式作品”的字样,一副盖棺论定的模样。
不由地,我眼前浮现如此景象:一群侏儒,争相围上了泰森、霍利非尔德和刘易斯的金腰带。
《弗农小上帝》读后感(三):青春期黑色意外有关整个世界的黑色惯性
虽是作者的处女作,但也是2003年布克奖得主。这次写作很任性,但连珠炮一般出现的绝妙比喻已经表露出作者非同一般的黑色幽默,让你无法不联想到《猜火车》或《两杆大烟枪》之类的意象。或者说,是关于黑色青春期的。
故事非常有针砭性。发生在校园里的一场枪击案中,墨西哥孩子打死了数位同学后,饮弹自尽——如果这么一说,想必大家的神经都要紧张起来,的确这是足以写成《冷血》那样的题材,有大量失血镜头,有案发后人们的颠狂困惑和追问不已。但作者恰恰没有这样写,甚至直到第21章节、也就是临近结束时才将那个场面一述而过,几无细节。
因为立场站在一个愤世嫉俗的男孩弗农身上。他是枪手墨西哥男孩的唯一的好友,他在案发现场、又没有参与,他甚至也有一把枪。所以,故事一开始他就成了众矢之的,是嫌疑犯,甚至……成了所有本县发生过的谋杀案的潜在嫌疑犯。
这孩子满口脏话,喜欢用耐克球鞋把人群分类,有一个胡里胡涂的单亲母亲,而母亲有一群毫无原则可言的肥胖姐妹,她们的日子就在炸鸡块、减肥药、吹牛皮中度过。这孩子痛恨这一切,总在心里追问“这是什么生活啊?”他的尊严告诉他,要逃跑,但忘记给予他足够的理智(或者说,处事之智),因而他始终没有说出足以澄清罪名指控的小秘密。
在这个孩子眼里,世界不仅是没有公正可言的,还是足够荒唐和卑鄙的。他不是被“误认”为杀人犯,也不是被“陷害”,只是被充盈世间(媒体和人群)的对罪恶的愚昧的狂热所玩耍。在指控未成立之前,他的身边早已是众叛亲离。在这种孤独下,他的愤世嫉俗、乃至他的傻几乎都可以被理解。 小说的结尾秉承整本书的风格,完美地画上一个黑色咧嘴冷笑的句号,看起来,谁都没有太多损失,甚至所谓正义。
《弗农小上帝》读后感(四):成为上帝前请加入黑色的游行队伍
读完时眼睛佝了。
或许是一件不甚了了的梦盘旋了一阵累了要落脚,所以似乎是心有戚戚的在图书馆旧架子里把它重新找出来。9月一天也是这么放回去的。
冬天把我摧残到几乎要和一个伙计发火了。这股罕见的无名之火震惊了我自己,以至在漆黑的睡梦里我一直看到一条红色的长长警报在跳。我很想对他说,我忍你很久了,你对生活的无动于衷让我发狂。但绝对不是这么回事。我是说,再恶毒的屎盆子也绝对扣不到远方一个带着一副永远也拆穿不了的不被击倒的假象,把漠视和悲哀合为一体泰然自若地活了好多年并将接着活下去的人的头上。
半路的弗农常说:我是想说,这是***什么生活。
弗农小上帝一直像burn after reading那样喋喋不休,不是拿枪对着你就是把人变成各色的垃圾袋拎到你面前打开展示直到堵满你的大肠。这节奏很让我消化不了。读的很不顺畅,放弃一次还想放弃。但你不能。作者自取笔名DBC,意为DIRTY BUT CLEAN。他试图证明了所有脏的污秽的存在都是必要的,因为那里总有一点消化不掉的真的柔情,前者是供消化的,后者是供储存的。大便拉出来了,弗农获释了。
我一直在一张废纸上记着后者出现的页码。后来可以拉成一条斜线了。直到280页,狱中的弗农对他老妈说:别熬夜等他。
如果干了老妈的情人是把自己亲手送进监狱的阴谋刽子手,这个假设如果在弗农以外的世界存在,多半会即刻切掉它的手脚,通过流水线迅速处理成1分钟滚动的社会新闻。像外科手术一样不计后果。世界早已不足为奇。将它扩大多少讲述的倍数都阻挠不了重蹈覆辙,残喘苟延的生活大军。在这点上,弗农的叙述多半都是无意义的。谁都可自认为弗农。然而让弗农成为上帝小弗农的,是上帝一直会一直会化身为邪恶直到他认为上帝就是他自己的那一天。
我对那位伙计和自己已经不生气了。
When I was a young boy,
My father took me into the city
To see
a marching band.
He said,
quot;Son when you grow up, will you be the saviour of the broken, The beaten and the damned?"
He said "Will you defeat them, your demons, and all the non believers, the plans that they have made?"
ecause one day I leave you,
A phantom to lead you in the summer,
To join the black parade."
------------My Chemical Romance's “Welcome To The Black Parade”
《弗农小上帝》读后感(五):被污染的世界
弗农小上帝
另一个美国人写的另一本《麦田里的守望者》,这听起来并不是一个好主意。当年,J.D.塞林格写完那本使他名扬世界的书之后,凭借着巨额版税销声匿迹,用铁丝网和狼狗来对付记者,并且逐渐由一个“青春小说写手”变成了短篇小说大师——《九故事》的优秀,使纳博科夫这样古怪、挑剔的水瓶座知识分子也不得不为之心悦诚服。然而我们不能期望每个“另一本《麦田里的守望者》”的作者都具有相同的志向和能力,并且,说到底,《麦田里的守望者》所表现出的才能,配不上它给塞林格带来的名气。无可避免,文学史就是这样一本充满了争执和耳语的乱帐。
《麦田守望者》的青春体验和对青春期愤怒的不自觉表演欲,都被这部小说完整地继承了下来。除此之外,这本书其实更容易让人想到梅勒的《刽子手之歌》:并没有多少塞林格笔下美国东部那种繁华浮丽的都市气氛,贫穷、荒凉、混乱反而是小说中世界的主要景观,而媒体和法律的介入仍然保持了一贯的冷漠无情。在这样的环境里,人们加之于弗农的一切都属正常。和那个当真因为愤怒而开了杀戒的加里·吉尔摩不一样,弗农并不生活在富有同情心的70年代;和塞林格的小男孩霍尔顿也不一样,他身上没有一笔巨款以供挥霍。作者的结论是,他什么也不能做,除了无望地逃亡,在逃亡中品尝更多的无望,并且最后被抓获。是否赏给弗农一个喜剧结局其实并不重要,因为从之前的情节已经能得出一个明确的结论:弗农只能任人摆布。所有不厌其烦的意识描写,虽然在小说的神经末梢上,保存了一丁点希望和敏锐,但仍然是对整个世界无能为力的。如同他的老师纳尔克斯所说,“乞丐无权挑选”。
可以肯定的是,即使给弗农杀人的机会,他也不会下手。这并不是因为善意,而是由于厌倦。在美国校园杀人案频仍的背景下,这一类行为已经成为了在摄影机前豁出生命的自我表演——试图参与塑造真实世界的“超真实”。而弗农想要的并不是关注,只是一个女孩儿,是她身上“湿透了的硬纸板和凝结变质的牛奶所发出的刺鼻气味”。一方面这是妥协:对一种极其传统的中产阶级“爱情”观的盲从,宛若小说结尾时好莱坞电影般的场面;一方面,在这个女孩儿和弗农之间,保存了一种基于情欲的微弱的神秘,对应于弗农唯一的可取之处:敏感。
这是整部小说唯一的“出口”:未免太小了。和塞林格在《麦田守望者》中用“你只要一谈起,就会想念起每一个人来”的单纯少年世界观来对抗整个成人世界相比,更绝望,也更多妥协和苟延残喘的气味。小说中经常提到“刀子”,“好比我才生下来时她就在我背上插进了一把刀”:弗农首先把这个词用在了他母亲身上。对于引领他进入这个世界的人,使用了办公室政治一般冷酷的语汇,那么他对这个世界的态度也就可想而知。毫无疑问,这是一本“社会批判小说”。这是典型的美国小说,苦涩、自嘲、不安于现状和听天由命混合在一起。然而在这部小说中,自嘲中的幽默和智慧已经被无奈和无力取代了大半,听天由命的顺服淹没了反抗的欲望,城市背景中嘈杂的市声盖过了主角的正义感、情欲、求生欲,污染着一切。
这是一部关于被污染的世界的小说。也许作者不这么认为,因为他极少向我们暗示:世界“原本”是什么样子的,除非通过女孩。正因如此,我倾向于把它看作一部比《麦田里的守望者》更“自传体”的小说:它尽管在描写上看起来热闹、丰富,却带有自传特有的自说自话的封闭感,对描述世界缺乏野心。2003年,这样一部小说获得布克奖,这多多少少说明了文学的“主流”标准在其他艺术媒介的挤压下,正在朝一个什么样的方向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