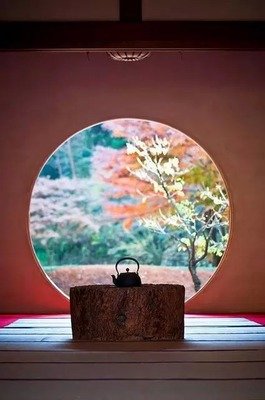
《周作人译文全集》是一本由周作人 译 / 止庵 编订著作,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的精装图书,本书定价:1880.00元,页数:7100,特精心从网络上整理的一些读者的读后感,希望对大家能有帮助。
《周作人译文全集》精选点评:
●饱经风霜者形如枯槁……不喜欢。
●价格很惊悚,只缺其中的1/10,各种纠结,最终半价弱入手。虽然编校质量有争议,但全壁难得,续盼日记与书信全集
●只读了译自日文的部分。怎么不出单行本呢?
●心向往而不能及
●止庵功德无量
●M
●2014年入手的。硬壳不是很自在。书本身内容不错。第六卷里的《平家物语》其实缺少了周作人自己的序一篇,不知为何止庵把它给拿去了。我到现在、受了豆瓣的影响,也因为自己的喜好,还是将钱稻孙与周作人的古典译文排在王座之上。真的,就是再也看不上其他后出者。
●《古事记》。最近都读不完全本,《枕草子》看来算是对日常表达审美和赞叹的早期文本了。
●我心中最尊敬的现代文人! 我必须买这套书籍。。。。
●翻译水平没的说。非常喜欢希腊四卷,此后的六卷选目则不是很合胃口,日本卷太清新,而欧洲卷又太过苦大仇深。第十一卷文言一本未读,一是有些审美疲劳了,二是留待老来好好玩味吧。
《周作人译文全集》读后感(一):蛮喜欢的
马上要有事去,这个人我还是喜欢读的,他的文章我小时候就比较喜欢读,尤其的他的文笔我是比较喜欢的,记得小时候虽说有些还看不懂,但买的第一本书就是周作人的,这个更加要看看了。这个外文全集值得拿来研读一下,重温此公的风采。
《周作人译文全集》读后感(二):周作人译文的风雅
有一本周作人的散文集《雨中的人生》,陪伴了多年。青绿的封面,很简单的样子。却和封面一样,内容也有些清冷了……
《锵锵三人行》和止庵的访谈,又一次提醒了我。提醒了对周作人的记忆,那个《枕草子》里最风雅的文字。
仿佛山野淡泊的风,不热烈、不激越,却正正的写出了很多人生的意味。
11本书,师傅送来时夹着的一整箱。一大纸箱,却见他轻轻巧巧……于是,认为,它的重量也是可以忽视的。
结果,公司的走廊我只走了一半就不得不停下,重的呀。用尽全力,分两次才放至自己的坐位。
打开,是质感厚重的书。青灰色的里子,厚重的纸盒包装。精致……而全国第一版的理由,也足够让自己陶醉了。
我爱的书,不只是包装,更重要的是内容。
当沉溺已成习惯,爱书就成了本能。
我相信,我对周作人的印象。
我喜欢,枕草子 周作人的译句
第二零八段 日
日是: 夕阳。 当太阳已经落在山后的时候,还看得见红红的太阳光,有淡黄色的云弥漫着,实在是有趣。
第二零九段 月
月是: 蛾眉月好看。 在东边的山峰上,很细地出来,是很有趣的。
第二一零段 星
星是: 七簇星,牵牛星,金星,长庚星。流星要是没有那条尾巴,那就更有意思了。
第二一一段 云
云是: 白的,紫的,黑色的云,都是很好玩的。风吹时的雨云,也是很有意思的。天开始明亮时的云,渐渐地变白了,非常有趣。
‘早上是种种的颜色。’诗文中曾这样说。月亮很是明亮,上面盖着很薄的云,这是很有情趣的事。
这样的文字,不由地欢喜,买他的译作应该不需要理由了吧!
《周作人译文全集》读后感(三):第九卷两篇老鼠的儿童剧还有其他版本
看到《周作人译文全集》第九卷里收录了上海儿童书局1932年出版的《儿童剧》,前两篇是译自坪内逍遥的老鼠寓言,1923年7月、1924年1月曾在《晨报副镌》发表,译文本身没什么变化。1923年,北京师范学校的浙江籍学生发起越光社,出版《越光季刊》,沈懋惠(慰予)主编,定位为面向小学生和小学教员的读物。1924年3月,周作人把这两个剧本给《越光季刊》1卷4号再次刊出,为供小学生表演用,前面加了一段说明,还有手绘面具图,但未收入后来结集的《儿童剧》。貌似周的传记作者和文集编者没注意到《越光季刊》,这里补充一下吧。
《越光季刊》版《越光季刊》版对比一下《周作人译文全集》里使用的《儿童剧》版本:
《周作人译文全集》第九卷1932年版《儿童剧》第二篇《老鼠会议》,《儿童剧》里的版本去掉了角色扮演人选的说明。
《越光季刊》版《越光季刊》版《儿童剧》版《译文全集》内容同上《越光季刊》的宗旨和编辑人如下:
1卷4号1924年3月10日出版
附赠彩蛋一枚,黎锦熙用注音字母写给《越光季刊》的祝词,纯属鸟语……
《周作人译文全集》读后感(四):(转载)《新闻晨报》:北止南陈话知堂
陈子善:华东师范大学中国现代文学资料与研究中心主任、中文系研究员、博士生导师。致力于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史料学的研究和教学。曾参加《鲁迅全集》的注释工作。在周作人、郁达夫、梁实秋、台静农、叶灵凤、张爱玲等现代重要作家作品的发掘、整理和研究上做出了重要贡献。著有《文人事》、《发现的愉悦》、《说不尽的张爱玲》等。
止庵:读书人,散文家,周作人、张爱玲的研究者和作品整理者。他的著作《周作人传》,被公认是相关领域的权威之作。整理出版有《周作人自编集》、《苦雨斋译丛》、《周氏兄弟合译文集》、《张爱玲全集》。此外还著有《樗下读庄》、《苦雨斋识小》、《老子演义》、《如面谈》、《沽酌集》、《相忘书》、《茶店说书》等。
星期日新闻晨报记者 王娜 编辑
作为中国现代文化史上的著名散文家、翻译家与思想家,周作人一生著译传世约一千二百万字,其中翻译作品居一半有余。然而近半个世纪以来,周作人的翻译成就一直被遮蔽在他饱受争议的政治问题与其文学创作成就之下。与之形成鲜明对照的是,1965年4月,80岁的周作人在遗嘱中写道:“余一生文字无足称道,唯暮年所译希腊对话是五十年来的心愿,识者当自知之。 ”理解周作人的翻译成就,对于理解这个在20世纪中国文化史中的风云人物具有着举足轻重的意义。今年,由著名周作人研究者止庵历时十五载编订而成的《周作人译文全集》由北京世纪文景公司正式出品面世。这部全十一卷,七千余页的《周作人译文全集》,汇编了目前所见周作人所有将外文译为中文的作品。周作人译作时间上起自1905年《侠女奴》,下迄至1966年未竟之《平家物语》,跨度长达六十余年。 《全集》第一至四卷收录其古希腊文译作;第五至八卷为日文译作;第九、十卷主要为英文及世界语译作;第十一卷为用文言文翻译的作品。作为首次全面整理出版的周作人译文全集,书中近三分之一的内容自原书首版之后数十年来一直持续绝版;某些材料如第八卷“其他日文译作”中的《瞎子做梦》(总计一万余字)更是从未面世,此次是从四十三页的译者手稿首次排印。对于广大的文学研究者与爱好者而言,这些都是极为珍贵的新鲜材料。
近日,止庵与陈子善,一北一南两位周作人的研究者与作品整理者沪上一聚,结合《周作人译文全集》的首次出版,共话构成周作人一生文字的另半壁江山——周作人的译文及其对中国文学、思想与文化的深远影响。
周作人(1885-1967),浙江绍兴人,中国现代著名散文家、翻译家、思想家。一生著译传世约一千二百余万字。周译特色有三:一是选目,二是译文,三是注释。所译多为世界文学经典之作,如欧里庇得斯的悲剧,路吉阿诺斯的对话,《古事记》,《枕草子》,日本狂言和 “滑稽本”等,取舍精当自不待言。周氏精通古希腊文、日文、英文等多种外文,追求直译风格,自家又是散文大师,所译总能很完美也很自如地传达原著的意味。周氏为译文所加注释向为其所重视,在译作中占很大比例,不妨看作是对相关外国的文学与文化问题的重要研究成果,而他一生置身于主流话语体系和正统思维方式之外,保证了这些注释不受时代局限,价值历久不衰。
据编订者介绍,周译具有三大重要特色:首先是选目,其所译多为世界文学经典之作,如欧里庇得斯的悲剧,路吉阿诺斯的对话,《古事记》、《枕草子》,日本狂言和 “滑稽本”等,取舍精当自不待言。第二是译文,周氏精通古希腊文、日文、英文等多种外文,追求直译风格,自家又是散文大师,所译总能很完美也很自如地传达原著的意味。第三是注释,周氏为译文所加注释向为其所重视,在译作中占很大比例,不妨看作是对相关外国的文学与文化问题的重要研究成果,而他一生置身于主流话语体系和正统思维方式之外,保证了这些注释不受时代局限,价值历久不衰。
一点题外话
陈子善:周作人作为20世纪中国文化史上的一个重量级人物,这不是一般重量级的人物,是特别重量级的人物。他的文学生涯无非就是创作和翻译,老一辈的作家当中相当多的,像鲁迅,既能翻译又能创作。周作人活的时间比较长,所以翻译的作品特别多,有11卷,等于是从他走上文学道路到最后结束始终跟翻译打交道。他这个翻译有从古希腊文翻译,有从英文和世界语翻译的,面非常之光,也说明他的视野非常之广。止庵兄编这套书是从头读到尾,但是我没有从头读到尾,但是就我读过的感觉真的是大家的翻译。举一个简单的例子,日本古典名著《古诗集》的翻译,把他跟后来的定本比较,周作人反复修改,精益求精。有的作品原来用文言翻译,然后再用白话翻译,这里有很多值得我们讨论的一个很重要话题,就是周作人为什么要翻译这些作品,他有他很严格的选择的。所以,我想如果你想真正了解世界文学,了解整个人类文学发展脉络的话,有一个很好的选择就是读周作人的翻译。我先讲这些。
止庵:谢谢陈子善老师,陈老师是我的启蒙者,周作人启蒙陈老师,陈老师启蒙我。这本书得了好多朋友的帮忙,今天跟各位聊,我不太想就这本书跟大家讲书有什么好,我觉得书的好坏刚才陈老师都说的,我跟大家说一点题外话。
第一个话题想跟大家说说周作人跟外语的关系,我觉得这是有意思的一个事。
周作人他的学历完整念的书只有一个,就是江南水师学堂,他是一个水兵,严格说是教海军的。他怎么去学呢?鲁迅考过一次,周作人考过三次都没有考上。当时年轻人能走的路,在绍兴这个地方一个就是科举,这路走不通,那怎么办呢?或者是教私塾,或者是当师爷。当时已经有了新的事物,已经有了洋学堂。学堂这个词,因为他们有一个叔祖在水师学堂督学,在那里是一个有身份的人,这个人先把鲁迅介绍过去了,然后再把周作人介绍过去,他们就分别先后进了水师学堂。鲁迅学了半年就退学转学了,周作人来的时候是一个插班生。他有一个叔叔也在这里当学生。周作人当时去先住在叔叔家,这个叔叔教了他英文字母,他学会字母之后,水师学堂是五天英文教学,一天中文教学,他上的第一课就是英文课,因为他叔叔教了字母之后他居然能听这个课了。而且他在水师学堂当学生期间出版了两本书了。周作人确实是有外语的天赋的,这个水师学堂相当于现在的专科学校,他在学校毕业已经出版了两本译著了,他的英文就是这么学的。
以后他到日本上了一个速成的日文班,他的日文就是在这个班上学的,他在日本生活过五年,更多是从日文和生活中学的,鲁迅先去日本当然对他日文也有帮助。以后日文和英文成为周作人主要翻译的语言。而他生平更重要的一件事是学习了古希腊文,因为1949年以后他在翻译方面的贡献,其实主要还是古希腊文,他晚年就是靠这个。周作人在日本上了一个礼教大学,他只读了一门课,就是古希腊文,是在真正的大学里学的,但是没有毕业。他干嘛要学古希腊文呢?因为他先跟章太炎学了古文,章太炎是古文大师,在日本开了一个班有8个学生,周作人从章太炎学了古文之后想把圣经译成中文,从希腊文把圣经直接译成中文,虽然最后没干成但是学了这门本事。他也曾经想学法文,后来说学法文不能当饭吃,所以没有学成。1920年代他想学朝鲜语,但是也没有学成,他学了世界语。以后这几门就成了他主要的翻译语言。那么特别在1949年以后他能够安心做翻译这个事情。下面我想请陈老师讲1949年以后周作人的处境。
一个特例
陈子善:1949年以后周作人回到北京,这个比较有意思。当时他从监狱放出来,已经判刑的可以提前释放,他放出来回北京交通是中断的,他就到了上海。上海有朋友接待他,都是他学生辈的。当时有一些人去看周作人,跟他接触,就是在那一段时间比较频繁,而且在大家眼光里看周作人是落难。等到大势已定才回到北京,因为他的家庭全在那里。他刚回去也很忐忑,他是没有底的。当时上海有一家小报叫《野报》,《野报》办了以后向周作人约稿,《野报》的负责人比较喜欢周作人的作品。周作人在解放初这一段时间给野报写了大量的小品,这一段生活主要靠稿费维持的。
他生活当时确实不是很好,所以在这样的情况下,他给中央写信,一方面为自己以前做解释,另一方面说可以为中国做一些事。这个时候最高层批示说这个人可以用,可以请他翻译外国文学翻译。在文学界里面尤其是五四时候那一代人对周作人还是非常尊重的,因为他毕竟是那个年代的领袖人物。1950年代以后,以翻译为生的人在北京、上海都有,你翻译一本书交到出版社他就给你一笔稿费。周作人这样还可以预支稿费,他靠这个维持生活,但是他没有工资,我们今天有一个名词比较流行,叫自由职业者,他当时就是自由职业者,靠自己的一技之长。他如果不懂古希腊文就麻烦了,因为懂日语的人不少,当然很多人没有他翻译得好,但是毕竟别人也可以翻。可懂古希腊文的屈指可数,也就三四个人。而且当时有很多特定的任务,所以有这样一个特定原因的。他当时学的时候没有想到这一门本事后半辈子可以用得上。
后来50年代中期,鲁迅纪念活动,上海纪念活动都登周作人文章,但用的是周其仁的名字。
止庵:我们看周作人1949年的文章基本没有新作,他翻译的东西没有一个是赶现实时髦的书,这是一个特别奇怪的例子,也是一个好玩的事。那个时代突然有一个人在孤岛里面默默干事,周作人在1966年曾经写过一封信给(徐徐),他说我有十几年时间能把一心想译的东西翻译。周作人是有可能去香港的,假如他当时像张爱玲或者其他人那样去了香港,看看当时香港真是文化沙漠,不太可能译古代文学,没有人给他钱,他译了也没有办法出。所以周作人真是一个特别的特例,能够就这么一本接一本译,又是自己想译,按自己想译的样子翻译出来。而且都是古典的名著。这个是我要跟大家讲的一个特别的特例,是任何人没法效仿的。
陈子善:这个人非常有定力,我们现在讲的浮躁,这个词对周作人根本没有用,他非常有定力。
止庵:这个人的一生,我问过他家人,他整个一生都是几点钟起床,然后上午工作到几点,中午吃完饭在凳子上休息,到下午几点钟开始工作,晚上很早睡觉,一生都是这种活动。贝聿铭写过一篇文章,一般我们收到信急急打开,但是周先生一般是拿剪子剪开编号再看,他家里的整洁,特别是到他晚年,他还是保持这个,整个生活规律没有改。
陈子善:他们兄弟俩都是这样,非常认真。鲁迅给人家寄书也是包得非常好,做任何事情都是非常认真,周作人也是这样,翻译也是非常认真。
止庵:他的手稿都是工工整整,全是毛笔字,这么多书他是拿毛笔字翻,修改的时候清清楚楚。这套译文集现在是11卷,有八卷译在1949年以后,还有一些丢了,五六十万字找不到了。周作人1949年是64岁,他译到81岁,这个书有八卷完成于64岁到81岁这个期间,这个真是不可想象的。
陈子善:这等于我们现在是退休以后重新开始人生。
止庵:而且基本上他当时身败名裂,什么都不是,然后他再重新做。同时还有一件事,他家人生活得非常不幸,周作人的太太到晚年臆病很重,认为鲁迅和周作人都是多妻,怀疑周作人是不是有什么问题,整天在闹。周作人日记里面天天都是不能工作,太太很闹了等等。书都是在这样的状况下翻译的。而且整个家庭的收入主要靠他,收入不稳定,派出所还动不动说你要写一个什么汇报和简历。此外鲁迅研究者也找他了解情况。所以他生平这一段时间生活是很不好的,不是说物质方面,而是精神方面很不好的状况。他收入并不低,但是整个一家人都靠他养,而且没有公费医疗。
我跟大家讲,我们的前辈文化人,比如鲁迅、周作人、胡适、张爱玲都是非常非凡的人物。鲁迅每天写七八篇文章,周作人一天写十篇以上。我看到人民出版社给他写信说你交的量太多了,你不需要交这么多。我们讲民国范,其实民国人的定力和他们本身的才能以及他们整个对待人生的态度是现在人很难达到的。
陈子善:周作人那一段生活,还包括经常有人会去找他,有的纯粹是把他当一个百科全书,问他什么都知道。有的人看他出版一系列关于鲁迅的书之后请教他,纯粹是功利性的目的。另外还有些人读了周作人的书以后,感到他的文章还是很好的,愿意去找他。周作人对这些素不相识的还是非常周到。
止庵:他们周氏兄弟对于普通人都是很好的。
陈子善:你这个时候找他你真诚对他,他也真诚对你。张铁真是中学老师,他经常看周作人,帮周作人做一些力所能及的事,他讲起周作人就很有感情,他把周作人看成活生生的人而不是符号或者是什么?不是,就是一个活生生的人,完全打破我们僵化的思维。这是很难得的,在那个年代可以想象,在外面这样一个大环境中还有一些不失赤子之心的人。
止庵:1949年之后周作人跟外面的一些联系也是非常好玩。1949年之后,他跟日本、香港的文艺界联系很密切,比方说他要在日本买很多书,包括买好多吃的。这个人实际上对于生活的要求是很高的,但是高不是说咱们说的奢侈。比方说香港有一个人,姓包,他的任务就是帮周作人买很多食品,包先生生在日本,他说很多周作人要吃的东西他都不知道,他得去找。还有周作人要买很多书,他们的通信里面也有很多关于国内时兴的议论。周作人实际上是很特殊的一个现象,一方面他是一个很被冷落的人,一方面又是很被关注的人。他当时的情况不是我们想象的那么可怜,但他同时又特别边缘。我觉得这是一个跟大家能够聊的一个话题。
一流的译者
止庵:还多说说他们早年翻译的情况,周作人一生最走红的时候是1920年代,现在这套丛书有两卷是在这个时候译的。五四以后咱们所谓新文化运动,周作人主要身份有这么几个,第一是翻译者,然后他是一个理论家、评论家。首先他是翻译。他翻译什么呢?周作人和鲁迅他们在1909年出过两本书,就是《意外小说集》,这是他们最早翻译外国新的作品。这本书特别遗憾,我也不知道为什么在1909年的时候中国文艺界没有任何的反响,我觉得这是新闻史特别大的一件事,他们翻译新的文学,主要重点在短篇小说。这个事情当时不成功,但是到了五四以后他们重新把这件事情重新做成了。当时周氏兄弟主要的贡献是翻译,我看鲁迅当时写东西,咱们说太有名了不能只给一个杂志写东西,他是分别给三家报纸写东西。当时他们的兴趣在新闻学,周作人转向古典。
我给大家提一个事情,就是周作人遗嘱的事。周作人在1965年写了一篇遗嘱,他说我的一生文字无足称道,只有暮年所译希腊对话是50年的心愿。就是说我这一辈子写的东西不值一提,只有是晚年译的儒家集是我想译的。这个书有一点意义,因为是译者想通过这个东西把自己一生思想表达出来。周作人对于儒家评价是“非圣无法”,周作人这个人从性情上很平和,但是思想上特别激进。“非圣无法”是他自己一生思想的定论。我们追究思想根源往往倒是他可能对于我们既有的思想和道德规范不承认,包括气节这个东西我们觉得很重要,他觉得不是事。实际上这个人思想很激进。他身上有两个鬼,一个叫身世鬼,一个是流亡鬼。周作人好多挑战传统的做法其实从流亡鬼出来的。他确实给我们那个时代提供了一个例证,这个时代是非常特殊的时代,是值得我们关注的时代。
再有一点,这套书里面的注释,11卷作品,把周作人写的文字去掉,可能连一半都没有,顶多一半。这里面有大量他的注释,他晚年因为没有人找他写关于古希腊悲剧的书,他就把这些都搁在这本书里面。他翻译古希腊悲剧的时候弄了好多神话方面的研究。再比如翻译《枕草子》,他将对于平安时代人们生活的研究也放在那里。
陈子善:像周作人这样的人物,他留下这么多文字,代表了那个时代国人对西方文化、日本文化的认知,这是值得花时间整理的,这个需要是要有魄力的,未必有很好的经济效益,但是是文化积累的基础。周作人花那么多时间、精力翻译这样的作品,如果我们不加以整理和出版,也对不起这些先辈。周作人在1920年代是非常重要的人物,尤其他的文学批评。我举一个例子,《成文》这本书出版以后受到批评,作者觉得很委屈,说你们对我的批评完全曲解了我的作品,他就把作品寄给周作人,给周作人写信说请你批评,如果你认为我的作品不行,那我也认了。周作人读了以后,专门写了一篇文章,做了一个非常好的评价,肯定这部作品。这人有一言九鼎的作用。这样的情况很多,五四的时候很多年轻人都把他看成一个领军者。我们都不能忘记周作人,无论是他的翻译还是创作,你可以不喜欢周作人,但是你不能无视周作人的存在。
止庵:即使是1949年非常特殊时期也没有无视他存在。
陈子善:他始终在写他的东西,翻译他的东西,而且无论是写还是翻都是一流的,这一点就够了。
原文地址:http://newspaper.jfdaily.com/xwcb/html/2012-09/09/content_878457.ht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