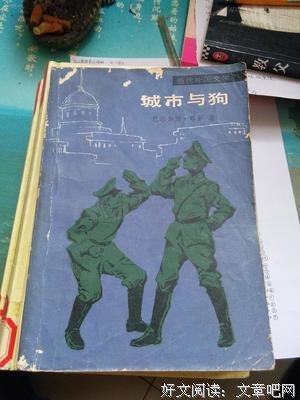
《城市与狗》是一本由[秘鲁] 马里奥·巴尔加斯·略萨著作,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平装图书,本书定价:45.00,页数:425,特精心从网络上整理的一些读者的读后感,希望对大家能有帮助。
《城市与狗》精选点评:
●结构很秀,但是翻译赵德明翻译的太差,严重拖原著后腿,什么水平啊!
●纯碎片化、多视角、多时间线的叙述手法,故事性很强。对美洲豹的执着,对奴隶的悲哀,对阿尔贝托的怜悯,以及对那帮士官生种种混蛋行为的厌恶,都随着结尾那云淡风轻的发展破灭了。这就是成长么,泯然众人矣。不知道那只瘸腿的母狗和博阿怎样了。
●其实看到最后我发现美洲豹的语言无比纯洁,谁能相信呢,最顽劣的美洲豹
●前半部在叙述方式上创新,后半部逐渐回归传统的叙事,像两个人写的。情节上运用了一些推理小说的技法。最后的部分把不同空间不同时间的对话连在一起,却丝毫不显凌乱,反而非常流畅,足见作者功力。
●给叙事结构跪了
● 略萨的叙事行文结构毋庸置疑的整饬清晰 叙事节奏鲜明舒服 美洲豹 诗人 奴隶 3个男人在结尾最终巧妙的和一个女人串联起来 人物的觉醒力道十足 !大家
●你的二十岁在哪里?在干嘛?身边美洲豹,奴隶,阿尔贝托嘛?
●时隔将近四年重读 依旧是我最喜欢的作品之一 每一处若隐若现的情感 每一次冲突 不同场景和叙事间的切换 堪称完美
●残酷青春。
●特别棒,到目前为止,今年读的最好的一部小说~拉美文学对我就是充满了吸引力呀!!! 小说里的叙事手法充满了浓郁的福克纳风味(时时让我想到了《喧哗与骚动》)这也是我喜欢这本书的原因。略萨叙事的文笔和节奏感真好,读起来特别能身临其境。
《城市与狗》读后感(一):天地不仁以万物为刍狗
22岁略萨的长篇处女作,虽说成名要乘早,那也得有料。略萨得益于19岁跟胡丽亚姨妈结婚,早早就拥有了一颗老灵魂。这不仅仅是一部校园青春小说,略萨向普拉多军校横向切了一刀,解剖了整个体制、社会、人性,诗人经此一役对秘鲁彻底失望逃离去美国,去做一个精致的利己主义精英。美洲豹虽说是个杀人犯,但读者对他肯定恨不起来,敢爱敢恨、个性鲜明的他既冷酷无情又有情有义,原生家庭的无奈、蠢萌的初恋、成长转变的心理历程都能让人共情。最终告别真诚残酷的骚年,改邪归正并娶了绿茶婊初恋,略萨下手虽狠,但总会给爱情一个温暖的结局。正直的中尉勇于挑战体制做一个吹哨人,结果是体制没起半分波澜,自己却被发配高原,仕途再也没有晋升的希望。要论初心,他才是一个理想主义者,但在那样的体制下却成了一个不知变通的傻瓜,一个loser。不能不说以上校的角度他是果断老练完美地处置了一起黑天鹅事件,而且处置结果除了死者奴隶和拎不清的中尉,对大家都好。只不过这样欺下瞒上的官员越多,对国家是幸耶悲耶?也就没人关心了。读完你就知道,略萨为何对独裁政府嫉恶如仇、痛心疾首。再一想,类似的事情不是每天在发生嘛,有过之无不及。这个故事写的是秘鲁,好像也发生在全世界:是过去的事,好像也发生在现在、将来。我们都是博阿的那条狗。4星+1星。
《城市与狗》读后感(二):直到最后我们才会发现,所有的曲折和坎坷,原来都是道路上过程。
你既不是美洲豹,也不是博阿。在很长的一段时间里,你是奴隶阿拉纳,甚至没有像阿尔贝托这样的朋友。
到最后的尾声,你也觉得可以理解了吗?甚至,可以释怀了吗?他们原来和你一样的怯弱,一样的不知所措。但你一定还是心怀不甘,挥着感到怨恨吧。
毕竟这是多么不公啊,为什么要用你这样弱小、卑微、无助的可怜人来冒充所有人的敌人呢?
美洲豹到底悔悟了,他的悔悟是因为奴隶之死?或者因为诗人阿尔贝托的正义和勇气打垮了他?二十岁确不是最美好的年华,他是愚蠢的、羞耻的、盲目的、易于冲动的、追悔莫及的,也同样是单纯的、真诚的、不知所措的、勇于面对的。
阿尔贝托放弃了从朋友那里抢来的爱人,因为这是他唯一能够为他做的。他曾在左右摇摆的时候选择了她,当奴隶死了,当愧疚、怜悯与痛苦来临时,他又做出了第二次选择——你的抉择总会伤害一些人,不是他人,就是自己。
至于美洲豹呢?他做他一贯的事,做他大概唯一最好的事。现在他消除了偏见,继续坚持和坚定。我们不能谅解他对阿拉纳犯下的罪行,不能原谅他的隐瞒。但既然没有人愿意将他审判,我们只好把过去和未来的评判,统统交给上帝吧。在这里略萨终于动了恻隐之心,他让诗人与美洲豹与特莱莎再不相见。
但可怜的阿拉纳呢?坚定的倒霉的甘博亚中尉呢?莫非我们需要一些牺牲才能够相互理解?大概,青春是容易受到感动的,但固执的青涩的内心总需要一些痛楚才能够真正死触动。
至于博阿与他那条受到虐待的母狗,他们终于同病相怜了,受虐者和施虐者原本是同一个物种。
关于略萨在城市与狗中的写法,我还能说些什么呢?用一句话来总结吧——直到最后我们才会发现,所有的曲折和坎坷,原来都是道路上过程。
《城市与狗》读后感(三):《城市与狗》还是“城市与我”?
《城市与狗》是略萨早期的作品,开始写作本书的时候略萨还只是个二十多岁的毛头小伙子,但是在那个年纪便有要写作这样一本书的愿望以及将其付诸实现的强烈冲动,略萨不可不说的确是个难得的文学奇才,就和才华绝代的兰波、马尔克斯一样。少年即老成的文学思想以及成熟的小说技巧在那个年纪的略萨身上体现出来,也在他最初的小说作品中体现的淋漓尽致,其中,《城市与狗》就是这些作品中完美的典型代表。
《城市与狗》算是一部青春感伤小说,但是绝不是国内某些蹩脚的三流作家所写的那种青春感伤小说,而是真正触及到少年灵魂深处的一部作品,是和《麦田里的守望者》与《少年维特之烦恼》可以相提并论的著作,但和上述二者所不同的是,《城市与狗》所表现的社会生活的广度与深度是它们远所不能企及的。相较来说,《麦田里的守望者》更多的是侧重于少年时期的叛逆描写以批判现实,《少年维特之烦恼》且只是单纯地写出了少男爱情受伤之后的感伤状态,而就故事的精彩程度来看,这两部作品有也难以和《城市与狗》相提并论。
《城市与狗》讲述了几个少年的不可思议的军校生活,这本书开头便以惊心动魄的偷试卷开始,“圈子”老大“美洲豹”怂恿山里人卡瓦去偷化学测验的试卷,但是卡瓦不小心打碎了一块玻璃,这样军官们便知道了试卷被偷的事情,但是无从查起,只能罚全体不许外出,但是“奴隶”阿拉纳却为了能够尽快出去去见他暗恋的对象告发了卡瓦。最后事情被“美洲豹”发现,于是他借一次演习的机会杀死了“奴隶”,而学校当局为了名声未调查此事,直接将这次奴隶之死定义为他自己杀害了自己。“奴隶”的好朋友阿尔贝托为了给奴隶报仇,又将奴隶的死因及士官生们私底下背着军官们所干的事告诉中尉甘博瓦,正直的甘博瓦不顾一个个上级的反对非要将调查报告上交到上校手中,最终上校抓住阿尔贝托的把柄逼迫他撤销了对“美洲豹”的指控。事后甘博瓦被当局调到了边防哨所,临走前“美洲豹”告诉他确实是自己杀死了奴隶,并让甘博瓦把他上交给上校,只要这样做他就可以不要去高原上服役,甘博瓦没有照做,二人经过了一番漫长的交谈之后,甘博瓦提着一个笨重的箱子走向了去往远方的道路。
故事的讲述过程远远比这样简单的介绍要精彩得多,全书有四个线索,分别以阿尔贝托、“美洲豹”、奴隶以及另一名“圈子”的成员博阿的角度讲述,第一人称与第三人称交叉叙述,看似十分混乱,实则井井有条,细腻的心理描写夹杂着意识流的味道缓缓而来,使读者洞察人物的内心世界,略萨被称为结构现实主义大师,其实是没有任何争议的,他用他的独特的叙事技巧讲出了一个又一个精彩的故事,早已征服了全世界的读者,而且日后他在小说叙述艺术方面的探索一直没有停歇,二零一零年的诺贝尔奖授予他,可谓是实至名归,要知道和他差不多时期的马尔克斯早在将近三十年前就已将诺奖收入囊中,《城市与狗》和《百年孤独》是同一时期发表的作品,同是拉美文学爆炸运动的中流砥柱。
在整个故事中,奴隶是所有人格格不入的一个,士官生和军官是两个对立面,士官生内部没有人不欺负他,所有人都看不起他,他们对他极尽侮辱,只是因为他不打架不翻墙外出不和其他人一样谈论下流女人。最初阿尔贝托和其他人一样欺侮他,但是在一次夜晚交谈之后两人莫名其妙的成了朋友,阿尔贝托不再欺负他,也不允许别人欺负他。阿尔贝托绰号“诗人”,因为他具有其他士官生所不具有的编写小说的能力,他给别人写信和黄色小说换取钱财,因此得名“诗人”。“圈子”最初是刚入校的时候由全班全体组成的反抗五年级对他们“洗礼”的组织,在一次开会时被甘博瓦中尉发现后强令解散,随后美洲豹又组织起了四个人的“圈子”,成员包括美洲豹、山里人卡瓦、博阿以及没有存在感的鲁罗斯。阿尔贝托总是和“圈子”保持着一种若即若离的关系,而奴隶则是被所有人抛弃的敌对分子,因此当美洲豹知道是他告发了卡瓦之后动了杀心。而奴隶外出去见的那个女生他也没有见到,她的名字叫特莱莎,这个女人将三个男人联系在了一起,奴隶暗恋她,阿尔贝托外出帮奴隶传达消息时又爱上了她,而她正是美洲豹未上军校之前当小偷时所交的女朋友,但她是个好女孩儿。 小说取名《城市与狗》,但是小说中只有一只狗,它的名字叫玛尔巴贝阿达,是军校里面的一只流浪狗,后来被博阿收养了,博阿对这只狗有着特别的情愫,虽然他也欺负过它几次,但是他对它比对人好多了,他能在这只狗身上找到被爱的感觉。玛尔巴贝阿达是否象征着什么?还有那只军校里面的小羊驼,它们是动物,但是它们竟然是这个学校里面最善良的。在军校里面,军官们伪善的面孔、卑鄙的手段,还有任意解释规定的行为,这不免又有了一种“第二十二条军规”的意味;士官生们可以说几乎无恶不作,但是从这几位主要人物身上看来,他们更多的是年少轻狂的放纵与霸道,人性之中的善意还是足够的,但是,迟早有一天,当他们成长为这个国家所谓的支柱,当他们到了军官们那个年纪,是否还会一直善良下去?其实,军官们只是这群小伙子们未来的样子,一切都只是时间问题。
略萨向全世界展现了利马这座城市的多个方面——光着脚在街上踢球的孩子、售卖烟酒的小商店、呻吟声迭起的妓院、通宵营业环境脏乱的酒吧,还有晚冬薄雾笼罩下朦胧的米拉芙洛尔大街上若隐若现的树枝,他没有过多地卖弄技巧,而是将笔触到秘鲁这片土地上面的一草一木,将目光放到利马街头肮脏的角角落落,一个个血肉之躯在那些杂乱无章的房子里生活着,世世代代,永不断绝。秘鲁既是美国也是中国,还是赞比亚和阿尔及利亚;利马既是纽约也是北京,更是卢萨卡与阿尔及尔;而城市与狗,也是城市与我,千千万万只狗,千千万万个我。
《城市与狗》读后感(四):略萨,大玩现实的魔方!
揭露军队的丑恶、政治的腐败、人民的悲苦?听起来就很无聊,没劲!不不不,略萨的处女作《城市与狗》会让你改变想法。
大多数作家在写作生涯开始时,都从短篇入手,即便是写作中篇/长篇,也不免在结构、语言、节奏、腔调上显得或生涩或矫揉,略萨却让你不得不相信天分这件事。初涉文坛,一出手就是洋洋洒洒四百多页坚硬、厚实的内容,而且略萨似乎特别钟爱写作这种“砖头”小说,可以说他的小说“分量”是与拉美历史成正比的。在疯狂多产的创作生涯中略萨不仅将拉美历史的厚重感跃然于纸上,更独树“立体结构现实主义”一派,把现实主义文学推向了另一种极致。
《城市与狗》刚创作完成时,科塔萨尔曾读过小说的手稿,他说“当时那本书叫《骗子》,后来他改了书名。那本书使我眼花缭乱,我建议他立刻出版,我甚至可以尽一臂之力。后来,我依然怀着非常钦佩的心情读巴尔加斯·略萨的作品。我认为他是一位杰出的小说家。”虽然,科塔萨尔认为略萨的语言中缺乏一种幽默感,但它的优点依然是巨大的,并称略萨是“世界一流作家”。(《科塔萨尔论科塔萨尔》)
在这本处女作中,略萨调用了“奴隶”阿拉纳、“诗人”阿尔贝托、博阿、以及“美洲豹”的视角组织起一个腐坏的军校和拉美社会。由于在叙事中蓄意打碎了故事的时间和空间,并借由不断切换的“主观视角”来观察整个事件的发展,因此这是一部“半成品”小说——略萨只完成了创作工作的一部分,而另一部分则需要由读者来完成。写作者将一堆零散的故事碎片转交给读者,随着阅读的不断展开,读者不得不将每一片新鲜到手的零部件拼凑到叙事版图上,阅读心理也在这个“建造”过程中跌宕翻腾。
这种创作方式有趣的地方就在于将读者“悬搁”(此处为字面上的意思,有别于现象学的“悬搁”概念)。传统的小说叙事在开篇几页就能把故事的背景、地点、人物、人物关系以及主线情节交代清楚,读者脚下迅速聚拢了涉足的基石,沿着文本铺平的路线翩然滑行。比如:
《茶花女》——“随着女主人的离世,她生前的种种秘事早已无从追寻。这些贵妇们乘兴而来,却只看到她死后留下拍卖的物品,没法儿知晓她生前的卖笑风流......”(2016浙江文艺出版社/白睿<译> )这是一个讲述某位妓女生前悲惨命运与爱情故事的小说;《傲慢与偏见》——“凡是有财产的单身汉,必定需要娶位太太,这已经成了一条举世公认的真理......有一天,班纳特太太对她的丈夫说:‘我的好老爷,尼日斐花园终于租出去了,你听说过没有?’......‘租尼日斐花园的是个阔少爷,他是英格兰北部的人’......‘噢!是个单身汉,亲爱的,确确实实是个单身汉!一个有钱的单身汉;每年有四五千榜的收入。真是女儿们的福气!’......一个女人家有了五个成年的女儿,就不该想到自己的美貌啦。”(2006上海译文出版社/王科一<译>)这一定是个关于婚配问题的故事,一个叫班纳特的太太想给自己的五个女儿找个有钱的好归宿。《雾都孤儿》——“从小奥利弗·退斯特这个例子可以看出,一个人的服饰真是法力无边!他本来裹在一条迄今为止是他唯一蔽体之物的毯子里,既可能身为贵胄,也可能是乞丐所生;旁人眼光再凶也难以断定他的身价地位。现在,一件旧的白布衫(因多次在类似的情况下用过,已经泛黄)套到他身上,他立刻就被贴上标签归了类。从此,他就是一个由教区收容的孩子、贫民习艺所的孤儿、吃不饱饿不死的卑微苦工,注定了要在世间尝老拳、挨巴掌,遭受所有人的歧视而得不到任何人的怜悯。”(2006上海译文出版社/荣如德<译>)《小妇人》——“年轻的读者们可能想知道‘她们的相貌如何’,我们愿意此刻给这四位在薄暮中坐着编织的姐妹画个小速写......玛格丽特是四姐妹中最大的一个,十六岁,非常俏丽,体态丰盈,皮肤白皙,大大的眼睛,一头柔软的棕色头发,甜蜜的嘴巴,一双她相当引为自豪的玉手。十五岁的乔身材又瘦又高,肤色黝黑,使人联想起一匹小马,因为对于她那很碍事的瘦长的四肢,看来她不知该怎么办才好。她长着一张坚定的嘴,一个好笑的鼻子,还有一双犀利的灰眼睛,这眼睛好像能洞察一切,有时厉害,有时有趣,有时深思......”(2012上海译文出版社/洪怡、叶宇<译>)......
然而,当传统的现实主义写作开始显得板滞、沉闷,读者对于人物命运、新奇事件逐渐缺乏耐心时,作者们不得不为小说的创作寻找一种新的步调和语言。维多利亚时代的小说在新世纪的动荡下被更新锐更先锋更具实验性质的现代主义小说所取代。文学家和文论家们开始重新思考作者与读者之间的关系,罗兰·巴特甚至在《阿斯彭》杂志上发表了《作者已死》的论调,在这篇文章中他将“意义和符号挂钩”的责任全部交给了读者,他认为作者不再拥有近似于神的权威。美国小说家约翰·巴斯在《大西洋月刊》上发表了题为《文学的枯竭》的文章,认为我们传统所理解的“小说”潜力已被耗尽,小说必须要寻找一种新的可能,以重新焕发活力。
文学创作的重点从”what to say”(说什么)转向了”How to say”(怎么说),当内容已经不再新鲜时,使用新鲜的讲故事手法让读者重新获取新鲜感是现代主义小说的重要特征。在精神分析理论的刺激下,许多作家选择向内追索,发展意识流派;而略萨则选择对“现实主义写作”进行重塑,在这个重塑过程中略萨独创了“通管法”和“对话波”的写作技巧。
所谓“通管法”即“将不同时间、不同地点发生的事件以及其中的人物和情景联系在一起。”“对话波”则是指将一组核心对话投掷到文本中,由“对话”推动“对话”,“从中心蔓延开去,一个涟漪接着一个涟漪,每个涟漪都是情节的一部分,都是由一组对话或若干组对话构成”(《结构革命的先锋》孙家孟)
略萨、马尔克斯因此,略萨的作品往往喜欢把读者悬在半空,通过作者喂养的破碎文本点亮散落各处、并不相连的孤立光点,读者既看不清地质的起伏变化,也无法确定身处的地缘关系,只能在蛛丝马迹中不断参详揣摩:这好像是根牛角......啊!不对,是大树的枝桠......咦?好像是艘巨轮的桅杆。在反复的推倒重建中,才姑且拥有了相对稳固的“立足点”。
由普鲁斯特、乔伊斯、伍尔芙、福克纳所形成的意识流,更强调某种“一维性”的心理体验——将时间、空间、物理和精神统统融化进意识的流动中,略萨的结构现实主义则呈现出一种鲜明的“立体感”,写作者在不同的维度上自由穿梭,叙事从一个平面忽然跳跃至另一个平面。过去、现在;外在、心理;略萨非但没有将这些元素熔于意识之一炉,相反,他通过从一个平面跳荡到另一个平面以强调界限的存在,让我们看见“叙述阴影”。在每一个叙事平面的背后都有阴影,它遮蔽或扭曲了一部分现实。如果说意识流就像莫比乌斯环融合了各个曲面,那么结构现实主义就像帕提农神庙,释放出恢弘、森然的立体感。略萨企图让人们看到事实的“方方面面”,360度无死角地透视、侧视、正视,因此,就连他笔下的对话也如曹衣出水,稠叠层出。
略萨的这种“立体结构现实主义”的写作方式让许多人觉得“头疼”,而在《城市与狗》中他甚至将“叙事视角”也纳入到“通管”的范畴中来,不仅遮蔽了事件发生的时间和空间,更通过遮蔽第一人称叙事的主角创造出“意料之外”的戏剧效果。《城市与狗》的大部分篇幅都采用“阿尔贝托”的第一人称视角来剖白军校的生活,同学的遭遇以及他和同学的关系。这其间穿插着军校学生阿拉纳、博阿等人的第一人称视角,他们的叙述丰富、补充甚至推翻了部分阿尔贝托的说辞。在他们自白式的叙述中我们知道了阿拉纳暗恋校外的一位女生“特莱莎”,由于遭受处罚不得外出,阿拉纳委托好朋友阿尔贝托向特莱莎进行解释,阿尔贝托却借此机会插足其间,和特莱莎成为秘密恋人。
随着阿拉纳的死去,叙事中突然出现了一段很奇怪的第一人称“回忆”,讲述家境贫困的“我”为了给心爱的特莱莎送礼物而找朋友借钱,最后为了还债,接受朋友的邀请去当小偷。叙事者完全没有给出任何标识身份的信息,而在此前出现的几位叙事者中,“家境贫困”的只有阿拉纳,读者被“障眼法”欺骗,认为这是死去的阿拉纳借由作者之手继续展开回忆。直到整本书行将结束时,军校中尉甘博亚约“美洲豹”在校外见面,会面结束后,文中写道,“他一面向悬崖边上走去,一面把纸片撕成小小的碎块,一路撒光。经过一座住宅门前时,他停住脚步张望。这是座大宅第,里面有个很宽敞的花园。他第一次盗窃就是在这个地方。”是的,正是这漫不经心的几个关键字“他第一次盗窃就是在这个地方”,一下子推翻了前面长达几十页读者所建立的信念,不是阿拉纳请特莱莎看电影,不是阿拉纳送特莱莎礼物,也不是阿拉纳为特莱莎沦为小偷,是“美洲豹”,原来爱上特莱莎的不止有阿拉纳和阿尔贝托,还有“美洲豹”!
尽管略萨野心勃勃,力图用五色妙笔还原“现实”的方方面面,但这种宽容似乎仅止于男性人物。从政治家、财阀、军官、士兵到普通底层,略萨的“立体主义”让男性显露出既残暴又仁慈的一面,而那些女性角色却被他的如椽大笔凿成了铁板一片,她们都被罩上了“欲望”的标签,几乎无一例外地成为勾引男性邪恶本性的“原罪”。他将夏娃和引诱她逾越雷池的蛇等同起来:她们是同谋,一起诱惑亚当偷食了“禁果”。她们就像耶洗别,像希罗底,是淫娃荡妇,是白花花的胸脯和丰腴的大腿。在这种男性的“立体现实主义”视角下,是“特莱莎”引发了故事中的关键悲剧,是交际花“奥登希娅”(《酒吧长谈》)贪婪地斡旋于权贵之间,搅浑政治泥潭。
在略萨所描绘的世界中,从政府到家庭,你能看到青年人对权威如稚子般驯顺,看到父亲对母亲肆意痛殴,看到某种温和、柔顺的秉气不容于社会土壤。在这块崇尚暴力和阳刚的土地上,他们鄙夷任何散发着非暴力的“阴性”气质,甚至褫夺他们的存在,扼紧他们的喉管。这便是阿拉纳成为“奴隶”并最终被杀害的原因,女性的声音则直接从叙事管道中被彻底抽离。我不知道这种女性声音的“绝迹”是略萨有意为之或是偏见的暴露,但我们的的确确能从他的作品中感受到对“阴性”的赶尽杀绝。
在阅读过这位“结构现实主义大师”的作品,经历了一番和文本的“殊死搏斗”后,有谁能相信这是一位文坛新秀的处女作呢?拉美结构革命的作品的确不好读,正如科塔萨尔所说,当文学跨入新时代后,作者们不再期待与“阴性读者”的互动,他们不再千方百计地试图迎合、吸引读者,相反,他们对读者有着更高的要求,并发起挑战。面对挑战,我想任何有勇气的读者大概也都不惧涉险闯关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