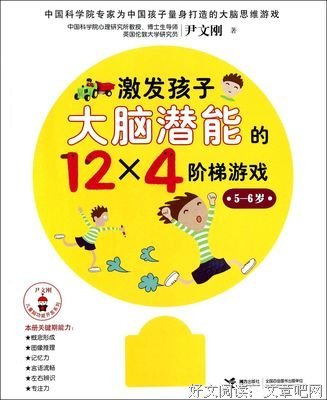
《发掘新闻》是一本由[美] 迈克尔·舒德森(Michael Schudson)著作,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的平装图书,本书定价:22.00元,页数:246,特精心从网络上整理的一些读者的读后感,希望对大家能有帮助。
●便士报真是个神奇的东西,一方面培育了民主市场社会,相信“事实”而不是相信“价值”的理念,进而滋生了对客观性的信念和新闻专业主义;但是这个时代好像也是封闭的私人领域被打破,被侵蚀的经济权力由扩大的政治权利(扩大的选举权)来补偿,专业编辑出现,基于私人领域的公共性被大众传媒制造出来的公共性取代的年代呢。
●1、首先你要熟美国史;2、然后你得被舒德森大神虐三遍以上才能召唤神龙;3、学渣答:“这本书主要讲了美国的新闻专业主义核心客观性的来源发展和展望,通过社会学视角。”大神回:嗯哼,然后呢?【十脸懵逼
●仔细看还是有软脚的地方。不过这种史观在当时新闻学里也算先进了吧……
●从大一读到大四,从最初的完全看不懂和(傻逼的)轻视到现在的敬佩……
●还是有不少逻辑断链的地方呀
●对新闻“客观性”的不一样的解读。过去我会认为,在新闻专业主义中,客观性是一种令人向往但难以到达的追求,但是每一个从业人都应该抱有这样向着它前进的自律准则,尽量避免偏见和意识形态的左右。而这本书告诉我,“客观性”理念本身就成了一种意识形态。既然人人都知道客观性无法真正达成,那为什么还要如此强调?书中提到了对它的质疑。目前,市面上有不少教材都会提到,新闻的“真实性原则”,简单的套路很容易被学子出于考试的目的而接受,因此这本书有了很大的推荐必要,除了它在学术上提出的讨论外,还有对新闻新鲜人的一种提示。
《发掘新闻》读后感(一):相见恨晚
看完了《发掘新闻——美国报业的社会史》。有相见恨晚之憾。这本书深入浅出,史料翔实,论证精细,非常适合新闻学爱好者或入门者读,迈克尔·舒德森的其他作品,如《新闻社会学》及《为什么民主需要不可爱的新闻界》也属于入门读物,生动细致,发人深省。
《发掘新闻》读后感(二):全新的视角:社会史
从作者的论述中可以发现,客观性理念并不是一个真理性的存在,它不单纯是一个道德上的要求,它的出现是需要许多社会基础的。新闻界中有关客观和主观的争斗一直没有停歇,如同美国两党相争,一方唱罢我登场,很难说是客观主观理念推动社会的变革,还是社会变迁导致理念的换面。我更倾向于社会建构论的视角,即它们都是互相建构,互相影响的,可能存在一个时间顺序上的先后,但并不代表先出现的一定决定后出现的。
纵观全书,作者虽然将绝大篇幅,或者说全书最精彩的论述之处给到了对新闻客观性理念的探索,但我们并不能对其他精彩部分视而不见。关于报业史,甚至美国新闻史的专著数不胜数,在历史梳理或原因解释方面比此书强的也不少,但这本书之所以受到如此推崇的原因,我想还是在于提供一种相对于那个时期(70年代写就)更新奇的解读方式:社会学视角,即使此方法放置今日都不会过时。挖掘一个东西,既要从内部探索其结构,也要从外部环境提炼它诞生的必然要素,而社会学视角的切入便是从外部入手。所以我们能看到此书新奇的表述方式:先丢出从各种报刊、书籍、相关人士的话语等事实依据来表达一种新闻界的趋势,于是提出一系列疑问,比如这个现象为什么会产生、它是如何依附于新闻人,成为一种理念的等等。接着就进行他大量的社会背景的阐释,有意思的是他的社会学解释依然是对各种事实材料的罗列,从各种信息中寻找蛛丝马迹来印证自己的观点,而非我们熟知的直接罗列研究者本人得出的观点,所以我在众多材料和论述中提炼他的论点颇费功夫,有点侦探破案的既视感哈哈。这种表述方式某种程度上更客观,显得有理有据,但同时也会容易得出不同的观点,因为对一则材料有很多很多的解读方向,我也不敢保证自己总结的笔记就是作者完全想表达的意思。
另外我觉得此书给我另一个大的启发就是,可以通过美国报业发展的历史背景来审视我国的发展现状,读到很多地方都不由得会联系现实,我会从外部的社会背景视角切入,去窥探整个新闻界的动向以及现象出现的必要性。不过很遗憾,关于中国新闻业的反思我还没有做好相应解读的准备,这又是另一个宏大而复杂的议题,留到后面再详谈吧。
《发掘新闻》读后感(三):一部关于新闻客观性的历史发展概述
《发掘新闻:美国报业的社会史》一书由美国当代媒介社会学学者迈克尔·舒德森所著,早在1978年就已付梓出版。出版问世近40多年的时间内,它仍然作为新闻传播学的经典著作,受到新闻传播学师生的爱戴。对于本书成功的原因,我有以下两点见解:第一,它超越了以往描述性研究注重史料但孤立地讨论新闻业发展的问题,把新闻业与经济、政治、社会、文化生活勾连在一起。第二,相比于这学期精读的鸿篇巨制《美国新闻史:大众传播媒介解释史》事无巨细地围绕新闻业的方方面面进行阐释,对美国报纸、报人、电视、广播、电影等方面都有所涉及,《发掘新闻》这本“小书”抓住了新闻客观性这一核心问题,资料翔实、论述深刻,对学界至今争论不休的新闻客观性问题仍有启示作用。此外,陈昌凤老师在其所作的序言中对本书的评述十分深刻,她认为,舒德森使用前沿的社会史研究方法,使新闻史研究走向科学,为新闻学研究留下了“观念遗产”。
本书从便士报的兴起开始谈起。在技术发展和“民主社会市场”的社会革命等原因共同交织下发展起来的便士报开启了现代新闻业的大门。便士报冲破了政党报刊中标榜政治立场的束缚,使新闻“飞入寻常百姓家”,成为市场化的产品,为客观性理念的诞生构筑了现实土壤。19世纪80年代,记者时代到来,记者成为一种专门的职业。在科学和文学的现实主义氛围影响下,新闻业开始出现对“事实”的追求,但此时的事实与现在强调的事实有所不同,是一种对自身的不信任态度。记者在新闻工作中充满矛盾,既强调报道事实又想要事实鲜活生动,他们认为在报道事实的基础上,可以存在个人的主观创造。随后,出现了“故事模式”和“信息模式”两类风格迥异的新闻模式,二者引发的的道德战,实质是阶级冲突的一种掩盖。此时,现代意义上的新闻客观性仍未产生。
终于,在公关和一战宣传技巧中,在怀疑主义和悲观情绪的社会氛围下,新闻客观性终于产生了,它成为新闻业对事实主观化的回击。但作者又继续指出,客观性从一形成就土崩瓦解了,它实际上是一种无奈的“折衷主义”,是一种纯理想,也是一种对怀疑主义无所适从地逃避。仪式化、固定手段的客观性成为了一种规避风险的工具。所以,客观性从诞生之日开始就一直受到质疑,它一直徘徊在真空之上,从未下凡,是新闻从业者的乌托邦。但在最后,作者仍乐观的表示,”新闻从业者不屈服于相对主义,也不会屈服于以客观之名行武断之实的传统”。他认为,虽然绝对的客观是不存在的,但是新闻业必须坚守客观性。只有当客观性在新闻从业者内心成为一种共有的意识形态时,才能使新闻业在这条准则的指引下朝着良性的愿景发展,不至于变得更糟。
在美国新闻客观性发展历程的观照下来看中国的新闻客观性,是有启示性意义的。其实新闻客观性作为难以实现的准则,在美国未曾真正实践过,其他国家亦复如是。但它却始终作为一种信仰、一种共识,驰荡在所有新闻从业者内心。中国新闻业从诞生之日起就与西方新闻业发生历史错位。在西方早已从政党报刊的藩篱中脱离出来转向商业化的大众报刊时,中国新闻业还处于国家危亡的艰难时期,作为政治斗争工具的政党报刊此时是中国报刊的主要形态。虽然早已有有识之士在西方新闻思想的影响下提出在中国新闻业实践新闻客观性的理念,此后《申报》《大公报》把新闻客观性写入办报方针,推动客观性在中国实践的努力,但在当时缺乏稳定的政治环境和战争动乱的社会背景下,客观性始终没有施展的空间,被束之高阁。
新闻客观性作为观念引入中国后一直水土不服。改革开放之后,商业文化入侵中国,新闻客观性思想才重新回到新闻从业者的视线之内,成为标榜专业性、获取受众关注度的工具,真正的客观性仍难以实现。值得反思的是,在中国现实的政治环境下,政治管控力度的强大常常使新闻业陷入“自我审查”,新闻客观性仍然缺乏相对民主的施展空间。但是,正如舒德曼在书中所希冀的一样,虽然新闻客观性在理论和实践上有所脱节,但是仍然是“不死之神”,特别是在中国,有一条更为艰难的道路要去探寻。
《发掘新闻》读后感(四):媒介社会学初见
在动辄跨文化、跨学科的今天,拿新闻学和社会学来说事儿实在是不大新鲜。但说这句话的时候需要尤为谨慎,不新鲜并非指新闻学和社会学就像是天然同盟一般,而恰恰因为新闻学与社会学之间出现了一种所谓文本上的跨越。通常我们理解新闻都是建立在新闻文本上的,而社会学所关注的更像是一个个具体的场景。当然你或许会说,新闻文本所描绘的难道不是一个个具体的场景吗?的确如此,但是新闻文本的形成受到众多因素的影响,致使其永远无法和真实的场景等同起来。其中的纠结之处就在于,这众多因素中最为根本的恐怕是新闻记者本身。换言之,新闻文本的诞生之初即遭遇真相永远无法被完整、客观的呈现。
而社会学的功能便是从某种程度上放弃这条路,转向一种“(凡此种种)不如说是一场……社会冲突、阶级冲突” 的社会学式总结。这也是为什么舒德森的媒介社会学总是给人一种笼统的印象。正如我们从小接受的教育,万事万物皆有联系,把诸如报刊演进这样的学科问题放在历史上的社会文化中来探讨,当然可以令人信服地做出前者归因于后者的结论。那舒德森岂不是在做一项永远无解的工作?
在拜读舒德森这本最富盛名的著作的时候我写下了这样的文字:
从舒德森起的题目便可略知本书的研究旨趣。“新闻”作为一种discover而来的物,即可知新闻必定不是be made,至少在他看来。那么正如曹晋在序中所述,本书“原本是想成为新闻行业历史和专业意识形态发端的案例研究,但其围绕新闻的客观性问题所展开的论述却成为全书的核心思考”。我们需要追问发掘新闻的土壤在哪里,似乎便是这个“新闻的客观性问题”了。
托马斯•曼写道,“我们这个时代无法就‘为什么’、‘目的何在’等问题给出令人满意的答案……客观性作为一种理想,在过去,乃至今天,都常被用来作为权力的掩饰,有时甚至是用不诚实的方式去掩饰。但客观性的根源并没有那么肤浅,它不是用来为权威、特权提供掩饰,而是用来遮掩我们在凝视现代社会时眼神中流露出的失落感。” 因此,我的理解是,我们在“遮掩”的方式、方法、程度上的共识便成了我们作为理解新闻的受众与新闻生产者之间的互动。当然,这个过程即发掘出了新闻。
现在来看,舒德森当然不是在做无用功。他是用一种貌似笼统的方式,引入不一样的思考,更为重要的是引出下一步研究的无限可能。比如前文提到的“客观性的根源”,乍一看这实在是一个突兀的问题,客观性即便不被理解为理所应当,也不应该有个多么深奥的婆家。但舒德森却用非常缜密连贯的历史知识点醒了一个我们隐约知晓却难以大声说出来的现实——我们只不过“需要一种逃避” 。一方面,他向我们展示了新闻学学科上的危机。新闻应不应该、能不能够专业化?这就不单单指向新闻教育了,更深层次地,它直接抛出问题——“既然这个行业没有自我约束的社会权威机制,那为什么还未客观性而争论不休?” 另一方面,二战以后世界变得越来越复杂,国际政治经济中心的转移仿佛令美国人苦恼该如何来理解现实。解释性报道、调查性报道的相继出现不仅是对上一问题的回答,更是因为美国人要按捺住世界第一的喜悦并客观地理解这一切,至少是看上去客观地。
有意思的是,这似乎不仅仅是美国人的事,中国人的“逃避”在当今社会语境下貌似更加明显。只不过我们更多地把目光放在了对党性原则、新闻管制的批判上,其实我们仅仅需要多看一眼自己的内心。
这样一来,舒德森结尾时的喟叹便显得深沉多了,“新闻从业者必须像其他真理探求者一样,学会相信自己、相信同事、相信世界,包容世界,但同时又要怀疑自己、怀疑同事、怀疑世界的表现,不迷失于世界。”
2012-10-1书
《发掘新闻》读后感(五):摘抄向读书笔记
20190629~20190701 三天断断续续翻完。同期在看《国史大纲》、尼采
序言
1. 从(天真的经验主义)客观地报道非世界本来面目的新闻→(一战后)主观地报道/客观地遵循规章制度2. 为什么客观性重要?科学从通往知识真、确、佳的途径(与意识形态相对)到差点变成意识形态
3. 有两种社会机制在不同领域中保持着客观性:高等教育、职业培训
4. 兴趣从对客观性的讨论转移到研究现代新闻机制与经济、政治、社会、文化生活之间的关系
平等主义时代的美国新闻革命:便士报
1. 便士报,一切向钱看,只要付出广告费,人人平等,谁都可以雇佣公共报刊。他们自豪地拒绝担当道德评判的权威或责任者,并毫不为耻地以自身利益来捍卫自己。
2. 新新闻学,有些便士报自称政治立场中立,甚至不谈政治。
3. 便士报开启了花钱雇佣记者的先河。
4. 19世纪30年代以前,报纸只为政党、商业人士提供服务,直到便士报出现,报纸才成为销售给一般读者的商品,再把读者卖给广告客户。便士报使新闻变成一个市场化的产品,其特性(尤其是新闻的时效性)可以被量化;更重要的是,他体认并增强了日常生活的重要性。
5. 为什么会发生这样的新闻业革命?(政治平民化)科技论、识字率论
6. 与其讨论识字率的具体数字,不如去研究促使识字率增长的诱因。
7. 若只“说”,而不能同时与表达自我、表达自己的世界观、创造、再创造、选择、决定等诸权利相结合,就根本不能算是真的会“说话”,不能够最终参与人类历史进程。
8. 现代新闻业(便士报)是随着民主社会的崛起而诞生的。民主的观念渗透到社会方方面面。
讲故事:1880年后新闻业成为一种职业
1. 赫斯特《纽约新闻报》:你提供图片,我提供战争。最没有道德感的编辑
2. 普利策《纽约世界报》
3. 小说家从记者起家,现实主义,关注人。
4. 科学的产生来源于市场经济、政治民主理念和制度的发展、城市居民阶级的出现。
故事与信息:19世纪90年代的两类新闻
1. 阿道夫·奥克斯《时报》追求事实→作为信息的新闻 富裕阶层爱看
2. 米德认为新闻业第一功能是审美。记者被派出去采集故事,而不是收集事实。
3. 本雅明指出,信息是一种新的交流模式,是成熟资本主义的产物。最高目标,不证自明。
4. 作为娱乐的新闻业:普利策《世界报》
5. 信息与故事、精英文化与通俗趣味
6. 能控制自我的人阅读政治新闻,而放任自己的人去读谋杀案和名人八卦。信息代表着一种自我否定,而故事则代表自我沉溺。
客观性成为意识形态:一战之后的新闻业
1. 一旦业界普遍接受了新闻报道中的主观性无法克服的观点,客观性就沦为一种纯理想。
2. 客观性的根源并没有那么肤浅,它不是用来为权威、特权提供掩饰,而是用来遮掩我们在凝视现代社会时眼神中流露出的失落感。
客观性、新闻管理与批判文化
1. “纯新闻”不仅味同嚼蜡,左右受限,而且它本身就是一种参与的形式,暗中同官方新闻合谋,自以为是地声称高于一切党派和政治之争,这一点才是最为危险的。
2. 新闻从业者的政治影响不在于公开声称支持什么,而在于不加检验地遵守他们职业活动的基本准则,最重要的是遵守客观报道的传统。新闻的偏颇不在于有意的偏见之中,而是在于新闻采集的方式强化了官方所建构的社会现实。
3. 首先学会把观点从事实中剥离出来。
4. 新闻从业者必须像其他真理探求者一样,学会相信自己、相信同事、相信世界,包容世界,但同时又要怀疑自己、怀疑同事、怀疑世界的表现,不迷失于世界。他们不会屈服于相对主义,也不会屈服于以客观之名行武断之实的传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