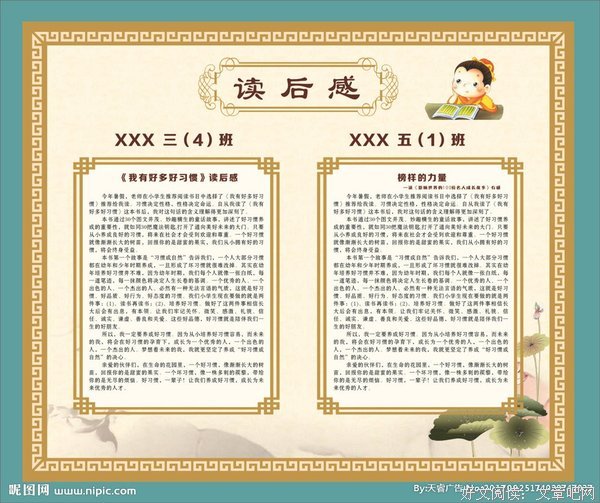
《离岸》是一本由[英]佩内洛普·菲茨杰拉德著作,中信出版集团出版的平装图书,本书定价:49,页数:200,特精心从网络上整理的一些读者的读后感,希望对大家能有帮助。
但是老九怎么知道他有胃病呢?他以前煮白水的时候在乎他的胃吗?
秋葵视频APP男人的加油站他还是有些良心的,四爷此时秋葵视频APP男人的加油站高兴地想。但这真的是一个美丽的误会。梅猜想他得了胃病。那是因为有一次他揉了揉肚子,苏培盛看上去有点担心,被小聪明梅看见了。
而煮白开水完全是因为他那天端上来的茶已经没了,只剩下一些秋葵视频APP男人的加油站高质量的茶,所以他无法忍受。这只是直接供应白水。不管怎样,茶盏经常是为了装模作样而摆放的,没有必要去喝它们。四爷回到东三所时,剑眉紧锁。事实上,他还在想,福晋给的食物真的这么好吃吗?要么她明天带来,他会不情愿地试一试。当时四爷一口也没吃,连零食都没吃,现在肚子已经饿疼了。
叫太医去看太平药方,说些没用的话,不要吃凉的,按时吃饭等等。当我等待晚餐时,我无法表达我对餐桌的胃口,但我实际上想到的是中午送来的餐桌。我不得不说,人们特别关心嘴里没有吃过的食物,尤其是当别人说它很美味的时候。
《离岸》读后感(二):她的兴趣是在人本身,情节只是角色的附属物 | Pechorin’s Journal
本文翻译自 Pechorin’s Journal ,发表于 23 OCTOBER, 2014 ,侵删。
我一直以来都有一个模糊的愿望,就是想在船上生活。小时候,我和父亲那边的亲戚一起去运河上乘船度假。我记得在英国的水道上轻快地航行,游览小村庄,阳光和平静的水面。当然,我不知道实际情况是不是这样。童年假期的记忆并不是特别可靠,我的记忆顶多是朦胧的快照。不过不管当时是不是这样,如今我认为是。
在船上生活的想法有一种深刻的浪漫,或者是一种绝望。这是一个二选一的选择。要么是它吸引着你,让你无视船居生活的不便;要么是你不得不这样做,因为你无法负担其他选择。
菲茨杰拉德确实在船上生活过一段时间。她的写作有丰厚的知识做背景,这一点很明显。这是一部很短的小说,大约180页,发生的事情不多。它写了这样一群人——生活在河岸之外的人,漂泊在主流社会之外的人,脆弱的人。
驳船上的居民,既非坚实陆地上的生物也非水生生物,他们本希望比现在更受人尊重。他们渴望切尔西岸上更为明智及充裕的生活条件,在六十年代早期,有大几千人在那里生活。船居者也渴望像其他人一样在陆地上生活,但失败了,这让他们十分痛苦,不得不撤回船港;那么多其他的东西也随之漂走了,或被冲到潮汐的泥泞之中。
故事发生在1961年,“六十年代人”这个称号还没出现。尼娜带着两个年幼的孩子住在切尔西附近的一艘小船上,勉强度日。她的婚姻已经破裂,虽然也许不是不可挽回的,但至少现在她孤立无援,脆弱不堪,被自责和无情地审问自己失败的内心叙事所撕裂。
这听起来很凄凉,但这并不仅仅因为她漂泊在主流社会之外,她并不孤单。她在河边的邻居包括理查德,他是退休的前海军,也是他们小社区的领导人,和他那不满的传统中产妻子住在一起,她只想在乡下买一栋漂亮的房子;莫里斯,一个男妓,也是尼娜最亲密的朋友;威利斯,一个六十多岁的艺术家,只画已经明显过时的海洋画;还有其他人。这个社区的成员们来来往往,但他们的共同点是,没有一个人完全适应岸上更大更繁华的世界。正如莫里斯对尼娜说的那样:
你非常清楚,我们俩是同类人,尼娜。我们俩现在这么活着,就挺好,在陆地和河流之间。你,我亲爱的,与你的老公只是半心半意;还有玛莎,半是孩子,半是大姑娘;还有理查德,还过着半是曾经的海军生活;还有威利斯,半是艺术家,半是码头装卸工;还有那只猫,半死半活。如果他曾想过说说自己,快说到时,他却打住了。
几乎没有什么情节。威利斯想卖掉他的船,但船的状况很糟糕,要大家为他撒谎才有希望成功销售,这可是个难题。尼娜想让丈夫回来,让他和她一起住在船上,但他是个相当传统的男人,把他们婚姻的失败归咎于她(她在低谷的时候也是如此)。莫里斯被当地的一个小混混逼着在船上存放赃物——放,就会有被逮捕的危险;不放,就会遭受暴力。如果作者愿意,这些情节中的任何一个都可以纺成丰富而有价值的故事,但这不是菲茨杰拉德的做法。相反,她的兴趣是在人本身,情节只是角色的附属物。
《离岸》读后感(三):真正的文学都是属于失败者的
01
不少人上了张爱玲的当,先是认定交付真心的女人很难善终,塑造了自己悲观的爱情观,又被“出名要趁早”蛊惑,做什么都急吼吼地,倒是迎合了这个时代的逐利和俗气。可是能有几个人会像张爱玲这么钟灵毓秀,提笔就老,早早显露看透世事的天才气;又有几个人像乔布斯那样,可以骄傲地说:“我很幸运。很早就发现自己喜欢做的事情。”
英国女作家佩内洛普·菲茨杰拉德出版第一本书的时候已经58岁了,放在以作家为职业的人里算够晚的,1975年出版的第一本书是有关拉斐尔前派重要艺术家爱德华·伯恩·琼斯的传记,后来被她称作是“我小小的一点写作”。
我在脑海中搜索不到佩内洛普年轻时的容颜,大概她出名的时候已经步入老年,媒体上的照片也多是她白发的样子,眼窝凹陷,有深深的鱼眼纹和法令纹,嘴角轻轻上扬,在镜头中的她有一点拘谨,有一点疏离。英国作家朱利安·巴恩斯写过回忆她的文章,在文章中直接把她描写成一位会做果酱的奶奶,再次证明她出道时就已经老了。
61岁的佩内洛普·菲茨杰拉德既《金孩》之后,出版小说《书店》,真正意义上开启了她的文学生涯,像是人生精彩的下半场。在她生命的最后二十年里不断给人惊喜,出版了九部小说,其中《离岸》(1979)获得布克奖,而她的最后一部小说《蓝花》(1995)无疑是她最伟大的作品,十九次被媒体选为“年度最佳图书”,并获得美国国家图书评论奖。她去世后,经常被定义为英国战后最好的作家之
在成为“英国战后最好的作家之一”之前,佩内洛普做过许多不同的工作,在政府食品部门、BBC电台工作过,当过杂志编辑、书店职员、做过老师,抚养了三个孩子,很长一段时间内捉襟见肘。她生于1916年,出生在一个被她传记作者Hermione Lee称为“聪明的英国家庭”,一位叔叔(Dillwyn Knox)是数学天才,是剑桥国王学院的古典主义者和学者,后来成为密码学家,并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在布莱切利参与破译工作。
祖父和外祖父都是主教,她因此一生也保持着坚定的基督徒信仰,另两位叔叔投身宗教,分别写了宗教书籍和成为牛津大学的天主教牧师。她的父亲埃德蒙·诺克斯对宗教没有如此狂热,是《笨拙》杂志的主编,身上有一种被菲茨杰拉德称为“爱德华时代的低调习惯”的天赋。她在父亲去世后写了合传《诺克斯兄弟》,记录了自己卓越的家庭成员。
佩内洛普考入牛津大学的索默维学院,主修的专业是英国文学,但在入学前几个月母亲去世,母亲曾是牛津大学萨默维尔学院最早的一拨女学生之一,一家人无人例外地拥有读名校的经历。成名后她对自己的婚姻讳莫如深,但我们知道她在毕业四年后嫁给了戴斯蒙德(Desmond),凭的是对爱情的一腔热血,丈夫一生不得志,于70年代后期因癌症去世。
三个孩子、一个任性的丈夫,这让很多人觉得佩内洛普很晚才开始写作的原因是被家事所累,她的确是在她的孩子们长大了、可以离开家照顾自己之后才开始写作的。她就像《书店》里弗洛伦斯有了对自我实现的热望,但她不愿意承认那是对家庭的牺牲,她说:“在早年的岁月里,我是能够写但没有写,我认为一个人可以在一生的任何时刻开始写作。”
02.
在英国文学史中,19世纪的乔治·艾略特在39岁发表了第一部小说被看作是大器晚成,60岁才起步的佩内洛普竟因大龄创作成为媒体报道的卖点。相比30岁就热衷冒险的年轻人,60多岁的女作家有着更加严肃的态度,广阔的视野,也更加柔顺和自信。对于小说家来说,所有不堪的经历都可以成为最珍贵的写作素材,她在《离岸》中借11岁的玛莎的嘴说,“难道你不明白吗,你学的每一样东西,你受的每一种苦,都会在你人生的某个时刻起到作用。”
她早期的作品从自己的生活经历中取材。我从《书店》里读出了佩内洛普和主人公相似的经历和不甘。她在索思沃尔德书店工作间,在父亲去世后开始创作,在丈夫去世后更是奋不顾身地写小说。
《书店》里,弗洛伦斯·格林夫人买下一间老宅想要开一家书店,这是她重启人生下半场的方式,“在哈德堡,她半生中有八年多时间,靠已故丈夫留给她的微薄薪金度日。她最近在想,是否应该让自己看看,同时也让别人看看,她可以靠自己过活。”就这样,一位年年连大衣都不曾更换的女士,在丈夫去世八年多后才决定寻求人生的意义,要做一件挑战封闭、保守小镇的事业,尽管阻碍重重,也没能击退她的决心。因为比起嘲讽、偏见、挑衅、阻挠、敲门鬼,更令人害怕的是老年孤独的幽灵。
某天的早餐时间,弗洛伦斯·格林吃在收音机里听到:“比起二十世纪的45.8岁和52.4岁,现在男性的预期寿命是68.1岁,女性的是73.9岁。”这些数字当然不仅仅说人类的寿命在增长,也许是佩内洛普·菲茨杰拉德怀着这样的期待——女人没有这么快老去,她还可以做很多事情。她在书中写弗洛伦斯·格林“她尽量感觉这消息令人鼓舞。”
在1960年至1963年期间,她有一段住在泰晤士河巴特西河段上船屋的经历,这是她人生的低谷时期,收入不够用,佩内洛普也绝不向父亲伸手。有天驳船沉入泰晤士河,终被拖走,她焦急地到当时教书的威斯敏斯特导师学校,向学生们宣布:“对不起,我迟到了,因为我的房子沉了。”在小说《离岸》中,她刻画了城市化秩序中的一群“船屋者”。
我也曾拜访过住在泰晤士河上的朋友的家,在潮涨潮落的摇晃中,我对逼仄的船屋不再抱有浪漫的幻想,真实的生活并不像惠斯勒的绘画那样如诗如纱,“在船上生活,无论从精神上还是身体健康上看,风险都太大……”
03.
《人声鼎沸》 (1980 年)则取材于她二战期间受雇于BBC的工作经历;喜剧小说 《弗雷迪戏剧学校》 (1982 年) 取材于她在伦敦意大利康蒂戏剧艺术学院授课经历。
佩内洛普说自己会被“那些似乎生来就会被打败或深深迷失的人”所吸引,“他们愿意承担世界强加给他们的条件,但尽管他们有勇气,尽了最大努力,还是未能屈从于这些条件......我写作时,就是想为这些人发声。”
正如她在《离岸》里探讨了城市边缘船上居民的生存处境,这些“船屋者”曾经是陆地上的失败者,他们的生活如晃动的船只一样不稳定。在《书店》的结尾,弗洛伦斯以失败告终,并得出令人伤心欲绝的结论:“那个小镇并不需要一家书店。”佩内洛普写的失败不单单是个体的失败,有时是一类无法界定的善良之人的失败,有时是弱势群体的失败,有时是脆弱文明的失败。失败也分两种,一种是做了自己喜欢的事情然后失败,另一种是纯失败。佩内洛普写的并非纯失败,是另一种意义上的成功,是迷人的失败者。
话说回来,真正的文学都是属于失败者的。谈论赢家是很无聊的事情,运气太好的事情也没什么好写的,失败者却提供了丰富而博学的乐趣。佩内洛普曾说,“我一直忠于我最坚定的信念,我指的是为失败而生的人的勇气,强者的弱点,因误解和错失良机而产生的悲剧。我已尽力将这一切视为喜剧,否则我们又怎么承受这一生呢?”
朱利安·巴恩斯说,“从长期来看,作家是由他们所发现的人类处境的真相,以及他们表达的艺术性来衡量的。”显然佩内洛普的作品里这两点都已经具备。即便我们读遍奥斯汀、勃朗特三姐妹、艾略特、伍尔夫等英国女作家,读佩内洛普仍有新鲜的收获,她漫不经心的叙述方式蕴藏了张力,含蓄、简练的语言,非常吸引我。
人们常说,长大就是目睹着自己的梦一个又一个地死掉。我不否认这个世上有很多职业的成功需要靠吃青春的红利。倘若只看少年成名的样本,我们不免怀疑人生,只能感慨命运都是天注定的。幸运的是,还有不少像佩内洛普这样“夕阳红”样本,让我们这些后知后觉才滑向梦想轨道的人认定,只要还留有生命力,就有再次尝试的机会。
我常常觉得,一个人离自己的生活太近了不是好事。我最近就是离生活太近了,生活的内容太丰富了,你会产生一种熟人社会的幸福幻觉,干扰了写东西。我需要看到一些作家的故事,需要看好的作品,从中感知自我,构建自己思考的框架。
这个世界上其实并不存在出名早或大器晚成的作家,我们要警惕,不要被虚荣卷走了,因为最终只留下好作家和坏作家。佩内洛普·菲茨杰拉德,让我们这些不够早慧的人看到希望。
《离岸》读后感(四):“你学的每一样东西都是有用的”
“你学的每一样东西都是有用的,”《离岸》中十一岁的玛莎如是说,“难道你不明白吗,你学的每一样东西,你受的每一种苦,都会在你人生的某个时刻起到作用。”她的小妹妹嘟囔说玛莎不过是在重复学校老师伊格纳修斯修女的智言慧语,但作者佩内洛普·菲茨杰拉德本人无疑对此是深有同感的。所有菲茨杰拉德的作品都是深思熟虑的产物,直达积累的知识和长时间生活经验的深度;她的创作反映出新的机遇感,可能伴随着晚年的丧亲之痛和流离失所而来。在她父亲埃德蒙·诺克斯1971年去世后,菲茨杰拉德才开始写第一本书———画家爱德华·伯恩-琼斯的传记,该传记1975年出版,彼时菲茨杰拉德五十九岁。她父亲本人是她下一本书《诺克斯兄弟》的写作对象之一,这部了不起的合传于1977年出版。这两本传记都取材于她之前几代人毕生的艺术、知识和精神生活,她通过自己非凡的家庭与之有所交往,对之有所了解,这些对她的创作至关重要。这之后,菲茨杰拉德开始了小说创作,《金孩》是为了让她丈夫德斯蒙德1976年去世之前有所消遣而写;随后的八本小说、短篇故事、另一本传记以及其他诸多杂志文章,都是她在将近二十五年的寡居生活里完成的。
作为小说家,菲茨杰拉德首先直接取材于她自己的生活经历,在她晚期的环境和视角转变之下,她充分挖掘并利用了早期生活中那些并不愉快且并不稳定的生活经历和职业生涯。她在索斯沃尔德书店工作的那段时间为《书店》(1978年)提供了素材;《离岸》(1979年)则取材于她最低谷最困难的一段岁月,那时她住在泰晤士河巴特西河段一艘老旧的驳船上;随后的《人声鼎沸》(1980年)则取材于她二战期间受雇于英国广播公司(BBC)的经历;最精彩的喜剧小说《弗雷迪戏剧学校》(1982年)取材于她在伦敦意大利康蒂戏剧艺术学院的授课经历。《离岸》是她所有作品中调性最多变的,当然有时也是非常有趣的,她自己称之为“悲闹剧”。
故事的中心人物是一位年轻的加拿大女性尼娜·詹姆斯,最终她不得不接受这个事实:她的英国丈夫已经抛弃了她和两个孩子,永远不会回到她身边。尼娜是个壮志未酬的艺术家(她曾是小提琴手),住在一艘名为“格蕾丝”的船屋上,正如菲茨杰拉德本人也曾如此生活;但尼娜结婚时更年轻,她三十二岁,大女儿已经十一岁了。这是对菲茨杰拉德本人的一个提醒和警告,菲茨杰拉德二十五岁结婚,有三个孩子,四十多岁时在泰晤士河上生活了两年,她灵活地、有选择性地在作品中重复了自己的生活经历。故事围绕着尼娜对住在周围的船居者的观察和了解展开。《书店》中,菲茨杰拉德塑造了一位脆弱的女主人公,渴望保护历史,故事背景并不太现实,有哥特似夸张及简朴之处。但在《离岸》中,已能看到她成熟简练的风格,寥寥几笔即能描摹出整个生活的本质所在。其他的船主:精明干练的理查德·布莱克和他心灰意冷对航海一无所知的妻子、能接纳各色人等的男妓莫里斯、老海洋画家山姆·威利斯,他希望能在船沉之前把船卖出去———都出现在故事开篇的画面中,但这组群像画在不停地发展变化着,因为该作品的核心就是变化和流动,菲茨杰拉德以看似漫不经心的智慧和轻巧让故事情节徐徐展开。正是在这部小说中,她找到了她的表现形式———她的技巧和她的优势所在。她在创作过程非常重视“质朴、含蓄和简洁”,这些在《离岸》中都得到了完美体现。
菲茨杰拉德本人曾坦言,作为作家她容易被“那些似乎生来就会被打败或深深迷失的人”所吸引,“他们愿意承担世界强加给他们的条件,但尽管他们有勇气,尽了最大努力,他们还是未能屈从于这些条件。……我写作时,就是想为这些人发声。”《离岸》中,她的船居者们“既非坚实陆地上的生物也非水生生物”,渴望切尔西岸上更为“明智”及“充裕的”生活条件。“船居者也渴望像其他人一样在陆地上生活,但失败了,这让他们十分痛苦,不得不撤回船港;那么多其他的东西也随之漂走了,或被冲到潮汐的泥泞之中。”之后她曾写道,很遗憾此部作品的标题翻译暗含着“远离河岸”之意———她想表达的意思指向泊在河岸几码远处的船只的不稳定性,以及“我人物的焦虑情感,介于安全需要和危险的可疑吸引力之间”
当然,他们皆有其各自缘由,有些人应对得比其他人好———菲茨杰拉德一如既往地对忧虑和困苦有敏锐的理解。这部小说敏锐的心理描写表明她对他们的心理习惯以及长期以来所依赖的观念有着清晰而富有同情心的理解,但那终究救不了他们。务实的理查德建议可怜的威利斯修补船只以便出售,理查德无法理解他“面对的,或者说他想帮助的是一个从未想过修理任何东西的人,无论是身体上还是情感上”。威利斯确实“早就开始怀疑各种新的开始了,并把信任置于一赖到底的精神上”(正如后来的进展一样,一个新的开始———或者说一个戏剧性的变化——将会降临到他头上)。尼娜非常清醒地意识到自己缺乏理性思维,她在想象的冗长听证会上,在法官面前检讨了自己的婚姻及前景,明白其在法庭审查面前不堪一击。即便富有、高效、令人尊敬如理查德,“那种在凌晨三点半还能拿出两块干净手帕的男人”,也受制于他在社交和海军训练中养成的思维习惯,令人唏嘘。“最后的这个念头似乎把整个事情都理清了,他的思维现在作为一个统一交织的结构开始运转了。”悲闹剧让他们一直处于变动之中,它那模棱两可的状态从不是非此即彼的。十年后,菲茨杰拉德在她的一篇文章中谈起莫里斯这个人物原型出自“一位风度翩翩的年轻男模”,住在隔壁那艘船上,为了让他那衣着破旧、疲惫不堪的中年邻居开心,带她去了布赖顿一整天。不久后,他又回到布赖顿,投海自尽了。“但当我把他塑造成一个人物时……我无法忍受让他自杀,那将意味着他是生活的失败者,但事实是他的善良”这样带有个人感情色彩且在我眼里正是成功的标志。飘忽不定、无法调和的价值范畴是菲茨杰拉德人际交往描写中的核心。
当然,还有那两个小姑娘。菲茨杰拉德作品中的孩子往往表现出闷闷不乐的成人所没有的不抱幻想的成熟,《书店》中十岁的克里斯汀·吉平,告诉没孩子的寡妇弗洛伦斯:“你已经过了生孩子的年龄了。”《早春》中十二岁的多莉十分冷静,“完全掌控一切”。她们是管家,真相的发言人,父母含糊其词,不得要领,她们却一下子就说透。“这些孩子不同寻常。”前来拜访的多莉的舅舅如是说。“我无法确信内莉和我能够自由地加入交谈之中。”菲茨杰拉德虚构的孩子原型也许可以在艾薇·康普顿-伯内特口齿伶俐的托儿所和教室里找到,虽然对一个朋友来说,这样的孩子“矫揉造作”,菲茨杰拉德却回应说:“我不这么认为……他们跟我的孩子很像,什么都逃不过他们的眼睛。”话虽如此,不可能完全像,他们的某些特征也许源于菲茨杰拉德曾经教过的那些沉着镇静的儿童演员。在《弗雷迪戏剧学校》中,他们满口方言,口若悬河,带着疯狂的决心执着于他们短暂的职业生涯。她在《离岸》中展示的孩童形象毫无疑问既有模仿也有创新。
在玛莎和蒂尔达身上,菲茨杰拉德塑造了两个最让人难忘且有趣的少女形象。她俩是书中仅有的孩童人物,永远的逃学生,也是作者探究作品环境和历史的方式。六岁的蒂尔达的整个世界就是泰晤士河,她故意爬上格蕾丝号主桅杆的高处,待在那儿研究它;她在过去和现在混合着的白日梦中度过了漫长时光。当然,任何一个人现在到巴特西河段都会看到一幅完全不同的景象,不同于菲茨杰拉德五十年前住那儿时的样子,与孩子们仍能回忆的维多利亚时代晚期的切尔西更是大相径庭。高耸的廉租公房、玻璃庙塔以及帆船形状的公寓现在充斥河岸。那些在巴特西桥上游———那曾是格蕾丝号的停泊处———的船,看起来也豪华多了。然而,十九世纪的大部分时间,那儿都是格雷夫斯船坞处,格雷夫斯家族的两代人都是船夫———先是为特纳工作,后为惠斯勒工作,惠斯勒从年轻的沃尔特·格雷夫斯的船上生动地描摹出了老巴特西木桥,转而教会格雷夫斯模仿他的风格,以绘画和蚀刻方式展现当地河流的景色。威利斯带蒂尔达去泰特艺术馆时所看的,正是惠斯勒最有名的“夜曲”:《蓝色和金色:古老的巴特西大桥》,惠斯勒把泰晤士河上这片并不入眼的地方点石成金了。“惠斯勒是个很不错的画家。”威利斯对蒂尔达说,他对该主题有务实的洞察:“潮水转向,驳船顺势而行。”这也是菲茨杰拉德作为一个小说家所具有的专业知识的典型代表,并非研究得来,而是从河流的四季和心情变化中的每一次起伏和吱吱声中学习而来。她就像个谨慎的抒情诗人,小说中对潮水和河流光线简洁精准的观察也许是最具有绘画效果的,尤其是黄昏时的描写:“夜幕似乎是从河面升起”;还有黎明的描写:“河流最神秘的时刻,一层黑暗驱散另一层黑暗,上一分钟还是影子,下一分钟,影子就清晰地变成了房子或停泊的船只”。
对河流历史和人物最为微妙的回眸一顾,在第六章“瓷砖”冒险中捕捉得最为生动。玛莎和蒂尔达手拉小车慢慢走过巴特西大桥,来到了老圣玛丽教堂旁泥泞的前滩。退潮时,在“二战”前沉没的一艘砖船残骸旁,她俩仍有可能在这儿找到泛着红宝石光芒的威廉·德·摩根的瓷砖。正如玛莎所知,他“最后的砖窑”“在富勒姆的桑兹·安得”。这些从泥里捡出来的宝贝碎片———一条尾巴蜿蜒的龙、“一只精致奇异的银鸟”———是来自威廉·莫里斯和拉斐尔前派艺术界的战利品,菲茨杰拉德本人曾对之进行过细致的探索。在二十年后一篇关于德·摩根的文章中,她回忆起了艺术家的弟媳威廉明娜·施蒂林夫人,一位在1965年一百岁时去世的圣火守护者,一位“勇敢的……甚至是英雄的”人物,菲茨杰拉德(像玛莎和蒂尔达随后一样)曾在巴特西的家中拜访过她,那里的“墙壁和壁龛都闪耀着色彩”。六岁的蒂尔达说:“威廉明娜·施蒂林夫人……她至少九十七了。”如此这般显示出她的早慧并建立起了跨越世纪的联系。两个女孩把瓷砖卖给国王路的一家古董店,入手三英镑,立刻去另一家店买了克里夫·理查德的唱片。
《离岸》的故事背景为1961年,或许是1962年(文本内部的证据并不一致,因为我们对一个时代的回忆往往是十五年多之后的事情),因此当该小说1979年出版时,它的当下已经是过去的时间和情绪了。出身名门的奥地利青年海因里希顺道拜访格蕾丝号,他热切渴望领略摇摆伦敦的激动人心之处,玛莎迷上了他。她带他逛国王路,那是“一天中最热闹的……整条街就像吉卜赛人的营地……一片混乱之中,真是孩子的乐园”。古董店与专卖店比肩而立,“向外飘出熏香和无趣的灵魂”,还有“伦敦的新事物”咖啡吧,在那儿,“闪闪发光的加吉亚咖啡机,把一英寸半的苦沫倒进陶瓷杯子,情侣们花两先令就可以在深棕色调的环境里坐上好几个小时,桌上还放着一碗红糖”。这个“魔咒解除前注定只能延续几年”的世界,这位上了年纪的小说家承认这是她自己的孩子曾经的乐园;但现在,这地方是成年人的世界了。我们非常微妙地触摸并看到代代重叠的模式,并感受到那种潜移默化的张力,这种张力一直吸引着菲茨杰拉德,并在她后期的四部历史小说中结出了累累硕果。
艾伦·霍林赫斯特
2013年
《离岸》读后感(五):佩内洛普·菲茨杰拉德:让不够早慧的人看到希望
佩内洛普·菲茨杰拉德张爱玲的“出名要趁早”被许多人奉为圭臬,但放在英国女作家佩内洛普·菲茨杰拉德身上并不适用。这位“大器晚成”的作家快60岁时才开始写作,年近70岁拿到了英国文学界最重要的布克奖。
“大概因为她出名时已步入老年,她在媒体镜头里眼窝凹陷,有深深的鱼眼纹和法令纹,嘴角轻轻上扬,有一点拘谨,也有一点疏离。英国作家朱利安·巴恩斯非常欣赏佩内洛普,在回忆文章中直接把她描写成一位会做果酱的奶奶。”近日,作家、中英文化社交媒体大使祝羽捷来到“大方live”线上分享会,向读者讲述她眼中的佩内洛普·菲茨杰拉德。
“佩内洛普于2000年去世。我读到她的小说时已看不到她在世的新鲜采访了。到现在为止,佩内洛普也不像其他女作家有大量的评论或者纪录片,她对我们而言依然是一个非常陌生的形象。”祝羽捷说,“但在英国文学界,她的作品的地位让人不能忽视。”
“大器晚成”的女性,一定是为家庭牺牲吗?
在生命的最后二十年里,佩内洛普·菲茨杰拉德不断给人惊喜,共出版了九部小说。其中《离岸》(1979)获得布克奖,最后一部小说《蓝花》(1995)十九次被媒体选为“年度最佳图书”,并获得美国国家图书评论奖。她去世后依然经常被评价为“英国战后最好的作家之一”。
《离岸》近日,佩内洛普·菲茨杰拉德系列作品《离岸》《无辜》由中信·大方出版。
三个孩子、一个任性的丈夫,这让很多人觉得佩内洛普的“大器晚成”是被家事所累。但佩内洛普曾表示:“在早年的岁月里,我是能够写但没有写,我认为一个人可以在一生的任何时刻开始写作。”
祝羽捷说:“她的确是在孩子们都长大了,可以独立后才开始写作,她就像《书店》里的弗洛伦斯有了对自我实现的热望,但她不愿意承认那是对家庭的牺牲。”
这让祝羽捷想到了罗斯·怀利这位在英国艺术界非常活跃的老奶奶。和佩内洛普相似,罗斯也是70多岁了才“出道”当艺术家,这时候丈夫已逝,三个孩子也都长大成人,有了自己的家庭,但罗斯到今天的艺术生命力依然极其顽强,也获得了英国最重要的艺术奖项。
“在‘为家庭牺牲’这点上,我在采访罗斯·怀利时也得到了相似的回答。好像这些出道较晚的女性都不愿意提到‘牺牲’这两个字,因为‘牺牲’仿佛贬低了她们对家庭的热爱,而她们本身也是非常享受家庭的人。”在祝羽捷看来,这一点对现代女性而言非常重要,“我们总觉得女性的事业一定都是与家庭对立的,其实并非完全如此。一个女性可以拥有自己喜欢的事情,但同时她也可以热爱自己的家庭,热爱自己的丈夫,喜欢照顾小孩。”
“也正是佩内洛普·菲茨杰拉德、罗斯·怀利这样的存在,让我们这些后知后觉才滑向梦想轨道的人认定,只要还留有生命力,就有再次尝试的机会。”
《无辜》为什么我们读佩内洛普仍有新鲜的收获?
朱利安·巴恩斯说过:“从长期来看,作家是由他们所发现的人类处境的真相,以及他们表达那些真相的艺术性来衡量的。”
祝羽捷认为佩内洛普的作品同时具备了这两点。“即便读过奥斯汀、勃朗特三姐妹、伍尔夫等英国女作家,我们读佩内洛普仍有新鲜的收获。”
她说,首先时代性就非常不一样,佩内洛普笔下的人物、生活更接近我们现在所处的时代。“她是一个非常现代的作家,她写的人物的关系、人物的困惑也都非常接近我们现在的一些课题。”
其次,跟其他女作家相比,佩内洛普有着非常丰富的社会经验和家庭经验。在成为“英国战后最好的作家之一”之前,佩内洛普有过一长串职业经历:在政府食品部门、BBC电台工作过,当过杂志编辑,做过书店职员,教过学生。“奥斯汀终生未婚,伍尔夫没有当过母亲,勃朗特三姐妹几乎只做过家庭教师。相较而言,她们的生命有一些单薄,经历并不像佩内洛普那么复杂,因而佩内洛普所面对的时代课题也更加复杂。”
对于小说家来说,似乎所有经历都可以成为最珍贵的写作素材。佩内洛普在《离岸》中借11岁的玛莎的嘴说:“难道你不明白吗,你学的每一样东西,你受的每一种苦,都会在你人生的某个时刻起到作用。”
祝羽捷也非常喜欢佩内洛普的叙事方法:“她用的是一种漫不经心的叙述方式,但是你能感受到里面蕴藏了力量。同时她的语言非常含蓄简练,非常吸引人。而且我觉得高级的叙事是这样子的——没有过度的渲染,但给你足够的想象空间;不把所有的事情都说得那么明白,但让你回味无穷。”
作家、中英文化社交媒体大使祝羽捷为那些被打败或深深迷失的人“发声”
佩内洛普在小说中创作了很多贫穷的、边缘的、不合时宜的人物,他们多少也映射了她自己的生活经历和状态。比如新近出版的《离岸》,就源于佩内洛普作为一个船居者的极其短暂的经历。佩内洛普在书里探讨了城市边缘船居者的生存处境:他们曾经是陆地上的失败者,他们的生活如晃动的船只一样不稳定。
“我非常喜欢《离岸》这本小说。”祝羽捷说,这些船只停靠在泰晤士河巴特西河段,她自己在巴特西这一块住过一年,巴特西的对面、泰晤士河的另外一边,是英国“老钱”的聚集地。“切尔西这个地方是伦敦一区少数的不通地铁的地方。为什么没有通地铁?是因为‘老钱’们不愿意改变自己的生活方式,他们要保留很古典的英国生活方式,拒绝地铁修建在那里。”
“我们可以想象得出,泰晤士河这边的船居者,每天望向岸边那些最有钱的英国居民,他们会感到巨大的生活反差。不可否认有一些人是为了追求一种波西米亚的浪漫生活才搬到船上,但如果在伦敦住久了,你知道比起住别墅或者公寓,住在船上是最廉价的。”
《离岸》里写到了很多住在船上的人们,这些人是邻居,是“在一条船上的命运”。 祝羽捷说:“尽管有那么多的艺术家都描绘过泰晤士河的风景,但真正生活在船上,你知道它并没有那么如诗如画。那是很闭塞的空间,每天涨潮退潮的时候,你都会感受到船在摇摆中的不稳定性。”
而这部分描写和佩内洛普的生活经历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在1960年至1963年期间,她住在泰晤士河巴特西河段上的船屋。那是她人生中的低谷期,收入不够,又绝不向父亲伸手。有天驳船沉入泰晤士河,终被拖走,她在当时教书的威斯敏斯特导师学校向学生们宣布:“对不起,我迟到了,但我的房子沉了。”
佩内洛普说过,自己会被那些似乎生来就会被打败或深深迷失的人所吸引——“他们愿意承担世界强加给他们的条件,但尽管他们有勇气,尽了最大努力,他们还是未能屈从于这些条件……我写作时,就是想为这些人发声。”
在佩内洛普的作品之外,约翰·威廉斯《斯通纳》和塞林格《麦田里的守望者》也成功刻画了“失败者”这一角色。祝羽捷认为,这些作品中的人物更接近大多数人的一生——没有那么宏大的人生课题,也没有波澜壮阔的人生体验。“但完美的人生和完美的自我完全两回事。我们可以有时候对自己的生活失望,但一定可以让自我更加完整。”
谈到自己的创作经历,祝羽捷直言自己在很多人眼里或许也是一个“失败者”,至今尚未写出特别好的作品。但她如今似乎已能坦然面对这个困境,因为她相信文学是一个包容失败者的地方,也包容人心里的幽暗之处。“我想这个世界上其实不存在出名早的作家和大器晚成的作家,最终只留下好作家和坏作家。佩内洛普·菲茨杰拉德,让我们这些不够早慧的人看到希望。”
原文刊载于澎湃新闻,2020年7月2日
责任编辑:梁佳
校对:施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