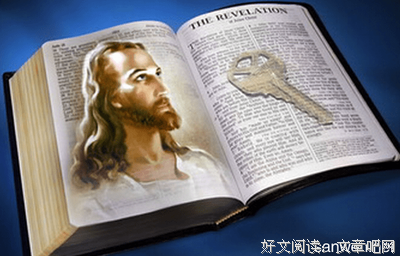
《圣经、新教与自然科学的兴起》是一本由[澳]彼得·哈里森著作,商务印书馆出版的精装图书,本书定价:72,页数:420,特精心从网络上整理的一些读者的读后感,希望对大家能有帮助。
●第一章,中世纪开始,基督教和希腊哲学融合诠释《圣经》,词指示物,物可以是其他物的记号。 第二章,至12世纪,700年时间,穷尽了自然和《圣经》的可能组合。 第三章,展示了种种天主教与新教的中间物,诠释学的优先级,伽利略的论敌,路德《九十五条论纲》,误译,逻辑的终点,分类混乱,独角兽的存在,圣餐变体论。 第四章,新教改革,打断了诠释链条物与物的联系,为自然科学提供了存在空间,因共同的敌人二者联合,《圣经》的字面真理与新科学的理论真理一致。 第五章,新教与自然科学的中间物,物理神学,动物寓言出现。 第六章,自然科学的神学动力,素食论的起源,园艺技术与殖民倾向,土地私有化制的起源,文与理的分离。
●上帝留下了自然之书和《圣经》之书。随着17世纪一种新教的文本诠释学的出现,物质世界的目的不再只是指称功能和象征功能,它需要自己的语言,这导向了一个机械化宇宙的出现。恢复神在人之中的形象被重新引向自然界,科学活动成为获得世俗拯救的一种物质手段。最终,科学活动与文学活动、宗教教义之间的共同基础越来越少,现代性得以诞生。
●看到最后难免觉得这是本个人主观意识太过于强烈的一本书,即便结尾有大量文献作为支持,我依然这样认为。“如果阅读就是不对其中的知识加以任何思考,不考虑其所适应的前提和界限而毫无保留的接受,不质疑不反驳,那么,我们的脑子就会成为别人思想的跑马场。” 但总结来说,还是有很好的阅读体验,故4.5分。
●五星,从寓意解经到字面主义,“起初通过认识神来认识造物,现在通过认识造物来认识神”,科学与重返伊甸园。#是不是应该预告一下《人的堕落与科学的基础》#
●人们普遍承认现代科学起源于17世纪,但是意识到现代宗教也是在这个时间出现的人并不多。新教的救赎乃是通过“拯救知识”的手段来实现的,拯救不再被视为恢复神在人之中的形象,这种救赎动力被重新引向自然界,科学活动成为获得世俗拯救的一种物质手段。但是从事科学活动并持有这些信念的人并非义无反顾地朝着一个经验科学的美丽新世界迈进,而是开始意识到他们对世界的新解读的完整含义,以及一种将正当知识归结为数学关系和分类系统的自然观的相对贫乏。我们必须将帕斯卡在沉思新宇宙的永恒静寂时所体验到的那种恐惧与17世纪的乐观主义并置对照。对新科学的肯定是暂时性的,而不是必胜主义的,它总是伴随着对人类境况偶然性的认识,以及越来越意识到后巴别塔世界中一切意义结构的任意性。始终存在的的堕落之阴影笼罩在新伊甸园的千禧年希望周围。
●读了四章。核心论点就是新教改革对于近代自然科学的间接促进作用。过去,在中世纪,对于自然的研究实际是在一种解释学中进行。一个词指称一个自然物,而这个自然物根据其相似性指称更多的物。由此它也带有许多道德的、神圣的内涵。但是,新教改革和文艺复兴时期的学术改革(主要是新的校勘学的发展),使得释经的方法发生了巨大转变,物与物的指称链条被斩断,自然不再具有内在含义,亚里士多德和盖伦连同教父们的释经传统被一并抛弃,《圣经》也逐渐变为一种历史性的文本。自然由此也只能等待着被词与词的能指链覆盖,被用一种数学的、机械因果的联系网络所解释。
●值得一读
●结论显而易见,看中文版序言就可以了。
《圣经、新教与自然科学的兴起》读后感(一):新教改革是反击"二道贩子"
quot;对古代文本的研究可能会引发现代革命,无论是思想革命还是政治革命"
中国人苦"二道贩子"很久了。谢谢商务印书馆和张卜天先生,让我们在需要的时候,可以找到"中间物",处理中国这一百多年积攒的二道贩子。
第一章,中世纪开始,基督教和希腊哲学融合诠释《圣经》,词指示物,物可以是其他物的记号。 第二章,至12世纪,700年时间,穷尽了自然和《圣经》的可能组合。 第三章,展示了种种天主教与新教的中间物,诠释学的优先级,伽利略的论敌,路德《九十五条论纲》,误译,逻辑的终点,分类混乱,独角兽的存在,圣餐变体论。 第四章,新教改革,打断了诠释链条物与物的联系,为自然科学提供了存在空间,因共同的敌人二者联合,《圣经》的字面真理与新科学的理论真理一致。 第五章,新教与自然科学的中间物,物理神学,动物寓言出现。 第六章,自然科学的神学动力,素食论的起源,园艺技术与殖民倾向,土地私有化制的起源,文与理的分离。
此书是福柯《词与物》的前传。
《圣经、新教与自然科学的兴起》读后感(二):上帝的工艺品:词与物
阅读最大的喜悦是,一边阅读,一边在生活的其他时候思考,而慢慢地,自己的猜想和推论却在之后的某个章节与作者悄然相合。
如果说《现代性的神学起源》是从唯名论的角度,系统的考察了“神-人”思想的发展脉络,以神的“退出“为主要结论解释现代性的起源,那么《圣经、新教与自然科学的兴起》是从诠释学的角度,通过人们对圣经解读方法的演变,以神的“命令”为主要结论得出现代性的起源。两者对现代性的看法也有所不同,都肯定了科学话语的特权地位为现代性的主要特征,但由于后者从诠释学的角度思考问题,“把文本的含义等同于作者的意图”也成为Peter Harrison眼中现代性的另外一个特征。后现代主义不仅终结了把含义等同于作者的意图,而且也使我们认识到,这种含义概念有一个开端。作者之死应当是我们想到作者在大约五百年前的诞生。”
作者的观点,以及书中提到的众多历史上的观点非常有启发性,比如对一种普遍的、原始的、更自然的语言即亚当的语言的追求背后是这样一个信念:神赋予亚当的语言天然地显示自然事物的真理。这种概念是难以理解的,例如将水叫做“那流动的”或者“那透明的”是否说明这样的语言显示了事物的真理?但那只是汉语,并且任何一个语言也可以做到。不过象形文字的特点的确受到了关注,我们要好好保护我们的语言。另外,在这样一种释经学的革命中,对时间的不同阐述也有着相当大的影响。比如圣经中的很多事件被认为真实发生,“犹太教-基督教启示录传统的时间二元论被纳入了历史时间或地质时间的单一维度。这也逐渐引出了本书的一个重要,也是非常有说服力的观点,即对圣经的解读方式从来不是对现代科学的敌对,相反对圣经字面主义的解读恰恰推动了现代科学概念的兴起。中世纪,甚至更前期的科学思想,例如亚里士多德和托勒密的自然哲学并不处于哥白尼和牛顿宇宙观通向的科学语境之下,”相信地球静止于宇宙的中心,在16世纪不仅仅是赞同太阳系的地心说,而且与一系列具有形而上学、道德、宗教和人类学意义的承诺有关,特别是涉及人的尊严及其在宇宙中的地位。对此,转折处的标志性人物——John Ray值得我们更多的关注。
我对于科学史这一系列丛书的最大兴趣是,想找到证明科学的不足的证据,这样的证据我不仅在一定的神学思想中找到了,科学的源起和科学的原理本身,如果近距离观察——在笛卡尔和牛顿的物理学中,简单的自然物除了基本的定量属性之外全都被剥夺了。在这种新的自然语言中,句法(syntax)胜过了语义(semantices)。从此以后,自然科学将会处理支配自然物之间的数学规则或分类规则。自然物的含义将只保存在如今专属于诗人的那些残留的、比喻性的表达之中。
如果要读它,将扉页那句话铭记在心吧:一段话应当类似于一个活的造物。
《圣经、新教与自然科学的兴起》读后感(三):中文版序言
最初激励我写这本书的问题是为什么现代科学始于17世纪的西欧。当然,各种形式的科学技术活动一直是不同文化和不同时期的典型特征。常有人指出,在17世纪的科学革命之前,中国在技术上比西欧更先进。中世纪的伊斯兰文明也产生了高级而精致的科学文化。但正是在17世纪的欧洲发生的科学革命,才使科学技术获得了前所未有的、不可逆的发展。 关于科学在西方的兴起,历史学家提出了许多解释。在19世纪末和20世纪的某些地方,流行的观点是,科学之所以成功,是因为它逐渐摆脱了宗教。根据这种观点,西方思想的世俗化乃是解释西方科学成功的关键。该理论的依据通常是,科学与宗教本质上不相容,注定彼此冲突。因此,只有完全摆脱了宗教的束缚,科学才能真正繁荣起来。 然而,通过研究科学革命中一些主要人物,我断言,这种理论不可能是正确的。例如,为科学的兴起做出重要贡献的人都怀有传统意义上的宗教虔诚。不仅如此,他们还常常在其宗教观点与科学活动之间建立起直接联系。此外,科学世界观的一些基本特征,比如认为自然受不变的数学定律的支配,在神学思想中有其基础。似乎更有可能的是,现代科学实际上不是通过反对宗教,而是通过基督教所固有的某些宗教预设来实现的。 但是,如果基督教对科学的兴起负有部分责任,为何它的影响力直到16、17世纪才发挥作用呢?这里,重要的是要知道,基督教自身在16世纪经历了思想和实践上的革命,即所谓的新教改革。虽然某些基督教观念可能为科学的兴起打下了基础,但新教思想家赋予这些观念的特殊形式可以促进对自然界进行研究,并且为新的科学事业提供理由和激励。 最重要的是,诠释自然和《圣经》的方法发生了变化。根据一种由来已久的中世纪隐喻,上帝为人类提供了“两本书”:“自然之书”(自然界)和“《圣经》之书”(《圣经》)。因此,自然和《圣经》被认为是由上帝创作的贮藏永恒真理的平行之所。基督教会从一开始就形成了诠释自然“之书”和《圣经》的统一传统。然而,诠释自然和《圣经》的这些传统方法在新教改革期间受到了彻底批判。正如我在书中所论述的那样,新教改革所推动的诠释方法为新科学方法的形成提供了重要催化剂。从本质上讲,新教坚持从字面上解读《圣经》,伴随着从字面上(或科学上)解读世界的新程序。这意味着,自然界中的事物渐渐不再按照它们所象征的永恒真理或者所教导的道德教训来理解,而是按照其内在结构和潜在的人类用途来理解。 对《圣经》中的特定段落作新的字面解读,强化了诠释策略中这种总体变化的影响。例如,在《创世记》的创世记述中,最初的人被命令统治地球,对其进行研究,使之变得多产和有用。对这些段落的传统的寓意诠释和道德诠释倾向于削弱它们的字面力量。但随着16、17世纪出现了对这些段落字面意义的重新强调,《圣经》成为鼓励科学活动的一个重要来源。现在,《圣经》中关于“统治地球”的命令被理解成对研究自然并以各种技术控制自然的一项命令。事实上可以毫不夸张地说,科学研究渐渐被视为一种宗教义务。 于是,回到最初激励本书的那个问题,我的看法是,宗教改革之后基督教的关键要素对于科学的兴起、对于现代西方所特有的科学活动被赋予的巨大价值具有至关重要的意义。 很高兴能为本书的中文版写一篇序言(这也是它的第一个翻译版),很欣慰现在它能够迎来一批重要的新读者。非常感谢我的译者——清华大学科学史系的张卜天教授。从我们在翻译过程中的许多交流中我意识到,这个译本融入了极大的悉心考虑和周到处理。希望这个新的中文版不仅能为更广泛地理解西方历史上的一个重要时代做出贡献,还能促进从另一种文化视角重新审视导致现代科学兴起的因素。 彼得·哈里森 2018年7月23日
附
张卜天︱《圣经》之书与自然之书①:寓意诠释及其瓦解
《圣经》之书与自然之书②:既是神的,又是自然的
《圣经》之书与自然之书③:重建伊甸园,统治地球
《圣经、新教与自然科学的兴起》读后感(四):论述优美,岌岌可危
章一:使徒圣保罗揣着希望来到雅典,其关于死而复生的断言遭到了在场的伊壁鸠鲁派和斯多亚学派的嘲笑,吃了瘪的使徒回家写道,神“叫这世上的智慧变成愚拙”,一两百年后,基督教作家欣然发现柏拉图主义实在好用,自此开启了奥利金以及后来的奥古斯丁为圣经开辟的寓意之路,后者比前者狡黠之处在于,在神圣与人之间安插了释经人的角色,但是奥利金对众生的淳朴信任仍打动着我,此外基督教的“真香”举动冥冥昭示了某种强大且持久的文化必须具有酱缸的品格。
章二:中世纪时人类生存的物质性被阿奎那牢固地确立于西方思想中,原先由圣经组织起来的世间万物的联系逐渐被它们本身固有的联系取代,但作者试图说明,此举仍是使人与神和解的手段,是释经家们非凡的技巧和能力无处宣泄的结果,是人们摸索着走向亚当时代的远古知识的神学举动。
章三:亚里士多德的博学受到了空前的质疑,尽管历史上他很努力地克服这一天的到来故此特意叮嘱亚历山大在四处打仗睡女人时不要忘记带回动植物标本,砸破偶像光环的是大航海、疾病与解剖学,实质上是身体力行,也可以说是到群众中去,因为之前的知识只是不断地在纸面上搬来搬去。自然事物的爆炸导致了一定的培根主义危机,即在没有任何的理论指导的前提下不遗一物地吸收,俗称无头苍蝇,瞎几把飞,而人们迟钝的想象力尚未能及时地为这些新事物安排好神圣或邪恶的寓意,于是寓言就蜷缩为文学手段而非通往世界的进路了,可尽管如此,大部头的自然志著作也只为无所事事的牧师服务,以追求花哨的布道效果。同时,路德引领的新教改革也正热火朝天,他剔除了圣经的标准注解(Glossa Ordinaria)就好比把毛传郑笺孔疏都踢出说文解字,让大家伙手捧新鲜热乎的原文,唯独圣经(Sola scriptura)这一座右铭对字面解读的狭窄专注通过反偶像崇拜影响了整个崇拜结构和信仰方式,一系列神圣的仪式被一部文本取代,这虽然造就了英国前工业时代一骑绝尘的识字率,可人们却悻悻然发现生活的滋味寡淡了不少。
章四:信徒不肯放弃圣经就像母亲不愿放弃在智商测评中失败的孩子,于是他从真理班进入了历史班,宁做鸡头不做凤尾,在历史领域,圣经是“纯粹的黄金”和“没有斑点的太阳”,与之相适应的,释经学家创造了types和principle of accommodation,前者承认神在自然领域的无能,其对历史领域的影响却永存,就好比你改变不了现实,但可以改变历史因为历史是任人打扮的小姑娘啊,而后者简而言之是把先民当傻子,不知奥利金会不会在地下打喷嚏。当时有限的自然科学发现甚至让牛顿都相信圣经早就以更简洁的方式包含了一切,在终末之事(the last things)的隐喻中,天堂和地狱有了确切的位置,重生得到了生物学的印证,启示录传统二元论被纳入了单一的维度,顺带一提,昆虫的变态令许多人看到了预先存在(pre-existence),这与原罪的概念协调至极,释经学家停止了战栗的梦境,夜夜笑醒。
章五:对于世间的造物,释经学家们认为它们服务于神的目的,这时如果一个孩子问你为什么要下雨啊,你要回答为了使大地湿润,那为什么梅雨季节天天下雨啊,我想可能是希望我长霉烂掉吧。由此产生的物理神学(physico-theology)再次刺激自然研究者的G点,如马勒伯朗士时常津津乐道“一只昆虫比整个希腊和罗马的历史更关乎神的智慧”,但较之想象力堪称诡谲的普吕什他则显得过于朴实,当后者说出木蛀虫其实有利于和谐的国际关系时,实在为他们不懂得后之视今犹今之视昔的道理而扼腕。此外,值得欣慰的是,斯多亚派的人类中心论随着新天文学的发现而走向终结,虽然传统的目的论犹存,但多少留存了一些浪漫。
章六:全程高能。人们对堕落前的历史神往不已,亚当曾经说着自然的语言,统治着自然万物,然而一旦成为“彻底的地球生物”,话都说不清活也活不久,看来地球真不是什么好地方,幸好堕落的诅咒一视同仁,小动物们也进入了失语时代,罹患冷热病的释经学家断言季节的变化也是由人的原罪引起的。另外两件灾难是大洪水和语言变乱,值得注意的是,那时的西方人认为圆滚滚滑溜溜像鸵鸟蛋的地球才是最完美的,这点确实逊色于东方天地玄黄宇宙洪荒的审美。为了扭转诅咒,人们绞尽脑汁模仿亚当在伊甸园中的活动,亚当的园丁形象也启发着人们犁地耕种(欧洲最著名的六个植物园就集中诞生于这两百年间),一方面他们穷尽花样,甚至主张采取亚当夏娃的素食习惯,另一方面如果尝试太辛苦,他们便认为这不属于那个神圣而优雅的远古时代,可是世上无难事,只要你是抢来的,在“治理土地”总口号的指导下,欧洲人自然而然开始了殖民,此处极为危险地声称殖民是为了培植和宣传宗教,不知上帝他老人家该作何想。关于亚当所操自然的语言,一部分人认为挪亚把那种语言带到了东方,可是汉语的博大精深使得他们望而却步,只能酸溜溜地打道回府。人们便只能妥协地在数学公式中寻找自然语言,牛顿和莱布尼茨发明了微积分,最大程度地将自然界数学化,而牛顿本人终其一生也未能将作用于物体的力的本质弄清,于是人们采取科学手段对自然语言的追求仅仅停留在处理自然物之间的关系,自然物的含义便只残留在比喻性的表达中,自此,两本书彻底分道扬镳,造就了西方社会两个分裂的群体:文人和科学家。
《圣经、新教与自然科学的兴起》读后感(五):圣经与自然之书的平衡
现在对科学的看法最具主流的观点大致是这样的:科学只有完全摆脱宗教的束缚才能昌盛繁荣。在现代人的普遍认知里面,科学的对立面是宗教。著名无神论者萨姆·哈里斯(Sam Harris)提出:“宗教与科学之间的冲突是固有的和(非常接近)零和的。科学的成功往往会以牺牲宗教教条为代价;维护宗教教条总是以牺牲科学为代价。”科学与宗教好似两大冤家,水火不容,科学的进步意味着宗教的衰弱。但这很难解释,为何现代科学的先驱如帕斯卡、笛卡尔、牛顿、哥白尼、培根等都怀有虔诚的宗教信仰?笔者认为,在他们身上的这份宗教虔诚绝非是因时代环境而获致的标签,这信仰乃是他们对世界、对真理的真实态度。本书作者哈里森的研究为这个话题带来一个有趣的角度,他认为现代科学实际上不是通过反对宗教而是通过基督教所固有的某些宗教预设来实现的。其中,对于《圣经》的诠释方法的改变,兴起了自然科学的研究。
《圣经》诠释方式的改变
奥斯丁说,是神使我们能够认识这个世界;而阿奎纳说,是世界让我们认识神。总之,中世纪的人们认为认识神有两种方式:沉思物质世界的秩序和认识《圣经》。自然之书与《圣经》是蕴含真理的两本书。沉思的生活以精神为中心,即便是古希腊的自然哲学,也提倡过一种灵性的生活,研究自然只为更好地培养心灵习性。因此在这一点上,中世纪的神学家与古希腊哲学家能够保持一致。因为自然隐秘了神的知识,它需要《圣经》的启示。由于堕落,人对创世之初最美善的万物之间的秩序早已忘却,这种知识随着堕落已经失去。重建并恢复万物之间固有关系的知识,与人的心灵重建是一回事。因此,中世纪的神学家努力试图解释人与世界的关系,在《圣经》中重新发现自然,对自然的研究也完全是神学的事。为了调和《圣经》中的启示与古代著作的内容相互统一,理性的任务就是运用逻辑和辩证法的工具协调两者之间的矛盾。对《圣经》的权威注释,一直遵循着四重寓意的规则。你会发现处于中世纪时期,对自然的任何解释都与圣经的寓意一一对应。《圣经》中所指的物经由相似性可指称自然界中的其他物,宇宙、世界和人的种种关系可通过这个寓意指称的诠释链条紧密连接在一起,形成一套系统的、完成的诠释图谱。中世纪的思想是一种图像文化,当时由于信众普遍不识字,教会在教导《圣经》启示时更多地采取了礼仪、图像(包括圣堂建筑的呈现等)的方式。《圣经》和自然之书在统一的图谱诠释方法之下,可彼此对照,相互呼应,《圣经》是天主的启示,而自然是天主作品的呈现。
然而之后的宗教改革者摒弃了教会中的传统,精美的十字架龛被拆除、圣像被摧毁、圣事被废除,为了抵制教会的权威,有关寓意诠释的方法被唯独《圣经》的字面主义取代。宗教改革者们意识到,经验世界可以作为文本表述的标准,以此改变中世纪寓意图像的缺陷。《圣经》被不可避免地当作一份历史资料来使用。大学里教授的课本不是教父集而是工具书。校勘学的发展更是掀起革命性的浪潮,揭示出古代著作的文本错误,而不是努力调和它们与《圣经》的矛盾。加之印刷机的发明和普及,从字面意义读取《圣经》成为不可阻挡的趋势,中世纪的图像文化逐渐转为文字文化。过去的那套寓意诠释链条被瓦解,自然界需要重新被赋予意义。
现代科学起源于到这一时期的科学革命。宗教改革可能是一个重要原因,其不仅仅改变了宗教格局,也产生了新的思想。在这个契机中,为自然科学的兴起提供了空间。新的科学依赖于对《圣经》字面意义和历史意义的诠释与根据。与此同时,强调自然之书优于《圣经》的人也不在少数。一位17世纪的英国诗人指出:“在自然之书中,愚蠢的人可以加快思考,未受教育的人可以学习它,不认识字的人可以阅读它。”对自然进行客观研究成为新风尚,就这样,自然之书越来越独立于《圣经》。人们转为相信,自然之物不是有待解读的象征,它们之所以被神设计出来是因为有用,要加以研究的是其用途,这可以帮助神实现其意图。同时,宗教改革家们深信在自然研究方面的细致工作也纯粹是为了恢复元祖亚当曾经在伊甸园拥有的知识系统,以便让整个人类的心灵重新掌握它并得到救赎。伊甸园不再是中世纪所认为的亚当沉思的场所,而是人类获得救赎的现实场景。他们为自然重新赋予了目的,并提供了一种新的理性话语来取代旧的象征秩序。他们把注意力集中在自然物对人类福祉可发挥作用的一面,或许这就是驱动现代科学的动机。如果说17世纪仍然可以在人们的思想观念中找到一种信念,即认为从自然中可以找到神设计的证据,那18世纪出现的休谟则利索地推翻了这一信念。一百年以后的达尔文抛出自然选择理论,进化论的发展影响深远,对神的敬畏之心荡然无存。
科学与世俗化
新教积极投身于自然科学和世俗事务,尤其加尔文派和清教徒强调基督徒应当致力于社会改革的“功用”和“好处”来侍奉神、荣耀神。路德直截了当地说:“人被创造出来不是为了闲暇,而是为了事功,甚至在无罪状态下也是如此。”加尔文在对《创世记》2:15的解释中也指出:“神把那人放入伊甸园去装点它和保有它”,“人被创造出来是为了投身于某种事功,而不是躺下来无所事事、百无聊赖。”神创造世界对人而言是有实际用途的,这点不能说有错,正如科学由此被激励得到发展也是一桩好事。然而,万事皆有利也有弊。宗教改革者所创导的字面主义,导致了自然科学特权话语中的那套系统的、唯物论的对世界的理解。诠释《圣经》方法的转变不啻为认识论的转变,这一转变对人类的命运产生深远的影响。启蒙的科学取代迷信的宗教这一看法常常出现在新教历史学家对天主教的批判著作中。将书籍审查、偶像崇拜、迷信和科学落后与天主教联系在一起的历史叙述版本成为世界的主流,直至今天。近现代有一些学者比如孔多塞、孔德等人就认为宗教阻碍科学发展,这些学者自觉地把这些看法塑造成理论。他们的成就不在于自己本身的哲学或对自然科学的贡献,而是构建出这样一种影响巨大的历史进步观:以孔德的历史三阶段理论为例,即社会从神学开始,经由形而上的阶段,最后发展到实证阶段或所谓科学阶段。科学和宗教在竞争同样的解释地盘,而且只可能有一个赢家。这种零和思维看起来很有道理,其实毫无依据,与历史事实是两码事。
这里不得不提一下,社会学的创设似乎从一开始就是为了打击欧洲天主教的社会秩序,其目标就是设计出一种“社会物理学”来指导并说明社会秩序。他们模仿自然科学的研究进路构建起社会学的科学性,以世俗化的意识形态取代基督教。他们标榜自己和科学一样中立客观,然而这种中立的结果是相信世俗主义,并迅速投入到功利主义的怀抱中。19世纪、20世纪出现的实用主义哲学大受欢迎,社会学和历史学都隐含着激进的进步观。另一个值得说明的学科是人类学,与社会学一样声称自己是有科学性的研究。《金枝》作者弗雷泽就曾认为宗教试图解释世界的野心应让位于自然科学。人类学的奠基者泰勒断言,科学解释和宗教神话解释不可相融,宗教的神话要素注定要被科学取代。人类学认为即便宗教不会消亡,也该退回到道德领域,宗教可以作为道德来源被保存下去。以上两门学科的读物由于其具备的叙事特征(掩盖了事情的复杂性,简单化处理的某种观点或理论)而广受欢迎,受众众多。人们相信科学和宗教正陷入一场永恒的争论,最终科学将取得胜利。科学史被理解成人类反抗宗教束缚不断取得进步的历史,进化论等一些世俗主义的社会理论大获成功。
《圣经》诠释方式的改变加速了自然科学的发展,而然这种加速却打破了中世纪对“两本书”的平衡。在今天科学地位一家独大的局面下,人类对自身理性的崇拜似乎无可阻挡,自然科学的研究不可避免地受到世俗化与功利主义的侵蚀。在饱受大量环境污染、物种灭绝的当下,天主创造的家园还能否成为人类的栖息之地?也许是时候该让我们这些现代人回想起现代以前那个注重心灵培育、以精神为中心的时代。我们应当借鉴中世纪的智慧,在两本书之间找到平衡点,始终保持敬畏之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