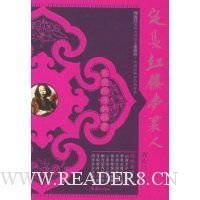
《定是红楼梦里人》是一本由周汝昌著作,团结出版社出版的平装图书,本书定价:24.00元,页数:253,特精心从网络上整理的一些读者的读后感,希望对大家能有帮助。
《定是红楼梦里人》精选点评:
●絮絮叨叨
●周老你想多了,别把现实里的人YY成你梦想中的女子。
●跟张爱玲有什么关系?!
●周汝昌写书太多,张爱玲的原著都没有仔细琢磨就写了这本书(他眼睛不好,是她的两个女儿读给他听的),对张爱玲和他接近的观点则大力表扬,不同的观点就说张爱玲没看明白,而且每一篇之后有一首诗曰,写得很烂
●人家才刚逝世了就马上跳出来吐长久的怨气。真是小气又懦弱。翻完马上把书转手卖了。影响心情。
●大二下
●红楼梦与张爱玲
●补记
●很讨厌这本书~~~
●周先生比张爱玲大两岁,相对于张爱玲的灵性,比较迂腐(从他不认同梦魇二字就可看出,梦魇只是个比喻,而且颇具张看风采,何必较真!),但这种迂腐是可爱的,还透露老者的宽容。有条不紊的阐述自己的观点,张爱玲早已把结论下了,让他欢喜中带着无奈。。。
《定是红楼梦里人》读后感(一):定是红楼梦里人
周老先生和我外公外婆是同时代的人,一看介绍才知道原来外婆和张爱玲同岁!顿时很感兴趣,在书中寻找的是过去那种民国的文风和语言。感觉良好。周先生一生痴迷红楼梦,是令人羡慕的。
如今多少人整天不知道该干什么,真是应该好好反省和惭愧啊!
《定是红楼梦里人》读后感(二):对看
看过《红楼梦魇》就有必要再看看这本,先不说论述正确与否,这本书提醒了我很多没有注意到的角度,可以让我回头再看一下《梦魇》。
这本书比较让人哭笑不得的是周汝昌似乎也没有读懂张的本意,无视张的贾宝玉可能正是脂砚斋同曹雪芹共同经验的合体再现(这个观点接近胡适)的明确表述,而硬是要把张拉到自己脂砚湘云论的统一战线,不知道张地下有知作何感受。
《定是红楼梦里人》读后感(三):握红小札:也说红楼梦里人
某公,居大荒山青埂峰无稽崖。
一日,一女学生前来索字,大书“自是红楼梦里人”付之,其妻暗喜。
又一日,又一女学生前来索字,再书“定是红楼梦里人”付之,其妻又喜。
再一日,忽来两女学生,某公抓破头皮,忽灵机一动,便书“都是红楼梦里人”,其妻甚喜。
又一日,无人前来索字,某公无聊至极。忽思之数十年饮食衣物皆其妻操办之力,待书“总是红楼梦里人”赠之,其妻愤而诟曰:“红楼女儿皆薄命,无故奈何以此语咒我?”其晚,某公不得归家,门外徘徊良久,饥寒苦甚,不得已捶门呼其妻曰:“酸菜总是可以免了,屋角的破毡还是给我扔块出来!”
《定是红楼梦里人》读后感(四):定是红楼梦里人
师兄给了个链接,说是追随一下长恨的脚步。打开,原来是周汝昌的《定是红楼梦里人》。作为红学专家,周在这本书里找到了新视角——张爱玲与红楼梦。尽管一直被长恨戏称古典文化盲,尽管确实对四大名著之类的东西不感冒,却也是翻过两遍红的。然而,如果不是由于高中阶段的一位语文老师对周的推崇,想必没有什么途径听说这样一个名字。
不过,张爱玲是红得发紫了,在今天,尤其是70、80那班人眼里。所以,挂上了张的名字的这本红学著作,一定会挤到畅销书行列里,远离纯粹的学术。
周在序里说——我是才华智慧的崇拜者,尤其是倾倒于曹雪芹所说的“正邪两赋而来”之人,“其聪明灵秀之气,在万万人之上”的才男才女。可是这样的人,平生所历不是“不多”,而是极罕。这使我常以为恨事。后来,终于自言自语:若论真才女,张爱玲其庶几乎?未见第二堪与比肩者也。
这些话,在我听来,并不为过。不管众人眼里的张有多少面,“真才女”的说法想必没谁会否认。
看完这本书,用了一个下午。无它。更喜欢的是书的题目,让人突然想到,张大概生来就是要与红纠缠不清的。
想起那本《今生今世》。我对师兄说,知道为什么长恨会特别喜欢了,因为他喜欢张与胡婚书上的八个字:岁月静好,现世安稳。简单有时就是完美,而完美向来是可望而不可及的,但愿他不会在未来的生活中失望。
都是红楼梦里人呢!
《定是红楼梦里人》读后感(五):一个伪学术者的倒打一耙
从书本身的文字来看,是典型的周氏写法,絮絮叨叨,反反复复,从二重书评的角度来说,本书不仅仅是失望,周老的治学态度甚至很让人鄙视。
不说张爱玲考证的正伪(其实谁又能说清真伪),周老在书中除了翻来覆去一百遍拿《梦魇》前言“生字自动跳出来”、“能省一个字也是好的”来夸奖说事外,几乎未有一处能以平常讨论心来加以注重或肯定。所以不在于你夸不夸,在于夸没夸在点上。
可以说,张氏红楼考证法不敢说后无来者,但至少从所谓“红学”界来看,几称前无古人,她的细琐和熟稔,任是你周汝昌的老师俞平伯也不能与之相提并论,结果惯来琐碎和避重就轻的周老,竟然反过来倒打一耙,回头来指责张的版本考证学“絮絮叨叨,繁琐无趣”,他的那种抒发了一辈子的红楼感情论,至老不休,似乎把“我多么崇拜红楼与曹雪芹”说一万遍就可以立地成佛,至此以专家自居了。
张在《梦魇》中的考证特点就是绝不凭添个人评论,这使得作批评论的周汝昌读者深感不过瘾,他一句话倒说的对,当作好话听就是,“她不像个文学家、艺术家,而像个科学家。”那不知周老说这话时想没想过,自己定位又是什么?我可以说张爱玲对版本学的考据成就,是你周汝昌再活百年也达不到的高度,都不说心态问题,这纯粹是能力水准的差异,你有什么资格在这指手划脚,断这个对判那个错呢?
最可气的是,周的以前著作就是如此,翻古阅今地在犄角旮旯找出零星半语来证明他那些自以为是的观点,本书对《梦魇》大赞特赞之处,就是觉得张爱玲字里行间有同意他所谓独创的“湘云即脂砚”、“湘云与宝玉因麒麟伏白首双星”的断论,这种以是否能辅助个人大论的学术评论标准,实在让人恶心,可全书居然都是这种调调。
还有那些把个鸡毛当令箭,在那儿拿人家海棠无香,鲥鱼多刺的譬喻说事的无聊感慨,更是让人可气而失笑,想必张在天之灵也会觉得这拿她《红楼梦魇》作噱头的破书才真正是“天日无光,百般无味”吧。想周老一生研究无非是翻来覆去嚼那么两个半无甚价值的理论,如今年高更好说是力乏,只管嚼这舌根子来骗钱争名了。
作为二重评论,二重考据,不怕对前人批驳,怕的就是你水平还不及前人零头高呢,让你批驳都是对《梦魇》的玷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