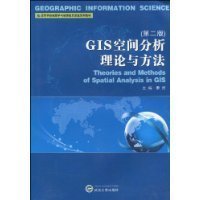
《中国地图学史》是一本由余定国著作,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的平装图书,本书定价:32.00元,页数:271,特精心从网络上整理的一些读者的读后感,希望对大家能有帮助。
《中国地图学史》精选点评:
●余定国是什么神仙,把我想写的都写了。。。哭泣我的作业怎么办啊
●史实分析的错误并不影响结论的正确……
●不強硬地以時代為順序、“科學性”為綱,挺不錯,“尚未解答的問題非常多”
●美国人写起来就是耳目一新啊。
●打破長期以來與朝代為框架、以科學測繪為主要內容的中國地圖史敘述方式。「地圖不只表現兩點之間的距離,它還可以表示權力責任和感情」
●三星半,反思“被定量”的中国地理学史传统,主要是与王庸进行对话,但具体论题稍嫌不给力(特别是对中国传统学术和思想的理解),越看到后面越不想仔细看~ 最出彩的在第一章对传统书写方法的反思
●作者意在与王庸对话,但其中的很多东西王庸都已谈到,越看到后面越觉得作者有点走火入魔了
●见识独到
●对附着于中国古代地图之上的政治、天文学、数学、宗教、艺术等观念的详细阐述,读的过程中数次惊讶于作者的学贯中西、古今及各个学科,意外的是还对于地图和绘画、地图和汉字、地图和汉赋等做了富有新意的讨论。只是最后的结语奇怪到不像是同一个人翻译的。
●作者是人文学科出身,能写到这种水平,实在让人敬佩
《中国地图学史》读后感(一):可读或可不读的《中国地图学史》
《中国地图学史》为美国芝加哥大学版的《世界地图学史》的一部分,由美国华裔汉学家余定国著作,姜道章翻译。
由此阅读可以发现中国古代地图的“左图右史”的图文融合传统与表现功能,还可以看见政治文化中的中国古代地图,其地势山形是与占星术、地籍分野密切相关的,最后也可以将中国古代地图视为特殊的艺术品,具有极高的欣赏价值。
古代中国地图一般都镌刻在石碑,以便于保护与拓印。笔者曾在苏州市博物馆怀着崇念的心情,细细的看过介于观察与文字之间的中国著名的古代地图之一“平江图”。这是1229年,即十三世纪初叶的苏州市地图,采用的界图线条,标明了640种以上的人文和自然现象。人文现象包括寺庙、行政、军事机构、各种作坊、桥梁和道路等等,自然现象有山丘、河流、湖泊、湿地等等。图上还标明方向,图的上方是北方。
当时,极想与这幅著名的古代地图合影留念,结果没有结果——这也是现在笔者购买这本《中国地图学史》的潜意识的内在驱动。
《中国地图学史》中指出:“现存最早的全国总图‘九域守令图”,1121年在四川荥州刻石,存放在荥州府学,流失几百年后,1964年被中国考古学发现。”
不过,在这里“荥州”不晓得具体指那里,因为在中国古代河南的郑州市的荥阳曾为“荥州”。因此,“四川荥州”到底指那里, 有待考证。
本图亦有大量插图:如“古今形胜图”、“长江图”、“海防图”、“清代永定河图”、“1709年中国所绘东半球”……
至于说本书可不读的理由为:一般认为中国的地图不是数学意义上的测绘,因此在现在没有实际上的应有价值;另外还有定量方法上的缺陷。当然,这样的缺陷也存在于中国古代的风水图上,笔者的“谢氏家谱”上的墓穴图就可以为证明。
不管可读或是不可读,开卷总是有益的。如果在你读了《中国地图学史》的某一天之后,万一出现你在旧书肆,或者说在旅行中对中国古代地图有了个人的新发现时,蓦然回首可能会加额庆幸当初幸亏读了《中国地图学史》。
2008-6-16于成都北门天开居
《中国地图学史》,[美]余定国/著,姜道章/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年8月一版,32•00元。
《中国地图学史》读后感(二):一张纸,力透过去与未来(转)
翻开墨香扑鼻的余定国《中国地图学史》,满眼都是发黄的地图,讲述着先辈们的故事。如中国现存最早的、被学者命名为“兆域图”的地图,竟是一张陵墓图,更确切地说是一张陵墓建设规划图。故事是这样的:战国时期,七雄混战,华夏大地弥漫着烽火硝烟,白狄人鲜虞部在河北续建中山国,定都灵寿(今河北省平山县三汲乡)。他们曾两次遭受灭国,之后励精图治,实行游牧和半农经济,国力逐渐强盛,公元前323年,与赵、韩、魏、燕同时称王,为历史上所谓的五个“千乘之国”之一,算得上是“军事第八强国”。到了中山王执政时期(约公元前327—公元前313年),更是国富兵强,连战国七雄之一的燕国都被它打败。
死后的生活对古人来说真是一件大事,埃及的金字塔和中国的秦始皇陵,是比较突出的例子。陵墓是一定要修的,而且规模要宏大(有些人到现在还有陵墓情结)。“兆域图”就是这样一张陵墓建设规划图,于1978年出土,标有内外宫垣、五间祭堂和四间较小的建筑物,总面积将近8万平方米。
这么庞大的规划,最终自然没有完工,因为不过数年,中山国就被赵国灭掉了。而且,据考古发掘报告,这个陵墓在战国时期就已经被盗过。
以上仅仅是中国地图发展的源头,地图所显示的信息却不仅仅是这些故事。学者们根据现有文献的研究表明,中国地图学至少在西汉就已经发展成形,并一直延续到清初,从清初起中国地图学开始西化(在我的脑中一直有个顽固的观点,中国地理学的西化始于晚明,在此以本书内容为准,按下不提)。成形的中国传统地图,大家应该都见过一二,现在跳过传统地图,来谈谈西化的故事。
事情要从欧洲地图学的传入说起,首要的功劳还是归于传教士,其中大名鼎鼎的是利玛窦。利玛窦相信,要让中国人信仰基督教,必须靠间接的方法,如依靠欧洲的科学成就,而不是直接挑战中国人的价值观,地图学就是一个重点。于是,在明万历十二年(1584),利玛窦应肇庆知府的要求,绘制了这幅名为《舆地山海全图》的世界地图。
他把中国特意画在地球中央,并用中文注上各国的宗教仪式和基督教神迹,标上南北回归线、子午线和赤道。
《舆地山海全图》潜藏着一个危险,就是它挑战了中国人天圆地方的世界观,挑战了惟我独尊的帝国观。天下怎么能是圆的?帝国怎么这么不起眼?这样的问题如果上升到政治高度,是极其危险的。因此,利玛窦一直未敢亲自呈送世界地图,或许他明白在专制国家里是没有纯粹学术问题这一说的。幸运的是,它并没引起任何政治麻烦。万历二十八年12月21日(1601年1月24日),利玛窦到达北京。他指导在工部任职的李之藻,学习组织地图空间的托勒密体系,绘制了大到6平方英尺的《坤舆万国全图》。皇帝见后很喜欢,下令用12幅丝帛织成全图,装在6对大屏风里。晴空万里,一如利玛窦的心情。
利玛窦的《舆地山海全图》投入中国,与其说是一张世界地图,不如说是为封闭的帝国,打开了一扇观察世界的窗,一扇通向未来之门,可震撼之余,好像也没什么改变。中国现行的世界地图,依然延续了他当时为讨好皇帝所作的改动,还是没有与世界接轨,中国科学院测量与地球物理研究所高级工程师、博士后郝晓光,深感痛心,正在努力想改变大明帝国以来的错误。
于我,一张地图,更像是一个窗口,张望出去,联结过去与未来。
王冰/新京报 2006-10
《中国地图学史》读后感(三):思想史家眼中的古代地图
中国地图史的发展,并不一定是一种客观技术层面的延伸。相较于民族主义情结主导的地图学史强调制图不断向科学规范化演进的话语叙述,芝大余定国并不关注地图技术推进演变,而关注到地图绘制背后的意图。 作者认为,清代受到西洋的影响,中国地图才成为一门纯粹的客观性学科。此前,中国地图的绘制绝不止于对地表状况表示的范畴,而强调地图多方面的功能。由于中国史地学者忽视了这种内涵,结果使得中国地图学史被曲解成为一种量度与数学方法不断改良的历史。 何谓”多方面功能“?其实在开篇,作者即认为: “地图学与与政治和制度史关系密切,但是地图学的发展跟政治变迁史并非完全平行。” 换言之,作者看来,地图绘制并非的一种单线性的“不断增加数字化或定量化,趋向现代化”的演变进程。如果将中国地图视为对空间进行一种理性的、数学的描述,那么这一观念将导致无法研究地图的所有功用。因此,这本地图学史根本不同于卢良志《中国地图学史》那种从半坡象形文字到清代杨守敬沿革图的叙事,而是分成不同的主题,比如地图测绘的政治环境、地图量度和文字附注的关系、绘制与艺术、中欧地图学的融合。 作者首先认为“只有将数学和地图学连在一起,定量的解释才站得住脚,因此只有与量度数据有关的图像才能视为地图学的,与文字记载有关的图像则不足以视为地图学的。”此语看上去似乎是在黑中国古地图不科学,实则恰恰相反,作者抛出这句话正是提醒读者应跳出现代人审视地图的标准化视角,而应注意到中国古地图本身的政教性。 显然,如今大量的地图在他看来并不是严格意义的“地图”。一方面,一般认为中国最早的地图是战国时期河北中山王墓出土的兆域图就显然是副陵墓建筑设计图,此后的放马滩和马王堆地图,也是出自墓葬,其中一幅纸片残图更是置于死者胸前。另一方面,如马王堆地图本身的比例尺并不确定,图内部也出现了比例尺变异的现象,这就表明它们并不定是科学观念绘画的地图。甚至于马王堆地图上三叶花纹以及太规律变化的曲线,都近似汉代漆器上的艺术,并不一定是写实的驻军图。近千年后,宋代才出现《禹迹图》《华夷图》(1136)这类“记里画方”网格,一直延续到明代罗洪先的《广舆图》(1555)。但作者认为,即使这种标尺也并不意味着其是以比例尺为准则绘制的,如广舆图的比例尺就缩减三分之二。换言之,是一种看似标准实际未必标准的想象图。事实上,明清大量的地图并不采用记里画方的方法绘制,并且常常没有比例尺,(p225)也就说明所谓从宋代建立起标准绘图法的说法并不成立,因此作者推论说: “古地图对于士大夫阶级,具有宗教上的功能——用于表示仪式中各种器物的安排,用于找到各种建筑的吉利地点,用于当做辟邪物以避开邪魔,用于力量的象征以保护通往阴世的道路,此外它还可用于记录天文信息,以帮助解释天象。”(p30) 当然,这显然裹杂着海外汉学家普遍对中国的臆想,而且有以偏概全的嫌疑。但是作者另一个思路却极有见识,他认为: “地图不但用于表示距离,也用于显示权力,用于进行教育,以及用于美学的欣赏。” 换言之,如果我们用现代科学观念审视古代地图,那么以准确性而论,卫星地图完全足矣取代了这些古代地图,如此而言,除了对古代政区名称有了解外,似乎纯无意义。但是如果我们理解古代地图的错误与疏漏其实恰恰意味着当时权力的边境、教育的理念或具体施政的界限,那么古地图反而具有更大的内涵。其实,更晚期的《大明一统志》所配图明确是一种宗藩体系的示意,其精细与标准程度远远不及宋代的禹迹图便足以说明问题。因此作者指明: “中国传统地图是中国传统学术的产物,好的地图并不一定要表示两点之间的距离,它还可以表示权利、责任和感情。”(p30) 书中作者也巧妙地追溯这种渊源,如其对《荀子》“循法则、度量、刑辟。图籍,不知其义,谨守其数,慎不敢损益也。”的解释,便认为地图主要作为一种典章制度的延续传承。而对<周语>:“若启先王之遗训,省其典图刑法,而观其废兴者,皆可知也。”作者也明白,地图不仅是对空间关系的了解,也有助于对道德的了解,就足以见得其见识不同于传统史地学者。俨然已有章实斋官师治教合一的方志纂修观念。正如作者在第三章图像与文字讨论中所表述的: “在中国跟在其他国家一样,政府支持量度技术的主要目的不是为了表示实际的状况,而是为了维持政权的延续。较之维持政府这件大事,对自然的了解当然就是次要的。”(p93) 由此作者也就注意到了土地簿籍、鱼鳞图册和地图的关系,并注意到“唐代流传下来的土地记录簿籍全部是文字说明,但是宋代以来所流传下来的,除了文字说明,常常还有地图。土地记录簿册中古代地图,表示所丈量田地的大概轮廓,所附文字则说明提供量度数字和其他信息。”这正表明地图作为一种财政档案,肩负着具体施政情形辅佐而行的意义。而水文图亦是如此,其中文字被用来描述计量信息和历史事实,地图则被用来表示相关地区的一般自然形势。通过这两个明确的案例,作者指明传统中国舆图绘制中,图上附注的形式不是偶然为之,恰恰表明中国地图作为一种佐助施政的载体,而非一种纯客观的自然实景描摹。 总言之,这种文详图略的载体,恰恰凸显了古地图的实用性。因此,作者提出一个论断,即传统国人认为裴秀制图六法如何如何科学,殊不知,裴秀、贾耽、沈括等一系恰恰注重的不是如何绘制科学的地图,而是重视地图图像绘制的有限性,“地图与注记互补好像才是沈括地图学的基础”(p116)因此,作者注意到,沈括仿照裴秀,有“七法”,其中处转袭裴秀的六法外,却多出了“牙融”、“傍验”两条,其或许正是强调文字考证,而非量度,在地图绘画的意义。所谓“探广内之书,参更四方之论,该备六体”。也就正是在强调对文字资料的查证。 因此,全书作者的思路都是在提醒读者,地图的绘画背后有着绘制者的意图,即使在看似已科学绘制的清代,《瀛环志略》这种地图仍旧寓有作者对时势的态度,在东半球图中,中国的面积远小于非洲,这正是作者为矫枉传统中国世界观的一种态度。显然,这不只是鼓吹科学的地图学,而是一种和政治宣誓。这就反射到另一点上,即清代地图采取图文并行的模式,正是因为“中国传统学者都是为政治目的服务的。这样说并不是贬低定量方法在地图学理论与实际中的重要性,而是要指出中国地图学中为大家所忽略的一方面,即强调以文字说明作为交通媒介的政治意味。”(p108) 当然,全书否定中国地图科学绘制的背后在于认为中国科学绘制地图正是拜欧洲人所赐。全书末章对大清帝国测绘、乾隆内府舆图与耶稣会的几段学术史梳理便意在此处。但作者也认为:”总的来说,各省和地方上的地图工作人员并没有受到朝廷中地图学创新的影响,因为与耶稣会传教士们的接触主要限于朝廷。“ 论说至此,总结全书的逻辑,我们可说作者正是提醒我们应关注古代地图非客观性的那一面,应该跳出现代标准地图的评价维度,试图去理解古代地图绘制蕴含的政制、文化意涵。也就是那种事实与价值的分离。地图是作为一种价值的表现。仅就这点而论,该书就远超中国史家的演进式地图史观,况其又非我华族,能理解这点就更显难能可贵。而最使我本人诧异的是,这本书的作者应该是没读过章学诚的,但他却完美的理解了治教与地志修纂的关系,并且全书均沿用思想史的手法去理解不同绘图者的理念,最惊诧的是,在该书139页,作者还注意到施莱尔马赫诠释学所言之“主观的重建”,显然,其已意识到后人应探究地图创作的主观意涵,例如在对地图题诗的研究中,他即指明”地图上的题诗表示地图读者可以知道地图绘制人的意图,并可根据这种意图来看地图。换言之,地图不仅用于复制,也用于表示绘制人的意图。“(p192)仅就其能兼跨经史、舆地、思想史三点而论,作者实属少见。 这不由得使我想起不就前成一农的一篇帖子,其哀叹为何大量四库中的地图无人重视,我们或许可以回答,正是近代沿革地理将历史地理向标准化、客观化的推进,甚至经史分科等因素,导致历史地理成为一门独立学科,当研究迫切为了对现代“致用”,最终也就丧失或剔除了对古代时间空间做全息理解的路径。当历史地理最终脱离政教性、甚至脱离史学,沦为古地名的考证,或许也就意味着再无人能够明白历史地理学对中国传统政制文化研究的助益,那么,当讨论中国经世之学时,也就只能将此空位拱手让给一批耍嘴皮子的“文化人”了吧。
作者:王晨光 武漢大學博士生
研究方向:中國思想史
《中国地图学史》读后感(四):裴秀与“制图六体”
裴秀与“制图六体”
一、裴秀其人
裴秀,字季彦。河东闻喜(今山西闻喜县)人。生于魏黄初五年(公元224年),卒于泰始七年 (公元271年)。裴秀生于官僚仕族家庭 , 祖父在东汉、父亲在魏晋朝廷中都担任过尚书令。裴秀自幼好学,才华显著,修养深邃,为当时统治者所赏识。因此从年轻时相继在魏晋朝廷中谋事,被曹爽聘为黄门侍郎,从事传达皇帝诏命,掌管皇室机要文书工作。后曹爽因专权图谋不轨而被诛,裴秀受到牵连被罢官。
裴秀34岁时随司马昭往淮南征讨诸葛诞的叛乱。在征讨中为司马昭出了不少的良谋妙策,成为司马昭的得力助手。平定叛乱后裴秀升任尚书,晋封鲁阳乡侯。魏咸熙初年(公元264年)封为济川侯。公元265年晋武帝即位,裴秀任尚书令。泰始四年(公元268年)晋升为司空,成为掌管工程、屯田、水利、交通等事务的宰相级官员。并于在职期间与门客京相璠共同绘制《禹贡地域图》,今亡佚。[有关京相璠事迹参见刘盛佳《晋代杰出的地图学家——京相璠》,《自然科学史研究》1987年第6卷第1期]
二、“制图六体”巡礼
(一)关于制图方法思考的缘由
裴秀职在地官,负责土地使用、水利交通等工作,经常接触各种地理书籍和查看地图。他发现汉代流传下来的地图,“各不设分率,又不考证准望,亦不备载名山大川,虽有粗形,皆不精审,不可依据”。
又由于土地规划、水利建设、军事指挥需要新的地图,于是裴秀提出绘制《禹贡地域图》的设想,并在地图绘制中创立了目前中国地图史上最早的保存最完整的地图制图理论[韩昭庆老师《制图六体新释、传承及与西法的关系》,《清华大学学报》2009年第6期中认为六体应理解为制图“六要素”而非“六原则”]——“制图六体”。
(二)“制图六体”的前世今身
1.“制图六体”的提出:
《晋书·裴秀传》记载了裴秀对之前舆地之图的看法,
“图书之设,由来尚矣。自古立象垂制,而赖其用。三代置其官,国史掌厥职。暨汉屠咸阳,丞相萧何尽收秦之图籍。今秘书既无古之地图,又无萧何所得,惟有汉氏《舆地》及《括地》诸杂图。各不设分率,又不考正准望,亦不备载名山大川。虽有粗形,皆不精审,不可依据。或荒外迂诞之言,不合事实,于义无取”
可见,裴秀是在批判前人的基础上来建立自己对于制图的理解。但被裴秀批判的前代舆地之图真的是“不可依据”吗?
因西汉马王堆汉墓中三幅地图的出土与复原使得今人对裴秀所言不敢盲目相信。谭先生就此问题,在肯定马王堆地图成就的同时,对裴秀所言给予几种解释。即:裴秀所见之图因多为全国性总图,准确性太差;或者裴秀为拔高自己《禹贡地域图》而故意偏低前人制图。
而本人比较支持谭先生的前一个说法,后一说法不置可否。因从《裴秀传》的记载来看,裴秀早年便以“后进领袖”的名望闻名于世。同时其又是为数不多先后得到曹爽与司马家族赏识之人。再者,时安远护军郝诩与故人书云:“与尚书令裴秀相知,望其为益。”可知裴秀的人品素长,不似妄加褒贬先人之辈。因而,极可能是裴秀因职位关系所见之图均不甚佳,因而与自身对舆图的高要求有所出入。这也为其创立“制图六体”打下了伏笔。
2.“制图六体”名称来源
“制图六体”的名称并不是裴秀所起。在《裴秀传》中仅称为“制图之体有六焉”。此名称最早源自朱正元的《西法测量绘图即晋裴秀制图六体解》,而且“制图六体”仅出现在题目中。20世纪50年代王庸先生在编纂中国地图学史时沿用之。因该名称恰当的表达了裴秀的制图方法而被广泛使用。也就是说六体内容早存,而名称是乾隆之后才出现的。这一点是需要明确的。
(三)“制图六体”的内容及解释
1.关于“制图六体”的内容,见于《晋书·裴秀传》,现抄录如下:(这里不引《艺文类聚》原文,两者不同之处参见韩昭庆:《制图六体新释、传承及与西法的关系》一文p113)
“蜀土既定,六军所经地域远近、山川险易、征路迂直,校验图记,罔或有差。今上考禹贡山海、川流、原隰、陂泽、古之九州及今之十六州、郡国、县邑疆界,乡陬及古国盟会旧名,水陆径路,为地图十八篇制图之体有六焉。一曰分率,所以辨广轮之度也。二曰准望,所以正彼此之体也。三曰道里,所以定所由之数也。四曰高下,五曰方邪,六曰迂直,此三者各因地而制宜,所以校夷险之异也。有图象而无分率,则无以审远近之差;有分率而无准望,虽得之于一隅,必失之于他方;有准望而无道里,则施于山海绝隔之地,不能以相通;有道里而无高下、方邪、迂直之校,则径路之数必与远近之实相违,失准望之正矣,故以此六者参而考之。然远近之实定于分率,彼此之实定于道里,度数之实定于高下、方邪、迂直之算。故虽有峻山巨海之隔,绝域殊方之迥,登降诡曲之因,皆可得举而定者。准望之法既正,则曲直远近无所隐其形也。”
2.关于“制图六体”的解释
从裴秀提出“六体”已降,历代文献收录了制图六体的内容。但是一直到清代的胡渭才有对六体的解释,并作为他绘制《禹贡锥指》图的理论依据。其他文献或节选或全文照抄,很少评述。即便如此,至今为止对于“六体”的解释也并不统一,现将几种主要的观点以列表的形式表述如下。
三、“制图六体”的影响
1.“制图六体”与“计里画方”
“计里画方”是在地图上按一定的比例关系制成的方格坐标网,并以此方格网来控制图上各地物要素方位和距离的一种制图方法。而从现有的研究资料看,较多的人认为其起源于西晋时期著名的制图学家裴秀。
因而“计里画方”之法在古代地图的绘制中便成为区分地图绘制质量高低的标准之一,也被历代作为判断是否运用裴秀“制图六体”之法的标准之一。如两宋之际的伪齐年间所做《华夷图》、《禹迹图》和罗洪先的《广舆图》便为计里画方之作。但是“计里画方”之法真的是“制图六体”的衍生品吗?换句话说,“计里画方”之图均是以“制图六体”为方法所制吗?这一点还需要讨论,可参见卢良志:《“计里画方”是起源于裴秀吗?》
2.“制图六体”之“时隐时见”
“制图六体”产生于晋代,而从其产生至近代西法绘图的引入这期间长达近1700年。但在这样长的时段里“制图六体”并未得到前人的足够重视,以至于清末绘图也无一定之规。而这期间出现的几种古地图可零星的反射出“制图六体”的影子,但也可以说的凤毛麟角。如元代朱思本所绘《舆地图》、明代罗洪先的《广舆图》。而明清地方志中的大量配图却良莠不齐,不能得“制图六体”之法。这一现象值得我们去反思与讨论……
现罗列自己所能想到的一些原因
第一、中国古代文人在传抄过程“制图六体”的过程中只重文本而不重实际操作,反映出他们对技术的忽视。
第二、绘制地图之时真正运用“制图六体”所需成本过高。且“中国自古为农业国家……政府编制地图,主要目标在分配土地,征收赋税、城池防守以及交通水利等项,注意于较大比例尺地图的绘制,包括地籍图和政区图等。”[陈正祥:《中国地图学史》]
第三、理论的提出与实际的运用之间存在一定差距。这一点尤其体现在地图绘制领域,如利玛窦17世纪之初所绘《坤舆万国全图》与康熙年间所绘《皇舆全览图》均是在先进技术指导下完成。但对于当时社会的影响并不及两图的名气。
第四,也有一种可能即如海野一隆所言“精去粗存”。可能在中国古代确实有很多精美地图,但因传抄与绘制难度大而渐渐失传,我们现在所见均为下品。这样的可能性也是存在的。
四、“制图六体”新解
“制图六体”辨析所用底本:
《艺文类聚》是唐开国初年由高祖李渊下令编纂的,下诏年份据《唐书·令狐德棻传》记载为唐武德五年(622年),《唐书·儒学 欧阳询传》载武德七年为成书上奏之年。因而可知该书的编纂与成书均早于贞观年间所纂之《晋书》。而且,《晋书》的编纂主要依据南齐臧榮緒所纂《晋书》,其他资料参考不多。使得此书一出便饱受非议,因为其在编修的过程中没有很好的利用之前所编的二十余种晋史,并且很少采录当时所能见到的诏令、仪注、起居注以及文集。故而被当时人指责为“好采诡谬碎事,以广异闻;又所评论,竟为绮艳,不求笃实。”故而,两相比对应以《艺文类聚》所载为主,《晋书·裴秀传》所载为辅。
《艺文类聚》卷六:
“一曰分率,所以辨广轮之度也。二曰准望,所以正彼此之体也。三曰道里,所以定所由之数也。四曰高下,五曰方邪,六曰迂直,此三者各因地而制宜(形),所以校夷险之故也。有图象而无分率,则无以审远近之差;有分率而无准望,虽得之于一隅,必失之于他方;(虽)有准望而无道里,则施于山海绝隔之地,不能以相通;有道里而无高下、方邪、迂直之校,则径路之数必与远近之实相违,失准望之正矣,故(必)以此六者参而考之。然(后)远近之实定于分率,彼此之实定于(准望,径路之实定于)道里,度数之实定于高下、方邪、迂直之算。故虽有峻山巨海之隔,绝域殊方之迥,登降诡曲之因,皆可得举而定者。准望之法既正,则曲直远近无所隐其形也。”
四、“制图六体”新解
逐一辨析:
定词性:不管对于“体”的解读为何,是原则也好是要素也罢。这一“体”字应该代表的是一名词。那么“制图六体”之六“体”应该是制图当中应该考虑到的六个因素与方面。因而我认为这六个要素应该在词性上一致,都应该是名词。
“分率、准望、道里”:
“一曰分率,所以辨广轮之度也。二曰准望,所以正彼此之体也。三曰道里,所以定所由之数也。”
“有图象而无分率,则无以审远近之差;有分率而无准望,虽得之于一隅,必失之于他方;(虽)有准望而无道里,则施于山海绝隔之地,不能以相通;有道里而无高下、方邪、迂直之校,则径路之数必与远近之实相违,失准望之正矣”
quot;分率"应为比例尺;“准望”应为方位;“道里”应为道路距离。前两者不再多言,对于“道里”多说两句:道里乃是“定所由之数”也就是来去的距离之“数”,为什么呢?下文载“有准望而无道里,则施于山海绝隔之地,不能以相通”。怎么解释呢?有了方位但是不知道距离远近,中间相隔山海便不可到达。很好理解,告诉你向东但不知道具体距离,只知道大概,一旦有山海阻隔于途,你便找不到准确的目的地。
因而前三个要素我想可以定性为“数”。不管是“分率”、“准望”、还是“道里”均为“数”,是一个具体的数量。其载“然(后)远近之实定于分率,彼此之实定于(准望,径路之实定于)道里”,这些远近、彼此、径路均为数。而后三者“高下”、“方邪”、“迂直”应该是“校”“道里”之数而衍生的。正所谓“有道里而无高下、方邪、迂直之校,则径路之数必与远近之实相违,失准望之正矣”,关键在于“校”。
“高下、方邪、迂直”:在解释这三个要素之时应以“校”“道里”为理解之前提。
“道里”乃是具体距离。而这个距离并非平滑面上之直线距离。那么为了得到更为精确的距离就应该考虑到“高下、方邪、迂直”。以下一一解释:
“度数之实定于高下、方邪、迂直之算。故虽有峻山巨海之隔,绝域殊方之迥,登降诡曲之因,皆可得举而定者。”
可见,后三个要素是为了解决“峻山巨海之隔,绝域殊方之迥,登降诡曲之因”的。那么遇到这些阻隔又如何将“道里”算的精确呢?
高下:专指山的阻隔,有山便有上下坡,有上下坡便会增加距离。那么对于上下山的距离计算就应该被考虑进去。
方邪:道路的方向不可能与“准望”一致,从一点到一点不可能方向不变。遇到与所达目的地方向不一致的道路也就被称作“邪”。那么“邪”也会增加距离,同样要考虑在内。
迂直:道路并不都是笔直的,九曲回肠之路有之。那么道路的曲折也会使得距离增大,因而在计算“道里”时也应考虑道路的弯曲顺直。
总体来看这三个要素就是一个“度”的问题。高下计算有角度,方邪要有角度,迂直也要角度。这样来看,可以将六体分为两大部分——“数”与“度”。“度”是为了精确“数”而提出的。以上是自己的见解。
复旦 论衡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