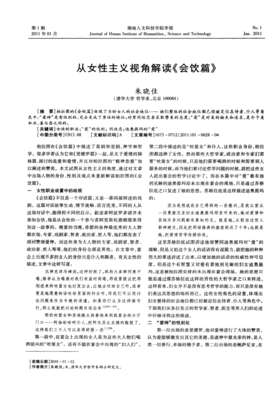
《女权主义理论读本》是一本由(美)佩吉·麦克拉肯 / 艾晓明 / 柯倩婷著作,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的平装16开图书,本书定价:48.00元,页数:666,特精心从网络上整理的一些读者的读后感,希望对大家能有帮助。
《女权主义理论读本》精选点评:
●在提到女同性恋的部分让人又有了新的视角
●这两篇开了我的窍:《此性不是同一性》、《自我的欲望:精神分析的女权主义与主体互涉的空间》。很好很强大
●如果你想了解女权主义,这本书怎么能错过?
●大爱,在读第二遍。向艾老师致敬!
●2015年女权主义理论学习小组的阅读材料。中大社会性别公选课已经停了,素凤姐姐回台湾了,艾老师不带学生了,柯老师出国访学,彩虹小组也变成了非法社团,认识的曾经非常活跃的朋友们,现在基本都在境外读博……
●南岸五楼借阅厅36排B面1架3层;影印书
●某个寒假看得我痛苦的论文集
●买了一本散了架的绝版书
●按需。
●2017.5.19 晴
《女权主义理论读本》读后感(一):女权主义到底在追求什么?
我有一个观点,女权主义者其实不太清楚他们在追求什么。 最近注意到一个现象,奇怪的现象。 按道理说,爱情电影反映了一般人男女理想化的择偶标准。 但是爱情电影在拍摄之前立意之时,必然先定个基调,即使没有形成书面报告,项目经理和导演们潜意识里也必然要考虑,这片子主要是面向男性观众口味的还是女性观众口味的。 面向男观众口味的或女观众口味的戏,我们不难看出来,不用赘述。 奇怪的是, 面向男观众口味的电影里,女主角大多和男主差不多高, 而面向女观众口味的电影里,男主大多比女主高一个头。 而妄图兼顾最广大群众口味的片子里,男女身高差正常,平均半个头。 这就怪了。 我分析大众媒体文化里窥出的民众心理,有这样一个结论: 无论男女,在促使自己的后代尽量体格健壮高大的权衡和给予异性赋权的权衡中,都两害相权取其轻。 男人找一个和自己差不多高的女人不利于支配她, 女人找一个比自己高一头的男人更不利于支配他。 所以可以推出两个结论: 一、女权存在生物遗传利益和自身社会权力的悖论,这是女权的重要阻碍之一; 二、由于男女都不得不向对方赋权,这有利于促进女权。
《女权主义理论读本》读后感(二):女人的声音
很久以前读过这本书。最近看一系列写女性的书,又想起了它。
以前跟老同学Martin聊过这书。那小子是书虫子,而且火眼金睛,我愣怕的那种人。我只喜欢其中一篇,关于月经与战争的。他说,整本书都是垃圾。我怯生生地问,那么谈论女性,跟谈论女人有什么不同?他肥厚的手掌在空气里划过一道弧线,在烟灰缸里掐灭香烟,牙齿碰着牙齿,斩钉截铁地说道:这是个伪问题。我胆气不壮,默默地喝茶。这样的牛人,只能让人失语。他读书多,他思考,他谈锋犀利,话语权自然是他的。就像历史上,男人在言说,女人往往是沉默的或混沌的一群。
科大卫说,有故事的人/家族,通常是社区内有权力的那一群,他们有言说的资格。可以把他这句话,置换来思考女人。前几天向一个日本女学者展示大泽山碑刻资料,她大吃一惊。碑阴题名里,大量的女性没有名字,只有刘门王氏,王高氏等。只有通过这些女人的父亲和丈夫,才能定位到这个女人。她不是一个有绝对坐标的人,只是一张隐藏在男人背后的脸。但是,她们不是沉默的。作为单个的女人,是被隐匿的,被消弭的声音,但是,作为一个群体,她们有自己的声音,也有自己的形象。她们可以组织起来,成立菩萨会/老母会,一起持斋念佛,一起上庙立碑,跟男人一起,在碑上并列。
我不懂女权,也不想懂。女性在我看来,更多是一个指向独立个体的概念。而作为women的女人们,是个可以言说,也可以被言说的群体。循着她们的声音,追寻她们的行为,体察她们的感受和态度,跟她们一起去面对那个时代,或许是可能的。
《女权主义理论读本》读后感(三):寻找父权制的出口:盖尔·鲁宾《女人交易》读后
又名:Gayle Rubin在她那篇惊天动地的研究生论文里究竟写了些什么?
为了帮助阅读:本文提到的社会性别(gender)所对应的二元概念不(仅)是男性/女性(male/female),而(且)是男性气质/女性气质(masculine/feminine)。
--------------
很难想象盖尔·鲁宾写作《女人交易:性的“政治经济学”初探》时只有25岁,这篇文章也只是她在密歇根大学读研时一个荣誉项目的结题论文。而今,当时的研究生论文不仅成了鲁宾学术生涯最重要的代表作之一,也已经成为一系列性别理论读本的必选篇目。在上世纪70年代“第二波女权运动”风起云涌之时,《女人交易》为女权运动家和“妇女学”研究者打开了全新的视野,也由此展开了一个绵延至今的学术领域:社会性别研究。
最近一年多来,我因为种种契机几次读过这篇文章,却始终觉得不得要领。盖尔·鲁宾在短短几十页里,从对马克思主义的批评出发,揭示出一个人类社会最根本的“性/社会性别制度”(sex/gender system);又利用列维-斯特劳斯的人类学理论提出亲属制度的本质——女人作为“礼品”在男人之间交换——如何使每个社会成员被规训为社会性别化的个体,并进入强制异性恋体制;最后引用弗洛伊德和拉康的精神分析理论,探讨性别意识如何内化于个人的心理。
鲁宾利用不同领域的学术成果构筑了一个颇为宏大的统合理论,尝试理解人类社会的性与性别。对马克思主义、结构人类学和精神分析理论不够熟悉的读者很容易陷入鲁宾细密的理论辩驳与商榷,却难以领会她最终托出的那个“性/社会性别制度”——或用她的表达,“性的政治经济学”——究竟有着怎样的价值。
这和我们的期待有关。从一个女权主义者的视角出发来读这篇文章,我们关心的不仅仅是性别压迫在社会中如何运行的问题,更是这种压迫有没有可能被终结的问题。否则,如果一种解释性别压迫的理论没能留出这样一个“出口”,那么这项理论越庞大坚固,尝试挑战这项理论来改变现状也就越困难。
这也是鲁宾在面对马克思主义、结构人类学和精神分析理论时所面临的问题:这些宏大且精致的理论对于分析性别和性的问题不无助益,甚至必不可少,但在它们内部也存在大量性别盲区,总有着把性别不平等合理化的倾向。鲁宾的工作即在于去芜存菁:在不同理论中漫游,收集可兹利用的结论和分析工具,同时挑战它们背后的决定论假设和本质主义,最终为读者提出一个改变性别压迫现况的方向。
马克思和恩格斯
在《女人交易》中,鲁宾主要是从人类学和精神分析这两种理论模型中去选取概念工具的,它们对于亲属关系的理论相互契合,分别描述这项制度的社会层面和个体层面。但在文章开头,鲁宾首先谈论的却是马克思主义——它虽然没能直接为鲁宾提供理论工具,但是为整篇论文提供了关键的批判方法和探索方向。
另一方面,由于“第二波女权运动”本身脱胎于上世纪五六十年代的左翼运动,这一时期的女权理论家也有不少是因不满左翼运动中的性别歧视倾向才另立门户。因此,此时期的女权理论不少都立基于马克思主义,鲁宾也要从前代学统出发,对前辈学者作出回应。
马克思主义的女权主义者尝试用经典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来解释性别不平等现象,争论的一个焦点即在于家务劳动的性质问题:是生产性活动还是非生产性活动?处于生产环节还是再生产环节?属于异化劳动还是非异化劳动?鲁宾在《女人交易》中倾向于把家务劳动置于再生产环节,认为正是女性的无偿劳动(洗衣做饭等)使男性劳动力顺利再生产,最终促使资本家获得了更大的剩余价值。
但是,鲁宾在指出马克思再生产理论的性别盲点之后基本略过了相关的争论,因为“解释妇女对资本主义的用处是一回事,以这个用处来说明妇女压迫的根源则是另一回事。”(p38)对资本主义的分析并不能解释贯穿不同时代、不同文化的性别不平等现象;相反,决定丈夫而不是妻子成为资本主义世界的受益者的,是一些其他的“历史和道德的成分”(马克思语,p39)。
是恩格斯而不是马克思找对了方向。在《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中,恩格斯把“性文化关系”和“生产关系”分开来讨论,提出一个不同于物质生产的“人类自身的生产”,即“人类的繁殖”领域。恩格斯在社会发展史中单独探讨家庭和“妇女的从属”的起源,一方面意味着这个“生育领域”并非从属于生产领域,而是独立存在、贯穿人类社会始终的;另一方面也意味着人类的性并不是禁锢于私领域的生物/文化现象,而是存在着广泛的政治经济联结。
在鲁宾看来,恩格斯凭借直觉已经模糊地提出了一个“性/社会性别制度”的雏形。但他总是趋向于把这个“生育领域”合并进“物质生活”概念,用后者解释前者。而且,《起源》中的结论——剩余产品和私有制的出现导致了“女性历史性的失败”——也实在过于草率和急切。按照这个逻辑,只有消灭私有制的共产主义才能最终拯救女性了。
“女人的交易”
因此,“我们可以模仿恩格斯的方法而不是他的结果”(p43):用审视一个亲属制度理论的方法来分析“物质生活的第二方面”。鲁宾正是循着恩格斯的方向找到了列维-斯特劳斯的人类学。
人类学者认为,在前国家社会中,建立亲属关系和礼品交换都是组织社会的重要行为。列维-斯特劳斯《亲属关系的基本结构》则进一步提出:“婚姻是礼品交换最基本的一种形式,女人是最珍贵的礼物。”(p47)在男性之间交换女性可以使男性们建立起最巩固的社会关系——亲属关系。亲属关系把个人组织起来,组织又为一系列经济、政治、庆典以及性的活动制定规范,并在成员之间分配权力。
列维-斯特劳斯的理论可以为女性普遍的屈从地位给出解释:在“女人交换”中,男性是交换的伙伴,而女性只是交换的导管,权力总是从女性身上流过却从不驻留。更重要的是,这个解释是社会性的而不是生物性的——亲属制度不是一份生物亲属名单,也不是人类性行为的延伸;它是一种组织社会的方式,社会成员的性行为这一生物性事件也同样被其规定。
“女人的交换”还可以解释性/社会性别制度中的更多机制。乱伦禁忌是为了保证交换总在两个不同的人群之间完成。强制性的异性恋保证交换的主体总是男性。性别的劳动分工则导致女性只有与男性才能结成可行的经济单位。
更重要的是,“女人的交换”还可以为社会性别制度提出解释:为了保障亲属制度的正常运行,每个社会个体都必须被社会性别化为二元性别,压抑人格中那些属于对方性别的特征,自我规训为本文化所认可的男性特质/女性特质。
虽然“女人的交换”的想法很诱人,但鲁宾指出这个理论背后同样有着性别歧视的色彩。在列维-斯特劳斯眼中,乱伦禁忌及其实行结果构成了人类文化的起源。也就是说,女人的“被交换”作为一项不可逆转的事实被嵌入到了“从猿到人”的进化历程——这几乎是结构人类学版本的“女性历史性的失败”。
而鲁宾认为这个结论至少是可疑的:“女人的交换”是否在所有族群文化中普遍适用?文化的创造力也为我们的社会留下了自我超越的可能——而不是被“乱伦禁忌”设限。因此,鲁宾把“女人的交换”理论定位为“对性和社会性别社会关系某些方面的敏锐而又浓缩了的领悟”(p50)“建立一个分析性的制度的理论武库的第一步”(p51),而且,它只是文化中的一种现象,而不是文化的定义或是本质。
精神分析学
列维-斯特劳斯的亲属关系理论可以解释性别不平等如何被写进社会结构的语法之中,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理论则关心性别意识如何跨越代际,在个人心理中完成“再生产”,鲁宾从前者进入后者有着从性别压迫的“集体发生学”走向“个体发生学”的内在逻辑。
另一方面,美国精神分析学派的临床实践始终有着“生理结构”崇拜的传统,希望按照所谓“正常”的标准来医治那些脱轨的个体,因此也成了女权主义和同性恋平权运动的大敌。可以说,鲁宾的理论商榷从马克思主义开始,到精神分析结束,好像是从女权主义的一个母体走向(拥抱)她的一个敌人,也必将在这里面临最艰难的战斗。
弗洛伊德在精神分析学中提出了“俄狄浦斯情结”概念,来解释男性如何在幼儿期驯化自己的性欲、形成关于性别的心理机制;但在如何解释女性相应心理过程的问题上他却始终犹豫不决。概括的说,弗洛伊德最终的结论是,本来倾慕母亲的女孩在俄狄浦斯阶段发现自己的阴部不如父亲的阴茎可以使母亲满意,于是女孩意识到自己是被阉割的,转而产生“阴茎妒羡”的情结,并且把对母亲的同性恋慕转变为对父亲的异性恋。
由于弗洛伊德描述含糊,他对“阴茎”作用的反复强调很容易被解释成一种生物决定论,虽然他同时也提出“所有成人的性欲都是心理发展而不是生物发展的结果”(p59)。于是,鲁宾在此引入了法国哲学家拉康对弗洛伊德理论的改造。
拉康把弗洛伊德的“阴茎”视为一种象征:纯粹生物学上的男性器官是无意义的,赋予其一套特殊意义的是“势”,也就是男女两性之间“有权”和“无权”的差异。因此,女性羡慕与嫉妒、为之感到自卑的,并不是男性凸出的生殖器,而是男性在亲属关系系统中所掌握的权力。
在鲁宾的解释下,拉康的精神分析学描述了本来是双性恋的和非男非女的婴儿被拉进亲属关系时,性别文化如何迫使一部分人克制自己的生物性欲,并在心理上适应其性别气质的过程。把精神分析理论和列维-斯特劳斯的结构人类学相互参照,会发现二者若合符节:
“亲属制度要求两性区分,俄狄浦斯阶段划分了两性。亲属制度包含了管理性欲的多套规则,俄狄浦斯危机是对这些规则和禁忌的适应同化。强制性异性恋是亲属关系的产物,俄狄浦斯阶段构成了异性恋欲望。亲属关系基于男女权力的巨大差别,俄狄浦斯情结把男性权力赋予男孩,并强迫女孩适应自己的次等权力。”(p68)
进而,鲁宾批评精神分析学关于女性气质的理论总是想要把女性的克制、痛苦、羞辱和自虐视为正常的、必要的,而不是对整个过程提出质疑。反之,鲁宾提出了一个激进的方向:“妇女们团结起来,去除文化的俄狄浦斯积淀。”(p68)
寻找父权制的出口
初读《女人交易》,读者很可能会感到失望:列维-斯特劳斯的人类学研究说明了性别压迫在不同文化中的普遍性,而弗洛伊德的资料则证明了它的现代性——今天的我们仍然生活在一个父权社会之中。或者如我的一个朋友曾说过的:“如果说性别不平等源于婚姻对女人的交换,那听起来可真够绝望的。”
不过鲁宾已经尝试说明,压迫女性的亲属制度虽然坚固但并非必然,仍然有着改变、颠覆的可能性。她也基于本文对亲属关系的分析给出了几个努力的方向:男性参与育儿可以改变前俄狄浦斯阶段女婴对母亲单方面的爱,接受同性恋会使得女婴的恋母不必被压制,打破二元对立的社会性别则可以终结男人对女人的交换。
在现代国家社会,亲属关系的政治、经济、教育和组织功能已经渐渐被剥离,它所能控制的只剩下了性和社会性别而已。鲁宾说,“女权主义必须号召一场亲属关系的革命”(p68)。
正因如此,鲁宾在文末又回到了马克思主义。如中国读者所熟悉的,马克思主义是一种关于社会历史的哲学,一种关心社会经济的哲学,更是一种实践和革命的哲学。鲁宾也要仿照马克思对人类生产领域的研究,展开对人类性/社会性别制度的研究,建立一套“性的政治经济学”,最终找到性和社会性别革命的方向。
在《女人交易》中,鲁宾始终关心一种反抗的可能性。不同文化中,男人总是在策划如何用婚姻控制他们女性亲属的性命运,而女性总可以用种种方式逃避甚至拒绝控制,以制造紧张事件(p54)。弗洛伊德同样给出了更多的选择:女孩除了“接受自己的阉割”,还可以“干脆发疯,压抑所有的性欲,变成一个无性欲的人;要不就是反抗,坚持自恋和自己的欲望,变成‘男腔的’或是同性恋。”(p66)性别压迫不是一成不变的事实,用王政老师的话来说,“这始终是一个战场。”
鲁宾之所以提出“性/社会性别制度”,而不是接受既有的“父权制”概念来描述这种社会系统,也正是因为“父权制”已经带有先见的贬义,而“性/社会性别制度”是一个中性词——每个社会、每种文化都有它独特的组织性的方式。在不同的系统中,女人也总可以在夹缝中持续地发挥她的能动性。女权主义者必须抛开僵化的父权压迫想象,深入不同时代的不同文化,具体地去考察它们独特的性/社会性别制度和在其中运作的权力关系。(由此我们也可以理解琼·斯科特对历史学者的号召:探究社会性别关系在不同历史情境中分别以何种方式塑造了政治经济、社会和知识结构。)
另一方面,鲁宾强调女权学者不能单独地研究性和性别,“亲属关系和婚姻永远是整个社会制度的一部分,永远同经济政治的安排相联系。”(p76)她想要像马克思主义者和人类学家那样展开宏大的视野,作大规模的分析,把“男人和女人、城市和乡村、亲属关系和国家、财产形式、土地所有制、财富的转换、交换的形式、食物生产技术、贸易形式等等”全部编织在同一个历史进程中,写一部新版的《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p78)——这正是鲁宾为“社会性别研究”这个崭新的学术领域所展开的远大前景。
最后,对于女权运动家,鲁宾也指出了革命的方向:虽然性/社会性别制度并非永远不变地是压迫性的,并且它已经失去了许多传统功能,但它不会在没有反抗的情况下自行消亡;女权主义者必须发起政治行动来重新组织它。而且,这项行动应该消灭创造了性别歧视的社会制度,也应该消灭社会性别本身,但不应该把矛头指向男人。 “一个彻底的女权主义革命最终要解放的不只是妇女。它将解放性的表达形式,并将人类个性从社会性别的束缚中解放出来。”(p69)在此意义上,鲁宾同时论证了基于自由主义的女权运动和同志平权运动的合理性。并且,通过把性和性别整合到同一个理论体系之中,她也模糊地为将来的酷儿理论指出了方向。
--------------
本文写于王政老师《社会性别史研究导论》课后
《女权主义理论读本》读后感(四):盖尔•鲁宾的性(sex)与性别(gender)
导言
本文为美国女权主义人类学家盖尔·鲁宾(Gayle Rubin)的《女人交易:性的“政治经济学”初探》(The Traffic in Women, 1975)以及《关于性的思考:性政治学激进理论的笔记》(Thinking Sex: Notes for a Radical Theory of the Politics of Sexuality, 1984),结合朱迪斯·巴特勒(Judith Butler) 对于鲁宾访谈(“ Sexual Traffic". Differences: A Journal of Feminist Cultural Studies 6/2-3. Summer-Fall1994, pp. 62-99.)的读书笔记,意在整理出鲁宾的两个重要分析工具——性(sex)与性别(gender)的框架。上述三篇文章的中译版全部收录在《女权主义理论读本》(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中,本文的各处引用也来源于此。
《女人交易》
一、写作背景
1970年,女权主义行动者和写作者盖尔·鲁宾参加了Marshall Sahlins在密歇根大学开设的部落经济学(tribal economics)课程。那是她第一次接触人类学,并对其方法产生巨大兴趣,在该课程的学期论文中,她想把结构主义同精神分析理论之间的联系整合起来,把性别与性欲纳入社会框架之中。(巴特勒对此评论到:“我想,《女人交易》的伟大之处在于,它确实提供了一条在精神结构与社会结构的关系当中理解前者的途径。”P463)1975年,《女人交易》用于发表的终稿修改完成。
这篇文章的写作源头是1960年代末的女权主义第二次浪潮,当时的女权主义者们试图解决应当如何思考和说清妇女受压迫的问题。在那时的政治环境中,占主导地位的是新左派;鲁宾当时(1969-1974)也尚年轻,对社会变革保持乐观,认为乌托邦很近。在那时的进步知识分子中,最有影响力的理论范式是不同形式的马克思主义,但是鲁宾和许多研究者后来都得出结论:马克思主义对待性(sex)和性别(gender)的问题存在局限——特别是在性别差异、性别压迫和性欲研究上。鲁宾把《女人交易》作为一种新马克思主义,无论就一般意义上的进步思想,还是就女权主义的特定思想而言,它处于两种主导范式转移的切换点上。(P459)
鲁宾后来提到写作此文的几个问题。一个是她简单吸收了当时的语言表达方式和天真的普遍主义(universalism),试图提出一个关于人类状况的总体描述,这在她写作《关于性的思考》时是被极力避免的。(P484)另外,她没有在这篇文章中区别性欲望和性别,将二者当作同一个社会过程的动态概念。“它可能是也可能不是对于部落组织中性与性别关系的确切评价,但是它肯定不是对于西方工业社会性状况的充分描述。”(P440)
二、性/社会性别制度
《女人交易》首先讨论了经典马克思主义对性别压迫在表述和理论上的失败,然后通过阐释结构主义人类学和精神分析学,发展出了一个较为完善的性/社会性别制度定义。
马克思对于资本主义的分析无法解释妇女和妇女压迫,因为在他那里,包含了整个性别、性文化和性别压迫领域的“历史和道德的成分”被掩盖、被忽略了。而恩格斯为后来的女权主义理论找对了方向:在他的《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中,其最重要的直觉是“性文化关系”能够而且必须同“生产关系”区分开来。(P40)鲁宾进而提出,性本身(社会性别认同、性的欲望和幻想、关于儿童时代的概念)就是一种社会产物,每个社会都有一个性/社会性别制度:在一整套组织安排中,人的性与生育的生物原料既被人与社会的干预所塑造,又在习俗的方式中获得满足。(P41)鲁宾发明这个概念是为了充分描述性欲的社会组织以及性与社会性别常规的再生产(P43),“模仿恩格斯的方法而不是他的结果”,以探究恩格斯没能发现的妇女从属地位的原因。
于是鲁宾考察了这一制度的一个重要形态:亲属关系。“由于列维-斯特劳斯认为亲属制度的精髓在于男人之间对女人的交换,所以他不经意地构造了一套解释性别压迫的理论”(P45)。他使用“礼品”和乱伦禁忌的双重表述构成了“女人的交换”的概念:前国家社会依靠送礼联结起来,婚姻是礼品交换最基本的一种形式,女人是最珍贵的礼物,因为不仅是互惠关系,还有亲属关系,由此被建立起来;乱伦禁忌是将与外族通婚和联盟的社会目的强加在性与生殖的生物性事件上,其结果是维系亲属关系结构。在这个由男人交换女人的组织中,只有男人是受惠者,而女人只是关系中的导管。因此,妇女的从属可以被认为是组织与生产性和社会性别的关系的产物,对妇女的经济压迫是派生的、第二位的。(P51)
通过列维-斯特劳斯对于劳动的性别分工的分析,鲁宾进一步提出,对性的社会组织有赖于社会强加的两性区分(即社会性别)、强制性的异性恋、对于女性性欲的限制及其变化形态。特定的社会与性的制度各不相同,而身处其中的个人却都必须符合一套有限的可能性——因而受到压迫。
精神分析学则解释了把性和社会性别习俗铭刻在儿童身上的机制,鲁宾认为这是一个有缺陷而又未完成的女权主义理论。“俄狄浦斯情节是制造合适的性个人的机器。”(P60)给孩子的选择是有无“势”(the phallus)的选择,负载着两性地位的差异:“势”意味着男人统治女人,意味着“交换者”与“被交换者”之间的差异。俄狄浦斯情结是家庭内部交换中“势”流通的一种表现,也是家庭之间交换中女人流通的一种倒置。“势”通过女人落实在男人身上,它留下的痕迹既包括社会性别认同、两性的划分,还包括“阴茎嫉妒”——“势”文化中女人的忧虑的丰富意涵。
对个人来说,俄狄浦斯危机出现在生物和文化之间的边界上,在乱伦禁忌引入“势”的交换的时候。女孩在此所经历的要比男孩复杂的多:对于男孩来说,乱伦禁忌是对某些女人的禁忌。对于女孩来说,它是对所有女人的禁忌。(P63)当她“承认了她的阉割”,她便接受了一个女人在“势”交换网中只能“享用”而不能得到“势”的地位。当她转向父亲时,她也压抑了自己性动力中的“主动”部分(一部分情欲可能性)。也就是说,女孩在这个过程中被剥夺了。如果俄狄浦斯阶段进行得顺利,她就已经成了一个小女人——女性味的、被动的、异性恋的。由此可见,女人对生活的全部反应是建立在一种强烈的隐秘的仇恨之上的。在达到女性特质的经典讨论中还有另一个要素:小女孩对父亲最初的性动力关系是自虐的。精神分析学关于女性气质的理论认为女性的发展主要基于痛苦和羞辱,而在解释为什么任何人应该乐于做女人时却千方百计地合理化这种安排。作为对“势”文化是如何驯服女人的以及这种驯化对女人的影响的一个描述,精神分析理论对于女权主义政治运动是不可或缺的。
鲁宾发现了弗洛伊德和列维-斯特劳斯理论令人惊异的吻合性。亲属制度要求两性区分,俄狄浦斯阶段划分了两性。亲属制度包含了管理性欲的多套规则,俄狄浦斯危机是对这些规则和禁忌的适应同化。强制性的异性恋是亲属关系的产物,俄狄浦斯阶段构成了异性恋欲望。亲属关系基于男女权利的巨大差别,俄狄浦斯情结把男性权利赋予男孩,并强迫女孩适应自己的次等权利。(P68)然而,“我们能发表的任何一个破坏性的主张都已经滑进了它企图辩驳的形式、逻辑和隐含的假定。”鲁宾指出,精神分析学和结构人类学是现存性别歧视最高级的思想体系。这两种理论自身的不一致暴露了对于妇女压迫问题的感觉迟钝,也抵消了理论本身蕴含的批判意义。(P70)
对此,鲁宾总结,性/社会性别制度并非永远是压迫性的,并且它已经失去了许多传统功能,但是它不会在没有反抗的情况下自行消亡。进而,她提出了女权主义运动的最终梦想:不仅要消灭妇女压迫,更要消灭强制性的性欲和性别角色,建立一个雌雄一体、无社会性别的(但不是无性的)社会,在这个社会中,一个人的性生理构造同这人是谁、是干什么的、与谁做爱,都毫不相干。(P73)
最后,鲁宾回到马克思主义,提出我们应该建立一种性的政治经济学,既注重性文化、经济和政治的互相依靠关系,又能充分认识其中任何一个方面在人类社会中的全部意义。(P78)
《关于性的思考》
一、写作背景
《关于性的思考》产生于1970年代晚期,促使鲁宾写作此文的根本动力是:在理论上,她认为女权主义不足以解释性的实践,特别是性行为的多样化;在实践上,政治形势正在发生转变(当时美国新右派开始占据优势)。该文的构思与《女人交易》没有直接联系,也没有背离《女人交易》所关注的问题,而是一种修正以及处理另外一组议题的方法,尝试研究性差异(sexual difference)与性多元问题。
这篇文章与早期结构主义者聚焦于语言二元结构分道扬镳,转向了后结构主义或后现代主义更为注重的“建构”话语模式。因为一旦远离异性恋的假设,或者异性恋/同性恋的简单对立,就难以按照二元模式来理解性行为的差异,需要更为复杂的分析工具。
鲁宾认为,对活生生的人群的评论应该基于关于这些人群的知识,而不是基于投机的分析、文学文本、电影的再现或预先的假设。(P491)她强调经验式的研究和描述性的工作方式同理论研究同等重要的地位。(P488)这种观念在本文的研究方法上得到了充分体现。
该文的写作背景与当时正在发展的男/女同性恋历史和人类学研究项目相关。该领域的许多研究工作可追溯到1970年代早期,源自同性恋解放运动,这些研究反过来又以早期基于同性恋运动的研究为基础。同性恋研究当时未能进入学术体制,那些从事该研究的学者在学术生涯中付出了高昂代价。但这项学术工作蓬勃发展,而鲁宾的同性恋研究则起步很晚,比如她的旧金山同性恋历史研究计划始于1978年。(P485)
写作该文的最终目的是试图把性实践列入社会阶层研究的庞大目录中,把性作为迫害和压迫的媒介。1960年代,重要的社会阶层分析范畴大多被认为包括等级、阶级和种族。女权主义的伟大贡献之一是将性别引入了社会阶层范畴中。到1980年代早期,鲁宾越来越感觉到,增加性别范畴不能照顾到性压迫的问题,性(sexuality)也应该被包括在分析的范畴之内。(P487)
二、性的政治学激进理论
鲁宾首先提出,性的具体制度形式是人类活动的产物,往往带有政治性。在某些特殊的历史时期,性会处于更尖锐的论争之中,性生活的领域会得到重新建构。接着鲁宾指出了三个这样的时期,分析了以英美社会为主的大量历史材料。19世纪末和20世纪初的性恐慌运动产生的后果,至今仍在性态度、医疗实践、儿童养育、父母焦虑、警察暴行、性立法重组等方面起到深刻作用。也是在这个时期,新的性社群形成,现代意义上的同性恋者出现。批量生产的色情品在市面上出现,性商业的可能性大大扩展。最早的同性恋权利组织宣告成立,对性压迫的最初分析见诸文字。1950年代发生的性压抑是一次回潮,矛头指向二战中所产生的性群体和性的可能性的扩大。同时,同性恋权利组织纷纷建立,金赛发表了对性差异持正面态度的性学报告,女同性恋文学也一派繁荣。《关于性的思考》发表于1980年代,这是一个性正在遭受巨大痛苦的时代。美国右翼发动了性反攻,对1960年代和1970年代初性解放进行反攻倒算。而它也导致了性激进派力量集结和自觉合作。性体系再次发生转变。
鲁宾认为,在西方社会,性受到过分的重视,性迫害却没有受到足够的重视:以性行为或性趣味为基础的系统迫害大量存在;对各色各样的性职业群体的严重惩罚大量存在;青少年的性被否定;成年人的性往往受到各种严苛的限制;对性的表现在法律和社会话语中遭到丑化;某些特殊群体成为当代性权力体系发泄淫威的对象。因此,我们必须鼓励性的创造性,发展一套准确、仁爱、真正自由的性思想体系刻不容缓。一个关于性的激进理论必须能够识别、描述、解释和批判性压迫。
而长期以来,主要有六种性的理论体系妨碍了关于性的正义理论的发展:本质主义、对性的否定态度、对性的错误度量、对性活动价值的等级划分、性危险的多米诺理论以及良性性差异概念的缺席。对于性的本质主义,鲁宾提出建构主义的解决方案,特别是福柯的《性经验史》。但是福柯过于强调性的发生方式,因此否定或缩小了政治意义上的性压迫的现实,鲁宾则认为新的性话语体系应当以压抑的性实践为关注重点。在其他五种意识形态中,最重要的是西方文化中对于性的否定态度,对性的错误度量是这种态度的必然结果。性价值的等级制(宗教的、精神病学的、大众文化的)同种族主义、民族中心主义以及宗教沙文主义的意识形态体系有着同样的运作方式,它们使性特权阶层(异性恋、一夫一妻、婚内、生殖性、非商业)的幸福以及性下等公民的厄运合理化了。性等级制的另一方面就是对于划清和保持好的/坏的性行为之间的那条想象中的界线的需要,在此基础上性危险的多米诺理论表达了对“性混乱”的恐惧。绝大多数性思想体系抱持着“存在唯一理想的性行为方式”的观念,仁慈的性差异的概念缺席,因此一套多元的性伦理学难以建立。
现代性体系发生了重大转变:性的亚群体和性的新类型出现,它们被意识形态和社会的等级制的运作划分成不同的层次;不同的社会价值观制造出关于这些群体的种种想象和虚构。当代性政治应当对这一体系的产生和发展、对其社会关系、对解释其意义的意识形态、对其特有的冲突模式,重新定义和概括。
当代对于性的不公正的抗争中缺少将性迫害的特殊差异放在性分层的一般体系中来看待的尝试。性法律是性分层和性迫害最强有力的工具(P414);而绝大多数日常的社会控制是法外的,这些社会惩罚非常有效(P418)。鲁宾总结,性是压迫的媒介,性的压迫机制不能被缩减为,也不能被理解为阶级、种族、民族或性别的压迫机制。(P420)
性冲突在当代西方政治生活中被完全掩盖了,因此鲁宾试着描述了围绕性体制的斗争。性意识形态在性体验中扮演了极其重要的角色;对性活动的法律规范是另一个战场(P421);此外还有围绕着性领域的性质和界线而展开的隐蔽的斗争(P422)。最重要的一种性冲突是“道德恐慌”(P424)。当这种性的政治机遇出现,散漫的观点汇集为政治行动,社会转变发生。道德恐慌很少能够使社会问题得到任何真正的解决,因为受到攻击的目标往往是幻想的替罪羊,而其最终后果是合法化那些侵犯无害的“变态者”社群的做法。
《关于性的思考》最重要的洞见是对于女权主义在性理论中的特权地位的挑战。她批判了女权主义中与保守的反性话语产生共鸣的部分,以反淫秽运动和文本为其最强烈的表达方式,也批判了处在上述性魔鬼学和提倡性解放的女权主义之间的性中间派这种较为温和的性沙文主义的形式。鲁宾指出,女权主义是性别压迫的理论,如果以为这一立场会自然导致性压迫的理论,那就是混淆了性别和性欲望这两个不同的领域。性体系的发展是在性别关系的背景下进行的,但二者分别成为两种不同的社会实践领域的基础,必须将性与性别区分开来,以便更精确地表达它们不同的社会存在。她认为,性压迫的激进理论脱离女权主义与当代女权主义思想脱离马克思主义是相似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