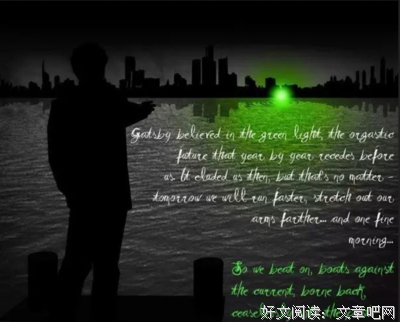
《追寻事实》是一本由【美】克利福德·格尔茨著作,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的平装图书,本书定价:28.00元,页数:196,特精心从网络上整理的一些读者的读后感,希望对大家能有帮助。
《追寻事实》精选点评:
●“但这却是一种很不错的度过人生的方式,它时而引人生趣,时而令人沮丧,却不能不说是富有裨益和充满乐趣的。”
●after the fact 理解在生活之后 追寻事实 (太多陌生的材料了,这也是人类学文本无可避免的“局外人”式的阅读吧 或许当我真正经受人类学的“成丁礼”后再读会有更深的感触吧
●文化的解释看崩溃了的时候就去猛翻这本……
●看完了真的好感动,格尔茨大概是我最喜欢的人类学家了吧
●人类学对我来说是一个大宝库,其中蕴含的财宝不可胜计,当然,这也是因为我从未真正接触过人类学。本书的作者是著名的人类学家,带有自传的性质,对我个人来说这本书再好不过,因为它并不侧重于介绍人类学的知识,而是人类学何以成为了一种智识生活。在这本书里,人类学家的眼光是最吸引我的地方,仿佛一张网,将任何生活中的细节网络在文化的基因里;另一个是人类学在人类生活中的属性,我真希望自己能多了解一点。此书经常让我在读完某句话后回味大半天,一种无语的状态,平静的震惊。真正的大师之作就是如此吧。
●一切理解都要滞后于实际生活。格尔茨在半个世纪之后写下的“实际生活”,在某种程度上已经自然地转化为一种理解,关于爪哇,关于摩洛哥,关于文化人类学的学科规范,关于现代性。而且这种理解通俗有趣,不招人讨厌,这实在比布罗代尔笔下的那些老一辈人类学家前进了许多,也许这正是after the fact的意义和结果。另外,翻译很赞,读起来很流畅。
●随波逐流到田野
●大师的内心世界。象征人类学不是像政治人类学、经济人类学一样是一个分支,而是对人类学定义和发展的一个颠覆。
●我的城镇、我的田野点、我的人类学
●其实我看的不是台版。。。某种意义上讲,可以算做《文化的解释》的下册,把Nuerland错翻成努尔岛。。。。
《追寻事实》读后感(一):索引哪去了?
查了原书是有三个页面的索引,但是中文版没有。
格尔茨用词颇有讲究,索引部分的关键词便显得重要。而各种人名也可以使读者按图索骥,展开进一步阅读。
真不明白为什么学术翻译做到今天,还有编辑允许索引被删去。
《追寻事实》读后感(二):After the Fact
一个人类学家,一个民族志学者,四十年的学术历程,两个田野地点,这就是克利福德·格尔茨对自己的总结概括。
我也想概括下,G爷,您就是那才华横溢好运连连、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主!您是认真玩票儿的吧,超级自我、超级自恋,在各种争论、混战中坚持着“科学的超然和无偏”(烛幽之光,P. 33)。您不可能不知道自己在干嘛,您就忽悠我们也向往那“一种漫游的职业生涯,易变,多彩,自由,有教益,收入还不坏”。(烛幽之光,P. 8)反正“这是一种很不错的度过人生的方式,它时而引人生趣,时而令人沮丧,却不能不说是富有裨益和充满乐趣”。(追寻事实,P. 185)这是您对这一路玩儿过来的陈词?!
今日您又会如何教导人呢?您是不是再也不这么劝人了?这只是您在“死亡登记员找到我之前,编出自己的寓言,为自己的案子申辩”。(烛幽之光,P. 17)您还能看得更远、想得更远吗?重要的是说点什么,而不只是威胁要说点什么,只要发出声音来,这声音就不会完全消失。
我喜欢您讲的一个个小故事,恰到好处地运用着您的人类学反讽、文学修辞,将冷冷的幽默和贼贼的狡猾隐藏在文字的边边角角。“就什么说点什么”,然后就能心平气和地“向前生活,向后理解”继续对意义的追寻。
我获得了哪些教益呢?我想您要表达的意思没有比您已经写下的东西包含得更多了。
《追寻事实》读后感(三):“事实之后“与”追寻事实“
看到格尔茨的照片,这是一个可爱的老头,”可爱“这个词通常是我对一个人的最高评价,不论是从人格魅力上,还是从个人才华上。毫无疑问,他是值得我们敬佩的。
我也决定在两周之后的读书会上来格尔茨专场,虽然预感压力会比较大。
这本书是一本自传式的,回忆式的著作,对自己四十年的人类学研究做了回顾和总结。巧合的是,最近在418博士之家来的几位社会学系的大牛,他们也都是几十年如一日在一个坑里深挖下去的,从他们身上我就觉得板凳还是要坐的久,才会出来真正的成果。不知道自己是不是有这样的耐心和毅力,更重要的是有一种淡然的态度。
After the fact 确实可以有很多种解释方式,只可意会吧。也很好的契合了本书的副标题,”两个国家,四个十年,一位人类学家“,在这些经历的事实之后,格尔茨写下了总结与思考。也可以认为是作为一个人类学家对事实的追寻,希望用自己的视角来记录下当地人的生活,正如他所说的深描的,阐释的方法。
之前看过格尔茨的《文化的解释》,那本书内容比较驳杂,除了文化的含义,还涉及到宗教、民族主义、种族、政治等,还有最著名的”深描“,巴厘岛斗鸡的描写。格尔茨在文化的解释中也写到了印度尼西亚的爪哇岛,写到了印尼的民族主义运动,这一点对我的吸引力很大,原因之一是今年暑假去印尼待了两个月,但后悔的是当时没有看有关的书,对印尼的民族主义缺乏基础性的理解;其次是伊斯兰教对我的吸引力比较大,这是一个神奇的宗教,希望有机会对它做个研究。《文化的解释》是个论文集,不同的部分虽然有逻辑上的一致性,但是没有必然的联系。
《追寻事实》这本书,可读性比较强,我是花了一晚上匆匆读完的,格尔茨写了六个部分,城镇、国家、文化、霸权、学科规范、现代性这几个问题,开篇写到这本书是献给Karen的,也就是他的第二任妻子也是一位人类学家。书中格尔茨其实表达了自己做人类学的一些体会,以及对这个学科存在的困境、在美国逐渐发展起来的过程,作为人类学家在进行研究的过程中立场如何确定。另外他也一如既往地关心新兴民族国家的问题,关心这些民族在现代化的过程中遭遇的现代性问题。
感触最深的是最后一段话,”在如此多元化的时代,在如此多样化的人群中进行如此不确定的追寻,我们不会有很多确定无疑或封闭的感受,甚至可能连自己到底在追寻什么都不太清楚。但这确实一种很不错的度过人生的方式,它时而引人生趣,时而令人沮丧,却不能不说是富有裨益好充满乐趣的。“
这是我理想的生活方式。说到我心坎里去了。
《追寻事实》读后感(四):一种很不错的度过人生的方式
人类学家遭遇新儒家
在柏林,年轻的杜维明在一次会议上提交了一篇论文,论文的主题自然是后来众所周知的“儒家的普世价值”。会上安排的评议人,便是当时已经声名鹊起的克利福德·格尔茨。他总结了杜维明观点中的三个困境:第一,儒家当时很多人未必知道,这只是一个地方知识而已,在这个专题上要与完全没有这方面知识的人沟通;第二,一个现代人要对传统文化进行诠释;第三,这还是一个跨文化的沟通,一个东方人要和西方人沟通。所以,这是跨学科、跨时代、跨文化的交流,这三个力量的结合所造成的语言上的困难是巨大的。格尔茨继续说,我看你的文章,你的语言方式总是“这不是说……”、“这不意味着……”,你为什么用这样的语言方式,是因为你常常被别人认为你就是“这样说”,这不只是语言的困难,更进一步是理解的困难(这则轶事,见杜维明所编《启蒙的反思》一书)。
这次交流的成果后来发表在《东西哲学学报》上。不过遭遇之后,山高水长,杜先生继续做他一辈子都在孜孜不倦的“儒家普世价值”,而格尔茨则以他在印尼和摩洛哥的多年田野调查厚积薄发,以《文化的解释》、《尼加拉》、《地方性知识》等著作成为20世纪后半期最重要的人类学家和思想家之一,当然,这其中也少不了他1995年写作的自传体反思著作《追寻事实:两个国家、四十年、一位人类学家》。
这本自传的副标题有点人生总结的味道,不过但凡能把人生中的四十年用来做一件事情的,总令人肃然起敬。作为二十世纪后半期,著述被人类学及其他社会科学领域引用最多的学者之一,格尔茨以他的解释人类学闻名社会科学界。1960年到1970年,格尔茨在芝加哥大学期间“和那些不安分的同事密切来往来,投入到日后极具影响、也极富争议的重新全面定义民族志事业的努力中。……对人类学的重新定义,在于将对意义的系统研究、意义的载体及对意义的理解,置于研究与分析的核心位置,从而使人类学或文化人类学成为一门解释学的学科。”
显然,青年杜维明遇到的便是这个时期的格尔茨,“跨学科、跨时代、跨文化的交流”不但困扰着文明之间(儒家—西方)的交流,同时也困扰着从事文化“翻译”的人类学家。从格尔茨与杜维明的这番遭遇中,我们似乎已能窥到“文化阐释”的雏形,也能看到这场“科学革命”的萌芽。“在所有的人文科学中,人类学可能是最为质疑自身是什么的学科,而对这些质疑的答复,听起来更像是各种总体世界观或信仰的宣示,而不是对‘一门知识’的描述”。如何为人类学建立一套新规范(方法)是格尔茨面对的难题,为了给出一个答案,他开始了在两个国家之间,四十年的旅行。
从印尼到摩洛哥
当我们站在“事实之后”看待四十年中发生的往事,需要我们回到学术巨人还是学术青年的那个岁月,重新绘制出这场“科学革命”的谱系。
1956年进入哈佛大学师从克拉克洪攻读博士的格尔茨,在皮博迪博物馆偶遇一位教授,“我们正在组建一个团队前往印尼。我们需要两个人研究宗教和亲属关系。你和你太太想一起去吗?”从这一刻起,原本正在无忧无虑区分纳瓦霍人和祖尼人葬礼仪式的格尔茨,便和印尼、爪哇、巴厘岛结下了不解之缘。这个项目意在研究“文化”的各个方面:家庭、宗教、乡村生活、社会分层、市场、华人。在冷战背景下,人类学家前往这个曾经是荷兰殖民地、在二战后苏加诺民族主义高涨情绪、两大阵营角力的国度,颇有些争分夺秒的意思。
与当地革命大学的合作在妥协中化解于无形,格尔茨选择了繁荣的市镇派尔作为调查地点。在之后数年里,格尔茨通过《爪哇宗教》获得博士学位,而印尼却不断陷入各种军事行动。1958年的苏门答腊,信奉伊斯兰教的米南加保人首府巴东镇,和妻子一同调查的格尔茨被叛军阻隔,“母亲在美国打电话给国务院,他们告诉她已经有一个多月没有听到关于我们的消息,只能假定我们已经死亡”。
六十年代中期,印尼爆发大屠杀,自由田野调查的可能取消,“带着两个五岁以下的孩子回到那里,似乎是一件很可疑的事情”。格尔茨陷入了“身为人类学家,却没有民族可供研究”的窘境(有趣的是,奥巴马的母亲斯坦利·安·邓纳姆倒是在1967年带着6岁的奥巴马搬到了印尼雅加达,后来还写成了人类学博士论文《逆境求生:印尼农村的工业》一书)。
剑桥的一次为增进欧美两国人类学共识的会议上,一位看起来不那么社会化的年轻与会者对他说道:“你应该去摩洛哥,那里安全、干燥、开放、美丽,那里有法国学校,食物很棒,而且还是个伊斯兰国家”。会议一结束,格尔茨没有飞回芝加哥,而是直飞摩洛哥。于是,这个美丽的北非国家向没有田野地点的人类学家打开了大门。塞夫鲁镇的居民在之后的几年迎来了不止一个人类学家,除了格尔茨夫妇外,还有后来以《摩洛哥田野作业反思》、《P C R传奇》闻名的保罗·拉比诺(他是格尔茨在芝加哥大学少数几位弟子之一),甚至以民族主义研究享誉学界的厄内斯特·盖尔纳也在附近研究柏柏尔人。
如果说印尼让人看到了新兴民族主义与传统文化的碰撞,那么摩洛哥则展现了殖民主义在传统文化中的烙印———一个启下,一个承上,人类学家靠边上。这十几年里,格尔茨也从芝加哥大学转到了普林斯顿大学的高等研究院,成为该院社会科学的第一个教授,开始了他专职研究的“隐居”生活。
解释变迁中的文化
格尔茨的四十年,从五十年代中期前往印尼田野,到1995年本书英文版出版,是世界发生巨变的四十年。“人类学家站在照片中央……常常穿着白色衣服或野营制服,戴着头盔,兴许还留着一撮胡子;土著们则穿着当地服饰,这些服装通常十分简单,有时也会携带武器。照片的背景中,常会有一些风景,像丛林、沙漠、摇摇晃晃的茅舍、或许还有几只山羊或几头奶牛,散发着边远、隔绝和自给自足的气息,”这类景象已经不复存在。
五十年代末的巴厘岛居民,会问前来研究灌溉水坝、乡村集市、制冰工厂和磨牙仪式的人类学家:“我们想向您请教一个问题。印尼国家广播电台报道说,苏联人朝天上放了一个月亮……它说的这件事到底是真是假?”清真寺的长老会认真询问:“美国宇航员真的登上了月球?”而人类学家可能会和花旗银行副总裁、强生国际副总裁、沃尔沃汽车公司董事长、法国前外长一同访问摩洛哥国王。
五十年代以来民族解放运动在世界范围内的兴起,帝国主义从殖民地的撤退,伴随着传统世界激烈的现代转型,带给所有人———无论是前殖民地居民,还是前往殖民地的研究者,同样还有以往的写作模式———全新的感受,全面的危机。变迁突然而至,昨天刚被记录的习俗,今天已经和新的元素融合,变换了模样;过去权威的民族志,可能连对应的实例都找不到了。所有人都犯难了,事实无从把握,真理不在人类学家手中,一切都在变迁之中:印度尼西亚从激进左派转为右倾军人政府,摩洛哥送走了法国、西班牙殖民者,却旋即迎来了跨国公司,轮换的速度,比来来往往的人类学家还要迅速。
格尔茨祭出了解释学(诠释)大旗,变迁并不比静止更难把握,表面的变化,并不改变文化的内核,关键在于如何发现那些决定文化本身的内在层面。解释学的方法是:通过描述现象的全貌,展现变迁中容易忽略的细节,让文化的逻辑自然显现。其核心在于摹绘细致入微的描述过程,不亚于文学描写的丝丝刻画,当我们将一个市镇的道路交通、经济结构、文化习俗、人口构成等等这些一一记录之后,这个聚落,及其所属于人群文化的盛衰、前世今生,自然全部在每个读者眼前徐徐流动。
知易行难,另一个研究巴西渔村的人类学家康纳德·科塔克同样用了四十多年时间(1962—2005)才细致描摹了当地在全球化中遭遇的变迁过程。而这种文化的解释更需要的是对文化的深刻理解,这无疑需要绵延四十年乃至一生的岁月。
现在,或许我们能更深刻理解格尔茨与杜维明之间的“知识鸿沟”,在谈到“普世价值”之前,或许少不了“对传统文化进行诠释”,只有这样才能避免空乏其辞,而这最需要的就是对某一文化细致的描述。
“追寻事实”是人类学家的工作与追求,“在如此多元化的时代,在如此多样化的人群中,……可能连自己到底在追寻什么都不太清楚”。但诠释文化的过程“却是一种很不错的度过人生的方式,它时而引人生趣,时而令人沮丧,却不能不说是富有裨益和充满乐趣的”。这或许就是2006年去世的格尔茨先生给我们最后的礼物吧。
版次:GB21 版名:南方阅读 社科 稿源:南方都市报 2011-12-11
http://gcontent.oeeee.com/6/e0/6e007f295ed3142b/Blog/d4c/632721.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