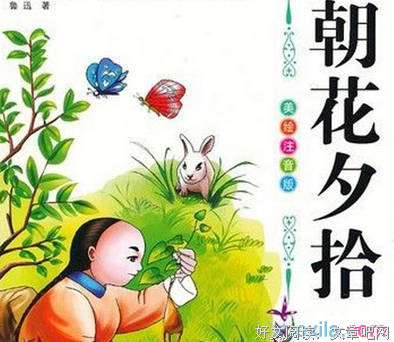
《我所经历的战争》是一本由徐启明著作,九州出版社出版的平装图书,本书定价:25.00元,页数:186,特精心从网络上整理的一些读者的读后感,希望对大家能有帮助。
《我所经历的战争》精选点评:
●不过给夏威打打下手而已……
●徐说刘斐不像共匪
●桂系人物,基本经历了桂系从出现到灭亡过程中的所有战役。
●作为1947年国民党北平行辕总参谋长和1949年国民党第10兵团总司令,《我所经历的战争(1911-1950):国民党第十兵团总司令徐启明口述历史》作者是三大决战之一的平津战役的参与者,因此《我所经历的战争(1911-1950):国民党第十兵团总司令徐启明口述历史》重点回忆了国民党军队在平津战役前前后后的情况,让读者从国民党军队的角度了解这场大决战的详细情形。此外,《我所经历的战争(1911-1950):国民党第十兵团总司令徐启明口述历史》也回忆了作者抗战中在台儿庄血战、蒙城之役及武汉会战中,率部痛击痛歼日寇的经历。
●从民国成立的那一天起,至49年丢掉大陆,整个三十八年间可以说国无宁日,无年不战。在国家层面上说,先是,为民主共和的护国护法讨袁讨逆,后来北伐完成统一,再后来中原大战,剿匪,抗日,及至解放战争,这些战争都是动员国家力量得以完成。除此之外,也有一些局部战争,比如一二次直奉战争,郭松龄反奉西南讨陆等等,乱哄哄你方唱罢我登场,卧榻之侧,都想着吃掉对方,可以说民国前四十年一直在打仗。 于是军人有了用武之地。军人成了一种职业,打来打去,变来变去,投来投去,没有节操的比如冯玉祥、吴化文等,完全深谙厚黑学,相机而动,保全了自己留下骂名。相比之下,从一而终者更得尊敬,历史不以成败论英雄。
●而今策马龙山上,北望中原总慨伤
●封底上说:亲历李宗仁与白崇禧由联合到分裂的内幕,揭示平津战役前夕,李宗仁与白崇禧如何与何应钦结盟,向蒋介石夺权的前前后后,指挥被称为“钢军”的第七军,与四野进行了解放战争后期最惨烈鏖战。这些在书中只是一笔带过,属于不实宣传!
●此人是桂系大将,兵败后之后独自逃生,晚年在台湾以行医谋生。
●口述史提供的周边信息,大抵可信,至于作者亲历的军事活动和政治纠葛,看看就是。作者台儿庄作侧翼,后来一直打游击;剿共时也没什么实际战绩,却总是一副心得满满文武全才的儒将语调,未必能取信于人。对日后留、回大陆的李宗仁、黄绍竑、程思远等人,与迁台的白崇禧、李品仙,下口颇有分别,皮里阳秋。心心念念的是桂系,其次是桂系支撑的民国。
●徐启明个人的战绩还是不错的,不论打日本人还是打共产党。但从他口述中的桂系本位,就可见国民党内部有多么松散、怎么可能对抗共产党严密的政战体制?大陆沦陷后,传主避居港、台,竟然学医有成,也是相当传奇的人生际遇。
《我所经历的战争》读后感(一):李宇清的老上级,书法医术比军事好
本书作者徐启明是重要的桂系将领,本书也基本谈到了桂系从建立到灭败的战役。主要史料参考价值在这一方面。
网友们说徐的军事才能一般,不是在打败仗就是根本没上战场。
我不是军事专家,也不能仅靠这一本书就做出这方面的判断。不过书中可以看出,在连年战斗中,与他资历相仿的人士都升迁快过他,他看起来也没有得罪什么朝中大佬,估计不得升迁的原因就是军事才具一般了。
他当过北平行辕的参谋长,正管着《北平无战事》里那个经常代表李宗仁出面的李宇清,所以说他是李宇清的老上级。
书里附录里有他的几首旧体诗,读起来不觉得很好。
书前附有他誊写的几首诗词,书法倒真是相当不错,看起来非常漂亮,有力。
他自己也提到:
“有人向我求字,裱字画的老匠们不相信一个在枪林弹雨中的战将能写这一手字,不相信我是官拜中将的行辕参谋长。”徐启明墨宝
《我所经历的战争》读后感(二):春秋无义战
从民国成立的那一天起,至49年丢掉大陆,整个三十八年间可以说国无宁日,无年不战。在国家层面上说,先是,为民主共和的护国护法讨袁讨逆,后来北伐完成统一,再后来中原大战,剿匪,抗日,及至解放战争,这些战争都是动员国家力量得以完成。除此之外,也有一些局部战争,比如一二次直奉战争,郭松龄反奉西南讨陆等等,乱哄哄你方唱罢我登场,卧榻之侧,都想着吃掉对方,可以说民国前四十年一直在打仗。
于是军人有了用武之地。军人成了一种职业,打来打去,变来变去,投来投去,没有节操的比如冯玉祥、吴化文等,完全深谙厚黑学,相机而动,保全了自己留下骂名。相比之下,从一而终者更得尊敬,历史不以成败论英雄。
书中记录了军校求学的种种,可以窥见当时朝代鼎革之际的教育理念,军校不仅仅是军校,而是文武并重,甚至微积分这种大学课程也被代入,足见当时的军事教育尤重全面发展,再加上晚清的一点旧学功底,这也是民国时期高级将领普遍都有点底蕴的所在,起码有些人写诗作文不亚于如今的中文系本科学生。
国军将领中文质彬彬文武并重者大有人在,比如张灵甫阙汉骞的书法,黄杰没事儿的时候也能填填词,而徐启明的书法以及诗歌水平也并不低。
由于徐启明在抗战中及解放战争中参战不多,书中多记述战时策略部署,并无细节的描述,也因徐启明只是二线将领,无法亲历高层政斗,而对最高决策的秘辛没有参与展示。封底的推荐语:“揭示平津战役前夕,李白如何与何应钦结盟,向蒋介石夺权的前前后后”多有不实。
解放战争中,不少国民党将领大军被困,只身化妆逃出生天,如王铁汉、李弥等,也有未遂者如王耀武、黄维等,徐启明口述当时队伍建制被打乱,自己化妆逃跑的一段往事,也算传奇。鲁迅说,有两种人要重视起来,一种是坐过牢的,一种是上过战场的。
从战场上扛过来的人,无论是将官还是士兵,无论是自己人还是所谓的反动派,他们的口述历史,不仅可以补遗官方史说,同时对人生也是一种补益。在这样的人生面前,任何小说家的想象力都是苍白的。
《我所经历的战争》读后感(三):刘斐是不是共谍?
我喜欢读杨奎松的书,原因之一就是他立论严谨。在《国民党的“联共”与“反共”》一书中,杨写道:
“传说自30年代即开始暗通中共,导致国民党淮海战役等作战失败的国防部参谋次长刘斐,实际上直到国民党退出大陆,都没有确实证据可以证明其与中共在这段时间里建立有秘密关系。”
在这段话下,还有一个注释:
“有关刘斐与中共建立有秘密关系的情况,近年所传甚广,但根据并不充分。至少依笔者所见文献档案资料,尚未发现刘在其担任国防部参谋次长期间向中共提供过秘密情报。”(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第781页)
但我仍有困惑。因为高华在《六十年后再论国民党大陆失败之原因》中,也给出了两条资料,证明刘斐也是在为中共工作的。一条是长期担任蒋介石已关的熊丸的口述历史。不过,我对这条的可信度还是抱持一定怀疑,因为并无实质内容,且是事后追忆,难免有偏见。一条则是郭汝瑰回忆录所提:
“据郭汝瑰说,情报人员多为单线联系,他本和刘斐关系很坏,只要刘斐有建议,他必反对,后党组织派人带话给他,叫他注意和刘斐的关系,不要被敌利用,他才意识到刘斐也是在为共产党工作。”(《革命时代》,第367页)
郭汝瑰的回忆,是我产生疑惑的主要原因。按理说,这里的回忆,说得有鼻子有眼,按理说,是可信的。郭汝瑰的回忆录,史料价值极高,想必杨奎松是看过的,但他并不采用这个回忆,估计还是觉得没有足够的根据吧。
自2011年起,九州出版社推出的“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口述历史系列”丛书,我很感兴趣。因此购置了数本。近日,读到其中两本,恰好都有涉及到口述者对刘斐到底是不是共谍的个人判断的小资料。读毕,觉得很有意思。口述历史,并不一定能够当做真实的历史来看待,但口述者针砭人物,常能说出一些档案资料所不及的鲜明形象来,故有其重要意义。
一条资料来自徐启明。徐启明是桂系,一直备受李宗仁、白崇禧信任,三年内战,他是一直参与其中的。在李宗仁代理总统后,甚至一度担任了第十兵团总司令,手下掌握着第八绥靖区的四十六军、五十六军和一二六军。后来去了台湾。他对刘斐的评价是:
“刘斐是健生(白崇禧字)一手提拔起来的,抗战初起跟健生到中央,供职参谋本部。此人在纸上谈兵很有一套,很多人赞赏他,但我只认为他小有才而已,不佩服他。他在国内没受完整的军事训练,到日本去学得如何不得而知,但他从没有实际带过兵作过战,因此所拟的作战计划有时是不切实际的,此人是不能担当重任的。由此可见健生用人有时亦不是没有缺点。刘斐随和谈代表赴北平后投共了,有人说他是共谍,我观察他的行动谈吐,不像。至于参谋本部指挥作战的情况我不大清楚,据我所知戡乱时很多命令是总统或其他高级将领直接颁下的,不经过参谋总部,我在北平行辕也拟作战计划,总统一来才做最后决定,总统并没有带刘斐开会,实施后才补报参谋总部,所以要说大陆军事失败是由于参谋本部有个共谍刘斐,还需要找到更多的证据。(徐启明《我所参与的战争(1911-1950)》,第130-131页)
另一条资料来自新近出版的《丁治磐先生口述历史》。丁治磐抗战时打了不少硬战,是个勇将。1946年春,他以第二绥靖区副司令部人员,至青岛组织胶东指挥部,兼任青岛警备司令。47年下令戡乱,当时的政略目标是在双十节前攻下烟台,蒋介石要丁治磐和刘斐商议作战计划。这次作战,政治目的达到了,但是,中共军队,基本上是稍一接触,就退却了,保存了实力,所以作者认为在军事上毫无所获。
在这次作战中,让丁治磐大为不满的是,刘斐等人竟直接部署军队,以范汉杰任胶东兵团司令,带领王凌云第二军、黄百韬第二十五军、李弥第八军、六十四军等四个大军十几个师走大路分四路进攻。因此,在丁治磐看来,“这是战史上的一个很大的教训”:
“其一,国防部不了解前线状况,不该直接部署军队,这应交由我这个前方指挥官负责部署,中央将任务原则交下即可。其二,国防部刘斐等人将四个军十几个师走大路分四路进攻,未预留第二线兵力的部署,显示他们根本不懂大军作战的部署要有梯次。第一线可部署四分之一至二分之一兵力,余留控为第二线,不能齐头并进。……国防部管作战的第三厅应负责,中央统帅部的参谋大多太年轻,有学识,但缺乏作战经验,刘斐不见得是通共才如此部署,可能是他根本不懂如何作战。”(《丁治磐先生口述历史》,第105-106页)
徐启明、丁治磐是长年在外掌兵的,他们对刘斐的印象,有一个共同点,即刘斐并不是通共,很可能是他缺乏作战经验,因此制订的作战计划有时不切实际,甚至会犯有大错。这两位后来都去了台湾,和刘斐也没有私人关系,因此根本无须为他开脱。由此可见,杨奎松的立论还是比较客观,比较严谨的。
《我所经历的战争》读后感(四):近代中国军人的两难
半个世纪以来,台湾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同人在首任所长郭廷以的主持下,积极致力于“抢救历史”的口述资料收集工作。大量在近代政治、军事、思想、文化方面有影响的名人的口述采访记录,最终汇集成为“口述史学丛书”。该丛书卷帙浩繁,凡二百余种,《我所经历的战争:国民党第十兵团总司令徐启明口述历史》便是其中比较有趣的一本。
徐启明,1894年生于广西,桂系高级将领,二战后曾担任过国民党北平行辕总参谋长和第10兵团总司令,是国民党军队中声望颇著的军官。徐完整受过从陆军小学堂到陆军大学的军事教育,这在近代军人中并不多见。同时,他几乎亲眼目睹或亲身经历了包括武昌首义、护法、北伐、抗日、国共内战在内的近代中国所有的战争。他的战争经历,固然是一部近代中国战史的精编版。但更值得玩味的是他的生平和个人经历,这对于了解观察近代军人群体,极具案例价值。
近代以来中国的内忧外患和战乱频仍,为军人集团的存在创造了条件。军阀割据中,军人逐渐掌握政权,成为社会中的显贵阶层。因此,在科举制废除,四民社会瓦解,社会流动呈现出多种方式的前提下,参军便成为很多人向上流动的重要途径。徐启明就是在这个大背景下选择了弃文从武。只是,他的特殊性在于,放弃科举之途而进入陆军小学,实际上是受“学陆军,强中国”思潮的影响,其参军的目的是为了报国,挽救民众于水深火热之中。其后,他进入军校乃至陆军大学,亦是受报国和救民之志的驱动。
清末民初的军事教育,其目的是为了铸造新式军人,进而最终实现中国军队的全面现代化。因此,徐启明在各级军事学校中受到十分严格的训练。这些军校无不是纪律严明,设有各种修身、算术、国文课程,考核甚严,正规程度不亚于一般学校。学校给他们的,亦是一种儒家思想和革命思想相结合的教育。在修身方面,要求学生洁身自爱,非礼勿视,非礼勿听,砥砺品行,以成仁成圣为目标。在思想方面,灌输以学生革命救国或三民主义的思想,使其认识到从军并非为争夺私人利益,而是要牺牲个人的“小我”,成就国家和民族的“大我”。徐启明非常认同于这种教育方式,也时刻以此种理念为行动准绳。因此,从理论上讲,这种军事教育之下培育出的人才,必定是德才兼备的新式军人,对中国现代化的平稳发展起到不可估量的护航之作用。但是落实到实际情况上,却大相径庭。
近代中国军队虽然引进了西方的制度,却没有引进西方的精神。无论是北洋还是国民政府时期,就实质而言,中国的军队都没有成为真正意义上的国家军队,而是隶属于个人或党派团体。在陈志让所谓的“军绅政权”之下,中国军队对外抵御强敌的能力有限,对内开战倒是颇具能力。无论是北洋直皖奉的内部矛盾,还是国民党和北洋的南北之争,或是国民党内各派系以及国共冲突等等,最后无不演变为动用军队,进行你死我活的争斗。即使内部会有正义和非正义之分,实质上仍是不愿通过谈判妥协的方式来解决,习惯性地诉诸暴力。因此,从很大程度上讲,近代军人的主要活动不过是集中于两方面:不断站队和参与内争。
徐启明便是一个极好的证明。武昌起义之后,他的军队本来隶属于广西陆荣廷,但其后,陆荣廷败绩,新旧军人难以并立,他看准时机,转投到新桂系白崇禧的麾下。到了北伐期间,其枪口不但要对准北洋政府,还对准叶挺、贺龙诸军。到30年代,中央和桂系发生各种冲突,徐启明作为桂系重要将领,在外有强敌的关头,又要时刻做好与中央一战的准备。好不容易等到抗日战争,在大别山建立了国军的根据地,却要分散一半精力用于对付共产派。抗战胜利后,徐启明又成为打内战的先锋官,参加了平津战役。总之,徐启明为了生存,必须时刻听从长官的意志,不停地枪口对内,将大半生都耗费在打内战的过程当中。
更为严重的是,那个时代经常缺乏统一的价值观,诠释战争的话语权单方面操之于单方,使得类似的内战常常借种种高尚的名义行之,变成“护国”、“护法”、“戡乱”、“剿匪”,给人以巨大迷惑,似乎那就是神魔不两立的正邪之争。比如1930年的蒋冯阎中原大战,纵横千里,伏尸十万,双方手上粘的都是自己人的鲜血,但在中央的话语中,那是替天行讨。其后,政府以行政命令的方式要求全国各界召开追悼大会,祭奠“讨逆”将士。因此,如徐启明者获得“战功赫赫”的过程,便也是和当年学习军事初衷的一种渐行渐远的过程。
按照研究近代知识分子的套路,很多知识人在学术和政治之间抉择时,往往会陷入彷徨的境地。而如徐启明这样文武全才的军人,有知识有见解,也发现了自己早年学习军事的初衷,与后来所从事的战争在性质上有所抵触。比如,他也常常会在口述中流露出“打内战没意思”的情绪,认为只有八年抗战中所打的仗才有价值。退到香港之后,他解甲归田,转学中医,实际上也正是对早年经历的一种反省。只是,像他这样处于第二梯队的将领,身在历史的激流中时,往往身不由己。而且,即使怀疑也是无济于事。一旦怀疑,则意味着将失去自己作为军人存在的依据,完全否定了自己职业的合法性。
若按照晚清民国初年中国军队现代化的路子走下去,军事上统一政令,军队归属国家,集中力量一致对外,其后招致的祸患或也不至于如此严重。只是,军事总是被政治裹挟捆绑,成为政治斗争的最佳工具。因此,只要军队没有实现真正的国家化、去党化,近代的中国的军事教育无论具有多么良好的初衷,军人无论如何胸怀报国之志,最后都可能被严重异化,成为梦幻泡影。从某种程度上讲,这不仅是个人的悲剧,也是整个民族和国家的悲剧。
《南方都市报》2012年3月11日,韩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