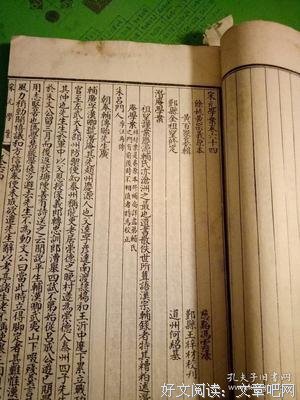
《宋元學案(全四冊)》是一本由[清] 黃宗羲 原著 / [清] 全祖望 補修著作,中華書局出版的精裝图书,本书定价:248.00元,页数:3335,特精心从网络上整理的一些读者的读后感,希望对大家能有帮助。
《宋元學案(全四冊)》精选点评:
●感谢课程,实实在在地精读背诵了不少名篇~
●不研究宋明理学却因为上课整理了几万字的人名别号注释,读完这间标榜经学小学研究的中文系,我最后所获得的,大概就是这些而已。
●备查
●好书是好书,但是出现了一些错别字,尤其《元祐党案》一卷,居然出现句读错误!……推荐读浙江古籍那版的
●二手转出了。读不下。
●态度客观,资料详备,至于若干作者,大多似乎只尽了穷搜博采,然后便雁过无痕。
●好看
●陳氏云造極趙宋,誠不我欺也。蠶絲牛毛,盡在此書矣。
●又杀书头了。需要时用来查阅更方便
●花了大半年时间水过一遍,好歹搞清楚了西山北山龟山玉山兼山,两峰五峰九峰,鲁斋止斋艮斋契斋勉斋等别号指的分别都是谁。
《宋元學案(全四冊)》读后感(一):“学者能常闭目亦佳”
为学大要,只在求放心。此心泛滥无所收拾,,将甚处做管辖处,其它用功总嫌慢。须先就自心上立得定, 决不杂, 则自然光明四达, 照用有余。(《宋元学案·晦翁学案上》)
詹阜民一日侍坐陆九渊,陆九渊曰:“学者能常闭目亦佳。”詹阜民“遂学静坐, 夜以继日, 如此者半月。一日下楼, 忽觉此心已复澄莹中立” ,乃自吟“翼乎如鸿毛遇顺风, 沛乎若巨鱼纵大壑, 岂不快哉”。(《宋元学案·槐堂诸儒学案》)
《宋元學案(全四冊)》读后感(二):名教中自有乐地
国史五千年,英才辈出,太多聪慧俊秀之人,于是湮没无闻了。如果一位古人,他不曾出现于中学教育的历史教科书中(这些教科书的选材自然有它的片面性和取向性),不曾出现于某部戏说历史的电视连续剧中,或者不曾与某一件近似传奇的历史事件有所关联,那么他被普通国人所知道的机会实在可是说接近于无。我曾无聊之间翻看一部《明史》列传部分的目录,发现居然多数是不认识的名字,那感觉倒很像翻看《聊斋志异》的目录。可被录入正史的自然不是寻常人物,可是他们最终在草野间留下了什么痕迹呢?
读这一部《宋元学案》,时常会有相似的感觉。梨洲先生这部书,只求客观地描述理学(宋学)在宋元两朝的师承与发展,而其中记载的诸人物,亦有许多是不为现代人所了解的。比如开篇即为“北宋五子”分别立传。这五人可是说是宋学的开创者,他们继承了晚唐韩愈的思想,加以发扬,最终建立了宋学的完整体系。这五人几乎处于同时代,一脉相传,但是时至今日,他们在人们心里的认知度相差极大。
周敦儒是二程的老师,另一篇《爱莲说》入选中学课本,所以他对于许多人来说并不陌生。二程是朱子学说的本源,另外有“程门立雪”等传说,所以他二人的辨识度也较高。另外两人,张载与邵雍,就没有这种幸运了。
说到张载,恐怕知道他的人不会太多。但是他的几句话应该流行甚广:“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这四句掷地有声的话,虽然是脱胎于“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古训,却更有宏伟博大的气势,把一个人在此生的责任,归纳得如此高尚深远,怎能不教无数热血青年血脉贲张?
冯友兰先生曾把这几句话称为“横渠四句”,先贤中把它们作为座右铭的也不在少数。我们善于引用的邻国,曾经在1988年汉城奥运会开幕式把这几句话放在大屏幕上,据说当时就震惊世界了。这几句话其实不过是横渠先生立言的一个代表,他倒是真为自己作了两则座右铭,分别是《西铭》与《东铭》,《西铭》一篇尤为突出,这一篇虽然“大抵皆古人说话集来”(《朱子语类》),但是其深刻纯粹实是前儒所未发。将个人的小我生命置于宇宙洪荒的无尽中,真正达到天人合一的境界。让人心中升腾起一种类似于宗教的体验般的崇高感,又不至于陷于迷信的虚无。所以朱子说过:“程门专以《西铭》开示学者。“ 正是因为这一篇《西铭》阐发了”仁“的本体,简直是”可达天意“。
横渠先生少年时有志于军事。范仲淹认为他是可靠之材,戒之曰:“儒者自有名教可樂,何事于兵!”横渠先生于是退而求学,卓有成就。后入朝为官,正值王安石第一次变法。先生与安石意见不和,以至贬官出外。最终托病归乡,潜心向学。先生极重礼教,身躬示范,关中风俗一变而有三代之风。他一生著述颇丰,对易学多有阐发。他推崇的“太虚”等思想虽是为对治当时佛学的思潮而发,但是对后世诸儒的学术观点有很大的影响。他一生以名教为己任,认识到宇宙的大秩序反映于人类社会上,就是名教二字,所以教诲每个人都应认清自己所处的位置,承担起自己的使命。
《西铭》一文,字数不多,却值得一生反复吟诵。所以全录于下:
乾称父,坤称母;予兹藐焉,乃混然中处。故天地之塞,吾其体;天地之帅,吾其性。民,吾同胞;物,吾与也。 大君者,吾父母宗子;其大臣,宗子之家相也。尊高年,所以长其长;慈孤弱,所以幼其幼;圣,其合德;贤,其秀也。凡天下疲癃、残疾、惸独、鳏寡,皆吾兄弟之颠连而无告者也。于时保之,子之翼也;乐且不忧,纯乎孝者也。违曰悖德,害仁曰贼,济恶者不才,其践形,惟肖者也。知化则善述其事,穷神则善继其志。不愧屋漏为无忝,存心养性为匪懈。恶旨酒,崇伯子之顾养;育英才,颖封人之锡类。不弛劳而厎豫,舜其功也;无所逃而待烹,申生其恭也。体其受而归全者,参乎!勇於从而顺令者,伯奇也。 富贵福泽,将厚吾之生也;贫贱忧戚,庸玉女於成也。存,吾顺事;没,吾宁也。
“存,吾顺事;没,吾宁也。”活着的时候,我做我该做的事;死去之后,我就得到我应得的安宁。这是最豁达上进的人生境界,是我们每个普通人都应该对追求的,虽然做到这此需要一生的修行。“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这几句话却不是人人可为,只把它们当作人生的终极理想吧。
有趣的是,我们热爱传统文化的总理曾经引用过这四句。而他在另一个场合又引用了王安石”三不足“:”天变不足畏,祖宗不足法,人言不足恤"。这让张载与王安石这一对政见完全相左的古人情何以堪!
《宋元學案(全四冊)》读后感(三):风起萍藻,凉生袖衣。林宗何在,范蠡何归。
是很多年前在读《宋元学案》时候写得瞎话,脑洞特别多,连读书笔记都算不上。后来百度空间没了,今天挖出来,存个档。
我认为,非议中国古典哲学的人,大部分根本没看过《宋元学案》,不懂宋人的宇宙与思辨。不服也不跟你掐。哼。
---------------------------
先拜黄宗羲,黄宗羲的牛逼儿子黄百家,全祖望大人,宋元学案是宝。书么,要考试的时候自然被小盆友瓜分了。幸好手上有张岱年的中国哲学大纲,钱穆的中国思想史六讲,今天借到一本两宋思想述评,是仅剩的看上去不错的存货,船山全书里有正蒙注,加上陈荣捷的资料汇编,反正只考周敦颐,张载,邵雍,应该凑合。
看书有废话,误入欢迎绕道。
1.
在新儒学方面,明承宋是脉络传承,然而宋代在学术,明代更多是行己。
明清之交是中国历史上又一个极有意思的时代,可以与魏晋对观。然而我说魏晋时代丧失的是人生观,是人之于生活的绝望,明清之交丧失的是宇宙观,是人对于世界的绝望。史景迁在写张岱的时候不经意写了一句话,大意是崇祯十七年是张岱对于时间最后的印象。
这句话其实很敏锐,张岱的印象可以概括晚明学者的普遍心理。再之后改朝换元,他们度量时间的准衡失去了。奥古斯丁那话好像是这么说的,时间是一种思想的延伸,是人借由度量自我的标准,人借由时间所谓的过去未来延伸自己,所以时间是意识之存在的标尺。对于他们来说,时间不存在,自我也随之湮灭。整个的身外和自我都失去了标准和意义,却又不能忘记继绝世兴废国的习惯,于是这种挣扎只能反求诸己身,守住良知,在一个不能成圣的时代做自己。
所以顾炎武的那句话其实是很悲壮的,行己有耻,博学于文。这两句话都不稀奇,孔子都说过。然而两句连起来作为座右铭,实实在是有在孤独的暗夜里石匮藏书用血肉之躯炼成标尺刻度的意思。所以晚明人喜欢做史书,读鉴通论,石匮书,日知录,甚至廿二史杂记。传统的史官精神在真实坦率,但这些私人的史书则更加的睿智,锋利。
魏晋人很有意思。看上去是极端自由主义的,但潜意识里都抱着一种“群”的态度和希望,怪也怪在一起,所以各种这个名士团体那个名士团体。魏晋的怪人提供的政治主张和治国策略其实一点不少,只不过这些他们真正想让人注意的东西在时间里淹没在行为艺术之下。反而明清之交的文人,显得沉默,坚韧,并且悲怆。不过这让他们看起来比魏晋精致的风雅多了一点英雄气。
比如说黄百家,他的故事有点像武侠小说。黄宗羲的儿子,著述就算不等身也可以算时代中一流的学者。然而这个内家高手曾经被挑战武功,于是无奈应约,直言不用兵器,恐怕伤人,捡起地上一根树枝,轻松击败刀剑相向的江湖中人。
如果黄百家的故事不可信的话,王阳明打过的胜仗在晚明总共的胜仗里也很可以一数。所以钱穆说,研究王阳明重在年谱。他生命的故事就是他的学术思想,这才是古之学者的风范呐。颜习斋的结交标准最有代表性:忠孝恬淡之君子,豪迈英爽之俊杰。
有点像司马迁的游侠列传是不是。所以,要我说,魏晋之学在通天人之际,明清之交在究古今之变。殊途同归在成一家之言。
2.
从张载《正蒙》开始吧。
一个问题,为毛到了末世的时候儒家就不管用了?战乱瘟疫的时候可以信佛可以信道,就是没人信扯淡狗屁儒家。仁仁仁,爱爱爱,人家把你儿子都吃了你还爱?儒家的原教旨都是很容易证伪的,比如说孔子说仁者是怎么怎么怎么的,那个谁谁谁他就不是仁,虽然他官儿不小然则不能成圣。
可是,你仁你爱你牛逼,那你怎么还丧家狗一个呢?素王,素王管个毛用啊,能吃么?所以儒家很容易就受到了信任危机。它很少去探讨一些不能够证实也不能够证伪的东西,比如说天地是怎么来的,宇宙是怎么运行的。就算说了,比如说易传,那也是为人世的事情找一个规律。
所以要解决儒家的信任危机就只好向道家学习搬出玄之又玄的宇宙论来。要说儒家是教,到了周敦颐邵雍张载这里算是发展完全了。能让人死心塌地相信的东西,只能是无法证实也无法证伪的。新儒家宇宙论的发展应该从周敦颐开始看起。不管先掠过,还是张载。
张载怎么解释那个仁了爱了还是没办法成圣的事儿?德不胜气,性命于气,德胜其气,性命于德。……气质不可变者,独死生修夭而已。
首先,像颜回那样啥都有了就是没命的人不在我讨论的范围之内。
而后,所谓天理也者,能悦诸心,能通天下之志之理也。能使天下悦且通,则天下必归焉,不归焉者,所乘所遇之不同,如仲尼与继世之君也——大意,你自个儿存了天理了,环境不好运气不成,成不了圣,那也不是我的理论的问题,是你的特殊情况。
张载老师这绝对是一个典型的哲学讨论。好比马克思那个交往异化对原始状况的定义,原始状况下我想得到你的东西,并不需要以别的为交换,你就给我。
有人问,谁说的?
马克思说我也不知道。这叫逻辑起点,逻辑起点不负实证的责任>_<(马克思这招绝对是跟黑格尔学坏了= =)
我原来觉得朱熹由释入儒奇怪,现在看起来是少见多怪。两宋的儒家对佛学和道家吸收的那真是不吐骨头的。你看它满口正心,诚意,格物致知,一不小心就发现,诶,这其实是从佛教里化来的。
比如说正蒙里面的大心篇有一句,圣人尽性,不以见闻梏其心,其视天下无一物非我。
最后一句典型的是禅宗的教化,坛经里面有一句,忘了原文是什么,大意就是坐在斗室之间觉得自己被困,不是被斗室困住,而是被心中给自己限定的斗室的概念给困住。
大心这个概念可不就是“无所住”么。
只不过禅宗不讲它的包容性而是讲它的不确定性,但是包容性实际上是被不确定性所概括的。
比如说慧能一个故事,到曹溪宝林山问一个地主划地建寮房,人家问你要多大的地,他就把坐具拿出来给人家看,人想坐具才巴掌大一块,结果那坐具一下子变得特别大,划了四座山中间的所有地方。这个按照禅宗的看法,坐具其实是空的,它可以就一块巴掌那么大也可以包含四座山甚至更大,因而看上去有欺骗性实际上还就是教义之一,意思是不能“着相”OTZ
禅宗讲不确定性为了揭示万事万物"空"的本质,所以要禅定涅槃。
而张载讲"大其心"是为了尽心穷理,物我合一。则天地与我并生。
就是所谓的惟大人为能尽其道,是知立必俱立,知必周知,爱必兼爱,诚不独诚的“尽性”。
诶,所以那句话是张载说的嘛,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
被张载吸收的“释”或者“道”的宇宙观最后都归于无,或者空。但是张载理论里的“气”或者“太虚”倒是与理相一致——气和理是事情的两个方面,一个可见,一个不可见。
所以张载和程朱他们不一样的就在于理气的合一,他的宇宙观从虚无走向了实在。所以我家实诚人王夫之大叔喜欢他。
这是张载的宇宙人生观比单纯化用道家的周敦颐,邵雍高明的地方。虽则他的本体论其实很有问题,既说“太虚”是本体,又把太虚与气二元对立“合虚与气有性之名”,二元对立了又让他们互相转化“虚空即气”。
就不从理论建构的瑕疵来看,后世的新儒家程颢之类的攻讦他大多就是因为这个“虚空”两个字让人联想到异教徒的本无信仰。
3.
今天上宗教课,说一个唯识宗大师说佛教的判教者(大概是说禅宗,净土的)就该被狠狠的骂。而后想到被骂了很多年的宋明理学,顺带儒家。它大概就是从周敦颐开始惹人讨厌的。
太极图说就是个为了把圣人宇宙化的阴谋,前一半基本cos道家的宇宙观只是为了将通书里面“诚”的至高地位在一元论的宇宙中间找到本体的位置。
钱穆这句话说的很一针见血,说先秦儒家是淑世之学,而宋明是自淑之学。
先秦,无论孔孟总有一副就算是丧家狗,虽千万人吾往矣的态度。
圣人对他们而言是一种行为,一种曾经有过而后绝版的典雅姿态。但是从周敦颐开始,圣人变成一种偶像崇拜,真正尸位素餐不食人间烟火起来。
所以他的那派,传下去的程朱,格物致知,主静立诚,越来越往虚里说。以至于王阳明格物终于没啥知,而后有明清儒家的行动派。
孔颜之乐本来的潇洒,到周敦颐终于没有了。他从道家和佛家的手里抢回来崇拜,偶像的样子却已经变了。
至于邵雍,人吧,有时候就很奇怪,明明是一个应该讨厌的神棍偏偏喜欢的很。
莫名其妙的。
算命的人叫神棍,算命算的很准的用什么皇极之数算世算运的叫邵神棍。
邵雍继续把周敦颐从道家那儿借宇宙观的办法发扬光大,只是本体不再是无极而是心。天地万物之道尽之于人。人之所以能尽天地万物之道者,以能尽心知性也。常人执我,至失其性而蔽于情,惟至人能以一心观万心。←抄完道家抄佛家。
周敦颐给儒家加了一个宇宙本体论,邵雍给儒家加上了神秘主义。虽则是北宋五家之一,神棍的学术并不算特别的重要,然而斯人萌。神棍曾经住过苏门山(嵇康也住过),布裘疏食,刻苦自励。而后发现昔人尚友千古,吾独未及四方,于是逾河汾,涉淮汉,周流齐鲁宋郑之墟。
一般这样的牛人都喜欢装,然而神棍先生群居燕笑终日,不为甚异。可惜他口谈德化,要是玄远的话可不就是道家那帮神经病。
可见天下神棍其实是一家。邵雍的学术,自然是皇极经世书。然而他的诗集,叫击壤集。应该典出那首击壤歌:日出而作,日入而息。凿井而饮,耕田而食。不就是他的生活状态么。
这卷诗集,终于名实相副,文笔一般,然而文风潇洒:风起萍藻,凉生袖衣。林宗何在,范蠡何归。他的生活态度,倒很有点先秦儒家的遗风诶。
----------------
当年我懂得真多。
《宋元學案(全四冊)》读后感(四):连凡:《宋元学案》的层次结构与学案设置——兼论全祖望与黄宗羲思想史观之异同
原载《北京社会科学》 2017年04期: 112-128
【摘要】现行百卷本《宋元学案》的层次结构与学案设置,由其实质意义上的完成者全祖望所决定。经过全祖望的修补,在层次性质上,《宋元学案》由比较纯粹的宋元哲学史演变为宋元儒学思想史与文献资料汇编。在结构内容上,《宋元学案》的史学(史传)与学术谱系(家谱)色彩非常浓厚。在学案设置上,全祖望修定与次定的学案反映了全祖望与黄宗羲思想史观的共识,补定的学案反映了两人思想史观侧重点的分歧,补本的学案体现了全祖望对黄宗羲道学思想史体系的突破。全祖望设置学案的标准与黄宗羲在“黄氏原本”中注重思想流派与地域学术的立场相比有继承也有突破,在考虑学术脉络、地位及宗旨等纯学术因素的同时,也注重人品道德与政治事功等方面的因素。这体现了作为哲学史家的黄宗羲与作为史学家的全祖望在思想史观上的差异。
关键词:《宋元学案》;全祖望;黄宗羲;思想史;哲学史
Abstract: The hierarchical structure and XueAn settings of Song Yuan Xue An was decided by its substantive consummator Quan Zuwang. With Quan Zuwang's editing, Song Yuan Xue An changed from a work of pure philosophical history to a work of Confucianism history of ideas and comprehensive collection of Confucianism of the Song and Yuan Dynasties. On the structure, the tints of history and pedigree of Song Yuan Xue An became very strong. On the XueAn settings, the XueAn modified and arranged by Quan Zuwang reflected the consensus of Quan Zuwang and Huang Zongxi, the additional explanations and correction of XueAn reflected different focuses between Quan Zuwang's and Huang Zongxi. The new add-on XueAn reflected Quan Zuwang's viewpoint of history of ideas and its breakthroughs on Huang Zongxi's Neo-Confucianism system. Comparing with HUANG Zongxi's emphasis on schools of thought and scholarship of region, the standard of XueAn settings by Quan Zuwang had both inheritance and breakthrough, giving priority to the consistent ideas and academic standing and purpose, with the consideration of morality and achievement. It reflected different viewpoints of history of ideas between Quan and Huang.
Key words: Song Yuan Xue An Quan Zuwang Huang Zongxi history of ideas history of philosophy
《宋元学案》是由中国清代浙东学派黄宗羲、黄百家、全祖望、王梓材、冯云濠等多位学者合力编成的宋元儒学思想史著作。关于《宋元学案》的层次及其性质,张艺曦通过考察中国台湾“中研院”史语所所藏《宋儒学案》(黄璋校补本),认为此《宋儒学案》是黄璋在保留其祖上黄宗羲、黄百家编纂“黄氏原本”原貌的基础上,适当选取全祖望补修的部分内容而成的。其学案之设置及内容与黄宗羲的《明儒学案》一脉相承。后来王梓材、冯云濠否定了黄璋校补本的编纂方式,改为以全祖望的补修本为底本,并尽可能地修补其中的资料,使得现行《宋元学案》成了一个资料汇编。[1](P451-506)关于《宋元学案》的学案设置及其思想史意义,目前学术界关注较多的是全祖望补本对于黄宗羲道学思想体系的突破。如何俊在《宋元儒学的重建与清初思想史观--以〈宋元学案〉全氏补本为中心的考察》中以《宋元学案》全氏补本为中心,从“突破道统与历史还原”“儒学源流的多元与丰富”“思想史的视野”三个方面考察了全祖望补本对宋元儒学史的重建,以及其中体现的思想史观。[2](P131-145)其后夏长朴在其《“发六百年来儒林所不及知者”--全祖望续补〈宋元学案〉的学术史意义》中围绕着全祖望对《宋元学案》的补修,指出全氏突破了朱熹《伊洛渊源录》的学术史 (道学史) 框架,探索了宋代学术发展的真相,补充了前代学术史之不足,全氏打破了门户之见,贯穿了其实事求是的基本信念。[3](P305-348)然而在学案设置及其所反映的思想史观上,全祖望对于黄宗羲的工作实际上是继承与突破并存,学界关注的往往是两者之异,而忽视了两者之同。
一、 《宋元学案》的层次结构
《宋元学案》作为学案体裁的思想史著作,除了具有沿着思想史的发展脉络 (体现在序录中) 将某一时代的学者分成若干学案 (学派),并以学者的传记及其思想资料作为主要内容这些一般学案体著作 (如《明儒学案》) 所具备的特征之外,由于前后三阶段数十位编者历经150年以上方才完成的缘故,其内容之层次构成的复杂性特别引人注目。简而言之,《宋元学案》的性质与层次,伴随其成书三阶段也经历了“三阶段”的变化,具体分析如下。
1. 《宋元学案》的层次性质
从成书阶段来看,《宋元学案》从开始编纂直至完成出版,时间跨度长达一个半世纪。依据吴光及葛昌伦的研究,[4]其过程大致可分为以下三个阶段:第一阶段 (康熙年间),黄宗羲晚年主持编纂,其子黄百家、弟子杨开沅、顾諟、张采等人具体负责而成“黄氏原本”;第二阶段 (乾隆年间),全祖望修补“黄氏原本”而成百卷本的《宋元学案》,即“全氏修补本”;第三阶段 (道光年间),王梓材与冯云濠在“全氏修补本”的基础之上综合诸本作了进一步的修补订正,最终完成出版。
第一阶段的主要编纂者黄氏父子在其“黄氏原本”中,一方面突破了《宋史·道学传》的程朱理学道统框架,对朱学 (理学)、陆学 (心学)、浙学 (事功之学) 等各学派兼容并包,从而使得《宋元学案》作为宋元儒学思想史的框架大体齐备;另一方面仍然以宋元道学的发展脉络 (先驱·高峰·后继) 为主线并致力于哲学思想的阐释与评价。因此,“黄氏原本”《宋元学案》的形式与内容与黄宗羲独自编著的《明儒学案》一脉相承,都致力于对哲学思想的阐释与评价。从这点来说,“黄氏原本”《宋元学案》可谓是精华版的宋元哲学史 (道学史)。
第二阶段的主要编纂者全祖望在第一阶段“黄氏原本”《宋元学案》的基础上进行大规模增补修订并决定了全书的总体规模。概括说来,全祖望基于其史学家的客观立场,在其补修本中进一步突破了黄宗羲的道学史框架,不仅为思想界的次要人物,甚至为道学所排斥的杂学 (新学·蜀学)、与思想界有密切关系的政治家和倡导者 (范仲淹·欧阳修·赵鼎等),以及与思想界密切相关的政治事件 (元祐党禁与庆元党禁) 设置了学案、略案或党案,又致力于学术源流的梳理 (序录)、师承关系的分析 (周程授受等)、史事的考证 (小传与附录文章)、乡土先贤 (浙东学派) 学术思想的表彰等方面的探讨。因为《宋元学案》的最终定本是以第二阶段的“全氏修补本”为底本,从而导致第一阶段“黄氏原本”的哲学史色彩为全氏的思想史框架所掩盖,并使得《宋元学案》的思想史色彩非常浓厚。学界一般认为《宋元学案》与《明儒学案》之间存在“思想史”与“哲学史”的区别即源于此。
第三阶段也是最后阶段的主要编纂者王梓材与冯云濠在第二阶段“全氏修补本”的基础上综合诸本并作了进一步的修补订正,留下了大量与修订、调整相关的案语,从而使得现行《宋元学案》的序录 (卷首)、学案表与师承关系的标记、小传、思想资料、附录、案语 (文章) 的构成趋于完备,使《宋元学案》在保留其哲学史、思想史意味的同时成为完备的宋元儒学思想文献汇编。这种文献资料汇编的特色在王梓材和冯云濠校订《宋元学案》的过程中以求全责备、述而不作为原则另外编纂的百卷本《宋元学案补遗》中体现得尤为显著。
总的来看,第一阶段的“黄氏原本”《宋元学案》近于“哲学史”,第二阶段的“全氏修补本”《宋元学案》近于“思想史”,第三阶段的“王冯校补本”《宋元学案》近于“文献汇编”。这三部分的内容由于前后三阶段的编纂而层层叠加在一起,从而导致现行《宋元学案》在内容构成上的复杂性。
2. 《宋元学案》的结构内容
现行百卷本《宋元学案》的结构内容,卷首的“宋元儒学案序录”为全书之纲领,其次正文共100卷,由86个学案、2个党案和3个略案构成 (下文有时也概括说成91个学案)。各学案一般由学案表、序录、小传、思想资料、附录五部分构成。全书共为2428位宋元时代的学者立了小传。除去小传而留下了思想言论与文章的学者 (包括编纂者本身) 共276人,其中209人包含于《宋元学案》收录的2428位宋元时代的学者之中。其他包括编纂者在内的67位则主要是明清两代的著名学者。此外,《宋元学案》的正文100卷与卷首中还收录有编纂者黄宗羲、黄百家、全祖望等人的2238条案语或附录文章,反映了编纂者的编纂工作与学术思想。
具体从学案的结构来看,首先卷首的《宋元儒学案序录》原本是全祖望所作,共计一卷作为全书之纲领,其后由王梓材将其分散到各学案正文之前的同时,卷首也予以了保留。接着正文凡一百卷,共计86个学案,2个党案 (《元佑党案》《庆元党案》) 和3个略案 (《荆公新学略》《苏氏蜀学略》《屏山鸣道集说略》)。其中有9个学案分为上下两卷。百卷之中有59个学案 (共计67卷) 出自黄宗羲的“黄氏原本”,占总卷数的三分之二,其内容主要由黄氏父子等人编纂,再由全祖望加以修订和增补。此外的32个学案 (共计33卷) 则由全祖望所创立,占总卷数的三分之一,其内容由全祖望所编纂。进而全祖望还确定了全书一百卷的构成、顺序和命名。此外由于黄氏原本与全氏修补本在流传过程中佚失了部分内容,因此王梓材和冯云濠也补修了一部分内容 (司马光的“涑水学案”与两个党案等)。总的来说,黄宗羲、黄百家和全祖望三人是《宋元学案》成书过程中最重要的编纂者。
深入各学案内部来看,《宋元学案》中各学案的构成一般开头用“学案表”揭示其中所收学者间的师承关系及其传承谱系,其次通过“序录”简要说明案主的思想特色或评价作为各学案之纲领,接着是记录案主生平事迹及学术活动等内容的小传,其次是从文集、专著等原典文献中辑录的案主思想资料,最后是补充说明案主的事迹或学术评论等内容的附录。案主之后,[5]与案主有师承关系的人物被区分成“讲友”“学侣”“同调”“门人”“私淑”“家学”等 (载于各卷卷首的“学案表”),同样排列其传记、学术资料、附录等内容。此外全书中随处可见编纂者自己的案语。
根据笔者对《宋元学案》全文所做的统计分析,《宋元学案》共为2428位宋元时代的学者立有传记。据此则《宋元学案》中所收学者的数量达到了《明儒学案》所收学者数量 (208位) 的十倍以上。[6]究其原因,相比于明代思想史而言,除宋元思想史的流派要更加复杂多端的客观情况外,主要还是因为黄宗羲与全祖望的编纂旨趣造成了两书性质的差异。黄宗羲独自编纂的《明儒学案》以阳明学为中心而展开,近似于我们今天的“哲学史”(“道学史”),其所收录人物基本都是明代哲学史上有哲学著作或言论流传下来的重要学者, 数量自然有限。而实际成书于全祖望之手的《宋元学案》则近似于我们今天的“思想史”,其思想史视野突破了《明儒学案》的“道学史”范围,对道学之外的各派兼收并蓄。其史学 (史传) 与学术谱系 (家谱) 的色彩非常浓厚, 其所收录的绝大部分人物是哲学史上次要甚至没有什么影响的人物。事实上《宋元学案》中绝大多数人物只记载有姓名或很短的小传,没有收录思想资料的文章和言论,在思想资料和附录中留有言论或文章的宋元学者仅有209人,只比《明儒学案》多出一人。如果黄宗羲生前能完成《宋元学案》的编纂,那么今本《宋元学案》可能只会收录这么多人。
《宋元学案》中除了传记之外,思想资料和附录中留有言论或文章的宋元明清学者共有276人,占全部人数的11%。这276人的时间跨度也很长,从北宋仁宗朝前后直到清代道光年间共约800年。其中209人包含在2428位宋元时代的学者之中,《宋元学案》中收录了他们的思想资料作为全书的主体。除此之外的67人,如刘宗周 (引语有62条)、高攀龙 (引语有76条) 等,包括黄氏父子等编纂者自身,主要是明清两代的著名学者,《宋元学案》中留有他们的大量评论和阐释之文章和言论。合并以上留有小传或言论的人数并去掉部分重复的,《宋元学案》的全文中共收录有2495位学者的资料 (传记、文章、言论等)。这样,《宋元学案》中收录了两宋 (包括金朝) 和元代的几乎所有儒者及其学派之思想资料,并明确其思想之特色,进而论述其学术之传承及其流派之影响,并将宋、元两代的儒学思想予以体系化,提供了基本的材料、评价的标准和思考的方式,可谓是宋元思想史研究领域中的必备参考书。
总而言之,经过全祖望的修补,《宋元学案》的资料和规模得到极大扩充,由比较纯粹的哲学史演变为宋元儒学思想史及文献资料汇编。虽然这样做提高了其文献学与史学考证的价值,但同时也给研究带来了困难, 其中值得注意的地方颇多。以下将理论阐释与统计分析、宏观分析与微观分析等方面结合起来,在上面分析的基础上,通过对《宋元学案》的学案设置及其学术意义的详细探讨,阐明全祖望与黄宗羲各自的思想史观并比较其异同。
二、 《宋元学案》的学案设置及其学术意义
1. 从《宋元学案》的成书过程考察其学案从草创到确立的过程
黄宗羲在其编著的《明儒学案》中兼顾“点”--学术宗旨 (持有独特宗旨的学者) 与“面”--地域学派 (具有共同思想倾向的地域学术集团),并以师承关系为纽带将各学派的创始人及其弟子、同调等集中起来,从而将明代儒学从大的方面划分为19个学案和学派 (为避免篇幅不平衡,许多学案被分成了一、二、三等多卷)。其后黄宗羲在编纂《宋元学案》“黄氏原本”时也沿用了这种做法,主要依据宗旨和地域两个标准,一方面如设置“濂溪学案”(本文中引用《宋元学案》时一般略去书名,只举卷数和学案名) 等“北宋五子”的诸学案那样,为开宗立派的学者单独设置一学案并收录其同调、门人等相关人物。一方面如设置“永嘉学案”(浙东永嘉学派)、“金溪学案”(江西陆学)、“北方学案”(元代北方朱学)、“四明朱门学案”(四明朱学) 诸学案那样,为属于同一思想阵营的地域学术团体设置了学案。黄氏父子等编纂的“黄氏原本”虽已亡佚,无法直接得知其学案设置的情况,但《宋元学案》最后的编纂者王梓材在各学案全祖望序录之后的案语中,一般都会注明“黄氏原本”与“全氏修补本”在学案设置及其名称上的差异。现行本《宋元学案》中的学案设置虽完全依据“全氏修补本”,但总结全书中王梓材的案语,仍可大致了解“黄氏原本”中学案 (共计40个) 的概要。按学案先后依次排列如下:安定学案、泰山学案、康节学案、濂溪学案、明道学案、伊川学案、横渠学案、上蔡学案、龟山学案、廌山学案、和靖学案、刘李诸儒学案、蓝田学案、永嘉学案之一、武夷学案、豫章学案、横浦学案、刘胡诸儒学案、艾轩学案、紫阳学案、南轩学案、东莱学案、永嘉学案之二、永康学案、金溪学案之一、金溪学案之二、金溪学案之三、勉斋学案、潜庵学案、潜室学案、南湖学案、北溪学案、沧洲诸儒学案、岳麓诸儒学案、丽泽诸儒学案、鹤山学案、西山学案、金华学案、双峰学案、四明朱门学案一、四明朱门学案二、新安学案、北方学案、草庐学案。
其后全祖望在补修《宋元学案》时,从“黄氏原本”中的学案中分出若干学案 (出自黄氏原本的共有59个学案),在此基础上又另立了32个学案,从而决定了现行本《宋元学案》91个学案共100卷的框架规模。全祖望之后,余姚黄宗羲家族的后裔黄璋等人在黄氏原本及全氏修补本的基础上编纂了“黄璋校补本”(包括浙江余姚梨洲文献馆藏“黄璋校补稿本”与台湾中研院史语所傅斯年图书馆藏“黄璋校补誊清本”等版本),[7](P162)但其意图实在于否定全祖望补修本中的学案设置及思想史框架并重新回归其祖黄宗羲的“黄氏原本”的学案设置框架。[1](P477-478)因此,“黄璋校补本”被视为现存版本中最接近“黄氏原本”的一个版本,其学案设置及卷数与依据全祖望的“宋元儒学案序录”的今本相比存在诸多差异。[3](P317)例如,全祖望一反成说将“宋初三先生”之一的石介附在其师孙复的“泰山学案”中而没有为其设置单独的学案,并在“序录”中明确只将胡、孙二人并称作为宋学之开山,并对石介的人品道德 (性格严峻而口无遮拦) 与学问 (辨析义理尚欠粗疏) 颇有微词。[12](卷首P1、112)“黄璋校补本”中则将石介独立出来作为一个学案 (“徂徕学案”)。而且黄璋还在“卷首”的案语中在黄百家案语的基础上进一步阐明了胡瑗、孙复、石介作为宋学开创者的思想史地位。[8](P20)其后,《宋元学案》最后的校订者王梓材与冯云濠 (二人均为全祖望的宁波同乡和私淑弟子) 又否定了“黄璋校补本”的这种作法,并依据全祖望的“宋元儒学案序录”中设置的91个学案整理了《宋元学案》的学案和卷次。[9](P21)这样最终现行本《宋元学案》中的学案设置与卷次完全依照全祖望的意见,集中体现了全氏的思想史观。
2. 全祖望对“黄氏原本”学案设置的修补及思想史观之异同
依据王梓材和冯云濠所作“校刊宋元学案条例”,全祖望的编纂工作可分为修定 (今本《宋元学案》中标记为“黄某原本、全某修定”)、次定 (标记为“黄某原本、全某次定”)、补定 (标记为“黄某原本、全某补定”) 与补本 (标记为“全某补本”)[10](P21)四个方面。[11](P64-69)此外,卷首的“宋元儒学案序录”作为全祖望概述全书学案卷次及其评论标准的纲领,在全祖望生前已经刊行 (“二老阁郑氏刊本”)。[12](P17)今本《宋元学案》的“宋元儒学案序录”之下标记为“全氏定本”(正文中则标记为“全祖望定本”)。王梓材在“校刊宋元学案条例”中指出:“盖次定无所谓修补,补本无所谓原本,修定必有所由来,补定兼著其特立也。”[12](P21)据其所言,则上述四种情形又可分成二组。“修定”与“次定”为一组,两者都对“黄氏原本”中学案的数目没有增减。“补定”与“补本”为一组,两者都是全祖望在“黄氏原本”之外设置了新的学案 (其中“补定”是部分增加,“补本”是完全增加)。王、冯二人所指出的修定、次定、补定和补本四种情况记载在全书目录中的学案名之下,但和正文各卷学案名称下的标记相比有一些差异。以下将两者对照起来分别予以论述
(1) 修定。所谓“修定”是指全祖望仅对“黄氏原本”中的学案内容进行了增损。此种情况在现行百卷本中共有31个学案 (共31卷),目录中标记为“黄氏原本、全氏修定”,正文中标记为“黄宗羲原本、黄百家纂辑、全祖望修定”。其卷次、学案名及主要人物如下表所示。
(2) 次定。所谓“次定”是指全祖望将“黄氏原本”中的某些学案由其原本的一卷分成上、下两卷。具体来说,即为宋代道学核心人物“北宋五子”及其集大成者朱熹设置的六个学案。“次定”在现行百卷本《宋元学案》中共六卷,目录中标记为“黄氏原本、全氏次定”,正文中则标记为“黄宗羲原本、黄百家纂辑、全祖望次定”。其卷次、学案名与主要人物如下表所示:
值得注意的是,与上述“修定”相对照的话,这六个学案都被分成上、下两卷,其上卷均标记为“次定”,下卷则标记为“修定”。其意思是指全祖望将“黄氏原本”中的这六个学案分成上、下两卷的同时,又在下卷中对其内容有所修补。即全祖望的修补内容只限于下卷,上卷的内容还保持着“黄氏原本”的原貌。以上的“修定”与“次定”合起来共31个学案 (共37卷)。这些学案的设置可说是反映了黄宗羲与全祖望的共识,也可视为全祖望对黄宗羲思想史体系的继承。下面按学案 (时间) 顺序简要归纳这些学案所包含的主要学派、学者及其学术师承、地位、要旨等。
①宋学初期:宋学的创始人之一、提倡有体有用之实学的教育家胡瑗及其弟子徐积 (卷一“安定学案”);与胡瑗齐名的宋学创始人之一、经学造诣更胜一筹的孙复及其弟子石介 (卷二“泰山学案”)。
②道学开创:北宋五子之一、先天象数易学的创始人邵雍 (卷九·十“百源学案上·下”);北宋五子之一、二程的启蒙老师、建立以太极说为主的宇宙本体论而被南宋的朱熹等人推为宋代道学开山祖师的周敦颐 (卷十一·十二“濂溪学案上·下”);北宋五子之一、洛学的创立者、提倡天理论、具有浑一思想体系的程颢 (卷十三·十四“明道学案上·下”);北宋五子之一、洛学的完成者、具有体用论之分解思想倾向的程颐 (卷十五、十六“伊川学案上·下”);北宋五子之一、与二程洛学鼎立、学问规模宏大而富于创见的关学创始人张载 (卷十七·十八“横渠学案上·下”)。
③两宋之间的道学传承:程门四大弟子之一、富于创见的同时又夹杂禅学、被黄宗羲视为洛学弟子之首席的谢良佐 (卷二十四“上蔡学案”);程门四大弟子之一、洛学南传之第一人、南宋“东南三贤”的师祖杨时 (卷二十五“龟山学案”);与谢、杨齐名的程门四大弟子之一、后被视为程门罪人的游酢 (卷二十六“廌山学案”);程颐晚年的高徒、固守师说的尹焞 (卷二十七“和靖学案”);洛学的私淑弟子、与杨时南传洛学同功的湖湘学派创始人胡安国 (卷三十四“武夷学案”);杨时的高徒、得洛学之正传的道南学派代表人物罗从彦,以及朱熹之业师李侗 (卷三十九“豫章学案”);杨时的高徒、被朱熹批判为杂学的张九成 (卷四十“横浦学案”);尹焞的高徒、又受王苹的影响、被视为江西陆学先驱的林光朝 (卷四十七“艾轩学案”)。
④南宋道学的高峰:“东南三贤”之首、杨时的三传弟子、宋学 (道学) 的集大成者、综罗百代并对所有学派采取取长补短态度的朱熹 (卷四十八·四十九“晦翁学案上·下”);“东南三贤”之一、与朱熹齐名的湖湘学派代表人物张栻 (卷五十“南轩学案”);“东南三贤”之一、东莱吕氏中原文献之学的集大成者吕祖谦 (卷五十一“东莱学案”);江西三陆之学 (陆学) 的创始人陆九韶、陆九龄兄弟 (卷五十七“梭山复斋学案”);朱熹的劲敌、直承孟子而以“先立乎其大者”为宗旨的江西陆学 (心学) 完成者陆九渊 (卷五十八“象山学案”)。
⑤朱陆之后的道学传承:朱熹的高徒、发扬明体达用之实学、被视为朱熹道统继承人的黄榦 (卷六十三“勉斋学案”);朱熹的高徒、虽无气焰而学术传承源远流长的辅广 (卷六十四“潜庵学案”);朱熹的高徒、浙东永嘉最早的朱子学者陈埴与叶味道 (卷六十五“木钟学案”);朱熹晚年的高徒、大力阐扬师说、同时坚守师门而猛烈批判异学 (陆学) 的陈淳 (卷六十八“北溪学案”);私淑朱、张之学的同时,又继承永嘉经制之学的精华,与真德秀齐名而经学造诣更胜一筹的著名学者魏了翁 (卷八十“鹤山学案”);推进朱学的官学化、名重一时的朱熹再传弟子真德秀 (卷八十一“西山真氏学案”);继承黄榦之传承而被视为朱学正宗的浙东金华朱学代表人物何基、王柏、金履祥、许谦 (卷八十二“北山四先生学案”);黄榦的高徒、吴澄的师祖饶鲁 (卷八十三“双峰学案”);新安朱学的代表人物董梦程、曹泾、马端临 (卷八十九“介轩学案”);元代朱学北传的第一人赵复与元代北方朱学的代表人物许衡 (卷九十“鲁斋学案”)。
(3) 补定。所谓“补定”是指某位人物虽已收录在“黄氏原本”中,但只是附在他人 (案主) 的学案中,或者只是隶属于为某地域学派设置的学案之中,全祖望将其独立出来别立一学案。“补定”的学案在现行百卷本的目录中标记为“黄氏原本、全氏补定”,正文中标记为“黄宗羲原本、黄百家纂辑、全祖望补定”。共计28个学案 (30卷),其中“水心学案”与“沧洲诸儒学案”各自分成上、下两卷。其卷次、学案名及主要人物如下表所示。
如前所述,“修定”与“次定”的学案反映了黄宗羲、全祖望两人的共识,而“补定”的学案则反映了全祖望在继承黄宗羲思想史体系的同时在思想史观侧重点上的分歧。从大的方面可分为以下两种情况。
第一,自成一家之门人后学的分立学案。黄宗羲在其“黄氏原本”中将某人作为门人、家学、后学附于其师门 (案主) 的学案之中,没有为其单独设置学案。但在全祖望看来,这些学者各自有其学问宗旨,并不固守师门之旨,已别为一家一派,因此应将他们从师门中独立出来别立一个学案。这当然与黄宗羲在其《明儒学案·凡例》中强调的各人学问自得之“宗旨”的见解一脉相承,黄宗羲在《明儒学案》中也曾为背离王守仁宗旨的王门弟子李材别立了“止修学案”。全祖望在补修《宋元学案》时将这种作法作为一个原则进行了全面贯彻,将“黄氏原本”中的许多学案进行分割,从而新增加了许多学案。这里以吕希哲、吕本中及刘因三人为例予以重点分析。
卷二十三“荥阳学案”是全祖望为吕希哲设置的学案,而“黄氏原本”中吕希哲作为胡瑗的门人原本附于“安定学案”中。东莱吕氏家族的学问 (中原文献之学) 最引人注目的特征便是朱熹所说的“博杂”。其表现就是吕氏家族的学者们往往不拘泥于一定的师传或一家之说,而是对当时内容各异、观点相反的各个学派甚至异端的佛道之学,也全部采取兼收并蓄的态度加以吸收。从《宋元学案》来看,东莱吕氏家族可谓宋代首屈一指的儒学世家,从第一代的吕公著开始到第七代的吕乔年兄弟为止,共计有七代二十一人收录于《宋元学案》中,是《宋元学案》中收录人数最多的家族。[15](P789)吕氏一族中最重要的学者是吕希哲、吕本中和吕祖谦三人。正如全祖望在其“序录”中所指出的那样,吕氏第二代的著名学者吕希哲的学问具有“不主一门,不私一说”的特征。具体来说,他先师事焦千之 (欧阳修的门人),是欧阳修的再传弟子,其后又师事胡瑗、孙复、邵雍、王安石等人,最终归依于程门 (二程洛学),晚年又沉溺于禅学,甚至认为儒、佛二教之道是一致的,但其垂范于后世的思想还是在于儒学。[16](P902)从全祖望的分析可知,吕希哲虽曾师事胡瑗,但其师传与学问非常博杂,而且别有宗旨,与师说不一,因此不应该单单作为胡瑗的门人附在“安定学案”中,应当为其别立一学案。同样,“黄氏原本”中吕希哲之孙吕本中 (卷三十六“紫微学案”) 原本附在其师之一的尹焞的“和靖学案”中,但在全祖望看来,东莱吕氏虽然转益多师,但其家学向来以“多识前言往行以畜德”为其宗旨,从吕公著开始便已如此,又经吕希哲传到吕本中。吕本中虽曾登程门高足杨时、游酢、尹焞之门,但他所遵守的依然是祖传的这一学术原则, 其学不名一师,自成一格。因此,全祖望将吕本中从“黄氏原本”的“和靖学案”中独立出来为其设置了“紫微学案”。[17](P1234)
元代大儒刘因的学问虽以朱子学为主,但又主张博采诸家之长而一以贯之,并不墨守朱子学成规。与其同出赵复门下的许衡则终其一生在元朝为官,并长期担任国家最高学府的校长--国子监祭酒之职,元朝数十年间的著名士大夫大抵皆出其门下。依据黄百家和全祖望的考证可知,刘因对许衡的出处进退 (终生在异族统治下的元朝做官) 与学术思想 (拘守程朱理学而流入章句训诂之学) 颇有微词,而且刘因的人格气象 (狂狷) 及学问思想与赵复、许衡二人大不相同,已经别为一派。[18](P3022)因此全祖望将其区别开来,将赵复及其学问的继承人许衡二人收入卷九十“鲁斋学案”(黄宗羲的“黄氏原本”称为“北方学案”) 中,并将许衡列为“江汉所传”。而为刘因别立了卷九十一《静修学案》(黄宗羲的“黄氏原本”附入《北方学案》) 并称他为“江汉别传”。
此外,二程早年的高徒刘绚、李吁及其他程门弟子 (卷三十“刘李诸儒学案”) 原本附在二程的“明道学案”与“伊川学案”之中;邵雍的弟子王豫、张等人 (卷三十三“王张诸儒学案”) 原本附在邵雍的“康节学案”中;继承胡安国的家学并致力于佛教批判的胡寅 (卷四十一“衡麓学案”),以及继承胡安国的家学、南宋初期儒学造诣最深的学者、湖湘学派的实际创立者胡宏 (卷四十二“五峰学案”),还有朱熹早年的老师之一、胡安国的侄子兼弟子胡宪 (卷四十三“刘胡诸儒学案”) 原本附在胡安国的“武夷学案”之中;朱门的领袖、主要继承家传律吕象数之学的蔡元定 (卷六十二“西山蔡氏学案”) 原本附在朱熹的“紫阳学案”(全祖望改称“晦翁学案”) 之中;朱熹的高徒与蔡元定的家学、同时继承朱熹理学与家传象数之数的蔡沈 (卷六十七“九峰学案”) 原本附于其父蔡元定的“西山蔡氏学案”(卷六十二) 之中;陆门高徒“甬上四先生”(浙东四明) 之一人、被认为颠倒陆学之为学次序 (禅学化) 的杨简 (卷七十四“慈湖学案”)、“甬上四先生”之一人、学问较杨简更为纯粹的袁燮 (卷七十五“洁斋学案”),“甬上四先生”的另外两人舒璘与沈焕 (卷七十六“广平定川学案”),陆门的江西弟子傅梦泉、邓约礼等人 (卷七十七“槐堂诸儒学案”) 原本附在陆九渊兄弟的“金溪学案”之中;四明朱学的代表人物之一、真德秀的再传弟子、折衷朱吕陆三家之学的浙东大儒王应麟 (卷八十五“深宁学案”) 原本附在真德秀的“西山学案”之中;元代陆学的代表人物陈苑和赵偕 (卷九十三“静明宝峰学案”) 原本附在陆九渊兄弟的“金溪学案”之中。
总而言之,全祖望将上述学者从“黄氏原本”中具有师承或学术渊源关系的相关学案中独立出来为之设置专门的学案,从而彰显了他们各自的学术宗旨及其学术地位。
第二,隶属地域学派之学者的独立学案。黄宗羲在《宋元学案》“黄氏原本”中与其所著《明儒学案》一样,依据地域学派设置了一系列学案,其后全祖望或者将其不拆分而直接以代表人物的姓来冠名,或者将其按各学派的代表人物拆分成几个学案,并以其代表人物的姓氏字号冠名,或者直接继承“黄氏原本”的地域冠名 (一般有“诸儒”二字)。这里以永康学派创始人陈亮为例予以重点分析。
“黄氏原本”中为朱熹的论敌、浙东永康功利学派的创始人陈亮设置的“永康学派”被全祖望变更为“龙川学案”(卷五十六)。需要指出的是,卷五十六“龙川学案”在目录中标记为“黄氏原本、全氏补定”,但在正文中则标记为“黄宗羲原本、黄百家纂辑、全祖望修定”,两者出现了不一致。依据王梓材的案语,此学案在黄氏原本中被称作“永康学案”,其后全祖望将其改称为“龙川学案”。[13](P1830)从其内容来看,陈亮小传之下的黄百家案语实际上是黄氏为此学案所作的“序录”。[14](P1832)由此可见,“黄氏原本”中已经按地域学派 (永康学派) 的命名为陈亮设置了“永康学案”,后来全祖望依其以学者的“号”来命名学案的通例将其改称为“龙川学案”,并对其内容进行了稍许修订。因此标记为“补定”或“修定”均有其道理。这里笔者采取目录的标记“补定”。
此外,“黄氏原本”中为折衷关学与洛学的吕大临及范育等其他关学弟子设置的“蓝田学案”被全祖望变更为“吕范诸儒学案”(卷三十一);“黄氏原本”中为继承洛学与关学、并被视为南宋浙东永嘉学派先驱的周行己、许景衡等人设置的“永嘉学案之一”被全祖望变更为“周许诸儒学案”(卷三十二);“黄氏原本”中为南宋浙东永嘉学派的三位代表人物,包括程门再传弟子、以礼乐制度为主的浙东永嘉学派创始人薛季宣,比薛季宣的学问更纯粹的永嘉学派代表人物之一陈傅良,扫除永嘉学派的功利之说并否定程朱理学之道统、与朱陆鼎立的永嘉学派集大成者叶适设置的“永嘉学案之二”分别被全祖望分割为“艮斋学案”(薛季宣)、“止斋学案”(陈傅良) 和“水心学案”(叶适);“黄氏原本”中为转变四明史氏的陆学传统、成为四明朱学代表人物之一的史蒙卿设置的“四明朱门学案一”被全祖望变更为“静清学案”(卷八十七);“黄氏原本”中为四明朱学的代表人物之一、学问造诣深厚的大儒黄震设置的“四明朱门学案二”被全祖望变更为“东发学案”。直接以地域命名的情况包括:朱熹的高徒杜煜、杜知仁兄弟及其再传弟子车若水 (卷六十六“南湖学案”),朱熹其他的直接弟子李燔、张洽、廖德明等 (卷六十九“沧州诸儒学案上”) 与朱熹的再传弟子 (卷七十“沧洲诸儒学案下”),继承张栻思想的湖湘学派后学胡大时、彭龟年等 (卷七十一“岳麓诸儒学案”),继承吕祖谦文献之学的金华学派门人后学 (卷七十三“丽泽诸儒学案”)。
从学案的命名来看,上述情况可说是全氏补本的一个通例,即学案 (党案除外) 一般是以案主的名称来命名。具体来说,案主为单个人的情况一般用其“号”作为学案名,如“庐陵学案”(欧阳修);案主为多人 (“诸儒”) 的情况则将其中两位主要人物的姓氏合起来命名,如“徐陈诸儒学案”(徐谊、陈葵等);此外也有个别以地域 (讲学地) 来命名的,如“古灵四先生学案”(闽中四先生)、“二江诸儒学案”(张栻的蜀中弟子)、“丽泽诸儒学案”(吕祖谦的弟子),而“荆公新学略”(以学派命名)、“苏氏蜀学略”(以学派命名)、“屏山鸣道集说略”(以著作命名) 三个略案则是特例。此外,“西山蔡氏学案”与“西山真氏学案”是因蔡元定与真德秀均号西山,为了区别开来才在学案名中加上姓氏的。
总的来看,全祖望在补定中的上述做法强调了各学派代表人物自身的学问宗旨及其学术地位,史传的色彩非常浓厚,而黄氏原本中黄宗羲的做法则强调了地域学术和学派整体的传承,思想史的色彩比较浓厚, 两者各有长短。黄宗羲的做法更注重整体和强调源流,全祖望的做法则更深入细致和强调个性。两者都为现代哲学史、学术思想史的写作提供了范式。
以上所述“修定”与“次定”合起来共31个学案 (凡37卷),“补定”有28个学案 (凡30卷),三者合起来即是现行百卷本《宋元学案》中出自“黄氏原本”的学案,凡59个学案共67卷。从这些学案所包含的学者及其学派构成上看,包括作为宋学创始人的胡瑗 (湖学) 及其弟子徐积、孙复及其弟子石介;作为宋代道学创始人的“北宋五子”的周敦颐 (濂学)、程颢和程颐 (洛学)、张载 (关学)、邵雍 (象数学);两宋之际传承道学的洛学直接弟子谢良佐、杨时、尹焞、吕大临,洛学的私淑弟子胡安国 (湖湘学派),洛学的再传弟子吕本中 (附吕希哲、东莱吕学的先驱),罗从彦与李侗 (道南学派),胡寅与胡宏 (湖湘学派);作为两宋道学高峰的理学集大成者朱熹 (闽学),朱熹的讲友和湖南学的代表人物张栻、中原文献之学的集大成者吕祖谦 (婺学),朱熹的论敌和浙东学派的代表人物薛季宣、陈傅良、叶适 (永嘉学派)、陈亮 (永康学派) 与江西的陆九韶、陆九龄、陆九渊兄弟 (陆学、心学);朱陆之后思想界交汇整合时期的朱学直系弟子黄榦、辅广、陈淳,陆学的直系弟子“甬上四先生”(杨简、袁燮、舒璘、沈焕),朱陆的再传弟子与私淑弟子魏了翁与真德秀、何基、王柏、金履祥、许谦 (金华朱学)、王应麟、黄震、史蒙卿 (四明朱学);元代儒学的代表人物许衡与刘因 (北方朱学)、吴澄 (南方朱学与朱陆折衷者)、陈苑与赵偕 (元代陆学)。由此可知,出自“黄氏原本”的59个学案已经基本囊括了宋元道学的发展脉络、学术流派及其代表人物。
(4) 补本。所谓“补本”是指全祖望为“黄氏原本”中未曾收录的人物新设置的学案,在现行百卷本中共计32个学案 (33卷),目录中标记为“全氏补本”,正文中标记为“全祖望补本”。其卷次、学案名及主要人物如下表所示:
“补本”中的学案集中体现了全祖望自身的思想史观。与上述“黄氏原本”中的学案对照,两者在思想史观上的差异体现得很清楚。如上文所述,从出自“黄氏原本”的59个学案来看,黄宗羲突破了《伊洛渊源录》与《宋史·道学传》以北宋五子 (朱子先驱)-朱熹-朱熹门人 (朱子后继) 为唯一道统传承的程朱理学框架,将作为宋学开山与道学先驱的“宋初三先生”,以及与朱学对立的江西陆学及浙东事功学派等其他学派的学者也纳入到宋元儒学思想史的脉络中并给予了其相应的思想史地位,从而使其宋元儒学思想史的框架大体齐备。但另一方面,正如全祖望所指出的那样,“公 (指黄宗羲) 以濂洛之统,综会诸家”,[19](P220)黄宗羲继承其师明代心学殿军刘宗周的哲学思想,出于其门户之见,无论是在编纂内容上还是思想评论上仍然是以宋代道学 (包括朱学、陆学、吕学、湖南学等) 主流学派为主导,其道学色彩还是很浓厚。而全祖望为了展现宋元儒学思想史的全貌,通过“修定”“次定”“补定”从“黄氏原本”中分立出59个学案,又通过“补本”另外设置了32个学案。其主要原因是全祖望的学术立场和思想史观较之黄宗羲更为开放和客观,基本没有门户之见,因此才能进一步突破黄宗羲、黄百家父子的道学思想史体系,广泛采录道学以外的人物或事件,从而展现了宋元学术思想史的全貌。[20](P102)这一点集中体现在其“补本”所设置的学案当中。其立案标准除了考虑黄宗羲所强调的学派和地域两方面外,还综合考虑了政治、事功等方面。大体可分为以下四种情况。
第一,思想史上的次要学者 (陈襄、三汤等)。与胡瑗、孙复同时在福建兴起复兴儒学的“闽中四先生”--陈襄、郑穆、陈烈与周希孟 (卷五“古灵四先生学案”),以及士建中、刘颜、王开祖等其他宋学先驱与齐鲁 (京东)、浙东、浙西、闽中 (福建)、关中 (陕西)、蜀中 (成都府路) 等各地域学派 (卷六“士刘诸儒学案”);继承司马光之刚健的高足刘安世 (卷二十“元城学案”),继承司马光之纯粹的高足范祖禹 (卷二十一“华阳学案”),继承司马光的数学及邵雍之易学的高足晁说之 (卷二十二“景迂学案”);为国捐躯的程门弟子郭忠孝 (卷二十八“兼山学案”);谢良佐的高徒、以象数易学闻名的朱震 (卷三十七“汉上学案”),杨时的高徒、夹杂禅学的陈渊 (卷三十八“默堂学案”);“东南三贤”的同调刘靖之、刘清之兄弟 (卷五十九“清江学案”),浙东永嘉学派的同调唐仲友 (卷六十“说斋学案”),陆学的同调徐谊、陈葵等人 (卷六十一“徐陈诸儒学案”);继承张栻思想的蜀中后学宇文绍节、陈概、范仲黼等 (卷七十二“二江诸儒学案”);邵雍象数易学的后学张行成、祝泌等人 (卷七十八“张祝诸儒学案”),与朱陆弟子同时代而师承不详的学者丘崈、刘光祖、楼钥、柴中行等人 (卷七十九“丘刘诸儒学案”);朱陆的再传弟子 (真德秀门人)、出入于朱陆之间的鄱阳三汤兄弟汤千、汤巾、汤中及其侄汤汉 (卷八十四“存斋晦静息庵学案”);朱熹的后学欧阳守道及其弟子、为国捐躯的南宋丞相文天祥 (卷八十八“巽斋学案”);陆学五传与朱熹续传、继吴澄之后和会朱陆的学者郑玉 (卷九十四“师山学案”);师传不详的萧、同恕等元代朱子学者 (卷九十五“萧同诸儒学案”)。
第二,与思想界关系密切的政治家和学者 (范仲淹、赵鼎等)。庆历新政推动北宋儒学复兴运动的政治家和学者范仲淹 (卷三“高平学案”);庆历之后的主要学者,北宋诗文 (古文) 改革运动的领袖与疑经思潮的倡导者欧阳修、刘敞等 (卷四“庐陵学案”);北宋六先生之一、洛阳旧党领袖与著名学者司马光 (卷七·八“涑水学案上·下”);司马光的同僚,北宋六先生的同调范镇、吕公著等人 (卷十九“范吕诸儒学案”);南宋初期支持道学 (洛学) 的政治家赵鼎、张浚等人 (卷四十四“赵张诸儒学案”);伊洛道学的同调范浚,以及传承中原文献之学的许翰等人 (卷四十五“范许诸儒学案”);张九成、吕本中的弟子、被视为纯粹儒者的汪应辰 (卷四十六“玉山学案”)。
第三,夹杂佛道异端之“杂学”(王安石新学、三苏蜀学等)。将洛学传至浙西 (吴郡) 并被视为陆九渊心学先驱的程门 (程颐与杨时) 弟子王苹 (卷二十九“震泽学案”);北宋末期学者,夹杂佛道异端思想的洛学私淑弟子陈瓘、邹浩等人 (卷三十五“陈邹诸儒学案”);作为北宋后期开始直至南宋初期的官学并与洛学相对立的王安石新学 (卷九十八“荆公新学略”);被朱熹视为杂学的三苏蜀学 (卷九十九“苏氏蜀学略”);以及宋元过渡期间,被视作王、苏两派之余波的以李纯甫、赵秉文为代表的金朝儒学 (卷一百“屏山鸣道集说略”)。
第四,思想界周边的政治事件 (元佑党禁与庆元党禁)。关系到两宋的治乱兴亡与学派兴衰的重大政治事件--“元佑党禁”(卷九十六“元佑党案”) 与“庆元党禁”(卷九十七“庆元党案”)。
3. 全祖望修补学案及对李觏等人不立学案之分析
全祖望通过补本设置以上学案,填补了大量思想史上的空白,从而大大扩充了“黄氏原本”并确定了全书91个学案共100卷的规模。这样就使宋元儒学的高潮与过渡、主流和支流、正统与异端、中心与周边得以齐备,并很好地交代了宋元儒学史上各学派的来龙去脉,贯穿着编纂者推崇学术思想上的创见 (自得) 以及道德与学问并重 (有体有用之实学)、兼包并蓄的开放思想史观,从而使得《宋元学案》成为完备的宋元儒学思想史著作。因此全祖望才自负地称道:“予续南雷《宋儒学案》,旁搜不遗余力。盖有六百年来儒林所不及知,而予表而出之者。”[21](P580)话虽如此,《宋元学案》中的学案设置还是有商榷的余地。特别是全祖望往往没有明确说明其设置学案的标准和理由,造成后世的研究者较难了解其真实意图。比如全祖望在《宋元学案》中似乎没有明确说明为何不给石介、李觏这些为学术界所重视的著名学者单独设置学案的理由。
目前学术界普遍重视作为“庆历新政”之同调的李觏 (号盱江,1009-1059) 的学术思想,特别其关于政治、经济、法制等方面的经世致用思想被认为开其后北宋王安石的政治改革思想及南宋浙东学派的功利思想之先声。[22](前言P1-13)李觏本人也被认为是宋学创始期的代表人物之一,完全有资格被单独立案。全祖望在《宋元学案》不为他设置学案予以表彰,相反却有意忽视其思想史地位的做法不免使人感到有些遗憾。实际上王梓材在其案语中已经指出,全祖望确曾考虑过为李觏单独设置“盱江学案”,但后来在定稿时又将其删去而并入范仲淹的“高平学案”中。[23](P133)关于全祖望删除“盱江学案”这一点,可从作为全祖望定稿纲领的“宋元儒学案序录”中没有“盱江学案”看出。而关于其并入“高平学案”这一点,王梓材修订《宋元学案》时,由于“全氏修补本”的“高平学案”的内容除了范仲淹的三传弟子韦许的小传以外已经全部佚失,因此现行《宋元学案》“高平学案”的内容基本上是由王梓材补修的。王梓材在李觏小传下的案语中指出,卢镐所藏全祖望补修本的原稿本中在李觏的门人孙立节的小传之前标记有“盱江”两字,可知全祖望确曾设置过“盱江学案”。再加上卢氏所藏学案原稿本的“序录”中的“士刘诸儒学案序录”中有“江楚则有李觏”一句,可证全祖望原本是将李觏视作宋学初期与胡瑗、孙复同时而在江西 (李觏是北宋江南西路建昌军南城人) 兴起的一大家,并为其设置一学案的。但后来作为定本的二老阁郑氏刊本的“宋元儒学案序录”中却删除了此一句,因为全祖望在其定本时将原本为李觏设置的“盱江学案”合并到了为其师范仲淹设置的“高平学案”之中。李觏可作为范仲淹门人的依据如全祖望在范纯仁 (范仲淹次子) 的小传中所指出的,胡瑗、孙复、石介、李觏均曾入范仲淹的门下,李觏的年辈较之石介稍迟,故可视为范仲淹的门人。[24](P156)这种做法与前述将石介 (“徂徕学案”) 合并到孙复的“泰山学案”的情况相似。实际上全祖望在其定本中确定《宋元学案》的91个学案时,将不单独立案的学者并入其师的学案的作法可谓其编纂的一个通例。全祖望删除“盱江学案”的理由,除了使全书的规模不至超出百卷的规模外,对李觏的思想与人品不太推崇恐怕也是重要原因。[25](P2048)总之,现行百卷本《宋元学案》中,将李觏附入其师范仲淹“高平学案”的作法,实际上是王梓材依据全祖望设置学案的规则而定的。
此外,依据王梓材的案语可知,全祖望还曾为胡安国的门人胡铨 (号澹庵,1102-1180) 设置“澹庵学案”,并从其著作《澹庵集》中辑录了若干资料,但定稿时又将“澹庵学案”删除,将胡铨附入卷三十四“武夷学案”中胡安国的门下,而且因其原稿的一部分已经佚失,今本《宋元学案》中只有胡铨的小传残留了下来。[26](P1188)又全祖望曾经为黄泽 (吴澄的同调) 的门人赵汸 (号东山,1319-1369) 设置“东山学案”,但定稿时将其删除并将赵汸附在卷九十二“草庐学案”(吴澄) 中黄泽的门人之下,而全氏修补本的原稿中这一部分的内容已经佚失,其后王梓材依据黄璋校补本对其进行了修补。[27](P3089)
综上所述,现行百卷本《宋元学案》中的学案设置完全依据全祖望的意见 (序录) 而定,其设置学案的标准与黄宗羲在“黄氏原本”中注重思想流派与地域学术的立场相比既有继承也有突破,在以学术脉络及学术宗旨为主的同时又通盘考虑到政治事功、人品道德和整体规模等方面。通观《宋元学案》中的案语评论,全祖望对于学者的学术思想、人品道德、政治事功等因素实际上是并重的 (如对于陈亮、杨简的评价),因此对于石介、李觏这样在学术思想上成一大家但在人品道德上有可议之处的学者,全祖望因个人不太推崇他们而没有为其设置单独的学案。而另一方面,对郭忠孝这样在学术思想上几乎没有什么地位的学者,全祖望却为了表彰其为国捐躯之忠义事迹而为其单独设置了一个学案。从这点来看,全祖望设置学案的标准除了考虑其人的哲学思想或学术地位等纯学术标准,同时也像正史一样考虑到表彰忠义、气节等人品道德方面的标准,因此,现行《宋元学案》中的学案 (包括党案) 在形式上与正史的列传 (学案与略案) 及大事表 (党案) 比较近似。作为思想家、哲学史家的黄宗羲[28](绪言P1-2)与作为史学家的全祖望,在学术倾向与思想史观上的差异在此也得到清晰的体现。
注释
[1] 张艺曦. 史语所藏《宋儒学案》在清中叶的编纂与流传[J]. 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 2009.
[2] 何俊. 宋元儒学的重建与清初思想史观——以《宋元学案》全氏补本为中心的考察[J]. 中国史研究, 2006(02).
[3] 夏长朴. "发六百年来儒林所不及知者"——全祖望续补《宋元学案》的学术史意义[J]. 台大中文学报, 2011(34).
[4] 《宋元学案》的成书三阶段及其版本的命名主要依据吴光及葛昌伦的相关研究成果. 参见: 吴光. 《宋元学案》成书经过、编纂人员与版本存佚考[J]. 杭州师范学院学报 (社会科学版). 2008(01). 葛昌伦. 《宋元学案》成书与编纂研究[M]. 台北: 花木兰文化出版社, 2007.
[5] 个别情况下也有置于案主之前的, 例如, 卷三"高平学案"中范仲淹的恩师戚同文被置于案主范仲淹之前. 卷九十"鲁斋学案"中赵复被置于案主许衡之前.
[6] 依据川胜守的论文〈明儒における学伝と政治実践——《明儒学案》记伝名人データベースをめぐって―〉(平成九年度科学研究费补助金 (基盤研究B) 研究成果报告书《黄宗羲の《明儒学案》成立に关する基礎的研究》, 研究代表者: 柴田笃, 1998年3月) 的统计, 《明儒学案》中共收录有208位明儒.
[7] 葛昌伦. 《宋元学案》成书与编纂研究[M]. 台北: 花木兰文化出版社, 2007.
[8] (清) 黄宗羲, (清) 全祖望. 宋元学案 (第1册)[M]. 北京: 中华书局, 1986. 王梓材"宋元学案考略"云: "梓材谨案: 谢山稿底, 零星件系, 诚如所云. 然悉心寻究, 仍复脉络贯通. 棃洲后人校补本为卷八十有六, 而冠谢山'百卷序录'于首, 盖亦以学案次第当遵'序录'. 特欲如谢山卷数而不得, 故以泰山、徂徕各为一卷, 而不知徂徕之当合泰山也, 高平、庐陵底稿无存, 即缺其卷, 而不知高平家学可分自安定, 庐陵学派间见于卢氏藏稿也. 华阳、景迁、说斋皆在藏稿, 而是本无之; 兼山流派与陈、邹诸儒, 藏稿有之, 而是本亦无; 刘、李、沧州、岳麓、丽泽、槐堂可自伊川、晦翁、南轩、东莱、象山分卷, 而未别其卷; 蛟峰、江汉卷第所无, 而不知蛟峰之当附北山, 江汉之当冠鲁斋; 北山四先生合为一卷, 而分卷者四; 李、张、胡、熊、李、俞、九江亦卷第所无. 不知各归学派, 而徒冠序录于首, 亦赘矣. 然卢氏藏底所遗如百源、伊川、三陆, 固具有之, 则是本亦安可少哉!"
[9] (清) 黄宗羲, (清) 全祖望. 宋元学案 (第1册)[M]. 北京: 中华书局, 1986. 王梓材"校刊宋元学案条例"云: "是书既经谢山历年修补, 自当从谢山百卷之目. 梨洲后人亦列谢山于续修, 而别为八十六卷之目, 于序录未能印合, 故是刻以百卷为准. 取卢氏藏稿细心校理, 具见百卷条目, 井然不紊. "
[10] (清) 黄宗羲, (清) 全祖望. 宋元学案 (第1册)[M]. 北京: 中华书局, 1986. 王梓材"校刊宋元学案条例"云: "梨洲原本无多, 其经谢山续补者十居六七. 故有梨洲原本所有, 而为谢山增损者, 则标之曰'黄某原本、全某修定'. 有梨洲原本所无, 而为谢山特立者, 则标之曰'全某补本'. 又有梨洲原本, 谢山唯分其卷第者, 则标之曰'黄某原本、全某次定'. 亦有梨洲原本, 谢山分其卷第而特为立案者, 则标之曰'黄某原本、全某补定'. 盖次定无所谓修补, 补本无所谓原本, 修定必有所由来, 补定兼著其特立也. 其曰'定'者, 谢山稿底尝自标之. "
[11] 林久贵. 《宋元学案》的作者及成书经过述论[J]. 黄冈师专学报, 1998(03). 如上条注释中所引, 王梓材认为从全书来看, 全祖望修补的部分占到三分之二 (黄宗羲所设置学案的大部分内容也由全氏加以增补和订正), 黄宗羲所编纂的内容则大约只占三分之一. 这是《宋元学案》最后的编纂者王梓材在比对不同版本并对全书内容进行全面校订之后得出的结论. 依据林久贵的考察, 对此尚有两种不同意见. 一种意见以梁启超、张舜徽、吴枫等人为代表. 他们认为黄宗羲生前大约只完成了《宋元学案》十七卷的序录及其正文, 远不及现行百卷本的三分之一. 另一种意见以吴光和卢钟锋为代表. 二人都依卷次认为黄宗羲编纂的部分达到现行百卷本的三分之二. 笔者经过对全书的比对分析取折衷两者的意见, 即黄宗羲生前本人完成的部分虽然并不多, 考察其案语分布于今本的32个学案 (34卷) 中, 而且全祖望修定与次定的 (与黄氏原本一致) 恰好也是32个学案, 大约占今本100卷的三分之一左右, 因此王梓材的意见确实有其依据. 但黄宗羲之后, 经过其子黄百家的修补, 黄氏原本的份量得以大为扩充, 今本91个学案中出自黄氏原本 (包括全祖望修定、次定与补定) 的共有59个学案, 最终占据今本的三分之二. 另一方面, 全祖望补本的份量虽只占全书的三分之一左右, 但却决定了全书的总体框架, 而且黄宗羲设置的学案基本都经过了全氏的修定、补定或次定, 占全书的三分之二, 因此从全书所涉及的范围来看, 出于全氏修补本的内容又较出自黄氏原本的部分为广泛了.
[12] (清) 黄宗羲, (清) 全祖望. 宋元学案 (第1册)[M]. 北京: 中华书局, 1986.
[13] (清) 黄宗羲, (清) 全祖望. 宋元学案 (第3册)[M]. 北京: 中华书局, 1986. 卷五十六"龙川学案": "祖望谨案: 永嘉以经制言事功, 皆推原以为得统于程氏. 永康则专言事功而无所承, 其学更粗莽抡魁, 晩节尤有惭德. 述'龙川学案'. (梓材案: 是卷本称'永康学案'、谢山定《序录》改称'龙川'. 又, 龙川在太学尝与陈止斋等为芮祭酒门人. 又先生《祭郑景望龙図文》称之曰'吾郑先生', 则先生亦在郑氏之门矣. )"
[14] (清) 黄宗羲, (清) 全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