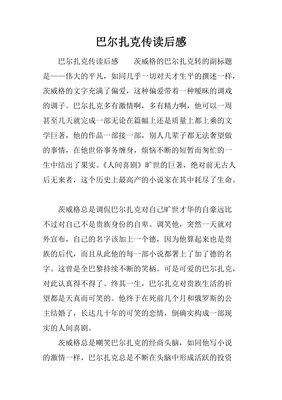
《巴尔扎克传》是一本由(法) 安德烈·莫洛亚著作,浙江大学出版社出版的平装图书,本书定价:69.00元,页数:610,特精心从网络上整理的一些读者的读后感,希望对大家能有帮助。
《巴尔扎克传》精选点评:
●三个印象: 第一,巴尔扎克太勤奋了,一天写作长达十六个小时。令人敬佩。 第二,巴尔扎克太悲催了,做什么买卖都赔本,从二十多岁开始欠债,欠了一辈子,写了那么多书,还是还不完。 第三,巴尔扎克虽然长得不帅,但特别擅长写情书。
●写得太震撼了,太好了!令其他任何一本巴尔扎克传记黯然失色。600页太短,不过瘾!
●「我曾经是将军,皇帝,我也当过拜伦,然后却什么也不是。在周游人间山巅之后,我发现依然有无数的山峰需要攀登。」曾用一根头发迷倒一众女人,在情史中浮浮沉沉的巴尔扎克啊,他的一生有多接近世俗就多有伟大。
●他是谁?大师还是普罗米修斯?不,他只是一个肥胖庸常的男人罢了,他为生活而拼命奔波,却坚持追求自己的梦想,尽管像飞蛾扑火一样
●和父母对抗、急性子、性欲、孤僻、昼伏夜出、投机、自以为是。漂亮的人各有各的幸运,而肥宅却有相同的宿命。
●读得很累,断断续续读了将近两个月,巴尔扎克20岁开始就债务一锅粥,基本是不断超前消费终其一生都负债累累。雪上加霜的是运气不佳,投资铁路遇到打仗,创办出版社报社因为经营不佳关闭,创作戏剧遇到大革命票房惨淡,导致为了赶稿应付债务一天协作16小时。一生都在追求出身高贵,富有贵族气质的女人,新婚燕尔事业出现转机时骤然离世。个人还是不太喜欢这种纪传体风格,书中提到的各种作品《幻灭》《驴皮记》应该比传记本身精彩,有空拜读
●创造了精神世界的就是这样的人。在他身上,美与丑,善与恶,聪明与愚蠢,大气和偏狭,无比的坚强与让人难以置信的软弱,往往以种种离奇的方式组合在一起。他们在作品中无所不能,在生活中却可能像孩子一样无知,这就是人的复杂性。
●1850年6月17日,巴尔扎克用难以辨认的字迹涂抹道:“我已经不能读书和写字。”读到这里我心里一阵难受。我相信巴尔扎克是上帝给人间的一个礼物,过了五十年便要收回。他生日是1799年5月20日,非常好记。我再一次想到我无意中看到的某句话,文学,应该靠着深情,而不是聪明。巴尔扎克可谓最深情。感谢莫洛亚的这本书让我经历了一个人五十年的人生。
●人的生命,就是成为人的过程。这条路没有终点,但两旁立有丰碑。
●“一定要让雨果看看我所有的油画。”
《巴尔扎克传》读后感(一):书很有意思,翻译非常好,还是老一辈的译者靠谱
读了这本书就会发现,原来巴尔扎克并不那么枯燥,巴尔扎克建构了一个想象中的世界,样样精通,在生活中却处处受挫,看来艺术家和现实的确格格不入。
语言读起来毫无翻译腔,流畅自然,还是过去的译者可靠。这本巴尔扎克传是莫洛亚的传记封笔之作,在目前国内出版的同类传记中最为全面,也最有感染力。
《巴尔扎克传》读后感(二):读后有感
有些人认为人生太短,不知道他们是否真正感受到了。如果他们不是那些在病榻上苟延残喘了好些时日的人,那么他们整天嗟叹的“人生之须臾”恐怕不过是些由多愁善感而致的无谓的自怜吧。
其实,人生的确短的很。一个智力健全的人根本没有去天国的铁栅门前探求这显而易见的一点的必要,他们只需随手翻翻优秀的人物传记便能体会到这看似寻常的道理。每次我从那个有着丰功伟绩的人的出生一直读到他带着荣誉入土,我都能深深地感到时间的流逝之快。这不,与这位在书中区区几百页中成长起来的人物相比,我们的一生倍显短暂。只要知道了这一点,我们便能够对从那些成日里无所适从的庸人口中说出的话付之一笑,任其人独自自怜解闷了。
手里握着一本之前读过一遍的传记,心中像书中主人公那样有着许多荒谬的幻想,无论到了哪里都不愿意停顿。我就像这样如饥似渴地吸收着作者那些如云的生花之笔,期盼着自己能够写出非同一般的文章。可惜追求名利之心尚不可彻,根植于心中无法去除。唉,这难道不是这个古怪的社会特有的习气吗?所有人都在疯狂地准备考试,以致于考完后根本没有时间享受干完大事常有的成就感,只能为下一次再做无力的准备。
展眼观望未来,哪一天没有这般灰暗的阴影笼罩?这简直像用慢火煮青蛙一样,只不过溃烂的青蛙的躯干变成了深陷的眼窝、蜡黄的面孔、不健康的关节的咔咔作响以及那不稳地立在鼻翼上的玻璃片。
写到这里,我不禁有些害怕了。出路在哪里?
时光飞逝,别以为这只是由多愁善感促成的空话,这是一句说不清也道不明的真理。
《巴尔扎克传》读后感(三):拾人牙慧式小论文
纵观巴尔扎克的一生,与金钱有着极大的羁绊。就像《巴尔扎克传》第二十四章“西绪福斯神话”的题记中,莫洛亚引用其曾经评论过西绪福斯神话那样:“有那么一段时间,西绪福斯不哭也不闹,他不停地把石头推向山顶,他的性格也变得同他手中的石头一样了。”巴尔扎克一生中的大多数时候,也像西绪福斯一样,不断的背负着“债务的巨石”在创作。挥霍、欠债、赚钱、还债、继续无限度的花销、如雪花般越积越多的债务、紧迫与压力之下天才般的创作以及精力消耗直至死亡。他这一生,是激情而又疯狂,随心所欲又不计后果的。而造成这一切的根源,便是那与之相伴相生的金钱观。
一、金钱观的种子埋下 1799年,巴尔扎克出生于法国中部图尔城一个富裕的资产阶级家庭。在1804年,拿破仑夺得政权建立第一帝国以至1848年爆发革命之前,在将近四十年的时间里,也即巴尔扎克大半生生活的地方中,波旁王朝统治下的法国是一个物欲横流的社会。资本主义的不断发展,资产阶级渐渐取代贵族阶级成为国家的统治者。并且由于资产阶级地位的不断提高,法国逐渐形成了一种金钱至上的风气,社会上弥漫着虚荣、地位、金钱至上的观念。而在童年时期巴尔扎克的家里,人们谈论得最多的话题也是金钱和遗产。在不断地耳濡目染、潜移默化之下,这种“金钱很重要”的金钱观种子已经埋在了他心中。
二、灰暗惨淡的少年时代 巴尔扎克父母的结合和社会上的大多数人一样,也与金钱挂钩。父母亲之间没有爱情,在巴尔扎克出生之后,夫妇俩就将其托付给别人喂养,从小就缺失母爱的巴尔扎克在他四岁被接回到父母身边时也一直活在母亲的冷漠之中。在他们家庭还富裕时,巴尔扎克的母亲一味追求奢侈、摆阔、讲排场,但却对当时刚满八岁就被送到多旺姆寄宿学校读书的巴尔扎克及其吝啬,她几乎从来不给巴尔扎克零花钱,不让他买任何东西,也很少关爱他,就像把他遗忘在那个艰苦的环境之中似的。从八岁到十四岁这段时光里,巴尔扎克就一直生活在那种压抑艰苦的环境之中。一个富裕家庭的小孩,活得却贫穷落魄,这种两极差别也是造成他日后追求极致奢华生活的一个原因。
三、惨淡经营的青年时期 青年时期的巴尔扎克一度宣称“我只有两个愿望:成名与爱情”是他的座右铭。但在成名之前,巴尔扎克为了生存经常替一些文学掮客写作一些不伦不类的玩意儿,如各种各样的指南。大约从1825年开始,他开始感到自己在文学上再无出头之路,便听信了父亲朋友指引的另一条路:经商。但不幸的是,无论巴尔扎克涉足哪个行业,每次都以失败告终。那短短几年经商所遭遇的失败让他经历了破产、负债的苦楚,同时也让他窥见了金钱世界的黑幕,体验到走投无路的苦难,而这些经验也在他的思想上留下了深刻的印记。然而,即使是在失败的同时,他仍然幻想着幸福的未来,那是怎样的未来?铺满着珠宝,萦绕着美女。
四、初露锋芒的思想成型期 1829年,巴尔扎克凭借《婚姻生理学》一举成名。这时候的人们都争相阅读他的书,出版商来讨取他的新作,久未联系的昔日同窗也找上门来。今日车水马龙与往日门庭冷落的极致对比,更是让巴尔扎克深刻的认识到“有没有钱,才是关键。”从少年时代起就形成的对日常生活与社会的观察,让他意识到金钱已成为当今社会的“上帝”,现代社会人的基石。当今社会上,哪个人不贪恋钱财?下层穷苦人民渴望钱财改善生活,上流社会人士需要钱财维持体面生活与奢华排场,资本家更是疯狂积累资本。在这个资本主义形成并稳定发展的年代,金钱便是当今社会的主宰。就像《巴尔扎克传》里的高利贷者高布塞克所讲:“金钱代表了人间的一切力量。金钱就是当今社会的支柱。”在这样一个金钱至上的社会下,巴尔扎克能幸免于难吗?不可能。除了是这个社会的冷酷观察者,法国历史的书记员之外,巴尔扎克更是这个资本世间的实际参与者。
五、《驴皮记》 的征兆 贵族出身的青年在破产后想要自杀之时得到一位古董商赠送的一张神奇驴皮。这张驴皮能满足主人的任何愿望,无论是善念还是恶念。但是,每实现一个愿望时,驴皮就会缩小一圈。等到驴皮消耗殆尽,主人的生命也将完结。
即便巴尔扎克在创作《驴皮记》时有着谴责当时社会上生活豪华、奢侈和放荡作风的意图,但是巴尔扎克也没能逃出《驴皮记》的征兆,他就像作品里的拉尔埃法一样,渴望荣誉、财富和女人。热切于挤入上流社会的巴尔扎克,抵挡不住奢华生活的诱惑。在作品大卖本该能够还清债务之时,他欠下的债务反而变得更多了。原因便是他抵挡不住花钱的诱惑,无节制的追求奢华生活。不计后果式的花钱让他负债累累。长期的失意让他走上了另一种极端,报复性的消费能够给他带来快感,但同时带来的也是欠债的阴影和被追债的提心吊胆。
六、疯魔的天才,虚荣的流氓 1828年到1837年这九年的时间里,巴尔扎克生动的诠释了“疯狂的天才,虚荣的流氓“这句话。他惊人的创作力一下子爆发出来,创作了数十部作品。如我们所熟知的《高老头》、《欧也妮·葛朗台》、《乡村医生》、《幻灭》、《幽谷百合》等等。这些创作除了是他疯狂的天才想象般的产物之外,也有不少是为了还清债务的应付之作。即便他也知道欲壑难填,但是为了满足自己的欲望,满足自己对地毯、家具和名画永无止境的追求,他成为了自己口中的笔墨的奴隶,不折不扣的思想贩子。虽然他无比虚荣,并且同时和好几位女性保持情人关系,但不得不承认的是,巴尔扎克本身对创作的热情与认真。他可以同时一下子进行好几部作品的写作,就像他的脑子里存在着一个巨大的材料库,只要他想写哪部分内容,他将相关材料提取出来就可以。而且,虽然赚钱是他写作的主要目的,但他对于自己的作品是极其严肃认真的,他总是对一些已经定稿或者准备排版刊行的作品进行大量的修改、增删。而这些工作,无疑也加深了巴尔扎克的债务。但是相比于作品的严谨来讲,负债又算得了什么?
七、西绪福斯神话 即便在1837年之后,巴尔扎克名满欧洲,但他依旧没有还清自己的债务,账单像雪花一样飞舞而来,相比于九年前,他欠下的债务反而多了好几倍。为了躲避穷凶恶极的债主和法庭执达吏,他东躲西藏,无一日不忍受着焦虑和煎熬。他就像西绪福斯推动巨石上山一样,为了还清欠下的债务不断进行写作,一天二十四小时里工作十八小时,他的生命也就在这样的劳作当中慢慢损耗了,连接不断的疾病侵袭着他,使得他的负担日益加重。然而,即便如此,他还是不能放弃对于生活的享受,对于名贵字画、地毯的热爱。即使负债累累之际,他也不懂得节俭。因为在他的意识里,一天之中已经花费了那么多时间去工作,他剩下用来享乐的时间已经不多了。或许,他必须进行一种报复性消费心理才能得到平衡,他必须要在奢华的环境中才能进行更好的创作。那么,在新的债务之下他只好继续撸起袖子加油干,就像西绪福斯一样不断地把石头推向高山。
八、尘埃落定 西绪福斯式的生活方式极其严重的影响着他的身体健康。他病的不轻,身体已经十分衰弱。各种疾病集于一身,心脏肥大、血液过浓、过度肥胖、支气管炎等等。在和他最心爱的女人结婚之后,他的身体状况更是每况愈下。终于在1850年的八月十八日晚上与世长辞。其实,他就像阿喀琉斯一样,对自己的命运有预感并且选择了怎样去度过自己的一生。平庸的生活不适合他,毕竟他是那样的睿智,从青年时代起就有着光辉理想,他要用笔完成拿破仑用剑未能完成的事业。最后,事实证明他成功了。他注定就是一个伟人,他注定就要热烈的燃烧他的激情。他的一生注定是耀眼而短暂的。就如莫洛亚在传记最后中写道那样:“欲火燃尽了他的生命,塑造人物的行动耗尽了他的精力,他是自己作品的牺牲品。”和他笔下的《驴皮记》一样,不断的消耗自己的生命进行创作。每一部伟大作品的诞生,所付出的代价就是代表着他精力的驴皮缩小一圈。直至最后他的生命与驴皮一样消耗殆尽。
《巴尔扎克传》读后感(四):自杀式艺术家巴尔扎克
自杀式艺术家巴尔扎克
卢德坤
在我看来,市面上流行的巴尔扎克传记,安德烈·莫洛亚这部原著出版于1965年的《巴尔扎克传:普罗米修斯或巴尔扎克的一生》是最值得读的一种。虽然对传主的天才颇有认识,不过茨威格完稿于1940年的《巴尔扎克传》(张玉书译,人民文学出版社2014年3月第一版)在资料的掌握上明显差了一截,臆测之词多。亨利·特罗亚出版于1995年的《巴尔扎克传》(胡尧步译,商务印书馆2002年5月第一版),细节上对莫洛亚有所补益,但整体的布局、规划仍不出后者范围。《巴尔扎克传:普罗米修斯或巴尔扎克的一生》是特罗亚引用最多的一部同类书,是特罗亚认为的“描绘细致、感人肺腑的范本”。此外,特罗亚的流水账写法,不及莫洛亚来得生动,常令人感到厌烦。更重要的是,在直面《人间喜剧》问题上,莫洛亚表现出了最大的勇气,特罗亚往往虚晃一枪,掩面而逃。自然,我们不必苛责特罗亚,也无需在莫洛亚身上求得比他所能提供的更多的东西。探索《人间喜剧》,并非传记作家的特定任务,而是身为普通读者的我们求诸于己的行动。虽然,不算太厚的24卷《人间喜剧》并非人人都能扛得牢,它的创造者巴尔扎克的重量反而轻一些。
莫洛亚的叙述详尽,有时候我们甚至不得不认为,或许是太详尽了一点!如果说,巴尔扎克最值得我们钦慕的品质是丰沛、雄壮、盛大,那么我们最需要问的问题便是:为什么是他,而不是别的什么人写出《人间喜剧》?他具备什么别人不具备的特性?他有什么秘密武器?
只要对巴尔扎克的生活、创作——普鲁斯特认为,巴尔扎克的生活与创造之间,并无一条明显界限,巴尔扎克像创作自己小说人物的生活一样,创造自己的生活。巴尔扎克的生活,就是一部巴尔扎克式小说——有一个起码的关照,就能发现,其实,并无秘密可言。或者不如说,就算有秘密,他也早已和盘托出了:没别的,只不过在任何事情上,他比别人投入多一点,再多一点,直到溢出来,但即便如此,也不是阻止继续投入,直至终点——死亡。如果一件事情没有达到溢出的程度,对巴尔扎克来说就算不上是完整的,连“近乎完整”都不必说。换句话说,巴尔扎克的生活、创作中,有种种令许多人感到极度恐怖并尽力摈除的“过度”、“过量”、“过剩”。
这种“过量”,在巴尔扎克外在的相对清晰的人生轨迹上,是一目了然的。巴尔扎克的靡费,是传记作者很喜欢展开罗列式描写的,仿佛什么奇景展览:1831年,因办印刷厂铸字厂失败欠了一屁股债、凭《舒昂党人》《婚姻生理学》等作品一跃成为“文学新贵”而赚了点钱的巴尔扎克首先买了一匹马,一辆马车,一块印有数字图案的紫色毛毯和一顶四周垂着羊毛穗的华盖。一个月后,他买了第二匹马。为伺候这些牲口,他需要一个马夫,他也雇了一名;在裁缝布伊松那儿,他为自己订做了包括三件白色晨衣、一件腰带上饰金流苏的僧袍在内的豪华服饰,为马夫置了蓝色号衣,红袖美式绿背心和人字斜纹布长裤。这些行头,让他得以体面地赴晚宴或看歌剧;他把住处面积扩大一倍,在沙龙里挂上贝克林纱,摆上华美的镜子、家居、食物。在往后的日子里,巴尔扎克的作品和债务都各自增长下去。3年后,巴尔扎克换了一个住处,房间打扮得如同《一千零一夜》中苏丹及其王妃住的地方,和他笔下的“金眼女郎”芭基塔·瓦勒戴斯待的地方差不离(参见莫洛亚,第十三章、第十八章;特罗亚,第二部第一章)。事实上,我们看巴尔扎克的一些行止,就如同看《一千零一夜》里的故事。巴尔扎克当初不是设想,把《人间喜剧》当西方的《一千零一夜》来写?在巴尔扎克笔下,那些初见世面口袋里没几个钱然而又想征服巴黎的青年,亦千方百计置办这些东西,雄心、耐力、背德,再加上一点运气,便是他们的神灯。普鲁斯特的观察,是精准的。
相形之下,巴尔扎克直接投入于写作之中的“过量”,倒似乎没那么令人震惊了。一天二十四个小时,他不过取其中十六个小时用于写作,偶尔花十八个小时而已,常常是连续干上两个月罢了。为刺激灵感,他喝大量高浓度黑咖啡;为保持清醒,他吃很少东西。作为一种必要的补偿,写完一部书后,他冲去高级餐厅胡吃海喝,一口气吞下一百颗生蚝,灌下四瓶白葡萄酒——这,仍旧不过是前菜,煎羊小排、芜菁炖幼鸭、烤鹧鸪、诺曼底鲽鱼还在后头等着他(参见《巴尔扎克的欧姆蛋》,安卡·穆斯坦著,梁永安译,立绪文化事业有限公司2013年4月第一版)。巴尔扎克用“过量”治愈“过量”。
对大部分作家来说,人生是供体验的,展现在他们面前的世界,可以远观,可以近触,可以摹想,亦可置身其间,但总可抽出身来,这人世,仿佛只是一条供随意晃荡潇洒来回的游廊;对巴尔扎克而言,人生是供浸没的,虽然时时有溺毙之虞,但如果没有沉溺到底的决心,怎么将世界看得更清楚、体会得更切肤?巴尔扎克是西绪福斯,是普罗米修斯,与此同时,他也是坦塔罗斯:吃喝得再多,仍旧在一种“零度饥渴”之中,所以才不知餍足。上述第一类作家,亦写得出好作品,但我们只能将其看作是妙手偶得的。《人间喜剧》,跟妙手偶得没什么关系。此外,还有另一些丰沛、雄壮、盛大的作家,不过,他们写的也不是《人间喜剧》式巨著,他们没有巴尔扎克这么“疯狂”。《人间喜剧》独此一家,《追寻逝去的时光》庶几近之?
大人先生们会说,巴尔扎克这么干,何异于自杀!事实上,他们说得没错。活力四射的巴尔扎克,只活了51岁。但是,这不是必须付出的代价么?不是必须呈奉上去的东西吗?1838年1月20日,巴尔扎克致信韩斯卡夫人说:“我的茅屋落成之日往往是我的另一所房子焚毁之时。”(莫洛亚,第295页;特罗亚,第240页)巴尔扎克的生命,是那座房子,《人间喜剧》,是那座茅屋。但是,在这里,我们是要更珍视这茅屋的,因为这茅屋比那房子,更显得不可能。实现不可能实现的愿望,驴皮自然缩短——早在写《人间喜剧》的第二部长篇小说时,巴尔扎克便已洞悉这个残酷的关节——《人间喜剧》,正是“不可能的可能”。说到底,在艺术面前,个体的生命是渺小的。在这个意义上,我们可以称巴尔扎克为“自杀式艺术家”。冷峻、审慎、谨严会生产艺术,或许还能延年益寿,但巴尔扎克的“自杀式艺术”中最主要的的成分是放浪、浮夸、轻佻,但他得到的亦是冷峻、审慎、谨严,此外还有明晰、透彻等等,只是赔上了命。巴尔扎克的“自杀式艺术”中,还有一种东西——愉悦,“过量”的愉悦,将忧郁症远远甩在后头。在这个意义上,我们得说,巴尔扎克是一个“快乐的自杀式艺术家”。如果抽掉巴尔扎克身上的放浪、浮夸、轻佻,巴尔扎克还会是那个巴尔扎克吗?如果抽掉葛朗台、高老头、伏脱冷、吕邦泼雷身上与巴尔扎克一致的“过量”品性,他们还会是葛朗台、高老头、伏脱冷、吕邦泼雷吗?论述《人间喜剧》时,莫洛亚引了其师阿兰一句极富洞见的话:“若要真正地研究人,就必须以巴尔扎克教给我们的这种粗暴方式去爱他们。”(第441页)
由此,便可以澄清一个问题:都说巴尔扎克是现实主义的,但是构成这种现实主义的,并非照着现实依样画出的葫芦;巴尔扎克式人物,并非现实中的甲乙丙丁,而是总因夸张、扭曲、偏激而显得超现实、反现实的一批人物。在巴尔扎克的现实中,总有什么东西是多出来的,多出来的还不是原本就有的事物的简单堆叠,而是被巴尔扎克浸染过的一种回溢物。因此,我们要注意一件事情:并非所有的“过量”都能达到巴尔扎克式的功效,过量的无根的幻想如同过量的空白物。与巴尔扎克有着形似“过量”的大仲马,无法生产出《人间喜剧》式作品。
莫洛亚以一个问句结束《巴尔扎克传:普罗米修斯或巴尔扎克的一生》:“谁不愿意成为一个巴尔扎克呢?”(第593页)对此,我是颇有怀疑的。首先,能不能再“成为”一个巴尔扎克?假设这是可能的,如何能再“成为”一个巴尔扎克?我想,最主要的构成因素是,作为一个孤绝的个体承受住那种绝对的“过量”。如果有人对莫洛亚说,“谁也不愿意成为一个巴尔扎克”,我一点也不会感到意外。
左拉曾很直白地说,巴尔扎克之所以能创造《人间喜剧》的世界,“仅仅是为了还债。是的,这个不知疲倦的巨人只是一个受到债主围攻的债务人,写出一部小说是为了支付债据,积累起一页页稿纸是为了不被抓起来,制造出这奇迹般的产品仅仅是为了付清每个月到期的票据。看来,在始终紧迫的需要压力下,在他可怕的金钱困境中,他的头脑扩展了,爆发成杰作”(《法国六文豪传》,郑克鲁译,安徽文艺出版社2011年7月第一版,第85页)。在生命的后期,巴尔扎克的创作力遭遇滑坡,莫洛亚认为,这是因为巴尔扎克终于能和韩斯卡夫人在一起,“经济上的宽松扼杀了创作上的多产”(第557页)。我禁不住想,1850年,如果疾病没能扼杀巴尔扎克,他还完了债,和韩斯卡夫人过上幸福美满的生活,然而,还能继续创造吗?有两种可能:一、巴尔扎克变成了一个体面的资产者,舒舒服服地过他的日子,艺术什么的,一点也不重要了。或者,在闲暇时,还能舞个文弄个墨,但写出来的,还是《人间喜剧》吗?二、情况一点也没有改变,巴尔扎克依旧过着自杀式生活,“烧掉一座又一座房子”。韩斯卡夫人再也无法忍受他,或者跟着他一起堕入地狱。疾病很快再缠住了他,死亡很快又找上了他,但他能不能再为《人间喜剧》添了几块砖瓦?我带着恶意,祈求第二种可能不只是一种可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