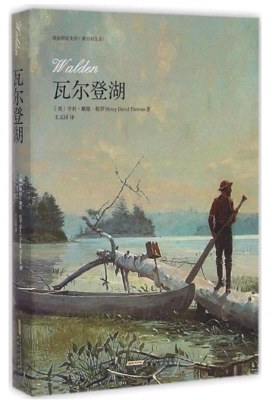
《自由国度》是一本由[英]奈保尔著作,上海译文出版社出版的平装图书,本书定价:20.00元,页数:323,特精心从网络上整理的一些读者的读后感,希望对大家能有帮助。
●无边境
●看比雷埃夫斯的流浪汉我就想起了卓别林笔下的丑角 。《孤独的人》已经是我最喜欢的文本之一了。
●读奈保尔的书,总感觉有一种阻力,即使写得很好的《米格尔街》也是。这书就更严重,因为篇幅越来越长。读《比雷埃夫斯的流浪汉》感觉很好,《告诉我,杀了谁?》就有点儿懒得看,主打的《自由国度》干脆没看完。
●退步了
●全书都是身处异地的不适应、惶恐和战战兢兢,读完让人畏手畏脚。值得读,但着实不喜
●到底是没有米格尔街写得好,但也不算赖,旅行那段很喜欢
●自由国度也好,自由意志也好。不管在哪里,永远不可及。 完毕。后殖民主义
●没有米格尔街好。给我的冲击力没有米大。
前段时间对印度感兴趣,看到这本印裔作者的书就看了。看了有段时间了,作者完美呈现了当事者的状态心理,谈的够深入,文字也不错。值得一看的作品。但对我来说不属于那种摧枯拉朽的作品,姿态不够力度。也没有带来新鲜的观点。所以评价就差一截了。
《自由国度》读后感(二):奈保尔却是冷峻
英国不是他的故乡。他觉得自己的灵魂属于印度,却又游离其外,他要成为一个作家。作家,意味着远离了日常,意味着孤独。但他又从未停下脚步,不断地在不同的土地上逡巡着,探索着。
上海译文的这个版本已经不好找了,很早以前读过。现在读的大部分都是南海出版的。个人觉得新版的翻译要更胜一筹
《自由国度》读后感(三):孤独的人
我读完整本集子后还是喜欢《孤独的人》,看完的时候给朋友推荐过。
至于第二个小说《告诉我,杀了谁?》味道有点类似余华。只是类似,却各有千秋。
真正到了《自由国度》的时候,我读不进去了,还要仰就书的翻译家后记。
《自由国度》读后感(四):每个人都远离故土
for 上海壹周
一个印度厨师跟随他的主人去了美国华盛顿;一个西印度青年远赴伦敦挣钱照顾弟弟;一对英国殖民者在新近独立的非洲国家旅行,目睹了部族残杀和社会动荡……在2001年诺贝尔文学奖得主奈保尔的虚构世界里,每个人都远离故土。这本获得1971年布克奖的《自由国度》,由三个短篇小说和两篇“旅行日记”组成,围绕“自由”这个主题,在殖民/后殖民的语境中,对“何为真正的自由、如何获得真正的自由”,对殖民主义进行了深刻的反思,并探讨了远离故土的异乡人的身份迷思。
奈保尔是个印度裔作家,生于特立尼达,十八岁时进入英国牛津大学攻读英国文学,毕业后迁居伦敦,加入英国籍。他的履历使他成为一个漂泊的“世界公民”,文学评论家们一度认为,他之所以直到二十一世纪才拿到诺贝尔,只是因为不知该以哪个国家的名义提名他所致。在六十年代,奈保尔周游了南美洲、西印度群岛、美国、加拿大、印度和非洲等地,获得了丰富的现实材料,为他的殖民书写奠定了根基。
瑞典文学院的颁奖词称赞奈保尔“将具有洞察力的叙述和不为世俗所囿的详细考察融为一体,促使我们看清被遮蔽的历史真相。”在这本短篇小说集中,我们同样可以看见奈保尔殖民书写的特别之处——他不但像大部分殖民书写者那样谴责殖民主义在殖民地的压迫和欺凌,更尖锐地指出被殖民者同样有错,他们的“奴性”和被殖民文化本身的局限性同样是问题所在。在《孤独的人》中,远赴美国的厨师对着新主人不自觉地喊出了“老爷”。奈保尔写道:“过去,这个词我一天要用一百遍。不过那时,我认为自己是老板存在的一小部分,所以这个词并无奴性。(……)对普里亚而言,‘老爷’这个称呼便具有奴性。”(P53)在标题甚为反讽的《自由国度》一篇中,奈保尔借上校之口讲得愈加明白:“知道是什么事情令我困惑吗?是这些非洲人一旦服从命令,是如何心甘情愿地被压迫。”(P258)作为一个离散的书写者,奈保尔以一种“他者”的眼光对殖名者和被殖民者各打五十大板,写出了多元种族文化的困境。
《自由国度》里有大量殖民地的地貌和景物描写,颓败破落的非洲图景仿佛是殖民地幽暗的社会政治现实的外化,一如在《告诉我,杀了谁》之中奈保尔将异乡人的凄惨处境变成心中无处发泄的呐喊:“哦,上帝!告诉我谁是敌人。一旦你发现谁是敌人,你就能杀了他。然而,这里的人让我困惑,是谁伤害了我?又是谁毁了我的生活?告诉我,报复谁。”(P119)就这样,在外化的地理图景和内在的心理图景之间,奈保尔以文字建构着殖民书写的力量。
http://btr.blogbus.com/logs/26516088.html
《自由国度》读后感(五):孤独,是对过往的剥离
读罢《孤独的人》,去阳光房冲咖啡休息眼睛,窗外夜色溶溶,远处高楼闪着荧蓝的霓虹,城市在进入睡眠前高调着喧闹,越过丛丛被黑暗浸溶色泽深紫的树冠,能听见马路上车来车往的呼啸。
适才的阅读仍给我快意的享受。V S 奈保尔,自从他以诺贝尔获奖作家的身份进入我的书单后,我一直在寻找他的所有作品。《作家看人》居然是我读的第一部,艰深之外,能感觉到他对待技巧的严谨态度。《自由国度》拿到后,我在中心花园的木亭里坐了一下午,阳光暖暖,树香风醉,有鸟鸣,但我完全沉没于印度打工仔的世界,那里没有一丝的柔情可以比拟。
桑什托呀,我想,给这个可怜的人什么评价并不重要,重要的是给作者什么要的感想。有评论认为,奈保尔的描写有些迎合一般人对第三世界打工仔的期待,是有些啦,比如拿飞机上的赠品,坐电梯时的恐慌感,第一次进华盛顿咖啡馆被赶出的经历等等,正如有评论认为帕慕克之所以受宠于西方见弃于土耳其是因为他的西方叙事视角。
但我总觉得没这么简单。作为一个目光冷峻的记者型写作人,奈保尔曾为加勒比海之声写了3年书评,他是不屑以暗含岐视逻辑的描写获取心理优势的。
他只是还事实以事实吧。
给我最深的感触,不是奈保尔稳重克制的叙事笔调,也不是不情感与判断力的冷静视角,而是他掌握呼吸一般的节奏掌控能力。金庸武侠世界里,越是高手越是讲究呼吸,呼吸可以调节心跳、调节神经反射、调节丹田之力。《孤独的人》只有一个主角桑什托,却在书中幻成了三个不同性格的人,在孟买时他快乐而无知,在华盛顿公寓里他平静而压抑,在印度餐馆里他张惶而狡黠,在故事的结尾,桑什托的叙事语气几乎可以比拟哲人,平缓、无奈、忧郁的气质追随不绝。
桑什托的改变是由环境引起的,而环境的改变是桑什托自已的选择。孤独的人之所以孤独,是因为他再也回不到出发的地方,即便他在心里几千几百遍的渴望回归,因此,故事的开始,桑什托说――“我现在是拥有绿卡的美国人,我住在华盛顿,然而,很久以前,我在孟买――”回忆之后,桑什托最初快乐的尽乎无赖的语言、表情、动作一一闪现,让人忍俊不禁。到华盛顿,住进高层公寓后,笔调开始放缓,幽闭的生活里,当年孟买同伴的话应验了――“美国人会跟你一起抽烟吗?他们晚上会和你一块坐着聊天吗?他们会跟你手拉手在海边散步吗?”
桑什托最终发现了这个悖论,当他越发自由越发有能力操控人生时,他变得越发的不快乐,他走过当初以惊恐眼神注视过的印度人歌舞团,此时此刻,他的目光坦然淡定,但他却“我边走边想,倘若圆场地那些穿印度服的人真是印度人那该多好。那我就会加入他们,和他们一起外出流浪;中午时分,在大树下歇歇乘凉,傍晚时,西沉的太阳会将粉状的云彩染得金黄,每天晚上,在某个村落人们会欢迎我们,给我们水和食物,晚上还有篝火。”
对桑什托来说,哪一个桑什托才让更让他欢喜?在成长的阵疼里,我们不得不挥过往,有时理由简单的仅仅是不愿回乡下去搬那些印度人的铁箱子,在角色转变的间息,我们却是迷茫的,迷茫的不知月落日升,不知斗移星转。
桑什托的生意伙伴普利亚有一句话露了天机,他说“你有老婆孩子,在乡下,他们在那里就好了,他们不会影响你。”
过去的一切,喜怒哀乐,放不下舍不掉,它们在那里就好了,别再让它影响当下。
我们孤独,因为我们总是必须和与我们有密切联系的曾经切断关联,无论有多少精彩的未来,都无法替代对曾经的怀念。这,也许正是东方民族在向西方发展模式痛苦转进过程中发出的呻吟。
是的,我们孤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