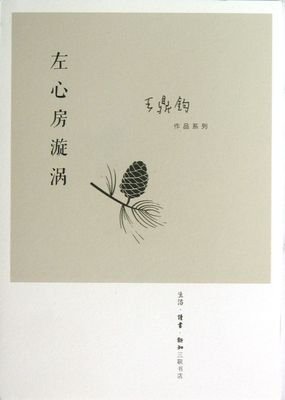
《左心房漩涡》是一本由王鼎钧著作,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出版的平装图书,本书定价:26.00,页数:258,特精心从网络上整理的一些读者的读后感,希望对大家能有帮助。
●高三最失神的那几个月吧,读王鼎钧的书,做了很多书摘。熬日子和熬粥不一样,后者越熬越香,前者只会越熬越淡。乏善可陈的这一年,还好有读点书吧。
●多言多败
●全书三十三篇全部围绕乡愁,不同角度相同情愫,从怨怼到释然,有情感的宣泄,有禅思的升华。鼎公的情感如此丰沛,初读有黏腻之感,卷终回味无穷。
●如詩般的散文,如細流般的鄉愁,心潮澎湃,淚濕衣襟。你為什麼說,人是一個月亮,每天盡心竭力想畫成一個圓,無奈天不由人,立即有缺了一個邊兒?
●3.5;与“回忆录四部曲”简洁凝练的文风大不相同,本书情感外显,文字浓墨重彩,锻字炼句均非常雕琢,大段排比激荡几乎认不出鼎公,或许书信体格式可以直抒胸臆之故;去国离乡,此去经年,“大陆是回不去的家,台湾时醒了的梦。”回忆是浸礼,乡愁是千秋万古,隔着海峡回望四十年,生有时死有时,聚有时散有时。
●虽是散文,却用了很多诗歌、戏剧、小说的技巧,多隐喻,多跳宕,讲究炼字和节奏。如果不了解两岸之间在四九年到八七年的关系和生态,是进入不了这本集子的。再加上鼎公长期供职于纸媒体和广播电视,擅曲笔,文字背后就更显意涵。以前与应凤凰老师交流时,她脱口而出的是该集子中的一句,“我的乡愁是浪漫而略近颓废的,带着像感冒一样的温柔。”
海中礁石,江流石转。巨石喻人、喻众生,海水江水喻时代、喻命运、喻流转。众生看似千差万别,实则生来平等,都是在时代命运中身不由己的流转。经过时代的洗淘,人由最初的处子之眸而变得千疮百孔,但美丽动人的恰恰便是这千疮百孔。
作家是人类心灵的医者。文学应是一种跨越一切时空、地域、种族、文化的,在人类最高精神层面的,无论喜怒哀乐的共鸣。但事实上,这种种差异落在现实的芸芸众生中,想要跨越,实在太难!但不代表文学做不到,因而世世代代多少杰出作家前仆后继,为此努力奋斗,为人类永恒的灵魂共鸣而呕心沥血!只要有此心,但做无妨,这是一种肩负人类道义,解救众生的文学观。
一个对文学有着深切感知,对人生有着洞彻见识的人不须再抱怨、不须再愁闷。因为无论此生遇到什么样的同行者,我们都要感谢他,感谢他敞开了自己的生命,感谢他让你“兼生”。容忍、赞成、鼓励,是我们实现自我救赎以免沉沦的唯一路径。
面对时代命途流转,个体生命要谦卑;面对后天的磨砺,先天的智慧要谦卑;面对众生,即便是心灵医者也要谦卑。由此可见个体自我是多么的渺小和不可说。多少人自视历尽沧桑,自视超脱,却在真正面对茫茫天道之时受不起半点挑战和诱惑。
《左心房漩涡》读后感(二):无用的伤逝
过几天就回学校了,有些舍不得家里的闲书。
王鼎钧先生的《左心房漩涡》,初入校,混着些专业书胡乱买的,寒假带回家,忘了看也忘了带回去。
夜深人静翻开,便停不下去了,那样美的文字,那样深的悲恸。读至《读江》一文,竟满脸泪水。
“回想当年经过的山山水水,都成了濛濛烟雨中的影子,像米芾的画,唯有这条江一根线条也不失落。”
“江上秋早,寒意扑人,江水比烈酒还清,水流很急,但水纹似动还静,江面像一张古代伟人的脸,我仔细看那张脸,看大脸后面排列的许多许多小脸,以他们生前成仁取义的步伐,向下游急忙奔去。”
于此,我暗叹作者几笔写出了我望江时难以言说的情感。小时,乘船穿越三峡,伏在栏杆上,脚在水波中,葱茏的树木与时急时缓的水,便如此轻易唤醒了未名的伤感。
但,历史总是个引子,有时比药重要,但不是药。
他写的纤夫,是那么骨血狰狞。
“那站在冷冷的江水里张网待鱼终此一生的,是人。”
宏大的时代中,我总是被告知纤夫的勇敢、坚毅,用精神的旗帜裹住裸露的身体与人生。
“表情漠然,撑一条船上游下游终此一生的,是人。”
“在长纤上拴成一串挣扎呼号度过一生的,也是人。”
纵深一跃的男女,转世婴孩的啼哭。
江是人生,是时代,是更磅礴莫测的符号。
字里行间,我隐隐感受着那个特殊的年代,叩合着永恒的流淌。
《左心房漩涡》读后感(三):满纸粘稠的乡愁,述尽心中的无奈和生命感悟
薄薄的一本小书,竟让也看了三天,若是一本如此体量的小说平时基本一天便可将其读完,是因为感觉此书的内容沉甸甸的,读起来也颇有些“费力”,需要即时消化和体悟。作者那浓得化不开的思乡之情和对阔别四十年故土的追忆贯穿始终,常常让读者充当第二人称,让我读着读着彷佛阅读一位老者的亲笔书信,又仿佛这位客居纽约的老者正拉着自己的同乡侃侃而谈,巴不得把他对祖国的怀念与他一生的感悟和无奈都倾诉出来。我仿佛就是那个被他拽着衣角,听他诉说一切的同乡。从他的文字中能感受到他眉头紧锁,白发苍苍的面容。
书中时而闪现的人生的感悟,被作者以极为形象优美的文字转述而出:
“我们都是靠自己的缺点活下来,理想化为钱币上磨损的人面,名声不过是生空飘摇的气球。”
“我们都有所不能,握住火把、握不住光,握住手、握不住情,不能扫起月色,揭下虹,不能将酒涡一饮而尽,我们都不能使兽变人。”
特别喜欢《我们的功课是化学》里作者把人生极为生动地比喻成化学作用,想想何尝又不是呢?
“听我说,生活是不断的中毒。人生修养就是分解这种毒素。不要再加减乘除了,我们的功课是化学,不是数学。化种种不公平,不调和,化种种不合天意,不合人意,化百古千痛,千奇百怪。” 确实我们人人身上都有不少毒素,如何”排毒养颜“我们的人生?如何化解一处又一处的危机和自身的心魔?而不是天天只想着赚票子,数票子的多少,计算得与失的差额.....
读到书的最后看作者写的小结,有种暖暖的感觉,作者最后的寄语充满诗意,回味无穷:
“愿生命是条河,是河中的微波,不停滞,不回顾,偶然有漩涡,终归于万里清流。”
《左心房漩涡》读后感(四):听她痛哭
你对社会现象的关心,原不后人。当年烽火遍野,流离道途,为了在困境中振作起来,老师教我们各言尔志,那个场面,现在回想起来十分感人。有一个女同学,她叫什么名字来?她和一个男生沿途互相扶持,有一夜投宿荒村,男同学突发高烧,寻水不得,记起村前有一条细流。就这月光看去,那水十分清甜,就急忙舀起来喝了,他喝完了水,就在溪边躺着,高烧不退,就挣扎着再喝。挨到日出,我的上帝!这才看见水中全是数不清解不开乱成一团的小虫子!日落之前,那位男同学就死了。我们一同埋葬了他。我们一同劝那女同学节哀。我们一同听她痛哭,她把自己哭成情侣,哭成妻子,哭成母亲。各言尔志,我们听她哭着说,她要使全国各地、无论多么偏远、无论多么高亢的地区都有自来水。 “我们一同听她痛哭,她把自己哭成情侣,哭成妻子,哭成母亲。”这句给我印象深刻,让我也想起给我留下印象最深刻的一次哭泣,那次是哭成女儿。
记得老家有一个叫叔叔的亲属,40多岁就去世了,接触不过,但人和温和,他的媳妇在村里有名的孝顺,长期照顾他有点迷糊的老母亲,他的女儿跟我姐姐差不多大,我喜欢跟在她们后面玩。
那会我还小,农村的葬礼给我感觉庄重严肃又热闹非凡。院子里到处被白色包裹着,一大群家属通身从帽子到鞋都是白色,没有白鞋的就缝上一片白布。下葬日期到后,一些给塞过烟的年轻壮汉,有力的抬起棺材,一路白色纸钱满天,哭声、丧乐让人觉得热闹又敬畏。
到达埋葬地后,年轻人开始挖坑,亲属在坑外转圈哭丧。中午12点准时往坑里放入棺材下葬,这时也是每次葬礼哭点最高的时候。我见过很多场埋葬,很多场哭泣。可能我太小,体会不到那种痛苦,或者他们的哭泣太假,感染不到我。在棺材放下的一刻,他的女儿,放声大哭,那天阳光很好,照着她的脸好像浸在了河里,看到我突然心里一颤,不自觉的也跟着哭起来,心里也跟着难过起来,好像她悲伤的眼泪只由她自己的眼睛流出已经不够用了,必须要借用我的泪腺一起流,心里的悲伤太大,必须借由我的心一并装下,年轻人多,埋土的铁锹也快,棺材被土一层层盖上,逐渐堆成了坟头。
女儿哭到呼吸困难,变成小声的呜咽,轻轻的跟她的父亲做最后的告别。
《左心房漩涡》读后感(五):有病呻吟王鼎钧
初识王鼎钧,是南君和我换书,那天他还带了一张古早的南艺展览券。我不专门收票据,但是逢着有点说头的还是统统拿下,毫不客气。
那次聊天聊起台湾作家,双方寒暄一番彼此熟识的那些之后,他提起了这位我此前没有涉猎的作者,率先提出的,便是他的回忆录四部曲。
这套书有台版和简体版,我未能均收入对比来看,无法谈论是否有严重变形与删改,仅就读到的而言,即便这是删改版,也足以伸出十个手指来称赞。
喜读台湾作家的回忆录,可能因为里面还存着一些创痛后依然理解“人何以为人”的尊严,当然明白两岸的纠葛是多少字也写不尽,但以对岸为镜,互相映射,无论如何要比偏听一言堂好些。
用王鼎钧书写下的话来说:“我们都有癌要割除,有短路燃烧的线路要修复,有迷宫要走出,有碎片要重建,有江海要渡。”
四部曲里的王鼎钧,是厚重的,信息量巨大的,令人感到掩卷后思绪渺远的。这很容易和齐邦媛等相观照,我们知道近代史在我们身上如何发酵,也需要知道在“那边”同胞的生命史里如何显影。
很喜欢他的这一句话:“我的心如同一张底片,既已感光,别的物象就再也难以侵入。”
你看他的书名,《关山夺路》,像直接奔到眼前的虎,同侪说他的一些书名不是从篇章里寻了吸睛的摘出,而就是一个言说整本书的词组,亮亮堂堂放出,大声告诉你,他就是预备在这样的心绪里抒写往日。
又很喜欢三联出的《碎琉璃》这一套装帧清雅的小书,体量上比四部曲轻,但气量未必弱。总觉得这种点到即止的形式更符合先生的气质。针扎似的追问,却针针穿透皮肉,在骨头上渗出痛。
此前我觉得他是少有大哉问的,他是那样关心具体的人,描写苦难都克制,可这样的王鼎钧一旦仰天长叹,便加倍于你脑内涂抹:
那些人无知,可是有知又怎样呢,学问能助人忍受痛苦,究竟能忍受多大的痛苦呢。学问能助人逃避现实,究竟能逃多远呢。学问能使人有眼光,究竟该朝哪个方向看呢。
这都不是没来由的喟叹,他写初恋的女孩在战乱中失踪,甚至恐荒诞般地就丧生于自己身旁,覆于一大钟之中;写野蛮的乡野里教育救不了孩子,他们食苍蝇代医疗,用痢疾治便秘;写老宅里的鬼传说,人心惶惶时期,大家竟盼着鬼来为心里做确证;又写一身病痛的母亲,写麒麟童沙哑的嗓子,写海外生存的华人如遇风之烛,飘摇惘然。
可能是一辈子太长,历经了太多,或许这辈子太短,只是恰好生逢20世纪的中国,王鼎钧笔下写不尽的细碎,令和平时期所有的艳丽博大都空洞。
“黄河能当得起那么多的歌颂吗,八千里痉挛的肌肉,四百亿立方尺的呕吐。面对上游,河水使我高血压;面对下游,河水使我心脏衰竭。不敢凝眸,不敢合眼,不敢吐痰,不敢吸烟。我为洗脸而来,不敢湿手。这条在三千里平原上随意翻身打滚的河,用老年的皮肤,裹着无数蝼蚁和人命,芦苇和梁柱,珍珠和乱石。狐狸会上山,老鹰会上天,饶不了放不过的是流泪的牛、下跪的羊和缩在母亲翅膀下的雏。那河几番灭省灭县灭人三代九族,使中国人痛苦,无动于衷,不负责任。为什么还要歌颂它,难道只是因为在河套有几块田,难道只是为了在河边喝几碗鱼羹,在龙门拍几张照片。”
有一册的附录里有友人称赞鼎公,说他的句子是“格言式”的。这不是一个基础性的评价,而是一种有力的,对有病呻吟的高度赞许。
和浅薄生活里勉强获得的感慨相比,读鼎公的文字,我双手是颤抖的,他就是他笔下的卜卦人,是能把酒还原成葡萄的烟火模糊的观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