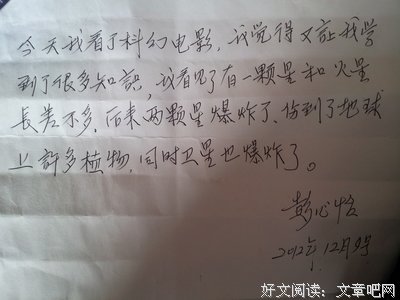
《私人摄像机:主观电影和散文影片》是一本由(意)拉斯卡罗利著作,金城出版社出版的精装图书,本书定价:55.00,页数:432,特精心从网络上整理的一些读者的读后感,希望对大家能有帮助。
●翻译太差了,还有些错别字。不过作为扩充知识和按图索骥功能还是可以。
●好书。不过介绍奥利维拉那里有一个明显的翻译错误,把波尔图译成波尔多了。
●不该加个书信电影吗
●翻譯增加閱讀難度... 作者的觀點還是很有啟發的:散文的異端性/作者再現的策略(聲音 found image 凝視 等)總之散文電影還是非常可愛的:我(導演)現在要講我對這件事情的看法 你(觀眾)既然點開視頻了 就恭敬不如從命吧!#大半夜的 為什麼這種書越看越high...
●关于散文电影一说有启发。翻译太烂了....太烂了....
●建议校对吃屎。整理了一个豆列 https://www.douban.com/doulist/45945247/
●时不时翻一下,醍醐灌顶。
《私人摄像机:主观电影和散文影片》读后感(一):整理了一个豆列
https://www.douban.com/doulist/45945247/
Experimental Film
Jonas Mekas:Independence for Independents
《私人摄像机:主观电影和散文影片》读后感(二):拉斯卡罗利致中国读者
《私人摄像机》最初于2009年出版于英国。当时,我并不知道这本书会获得什么样的反响,更别谈会影响多深远。这不仅仅因为我感觉这本书是为我自己而写的——关于我喜欢的主题,关于我喜欢的电影,关于为什么电影对我如此重要。我只希望这本书能够得到一些关注,因为这是关于散文电影的第一本英文书;同时,我也知道和其他更宽泛更主流的主题、流派和电影形式相比,这是一个相对小众的领域。然而,由于人们可以轻松接触到新数字技术和发布平台,这个领域也处于快速的扩展中。今天,这些技术鼓励人们更个人、更主观地参与到电影中,也使得实验电影、第一人称电影和独立电影等多种电影形式有了发展的可能并在全球范围内欣赏。
这本书出版之后,阅读的人越来越多,我也幸运地收到来自于各方关于《私人摄像机》的赞扬,有讲师、学者、学生、批评家和电影人。对于这些,我深表感激。每次,我都又惊又喜:惊的是我没有预料到这本书的阅读范围如此之广,对于人们来说如此意义重大;喜的是对于我来说,这个主题有着非同一般的个人意义。因此,当我知道这本书即将出版中文版时,我感到了新的惊喜。想到这本书将要漂洋过海,离我最初写作的地方如此遥远,我就非常激动,这远远超出了我原来的设想。我非常感谢余天琦博士,她策划并促成了这本书的中文版。我也要感谢每一个参与其中的人。我还要感谢你们,我的读者,感谢你们打开这本《私人摄像机》。散文电影是一种关于对话的电影,是不同主体之间的对话,也是在共享的思维领域里不同观念之间的对话。我希望这本书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带来独特的体验,为共同的反思提供一个类似聚会的地方。
劳拉•拉斯卡罗利
2013年9月16日,于科克
《私人摄像机:主观电影和散文影片》读后感(三):走向镜头前的“我” 原载《艺术世界》2014年09期
(原载《艺术世界》2014年09期)
如果有意识地纵观那些集中于电影领域的讨论,我们可以发现,有两个明确的主题一直徘徊其中:首先是对电影艺术性的正名,另一个则是影像的主观化与客观化的论辩。当意大利人卡努杜将电影划归为人类的“第七艺术”时,“电影是一门艺术”似乎可以不再迟疑地表达。但接踵而来的是,电影需要面对几乎所有艺术形制都无法回避的问题:它是主观个人的,还是客观写实的。安德烈·巴赞在《影像本体论》一文中说:“一切艺术都以人的参与为基础,唯独在摄影中,我们享有不让人介入的特权。”一具用泡碱处理过的、干瘪的和呈深褐色的木乃伊是巴赞对于摄影影像形象化的比喻,克拉考尔随声附和道:“当影片记录和揭示物质现实时,它才成为名副其实的影片。”讨论至此戛然而止。
但是从另外的先锋电影的轨迹来看,它们似乎从来没有遵循过客观化或现实主义的影像标尺。欧洲的现代主义思潮、美国先锋派都在表现人和人的个体情绪上下足了功夫,戈达尔、布里奇切、梅亚黛伦,个人化的精神和梦境置放于镜头中,将记录普遍意义的生活场景的摄影机趋向于私人化了,发展了主观电影的方式。当然,主观电影本质上只是更重视“我”眼睛中看到的世界,而不是所谓摄影机的记录,摄影机服从于主体。
主观电影不是作者电影。戈达尔说:“当我还是影评人时,看了一些布努埃尔的电影,就十分喜欢。那些电影很独立,我觉得他应该属于那种完全躲在摄影机后面操控的人。”这是他对电影作者论的认知,而主观电影强调导演从镜头后面走到镜头前,用第一人称的口吻向观众陈述、分享自我,以实验、激进式的方式呼应我们今天需要的更即兴的自传式私人表达形式,例如费里尼的作品《八部半》。因而,拉斯卡罗利在《私人摄影机》中,用大量篇幅来解析“第一人称电影”。第一人称将镜头聚焦的内容和方式变得私人,并不妨碍影像精神视野上的宽阔,甚至比客观镜头表达的电影更加具有实质内涵,私人化使这类电影的形式更像文学作品中的日记、笔记和抒情散文。
拉斯卡罗列认为电影技术的革新助力了私人化电影的发展:“新数字技术鼓励人们更个人、更主观地参与到电影中,也使得实验电影、第一人称电影和独立电影等多种电影形式有了发展的可能。”可是很奇怪的是,私人的往往被暴力地等同于先锋,大多数人更乐见那些用以展示共同经历、已经发生,没有丝毫内容创作力的艺术作品,摄影机无力地重复现实,却忽视对个人的认同。早已无需去强调电影作者创作的现实倾向,反而该强调从私人化的角度认识主观电影的无限可能性。这本书也就是在推动这种转变的发生。
在《私人摄影机》中,拉斯卡罗列同样对散文电影进行了系统化的梳理。散文电影,以及诗电影在诸如帕索里尼等导演那里也有着极多的讨论,以探求电影语言的文学传统。本书最为可贵的是它对一种还没有产生公认标准的电影类型进行了定义,极富开创意义。而且与主观电影结合,成为“私人摄影机”这枚硬币内容和形式的两面。因为主题的明确性,《私人摄影机》这本书不艰涩却十分耐读,可以成为专业电影人和喜爱电影的观众进一步了解影像私人化的优秀读本。
《私人摄像机:主观电影和散文影片》读后感(四):非真实的童年
以下故事都不一定真实,如果你认为有真实的部分,那应该是真实的。
1962 《伊万的童年》
《伊万的童年》电影海报 19621849年12月22日,陀思妥耶夫斯基被押赴刑场执行枪决,在枪响前一霎那,传令官送来了沙皇的赦免令,把刑罚从改枪决为苦役,在生死界限上走了一遭的陀思妥耶夫斯基,思想从此转折,写出了许多鸿篇巨著。俄国这个国家什么都喜欢学习法国,连绞刑也要学习,12岁的伊万也不幸被绞刑处死了。
我12岁的时候在做什么呢?我好像每天在做白日梦,像极了一个特别平凡的童年,没有故事,什么都没有,连记忆的片段都不敢确定是否真实存在过。12岁的伊万在死之前想什么?他的世界对我来说是完全陌生的经验,我总是羡慕那种陌生的经验。如果我在12岁的时候,也遇到了绞刑,然后幸运地像陀思妥耶夫斯基被赦免,我的人生是否会改变?我不确定我是否能写出些什么鸿篇巨著,我可能会战战兢兢地过完一生,我还是会过完看似波澜不惊且平凡的一生。我相信那才是大多数人的命运,毕竟传奇的事情你没有体会过,那你就没有足够的勇气相信所谓的传奇。
好像伊万也没有被绞刑,他只是在12岁的年龄战死在沙场上。他好像是被一颗炮弹击中,没有得到及时的救治,失血过多而死。所有我们认为的传奇结局,一定是战死以后就没有了,一定没有特别真实地结局,我们愿意描述一段看似和传奇结局所匹配的内容。12岁的我那时还在做白日梦,也没有当军人的梦想,只是想在下雨的时候,躲在温暖的被子里听雨声。
如果一个电影艺术家找到了可以表达自己的主观真相的视觉隐喻,我们就不再觉得那个主观愿景是关于宇宙,甚或是独特个人的唯一真理。现在,我们可以把主观性和真理看成是复数的,它们不仅存在于主体之间,也存在于主体内部分散的自我之中,有些部分甚至连我们自己也不知道。(图里姆,1992:202)
1984《冬冬的假期》
《冬冬的假期》剧照 198480年代,侯孝贤电影里闪现了侯孝贤、朱天文、吴念真三人三段对应的个人经历:分别是在《冬冬的假期》里朱天文的孩时点滴,《童年往事》里侯孝贤的伤感追忆,还有《恋恋风尘》里吴念真的淡然初恋。至于朱天文著作改编的几个电影则另外在列。《冬冬的假期》里虽然包含着两个孩子(冬冬和婷婷)的不同视角,但真正出发点则是朱天文零散的点滴回忆,再以侯孝贤电影散文般的笔触一一展现出来,其故事原本是朱天文《炎夏之都》里的一篇《安安的假期》。因此《冬冬的假期》是一本不折不扣的儿童电影,同时又让成人世界的纷纭无奈晓于孩童的目光所察中。
在1982年,内地也有一部题材类似、口碑颇佳的电影《城南旧事》。“不思量,自难忘……”,台湾作家林海音同名著作改编的影片是以这样一句饱经沧桑后的感慨嘘叹开场。[注1]不难理解带着乡愁的回忆是该如此的沉重,而随着影片里人物的纷纷离去,英子也告别了她的童年。散文诗般的影片在最后一个摇升镜头里结束,红叶叠化、马车远去,英子向童年的北京作别。“爸爸的花儿落了,我也不再是小孩子”,城南的往事成了英子一生难以磨灭的记忆。多年后林海音重返北京,旧地重游,看着面目全非的一切,不禁喊了声:“我的城墙呢?!
”所有伟大的虚构电影都倾向于纪录片,就像所有伟大的纪实文学都倾向于小说。(让-吕克戈达尔,1985:181-182)
2000《一一》
《一一》剧照 2000看《一一》的时候我一直在走神,电影太像生活,不像电影,常常让我和自己的个体经验联系起来。片中那个少年所说,“电影把我们的生命延长了两三倍”。但是像《一一》这样的电影是不能延长我们的生命的,它只是提醒我们生之短暂,生之纷扰。那些相似的人生悲欢,总是能从电影中走出来,为此,我一直陷入回忆而忘记了自己是在看一部电影。
比尔尼科尔斯(Bill Nichols)所说:“传统上,纪录片这个词代表圆满,完成和关于社会世界及其机制的知识、事实和解释。但是最近,纪录片已经开始代表未完成和不确定,记忆和印象,个人影像及其主观建构。”(尼科尔斯,1994:1)
杨德昌
杨德昌去世后的半个月,有一天夜里,突然下起雨来,湿漉漉地上了公车,经过一个商业区,上车的人顿时多起来,间或有人好奇地向车上的电视张望一眼,看到一个陌生的名字之后便垂下眼睛,继续谈笑,看往别处。当时电视屏幕放的是杨德昌的简介:他的生卒时地,两次婚姻,和作品年表。
2019 台球和麻雀
小时候有一段时间总是放学后去打台球,有一次打完台球以后和一个大几岁的小伙伴去用气枪到田地里打麻雀,那一天回去的很晚,母亲很着急也很生气,每次想起这件事,泪流满面......
其实故事不一定是你看到的样子,因为时间和伙伴不是真的。那天应该是中午,有气枪的好像是台球厅老板,应该是在他家的院子里打麻雀,而且好像也没有开枪,母亲就找到我了。最近我每周会去看父母,父母年龄大了,想让我给买一个电动的搓澡按摩棒。昨天晚上,妈妈像个孩子一样告诉我快递收到了,也许我们老了以后,又可以回到童年了。
不论如何,情感一旦公开鲜明的表达出来,它马上就有一些虚假的东西,成了做戏与卖弄。真诚的人从不公开表达自己的情感,真正的情感总是蒙了一层面纱。只有虚伪的人才用情感作秀,为了给大家看他们有多敏感。_《时光中的时光》安德烈·塔可夫斯基
《私人摄像机:主观电影和散文影片》读后感(五):私人摄影机——我们把镜头对准世界,却试图找到自己
戈达尔说过一句话“所有伟大的电影都倾向于纪录片,所有伟大的纪实文学都倾向于小说”
我们普遍所说的,在作品中通过叙述和符号表达自我,都是处于一种现象学的视野之中。
笛卡尔有过一个声明「自我的透明」。后来被Paul Ricoeur质疑——自我怎么可能同时既是我们讨论的那个人,又是指定自己为第一人称而讨论第二人称的人?
运用到文学或任何艺术形式里,利用这一思维模式,可以推导出,第一人称表达的不可能性。
我只能表达出以「我」的第一人称视角所观察出的第二人称视角中的「我」。
电影的私人经验共鸣就是这么一回事。——永远以第二人称的视角去表达自己
帕索里尼有一段关于蒙太奇的现实意义解释十分精彩——「死亡是影响我们生活的即时蒙太奇,它让我们选择时空里真正有意义的时刻,再把它们放入此生唯一的序列里。我们将一个无限的、不稳定的、不确定的且难以解释的现在,转化为一个明确的,稳定的很容易描述的过去。」
所谓人人都是导演,不过就是如此。
文化理论家Stuart Hall 进一步说明了人物身份的问题。个人的身份在自我体内,总是有着整体性的缺乏,必须拥有外部“填充”进去,以一种我们假象自己被他人看见的方式。
这是人类需要总结过去的原因之一,我们通过总结构建出更加完整的外部身份,同时也更加完善自己的生命意义。
作者作为作品的经验主体。所书写与拍摄的自传不是一种类型或者方法,它是一种读解方式。
如同当年错误翻译的马克思理论「群众掌握理论」应译为「理论掌握了群众」一般,纪录片的本质也可采取同样的解读「是我们的观看方式创造了“纪录片”」。
我们决定演绎的事实和个体智力的发现过程,这两者相交从而完成一部纪录片。
纪录片对于社会:保存与揭示;对人:说服、分析、宣传、表达。
日记、记事本、自画像的区别
日记「记录下我亲眼目睹和亲身体验的事件与过程中的想法与情感」
记事本「记下想法、事件、存在,以备将来使用」
自画像「我展示我自己」
演员的表演,是作者和电影、电影和主体、观众和电影之间的主要协商场所。
一个人和我们的对话方式,也是他所说的内容之一。
思想可以随时放弃自己的主题,而来检视自己的作品,质疑已有的知识,或是发掘自己附带的潜力。
散文结构中隐藏了一个假定,即是个人与观看者的经验是共同的,两个主题之间可以依据这样的经验进行沟通。传播性广的散文,即是个人与人类族群的经验高度一致。
散文式的发生,往往只是对「你」,而不是对群体。
散文应用到电影层面,所说的散文电影,更多的是一种态度和尝试。
当散文式第一人称的「我」,在电影中出现的时候,「我」是如何通过电影和我说话,一个在对「我」说话的电影是如何看待我的?
电影中,经过精心设计后的画外音为何是比平时对话质量更高的声音,因为它的信息量更大,更规整。
这样的画外音成为了一种权力,它被假定了解所有的事实。并且画外音的说服能力,促成了一种共同经验。
于是诞生了一个必要的思考,是画面包含了声音,还是声音包含了画面。
资料片电影是一种元历史的形式,它点评历史背后的文化话语和叙事结构。资料影片的艺术家们批判性地审视影像背后的历史,以及它是如何通过话语嵌入制造、流通和消费历史的。作为一个纪录片导演,最终目的可以不是力求展现真实,而是对影像,以及产生这些影像的社会进行一个元批判。
在这样的元批判活动中,外部世界不是唯一的分析和批判对象,这种活动反思也延续到了电影意义产生的活动之中。电影意义的组成形式感,外部表现为一种抽象的电影感,我认为电影感,是一种召唤仪式,企图让观众沉浸后产生回应。如果观众回应了,那么他就已经被卷入电影的世界观内。这就是现实之外的电影感。
此般的回应是生命全部感知上的回应。
对于人类而言,视觉就是终极语言。因为我们观看物质世界的方式即是观看一张,或者一系列连续的图片。视觉在脑中将视网膜形象构建成影像,于是我们能做的,就只是观看影像,或者制造影像给包括我们在内的其他人看。
阿伦.雷乃认为「雕塑一旦进入博物馆就标志着其死亡。因为他们不在被当成活着的文化的一部分」
博物馆是一座抵抗「这个世界被数位化且虚拟驱动化并逐渐去物质化的物质堡垒。」
嗅觉电影的诞生,才能够使得战争电影成为可能。
无论如何来说,信息都不是经验。艺术家、创作者,就是世界经验的学者。不只是传递讯息,而是具像化社会经验,自我经验,历史经验。人类不是靠讯息发展的,而是处理讯息后,内化而成的经验。
我们有机会对于历史事件、他人生活产生经验上的感受,但这些感受是基于自我经验而来的,我们的共鸣不可能达到所谓的第五等级「经验级」。这一层次(经验)的获取是利用任何记忆工具都无法达到的。
将来或许有技术可以达成,我愿意把这种直接参与经验的技术叫做,时间工具。个体可以直接参与他人的经验过程,而不是用看的。如德勒滋所说,时间是一种晶体。
表演性是社会生活中的内在特点,是社会身份与人类行为共有的特点。即在特定环境下,某一特定的人以某种方式向他人施加影响。
自我无法表达自我的感受,只能对他人产生影响。但我们在述说「我冷」时,接收者由于不是「我」,在这样的语言表达中,「我」已经消失,剩下的只是那时刻的冷,已经冷的感觉在他者那儿的再现。
所以个体对每一个文本的接收,都是一个商议过程,这样的商议可能成功,可能失败。
人类学研究,经常会与记录片制作周期不期而遇。第一人称电影不仅仅代表了创作者的主观性,还有代表创作者在社会以及历史论述中的关系,这恰恰就处于人类学的范畴。
影像工作者的觉醒
拉塞尔说过一段话「作者是否意识到个人历史是与更大的社会结构和历史进程密不可分的。身份不再是一种先验的本质的自我,而是一种历史性的“主观表演”——自我呈现如同一场表演一样。在政治化的过程中,在基于部落、国家、性、种族、和阶层的不同文化语境下,一个个体演绎出不同的身份。」
attistini说过日记的效果「间歇性重复的镇定效果,我们在其中寻找一种生活上的避难所,寄存安全感在那已经发生的过去。日记也代表了一种母性的隐蔽、人造的乐园和回归的亲密感」
日记作者的三种类型;①理想的主体②他者性的体会③角色与装扮的面具
最后
我们把摄影机对准世界
「我不会告诉你我做了什么,但我会告诉你我是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