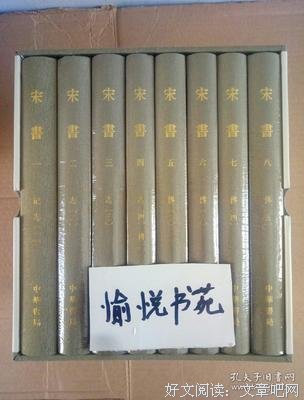
《宋书(修订本)(全8册)》是一本由(梁) 沈约 撰著作,中华书局出版的精装图书,本书定价:480.00元,页数:2798,特精心从网络上整理的一些读者的读后感,希望对大家能有帮助。
●专业!
●书很好,值得一读
●杨老师真棒,UPUP!
●修订的一般
●写得很好!
●写的太好了
●很棒的一本书值得推荐!
●好书一本,非常推荐。正史,丁老师杨老师认真修书的品质值得大家学习
●受益匪浅
《宋书(修订本)(全8册)》读后感(一):好
好。(1)评论书法。 元王恽《<颜鲁公书谱>序》:“ 东坡云:评书兼论其平生,苟非其人,虽工不贵。” 元黄溍《跋荆公帖》:“今观此帖,风神闲逸,韵度清美,临学之家,宜有取焉,评书者未可以彼而废此也。”(1)评论书法。 元王恽《<颜鲁公书谱>序》:“ 东坡云:评书兼论其平生,苟非其人,虽工不贵。” 元黄溍《跋荆公帖》:“今观此帖,风神闲逸,韵度清美,临学之家,宜有取焉,评书者未可以彼而废此也。”
《宋书(修订本)(全8册)》读后感(二):好书
这本书很棒,内容丰富,很值得一看!可以提供很多的资料,对我的专业很有用处。尤其是古代文学专业的同学,在做资料查阅时,这不失为一本很好的选择。这本书很棒,内容丰富,很值得一看!可以提供很多的资料,对我的专业很有用处。尤其是古代文学专业的同学,在做资料查阅时,这不失为一本很好的选择。这本书很棒,内容丰富,很值得一看!可以提供很多的资料,对我的专业很有用处。尤其是古代文学专业的同学,在做资料查阅时,这不失为一本很好的选择。这本书很棒,内容丰富,很值得一看!可以提供很多的资料,对我的专业很有用处。尤其是古代文学专业的同学,在做资料查阅时,这不失为一本很好的选择。
《宋书(修订本)(全8册)》读后感(三):孝武帝刘骏黑料汇编
《武帝纪下》:孝武大明中,壞上所居陰室,於其處起玉燭殿,與群臣觀之。床頭有土鄣,壁上挂葛燈籠、麻繩拂。侍中袁顗盛稱上儉素之德。孝武不答,獨曰:“田舍公得此,以為過矣。”
《孝武帝纪》:克广陵城,斩诞。悉诛城内男丁,以女口为军赏。
《天文志》:及屠城,城内男女道俗,枭斩靡遗。将军宗越偏用虐刑,先刳肠决眼,或笞面鞭腹,苦酒灌创,然后方加以刀锯。
《刘德愿传》:上宠姬殷贵妃薨,葬毕,数与群臣至殷墓。谓德愿曰:“卿哭贵妃若悲,当加厚赏。”德愿应声便号恸,抚膺擗踊,涕泗交流。上甚悦,以为豫州刺史。
《宗越传》:城陷,世祖使悉杀城内男丁,越受旨行诛,躬临其事,莫不先加捶挞,或有鞭其面者,欣欣然若有所得,所杀凡数千人。
《沈怀文传》:竟陵王诞据广陵反,及城陷,士庶皆裸身鞭面,然后加刑,聚所杀人首于石头南岸,谓之髑髅山。怀文陈其不可,上不纳。
《羊玄保传》:子戎,有才气,而轻薄少行检,玄保尝云:“此兒必亡我家。”官至通直郎。 与王僧达谤议时政,赐死。死后世祖引见玄保,玄保谢曰:“臣无日磾之明,以此上负。”上美其言。
《江智渊传》:时上方盛淫宴,虐侮群臣,自江夏王义恭以下,咸加秽辱。
《王玄谟传》:孝武狎侮群臣,随其状貌,各有比类,多须者谓之羊。颜师伯缺齿,号之曰齴。刘秀之俭吝,呼为老悭。黄门侍郎宗灵秀体肥,拜起不便,每至集会,多所赐与,欲其瞻谢倾踣,以为欢笑。又刻木作灵秀父光禄勋叔献像,送其家听事。柳元景、垣护之并北人,而玄谟独受“老伧”之目。凡所称谓,四方书疏亦如之。尝为玄谟作四时诗曰:“堇荼供春膳,粟浆充夏飧。瓟酱调秋菜,白醝解冬寒。”又宠一昆仑奴子,名曰主。常在左右,令以杖击群臣,自柳元景以下,皆罹其毒。
《江夏王刘义恭传》:时世祖严暴,义恭虑不见容,乃卑辞曲意,尽礼祗奉,且便辩善附会,俯仰承接,皆有容仪。每有符瑞,辄献上赋颂,陈咏美德。大明元年,有三脊茅生石头西岸,累表劝封禅,上大悦。
《柳元景传》:世祖严暴异常,元景虽荷宠遇,恆虑及祸。太宰江夏王义恭及诸大臣,莫不重足屏气,未尝敢私往来。世祖崩,义恭、元景等并相谓曰:“今日始免横死。”
《宋书(修订本)(全8册)》读后感(四):修訂前言小識
1、宋書
《宋書》一百卷,包括本紀十卷、志三十卷、列傳六十卷,南朝梁沈約撰。
2、劉宋
晉恭帝元熙二年(420),劉裕受禪建宋,改元永初,仍定都建康。
劉宋凡八帝,歷時六十年。至宋順帝昇明三年(479)年,蕭齊代宋,劉宋滅亡。
劉宋之初,西有漢中,東與卑微夾黃河相對,後期疆域退縮至淮河、秦嶺一線,與北魏稱南北對峙局面。
3、劉宋國史
起於宋文帝元嘉十六年(439),著作郎何承天,後來山謙之、裴松之(未及而卒)、蘇寶生等陸續受诏參與編輯。
宋孝武帝大明六年(462),徐爰領著作郎,「因何、蘇所述,勒為一史,起自義熙之初,訖于大明之末」,其中臧質、魯爽、王僧達等傳,為孝武帝劉駿親撰。
《隋志》二:《宋書》六十五卷,宋中散大夫徐爰撰。
泰始三年(467),徐爰爲宋明帝劉彧斥退,劉宋國史修撰隨即停止。
南齊永明五年(487),齊武帝蕭賾命沈約修撰《宋書》。沈約以何承天、徐爰等人舊作為基礎,用將近一年的時間,完成紀傳七十卷。至永明末應已全部完成。但根據避諱,可能在蕭鸞甚至梁武帝即位後才最終定稿。
4、其它宋書
孫嚴《宋書》六十五卷;王智深《宋紀》三十卷;
裴子野《宋略》二十卷;王琰《宋春秋》二十卷;
鮑衡卿《宋春秋》二十卷。皆亡佚。
5、沈約
(441-513),字休文,吳興武康人,出身世族之家。其祖沈林子,爲劉宋開國功臣,仕至輔國將軍,留心文義,頗有著述。其父沈璞,曾官淮南太守,元嘉三十年(453),以奉迎武陵王劉駿不及時而被誅。其時沈約十三歲,潛逃後逢赦免,篤志好學,晝夜不倦。
宋時官至尚書度支郎,入齊後歷官著作郎、中書郎、尚書左丞、五兵尚書、國子祭酒。梁朝建立,封建昌縣侯,歷官尚書左僕射、尚書令等職。
梁天監十二年(513)卒于官,年七十三,謚曰「隱」。
爲南朝著名詩人、文壇領袖。一生著作頗豐,除《宋書》一百卷外,尚有《晉書》一百十卷、《齊紀》二十卷、《高祖紀》十四卷、《邇言》十卷、《謚例》十卷、《宋文章志》三十卷、文集一百卷。今僅存《宋書》,明人輯其文集九卷。
6、評價
涉獵廣泛、史料豐富,後世讚譽爲多,但評價也有爭議。
① 篇幅問題
趙翼《廿二史札記》:「凡詔誥、符檄、章表,悉載全文,一字不遺,故不覺卷帙之多也。」「《南史》于宋書大概刪十之三四,以《宋書》所載章表符檄,本多蕪詞也。」
但今天看來,保留了大量原始文獻,如著名的《僑人歸土斷流疏》《禁淫祠詔》《興學校詔》等。
② 史志問題
劉知幾以八志「上括魏朝」爲病。(《史通·斷限》)
晁《志》沿其說,「兼載魏晉,失於限斷」
沈約:「何書自黃初之始,徐志肇義熙之原。今以魏接漢,式遵何氏。
陳《錄》:揆以班馬史體,未足爲疵。」
葉適《習學記言序目》:「至沈約比次漢魏以來,最爲詳悉,唐人取之以補《晉記》,然後歷代故實可得而推。」
顧炎武《日知錄》:「陳壽《三國志》、習鑿齒《漢晉春秋》無志,故沈約《宋志》諸志并前代所闕者補之。」
《四庫提要》:「推原溯本,事有前軌」「約詳其沿革之由,爲大失」。
余嘉錫《辨證》:「若沈約《宋史》,上括魏朝,蓋因《三國》無志,用此補亡,斯誠史氏之良規。」
唐長孺:「不但補闕,亦且溯源。」
————《宋書》八志,篇幅佔全書近半,上溯魏晉,補前史未備。
③ 隱諱問題
承襲徐爰舊史,於晉宋易代之際,多爲劉宋避諱。
e.g.晉恭帝本爲劉裕所逼而遜位,卻稱「禪讓」,並連番推辭方即位,「儼然唐虞揖讓光景,絕不見有逼奪之跡」(《廿二史札記》)
又沈約奉齊武帝蕭賾之命修史,多遵齊武帝旨意。
e.g.袁粲。
涉及宋齊革易之處,多爲蕭齊迴護,對齊高帝蕭道成讚揚備至。
e.g.「其於諸臣之效忠於宋,謀討蕭道成者,概曰反,曰有罪。」「其於道成而爲之助理者,轉謂之起義。」《廿二史札記》
④ 門第
編次多依門第,傳中往往綴列親族,對門閥士族成員普遍多溢美之詞,對少數聲明不佳者也不免曲飾。
7、散佚與編次
宋代,嘉祐末詔館閣校讎,尚多殘脫舛誤,或雜以李延壽《南史》。
e.g.卷四《少帝紀》、卷四六《趙倫之傳》、卷七六《朱脩之宗慤王玄謨傳》,都是後人用《南史》補足的。而卷六二《張敷傳》卷五九《張暢傳》本不闕,卻被補入,導致二者各有兩傳。
書中的篇目,按《志序》所云,以《律曆志》為首。但歷代傳本卻都拆分《律曆志》爲《律志》《曆志》,將分別題作「律上」「曆上」「曆下」。
四庫:出於後人編目,強爲分割,非約原本之舊次。
錢大昕:自孟堅合律、曆爲一志,後之作史者皆因之。休文序例不言更分爲二;則亦固、彪之舊矣。此志三卷,當題『律暦上』,次篇爲『中』,末篇爲『下』。今以首篇爲《律志》,下二篇爲《曆》上、《曆》下,蓋後人妄改,非休文之旨也。
故點校本改之。
8、版本
① 宋代
兩種版本。
《宋書》校刻始於北宋嘉祐年間、治平年間。
嘉祐六年,「詔三館、秘閣校《宋》《齊》《梁》《陳》《後魏》《後周》《北齊》七史,書有不完者訪求之。」(《續通鑒長編》)
三朝本《南齊書》載治平二年勑節文:《宋書》《齊書》《梁書》《陳書》《後魏書》《北齊書》《後周書》,見今國子監並未有印本。宜令三館秘閣見編校書籍官員精加校勘,同與管勾使臣選擇楷書如法書寫板樣,依《唐書》例,逐旋封送杭州開版。
《郡齋讀書志》:治平中,鞏校訂《南齊》《梁》《陳》三書上之,劉恕等上《後魏書》,王安國上《周書》。政和中,始皆畢,頒之學官,民間傳者尚少。…中原淪陷,此書幾亡。
南宋
「紹興十四年,井憲孟爲四川漕,始檄諸學官,求當日所頒本。時四川五十餘州,皆不被兵,書頗有在者,然往往亡闕不全。收合補綴,獨少《後魏書》十許卷。最後得宇文季蒙家本,偶有所少者。於是七史遂全,因命眉山刊行焉」
——所謂宋蜀大字本「眉山七史」。
這兩種都沒有流傳下來。
.s.我們所見《宋書》三朝本,張元濟以爲其中「版心畫分五格者,可定爲蜀中紹興原刊」,但據王國維、趙萬里、尾崎康等人考訂,現存三朝本實爲南宋前期江浙刊本。南宋前期江浙刊本一直沿用到明代中期,李靖多次補休。
e.g.現存數種三朝本《宋書》,分藏於國圖、台北國圖等地,《中華再造善本》影印前者。
明清
明萬曆二十二年(1594)南京國子監刻本、萬曆二十六年北京國子監刻本、崇禎七年毛氏汲古閣本、清乾隆四年(1739)武英殿本、同治十一年(1872)金陵書局本。
明清刊本,迭有修訂,但總體面貌較為一致。
民國
張元濟百衲本搜集數種三朝本《宋書》。
北平圖書館藏六十七卷,據嘉業堂殘本補入二十三卷,另志第四、列傳四十四、五、六,第四十八、九,第五十一、二,第五十九,第溜溜食,以常熟瞿氏鐵琴銅劍樓暨涵芬樓藏元明遞修本合配。
今修訂本以此爲底本。
《宋书(修订本)(全8册)》读后感(五):【转】丁福林谈《宋书》的编纂、点校与修订
丁福林(蒋立冬绘)点校本“二十四史”及《清史稿》修订工程自2005年启动以来,已陆续出版了修订本《史记》《旧五代史》《新五代史》《辽史》《魏书》《南齐书》。作为南朝正史的第一种《宋书》,其修订版也终于在今年夏天与读者见面。 修订本《宋书》主持人丁福林先生1979年考入南京师范学院中文系,师从著名的经史大家段熙仲先生。丁先生精于六朝文史校雠,治学有乾嘉遗韵。2018年7月28日,南京大学文学院童岭老师对丁福林先生进行了访谈。《宋书》修订本采访︱童 岭
第一次来您府上拜访,还是十五年前,记得那时您的《宋书校议》(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刚刚出版不久。时隔多年,围绕点校修订本《宋书》采访您,是我的荣幸。您、中华书局总经理徐俊先生和我都出生于镇江,三位京口人为一千六百多年前“乡皇帝”刘裕开辟的南朝刘宋历史《宋书》策划了一次访谈,想到这一点,我的心情非常“澎湃”。
丁福林:能和徐俊先生以及您三个京口同乡一起合作,对我来说本身就是值得高兴的事,更何况是三人共同为记载“乡皇帝”开辟的刘宋王朝历史的《宋书》修订而合作呢!我可以算得上是一个研究乡土文史的人,除《宋书》而外,我研究的两个六朝著名诗人鲍照和江淹也是京口人。可能是镇江历代人才辈出的缘故,当地无法对历史文化名人一一加以关注,但对镇江的著名科学家沈括、茅以升以及曾经在镇江编撰过《文选》的南朝梁昭明太子萧统还是十分重视的,如在梦溪园巷就修建了沈括故居。不过随着时间的推移,我想刘裕和鲍照、江淹等对镇江作出过重大贡献的历史文化名人还是会引起镇江人重视的。
宋武帝刘裕初宁陵石刻,魏宜辉摄中华书局自从2013年推出南京师范大学主持修订的《史记》以来,《旧五代史》《新五代史》《辽史》《魏书》《南齐书》修订本都陆续面世,您主持修订的《宋书》是第七种,请问您如何评价《宋书》?
丁福林:沈约《宋书》记述南朝刘宋一代史事,涉猎广博,史料丰富,体例完备,后世对此书的总体评价很高。但是,不少学者也对其中的不足之处提出了批评。对《宋书》的批评主要集中在两个方面,其一是《宋书》的繁冗,如清赵翼《廿二史札记》卷十就说:“盖《宋书》本过于繁冗,凡诏诰、符檄、章表,悉载全文,一字不遗,故不觉卷帙之多也。”“《南史》于《宋书》大概删十之三四,以《宋书》所载章表符檄,本多芜词也。”但今天看起来,这也使大量原始文献藉此得以存留,如《武帝纪》三卷载《侨人归土断疏》《禁淫祠疏》《兴学校疏》等诏令、策文、奏疏、符檄三十馀篇,反映出晋末宋初的历史状况和刘宋初创基业的过程,是弥足珍贵的历史资料。又如《乐志》记述汉、晋以来宗庙雅乐舞曲的源流以及金、石、土、革等八音的各种乐器的形制,“自郊庙以下,凡诸乐章,非淫哇之辞,并皆详载”(《宋书》卷一一《志序》),保存了许多汉、魏以来的大量乐府歌辞。值得一提的是,沈约为《宋书》的志传撰写了多篇序文传论,或说明史例,或表达己见。如列于八志之首的志序,概述志的源流和《宋书》志的缘起,阐明汉、晋志书的承续关系。又如《谢灵运传》传末史论,叙述自诗、骚之后文学的发展和演变过程,以及作者关于诗歌声律的主张,乃是南北朝文学史研究的重要资料。
其二是以为《宋书》多有曲笔,为执政者回护掩饰。如晋恭帝本为刘裕所废,而卷二《武帝纪》却称禅让,“俨然唐、虞揖让光景,絶不见有逼夺之迹”;刘裕杀晋恭帝,手段阴狠凶毒,但卷三《武帝纪》却记载说,“零陵王薨,车驾三朝率百僚举哀于朝堂,一依魏明帝服山阳公故事”,“太尉持节监护,葬以晋礼”,也不见谋害痕迹;宋孝武、宋明帝诸鄙渎事,沈约也多有省除。同时,《宋书》也多为萧齐回护,对齐高帝萧道成颂扬备至,“其于诸臣之效忠于宋,谋讨萧道成者,概曰反,曰有罪”,“其党于道成而为之助力者,转谓之起义”(赵翼《廿二史札记》卷九)。这些都是《宋书》的不足之处。但是,沈约撰《宋书》是在齐代,事涉本朝,他不能不有所顾忌,因此以上这些也是可以理解的。而且我们如果综合《宋书》的纪传看,沈约对本纪采用为尊者讳,为本朝讳的笔法,而在列传中则并非如此,诚如赵翼《廿二史札记》卷九所说这乃是“讳之于本纪,而散见于列传”的写法。如《褚淡之传》绘声绘色地记载了刘裕主谋杀害晋恭帝的过程;在《孝武帝纪》末也评论说:“役已以利天下,尧、舜之心也;利己以及万物,中主之志也;尽民命以自养,桀、纣之行也。观大眀之世,其将尽民命乎!”比宋孝武帝刘骏为桀、纣般的暴君,又在其他一些传文中记载了刘骏的残暴和丑行;在《良吏传》末分析当时之所以少有良吏乃是因为帝王“弥笃浮侈,恩不䘏下,以至横流”,以为“岂徒吏不及古,民伪于昔,盖由为上所扰,致治莫从”,词锋锐利,言辞激烈。这些都是值得肯定的。总之,尽管《宋书》有这样那样的缺点,但它仍是一部有重大价值的史书,是我们研究刘宋一代历史的主要依据。
《宋书》的作者沈约,您怎样看待他的文学、学术?二十四史的作者里面,能同时具有史学与文学地位的似乎不多吧?
丁福林:在二十四史的作者中,除了《史记》的司马迁,《汉书》的班固而外,沈约可以说是文学成就最高的。沈约字休文,吴兴武康(今浙江德清西)人,《梁书》卷一三、《南史》卷五七有传。沈约历仕宋、齐、梁三朝,梁时封建昌县侯,历官尚书令、尚书左仆射等职。梁武帝天监十二年(513)卒于官,年七十三,谥曰隐。他自幼博通羣书,南齐时,受齐武帝长子文惠太子萧长懋亲遇,出入东宫,参与四部图书的校定。齐武帝次子竟陵王萧子良礼贤好士,沈约为府中嘉宾,与后来的梁武帝萧衍同在“竟陵八友”之列。沈约一生著述甚丰,除《宋书》一百卷外,尚有《晋书》一百十卷、《齐纪》二十卷、《高祖纪》十四卷、《迩言》十卷、《谥例》十卷、《宋文章志》三十卷,文集一百卷。今仅存《宋书》,余皆亡佚,明人辑其文集九卷。
沈约不仅是杰出的史学家,同时也是南北朝时期的著名文学家,他诗文兼备。《梁书》本传说他:“好坟籍,聚书至二万卷,京师莫比。”“该悉旧章,博物洽闻,当世取则。谢玄晖善为诗,任彦升工于文章,约兼而有之。然不能过也。”钟嵘《诗品》于“梁左光禄沈约”条说:“观休文众制,五言最优。详其文体,察其馀论,固知宪章鲍明远也。所以不闲于经纶,而长于清怨。永明相王爱文,王元长等皆宗附之。约于时谢朓未遒,江淹才尽,范云名级故微,故约称独步。虽文不至其工丽,亦一时之选也。”其诗多清怨之作,音调和谐,抒情也较自然。但由于他过于讲究声律与对仗,所以某些诗作就失之刻板,兴寄之作也较少。但总体上说,他的作品眼界宽阔,气质厚重,思想格调虽不算高,却不失为当时大家。
沈约在我国文学史上最大的贡献是他与谢朓、王融、范云等人创立了“永明体”的新诗体,魏晋时,文人已经逐渐讲究声律,到齐永明年间,由于佛教盛行,佛经梵音对四声的创立产生了较大的影响。周顒著《四声切韵》,沈约著《四声谱》,提出平上去入四声。《南史》卷四八《陆慧晓传附陆厥传》:“时盛为文章,吴兴沈约、陈郡谢脁、琅邪王融,以气类相推毂。汝南周颙、善识声韵,约等文皆用宫商,以平上去入为四声,以此制韵,有平头、上尾、蜂腰、鹤膝。五字之中,音韵悉异;两句之内,角徵不同。不可増减,世呼为永明体。”唐封演《闻见录》说“周颙好为韵语,因此切字皆有平上去入之异。永明中,沈约文辞精拔,盛解音律,遂撰《四声谱》,时王融、刘绘、范云之徒,慕而扇之,由是远近文学,转相祖述,而声韵之道大行。” 四声根据汉字发声的高低、长短而定,音乐中按宫商角徵羽的组合变化,可以演奏出各种优美动听的乐曲;而诗歌根据字词声调的组合变化,按一定的规则排列,则可以达到铿锵、和谐,富有音乐美的效果。正如《宋书·谢灵运传论》中所说的“一简之内,音韵尽殊,两句之中,轻重悉异”。这种新体诗,为唐代格律诗的完成奠定了基础。甚至可以说,如果没有四声的发明和永明体的出现,唐代的诗歌恐怕也就不会有那样的辉煌。
丁福林校注南朝别集两种《宋书》的笔法,一直是后世史学家与文学家津津乐道的话题。有的史家认为沈约过于重视文人,谢灵运、颜延之竟可以独立为一卷。但同样为著名文人的鲍照,却附在《刘义庆传》中。众所周知,您的《鲍照集校注》(中华书局,2012年)是继钱仲联《鲍参军集注》(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年)后的最善注本,您觉得《宋书》处理这些浮沉于时代大变革中的文人,与六朝其他史书相比,有没有什么特别之处?
丁福林:沈约作为创作强调声韵和对偶的文学家,又处于四六文体盛行的时代,他撰写《宋书》重视文采也就是很自然之事。如在卷八八《薛安都传》记载薛安都阵斩鲁爽的一节:“安都望见爽,便跃马大呼,直往刺之,应手而倒,左右范双斩爽首。爽累世枭猛,生习战陈,咸云万人敌,安都单骑直入,斩之而反,时人皆云关羽之斩颜良,不是过也。”笔墨酣畅淋漓,写得栩栩如生,使人有亲历其境之感。《宋书》较之其他史书的人物传记,文人的比重确实较大。个中原因,我觉得与史书作者本身爱好文学是分不开的,也可以说是惺惺相惜吧。但是,作者并不是无原则的为文人立传。如谢灵运和颜延之,二人乃是刘宋时的文坛领袖,钟嵘《诗品》评论说:“宋临川太守谢灵运诗:其源出于陈思,杂有景阳之体,故尚巧似,而逸荡过之,颇以繁芜为累。嵘谓若人兴多才高,寓目辄书,内无乏思,外无遗物,其繁富,宜哉。然名章迥句,处处间起,丽典新声,络绎奔会,譬犹青松之拔灌朩,白玉之映尘沙,未足贬其高洁也。”“宋光禄大夫颜延之诗:其源出于陆机,尚巧似,体裁绮密,情喻渊深,动无虚散,一句一字,皆致意焉。又喜用古事,弥见拘束,虽乖秀逸,是经纶文雅才。雅才减若人,则蹈于困踬矣。汤惠休曰:‘谢诗如芙蓉出水,颜如错彩镂金,颜终身病之。’”而且颜、谢二人皆出身高门世族,又身居高位,因此他们有较多的事迹得以保存到后世。二人在《宋书》中立有专传,可以说顺理成章。
然而鲍照则出身贫寒,一生流离,仕宦不显,事迹多所湮没。所作诗文于身后也多所散失,直到南齐武帝太子萧长懋令人收集鲍照遗文并编次成集,其诗文才得以流传。所以,鲍照并不适宜在《宋书》中立有专传。从这一角度来说,明张溥《汉魏六朝百三家集·鲍照集题辞》所说的“鲍明远才秀人微,史不立传”,并不准确。我们设想如果换成别人来撰写《宋书》,鲍照恐怕连能不能列入人物的附传都很难说。我认为,沈约将鲍照事迹附载在《刘义庆传》中,乃是非常确当的做法。宋临川王刘义庆爱好文学,“招聚文学之士,近远必至”(《宋书》卷五十一《刘义庆传》),鲍照始仕即进入义庆幕府,为义庆所赏识。义庆死后,鲍照即离开临川王幕,从此漂泊流离,直至为乱兵所杀。可以说在义庆幕期间,鲍照度过了他人生中最为美好的时光。而且,沈约将鲍照的名作《河清颂序》全文录入《鲍照附传》中,不能不说是对鲍照文学成就的极大肯定。《宋书》处理如谢灵运、鲍照这些浮沉于时代大变革中的文人,能够根据他们各自的处境与特点,作出不同的安排,与六朝其他史书相比,处理得更为灵活,更为妥善合理,也更能反映出他们各自在我国历史上的地位。
丁福林2009年在北京香山宾馆参加点校本“二十四史”及《清史稿》修订工程第三次修纂工作会议照义熙北伐的重将中间,沈林子和沈田子看似没有独立传记,但沈约把他们大篇幅地写进《自序》里面,这是模仿《史记》《汉书》吧?
丁福林:沈约在《宋书》中将他的伯祖父沈田子和祖父沈林之的事迹大篇幅地写进了《自序》,这明显是借鉴了《史记》和《汉书》的体例。但是,《宋书》的这种写法可以说又不是完全仿照《史记》《汉书》的写法。这是因为司马迁的父亲司马谈和班固的父亲班彪可以载入史书的事迹较少,并不适合单独立专传以记载他们的事迹,所以《史记》和《汉书》的写法是比较可以理解的。而沈田之和沈林之则不同,此二人为刘宋王朝的开国名将,在平定桓玄叛乱和北伐南燕,平定岭南以及讨灭后秦的诸多战役中立有重大战功,为刘宋王朝的创建立下卓著功勋。按照《宋书》立传的惯例,二人完全可以和其他开国功臣一样列有专传,但沈约却将他们的事迹纳入《自序》中。这种写法,不但不会削弱二人在刘宋立国时作出的贡献,而是更突显出了吴兴沈氏这一江南著姓士族自肇始至沈约一脉相承的联系,沈氏家族的一些重要资料也藉以得到保存。这也同样表现出了沈约作史的灵活性和合理性,是值得肯定的。
在一百卷《宋书》中,《志》占三十卷,历代对这些《志》文评价不一,比如赵翼《十七史商榷》就非议《五行志》和《符瑞志》枝蔓。请问您怎么看待?
丁福林:《宋书》一百卷,《志》占了三十卷,篇幅上大致占了五分之二。对此,后世多有微辞,除赵翼外,唐刘知几《史通》卷四《断限》即以《宋书》“上括魏朝”为病,宋晁公武《郡斋读书志》卷五也说此书“兼载魏晋,失于限断”。但后代特别是明清以来的学者对此书八志则普遍持肯定的评价。宋陈振孙《直斋书録解题》卷四说:“揆以班、马史体,未足为疵。”顾炎武《日知录》卷二六说:“陈寿《三国志》、习凿齿《汉晋春秋》无志,故沈约《宋书》诸志并前代所阙者补。”四库馆臣则以为“推原溯本,事有前规”,“约详其沿革之由,未为大失”(《四库全书总目》卷四五)。今人亦多肯定意见,余嘉锡《四库提要辨证》卷三说:“若沈约《宋史》,上括魏朝,盖因《三国》无志,用此补亡,斯诚史氏之良规。”唐长孺《魏晋南北朝史籍举要》则高度肯定《宋书》八志“不但补阙,亦且溯源”,“其志大体系何承天之旧,诸志之中,地志远胜晋志,固有定评,《礼》《乐》特为详该”。沈约在编撰《宋书》时,认为自司马彪《续汉书》有志以外,《三国志》《晋书》都没有志,所以《宋书》纪、传,虽以刘宋为断限,而志则上起三国,下迄宋末,上继《续汉志》以弥补陈寿以来史书的缺略,对前朝典章制度多所综述。到唐初修撰《晋书》,其中志的部分大体上即抄自《宋书》,就是这一原因。客观地说,《宋书》八志上包魏、晋,弥补了《三国志》无志的不足,有些相当珍贵的历史资料借此得以保存。
《律历志》收录曹魏杨伟《景初历》、宋何承天《元嘉历》、祖冲之《大明历》的全文,反映了当时数学与历法应用的最高成就。《州郡志》详记南方地区自三国以来的地理沿革,以及东晋以来的侨置州郡分布情况和各州郡户口数,是一篇反映人口变动和区域建置变动的重要文献,为研究当时政治经济和社会生活的重要史料。《州郡志》序说:“地理参差,其详难举,实由名号骤易,境土屡分,或一郡一县,割成四五,四五之中,亟有离合,千回百改,巧历不算,寻校推求,未易精悉。”当时社会的动荡于此可见一斑。另外,《宋书》创立《符瑞志》,从远古到刘宋,历举许多神怪荒诞之事,宣扬“有受命之符,天人之应”,具有相当多的迷信成份,值得批评。不过其中也记载了一些自然现象,如果用科学眼光来看待,也还是具有一定的价值。
您怎样评价《宋书》原点校者王仲荦先生的业绩?以及他的《宋书校勘记长编》?
王仲荦《宋书校勘记长编》《宋书校勘记》丁福林:王仲荦先生点校本《宋书》,校勘精审,考辨广证博引,在吸收前人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又多所创见,实他人难以企及,可说是迄今最为完善之精本。《宋书》的点校自1962年始,至1974年正式出版,历时凡十二年。2009年3月,中华书局将王先生遗稿《宋书校勘记长编》列入“二十四校订研究丛刊”影印发行,这部手稿,是先生十二年《宋书》点校心血的结晶,也是先生从事《宋书》点校工作的原始记录,展现了他严谨学风和过人的学识素养。《长编》以百衲本为工作本,依原文顺序逐卷逐条详细记录了他在版本对校、他校及理校过程中所发现的有关问题,并参考前人相关研究成果,提出校改意见。根据统计,《长编》出示条目共达九千一百余条之多,用力之勤,前所未有。乃是《宋书》整理史上集大成之作。当然,智者千虑,百密一疏,加上当时检索条件的限制和人手的缺乏,点校本中极个别地方出现一些问题,是可以理解的。但这并不会掩盖点校本《宋书》和点校长编的重大成功。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如果没有王仲荦先生开创性的工作,就无法进行今天对《宋书》点校的修订。
从篇幅上看,中华书局点校本南朝四史,《宋书》八册,余下《南齐书》《梁书》和《陈书》加起来方才八册,分量可谓“以一敌三”。文献浩瀚,修订过程一定是充满艰辛吧。可否请教您一个具体的例子?我留意修订版第一卷《武帝纪上》“彭城县绥舆里人”条,旧版王仲荦先生校勘记引文顺序是:《太平御览》《宋书·符瑞志》《南史》;您修订版校勘记引文顺序是:《宋书·符瑞志》《南史》《太平御览》。这样细微的差别,也可以看出您的精细用心。类似的例子,可以和我们多谈一点吗?
丁福林:由于王先生点校本是采用多个版本互校,不主一本,择善而从的校勘方法。所以校勘记就要先列出《太平御览》引徐爰《宋书》“彭城绥舆里人”的异文。而我们这次修订是采用以百衲本作底本,用多个版本互校的方法,所以一些不十分重要的异文就不必引用。根据这次修订总则体例,所以我们采用了现在这样的引文顺序。这样的例子又如同卷中的“立留台官”条,王先生点校本因为是不主一本,择善而从,故校勘记中列有“三朝本、毛本作‘立留台官’。北监本、殿本、局本作‘立留台总百官’。《通鉴》作‘立留台百官’”数句,而修订本所用作底本的百衲本即作“立留台官”,所以修订本删去了“三朝本、毛本作‘立留台官’”这一句。另外,王先生点校本此条在列出各本异文以后,就以理推断说:“据下文众欲推刘裕领扬州,裕固辞,则此时刘裕必无总百官之事。以此知作‘总百官’者,误。”这一推断的结论虽然很正确,但这必竟是推断。我们修订时认为想要坐实此事,最好能找出当时总百官的究竟是谁,经过查核,我们发现在《通鉴》卷一一三记载有“刘裕称受帝密诏,以武陵王遵称制,总百官行事,加侍中、大将军”之事,因而得出当时“总百官者,乃武陵王遵”的结论,并对原校进行了补充,肯定了王先生原校的正确性。
如上面这样为王先生原校作补充,以使点校本《宋书》在修订后更为完善,也是我们这次修订的一个难点。又如王先生点校本卷三《武帝纪下》“镇西将军李歆进号征西将军”一句,校勘记:“《南史》《通鉴》作‘征西大将军’,此疑脱‘大’字。”王先生根据《南史》和《通鉴》的记载而怀疑脱一“大”字,不免有所缺撼。为此,我们又查找了其他证据,并在《宋书》卷九八《氐胡传》中找到了内证:“高祖践阼,以歆为使持节、都督高昌敦煌晋昌酒泉西海玉门堪泉七郡诸军事、护羌校尉、征西大将军、酒泉公。”说明了《南史》和《通鉴》记载的正确。于是我们修订时就补了“大”字,直接以“镇西将军李歆进号征西大将军”出校。可以说弥补了王先生只是怀疑的缺撼。
修订版《宋书》似乎并没有逐条纳入您早年出版的《宋书校议》意见,比如《武帝纪上》:“至是桓修还京,高祖托以金创疾动,不堪步从。”《宋书校议》引王鸣盛《十七史商榷》卷五四认为“京”下当补一“口”字,但修订版这里似乎没有补上?
丁福林:《武帝纪上》中的“还京”,《南史》作“还京口”,《建康实录》卷一一:“三年二月丁酉,帝还丹徒,潜谋匡复。”当时的丹徒也称京口,或称京城。建康则称京师、京邑、京辇、京都。但是京口又可以简作京。《三国志·吴志·张纮传》:“纮建计宜出都秣陵,权从之。”注引《江表传》:“刘备至京,谓孙权曰:‘吴去此数百里,……将军无意屯京乎’。”这里的“京”明显是指京口而言,类似的例子还可以找到一些。既然京口可以简作京,那么“还京”后就没有必要补一“口”字。我在做《宋书校议》时忽略了京口可以简作京这一点,因而采用了王鸣盛的说法,这是欠慎重的。所以这次修订,并没有采用王说。所以如何利用自己《宋书校议》中的内容,也是我非常重视的一个方面。《宋书》卷五五《臧焘传》有“迁通直郎,髙祖镇军、车骑、中军、太尉咨议参军”一句,我在《宋书校议》中据《宋书·武帝纪上》《通鉴》所载,怀疑“镇军车骑中军”为衍文。这虽有一定的道理,但因为很难找到足够的理由去支撑,所以最后还是决定舍去而未予出校勘记。
丁福林:《宋书校议》《南齐书校议》我是学魏晋六朝文学的,在有关论文写作时,会较多的涉及到《宋书》《南史》《通鉴》《建康实录》等史书的内容。特别是在考证一些文人的生平事迹以及他们的诗文创作年代等相关内容时,往往会发现各史书有关记载有些微小的差异,这些微小的差异往往又会造成结论的不同。而我又有追根刨底的习惯,喜欢穷究各史书内容差异的原因,谁对谁错,总想搞清楚,以便找到正确答案。偶然有所领悟,就逐条记下来,积累多了以后,也就有发表出来,希望引起中华书局再版此书时能有所重视的冲动。我第一篇有关《宋书》校勘的论文是三十年前发表在《徐州师院学报》1985年第一期上的《点校本〈宋书〉〈南史〉献疑》。至今还清楚地记得后来一次投稿给东北某著名高校的《古籍整理研究学刊》,结果稿子不但未被采用,反而受了一通奚落。编辑回信大致说,稿子的内容很好,但应该都是古人已经说过的,并含蓄地说以你们这种不入流高校的教师是写不出这种高质量的文章的。看了编辑的来信,我感到很高兴,因为我知道这位编辑只是臆想出来我窃取了古人的研究成果,但对文章的质量却是肯定的。
这一事件也促成了我想要完成《宋书》等南朝史书校勘的想法。《宋书校议》的撰写,我还要感谢中华书局的张忱石先生。1986年中华书局推出了张忱石先生的《建康实录》点校本,我对其中与《宋书》有关一卷草成一稿寄给了张先生,不久收到了张先生的回信,说他利用休假时间对我的草稿逐条进行了复核,对稿中内容完全同意,并表示如果再版将采用我的意见,对原点校本进行修改和补充。同时,他又将他新出的《北朝四史人名索引》上下二册寄了给我。张先生的鼓励和赠书,表现出一个著名学者虚怀若谷的胸襟,给我撰写《宋书校议》以极大的信心。但是,我早年《宋书校议》的撰写,由于条件有限,并没有运用多个版本的对校,而且受到知识面等各个方面的局限,所以《宋书校议》中还存在有较多的不足和错误之处。利用这次《宋书》的修订,能够改正《宋书校议》中的一些错误,实在是一件幸事。
旧版《宋书·出版说明》特别把谢弘微拎出来骂了一通,说他“忙于经营谢氏产业”。但我自己读了《谢弘微传》,他的叔父谢混因附于刘毅被诛,叔母被迫改嫁前,将家事全部委托谢弘微。九年后,叔母听还谢氏,回家看见当年门徒业使,不异平日,感慨谢混“平生重此子,可谓知人”。乡人莫不叹息,感弘微之义。说实话,读到这里我也是废书而叹。您早年就著有《东晋南朝的谢氏文学集团》(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98年),记得卞孝萱老先生生前对此书非常推崇。您觉得对于六朝贵族的理解,王仲荦先生那代学人与您,主要的不同点在哪里呢?
丁福林:《东晋南朝的谢氏文学集团》丁福林:对于陈郡谢氏家族,我一直怀有崇敬之心,当年我做陈郡谢氏家族的研究,并撰写《东晋南朝的陈郡谢氏文学集团》一书,也正是基于这一点。这一家族在六朝时人才辈出,长盛不衰,在文学创作上形成了一个庞大的体系,取得了巨大的成就。更为可贵的是这一家族以素退为业的家风,家族中大多为风流自赏的恬退人物,政治上不求闻达,谢弘微可以说是其中的代表。谢弘微性行宽厚,不慕财利,嗣谢安之孙谢峻为子,对谢峻的僮仆财产却一概不肯继承,只接受了数千卷书籍。谢混被杀后,弘微为之经营财业,勤勤恳恳,一文钱、一尺帛的出入,账面上都记得清清楚楚。谢混妻子东乡君卒后,家中“遗产千万,园宅十余所,又会稽、吴兴、琅邪诸处太傅安、司空琰时事业,奴僮犹数百人”(《宋书·谢弘微传》),可他却一无所取。我认为,沈约在《宋书》中对谢弘微的这些行事作较为详细的记载,并在传末对他作出高度的评价,应该是值得称道和肯定的。因为在谢弘微的身上体现了某种精神,能抵御物欲的诱惑,行事谦退,严于自律,珍惜名声,淡泊名利,信守承诺。这种精神,应该就是中华民族一脉相承的优秀品质的体现。王先生在本书的“出版说明”中对谢微有较尖锐的批评,我以为应该是受到时代局限的缘故,是可以理解的。
的确如此,日本京都学派川胜义雄、谷川道雄等氏,就认为这是一种六朝时代特有的“贵族”精神。海内外六朝文史名家往往都是学有师承,您的老师段熙仲老先生是今文经的大家。他的经学造诣对日后您的文史研究有怎样的影响呢?
丁福林:我导师段先生对古代文史有着极深的研究,不过他最大的成就却是在经学上。在今文经学界,他堪称是大师级的人物。他有《春秋公羊学讲疏》(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2年)等专著多种,并点校了《水经注疏》(江苏古籍出版社,1989年)与《仪礼正义》(江苏古籍出版社,1993年)等。我在1979年进入南京师范大学就读他的硕士研究生时,已是八十三岁的高龄的他精神矍铄,思辨清晰,教学一丝不苟。段先生文史兼通,以治学严谨闻名,对我们极其严格。要求我们做学问一定要兼通文史,凡写文章必须要有根,也就是说必须要以史实为根据。记得入学以后给我们几个学生布置的第一个任务就是通读《史记》。这些对我今后的治学都有着重大的影响,使我在每引用一个材料时都要查证原始资料,找到出处。我之所以能够与《宋书》《南齐书》等史书的点校结缘,与段先生的严格教导是分不开的。
段熙仲授课讲稿《春秋公羊学讲疏》,其中第二、三编由丁福林整理段熙仲《春秋公羊学讲疏》手稿说起来段先生和我与中华书局都很有缘,中华书局主办的《文史》创刊号第一篇文章即刊载了先生的《礼经十论》,皇皇十多万字。而我的处女作《虞炎〈鲍集序〉的一处传写错误》也发表在《文史》上,虽然只是仅一千多字的补白文章,但却足以使当时初出南师校门的我感到荣耀。这次我能够参与中华书局《宋书》的修订,也可以说是一种缘分吧。只是段先生1987年就去世了,未能见到我的书出来,心里感到很遗憾。
从“文史结合”的角度看,史学大家王仲荦也有《西昆酬唱集注》(上海书店,2001年;中华书局,2007年),故而周一良挽王仲荦云:“章门高弟一生游心文与史;吾道先驱两部遗编晋到唐。”同样是先后两代《宋书》的点校者,您恰恰也是继承了章黄学派文史校雠、文史互证的优秀传统,令人感佩。
丁福林:谢谢!但您的奖掖实在愧不敢当。王先生是我最为敬重的前辈学者之一,我对他的仰慕,是从读他的《魏晋南北朝史》和《隋唐五代史》开始的,这次能够为他点校的《宋书》做一点修补工作,实在是一件十分荣幸的事情。
丁福林文史论文集两种